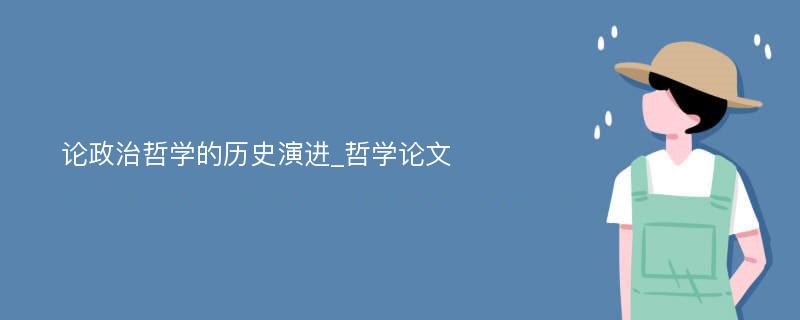
论政治哲学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名思义,政治哲学涉及政治和哲学,而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就是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涉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前现代——非政治的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现代——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后现代——哲学的去政治化和政治的去哲学化。
一、前现代:非政治的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
施特劳斯主张政治哲学“回到古典”,也就是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但是,前苏格拉底哲学恰好不是政治哲学,而是自然哲学,也就是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在自然界,而不在人和人类社会,他们探讨的是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和本原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问题。这里,哲学是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哲学家们虽然是生活在某个城邦(政治社会)里的公民,但他们在进行哲学思考时却超越了自身的政治社会视角,以一般人或人类社会的代言人的身份发言。非政治的哲学还表现为,哲学家们自以为是知识的代言人,而不是仅仅提出了某些个人意见,也就是说,非政治的哲学所构造的不是一个臆见的王国,而是一个知识的王国。当然,这个知识王国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也就是这样一批非政治化的哲学家。
与此相应,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城邦政治社会也不是建立在任何哲学理念之上,当时的政治是非哲学化的政治:政治建立在传统习俗、伦理和宗教基础之上,而不是从理性形而上学推论的结果。
这种非哲学化的政治生活持续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整个前苏格拉底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非哲学化的,也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总起来说,作为传统政治的基础,传统习俗、伦理和宗教是人们在漫长历史时期内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任何理性形而上学的论证。起初的伦理和宗教与后来的伦理和宗教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哲学成分和意识形态成分。
政治的非哲学化同时意味着哲学的非政治化。尤其在早期希腊的政治和哲学中,这一特征是非常突出的。在政治社会里,人们按照传统习俗、伦理和宗教生活,但哲学家们所思考的却不是政治社会,而是自然界。政治社会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则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哲学主要关注自然界只是早期希腊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哲学传统主要关注的是人事问题,印度的哲学传统主要关注的是人生问题,二者都不具有早期希腊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形态。而无论人事问题还是人生问题,都与政治相关。不过,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虽然并不存在一个自然哲学阶段,却存在一个哲学与政治相对分离的状态。
传说中国上古时期曾有过一次“绝地天通”的文化事件:“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尚书·周书·吕刑》、《国语·楚语下》)由此,天地两离、民神二分,地与天、民与神之间形成了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个世界的雏形,从而为哲学与政治的分离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哲学传统对于自然并无多大兴趣,而是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上古典籍《尚书·皋陶谟》借用大禹名义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孔氏传》解释说:“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民则归之。”这两句话简要勾勒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从哲学中开出政治、伦理乃至宗教。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不像希腊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其实不然。《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传上》),就划分了两个世界——“道”的世界与“器”的世界(“形而上”与“形而下”)。即使都是“形而上”的“道”,孔孟之“道”与老庄之“道”也截然不同。所谓儒家“入世”,表明以儒家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属于政治哲学,确切说是一种伦理化的政治哲学;所谓道家“出世”,表明以道家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属于自然哲学,确切说是一种审美化的自然哲学。因此,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而在于同为“两个世界”却景象各异。
印度人是生活在另外“两个世界”里的。在婆罗门教中,“梵”有二相,一是无形、不死、不动之相,二是有形、有死、变动之相;“梵”有真假。“幻”是梵我本体的幻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世界,产生生物界的生命,即个我或个体灵魂;二是客观世界,产生非生物界的物质现实。这两个方面同时朝向梵我本体幻归。《奥义书》将“梵”分为“上梵”(“无形”的梵)和“下梵”(“有形”的梵),与之相应,将“我”分为“遍我”(“主我”)和“个我”(“众我”),将知识分为“上知”和“下知”。前者是超验性的,无规定性、不可描述、不可思辨的;后者是经验性的,有规定性、可以描述、可以思辨的。《奥义书》对于梵的认知和表述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肯定的方式(“表诠”),一种是否定的方式(“遮诠”)。无相之梵的原理模式是“非如此,非如此”;有相之梵的原理模式是“一切即此”。
与中国哲学传统和印度哲学传统相对照,希腊哲学传统以自然哲学为开端,这反映了希腊文化的基本精神。希腊神话是希腊哲学的源头活水。希腊神话是指诸神故事——奥林匹斯诸神(以宙斯为万神之王)以及英雄传说,主要保存于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神谱》中。在希腊神话世界里,有人、有神还有英雄。人神之恋的结晶是英雄。所谓英雄亦即半人半神,他们拥有像神一样的智慧和力量,而又像人一样必死。希腊神话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他们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以“征服世界”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实现。这就是希腊神话的基本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造就了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辉煌。
出于“征服世界”的精神诉求,才有对于自然的求知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首先根源于人的一种形而上学本能——“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世界是奇异的,人生是奇异的;人们由于对此感到诧异、困惑、觉得自己无知才开始研究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次,哲学根源于一种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识。因此,在一个大家为生计而奔波的时代和国度,人们是不会考虑哲学的。只有在文化(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和地方,才会产生哲学。这是哲学发生的外部条件。总之,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求知是爱智的表现,只有获得闲暇的人们才能发生哲学的兴趣。故哲学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参见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1、5页)
因此,这种哲学起初不是政治哲学,而是自然哲学,希腊人首先关注自然界。他们从变化的万物中寻找不变的基质,叫做“本原”(“始基”),其原义是开始,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同上,第7页)这样,世界开始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生活世界和本体世界。前者是形而下的,是现象,是感觉的对象;后者是形而上的,是本质,是理知的对象。这样一种观念不仅支配了希腊哲学传统的始终,而且决定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一个关于泰勒斯的轶事谈道:“他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坑里,因此人们就嘲笑他说,当他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在介绍这个轶事后评论说:“人们嘲笑这样的事只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哲学家们不能使他们知道天上的事物,他们不知道哲学家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更高远的东西。”(黑格尔,1959年,第179页)这也就是哲学和政治的分离状态。极少数、极个别哲学家关注“天上的事物”——自然的奥秘,虽然他们与绝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坑”里——政治社会里。也可以说,生活世界就是政治世界,本体世界就是自然世界。自然哲学深入本体世界,一旦我们返回生活世界,就出现了政治哲学。
二、现代: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
现代性最早发端于苏格拉底,这是以苏格拉底的心灵转向为代表的,这一转向终结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形态。苏格拉底将哲学家们的兴趣从自然界引向了人和人类社会,引向了政治社会。
苏格拉底要求“心灵的转向”,即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在苏格拉底那里,首要的知识是关于“善”或“好”的知识,而不是任何自然知识。在苏格拉底“美德就是知识”这一著名命题中,所谓“美德”也就是衡量一切政治社会的价值标准。美德作为知识,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修行。换句话说,美德不是理论知识,可教可学,而是实践知识,不可教不可学。理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实践知识具有价值倾向。当美德被确认为知识的时候,就意味着政治和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实现了“哲学的政治化”,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政治的哲学化”。“哲学的政治化”表现为: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求知欲望变成了一种公共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了哲学的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政治的哲学化”表现为:政治从以传统的习俗、伦理和宗教为基础变成了以哲学意识形态为基础,实现了政治的知性化、理性化、哲学化。严格地说,这也就是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异化。
政治和哲学的结合亦即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异化,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柏拉图认为,个体事物是处在实在和不实在之间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对立。著名的“太阳的比喻”认为,太阳照亮了可见世界,即臆见世界,而善(好)则照亮了可知世界,即知识世界。著名的“洞穴的比喻”认为,人们在洞穴中由于没有太阳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事物的影子,不能看见事物本身;同样,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没有善(好)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理念的影子——事物,而不能看见理念本身。当柏拉图要求人们从臆见王国过渡到知识王国的时候,他就是在推动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异化。因为古老的政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臆见的王国,而现在他又明确要求这样的政治社会必须置于知识的支配之下,因此,柏拉图开创了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在《理想国》里,他提出了“哲学王”,认为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参见柏拉图,第214-215页)
亚里士多德划分了两种哲学:第一哲学即他的形而上学;此外是实践哲学,包括他的伦理学、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哲学的划分是与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相对应的。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生活归结于人的政治本性。(参见亚里士多德,1965年,第7-133页;2003年,第19页注1)亚里士多德所谓人类的政治本性以及城邦的政治属性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这里的政治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组成社会的、与经济文化相并列的领域;就其实质而言,政治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公共领域。家庭生活属于私人领域,城邦生活属于公共领域,亦即政治领域。希腊人只有政治的概念,没有社会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只会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而不会理解为“社会的动物”。这是因为希腊人对人的理解不像现代人将其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并认为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形成所谓社会关系;反之,希腊人将公共领域(城邦)和私人领域(家庭)划分开来,认为政治是人类公共生活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将人的活动领域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亦即政治领域:家庭以内的是私人领域,它由夫妇、父母子女、主奴三种关系构成,这些是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的关系;家庭以外亦即城邦属于公共政治领域,参与公共政治领域的是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不包括奴隶、妇女和外邦人。在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之间是自由人的平等关系。就其目的而言,城邦先于家庭,先于个人,应当是人生自然意旨的实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基本理解。
在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哲学确立了宗教对哲学和政治的统治地位。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王权两种权力的斗争,以及基督教哲学关于神学真理和哲学真理两种真理的争论,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奥古斯丁将现实世界划分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认为后者由按照肉欲生活的人组成,前者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前者是上帝的选民——基督徒的社会;后者是撒旦的信徒——异教徒的社会。安瑟尔谟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理解上帝。阿奎那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但是,在宗教神学的旗号下,出现了宗教哲学化、信仰理性化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加强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首先,宗教是经过哲学论证的,宗教化的哲学就是哲学化的宗教;其次,宗教对政治的统治同样是经过哲学论证的,而在哲学宗教化和宗教哲学化的背景下,这种统治就是哲学对政治的统治,宗教化的政治就是哲学化的政治。
近代以来,无论经验主义者诉诸感性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者诉诸理性思维,都将哲学指向了人,作为主体的人得到彰显,这与早期希腊哲学对自然界的关注截然不同。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说明了要改造自然就要认识自然,能认识自然就能改造自然;它显示了人类知识和人类力量(权力)的高度统一,一举颠覆了古典知识体系只求知、不实用的贵族自由精神,同时也摧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无谓感伤,奠定了现代知识体系实用化、功利化的大众世俗气质。在《新大西岛》里,培根设计了一个知识立国的“本色列岛”。其中的核心是“所罗门之宫”(或“六日大学”):“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培根,第28页)这就是“知识万能”的梦想。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是一个理性形而上学膨胀的时代,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我思”优先,这就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康德认为先验统觉(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并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黑格尔强调逻辑在先,构造了由绝对理念到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理性的绝对统治地位:“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黑格尔,2001年,第441页)
现代哲学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现代政治也完全受到这种哲学意识形态支配,这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表现。马克思同样是现代性的突出代表: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强调的是哲学对政治的干预作用。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正在世界化”是说哲学正在政治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则是说政治正在哲学化。此外,实用主义宣称“有用就是真理”。将真理归结于价值,与将知识归结于权力、将哲学归结于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后现代:哲学的去政治化和政治的去哲学化
“哲学去政治化”与“政治去哲学化”是对哲学与政治双重异化的扬弃,是当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当代政治哲学主流的基本主张。“哲学去政治化”就是哲学回归“纯粹哲学、纯粹思想、纯粹理论”的状态;“政治去哲学化”就是政治回归“前哲学、前意识形态”的状态。
当代政治哲学主流虽然是哲学和政治密切结合的产物,但它本身却表现了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倾向。也就是说,当代政治哲学主流通过对现行哲学和政治的反思提出了“哲学去政治化”和“政治去哲学化”的主张。
现代性的政治和哲学实质是党派性的。政治的党派性意味着现代政治表现为政党政治。现代政党政治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政见型政党,一是意识形态型政党。政见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政见是具有宽容性或包容性的政治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的政治意识;也可以说,政见是弱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强化的政见。因此,无论政见型政党还是意识形态型政党,其要害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某种哲学观念,它通常反映着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被想象为是以社会利益集团(如阶级、民族、国家等)的方式存在的。说这种存在方式是被想象的,不是说它是纯粹被虚构的,它显然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根源;而是说它是被意识形态所规训的,它的前提是现代性的人性假设,其典型表现是经济人假设(即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就是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经济人集团即理性人集团。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将政治理解为党派政治,认为政治是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要么一个利益集团支配其他利益集团,要么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利益和权力的均衡。这种博弈均衡既决定了个人和团体的战略选择,又决定了团体和社会的制度安排。
政治的现代性决定了哲学的现代性,政治的党派性决定了哲学的党派性。哲学的党派性意味着现代哲学表现为意识形态:虽然它依然采用理性论证的形式,但在实质上却是为某个或某些社会利益集团辩护的。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是进行社会动员,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这种社会目标又是某个或某些社会利益集团意志的表达。
政治的哲学化即意识形态化是否不可动摇?一种非哲学化即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是否可能?许多政治哲学家探讨了这一问题。
洛克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洛克所谓的私有财产不是狭义的,专指人们物质方面的财产,而是广义的,泛指人们身心和物质各方面的财产,实质是指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人领域。(参见洛克,第106页)洛克否决了政治权力干预私人领域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认为私人领域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一方面确立了私人领域的非政治性,另一方面确立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性。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就是确立社会对个人控制的边界:哪些方面个人要受到政治的约束,哪些方面个人不受政治的约束。康德把“理性的运用”区分为“公开的运用”和“私下的运用”:前者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后者则是指“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康德认为,理性的运用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由此,康德把自由相应地区分为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理性的公开运用”和言论自由应当是充分的,而“理性的私下运用”和行动自由则应当受到限制。一个人作为军官、纳税人或牧师等等,其“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自由应当是消极的;而一个人作为学者,其“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言论自由则应当是积极的。(参见康德,第22、24-25、30页)密尔指出:“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密尔,第1页)他更加明确地划分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界限,强调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
贡斯当和伯林提出了各有特点而又相互关联的两种自由的划分。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前者就是公共领域的自由,后者就是私人领域的自由。(参见贡斯当,第40页)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免于……”的自由,后者是“去做……”的自由。(参见伯林,第189页)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类似于贡斯当所谓的“现代人的自由”,而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则类似于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这里应该指出,在比较英国自由主义和法国自由主义的优劣时,有些学者片面强调“消极自由”或“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它们比“积极自由”或“古代人的自由”更优越,由此论证英国自由主义比法国自由主义更优越。其实,私人领域的自由和公共领域的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
韦伯提出“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与政治的主张。他认为,“世界的祛魅化”亦即世界的理性化和理智化表现为意义的消解,这是我们时代的命运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特征。由此,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的学术态度与政治态度,认为作为学者或政治家,我们必须承担我们时代的命运——“世界的祛魅化”,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消解各种价值倾向,同时又以一种责任伦理的态度来消解各种心志伦理。(参见《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价值中立的论述就是试图消解学术与政治的党派色彩。学术与政治的价值中立其实就是学术与政治的意识形态中立,就是学术的去政治化、政治的去哲学化。这里包含了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哲学的学术化方向,二是政治的公共化方向。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突破了其在《正义论》中的思维模式,以理性多元意识形态为背景,力图确立公共政治文化领域。这意味着当代政治理想具有一种最大的包容性:只要政治社会成员具有理性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他们就都能在一个共同的政治领域中共存。在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这种当代政治理想也有着鲜明的表现,特别是他描述的“元乌托邦”(即“最低限度的国家”),是一个可以将理性多元的乌托邦整合成一体的概念。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人的理念表明,政治从党派性到公共性的发展是当代政治社会发展的方向。公共性政治必然扬弃党派性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从而回归非哲学化的政治——这一过程也就是政治的去意识形态化。与此相应,哲学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哲学扬弃了政治的时候,也就是扬弃了自身的异化,也就是回归非政治化的哲学——这一过程也就是哲学的去意识形态化。施特劳斯提出的“回到古典”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哲学的去政治化”与“政治的去哲学化”的主张和倾向,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呢?这里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重估“哲学的党派性”?二是如何重估“政治的党派性”?
首先,哲学的党派性是列宁根据恩格斯相关论述提出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世界本原、思维和存在的第一性问题(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是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认识论问题);根据第一方面划分出哲学的基本派别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根据第二方面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哲学上的党派”,批评“哲学上的无头脑者”。(《列宁选集》第2卷,第227页)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战斗唯物主义”,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毫无疑问,强调哲学党派性是现代性的表征,但是,这个观点是列宁的观点。虽然恩格斯甚至马克思也有相关论述,但他们却具有更为根本和重要的见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在社会状态中”“通过实践方式”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324页)所谓“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哲学,它即使不是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新哲学,也是超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甚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依然强调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批判“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5页)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列宁关于哲学党派性的论断。
其次,政治的党派性同样是列宁根据恩格斯相关论述提出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同上,第170、172页)因此,扬弃这种异化,国家消亡,回归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局。“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同上,第174页)社会是公共性的领域,国家是阶级性的领域,既然国家是社会的异化,那么扬弃这种异化就意味着党派性政治的消解,公共性政治的回归。列宁只是注意到了恩格斯论述中的一个方面,只讲国家的阶级性,而不讲社会的公共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阐述,将国家归结于阶级统治的“强力”或“暴力”组织。(《列宁选集》第3卷,第114、130页)这一观点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在于: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消灭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消灭阶级的“半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同上,第128页)阶级和国家的消灭就意味着党派性政治的消解、公共性政治的回归。
总之,政治权力不仅不能干预私人领域,而且即使在公共领域中,就其本质而言,政治也不是党派性的,而是公共性的。这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它在当代国际和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社会中已初见端倪,其历史意义相当于第二次“政教分离”。第一次政教分离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宗教不再干预政治,意味着政治的去宗教化。这第二次“政教分离”是政治与哲学的分离:哲学不再干预政治,意味着政治的去哲学化、去意识形态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无论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还是当代政治哲学而言,“政治的去哲学化”与“哲学的去政治化”可能都是一个“乌托邦”,但它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党派性和政治党派性问题,却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总起来说,无论是“政治的去哲学化”还是“哲学的去政治化”,作为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对此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才能消亡,意识形态才能消亡,这也就是说用实践来解决理论问题。反过来说,在整个过渡时期里,由于阶级存在,政治的党派性、哲学的党派性是无法消灭的;但是,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公共政治领域的建设、哲学学术领域的建设则是必需的。
标签:哲学论文; 政治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哲学史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