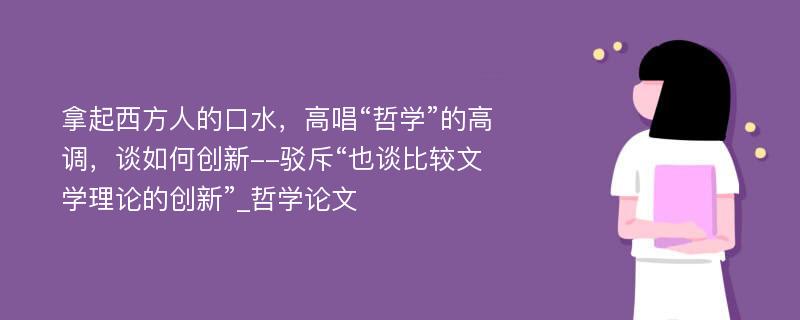
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学”之高调,谈何创新——驳《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人论文,比较文学论文,高调论文,也谈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185-04
拙著《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后,有相识不相识者陆续发表了七八篇评论,认同与赞扬者有之,商榷与批评者有之,对此我都表示感谢。但对于后者,除了感谢之外还要回应,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学术往往是在讨论和争鸣中推进的。近来读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弘先生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上的文章,题为《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读后》,张文对拙作提出了指责与批评,并由此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创新中所谓“更根本的问题”。张先生提出的“根本问题”从该文的三个标题上可一目了然。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第二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渗入?”我认为这些的确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为了讨论方便,拙文现在也想套用张文的这三个标题,并提出我的看法。
一、“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
我认为张先生的“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这个问题提出的方式本身,就很成“问题”。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即:你是要“中国特色”还是要“国际规范”?二者必居其一。这很能代表张先生的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回答的价值。但在张先生的大文中,还存在着更严重的理论上的悖谬。他不同意我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的“前言”中的说法,即:
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而人文科学必须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者的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
对此,张先生写道:
比较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跨民族跨国家当成本身的一个根本属性,把“世界文学”当成自己的一个理想。这是比较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它的研究对象,不是通常所说的国别文学,而是那些超出了民族、地域、国界的有限关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比较文学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
这段话似是而非。比较文学确实“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然而,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是矛盾的吗?显然,张文认为它们之间是矛盾的,因而才极力反对我提“中国特色”。而且,当张文拿这段话当成理论前提来批驳我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转换了上述我那段话的语境。我说“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的不同之一……”,是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相比而言,是在相对意义上的比较,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在绝对意义上,一切科学研究都有世界性,都可以、有时也必须超越国界;但在相对意义上,人文科学研究又带有民族性,从研究者自身来说,这种民族性集中表现为他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立场、民族文化教养。这种背景、立场、教养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它与研究者的关系如影随形。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正如严绍璗先生所说:“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是以何种语言文字从事学术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家都是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发育长大的,这一母体文化无疑应当成为比较文学家学术话语的基本背景,成为构成他的‘文化语境’的基本材料。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家来说,中国文化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基础,也是他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最深刻的根源……立足于这样的学术教养之上的中国比较文学家,才能真正地创造出他的学术天地来。”[1]我认为严先生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民族(中国)文化背景和立场的阐述十分正确,正合我意。这里强调的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家要从自己的文化教养中体现出独创性,形成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而张文却断言:“中国比较文学20年的事实表明,迄今为止,所有想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体现‘中国特色’的做法,都很难获得成功”。他举出的例子是“阐发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把这两个例子作为“中国特色”不成立的例证,并说“以上两个事例,王著也注意到了,并坚决表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在《新论》及有关文章中所反对的,是将“阐发研究”法和“跨文化研究”作为中国学派的独有特征,而决没有反对比较文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也没有反对“阐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本身。关于这一点,在一篇论文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应当明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是没有国界的,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也同样不能因国别的不同而有对象与方法的区别;比较文学学派的划分,也不能简单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依据。一切科学研究的不同因素是研究者的科研条件与环境,研究者的出发点、立足点、独特的思路、视角,以及由上述条件决定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由大量创新的成果所体现出的整体的研究实力、学风和整体的研究风格,这就形成了“学派”。“中国学派”也只能在这些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2]
很清楚,我在这里强调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特征强调“独特的创新的成果”对形成“中国学派”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中国学派”,而“中国学派”当然是“中国特色”的集中的、高度的体现。但张文却断言:“知识科学的根本特点是普适性和规范性,想在其中寻找专门属于中国的东西,并非靠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对比较文学是同样适用的。”然而,科学固然“无国界”,但科学家和研究者是有“国界”的,是有文化归属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与张先生相去甚远,简直是云泥之差。他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东西”是不合“国际规范”的东西,“国际规范”必须将“中国的东西”排斥在外。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无国界”。说穿了,这就是无条件抹杀“中国特色”。像这样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将“中国特色”和“国际规范”对立起来,只能得出这样错误的有害的结论。
这里我想请教张先生的是:就比较文学而言,所谓“国际规范”是谁制定的?谁来认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相对年轻的学科,有哪些是必须恪守的“国际规范”?张文本身似乎没有明确解答,但他接下来举的一个例子,却能够说明他所谓的“国际规范”究竟是什么。张先生举的例子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涉外文学”。张文认为:“经过法国学者的持续努力,也经过国内一些专家的热情介绍,形象学在近年来在比较文学领域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但王著对形象学表示不满”。由于“王著”对法国人的概念有所不满,于是张文就对“王著”更为“不满”。他详细地论述了法国人提出的“形象学”概念,认定“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形象学的有关界定明确清晰得多,而所谓‘涉外文学研究’反而模棱两可,含糊其事,不得要领”,说“王著对形象学的非难实际上都建立在误解乃至不解上”。显而易见,在这里,张文是把法国人的“形象学”的概念及其界定看作是“国际规范”了,于是对我提出的“涉外文学”这一概念格外看不顺眼,他在对“涉外文学”的评述中充满“不解乃至误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指责“涉外文学”的范围“无所不包”,“恰恰模糊了‘涉外文学研究’自己的界限”。然而事实上,涉外文学无论怎样“无所不包”,它还必须是“涉外文学”,因为它有自己明确的内涵——就是“涉外”;而张文指斥的“无所不包”,其实是它的外延。自诩有“扎实的哲学方法论素养”的张先生,怎么会连这么一点点逻辑学常识都不顾及了呢?或许在他看来,“王著”竟然敢“非难”这一“国际规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才站出来用激昂的言辞,拿他认定的“国际规范”对“王著”下了如上的判书。其实,我在《新论》中曾写道:“我提出‘涉外文学’这一概念,既受到了‘形象学’这一概念的启发,同时也是出于对‘形象学’这一概念的不满。”(第234页)换言之,对法国人的“形象学”我当然是有所吸收的,但老实说,我没有像张先生那样把它视为不可触动的“国际规范”。而“涉外文学”这一新的概念究竟可行否,还要经过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反复检验,张先生在“误解乃至不解”的基础上匆忙下的判书,恐怕不会有多大效用。
二、“方法论问题”
张文的第二部分是“方法论问题”。“哲学”的派头十足,“哲学”的气味似乎很浓。他开门见山地写道:
王著的整个学科新论体现着强烈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这点是值得嘉许的。王著也正确地领会到,方法论有哲学论和工具论两大层面。但遗憾的是,王著在哲学论意义上的方法论方面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见解,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这一指责令我困惑。这就好比是指责一部哲学著作为什么不发表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见解一样,令人啼笑皆非。我在《新论》中确实没有讲“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如果说这是“缺失”,那不是无意的“缺失”,而是有意的放弃。所谓“有意的放弃”,就是我认为不能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大谈哲学问题。我在《新论》的后记中说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书很容易流于什么‘全球化’、‘某某主义’、‘跨文化对话’之类的空泛话题,让人读了之后仍不明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怎样研究。”我在《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一书中又说:
近来出版的一些比较文学理论教材越写越厚,塞进了太多的相关学科的材料,成为哲学、美学和一般文化理论的大杂烩,反而淹没了比较文学理论自身,使比较文学理论趋于繁琐化、经院化,乃至玄学化,从而背离了“把问题讲清楚”这一理论表达的根本宗旨,也导致了比较文学理论脱离研究的实际,使理论失去了对研究实践的引导意义。[3](P21)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写作《新论》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免大唱“哲学”高调,而想踏踏实实地讲清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问题。而张文却刻意在《新论》中找他心目中的“哲学”及“哲学方法论”,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他找不到鱼就抱怨树上为什么无鱼。实际上,哲学之“鱼”在学术的餐桌上可能以种种形式存在,有人在这里吃不出鱼味儿,只能怪他感觉迟钝。大多数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著作都很少、也不必直接谈论抽象的“哲学”和标榜“哲学方法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哲学或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任何思想言论都有哲学基础,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正如任何人张口说话都会吸进和呼出空气一样。哲学方法论在具体的学科理论中,其理想的状态应该像水中之盐,融化于无形之中。可是,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我国学术深受西方各种哲学“主义”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只要“掌握”了某种哲学及“主义”,只要“解决”了“世界观”及“哲学方法论”问题,无论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会所向披靡,这就使得某些文章和书籍充满了大话、套话、空话,甚至玄言虚语,而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和具体的学术问题。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哲人之高论玄微、大言汗漫,往往可惊四筵而不能践一步,言其行之所不能而行其言之所不许。”[4](P436)这种“高论玄微、大言汗漫”的流弊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学术界——当然也包括比较文学界——仍然存在,甚至被有些人误认为是学术正规。况且,那些口口声声“哲学方法论”者,自己并没有什么“哲学方法论”,多数情况下是拿西方某某哲学家的话来装潢门面,不过是唬人罢了。这样一来,所谓的“学术研究”就成了从西方来的某某哲学、某某主义的注脚,其引以为骄傲的所谓“哲学”、所谓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拾西人之唾余。对此,我本人是唯恐避之不及。另一方面,我虽然不如张先生懂“哲学”,但我知道,所谓“哲学方法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只能从各门具体的学科研究实践中抽象出来。换言之,“哲学方法”是“一般”,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是“特殊”。我相信应该是先有“特殊”后有“一般”,而不相信先有“一般”后有“特殊”,正如先有实物后有概念一样。即使抽象概念也是从多个“特殊”中抽象出去的。这恐怕是哲学上的常识。哲学方法论一旦产生出来,对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是有指导作用的,但“哲学方法论”永远也不能取代具体学科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也不能取代比较文学方法论,不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问题,如果能,比较文学就可以不要自己的学科理论了。
正由于张文在上述问题上的认识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他对《新论》的指责也带有明显的“哲学偏执”倾向。例如,对《新论》中关于“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的分野,他指责道:“在文学关系上,王著把事实性的联系和精神性的联系相提并论,这同样是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两种基于不同哲学方法的观点杂凑在一起了。”然而,在隔了十几行字之后,他又指责道:“王著把通常说的影响研究拆分为二,一是‘传播研究’,以揭示事实联系为宗旨,属于实证考察;二是‘影响分析’,以探讨精神联系为目标,属于审美批评”。似这样一会儿指责《新论》将两者“相提并论”,一会儿又批评《新论》将两者“拆分为二”,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两者“拆分为二”是错误,将两者“相提并论”也是错误,这样露骨的自相矛盾,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张先生对《新论》中有关章节根本就没有读懂,或读懂了故意装作没有读懂。同时这也使我更加感到:带着这种“哲学偏执”来搞比较文学学术批评,实际已经很不“哲学”了。
再如,关于平行研究,他批评说:
……王著对究竟何为文学的精神现象及精神性的联系,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导致王著对平行研究也采取了一种极为简易的、甚至可谓轻率的态度。……对平行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可比性原理,也被化解为‘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这样一句颇有俏皮味的话,并断言这就是“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
诚然,在戴着“哲学”西洋镜的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这句话真是太不够“哲学”了,也就是“极为简易的、甚至可谓轻率”的了。但我却认为这句话很有哲学意味。记得钱钟书先生1986年3月在为《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的“寄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真理就是这样简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就应该这样简单明了——“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你可以把这鄙夷为“简易”,但我觉得这“简易”是直接击入事物本体的“简易”,与故作高深而实则浅陋者完全不同。
张文在讲了一通比较文学与哲学之关系的大道理(实际上是常识)之后,写道:
面对国外风起云涌的新知学说,如果搞不清它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基和脉络,又无法有所割舍,自然只有像大拼盘一般罗列在一起。同样的道理,不明白对方的哲学根基在哪里,又如何弄懂别人关于文学、比较、文本、历史、语言、主体、社会、自然等等的一大套见解,哪里谈得上消化、改造及超越?在哲学的贫困中,试问怎么超越?难道就是跟着感觉走,或者换个措辞、换个说法、换个拼盘的摆法?那样的话,样子或许是变新鲜了,实际上还是新瓶装的旧酒。
这段议论没有直指我的名字,但既然它是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出现的,也可以理解为对我的指责。我在《新论》的“前言”中说:“以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从西方引进某些理论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引进之后必须消化、必须改造,必须超越。”张先生似乎断定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拥有这个能力的自信,因为我一直认为这将是无数学者长期努力才能逐渐实现的。但是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已经和正在有意识地这么做。至于“消化”得怎样,“改造”得如何,“超越”了与否,留待众人(当然也包括张先生)和后人评说就是了。
在上面那段引文中,张先生力斥“哲学的贫困”,使人一时不由不对张先生这样的“哲学的富有”者肃然起敬,起了见贤思齐的念头。幸好张文大谈哲学的时候有一个“注释②”,提示读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可参拙文《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遵照他的指引,我找来大文拜读,指望他能给我们提供“哲学方法论”,但读罢却十分地失望!原来,他的中心意思是论证现代西方人提出的“主要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游戏原理’和‘家族相似性’”理论提出的“类似性(affinity)”范畴真正解决了的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他断言:有了这个范畴,“在比较文学的视野内将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同和异的问题,为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理念和方法”;声称“类似性的提出,既为比较文学的学理根据奠定了新的基石,也使比较研究的机制和性质呈现了不同于往日的面貌。最重要的一点是‘求同’的原则彻底地被颠覆了,重点放在了求异上”云云。张文张扬了半天的“比较文学哲学方法论”原来如此!真是匪夷所思。在他的大文中,连他所鄙夷的“换个措辞、换个说法、换个拼盘的摆法”都没有做到,不过是替西方某哲学叫卖罢了,而且叫卖时对国人的“标价”远远高于其货色的实际价值。“哲学的贫困”者如我,从张文中横竖上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所推崇的所谓西方人的“类似性”究竟有什么“全新”之处,对比较文学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它又如何能够一劳永逸似地解决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我只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求同”还是“求异”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实际和研究的宗旨,而不取决于某西方人如何主张。不过,我倒是从张先生推荐的这篇大文中得到了另外的收获,那就是由此而更坚定地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倘若这样的将西方某派哲学奉为圭臬并强加于国人,这样地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寻求“国际规范”,是永远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而这种自诩的“哲学的富有”,实际上是真正的“哲学的贫困”。
说到底,这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抱有这种念头,也就无怪张文对我附在理论阐释之后的“例文”也不以为然,说“这些专题研究的论文,因作者专业素养之故,集中在日本文学及东方文学,而与西方文学毫无关系,那么因此引出的结论是否全面周到,有无足够的涵盖度,也是需要反思的”。其实,稍微翻阅一下《新论》就会发现,这些以中日比较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为基本领域的论文,非但不是“与西方文学毫无关系”,反而是关系十分的密切。原因是中国文学、日本文学、非洲文学等,本来就与西方文学关系密切,谈东方比较文学而不涉及西方文学是不可能的。可惜张先生没有好好读这些文章,所以只能望“题”生义,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结果弄错了。这一点弄错了倒不要紧,关键是张文确信中日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足够的涵盖度”,认为由此而总结和提炼出来的理论有无普遍性还需要“反思”。我认为这要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作怪,要么是张先生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把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和具体的研究工作混为一谈”了。研究工作永远都是具体的,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正如张先生认为我不懂西方文学,张先生好像也不懂东方文学。但是,是否可以因张先生不懂东方文学,就断言他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看法没有“足够的涵盖度”呢?请问张先生:为什么您不怀疑研究西方文学得出的结论“有无足够的涵盖度”,那样起劲地推崇西方人的所谓“类似性”,而认定一个中国学人从东方文学中提炼出的结论就需要“反思”呢?您一方面是那样强调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另一方面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反倒对东西方文学研究的差异这样地看重呢?
三、“如何对待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渗入?”
关于这个问题,张文写道:“对于比较上述发展趋势的最大忧虑,是因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大量渗入有可能丧失比较文学学科的特征和个性,由此主张比较文学壁垒高筑,把种种新论和文化理论拒之门外。这其实就是王著的立场。我们看到,书中明确反对把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淹没在一般的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中,全书根本没有探讨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研究的内容。”然而,这段话再次表明张先生没有认真地读过《新论》,说“全书根本没有探讨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研究的内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只要翻阅过《新论》的人都会知道,我不同意把“跨学科研究”看成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是因为从学科范畴上说,“比较文学”不能囊括和涵盖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但是同时,我主张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我称之为“超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四种“基本方法”之一,并在《方法论》一章中专列一节加以论述。那一章讲的正是“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研究的内容”。因此,张文在第三节对我批评可谓无的放矢,况且他表示“只简单说几句”,我也不必多费口舌。
这在张文的第三节的最后,也是全文的结尾处,张先生写道:“理论创新也离不开扎实的方法论(包括哲学论和工具论)素养,而不能单凭感觉、聪慧与勇气。在这方面,我愿意同王向远先生和比较文学界的同仁们共勉。”谢谢张先生邀我“共勉”,但我不敢当。因为我自知在“感觉、聪慧与勇气”方面,实在不能望先生之项背,岂敢“单凭”?!
总而言之,我不赞同张文的看法,而是认为——
一,西方的比较文学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比较文学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与“国际规范”(如果它存在的话)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应是对立的统一;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也必须参与“国际规范”的形成过程。
二,单靠贩运西人时髦的哲学理论,拾西人之唾余,不是理论“创新”。如果说那是“创新”,也是人家的“创新”,不能代替中国人自己的创新;不能将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某些尚待实践检验的理论强加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固然要借鉴西方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自身丰富的研究实践中加以提炼和总结。
三,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不能拿所谓“哲学方法论”取代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不能拿西方哲学或文化理论充塞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那样的话,任凭你把文章写得多么多、书写得多么厚,仍掩饰不了“失语”的症状。大唱“哲学”高调,除了高自标置、故作深沉之外,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没有多大意义。
四,学术批评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工作,批评者应该与人为善,尊重原意,细读文本,谨慎从事,力求公正;学术批评不可逞纵一己之好恶,不可“凭感觉、聪慧与勇气”甚至偏见而自以为是、据“高”临下、盛气凌人、断章取义、妄断是非;不能一见到与西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述,就拿自己心目中的所谓“国际规范”(实际上是西方“规范”)严加拷问,俨然是“国际规范”的执行法官。这不但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更是一个学风问题、学养问题。用批评的或鼓励的方法,支持和呵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尝试,应该成为有学术良知的比较文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这些,我自知做得还很不够,不敢邀人“共勉”,但愿以此“自勉”。
收稿日期:2004-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