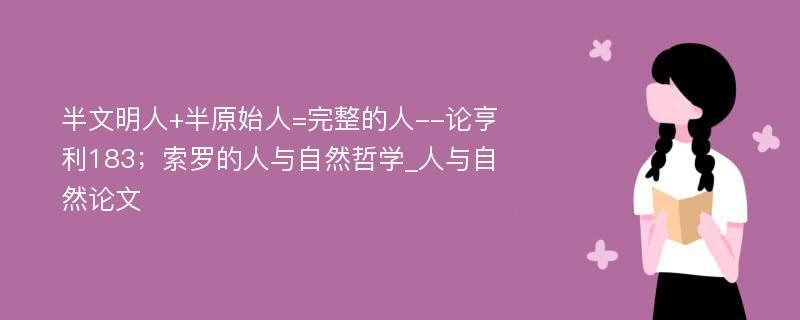
半个文明人+半个原始人=一个完整的人——论亨利#183;索洛有关人与自然的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个论文,的人论文,亨利论文,文明人论文,原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大卫·索洛(Henry David Thoreau)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美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19世纪中叶,他与爱默生(Emerson)一起,扛起了先验主义的思想大旗,创立了美国式浪漫主义哲学观,其影响不仅贯穿于美国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作品,而且对20世纪中叶的颓废派和嬉皮士文化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索洛重要,所以国内外研究索洛的作品、著作已相当可观。不过,在笔者看来,在对索洛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其“自我依赖”和“文明不服从”的思想已有相当深透的分析,但对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哲学观点却显得把握不足。依笔者之见,恰恰是索洛在后者上的观点才决定了他在前者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因此,探讨索洛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观点,而且还将帮助我们全面地把握索洛的整体思想发展。
人的一半:荒野 自然 想象 精神
众所周知,美国先验主义的基本命题是:物质世界以外,存在着一个比它层次更高的真实--精神世界;低层次的物质现实和高层次的精神真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自然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折射、反映出精神真实;人的最高追求不是物质的占有,而是精神的升华。
基于这个基本命题,爱默生在1836年曾宣称:“大自然是精神的象征……整个世界都是象征性的”①。也是在这个基本命题的意义上,索洛在1842年告诫人们:“我们千万别低估了事实的价值,它们终有一日会显现出精神真实的。”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爱默生、索洛所说的精神,指的都是上帝的精神--上帝在创造自然世界时赋予它的精神。根据逻辑推论,我们可以把索洛和爱默生的观点表述如下:大自然只是表象,上帝的精神法则才是本质;上帝的精神是借助大自然的物质现象显现展示出来的。
既然大自然世界与上帝精神之间存在着这种内在联系,人怎样才能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到从“表象”走向“真实”的目的呢?
先验主义的解答是这样的。它认为,人的物理存在使其像其他自然物质一样,深深地根植于物质世界里。但先验主义强调指出,人除了物质因素以外,还有精神因素,即他的灵魂。人的灵魂可以帮助他超越生理方面的局限;借助灵魂的精神力量,人可以透过自然物质表象寻找到上帝的存在,从而达到使自己与上帝精神“衔接”起来的目的。一旦人超越自己的生理局限,与圣神力量“沟通关系”,那么,他就会发现,接近真实的道路也就平坦无阻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爱默生和索洛的先验主义与先前的宗教哲学观存在着两大不同。第一,它与自然神思想不同。我们知道,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的理性主义认为,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其井然有序的运动和完美无缺的安排,人们可以借助上帝赋予人类的理念来加以理解和认识,并进而通过它领悟上帝的精神意志。先验主义在认识目的上与它相同,即把大自然看作上帝精神的存在之源,但在通向这一源泉的途径、手段上,先验主义不相信理性力量,而认为人类的想像力、直觉和感悟力才是接近上帝精神真实的唯一途径。第二,它与加尔文教不同。加尔文教的核心是它的“原罪说”。因为人生来有罪,如果让他在大自然放任自由的话,他就会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直至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此,人类有必要组建社会,以便用严格的清规戒律约束、控制人们的言行。先验主义与此相反,它既不认为大自然内在本身存在着恶的势力,也不认为人是带着沉重的罪恶枷锁来到这个世上的。在索洛等先验主义者们看来,人性生来是善的,大自然内潜藏着无数能使精神升华的美德。因此,当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溶于一体时,人就能扬弃其身上的不纯部分,达到道德完善、精神超脱的境地。
基于这种对人、对大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思想,当索洛注意到19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逐步呈现出商品社会气息、人们日益崇尚物质享受时,他开始感到忐忑不安,心神不宁,总觉得技术文明力量及其不断追求发展的动力,正在慢慢地侵蚀人的个性、人的独立和人的完整。在索洛看来,这些由技术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力量--破坏人性、破坏个性发展的力量,和随之而来的崇尚精神,如同侵蚀人们肌体的毒菌一样在伤害着美国社会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③。为了避免人性被技术文明泯灭,索洛提出了“走向自然”的观点,并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这一观点。
索洛所说的大自然,常常是荒野旷地的同名词。对他来说,荒野之值得赞颂,首先是因为它是发现自我的最佳场所。前面提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开始腾飞,商业价值观逐渐替代建国初期的农业社会价值观。人们对物质商品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他们对大自然的一味索取。结果大自然横遭破坏,人们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城市。索洛认为,在这种“人造”生活环境里,人是难于认识、发现自己的,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被这种“人造”生活环境所制约了。要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发现“原先的我”,索洛提倡人类走向自然、回归自然,因为只有在处于原始状态的大自然环境下,人们才可能真正感悟到自己的存在,才可能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本质。
索洛是这么劝人,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1841年,年仅23年的他,只身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野莱为食,荒地为床,终日与树林和溪流作伴话语。在给友人的信中,索洛曾这样描述自己:“在荒野中生活,我变得日益野蛮和粗犷。”④有趣的是,索洛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无半点后悔,相反,他感到格外的兴奋和由衷的高兴。他自由自在地在康考德(Concord)荒野里闲逛、徜徉,尽情地享受着那里每一颗校郏ㄝ的芬芳、每一寸土地的泥土芳香。
然而,投身大自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身居自然世界是为了使人们无忧无虑、不受干扰地思索和感受,从而让人们的各种思绪、想法和情结畅通自然地流露出来,并进而在这一流露过程中找到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荒野中,必须注意与大自然的“对话交流”,因为只有同大自然“对”上了“话”,人们才可能与存在于自然物质中的精神真实沟通起来。显然,这里说的“对话”,不是人类间的语言交流,而是人与自然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互感悟。这种感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身处远离尘嚣的荒野之地时,他们将有能力排除一切尘世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内心体验活动中去。这种感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荒野给我们以精神上的解脱”⑤,从而帮助我们发现真实的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洛在只身进入当时仍是一片不毛之地的缅因州和加拿大时宣称,“除非我发现那两大荒野,不然,我将永远处于迷惘状态。”⑥
荒野在索洛的心目中,不只是为人提供了认识、发现自我的良好环境,而且还是人们开发心智、锻炼意志、发展才能的巨大源泉。在1851年的一次康考德学术演讲会上,索洛这样评论到大自然的力量:“森林和荒野里有各种各样使人兴奋的东西和令人心寒的叫声。它们能帮助人们振奋精神,增加胆略”。因为荒野是“生命的最基本原始材料”,所以,它是人类活力、灵感和力量的最根本源泉⑦。1856年,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索洛又一次高度赞扬了荒野的作用:“荒野对人的心智发展有极高价值,我无时无处不感受到它对我精神的刺激作用”⑧。1857年,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只有在荒野里,我的神经才得以安宁,我的感觉和思维才处于最佳状态。”⑨显然,对索洛来说,人类的伟大取决于其对自然界中原始力量的汲取;人类的感悟一旦与荒野中的精神沟通上,他的激情、思绪、灵感和想像便会自然而然地喷涌而出。此时,人类即可轻而易举地发现自己、升华自己。
因为荒野给人创造了一个任凭思绪、感受和激情驰骋的境地,人们的才智也才可能在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鉴于这一原因,索洛极力鼓励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到荒野中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忘却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清规戒律,忘却人世间的各种羁绊,忘却社会中的繁琐事务,无拘无束地与树林、溪流和鸟声一起思索、一起想像,发现大自然中的真、善、美,并进而使自己与这种真、善、美溶为一体。完成了这个过程,人们不仅能创造出最佳的作品,更主要的是,他将真正懂得生命的内涵,真正懂得如何生活才能体现出生命的全部意义⑩。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索洛来说,精神追求胜于物质享受。他认为,文明社会过于强调物质享受,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日益贫乏。要纠正这一偏差,人只有到未受文明“污染”的大自然中去。荒野是孕育人们精神财富的源泉;在那里,人能发现自己,并为自己健康、全面的成长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人的另一半:素养 文明 赏美 高雅
索洛对荒野的赞颂并不是无节制、无条件的。事实上,西方文明中那种把荒野看成人类生存威胁的思想仍存在于他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上。
根据《圣经》,人类因为亚当经不起夏娃的诱惑,偷吃“禁果”,所以被赶出欢乐、无忧无虑的伊甸园,来到这个黑暗、可怖的人间,接受上帝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间犹如炼狱,处处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命的成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自然荒野、崇山峻岭和冰川河流。人类要避免被自然荒野力量吞噬,就必须使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并降服它,控制它,把自己从黑暗中转向光明。
根据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观点,大自然的存在是为人类提供资源服务的。人类利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去了解、认识和利用这个自然界。在这个思维框架下,人处于主导、制约的地位,大自然处于被动、受摆布的地位。人类认识、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便构成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无论从圣经宗教意义上讲,还是从启蒙主义的理性意义上讲,这两种代表西方文明主骨架的观点都把人与物对立起来,都把前者的存在与发展(或者解救)建立在对后者的控制和驾驭上。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之一,也是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因其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作赘述。
与本文有关的是,索洛在近似狂热地追寻大自然净化人性魅力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仍受着上述两种文明观的影响。当他1846年离开康考德前往更荒芜的缅因后,他在那里目睹了一片更加原始、更加峻险的大荒野。根据他在康考德的笔录,他本因陶醉在这未经文明手笔“涂染”的大自然才是。然而,叫人诧异的是,索洛从那荒野里出来后,与其说多了一层对荒野的挚爱,不如说是多了一份对文明的尊敬。且读读他对缅因荒野的描述和他即时即刻的感受。当他爬上卡塔定山巅时,索洛这样写道:“这里的荒野景色给人一种野蛮、可怖的感觉”,处在这种境地中,人们脑中产生的不是一种欢喜若狂的感觉,而是一种“他人难以想像的孤独感”。人在这种野蛮环境下,不仅没有净化的感觉,反而似有被剥夺思考和超脱能力的感受。“自然荒野如此无情,把他孤零零地抛在一边,使他感悟神灵的能力失却了一半。荒野不像平原那样令人可亲、可爱了”(11)。
这种把荒野描述成可怕的异己力量的观点,显然与前面所述他对自然荒野的赞赏是迥然不同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索洛深信自然荒野中存在着某种净化人类精神的神圣力量,但与此同时,索洛又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悟到,并非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同等的美化、净化力量,荒野中也并非所有一切都是真、善、美的象征。那么,人们该怎样区别自然荒野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呢?
这里,从本质上讲,涉及到索洛对文明的看法,以及他对文明人与野荒人的比较。
索洛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年轻时,索洛曾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善的东西与野蛮人和自然荒野联系在一起。譬如,在《野蛮与文明》一文中,索洛便争辩道,印第安人之所以优越于白种人,就在于他们与大自然的不间断接触,从中汲取有益于道德发展的养料。以后,在他的日志中,他又饱醮笔墨赞扬野蛮人,说他们“在自然荒野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那里的真正居民,而文明人去那儿只是作一次客而已”(12)。然而,随着索洛与自然荒野的不断接触,尤其是去了一片荒芜的缅因州后,他开始对自己先前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在那里,他发现“印第安人阴险可恶,懒散无神”。他们“粗鲁地对待自然,随意地糟踏原野”,一点也不像“自然的孩子”(13)。到了1851年,索洛基本上彻底摒弃了他对野蛮人与荒野的无保留崇敬。荒野里,玫瑰花“在盛开,但却无人欣赏,因为野蛮人只顾到处漫游闲逛”(14)。
索洛的这些言论表明,他的观点已从一味颂扬野蛮人和荒野到有条件地称颂他(它)们。自然荒野中有无穷的魅力,这一点洛索一点也不否定;但存在于荒野中的美,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到、捕捉到。索洛对印第安人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就持怀疑态度,而只有像他那样既有相当文化修养又善于体悟真、善、美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是,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一定的文明修养、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感悟天赋。因此,索洛这里实际上已明确提出了他的新观点:只有文明人才具有真正体悟自然魅力的能力。其道理很简单,美是客观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但当它没有被主观意识到、没有被具有欣赏能力的人发现时,这种美就很难体现其真正的内在价值。这种美学观是否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对索洛来说,人、自然、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关系。
用这种观点来观照索洛的思路,我们便可以较顺利地抓住其本质之处。在索洛看来,他同时代的文明人对他所关注的人生大问题--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漠不关心。他们虽有超越低层次物质需求的能力,但因为被商品拜金主义所迷惑,他们的双眼只顾盯在聚积物质财富上,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发展,更不会考虑怎样从荒野中汲取有益于人们心智和道德发展的精神力量。这样,在索洛面前,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野蛮人太野,心智不发达,因而无能力欣赏、发掘荒野中的美。另一方面,文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尽管有能力,但不愿去考虑自己的精神成长。为此,索洛对野蛮人和文明人各打五十大板,说两者“各有优劣,半斤八两”(15)。
那么,原野中美的发掘是不是就此没有希望了呢?索洛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把自然原野中的刚毅、顽强和硬朗与文明中的心智、智慧和悟性和谐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各自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的目的。换句话说,人们必须借助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去寻觅、开发自然荒野中的真、善、美部分,在两者之间寻找它们的契合处,使两者得到完美的统一。
在这两者的统一过程中,索洛特别强调“中庸之道”。荒野中先天存在着粗旷刚强精神,先天存在着一种催人进发、顽强拚搏的活力。但是,这种精神和力量需要控制,万万不可让它们毫无羁绊、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如果它们占主导地位的话,这个世界将是一个混浊、紊乱的世界,安宁和秩序都将与它无缘。
同样的道理,人类创造的文明也积累了自身的智慧,产生了摄人魂魄的艺术,发明了令人惊叹的技术。但是,这种科学技术创造力和典雅精致的艺术既需要一定的限制,又必须不停地增添新的养料。如果让技术创造力无限制地发展,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将逐渐消失,直至最终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结纽带。一旦原始自然环境消失殆尽,人们将完全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下。这样,人的自然属性也就会因失去根基而难以培育,更不要说保护维持了。其结果,是人的道德力量的萎缩和人的性格的扭曲。
显而易见,这里的关键是在荒野和文明之间建立某种平衡,用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去弥补荒野中的糟粕部分,用荒野中的美好部分来抵消文明中的欠缺部分。因为两者间存在着这种互补性,索洛把它们的互相平衡比作犹如白天和夜晚、夏天和冬天一样互相不可或缺。(16)
很清楚,索洛心目中的完整的人,是一个对文明和自然之优秀美好成分兼收并蓄的人。他常以自己为例,向人们说明这样做既有可能,也很现实。譬如,在有关他华尔登湖边的生活日志中,他曾这样写道,我的一半呼唤着我“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另一半催促我去过原始的、野蛮的草丛生活。”他自称两者都喜欢,都热爱,但决不走极端,绝不顾此失彼。在这个基础上,索洛归纳说,“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往往是野蛮人结束其野蛮生活的时刻”(17),即人类和时代处于野性与文明交替的时刻。他进而以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为例进一步阐述说,欧洲文明发展过于迅速,消灭了荒野,从而慢慢地走向堕落,失却其早先的冲动劲和青春活力。美国的文明起源于一片荒野,19世纪中叶仍在向西部荒野拓殖,所以,直至那时,美国文明仍充满朝气,蓬勃向上。但是,由于美国文明起始于荒芜不毛之地,它的文化便显得粗糙有余,高雅不足。为此,美国有必要汲取欧洲文明中的精致、典雅部分来弥补、消除自己过于野性的部分。当美国文化兼得本土的原野沃土和欧洲的高雅文化之美好优秀部分时,它就能使活力和雅致和谐地结合成一体,使之永葆生机,永放光彩(18)。
为使这两者始终处于和谐的地位,索洛建议人们与两者保持不间断的接触。就他本人而言,他一方面不断地去原野荒地中去寻找精神启迪,丰富自己的感受,并不失时机地让自己身上的野性本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泄。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永久性地生活在荒野中让自己“野蛮化”,而是适时地走回文明社会,吸收文明精华中的健康养分来充实、提高自己(19)。索洛相信,通过这种有选择的接触联系,人就能取得较平衡的发展,不仅能发现自己,而且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完整的人。用一个通俗的比喻,索洛要人们脚踏两只船--一端是文明船,另一端是野蛮船,脚心用力平衡,不可偏颇一边,不然,他就会掉下河去。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别说半个人,恐怕连四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希望。可见,要做索洛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人们必须学会平衡地兼顾文明和荒野中的优秀美好部分,摒弃它们的劣质部分。能把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的人,就有可能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修养、自觉从自然荒野中汲取精神力量、个性健全发展、人格完全独立、视精神追求高于物质追求、最终获得道德自由的人。
几点小结
1.索洛提出的半个文明人+半个野蛮人=一个完整的人的模式很具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了19世纪初盛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又不囿于这种思潮的局限。在指出科学技术文明的破坏作用时,他没有完全否定文明的积极作用。同样的道理,在赞美自然荒野对人格塑造不可或缺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成分。索洛追求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平衡,以一方之长补另一方之短。
2.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起至索洛时代,无论从理性角度看,还是从宗教眼光看,它的主流文化倾向于把荒野看作恶的象征,看作征服的对象,看作阻碍文明进步的绊脚石。索洛是第一个(与爱默生同时)比较完整地向这种主流文化观提出挑战的人。他赋于自然荒野以真、善、美的秉性,劝告人们敬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生生相息,“和平共处”。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来看,索洛的观点很具积极意义。
3.索洛当时在技术文明铺天盖地袭来之时隐居深山似有逃避社会现实之嫌。但依笔者看来,这其实不失为一种与世争斗、与人争辩的方式。要知道,索洛的观点在当时是很孤立的,要他单枪匹马地与主流文化作战是不够现实的。以笔者之见,索洛实际上是在用他的个人经历向世人表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他进入荒野,又回到文明社会,这实际上是在向世人揭示:人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使人通向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世界。
4.索洛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农业社会逐渐被工业社会替代的时代。他对荒芜土地日益被工业文明侵占、蹂躏极为忧虑,对美国民众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状况极为不安,担心美国民族就此堕落下去。为此,他提出了走进自然、回归自然的主张。走进自然和回归自然本身并非目的,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才是它们的目的所在。我们对索洛所说的精神生活之内涵不一定赞同,对他所采取的或建议的方式也不一定完全接受,但他注重人的精神富足,要求人们别做物质商品奴隶的观点则是可以同意的。
5.索洛的观点在他那时是一种“超前意识”,所以难以被同时代人所接受。何况,他的观点和主张,浪漫色彩多于实际现实,因而长期以来未受人注意。本世纪初,尤其是60年代末,他的许多观点才开始被人“重新发现”,并为人接受。用生态学观点来反观他的主张,我们应该承认,其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进步、积极的因素。
注释
①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默生作品集》,斯坦福图书馆,1883年,第31、38页。
②④⑤⑦⑧(11)(13)(16)(17)(19)亨利·索洛:《亨利·索洛作品集》,河边版本,1893年,第9、1、223、9、275-277、489、82、85、94-95、3、105、258、9、210-211页。
③瑞金纳尔德·L·库克:《通往沃尔登湖的路》,波士顿,1949年,第99-100页。
⑥⑨⑩(14)(15)(18)布雷德福德·托雷和弗朗西斯·爱伦编:《亨利·索洛日志》,14卷,波士顿,1906年,第2、46、9、519、166、301、147页
(12)F·B·桑鲍恩:《亨利·索洛生平》,波士顿,1917年,第180-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