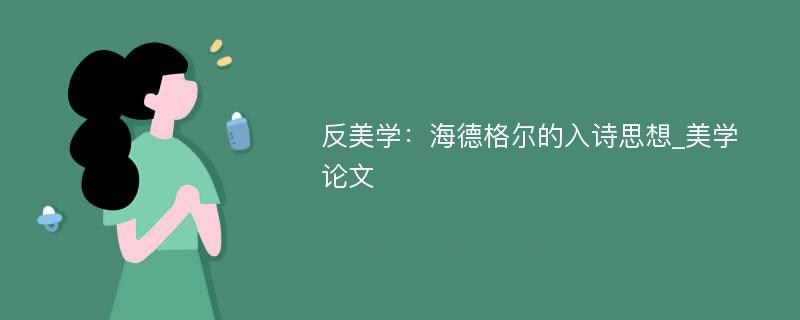
反美学:海德格尔的入诗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界有不少人将海德格尔有关诗与艺术的思考归入“美学”,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海氏这方面的思考恰恰是反美学的。科克曼曾在《海德格尔论艺术和艺术作品》中指出:“海德格尔曾详细解释过他为何坚信任何试图从一种美的理论和艺术理论来理解艺术的本质都是不合适的,甚至这对美本身的思考也是不可能的,美本身与存在和真有关。”〔1〕
迄今为止,“诗”(艺术)的问题一直被看成一个美学问题。诗被预设为一种感性的审美活动而与理性活动相对应,诗要么被看成诗人创作的主体行为,要么被看成读者阅读的主体行为。作为主体行为的结果,诗是由人任意摆布的东西,其目的是供人娱乐消遣,因此,诗不过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或文化饰物,在功利化的技术时代无足轻重。
奇怪的是,就在人们轻视诗,忽略诗的时候,海德格尔却将自己的思想坚决地转向诗,并强调说:思之转向诗并不是要“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作出什么贡献,而是思之必需。”〔2〕
作为“思之必需”,入诗之思先展示为这样三个方面:1、 在一个误解“诗”的时代,重审诗的意义至关重要,因为在海氏看来,诗的本质并不是主体的审美行为,而是存在敞开自身的方式,是“真”确立自身的方式,因而是人生存得以可能的基础。就此而言,诗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生存之必需。2、 诗所敞开的存在之真以及暗含其中的生存方式与技术时代的真理及生存方式截然不同。在海氏看来,后者在根本上危及人的本真生存——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而拯救之道是重新思考诗的本质并坚决地进入诗意地栖居。3、 由于诗是存在敞开自己的了然样式,所以存在之思当以诗为自己思的起点和归宿,这是摆脱形而上学存在者之思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海氏的入诗之思在其根本上就不是“美学的”,而是“存在论的”。
关于“本质”,海氏的见解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通常我们认为一事物的“本质”是从某一类事物中归纳出来的共性,因此,诗的本质原则上应该从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诗中归纳出来。但海氏问道:我们凭什么说这是诗那不是诗呢?我们凭什么能先行将所谓的“诗”从各种文本中选出来并加以归类呢?如果没有这个先行的筛选归类过程,我们又如何归纳出诗的共性呢?为此,此一归类要得以可能,就先得有一个区别诗与非诗的尺度,这一尺度是先于归纳之共性的。
作为尺度,诗的本质是一种要求,一道命令。在海氏看来,这种要求和命令绝不可能是任何主观意愿而只能是“天命”(神圣旨意)。海氏的“天命”虽有神秘色彩,但我更愿将其从存在论角度来加以理解,亦即将它理解成一种存在论要求或生存对人的要求,将它理解成海氏反人本主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表达。
海氏认为荷尔德林是受天命所托而向世人昭示诗之天命的诗人之诗人。海氏是这样说的:“荷尔德林之被选中,并非其作品道出了诗的共同本质,而仅在于,他受诗人使命的驱遣,直接道出了诗的本质。”〔3〕这种“本质”恰恰在其本质上不是既有的所谓诗作的共性, 因为既有的所谓诗作完全有可能是非诗性的,它们之被称为诗只是出于习惯。
由荷尔德林道出的诗的本质何在?或是说海氏从荷尔德林的言说中看到的诗之本质何在?综合海氏的零散述说,我们得到这样三大要点:
1、“诗以语词确立存在”。〔4〕
2、“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5〕
3、“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6〕
下面我将分别予以解说。
一、“诗以语词确立存在。”
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如此写道:
“首先,了然的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7〕
语言是怎么回事?语言的本质何在?海德格尔批判了俗常的语言观,后者将语言看作一套词汇和句法规则所构成的符号系统,一种摆在那里,被人用来传达信息的工具。海氏指出:“如此理解到的语言不过是语言的入口而已。”〔8〕还不是语言的本质。 语言的本质似乎刚好与我们通常看到的现象相反,语言的本质是“语言言说”而非人言说。
海氏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作为显示的言说,语言的显示性并不是基于任何符号。相反,所有的符号来自于一种显示关系,在此领域中,并为了显示的目的,这些符号才成为符号。”〔9〕“作为显示”的言说,这一规定乃是海氏语言观的核心。在海氏那里,“存在”与“显示”(无蔽)是一回事。“作为显示”的言说,在根本上是挑明“言说”之所属,即“谁说”的问题。“作为显示”的言说强调的是:1、 “言说”即(作为——as)“显示”;2、“言说”是“显示”的言说。 因此,语言言说,显示的言说,存在的言说在根本上是一回事,其关键在于它区别于“人言说”。在海氏看来,前者是“本质性的”,后者是“派生性的”;后者之可能是由于前者已发生。
海氏的语言观十分复杂,在此我只关注它与其反美学的诗之思之间的关系。十分显然的是,海氏的语言本质观之不同于传统语言观,主要是它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对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看法。后者认为人说语言或人使用语言是了然大白的事实,而海氏则认为是语言言说或语言使用人来传达它的言说。经过了二十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关于语言言说先于人言说,语言言说制约人言说的看法已不难理解。
语言用人,这一看法使海德格尔的入诗之思与美学视野中的诗学大异其趣。事实上,由于诗在其本质上的语言性,任何诗学都免不了以一定的语言观为基础。传统诗学之所以信心十足地认为诗可以用来言志或摹仿,消遣或审美,就在于它相信语言是供人使用的工具,人说语言。海氏则认为,这种诗学观虽然从经验现象上看也不错,但却不是诗的本质,诗的本质当从语言的本质上来理解,语言的本质是语言言说,是语言使用人。作为语言言说的诗在其根本上不是用来摹仿或表现,消遣或审美的工具,而是存在以语言的方式显出自身的方式,是存在之真的发生的方式。诗是存在发生的事件,在此事件中,人被诗(语言)所使用(被诗召唤来写诗和读诗)。海氏称此为“强行占用”,“强行占用,需要并使用人的强行占用让言说成为言说。”〔10〕
人(诗人和读者)作为被“强行占用”者就不能随心所欲使用语言,而只能虔心聆听语言言说(Say),跟着此言说言说(say)。诗作为跟着言说(Say)而方说(say)的本真语言事件在其本质上不只是人的主体行为,而是“天地人神”之“四重体”的游戏。
在《诗中的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具体分析了诗人特拉克的诗歌言说。在海氏看来,特拉克所有优秀的诗作中都回响着一个未曾明言但却贯穿始终的声音:离去。“离去”作为特拉克诗作中隐晦不明但却支配着特拉克诗歌歌唱的声音,显然不能归结为特拉克这个人的主体的声音,而是特拉克作为伟大的诗人所听到的声音。海氏认为此声音是特拉克所处的时代之天命的言说(Say)。此言说(Say)说的是人正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如果不离开这个可怕的金属与功利的世界,人将毁灭;如果不离开人已异化的金属性躯壳,人不能复活。离开世界之夜而走向世界之晨是这一代人最隐秘的天命,这一代是离去的一代。作为伟大的诗人,特拉克听到这一天命(神圣命令),并以自己的歌唱向世人昭示这一天命。正是在聆听应和这一天命的言说中,特拉克的诗成了真正的诗。海德格尔是这样说的:
“诗人特拉克的作品意味着:跟着说,重唱离去之精神的音乐,此音乐已经对这位诗人讲了。很久以来(在此音乐被说出之前),此诗人的作品仅仅是一种聆听。离去状态首先将此聆听聚入它的音乐,以便此音乐能通过讲出的言说而鸣响,在那言说中回响。通过这一切注视与言说,此神灵之夜的神圣蓝色的阴冷鸣响着,闪耀着。此清冷状态的语言成了跟着说,此跟着说便成了诗。”〔11〕。
将诗人谦卑地放到一种聆听与应和存在之说(语言言说)的地位显然与十九世纪以来的主体论美学诗学截然对立,诗人重新从“上帝”(雪莱等人就认为诗人即上帝)的位置下降,最多只是一位上帝的使者。
就此而言,诗之所言既不是人心之“志”,又不是对经验之物或超验之物的“摹仿”,而只是“存在”本身。本真之诗只是存在的诗,因此,归根到底,不是人在写诗而是存在写诗。“诗以语词确立存在。”
诗的问题缘此而还原为存在论的问题。
二、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
“诗以语词确立存在”也就是“对存在的原初命名,是对万物本质的原初命名”。〔12〕海氏将这种“原初命名”解释为“给予”、“奠基”和“开端”。
“给予”是给无名之存在一个名字。取名似乎是自由的,“让诗人们自由如燕吧!”(荷尔德林),因为事物的存在与本质绝不能依现存者来计算,也不是经验的归纳,而是一种给予。从表面上看人是事物本质的给予者(我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但,此自由不是无原则的任意专断和随心所欲,而是最高的必然。”〔13〕“诗,作为确立存在的活动,受到双重控制。”〔14〕这便是诸神之声的法则和人民之声的法则在根本上控制着诗人的聆听,使其歌唱得以可能。因此,“给予”最终是存在通过诗人给自己命名,诗最终是“存在将自己在语言中给出。”
在语言中出场并居于语言中的存在之显现是“奠基”。“当诸神得到根本的命名,当万物被命名而首次彰显出来,人的生存便被带入了一种确定关系,便获得一个基础。诗的言说作为一种确立行为不仅是一种给予行为,同时也是给人的生存以坚实基础的行为。”〔15〕
海德格尔指出:诗作为“给予”和“奠基”又具有“开端”的性质。因为给予和奠基都是原初的直接一跃,是时间和历史的真正绽开。这种“绽开”并不仅仅指世界史之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之开始,它主要指生存论意义上的“另取一路”。因此,海氏说:“不管艺术何时发生,一种插入便进入
在给予、奠基和开端的意义“确立存在”也就是给万事万物以最初的尺度,那最初的“神性尺度”是由诗人采纳的。
自希腊智者宣布“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人性尺度”逐步取代“神性尺度”,“神”作为虚妄之物被驱逐出人的世界和心灵,“人”成了万物的主宰,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界形成了。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之为“世界”乃是一个“天地人神”的“四重体”。“神性之维”的缺失在根本上意味着世界的“无度”。因为,真正的原初尺度不是人而是神。海氏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说明这一点:
只要善——这纯真者
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
以神性来测度自身。
……
神乃人之尺度。”〔17〕
一个“无度的世界”是混乱的世界,一个混乱的世界已不算真正的“世界”而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在这个世界之夜的“贫乏的时代”,人们最缺少,也最不了解的是“神性尺度”。“神是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这不可知者何以成为一把测度之尺?但人们普遍的盲视并未遮住诗人的洞见。海氏认为,真正的诗人荷尔德林让我们相信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这并不等于无神或神死,而只是神隐。神之隐匿是我们闭目塞听自以为是的灾难性后果。只要我们返回纯真善良之心,返回谦卑虔诚之态,观看无形,倾听无声,“神便宣告他稳步到来的近。”〔18〕
海德格尔强调:“人不仅栖居在大地上,天空下,不仅靠培养植物和修建房屋而居留。人之能筑造,只有当他已经(在对尺度作诗意采纳的意义上)筑造才有可能。只是有了诗人,有了为筑造即栖居的构建而测度的诗人,本真之筑才得以可能。”〔19〕由此,我们在海氏那里听到这样的断言:“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是为了人的栖居而对神性尺度的采纳。”〔20〕
三、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晚期海德格尔之思中有一个重要语词对深入理解其思想至关重要,那就是“大地”(earth)。
关于“大地”,海氏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却多次使用。从其语用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海氏笔下的“大地”之意。“大地”是与“世界”(world)相对立而使用的概念, 海氏将这两者的关系描述为斗争中的亲密(见《艺术作品的本源》),也就是说它们既对立冲突,又相互依存。这种关系颇似黑格尔说的对立面的矛盾与统一,但这仅仅是貌似而已。因为海氏指出世界与大地之间始终有一本质差异,此差异是不可能弥合的(即黑格尔式的统一)。不过,海氏认为,就生存论之维而言,大地与世界又是彼此依存的,是一种争吵中的“亲密”。
大地与世界之作为隐喻,我认为它们对应于“自然之域”和“社会历史之域”。
早期海德格尔(主要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关注的中心是“此在”问题,即“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此在”之“此”是作为“世界”来理解的。“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 —world)与此在(Dasein)是一回事。因此,“世界”作为人生存的必然环节是他分析的核心。晚期海德德格尔有一隐秘的“转向”,那就是,他不再孤立地谈“在世界中存在”,而总是联系着“大地”来谈人的存在(栖居)问题。正是此一转向规定着晚期海氏诗之思的路向。
在我看来,海氏此一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对“技术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对人“在世界中存在”这一表述的一般性感到不满,甚至感到这一表述的危险性:忽略大地。
“在世界中存在”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并未对人如何在世界中存在的正当性和本真性作出说明。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是回避这种说明的,其幌子是“现象学描述。”但即使在《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描述中也可以看出海氏对“沉沦在世”的批判和对“良知呼唤”的向往。但毕竟在《存在与时间》中,差异与界限的述说是含混的,甚至是传统的。
只是在对“技术本质”的深入思考中,海氏才对不同“世界”的差异性本质有了切实而独到的理解与表述。这一切是借助于世界与大地的关系来展开的。
在海氏看来,迄今为止的西方史至少有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技术世界和艺术世界。前者是以摧毁大地为代价的世界,后者是看护大地的世界。
在海氏的思考中,技术是一种在根本上无视大地(自然)的极端世界化要求,技术作为人肆无忌惮地贯彻自己主观意志以追求最大效率和利润的手段,将大地(自然)置于毁灭的境地。在技术的本质中,没有什么能制止它对大地(自然)的无度掠夺、占有和耗废。因此,技术意志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意志。
在技术意志的控制下,世界便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其后果是:世界越来越精彩,大地(自然)越来越荒芜。同样的后果是:人们愈是在这个精彩的技术大厦(世界)中安居,也就愈是处在被荒芜的大地抛弃的危险之中。
海德格尔对此的深深忧虑在于:居于世界大厦中的人早已忘了这幢世界大厦是以破坏自己的大地的基础为前提的,即将失去大地之基的世界大厦正摇摇欲坠。
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功业卓著,但他却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海氏在阐述这句诗时指出,人居住在其“功业卓著”的世界大厦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生产并追求的东西是通过他的努力而应得的。‘但’(荷尔德林以鲜明对照的方式说),这一切都未触及人旅居大地的本质,这一切都还不是人生存的基础。人生存的基础在根本上看是‘诗意的’。现在我们将诗理解为诸神的命名和对万物本质的命名。‘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21〕
十分显然,“诗意地栖居”是对立于“技术地栖居”的,“这两种栖居的分野集中于对“神”和“万物”的态度。在技术性栖居中,神是被嘲弄的,万物是被蔑视和征服的,“人”就是一切,这种栖居的实质是人在人自己盲目自大的意志中的栖居。由于神被驱逐,人便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万物被征服,人便可以主宰一切。问题在于:人在根本上能为所欲为,主宰一切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作为有限而必死的人在根本上是无知的,他的知(尤其是最初的尺度之知)必然是向外获取的,是被给予的,尤其是有限而不可靠的。因此,人必面对神而承认自己的无知以便聆听神谕,与神共在以保证用神性尺度来度量自身。
此外,作为有限而必死的人在根本上是肉体的,他的肉体存在规定着他的自然性(大地性)和大地上的旅居。他来于自然,终又归于自然。自然(大地)才是他最终的家园。因此,人必得依存于自然万物,与万物共在是他的本质规定。而要与物共在,首先就得让物在而不是无度地掠夺自然。要让物在就得接近万物的本质,让其在本质中在而不是将树看作木料而随时准备投放到机器中加工生产。
“‘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就在于“诗”(本真之诗)之中隐含了一种全然不同于技术的眼光和态度。
在《赫贝尔——家之友》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说诗人赫贝尔是“自然之家”的朋友,在这个“技术世界”中他深切地看护着“自然的自然性”,而不至于让“自然”彻底消失在数字的计算和欲望的打量之中。“在家之友言说的每一事物中,他都看护着那本质性的东西,作为栖居者的人就是被托付给这本质性的东西的,可是人在打盹的时候却很容易将之遗忘。”〔22〕。
那本质性的东西是自然的自然性或物的物性,正是本真之诗看护这本质性的东西并启示我们不同于技术的以物观物方式和事物共处的态度。不过,海氏所谓的“诗意地栖居”绝不是一种中国式的出世隐居之路。海氏认为人是大地和世界之间的居者,纯粹的自然之居只能是动物性的,因为它无视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天命。当然,纯粹的世界性生存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无视了世界必立足于大地之上与大地共存亡的天命。
在这个技术时代的白夜,本真生存的隐匿,是以诗之真义的遗忘和盲视为前提的,为此,重审诗的意义并澄清诗的本质就是至关重要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诗意的前提下,我们才能随时了解到我们非诗意的栖居,了解到我们以何种方式在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对诗意的注意下,我们才可能期待在我们非诗意的栖居中,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出现一个转机。”〔23〕
到此为止,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海氏为何一再强调他的诗之思既非美学亦非诗学而是“思之必需”了。
尽管如此,海氏的诗之思对我们重新思考美学和诗学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至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中心的思路,此一思路对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和诗学影响深远。不过,真理之道往往是危险的,诚如德里达等人对海氏的批判,在海氏的“存在”依恋中也许有导向神秘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危险。但:
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有救。
注释:
〔1〕 科克曼:《海德格尔论艺术与艺术作品》,英文版,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6,第88页。
〔2〕 海德格尔:《追忆诗人·按语》,见《生存与存在》, 英文版,芝加哥,1968,第232页。
〔3〕〔4〕〔7〕〔8〕〔12〕〔13〕〔14〕〔14〕〔2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见《生存与存在》,第271页,第281页,第307页,第277页,第307页,第287页,第281页,第282页。
〔5〕〔18〕〔19〕〔20〕〔23〕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见《诗·语·思》,英文版,纽约,1971,第224页,第226页,第224页,第226页,第227页。
〔6〕 荷尔德林,转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
〔9〕〔10〕 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 见《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英文版,第123页,第129页。
〔11〕 海德格尔:《诗中的语言》,见《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英文版,第188页。
〔16〕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诗·语·思》,英文版,第77页。
〔17〕 荷尔德林,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
〔22〕 海德格尔:《赫贝尔——家之友》,见成穷等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大版,1992,第254页。
标签:美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存在与时间论文; 大地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