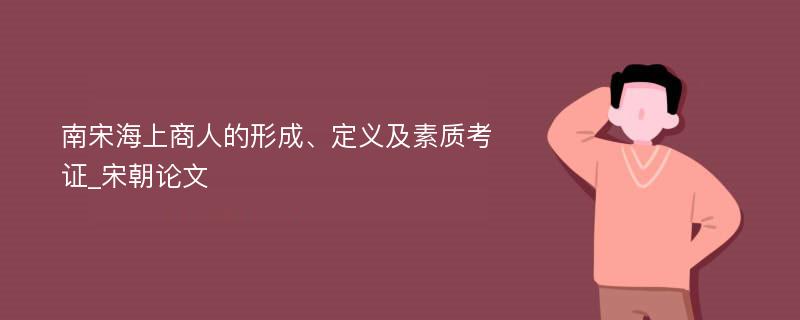
南宋海商羣體的構成、規模及其民營性質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商论文,南宋论文,民營性質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江浙閩廣一帶,不僅湧現出大批從事外貿經營的本國巨賈豪富和中小經營者,而且聚集着越來越多的以阿拉伯人爲主的“蠻賈蕃商”,其總數或許在十萬上下;以至廣州、泉州等港出現了外商聚居的“蕃坊”、“蕃學”和專門的蕃人墓地。華夷商人的交往與雜居所造成的“國際化”氛圍,以及當地民戶對海外貿易趨之若騖的經商風氣,是東南沿海地區區別於內陸各路的顯著特徵。史料反映,南宋時期的海外貿易較之北宋更爲繁盛。對其时海商羣體的構成、規模及其商業資本進行考察是理解南宋海外貿易之民營性質的基礎環節。是故,不揣翦陋,撰成此文,以求證於方家。
一 東南沿海海商羣體的廣泛存在及其構成
宋代以前,來往於東南亞、印度洋至中國航線上的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但到宋代,中國商隊逐漸與阿拉伯商隊一道成爲世界貿易的兩大軸心,雄踞於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地區。整個兩宋時期,中國海商在擴大貿易範圍、發展貿易規模、開發貿易產品、創新集資方式等諸多方面付出了艱辛努力,馬海外貿易注入了巨大活力。同時,宋朝對待海外貿易的官方政策與漢唐時期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漢唐外貿主要是朝貢貿易,以“重義輕利”、“招撫遠夷”爲主導思想;宋朝外貿主要是商業貿易,政府重視外貿的主要動機是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所以對待朝貢貿易,漢唐的做法是大量“回賜”來朝貢的“外夷”,使得“回賜”貨物價值遠遠超過其貢物價值——即“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而宋朝對這種貢賜貿易采取限制政策,以求減少“回賜”損失,造就使得民間海商成爲從事海外貿易的主體力量。民間海南作爲海外貿易主體力量,是宋朝,特別是南宋時期對外貿易的一大特徵,這與漢唐時期的朝貢貿易、元代的官本商船以及明初鄭和下西洋等在性質上截然不同。中國傳統社會從“頭枕三河,面向草原”至此一變而爲“頭枕東南,面向海洋”。①
兩宋時期,一艘海舶即是一個商隊,少則百餘人,多則數百人,結隊飄洋過海,從事海外貿易。其規模及商品運載量遠遠超過漢唐時期陸上絲路之駝隊。宋代的《市舶法》規定:“商賈許由海道往來,蕃商興販,並具入舶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物力戶三人委保,州爲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給公據聽行。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②從事外貿的“舶商”在準備好船隻和水手,招攬到貨主和貨物後,先攜當地殷實戶出具的承保書向當地市舶司提出“放洋”申請。市舶司對船上人員和貨物一一核查,批准後發給“公憑”或“公據”,作爲外貿許可證。許可證上除事先印刷的相關條例法令外,還要詳細登載船主、船員姓名,人數,始發港口,前往地點,貨物品種、數量,保人姓名等欄目。半年或一年後返航,舶商即憑此種“公據”向市舶司報關登岸。③因此一艘“海舶”就是一個出洋商隊。其內部構成可以大體別爲海舶綱首、中小貨主和船員水手三個大類。
宋人朱彧說:“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卧其上。”④可見衆多貨主是隨船出海的。這支百餘人至數百人的商隊,非有嚴密的組織不可。每艘海船的船主爲商隊首領,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綱首”,負責在航行途中管理整個商隊和在域外招誘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的雙重任務。⑤“綱首”既是價值成千上萬缗之海舶的主人,則非沿海港口資產豐厚的鉅賈富賈莫屬。“網首”之下有兩撥人,一是上述之“貨主”,一船有數十至上百人不等;一是船員,也有十数至數十人之多。船員中有部領、水手長、雜事、直庫(貨艙主管)、火長(執羅盤領航者)等不同職務,此外還有艙工、梢工、旋工、纜工等水手。這些船員和水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貿商人。因爲按宋代貿易法條,船上所載出口貨物中有20%爲船員和水手的私貨,⑥販易所得(一般是以出口貨物換易所得的蕃貨即進口商品)作爲其勞動報酬,回航入境時不在抽稅範圍之內。因此他們到海外同樣從事外貿交易。
海舶綱首、隨船出海的中小貨主以及各色船員、水手,共同構成了出洋販易的海商隊伍。他們主要分佈在江浙閩廣即東南沿海一帶。南宋中葉包恢所說:“販海之商……江淮閩浙處處有之。”⑦因而在宋人的筆記小說中,東南沿海一帶就有不少此類舶商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兩浙和江東地區:
臨安人王彥太,家甚富,有華室,頤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⑧
溫州巨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⑨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⑩
四明人鄭邦傑以泛海貿遷爲業。(11)
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因販海往山東,爲偽齊所拘。(12)
明州有道人……自云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上。(13)
張端慤,處州人,嘗爲道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徵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14)
鄭四客,台州仙居人,爲林通判家佃戶。後稍有儲羨,或出入販貿紗帛海物。(15)
福建地區海商更多。早在北宋中葉,蘇軾即言:“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馬業。”如泉州海商徐戬,“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即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16)南宋時期此類記載更是屢見不鮮:
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17)
泉州商客七人:曰陳、曰劉、曰吴、曰張、曰李、曰余、曰蔡,紹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18)
泉州僧本偁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及舊相識,急登之……乃得歸。(19)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度今有四十萬緡。(20)
廣南瀕海州縣居民,同樣是“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21)相關事例後文還將述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南沿海從事海外貿易的人,除了數量衆多、富可敵國的大舶商外,還有不少港口或沿海地區的平民百姓。他們自己並不出海,而是以數十上百貫銅錢作爲资本,輾轉相托,交給出洋舶商帶買域外蕃貨,回來再貿販取利,頗似今日的集資貿易方式。但從政府角度看,這種帶買方式泄失了銅錢,所以時稱“帶泄”。南宋中葉包恢說:“所謂帶泄者,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托,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22)正因爲獲利豐厚,所以東南沿海地區以帶買方式從事外貿的沿海民戶必不在少數。這部分人的數量有可能超過專業舶商,惜無數據傳世,俟後再證。
甚至沿海地區的官員和軍將也以各種方式參與海外貿易,此類事例尤以廣南地區爲多。孝宗乾道七年(1171),宋廷嚴令禁止官員染指外貿:“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23)儘管宋廷屢次下發禁令,但張方平所說的“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24)的局面在兩宋三百年間從未得到遏止。正如淳熙二年(1175)戶部所說:浙閩廣“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25)禁而不止,這就是歷史實際。因此史籍中反映官員和軍將從事海外貿易的事例並不少見。
軍將經商的著名事例首推南宋初年大將張俊。他以“回賜”爲名,把五十萬缗現金付給一個軍中“老卒”設法生利,“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其獲利秘訣是:“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珠犀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遣甚厚,是以獲利如此。”(26)這是以南宋綾錦之類紡織品和金銀器皿爲出口商品,歸國後再將進口的“珠犀香藥”之類舶货賣出,一進一出即獲超額利潤。南宋後期有廣東摧鋒軍人假公濟私,從商取利之事。開禧元年(1205),廣東提刑司陳映言:“廣南有摧鋒軍,專以防盜。軍中有回易,所以養軍。比年以來,於海洋僻速去處,或稱巡鹽,或稱捕盜,客舟往來,寔受回易軍兵之擾。乞木(下)本路經略提刑司,今後摧鋒軍除捕盜外,不許諸司別作名色,差撥下海。”(27)廣南近海有海岸護衛隊性質的摧鋒軍兵將從事“回易”,十之八九與海外貿易相涉。
官員染指外貿在整個南宋時期就從沒停息過,其中少數官員受到過相應處罰,故在史書中留下相關記載。如嘉定五年(1212)九月十二日,“知雷州鄭公明放罷。以廣西提刑崔與之言,其三次般運銅錢下海,博易番貨”。(28)理宗朝杜範奏劾宰相鄭清之,稱其子曾“盗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29)其實此類事件從南宋初年以來相當普遍,紹興三十年(1160)即有言者論及“將帥、貴近各自遣舟”從事海外貿易的弊端,要求朝廷設法禁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
言者論國家之利,莫盛於市舶。比年商販日疏,南庫之儲,半歸私室。蓋商賈之受弊有四,官中之虧損有二。……向來舶賈,率皆土人,事力相敵,初無攘奪相傾之患;其後將帥、貴近,各自遣舟,既有厚貲,專利無厭,商賈爲之束手。……海濱之民,冒萬死一生之利,而得不償費,人人失業。……舊海賈既多,物貨山積,故抽解所入,不可以數計;今權豪之家,势足自免,縣官歲入,坐損其半。往歲土人入蕃之貨,不過瓷器、絹帛而已;今權豪冒禁,公以銅錢出海,一歲所失,不知其幾千萬。此二損也。市舶一司,自唐以來,恃此以爲富國裕民之本,今其弊至此,願詔將帥、貴近之家,毋得歲發舶舟,攘奪民利,虧損國課。仍詔有司講究,除去宿弊,以便公私,其於國計,誠非小補。戶部奏:“復抽解舊法,違者許商人陳訴。應命官以錢物附舶舟、或遣人過海者,依已得旨,徒二年。其發舶州軍,毋得抑勒,仍檢銅錢出中國界條約行下。”從之。(30)李心傳注稱: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敕:廣州見任官將錢物寄附綱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敕徒二年科罪”。(31)
不難看出,“將帥、貴近”等權豪世家多有染指外貿者,他們“攘奪相傾”,以權謀私,已經影響到民間正常貿易活動的開展,“商賈爲之束手”。其方式或“各自遣舟”出洋興販;或“以錢物附舶舟”,搭夥取利;以至鬧到海濱之民,“人人失業”、“縣官歲入,坐損其半”的嚴重程度。可見趙氏宗室、官員、軍將之類權勢人物在外貿中與民爭利之事的確相當普遍,所以中央政府纔下令嚴行禁止。但是第二年又有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趙士街等“强市海舟,爲人所訴”的事情發生。(32)連皇族宗室都在“抵法冒禁”,躋身外貿,說明此類禁令效果不彰。
甚至連和尚、道士之類的“出家人”,亦有經不住財富誘惑、出海牟利者。除前述處州道士張端愨、溫州道士王居常外,北宋“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客至高麗,交譽之”。(33)南宋中葉泉州海商王元懋亦出身僧道。史稱:
少時祗役僧寺,其師教以南番諸國書,盡能曉習。嘗隨海舶詣占城,國王嘉其兼通番漢書,延爲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緡,而貪利之心愈熾。遂主舶船貿易,其富不貲。留宰相、諸葛侍郎皆與其爲姻家。(34)
隨着海外貿易的持續發展,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海舶戶”。其中既有漁民,亦有海商或給海商提供船舶的“舶主”。“舶主”用自造或者買來的航海船隻爲客商承運各色貨物,以收取雇僦之費爲主要收入。北宋時,朝廷遣使高麗,即曾雇募浙江、福建的民間船隻出航。(35)南宋時,葉夢得奏札云:
本州(指明州)舶船舊許與高麗爲市,間有得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因令舶主張綬,招致大商柳悅、黄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賈販高麗。(36)柳悅、黄師舜是泉州當地的海商世家,多半擁有自家(或造或買)海舶。以航運爲生的“舶主”和“海船戶”,須向當地官府登記入籍,纔能擁有航運營業權,此即“給官印,以驗實乃得行棹楫”。(37)這是北宋的規定,南宋延續了這一制度。孝宗淳熙末年,江文叔任廣南市舶使時,允許已溺沒風濤的舶戶子孫免除海船戶籍:“舊例,舶舟溺風濤者,抑子孫續其業,人以爲苦。君(指江文叔)首列於朝,詔刊其籍,舶貨亦通。”(38)海舶戶占籍時,先由官府“檢量丈尺,辦驗木植之新舊,雕刻帆樯”。(39)市舶司爲完成每年的舶入歲課,“每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願者,照籍點發”,(40)强驅出海。南宋時沿海地區上供錢物,多走海道,仰賴民間海船,因而當地官府常常“拘留海船”,“輪流差使”。(41)
東南沿海地區此類海船戶爲數衆多。建炎三年(1129),張俊部將辛道宗“家有青龍海船甚衆”,可以運載水軍從浙西“由海道趨錢塘”。(42)乾道四年(1168)十二月十三日,“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撥海船百艘至明州定海馮湛軍前”。(43)乾道五年四月五日,統制官左祐所統轄海船二百餘艘,亦從民間徵得,“皆積久捕魚射利之民”,看來此次所徵多係漁船,不過亦有部分專事運輸的海舶在內。故前引“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即福建沿海的四個州、軍均有民間自設的民營船廠,以滿足近海和遠洋等各種運輸需要。
二 中外海商的數量估計
活躍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各類“舶商”爲數衆多,活動頻繁。他們可粗略分爲中國“海商”和“蠻賈蕃商”兩類。其人數因史無明文,只得輾轉推求。兹先估测中國海商的數量規模。
如前所述,東南沿海各州都有上百條甚至數百條海船,除漁船外,有相當部分從事運輸和外貿。而能遠洋航行的尖底海船,大多吃水深、運力强。一般五千料的大型海舶,長三十丈,約近百米,載重五千石,載貨量六百噸,可搭乘五六百人。(44)這類出洋的大型海船上有衆多商人,如前引《萍洲可談》說,他們“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結伴而行。整條海船是一羣經濟自主的商人們的組合體。在這個組合體中,常常以鉅賈爲綱首、副綱首、雜事,他們經濟實力强大;又因“市舶司給朱記,許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財”,(45)而具有政治特權。海船上除了這個特權階層和船主、事頭、火長、舵工、碇手、稍水等海員以外,大部分是一般中小商人,時稱“船客”。中小型海舶亦可載一百人以上,吴自牧說:“且如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餘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46)南宋海舶較之阿拉伯商人使用的“蕃舶”要大上好幾倍。《宋史》稱:“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之一。”(47)其最大的帆船“獨檣”,載重量僅一千婆蘭,即爲二三千料,只及南宋的中型海舶;次等的“牛頭”(不到一千料)、“木舶”(三四百料)就更小了。從海舶的載重量和製造技術看,這一時期海上貿易的主導力量確非南宋舶商莫屬。
南宋海舶規模巨大,構造複雜,加之航程遥遠,必須使用大量海員和專業化水手,分任各工種之具體操作任務,並互相協作,方能行駛於遠洋大海之中。一艘海舶的內部組織和分工大致如下:
綱首,又稱都綱,職責相當於船長或船隊長,係全船之總管。對於選擇水手,船貨的買賣,指揮航行等,擁有全權。
副綱首,相當於大副,協助綱首管理航行和貿易事務。
雜事,又稱事頭,經手處理船上日常事務。以上三個職務在船上最爲重要,相當於船長、大副和二副級別,所以通常由鉅賈或船主自己擔任。船上還有一批技術型的高級船員:
舟師,指揮舶船駕駛人員之統稱,包括懂得依水之流向、深淺,掌握船舵之定向、升降的梢工(也稱“舵工”)和認針路、掌針盤,負責計程計時的火長。
直庫,保管船上糧儲物资和防盗兵器。
部領,又稱招頭,即水手長,負責航行事務。
篙師,又稱海師,指揮篙手撑篙航行。
司繚,管觀風向,掌帆之升降。
碇手,指揮下碇和收碇。(48)他們負責航行和日常管理事務,負有較大責任。此外,船上還有許多從事繁重艱苦的體力勞動,而又不需要很高技能的水手,他們主要從事搖櫓、撑篙、收放碇、牽拽、搬運等雜役。一般地說,宋代的海船面闊二丈,“梢工二人,招頭一人,碇手三人,水手二十七人。二丈一尺以上,梢工、招頭各二人,碇手三人,水手三十三人”。(49)這樣,一艘中型海舶的船員、水手至少在四五十人以上。如前所述,他們同樣是海外貿易的參與者。
耐人尋味的是,在泉州出土的宋船上發現的貨物木籤中,除了標有“幹記”之外,還有一些木籤上分別寫着“吴興水記”、“丘碇水記”、“陳小工記”、“張什”、“張絆”、“楊工”、“尤工”、“三九工”、“六十”、“安廚記”等字樣。廖大珂認爲,這些“水”、“碇”、“絆”、“什”、“十”、“工”、“廚”等字指的是從事不同工種的船員和水手,這些木籤是用以標明他們各自販運的貨物。(50)這種“以艙代薪”制,將船主、商人、水手的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促使他們同心協力,達到“賠費既少,優獲利息,則足以得其心力矣”的目的。(51)前引《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五○所載福建綱首陳應一次就率五艘海舶去交趾販易,更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外貿船隊。所以紹興二十九年(1159)右正言朱倬曾將活躍在東南沿海“山海之間”的各色人等,除逃兵外分爲四種:
一者海賈,頃因市道交爭,互相殺戮;二者私商闌出,爲人所告,官司見行收捕;三者遊手廢業之人,比因强奪財物,或致傷犯,勢不可還;四者篙工、水手,曾從海寇,景迹昭著。物色根尋此曹,自閩、浙、二廣,十數爲羣,無所得食,竄伏山海。(52)除“逃犯”外,其餘“海賈”、“私商”和“篙工”、“水手”之類,一般都是海外貿易的從業人員。一艘海舶即以數十人至上百人計,沿海二十來個大小不等的外貿港口,保守估計若有二三百艘海舶,則每年即有數萬人放洋赴蕃。這還不包括前述爲數衆多的“帶泄戶”,雖然他們只是海外貿易的間接參與者。
可喜的是,筆者在相關方志中找到數則記載水手具體數據的材料,可供推算之用,彌足珍貴。紹興三十年(1160),宋廷從“漳、泉、福、興積募到海船三百六十只,水手萬四千人”。(53)每艘海船平均擁有水手三十八九人。無獨有偶,淳熙五年(1178)泉州大海商王元懋“使行錢吴大作綱首,凡火長之屬一圖帳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載。以十五年七月還,次惠州羅浮山南,獲息數十倍”。此次載回的貨物有“沉香、真珠、腦麝,價直數十萬”。(54)這次出航的海船擁有水手也是三十八人。我們看到,當時東南沿海各州從民間徵收一二百艘海船是尋常之事,按一艘海船擁有三四十名水手計,每州至少擁有水手數千名。如此算來,沿海各州從事海上運輸和貿易的水手羣體可達數萬人之規模。
南宋時期各國來華的“蠻賈蕃商”亦不在少數。東亞地區的日本、高麗商人和使節多自明州登陸上岸。林真奭據高麗史統計,在1012—1192年的一百八十年間,宋代海商前往高麗進行貿易見於記載的就有一百一十七次,其中能確知人數的有七十七次,共四千五百四十八人。(55)據此,平均每次近六十人,若按一百八十年平均,每年到高麗去的宋朝商人有二十五人。當然,還有很多小規模的商隊未被記載,事實上,每年均有華商前往高麗等地。因此我們說在多數年份僅僅到達高麗的宋商,每年就有數十人應是比較近實的估計。《宋史》稱,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56)來華的高麗商人應當不如去高麗的宋朝商人之多,但文獻中亦有高麗貢使和商人來華之記錄。如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57)在日本國,南宋時武家興起,鼓勵外貿,《實慶四明志》和《開慶四明志》中有不少日商販運木材、硫磺來華的記錄。泉州則是日商常來之地。《諸番志》載,日本“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十四五丈,徑四尺餘,土人解爲枋板,以巨艦搬運至吾泉貿易”。(58)
在東南亞,交趾商人來華貿易主要集中在廣西欽州,而占城商人在被宋朝政府限制在廣州一地。據《繫年要錄》和《中興聖政》載,高宗、孝宗兩朝僅占城就有八次朝貢。三佛齊(印尼蘇門答臘)一度控制麻六甲海峽,勢力强盛,來華商人更多。紹興二十六年(1156),其國遣浦晉攜乳香八萬斤、胡椒一萬斤、象牙四十斤入宋,當爲朝貢貿易。(59)三佛齊商人亦有在泉州定居者:“三佛齊之海賈,以富豪宅生於泉者,其人以十數。”(60)真臘(柬埔寨)屬國真理富國商人“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五日抵波斯蘭,次昆侖洋,經真臘國,數日至賓達椰國,數日至占城界,十日過洋,……方抵交趾界,五日至欽、廉州”。(61)乾道四年(1168),有一“真里富國大商”死於明州,“囊齎巨萬”。(62)南宋後期有阿拉伯商人佛蓮,“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63)佛蓮家富,在其生前從阿拉伯地區發往南宋的商船達八十艘,至少需要數十年時間,據此推算,佛蓮家經營阿拉伯與南宋之間的海上貿易主要是在南宋中葉時段。佛蓮死於泉州,其遺產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可以稱之爲富豪級外商。
甚至連廣南西路的貴州(今廣西貴港市)也有外商活動的記載。南宋初年,向子諲(1085—1152)知貴州,“時南海賊號大棹,與福建多槳船商販者劫掠海道”。向子諲偵知“城中富家某人,大棹之囊橐也”。捕此富人及其徒衆,又“其多槳船,命依市泊(舶)過蕃法召保給據,然後得行。於是賊黨消散,河道清靜。”其時貴州“爲蕃商所聚,人多入其貨而隱其置(值),訐訟,則書不可識,語不可曉,官必憑譯者”。向子諲“乃命吏以蕃書告喻,羣商爭來愬,盡得其情,應負之者悉徵還,咸呼舞歸其國。清明之政,播於海外”。(64)可見今廣西貴港一帶外商不少,當地官員需憑“譯者”和“蕃書”方能與之溝通,平息糾紛。
至於來華外商及其後裔的數量,估計亦有數萬之衆。前已述及,這類海商集中居住在廣州和泉州的蕃坊之中。而廣、泉城中則常現“華夷雜居”的情形,說明散居在蕃坊之外的各國商人亦有不少。即以泉州爲例,前引理宗初年真德秀知泉州時,一年之中駛達泉州港的外國船舶就有三十六艘,以每艘數十人計,總數可能達近千人之多。《輿地紀勝》卷一三○引陸宇《修城記》稱:“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65)而如南宋劉克莊所說,泉州是一個“以番舶爲命”的城市。(66)宋末元初,泉州更是“番貨遠物、異實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爲天下最”。(67)泉州五十萬人口,即以五分之一戶從事外貿計,僅泉州就有舶商二萬餘人(以每戶二人計)。其中外商不下数千人。廣州情況與泉州大同小異,不再贅述。兩地合計,已近萬人。
考諸兩宋史籍,有名有姓的外商,筆者所見不廣,亦發現有十四五人。前引趟汝适《諸蕃志》一書所提到的阿拉伯商人有莆亞利、時羅巴和智力干父子、陁那幃等人。《宋史·外國傳五·勃泥》提到施弩(Sina)、蒲亞里(Abu Ali,今譯阿布阿里)、哥心(Kgsim,今譯卡欣),不過此三人是貢使身份;(68)而蒲羅歇(Abdallah,今譯阿布杜拉)則是真正的商人,常年來往於阿拉伯、中國和印尼之間。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97)渤泥國王向打遣使進表,表稱“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69)南毗國的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倆,則已定居泉州,“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70)見之於現存史籍的其他大食商人還有陁離、陁婆離、(71)蒲囉辛、(72)蒲押羅、(73)辛押陁羅、(74)蒲希密和蒲押陁黎父子、(75)李亞勿,(76)以及南宋末年官至泉州市廂使、“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壽庚等。(77)《宋史》所載來自南洋三佛齊的還有蕃商李甫誨、舶主金花茶(78)和前已述及的高麗商人徐德榮等。
依據上述情況參酌權衡,竊以爲南宋東南沿海常年有近十萬人涉足外貿的估計並非夸大的不實之辭。
三 中外海商的內部分層及其金字塔結構
我們看到,南宋從事海外貿易的舶商羣體龐大、成份複雜,其中既有趙氏宗室、貪瀆官員和擁兵軍將,也有自造海舶、興販牟利的一般民衆;既有富埒王侯、數代泛洋的海商世家,也有資力微薄、偶一販易的“帶泄戶”;既有自備海舶並身任船隊頭領的“市舶綱首”,也有“以艙代薪”、附搭些許舶貨的下層水手,甚至還有僧道等出家人裹挾其間。所以,南宋海商羣體的經濟實力和地位差別如隔天壤,其內部階層結構猶如金字塔,難以一概而論。
處在金字塔頂端的自是宗室、官員和軍將等權貴海商,如前述“强市海舟”的宗室貴胄趙士街和以五十萬緡付老卒“造巨艦”放洋販易的大將張俊。一般海舶的造價動輒數千緡、上萬緡,一般平民根本無力承擔。如南宋初年曾有沿海富人金鼐,補粟授官爲武義大夫,“嘗造海舟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79)南宋中葉臣僚陳自强“運以海舶,不知其幾。有幹僕陳宗顥者,本封樁庫吏,自强倚爲心腹”。(80)這類海商發財致富,依賴的主要不是自由競爭,而是手中的權柄和强力。這說明當時“只有貴纔能富”的傳統規則在外貿領域中的顯著作用和影響。
居於金字塔第二層的是那些蹈海數十年、以放洋興販爲畢生行當的職業海商。如建康鉅賈楊二郎,在往來南洋十餘年後終得以“累貲千萬”。(81)泉州海商楊客亦“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82)合銅錢二十萬貫。另一個僧道出身的泉州海商王元懋,既“通番漢書”,又在占城住過十年,其貲財超過百萬貫。(83)紹興年間泉州有一海商爲逃避舶司查驗,“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沉於海,官司知而不敢問”。(83)銅錢只是出口商品之一種,若再加上絲帛、瓷器之類大宗貨物,則整船所載貨物之價值肯定不下數十萬貫。至於前述世販高麗、日本的海商柳悅、黄師舜和舶主張授等人,作爲外貿世家,其財富自不待言。
亦有不少來華外商,其豪富程度較之中國海商毫不遜色。如南宋初年:
大食人使蒲亞里所進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在廣州市舶庫收管。緣前件象牙各係五七十斤以上,依市舶條例,每斤價錢二貫六百文,九十四陌,約用本錢五萬餘貫文省。欲望詳酌,如數日(目)稍多,行在難以變轉。即乞指揮起發一半,令本司委官秤估一半,就便搭息出賣,取錢添同給還蒲亞里本錢。
揀選大象牙一百株並犀二十五株,起發赴行在,準備解笏造帶、宣賜臣僚使用。(85)阿拉伯商人蒲亞里所攜舶貨僅象牙一項即價值五萬餘貫省(以九十四陌爲一貫),若加上香料等大宗貨物,其總值恐亦達數十萬貫。前曾述及,南宋後期的另一個阿拉伯商人佛蓮死後遺產僅珍珠一項就有一百三十石,他的家族在南宋中葉時“凡發海舶八十艘”。他們可謂超級富豪,爲數不會太多。此類海商冒着極大的財產和生命風險,憑藉自身技能、才華和膽識,積累了豐富的海外經驗,從而也獲得了巨額回報。他們創造了一個個生動的財富神話。
處在金字塔第三層的是中小海商,人數衆多。他們或是海舶上“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许”的“搭載客”,一船可搭乘數百人之多;或是海船的舟師、直庫、部領、篙師等高級船員,他們長年生活在船上,奔波於浩瀚的遠洋航道,具有豐富的航海經驗,整個商隊的生命、財產安全繫於一身。在“以艙代薪”制下,可獲得一份不錯的應得收入。
處在這個金字塔底層的是數量最多的水手和“帶泄戶”。作爲南宋海外貿易的一般下層參與者,其人數可以萬計。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只能從巨額外貿利潤中分得一小杯羹。其中也有“因商販折本,無路得食,不得已求生”(86)而淪爲海盗者,此即前引朱倬所言“遊手廢業之人”。當然,若從資本角度看,那些采取集資方式參與海外貿易的沿海居民,雖然每戶只出數十百緡“轉相結托,以買番貨而歸”,但因人數衆多,彙聚起來亦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雖然宋廷曾多次嚴申禁止銅錢出海之法令,但因“利源孔厚”而“趨者日衆”,(87)此類法令實際效果甚微。民間自行販易的活動仍然活躍,“帶泄”集資者的數量依然龐大。這是一支强力不能壓制的求生力量,亦是南宋海外貿易不竭活力的源頭之一。南宋海商羣體的廣泛存在及其作爲海外貿易的主導力量這個事實,可以充分說明南宋海外貿易的民營性質,同時亦是南宋時期的江南區域經濟一度出現海洋發展路向的確鑿史據之一。
注释:
①參見葛金芳《宋代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光明日報·理論版》2004年12月28日,又載《新華文摘》2005年第5期)以及《頭枕東南,面向海洋——南宋立國態勢及經濟格局論析》(《鄧廣銘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年,頁3367下。
③據《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和《宋會要輯稿》職官部分之相關記載撮述。
④朱彧《萍洲可談》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33。
⑤《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載“諸市舶網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4537。以“承信郎”、“忠訓郎”之類低級官職作爲其擴大外貿、增加稅收的酬獎。
⑥《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五載:綱運船隻所載貨物,“依條八分裝發,留二分攬載私物。”頁5619下。此種規定對於出洋海船亦適用。參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80—81。所謂“私物”,即船員、水手個人置辦的貨物,其販易所得在回國時不在抽税範圍之內。
⑦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8册,頁714下。
⑧洪邁《夷堅志》支乙卷一《王彥太家》,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796。
⑨洪邁《夷堅志》支丁卷三《海山異竹》,頁987。
⑩同上書補卷二一《鬼國母》,頁1741。
(11)郭彖《睽車志》卷三,載《筆記小說大觀》(三),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頁67上。
(12)《夷堅志》甲志卷七《搜山大工》,頁62。
(13)同上書乙志卷一三《海島大竹》,頁295。
(14)同上書甲志卷一一《張端愨亡友》,頁96。
(15)同上書支景卷五《鄭四客》,頁919。
(16)《蘇軾文集》卷三○《論高麗進奏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47,848。
(17)《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七,頁6564上。
(18)《夷堅志》三志己卷二《余觀音》,頁1318。
(19)同上書甲志卷七《島上婦人》,頁59—60。
(20)同上書丁志卷六《泉州楊客》,頁588—589。
(21)《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一六載淳熙十二年刑部尚書蕭燧言,頁6215下。
(22)《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頁714下。
(23)《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頁4566。
(24)《宋史》卷一八○《食貨志二下》,頁4384。
(25)同上書,頁4566。
(26)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老卒回易》,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69,270。
(27)《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七之二,頁6253下。
(28)《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四三,頁4072上。
(29)《宋史》卷四○七《杜範傳》,頁12282。
(30)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下簡稱《要錄>)卷一八六紹興三十年十月己酉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27册,頁658下—659上。
(31)《要錄》卷一八六紹興三卜年十月己酉條,頁659上。
(32)同上書卷一八八绍興三十一年二月甲子條,頁689下。
(33)《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五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午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0493。
(34)《夷堅志》三志己卷六《王元懋巨惡》,頁1345。
(35)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客舟》,叢書集成本,3239册,頁117。
(36)《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夷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4516下—4517上。
(37)程俱《北山集》卷三○《王公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0册,頁295上。
(38)周必大《文忠集》卷七二《廣南提舉市舶江公文叔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47册,頁758下。又,江文叔一作江文敍,於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任廣南市舶司使。參見林天尉《宋代香藥貿易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40。
(39)周必大《文忠集》卷八二《大兄奏劄》,頁847上。
(40)《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四,頁6567下。
(41)《要錄》卷一五一紹興十四午二月己丑條,頁103上。
(42)《要錄》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癸巳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25册,頁338上。
(43)《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二,頁5667下。
(44)吴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頁102。又見《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報告》,載《泉州灣海船發掘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頁55—61。
(45)《萍洲可談》卷二,頁133。
(46)《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頁102。
(47)《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頁4565。
(48)參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頁78—79;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80—81。
(49)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海船戶》,載《宋元方志叢刊》(8),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7902下。
(50)前引《福建海外交通史》,頁81。
(51)廖剛《高峯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42册,頁363下。
(52)《要錄》卷一八一紹興二十九年正月庚辰條,327册,頁556上。
(53)《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五《海防》,載《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2),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587下。
(54)《夷堅志》三志己卷六《王元懋巨惡》,頁1345。
(55)林真奭《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5。
(56)《宋史》卷四八六《外國傳三·高麗》,頁14053。
(57)同上書,頁14052。
(58)楊博文《諸番志校釋》卷上《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55。
(59)《要錄》卷一七五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條,頁476上。
(60)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五《泉州東坂葬蕃商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40册,頁490下。
(61)《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九,頁7763上。
(62)樓鑰《攻媿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四部叢刊縮印本,244册,頁794上。
(63)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佛蓮家貲》,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93。癸巳,應爲紹定六年,即1233年。
(64)胡宏《五峰集》卷三《向侍郎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7册,頁163上,下;又見《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76。
(65)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2年,頁3733。
(66)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行狀》,四部叢刊縮印本,279册,頁1494下。
(67)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六《送姜曼鄉赴泉州路錄事序》,文淵閤四庫全書本,1197册,頁299下。
(68)《宋史》卷四八九,頁14094。《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八亦載此三人,頁7843下。
(69)《宋史》卷四八九,頁14095。
(70)《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傳五·南毗》,頁14093。
(71)陁離、陁婆離,《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一載,真宗咸平元年“大食國王先差三麻傑託舶主陁離於廣州買鍾……”;咸平三年,又“詔賜其舶主陁婆離銀二千七百兩……”頁7759上。不知此二人是否一人,待考。
(72)《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四載,紹興元年福建市舶司言,“大食蕃國蒲囉辛造船一隻,般載乳香,投泉州市舶,計抽解價錢三十萬貫,委是勤勞,理當優異”,朝廷遂授予“承信郎”官職,頁7760下。
(73)《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一載,太平興國八年,“三佛齊國遣蒲押羅貢方物”,頁7845上。
(74)《宋史》卷四九○《外國傳六·大食》載,神宗熙寧年間,“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頁14121。觀此,辛押陁羅當爲商人,而非貢使。
(75)同上書,頁14118—14119。
(76)同上書,頁14118。
(77)同上書卷四七《瀛國公紀》,頁942。
(78)均見同上書卷四八九《外國傳五·三佛齊》,頁14089。
(79)《要錄》卷一八九紹興三十一年三月辛卯條,頁695上。
(80)《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衛涇奏乞籍沒陳自强家財狀》,頁2420下。
(81)《夷堅志》補卷二一《鬼國母》,頁1741。
(82)同上書丁志卷六《泉州楊客》,頁588。
(83)同上書三志己卷六《王元懋巨惡》,頁1345。
(84)《要錄》卷一五○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己酉條,頁100下。
(85)《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三至一四,頁3370上—下。
(86)洪适《盤洲文集》卷四《招安海賊剳子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58册,頁525上。
(87)《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四,頁6567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