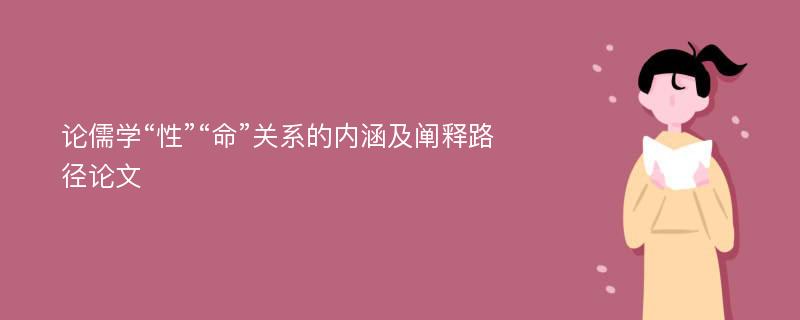
论儒学“性”“命”关系的内涵及阐释路径
谭绍江,涂爱荣
(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205)
摘要 :在儒学思想中,“命”具有形上超越的道德本体与形下现实限制两重内涵,“性”同样也具有应然的道德主体与实然的自然欲求两重内涵。“性”“命”之间的关系正是以这种复杂内涵为基础。围绕二者之间关系,儒学采取了“内圣”与“外王”两种阐释路径。“内圣”路径注重道德主体修炼,又分为“‘性’‘命’对扬”与“‘性’‘命’统一”这两种主张。但是,单纯的“内圣”路径不能化解其中蕴含的理论难题。“外王”路径则注重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也分为君循礼制基础上的“‘性’‘命’统一”与“同心一德”目标下的“‘性’‘命’统一”两种主张。其中,后者因为重视了以政治架构作为道德的实践的间接手段,对于儒学“性”“命”关系的阐释更为充分。
关键词 :儒学;“性”“命”关系;途径;内圣;外王
“性”“命”关系是儒学一贯重视的命题。但是,二者关系究竟应如何合理建构则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以儒学经典中的“天命之谓性”“性自命出”的阐释为例,陈来教授指出,“其实,如果不按宋儒的解释,仅就‘天命之谓性’说,其意义并不能够归结为性善论,而只是说,性是天赋的。《孟子·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露,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天之降才’即是天生的资性,即是‘天命之谓性’,也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并不意味着性就是善的”[1]。郭齐勇教授则指出,“郭店简诸篇所透露出来的继《诗》、《书》、孔子之后的‘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孟子心性论的先导和基础。天为人性之本,是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终极根据和价值源头”[2]。约略可见,陈教授在此的解释更重视命题的现实性意涵,郭教授的解释则更重视命题的超越性意涵。这里面的原因既与“性”“命”范畴各自的复杂内涵有关,亦与儒家学者对于儒学宗旨实现途径的争论相关。在优秀传统文化备受重视的今天,我们再来梳理这一命题并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十分必要。
一、儒学思想中“性”“命”范畴的复杂内涵
作为儒学鼻祖,孔子未专门探讨“性”“命”范畴及其关系,但是他在推行儒学思想的艰难实践中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纵观相关讨论,孔子所说的“命”显然具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描述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之状态。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3]54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3]141
以上孔子之言,无论是对伯牛身患绝症的感叹,还是对大道运行之兴废的喟叹,都清晰展示了“命”所具有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内涵。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子所谓命,是何意谓?大致说来,可以说命乃指人力所无可奈何者”[4],这种“命”显然为消极意义,“命在消极方面,可以说是自然对于人为的限制。人事已尽,而还不得成功,便是命所使然”[4]。
“命”的另一层含义则具有积极意义,即孔子在“知天命”中所阐述的带有超越性的道德本体之“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11
除了“U”字形的城市外围的绿化带外,城市内部开放空间主要包含公园、广场、路边休憩等类型,其中大大小小公园共有十余处。但是城区现状功能分区散乱,各类用地布局混杂,缺乏系统安排;空间效率较低;老城区空间布局零碎,城中村问题普遍,平房多,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188
在这里,孔子之“天命”与“命”,都带有超越性含义。崔大华教授指出,“全幅的儒学思想史显示,‘命’或‘天命’是儒学所确认的唯一具有外在超越性质的客观存在(实在)”[5]。这种内涵的“命”(天命)正是儒学思想道德本体之代表,“‘命’的观念是儒家对人生终极的严肃思考,是儒家思想中最深刻的、能将其和其它宗教最终区别开来的那个方面、那个关键之处”[5]。另一个关键之处则在于,面对道德本体之“命”,孔子不再是悲观消极地哀叹,而是乐观积极地强调了人应该去“知”的责任。其用语虽然十分简约,但已然奠定了传统儒学关于这一命题的基调。
践行—实践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促使不同素质、不同特长的学生扬长补短、各得其所。徐老师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有效性上大下功夫,她逐句逐段地培养学生阅读文本的能力,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再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小组团队解决问题的能力,近两年的坚持不懈与学生共同探讨磨合,学生被真正打开,所提问题的质量甚至超越了一般教师的思维范畴,同时小组合作的能力达到了教师可以退居幕后,而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同时,孔子“知天命”的说法也开启了后世儒学探讨“性”“命”关系的端绪①。因为,“知天命”问题一旦深入,就会涉及“何以能知”“谁来知”“如何知”的问题,这实际就进入“性”“命”关系的讨论。欧阳祯人教授指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6]。因之,儒学也就要更具体地探讨“命”和“性”的复杂内涵。
似乎正是为了清晰回答这一问题,由孔子之孙孔伋(子思)撰写的作品《中庸》开篇就写道:
再由定义7,仍从最底层并行工序任务串:①pts1和pts2;②pts3和pts4;③pts5和pts6开始,第③组已完工,不再考虑。第①组pts1,pts2的相对完成工时量为50-max{20,30}=20,第②组pts3,pts4的相对完成工时量为30-max{30,10}=0;对于第二层并行工序任务串pts5,pts6,pts7,其相对完成工时量为80-max{20+20,70,30}=10。则t4的相对完成工时量为40+20+10=70,于是涡轮部装任务t4的进度ra4=70/150=46.7%。
陈亮又举出孟子劝说齐宣王行仁政时的理论来说明儒学并不迂阔。齐宣王想要为自己不行仁政找借口,说自己“好色”“好货”“好勇”,都是一些贪图感官享受、鲁莽冲动的问题。但是,孟子并没有简单否定齐宣王这些问题,反而给予了称赞与鼓励。孟子让齐宣王从自身欲求感受出发,推己及人,在满足自身欲求的同时,也让百姓满足欲求;把自己鲁莽冲动的情绪不止用在发泄自身不满上面,也用在修正天下不公正的问题上面,反而会做成利天下的功绩。显然,孟子的劝说中确定的理论前提,就是认可了人性中感官享受、情绪释放的正当性。这也正与陈亮的主张一致。
按照前文所列举的郭齐勇教授所论来说,这里的“天命”所指的就是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本体。更进一步,作者通过“天命之谓性”的表述把“性”范畴强势引入。此时所论之“性”就是承接“天命”道德本体的应然道德主体,也正因树立了人作为“知天命”主体的地位,就回答了“何以能知”“谁来知”的疑问。紧接着“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两句,就回答了“如何知”的疑问。崔大华教授指出,“‘天’或‘命’这种外在的超越对象,也从周人的具有人格特征的、被虔诚信仰的对象,转变为一种可被理智体认的对象,进而通过道德实践的桥梁,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本身的那种对象”[5]。籍此,《中庸》作者基本建立了儒学关于“性”“命”关系在超越性这个层面的大致架构。
但是,这显然还不足以完全涵盖“性”“命”关系的全部内涵,因为“命”所具有的形下的现实限制这一层含义尚未说清。此亦前文所列举的陈来教授所论之关注点。对此,《中庸》提出“大德必受命”的说法:
砂石及水泥等材料应在搅拌站搭设遮阳棚,避免在阳光下暴晒,混凝土搅拌用水应尽可能采用温度较低的地下水,以降低混凝土的搅拌温度及入模温度。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3]225
在这里,作者借孔子之口,以儒家理想人物舜为例来解释,当个人达到超越道德境界后必然拥有最美好的生活环境的道理。其中,“大德必受命”之“大德”就是指个人道德主体的完成,“命”之内涵就涵盖了道德本体和个人现实境遇两方面的含义。从“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等语句可以看出,作者对“命”所包含的美好生活境遇十分重视。他不厌其烦地描绘舜不仅本人拥有的最高天子地位、最多的财富、最荣耀的名声、健康长寿,而且在死后还绵延不绝,有子孙世代祭祀其宗庙。作者这样详细阐述,就是要清晰地告诉读者“命”除了表示道德本体之外,还代表着极致丰盛美好的世俗生活。张岱年教授指出,此时的“命”,就不仅是消极之义,“还有积极的方面,即一事的成功也。所以命也可作为一种鼓励”[4]。但是问题在于,《中庸》作者的论证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作为证据,几乎无法拿到现实中来证实,反倒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这一隐患就是社会中的“缺德者”利用这种论证来掩盖自身的罪恶。也就是说,我们难以找到因为“大德”而享受最富裕生活的例证,而那些已经享受到极富裕生活的统治者、剥削者尽管实际上“缺德”,却仍可以大言不惭地论证自己是“大德”。造成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性”“命”范畴的复杂内涵需要进一步理清。
1989—1993年对路堤状态进行了专门的野外观测。测量了土的温度、水平位移、溢洪道侧墙的水平位移以及溢洪道侧墙的土压力。在深度为2.5 m处各项指标最大值为:温度30 ℃,膨胀压力-0.30 MPa,距墙15 cm处水平位移0.6 mm。在冬季坝顶深度为0.2 m处最大水平移动距离为4.5 mm(即溢洪道侧墙与土之间的裂缝张开的近似宽度)。
以上分析可见,“性”“命”范畴自诞生以来即表现出复杂内涵,很大程度上成为阐释这一命题的基础。
二、儒学阐释“性”“命”关系之“内圣”路径
正是在对“性”“命”复杂内涵的探寻中,儒学形成了阐释“性”“命”关系的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注重从道德主体修炼角度来进行阐释,即“内圣”途径;另一种途径则注重从社会制度建构角度来进行阐释,即“外王”途径。
从注重道德主体修炼的“内圣”路径来阐释“性”“命”关系以孟子为开端,后儒亦多有建言。具体来看,这种路径又可以分为主张“‘性’‘命’对扬”与主张“‘性’‘命’统一”这两种趋向。
(一)“‘性’‘命’对扬”的“内圣”路径
相比于孔子、《中庸》作者,孟子对“性”“命”范畴各自的内涵阐释更为详尽: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7]279
孟子在这段著名论述中的阐释被牟宗三先生概括为“性命对扬”[8]111,也即着重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以“性”之两层内涵对扬“命”之一层内涵。对于“性”范畴的两层含义,牟宗三先生指出,“依孟子,性有两层意义的性。一是感性方面的动物性之性,此属于‘生之谓性’,孟子不于此言‘性善’之性,但亦不否认人们于此言‘食色性也’之动物性之性。另一是仁义礼智之真性——人之价值上异于禽兽者,孟子只于此确立‘性善’”[8]111。概言之,“性”包含人的“实然”之性与“应然”之性。前者指人所具有的感官欲求,后者则是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要求。
而对于“命”范畴,孟子则只强调了一层含义——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牟宗三指出,“‘命’是个体生命与气化方面相顺或不相顺的一个‘内在的限制’之虚概念。这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亦不是知识中的概念,而是实践上的一个虚概念。平常所谓命运就是这个概念”[8]111。把“性”“命”两者放在一起来看,则可见“命”对于“性”的全面限制,“在道德实践中,于此两层意义的性方面皆有命限观之出现”[8]104。但是,正是在描述“命”对“性”的限制之中,孟子竭力推崇“性”之“应然”——即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要求。他这种推崇又展现为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来讲,他辨析“性”的两层含义,并以“君子不谓性”来坚决排除人的感官欲求这些“性”之实然。从主观来讲,他在承认“命”对“性”之应然有限制的基础上,以“君子不谓命”强调人在追求达到道德目标之时不去考虑客观的限制。显然,在这种论述中,孟子挺立起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应然属性是非常强大的,以至于基本可以忽略人的感官欲求和外在条件制约。
(3)平等保护和适时保护相结合的原则。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中,应将实际追缴到的财物依各被集资人资金损失的情况按比例分配。即使某一集资参与人就某项涉案财物设置了担保,其也不享有优先受偿权。集资参与人被退还的财物不足以清偿其债权的,在有第三人担保的情况下,其可针对担保人提起民事诉讼。为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应当在案件审结后立即对涉案财物依法处置,将赃款及时发还被集资人。
孟子这种思路的确对儒学挺立道德主体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正是在这种挺立之中,他的论证造成了理论矛盾。
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过,怨天尤人,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回于毫。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7]184
在此,孟子明显是在阐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其所谓“大德”与《中庸》原文含义一致,而其所谓“命”则与《中庸》所说的“命”就不太一样了。相比而言,他通过“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的说法将“命”只界定为“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这个层面。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把舜、禹、汤、益、伊尹、周公以至仲尼等儒学圣贤之命运遭际都拿出来讨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圣贤之地位不因其命运起伏而受影响(不谓命也)。对他们而言,不管是出身贵胄还是平民,不管执掌政权还是辅佐君王,不管人生顺利还是坎坷,都不对他们最终的圣贤地位产生阻碍。也即,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主要在于其主体追求彰显出了高尚的道德价值(有性焉)。
这样的论证是存在矛盾的。按其所言,如果大家不用管客观条件如何,只管努力追求道德目标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列举这么多圣贤的穷通遭遇。既然“命”对于个体的道德养成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还体现为消极意义,那就根本不用去管“命”的问题了。甚至可说,既然儒学圣贤的命运其实根本不具有价值意义,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了。
朱虹则在《走进全域旅游新时代》一文中提出,全域旅游发展的特性在于:管理的统筹性、产业的优势性、发展的融合性、供给的丰富性、服务的便利性和目标的共享性。
(二)“‘性’‘命’统一”的“内圣”路径
两宋理学家特别是朱熹对“性”“命”二者的形上与形下内涵都非常注意,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阐释“性”“命”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孟子“性”“命”对扬模式中的不足。崔大华教授指出,“宋代理学家在诠释、界定‘天命’时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天之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朱子语类》卷十四)”,“最终将‘天命’诠释为、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本身。将外在的‘命’内化为人之性,消解了‘命’的外在性、异己性,是儒学的超越理论的最大特色与最大成功”[5]。诚如斯言,理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以朱熹为例,他认定“天理”为万物之最终本体,这一本体赋予在人性上就是“天地之性”,即应然之道德主体。
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但得气之清明则不蔽锢,此理顺发出来。蔽锢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则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9]26。
这一“天地之性”也即孟子所说的“君子不谓性”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抽象的,无法单独实存,必须要借助人之身体感官才能存在。人的身体感官所具有的就是“气质之性”,也即孟子所说的“性也,有命焉”之“性”。可见,朱熹对“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似。而不同之处在于,朱熹承认了“性”必须是二者兼有,并未如孟子那样排斥“气质之性”,这就比孟子之说更显完备。
X1=[9 438.31 10 552.06 12 435.93 15 490.73 18 516.87 22 077.36 25 965.91 31 072.06 33 896.65 39 169.92 45 361.85 50 013.24 54 684.33 59 426.59 63 002.33]; %输入GDP(x1)
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说,天非苍苍之谓。据某看来,亦舍不得这个苍苍底。”[9]82
就统一性而言,“命”与“性”完全一致,都指向“天”“理”所代表的超越性道德本体;而就区别来说,“命”代表个体从道德本体那里已禀受的潜质,“性”则代表个体把这种潜质通过生命活动展现出来的程度。
道夫问:“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这处性、命如何分别?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将碗盛得来。大碗盛得多,小碗盛得少,净洁碗盛得清,污漫碗盛得浊。”[9]995
汽轮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电机转速为3 000 r/min,风扇叶片与风扇大小环之间承受复杂的交变应力动载荷[1],因此对风扇强度要求较高。美国西屋、日本三菱等国际大公司的无刷励磁机离心式风扇均采用焊接方式[2]。我公司设计的70 MW汽轮发电机励磁机风扇也为焊接结构,其焊接空间狭小,风叶较薄,焊接容易产生变形,加之母材为80 kg级高强钢B780CF,焊后退火会大大降低材料的冲击韧性等性能,因此选用合适的焊接方法、材料及工艺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的比喻更清楚,将“理命”比作流动之水,代表个体已具有的潜质状况;同时,将现实中个体之“性”比作盛水之碗,代表人实际上可以实现的程度。换句话说,即使个体先天在“命”上的禀受有差异,但个体最终成就如何还要取决于在“性”上的努力(将碗盛得来)。显然,这是对道德主体修炼极大的鼓励。牟宗三先生指出,“圣人都是体证天道者,但体证得有多少,以何方式来体证(耶稣之方式乎?孔子之方式乎?释迦之方式乎?)这都有个体生命之限制。是故孟子总说:凡此皆是命,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不是说仁义礼智天道本身是命,而是说它们之能否得其表现,表现得有多少,是命。它们本身皆是性分中之事”[9]112~113。牟先生之言是在解释孟子,但严格地说,牟先生此处解释用在朱熹思想上更合适。
以此而言,朱熹(包括两宋理学)就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改成了“大德必受‘无关贫富穷通’之命”。显然,这仍与儒家经典原义有差距,也是朱熹“‘性’‘命’统一”思路的困境。
问:“先生说:‘命有两种:一种是贫富、贵贱、死生、寿夭,一种是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一种属气,一种属理。’以僩观之,两种皆似属气。盖智愚、贤不肖、清浊、偏正,亦气之所为也。”曰:“固然。性则命之理而已。”[9]30
“‘命’之一字,如‘天命谓性’之‘命’,是言所禀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禀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9]31
朱熹此处论述涉及“气命”之说法,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命”究竟有无“气命”的问题?一种观点是肯定“气命”的存在。赖贤宗指出,“以气言命,命指气化之限定,即命限的意思,是形而下者”[10]。这里的“气命”即孔子论“命”所包含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限制含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朱子不讲“气命”,只讲“理命”(性命)。赵金刚指出,“朱子始终不认为气可以成为命,认为不能用气来命名‘命’”[11],“当学生强调‘命’与‘气’的关系时,朱子始终要把理(性)提出,强调命与理(性)的关系”[11]。这里的“理命”(性命)即前文所言那种代表形上超越本体之“命”。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如果我们对照上面朱熹原文来看,可以说,朱熹在这个问题上是充满犹豫的。一方面,以其“‘性’‘命’统一”的理论架构来说,他不能承认“气命”的存在。因为“气”在其思想中不具有超越性,一旦“气命”成立,势必破坏“命”的形上超越地位。但另一方面,当他面临《中庸》论“大德必受命”时遇到的难题时,他又必须承认“气”对“命”的影响。
门人问:“得清明之气为圣贤,昏浊之气为愚不肖;气之厚者为富贵,薄者为贫贱;此固然也。然圣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气,宜无所亏欠,而夫子反贫贱,何也?岂时运使然邪?抑其所禀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禀得来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圣贤,却管不得那富贵。禀得那高底则贵,禀得厚底则富,禀得长底则寿,贫贱夭者反是。夫子虽得清明者以为圣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9]210~211。
在这段对话中,门人之问正是“大德必受命”中的老问题:怎样解释孔子等圣贤没有获得财富、权势等尊贵世俗生活?朱熹只能把类似东西归结为“气”之“厚薄”“长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说到底,朱熹是通过将富贵、长寿、尊贵这些世俗生活划在“命”之外来应对问题。但这未必符合《中庸》经典原义。与前文所言孟子的问题一样,如果富贵、长寿、尊贵完全与“命”无关,那么,《中庸》作者为何偏要在“大德必受命”的论述中大书特书这些内容呢?
总体上看,家庭、宗族、社区、政府等均为农村养老提供了资源供给,而家庭是主要的供给者,政府一直都充当着有限养老供给的角色。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供给者,不能只满足农村地区最低限度要求,而是要成为主要供给者,为农村养老提高充分的制度支持与资源支撑。
三、儒学阐释“性”“命”关系之“外王”路径
从道德主体修炼来阐释“性”“命”关系的途径有其理论意义,而同时也有其绕不开的弊端。这种弊端即催生了儒学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的“外王”途径。
(一)君循礼制基础上的“‘性’‘命’统一”
作为众所周知的儒学事功学派,陈亮注意到了从社会制度建构来阐释“性”“命”关系的途径,他的核心论证就是以君长遵循儒家礼制来行使权力,在此基础上达到“‘性’‘命’统一”。
陈亮的切入点正是孟子所说的“性也,有命焉”问题:
而朱熹对“命”的论述就比孟子论述得复杂一些,其论带有“统一中有区别”的特点。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12]153。
在这里,陈亮肯定孟子所界定的“命”之内涵,认可“命”是一种对人之口、目、耳、鼻等感官享受的现实限制。那么,如何面对“命”这种限制呢?前文已分析,孟子提出“君子不谓性也”的主张,通过把感官享受排除在人之应当追求的本性之外的方式让人们不要在意外在之“命”的限制。陈亮则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对这种“命”的探讨:
富贵尊荣,则此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故天下不得自询其欲也;一切惟君长之为听[12]153。
陈亮的解释将感官享受与价值观之荣辱关联起来,认为感官享受之满足就是一种尊荣;反过来,感官享受之缺乏就是一种屈辱。同时,这种荣辱与夺的权力不得个人自己行使,而是委之于有权力的君长。显然,这个论点在孟子或理学看来,无异于石破天惊,似乎在偏离儒学宗旨。但陈亮进一步的论述则证明并非如此。
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12]153。
陈亮认为,君长并非行使掌握荣辱与夺的权力,而必须要凭借“经典”“礼制”的规定来行使。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人的荣辱、利害虽然表现为君王的举措,但其源头则是礼义秩序。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乡村振兴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实践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观念新颖、技术先进、理论要求高。这无疑是地方高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切合点,是高校人才锻炼和理论知识应用的最好平台和机遇,同时也有利于高校综合办学质量的提高。
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报,谓之劝惩。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岂以利而诱之哉!为恶者受其所同恶,岂以威而惧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12]153。
陈亮指出,一个人表面是获得君王执行的赏罚,实质上是获得了自身言行的回报。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就是让人之道义实践与感官享受统一起来,让“性”与“命”统一起来。也即,做善事者同时获得好的感官享受;做坏事的遭受严厉的感官肉体处罚!这不是用利益诱惑或者用权势威胁,而是因为这本就是人性内涵。换句话说,如果做好事者总是处于困窘,没有感官享受,反而做恶事者总是享受荣华,这就是违背人性的情况。
当然,陈亮也注意到这种论证容易让人联想到为君主辩护的问题,他也对此作了充分解释。
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善恶易位,而人失其性,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后世之用赏罚,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非赏罚人人之浅,而用之者其效浅也。故私喜怒者,亡国之赏罚也;公欲恶者,王者之赏罚也。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霸者之术也[12]153。
陈亮指出,天下人之“命”系于君王之执掌,就要防止君王以个人私心中的喜怒来运用这一权力。如果君王将刑赏权力当做个人所有来行使的话,正是失去人性的表现。孔子早已对此有预防,其著《春秋》就是要界定“赏罚”权的公共属性,也是对人性的恢复。从这个角度出发,陈亮清晰地判定了“赏罚”之本与“赏罚”之用的区别,“赏罚”之本是顺乎人性,劝善惩恶的重要举措;但是“赏罚”之用却出现了部分君王以之为一己之私服务的问题,这是使用上的错误,不能因此否定“赏罚”本身。顺乎人性来“公赏罚”是王者之举,为一己之私行“赏罚”才是霸道之举。因之,如果完全抛弃“赏罚”举措追求王道,乃是迂腐之儒。
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齐宣王之好色、好货、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谁不好勇,而独患其不大耳[12]154。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213。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天佑下民而作之君,岂使之自纵其欲哉,虽圣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12]154。
第一,阳明通过论述圣凡“同心”理念奠定论证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儒学的“‘性’‘命’统一”的“内圣”路径。
从这种“性”“命”一致的思路出发,陈亮描绘了他所认可的儒学社会制度构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一方面,这种状态符合天地本身“类聚群分”的道理,贤能者自然应在上为君王、为宰相,这绝非人之私意所能决定。另一方面,这种状态有外在的检验标准,这就是百姓之安居与万物之和谐生长,也并非任何人主观想象可以决定的。
从这个角度看,孟子已经把《中庸》“大德必受命”的命题改成了“大德必受性”(而无关“命”)。不能完全解释儒学经典的问题,正是孟子“‘性’‘命’对扬”思路的困境。
可以说,陈亮的这种论证应当是儒学追求的理想状态之一,如《大学》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陈亮的解释有理有据,与理学主张相比,确实别开生面,也有很好的可操作的现实方法。但其唯一的缺憾则是太偏重物质需求,容易滑落为完全没有理想指导的权谋手段。
(二)“同心一德”目标下的“‘性’‘命’统一”
明朝的王阳明属于广义的宋明理学大家,但若与朱熹之理学相比,在治学途径上还是大有区别。他从“心”学基础出发,提出在“同心一德”目标下进行社会制度建构,以此达到“‘性’‘命’统一”。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这就是他迟到的原因。)why只用于reason之后的限制性定语从句中,在定语从句中做原因状语。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13]115。
综上所述,在计算能机网络中进行安全管理,不仅需要管理者加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培养安全意识,还需要积极进行对网络技术的发展,不断的进行对技术层次上的漏洞进行防范,提高网络安全的系数,促进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运行。
在这里,阳明论证的逻辑是肯定圣、凡之“心”相同,但各人由于追求物欲而产生“私”心,进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甚至会将至亲的父子兄弟当作仇人来看待。显然,他使用的范畴没有“性”“命”,但问题却仍在儒学“‘性’‘命’”关系之内。相比较而言,他所说的圣、凡相通之“心”,正是孟子所言之“性善”、朱熹所言“天地之性”;反过来,他所说的人在物欲诱导下所产生之“私”心,即是孟子所言之感官欲求之“性”、朱熹所言之“气质之性”。而他所说的亲人之间互为仇敌的状态,则属于一种“性”“命”分离的状况了。这种状况如何解决呢?阳明指出:
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3]115。
既然天下之人原本之“心”是相通的,那就应该在圣人指导下克私、去弊,复归本“心”。从这里看,阳明的主张与孟子主张的“君子不谓性”路径、朱熹主张的“穷理尽性”路径有相似处,带有“内圣”路径色彩。
第二,阳明通过在“同心一德”基础上的构想,从专业化、职业化角度详尽探讨了“外王”路径对“‘性’‘命’统一”的保障。
首先,阳明构想了个体“成德”的专业化机构——“学校”。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3]116。
阳明之论在此有两方面突破。一方面,他通过引入“学校”机构为个体道德养成提供场所与环境,正是由“内圣”路径转到“外王”路径上的关键;另一方面,他在学校培养的素质之中,除了儒家十分看重的“礼乐”“政教”等道德禀赋,亦有“水土播植”等传统儒家并不太看重的专业技能禀赋。此为“外王”路径可以展开的条件。
其次,阳明还提出构建让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的职业化道路。
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13]116。
他所说的“举德而任”理念一贯以来也是儒学所强调的政治举措,但阳明的创造则在于并非就“举德而任”泛泛而谈,而是挖掘出其中所可能引申出的职业素养、职业信念——使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可以说,这正是“外王”路径所极需要的职业化道路,极其充实地阐释了“外王”路径的全部内涵。一方面,“外王”代表“德”之外化,一定要在社会中展现实际的功效。那么,一个社会人人“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的职业状态正是一种功效的体现。另一方面,“外王”不能脱离“德”之指导,“同心一德”理念就为社会提供了本体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无论是“用者”(执政者),还是“效用者”(普通民众),大家都不再以单纯的“功利”标准来衡量职业高低。“用者”(执政者)注重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任用臣属通过他的才干判断是否称职,而不凭地位的高低来分重轻,更不凭借其所从事职业来分美丑。“效用者”(普通民众)同样也以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为目标,注重自己才能与岗位相称,(假设某人之才能适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即便终生从事繁重工作,也并不以此为辛苦;(假设某人之才能适合做相对卑微的工作)即便从事卑微琐碎工作也不以此为低贱。显然,这是儒学认可的“外王”理想图景。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13]116。
这一图景的基础就是人人明白“同心一德”的道理,按照各自才能禀赋各安其位,为社会提供必要的供给。同时,人人充分明白各自职位之价值,都全副身心投入自身职业创造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别心,亦无消极怠惰之心。钱穆先生对阳明之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既理想,又具体,实足悬为将来人类社会所永远追求的一远景”[14]。钱穆先生以阳明主张为人类社会理想之评价或有过誉之处,但若从儒学所讨论的“‘性’‘命’关系”问题来看,阳明确实做了充分解释。
整体来看,阳明此论以“心”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同心一德”之目标统摄了儒学“性”“命”关系内涵,既注重了个体道德修炼的“内圣”路径,更注重社会制度建构的“外王”路径,达到高水平的“‘性’‘命’统一”。安靖如教授在研究相关思想时指出,“当个人的道德活动在政治生活中融合在一起时,政治从中产生,而且,最终需要某种政治架构作为更完整道德的实践的间接手段”[15]。此评价用于阳明之论亦颇多启发。从“性”角度看,圣凡同“心”“性”,个体先天的“禀赋”不重要,关键在于后天践行道德的主动性上面;从“命”角度看,就要求个体与社会都要按照符合“同心一德”价值目标来实践,就可以创造足以保障天下和谐之状况,也就是使得各人客观之“命”得到保障。在此情形下,孔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的感叹中对“命”所赋予那种无可奈何之感受已经被极大地稀释,而儒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亦得到极大地彰显。
综之,“性”“命”关系是贯穿传统儒学发展历程的重大问题,其所包含的复杂内涵及“内圣”“外王”的阐释路径亦是儒学思想重要之特色。今天,我们回过头审视儒学的这一传统问题,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用心,更有助于在现代化视角下吸取其经年累积所形成的思想智慧。
注 释 :
①孔子除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外,基本未直接谈论“性”的问题,如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故此,他对“性”“命”关系进行的是间接探讨。
参考文献 :
[1] 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篇初探[J].孔子研究,1998,(3):52-60.
[2] 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3] 杨逢彬,欧阳祯人.论语大学中庸译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28.
[5] 崔大华.人生终极的理性自觉——儒家“命”的观念[J].孔子研究,2008,(2):4-11.
[6] 欧阳祯人.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J].孔子研究,2000,(3):58-65.
[7] 杨伯峻,杨逢彬.孟子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16.
[8] 吴兴文.圆善论[M].长春:吉林出版公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9]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 赖贤宗.义命分立、性命对扬与义命合一——中西哲学对话中的孔子儒学关于“命”之省思[J].哲学分析,2017,(6):40-56.
[11] 赵金刚.朱子论“命”[J].中国哲学史,2015,(3):103-110.
[12] 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宋元明清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13]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译注集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 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86.
[15] 安靖如.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56.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9)05-0114-09
doi: 10.3969/j.issn.1672-626x.2019.05.012
收稿日期 :2019-04-29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8Q136)
作者简介 :谭绍江(1981- ),男,湖北恩施人,湖北经济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涂爱荣(1970- ),女,湖北鄂州人,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儒家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彭晶晶)
标签:儒学论文; “性“”命”关系论文; 途径论文; 内圣论文; 外王论文; 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