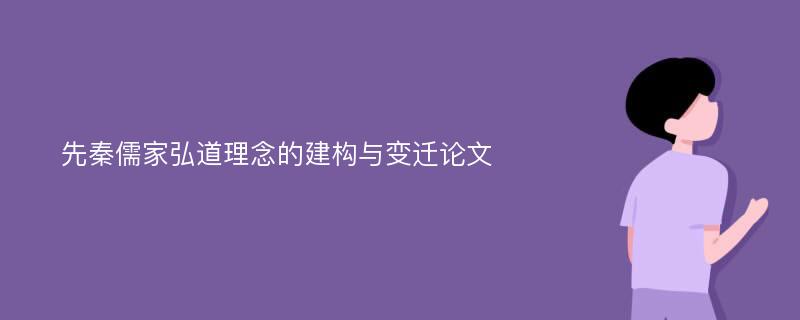
先秦儒家弘道理念的建构与变迁
周学熙
(阿坝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汶川 623002)
摘 要 :自孔子开创出早期儒学顺时因类的弘道理念,并在其所主导的周代哲学突破中成功运用起,直至战国的孟、荀仍在“修己安人”的授业理想中贯彻此一精神,但在春秋以降政治体制与学术趋向不断变革的背景之下,孟子作出的理论调整因未能突破原有心性——境界论框架而成效不佳,原始儒学最终经由荀子逐渐拓展为适合形势的兼综之学。其过程中延续夹杂变革,授业边界从心性修养拓展至政治实践,既顺应战国实用主义抬头的学术形势又坚持对形上世界的关注,应当是孔子至孟荀间儒学弘道理念的大致变迁状况。
关键词: 孔子;孟子;荀子;弘道
先秦时期儒学的形成与传播,在文化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早期儒学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显学的过程中,其始终与时偕行的弘道思路尤其值得关注。①伴随春秋以降的历史推进,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孟荀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采取的弘道手段也有所不同,但就其目标而言都是竭力弘扬圣贤之道,且在不同阶段都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多瞩目于孟荀因各自人性论观点分歧所开出的“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与“化性起伪”“知通统类”间的逻辑冲突以及“仁义”与“礼法”之间的手段分别。但不容忽视的是,大体发生于孔子时代的“轴心突破”,乃是先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转折,对学术与社会影响巨大,而以往学者对这一背景因素及其与王权观念和学术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够,譬如从孔子到孟荀之间的早期儒家究竟是在何种内在逻辑的指引之下,又是通过何种理论调整使其学说不断适合于变化的历史与现实政治背景之中,皆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梳理相关文献,缕析孔子及其后继者在时代变化中就其弘道思路做出的种种尝试与改变,以期藉此揭示先秦政治与学术形势变迁对于早期儒家弘道理念的建构与调整过程的深刻影响,管窥早期儒家弘道思路变迁的总体轮廓。
(27)攝制魔蹤:鎮伏魔勞,大刑攝擯。(《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三,《中华道藏》30/554)
从工业到医学研究,像这样的激光器应用范围很广。然而,穆鲁和其他人员已经意识到,这些高功率激光器可以作为一种全新的方式,将粒子加速到高能量,而BELLA正是用于这方面的研究。科学家梦想有朝一日:这些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可以缩减粒子物理实验的规模,以至于不再需要像瑞士大型强子对撞机那样的大型基础设施。总有一天,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可能会出现在日常环境中,可以作为一种癌症疗法,利用其中的粒子靶向和损毁肿瘤。在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背景介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到了激光等离子体加速技术和BELLA。
一、顺时因类:切中肯綮的“性与天道”
在孔子时代,早期儒学的基本纲领业已形成,并形成了学术流派。用《礼记·中庸》里的话说,这个基本的纲领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简而言之便是“天道性命”四字。余英时称孔子为“中国轴心突破的第一位哲人”[1]便是因孔子孤明先发,将属于凡人的“性”与作为三代以来指向终极信仰与意义的“天”通过其所创造的全新的哲学概念“道”联结起来,让普通人得以从理论上突破殷周以来被最高统治者以占卜、祭祀甚至血缘等手段垄断的“天人之际”,再让门生们担负起教人修“道”引人证“道”并最终去追索“天人合一”的终极精神境界的学问(也就是余英时称之为“内向超越”的过程[1]),亦即是期望造就一个人人慕“道”修“道”的君子天下,子路曾经问孔子说君子该如何作为,孔子这样答复他: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
自我的修养究竟要修到何种程度?众所周知,孔子的最终目标是“仁”,而“仁”似乎是一个不太具体的概念,孔子没有确说,后来的学者则大概将其解释为“统摄诸德”(蔡元培语)[1]。但孔子曾在与颜渊的一次对话中交代了作为衡量尺度的“礼”说“克己复礼为仁”,并强调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明确了“仁礼合一”的方法论。然而子路似乎对孔子的答案并不满意,孔子所谓“敬”的对象应是“道”或“天”(这两个概念在孔子之后往往可以互相代用),但子路感觉“修己以敬”并不是终点,于是继续向孔子发问。
(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学而知不足,教后而知困”。只有不断反思我们的教学,才能知得明失,不断的提高。之前笔者参加了一次评课比赛,课题是《二次函数》。这是一节概念课,这节课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反映等几方面情况看效果都不错,课后也得到了评课教师的一致好评,于是笔者开始思考如何开展数学概念课教学。以下是笔者反思所得。
显然孔子其后的回答已不是在向子路解释如何去做君子,而是藉子路的追问,表述出了更高级的追求和愿景,这一愿望便是落于“弘道”之上的“修己安人(天下)”。在孔子构建的人性论体系中,“君子”高于常人而低于“圣人”,我们注意到在孔子的话语中,并不存在某个可供瞻仰的具体“圣人”,而更像是一个掺杂旧有天神信仰与其全新的“道”论中终极精神成就的混融体,甚至连尧舜这样的古圣王,在孔子的标准下,也不够称之为“圣人”。
为缓解这一窘局,密集烤房生物质燃烧机应运而生。生物质燃料来源广泛,制作工艺成熟,简单可靠,可以变废为宝,实现工厂化生产,近年来已经大量用于节能自动化烘烤中。而且燃烧充分污染少,可以实现智能化烘烤,把烘烤师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用长时间值守在烤房旁边。
我们看到孔子在与学生的上述几段对话中始终在强调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圣人意味着终极追求,或者是圣人就近似于真理本身,如在《论语·季氏》中孔子便将“圣人之言”与“天命”并列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易传·观》中也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其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我修养,以“仁”为标准,以“礼”为约束,让自己至少能走在成为“君子”乃至“圣人”的路上;最后,圣人除去在个人修养上臻于完美外,一定要有“济众”“达人”“安百姓”这样高于一般“君子”的作为,亦即是说儒生的终极愿望乃是弘道于天下,此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合于“修己安人”之说,可谓是建立在儒学“天道性命”基础之上又一基本纲领。
在《论语·公冶长》中,子贡曾描述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如前所述,孔子既构建了“道”这一处全新的哲学概念并将其置换到旧有的鬼神信仰之中作为其终极价值的新表征,并且希望将这一“修道”的理论弘于天下,又为何罕言性与天道,甚至在面对固鬼神信仰时还抱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的模糊态度。究其缘由,概与孔子在传道弘道中遵循“顺时因类”②的思路是完全契合。笔者曾在旧文中将“祭神如神在”的逻辑解释为“孔子构造了“圣人”的理想境界及其所依存的“神道”的价值,但孔子从未声称自己抵达了“道”的境界。实际上也没有人抵达过“道”的境界,就如同没有人见过神明一样,人们所“祭”所“求”所“见”的其实都只是出于某种对于“神在”或者说“道在”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依存于鬼神时是宗教,依存于心性时便是“圣人以神道设教”了,因此“祭神如神在”实则在说“求道如道在”……或是“慕圣如圣在”[2]。故而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并非是道不可说,而是如何去说的问题,孔子是不刻意、抽象地谈性与天道,而是极其巧妙地顺应了时人自旧时代的天神信仰中延续而来的思维惯性,将对天神的崇拜与祭祀礼仪转化为对更生动的“圣人”境界的追慕与向往。因此可以说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对礼乐制度的特别关注同样映射着这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其顺时顺势的弘道思路。在孔子及其所引领的“轴心时代”到来之前,殷周时人大约已在对天神权威的崇信与祭拜中度过了千年以上,按《说文》释义,最初的“礼”便是“事神致福”之礼,儒学中对于礼的强调实际上亦是顺应时人长期而普遍的思维惯性,从而使其更为舒适地接纳“圣人”之“道”。换言之,可说孔子对于“圣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乃是一次极具创造性的发明,其将纯粹哲学性的“道”巧妙转化为更容易被时人理解的“圣人”,相较于从前冷酷的天神权威,自会有更多人愿意选择并聚集在一位极具包容性的“圣人”身边。而更重要的是,在“圣人”的身边不仅有平民,更有一批迫切希望突破旧有“天人障壁”的贵族甚至国君在内,这些人也是孔子及其门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孔子主张“以道事君”(《论语·先进》)便是希望自家学术被贵族君王所接受,依靠台前的君主自上而下去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故而向来所谓“内圣外王”之“王”绝非是落在现实政治,也不是落在礼义人伦之上,而是落在以道事君——赖君弘道的理想逻辑之上。
情况 3.2 {4,5}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则C2∪C3中至多有5个集合,设为D1,D2,D3,D4,D5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且C2中至少有一个集合是Y中顶点色集合,不妨设{1,2,5}是Y中顶点色集合,可得:至少有两个C(ui)包含{1,2},其它C(ui)包含{1,3}或{2,3},由于C(ui)≠C(vj),从而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2},{1,3},{2,3},{1,2,3},D1,D2,D3,D4,D5,矛盾。
具体而言,在孔子之前的数百年里,王权政治走向衰落,诸侯乃至卿大夫所代表的君权政治逐渐崛起,期间出现了齐桓晋文等一时霸主。但春秋与战国政治体制间有一处关键不同,春秋时期的列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认同周天子,其结果便如雷戈曾指出的,在春秋时期“只有天子能祭天,诸侯不能直接通天,故而诸侯还不能真正的享有天命。这样,君主制具有一种世俗身份,国家只是一种世俗存在,君臣关系只是一种世俗关系。君臣关系的这种世俗性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人们对君主所普遍持有的不恭敬态度,它使得人们对君主的蔑视和憎恶常常不加掩饰地以弑君或逐君的方式表现出来”[3]。像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或许有国家有社稷,却仍然无法从严密的宗法逻辑中获得任何的权力合法性。而孔子及其新的天人哲学的出现则几乎完美地化解了这一难题,并给了赖以维系天子神圣性的天神权威最后一击,长期为此苦恼的诸侯们也自然乐于接受并希望更多人认可这一理论。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孔子时代的早期儒学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祭神如神在”或是“以道事君”实则都可归溯至同一出发点,便是以最能贴近时人思维立场与精神需求之处,作为“道”的载体,亦可归纳为同一方法论,便是“顺时因类”的工夫。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及至战国汇成孟荀两派,彼时思想史上轰轰烈烈的轴心时代延绵了数百年,社会思潮与现实政治业已几经变迁,“三家分晋”之后的周天子已无任何实际或形式上的权威可言,唯独此种顺时因类的弘道思路仍在孟荀的实践中得到延续与发扬。
二、“仁者无敌”:理想主义与弘道愿望的艰难平衡
按学术史上一般的共识,自孔子殁后到战国的孟、荀之前,早期儒家经历了一个分裂与重整的时期。关于这一阶段的文献遗存,我认同李学勤曾指出的在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4]。而在郭店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孟之间影响最大的曾子及子思一系对于前述孔子“以道事君——赖君弘道”逻辑的继承:
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郭店楚简《成之闻之》)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郭店楚简《缁衣》)
2017年建立马铃薯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135.38 hm2,标准覆盖率100%,涉及农户852户,实现总产量444.65×104kg(单产32844kghm-2),总产值449.24万元;新增产量68.0×104kg,新增产值97.98万元,农户年增收入1150.0元。辐射示范1200hm2,涉及农户7800户;常规种植区马铃薯单产25308.75kghm-2。通过示范区建设及辐射,增加了农民标准化生产意识,激发了农民种植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马铃薯生产标准化水平。
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子·不苟》)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荀子·天论》)
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始则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
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
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人皆可以为尧舜……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我们能看到在《孟子》中,许多曾经不甚明朗的概念如“仁”“圣”都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阐释,这种调整正是为了适应时人精神领域的需求变化,殷周以来的的天人障壁已被打破许久,时人钻研圣贤之道已不是为了填补当初“天神”跌落后的精神缺位,而是希望得到更为实际的体悟或效用,因此孟子将孔子不曾具言的“性命之道”从天际拉至人间,应是孟子的为弘道所做的第一次顺时顺势的调整,但这次调整并未突破孔子以来的旧框架,而是针对有志于求仁问道之人进行了一次“重点辅导”。但孟子所在的时代,战乱较之春秋时更为频繁惨烈,列国的君主们也早已称王,无人再去理会莫须有的“合法性”问题,甚至思想家们已多不再纠缠于天人逻辑之中,因此单纯依靠细节调整仍不足以契合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焦点,故而孟子为此又推出了另一次更为大刀阔斧的理论创新,即将原本主要指向心性修养工夫的“仁”的概念外延明确拓展至“政”,以期藉“仁”与“政”的融合打动希望治国安邦的梁惠王,但梁惠王对孟子的王道仁义并无兴趣,战乱中的国君所关心的只是强国之策:
一闷棍打得镇长半天寻不到话头。他早把这事忘了。这家伙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自己原本是想打发他离开会场,莫搅了庆典。一来怕上头怪罪,二来什么事情总寻求个开门大吉,怕触霉头。谁知这家伙真就顺杆爬,没病没灾住到卫生院居然就不出来了。有吃有住还不用花钱,谁不愿意呢!问题是一般人谁敢这么做?但这是牛皮糖。没由头要找个由头白吃白住,有了镇长的指示,他能放过这机会么?!啊!镇长伸掌在自己的头顶拍了一下,差点没把自己拍成脑震荡。但镇长拍过,眼前冒的金星还没消失,他却晕晕地笑了。我差点忘了。是有这么回事。那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啦?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在魏国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使惠王相信“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整段对话中孟子只字未提心性、天道、圣人等问题,显然是针对梁惠王的身份和需求做过思考与准备。虽其结果并不理想,但却仍可以反映出孟子能够为弘扬其道而作出顺时因类的调整与努力。唯是早期儒学作为心性道德之学的底色过于浓重,使孟子这样一个极具自信且对孔子性命之道十分崇尚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从自身突破其局限。
综合来看,作为一个与“匡人其如予何”的孔子相近的理想主义者,孟子因其所处时代的缘故,虽自理论上作出过一些调整和创造,但囿于其对形上追求的执着,始终难以与当时学术社会的焦点相契合,故其作为以弘传圣贤之道为己任的儒者而言,可以说较孔子更不得志。
三、《荀子》的批判、兼容与突破
与身具明显理想主义情怀的孔孟不同,荀子偏向实用主义的性格特点与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使其能够更好地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适应,将法术刑名之学纳入儒学的框架之内,对其后的儒学发展理路带来了相当的影响。就荀氏的学说而言,历来注释家虽视荀学为儒家之歧出,但其学术根底仍是出自于孔子门下的,与孟子之间在人性论领域的分歧毫不影响二者在对于早期儒学“修己安人(天下)”根本逻辑的认同。首先,从这一逻辑的起点看,孟荀几乎用相同的话语明确认同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平等观念,这种认同在《孟子·告子下》中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在《荀子·性恶》中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而对于如何作“为”,孟荀同样肯定人心的作用,看重修炼人“心”的过程,并肯定持续学习的意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荀子·不苟》)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的此番调整将方法论的阐释作为重点,一改《论语》中对形上概念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如孔子论“仁”时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虽将“仁”指向内心,但却没有像孟子直接具体地说“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又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其中有概念也有方法。再如孟子论圣人时尽管也从境界上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但却明白列举了诸多往圣如“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接着又进一步将上述鲜活的“圣人”们请下“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传·系辞上》)的缥缈神坛,回到人间做起了可望可即又可“复制”的“老师”:
王爱国:为规范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确保质量效益,促进工程良性运行,2013年,我们除抓好规划等基础工作外,还着重强化了项目建设监督、基层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
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如前所述,在《论语》中孔子的“圣人”标准可望不可即,孔子不曾亲口承认有人抵达了“圣人”的境界,而是将“圣人”作为终极人格典范,与天、道、性、命等一切哲学概念并列在可望不可即的哲学“神龛”之上。彼时的“性与天道”大体上是朦胧的,只可意会的,人们需要的也恰是这种朦胧的宗教意味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包容性的融合,方能藉此无缝填补在天神权威崩塌后的精神空位。然而在《孟子》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无论是人性论中的“君子”“圣人”还是境界论中的“仁”“道”都逐渐被赋予了细节,形成了更具体更可靠的方法论,我们可以将此看做孟子面对新的社会历史形势做出的一次弘道思路的调整。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其次,从作为逻辑终点的“性与天道”论,荀子同样肯定其终极价值:
下面的访谈资料讲述的医学叙事和共情,发生在作为医者的活佛和作为患者的学生之间。曼巴扎仓的学生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志于藏医的农牧民子弟;二是寺院收留下来的孤儿;三是因病学医者。德钦是来自恰卜恰一个单亲家庭的姑娘,跟母亲过。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厘清的是,孟子这个人虽生在战国,但其学说却有着很浓厚的春秋底色。所谓“春秋学术底色”,便是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轴心时代”思想家对于天道性命之类的形上命题有的执着追求。而到了战国时期,“轴心时代”的帷幕虽还没有完全落下,但由于激烈的兼并战争催生出实用主义学术倾向,逐渐取代天人关系成为新兴的学术焦点并为列国统治者所重视。而我们在《孟子》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如“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这样与《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出一辙的话语,因此在《孟子》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甚至比孔子更为理想主义的儒家在与之矛盾的现实学术趋势中不断寻求艰难平衡的过程。
孟子之学上承子思又有所发微,在《孟子》的文本中,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做为夫子之学的坚定后继者,孟子不仅在《滕文公》《梁惠王》中践行“以道事君”的弘道理念,亦在进一步拓展孔子“性与天道”的形上命题上花费了极大的功夫,为孔子的天道性命之学继续发扬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对此笔者认同余英时的阐释说“‘道’在‘心’中,‘知天’必先通过‘尽心’‘知性’一道转折,这是孟子为儒家的内向超越所开示的基本方式”[1]。如前所述,在《论语》的语境中,个体修养并非是圣贤之道的终点,弘道于天下才应是儒生的最终愿景,也更应是有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样自信与使命感的孟子的最高理想。那么值得探讨的是,孟子致力于心性论上的拓展如何与此弘道愿望相关,其对于孔子顺时因类的弘道精神的继承又体现在何处。
(3)在城镇化、信息化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城镇化发展不仅要快,更要好,要智慧,“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不仅经济要智慧,建筑、移动、能源、规划、治理都要智慧。“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综合协调政、产、学等各方资源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最终实现“智慧城市”服务于民生。
此处关于“天功”,《荀子·天论》中另有一段说:“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不求知天”亦可以“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作解。荀子主张“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并非是否定“天”的终极价值,而是暂且回收好高骛远之心,只将眼前“修己以敬”的功夫做好,方有机会抵达“全其天功”的境界。
此外,从“圣人”观念看,荀子也与孔孟同样认可作为人性论中完美样本的“圣人”与“道”有着同等象征意义,并肯定其不可替代的模范作用:
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荀子·臣道》)
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
最后,荀子的“圣人”也与孔孟的标准一致,即在“修己”的基础上“博施济众”: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 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大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荀子·君子》)
于造模后第7、10、14、21、28天时按AI评分标准[7]评价各组大鼠的关节炎严重程度:关节无红肿计0分,趾关节红肿计1分,趾关节和足跖肿胀计2分,踝关节以下的足爪肿胀计3分,踝关节在内的全部足爪肿胀计4分。每个关节最高得分为4分,4个关节得分之和即为每只大鼠的AI。
因此,就早期儒学“天道性命”“修己安人”的根本纲领而言,同为儒家的孟荀之间始终有着足够的前提认同,而其人性论的分歧之处实则是一个工夫论的区别,就是人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去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是“尽心知性”的内力,还是“化性起伪”的外力。《荀子·性恶》篇云“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然孔子讲“为仁由己”,又说“克己复礼为仁”,此“为”,与孟氏“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为”尽皆相同,都是用功夫去做的意思,其中不同只在孟子将重点用在“心”内之“为”,做“尽心尽性”的功夫,荀子则自同一出发点开出另一条通路,将功夫用在“心”外之“克”上,克便是克己制欲,化性起伪。孟子认为“善”是内在的,所以要克制后天的不好的东西,从而去达到“率性之谓道”。荀子则是以恶为与生俱来的,但人性之中还包含着一种“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也就是人性虽“恶”,却在天性中有着可以知善、向善的能力。荀子就是要求人用这种能力去克制住人性中不好的东西,再去积累好的东西,从而积善成德,最终达到那个境界,所以说他亦是做戒慎恐惧的功夫,最终也与孟氏殊途同归于“天道性命”之处:
NLRP6炎症小体在肠道组织中表达较高[28],参与调节肠道以及内环境菌群稳态。因此,一般认为NLRP6是NLRPs炎症小体家族中特异性调控肠道炎症的一类炎症体[36]。也有研究发现,NLRP6信号在不同的细胞类型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NLRP6调控炎症小体依赖及非依赖功能通路[37]。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 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
而孟荀真正分别之也在此处,上段所列修身手段中“礼义”本是孔孟故论,与之并列的“法正(政)”却是荀子所添加,这一细节调整正体现荀子异于孔孟的兼容精神,荀氏曾有一段经典的批判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正因其人有此批判的兼容,才使得荀氏能够将孔子以降“顺时因类”的精神开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兼纳诸子之长,补避早期儒学在实用中的短处,将其时流行的礼法刑名之学纳入其学术体系,从而顺应当时早已不同于孔子时代的学术趋向。
孟荀所处年代相近,荀氏稍晚于孟,二者所面对之学术现实亦大体相同,彼时葛兆光曾于此有一精辟论断说,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的思想融合大体就是“百家争鸣的尾声与中国思想世界的形成……这背景中不是诸子中的一家一派,而是融汇了包括人文与社会思想与兵法、术数、方技等实用技术在内的巨大知识网络”[5]。显然荀氏之学与此趋势颇为相合,更适合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形势,在弘道层面上也较为成功。自此之后,原始儒学最终向经学为表,兼综百家的汉代儒学转变,亦可看作荀氏弘道实践的遥远回响。
不同地区有着自己国家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语言、工作方式及宗教信仰,我国企业在管理本土化劳务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充分的了解,避免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纠纷的情况,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5]。因此,企业劳务管理人员应及时与当地的人民进行沟通,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为此,企业应定期加强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学习,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融入管理过程中,使我国的管理人员与当地的劳务人员相处的更加融洽。
四、小结
自孔子以降儒家弘道逻辑的建构与变迁,是推进先秦儒学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孔子在其授业实践中将其学说融汇于其所引领的“轴心时代”天人关系破而后立的学术趋势之中,客观上开创了后来儒家顺时因类的基本弘道理念。
自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几经周折传至战国的孟、荀,但其学术根底却是唯一的,二者对于早期儒学中“性与天道”“圣人设教”“有教无类”等关键问题上都存在明确的价值认同,对于孔子所建立的“修己安人”的弘道愿望也始终有着共识,在实践中也都不同程度地践行着孔子顺时因类的基本精神。其有不同在于孔子在先秦哲学突破过程中的发挥的开创性作用使其准确地把握并在理论上适应了“轴心时代”破而后立的思想趋势,建立了“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最初模式。而孟子的贡献在形上领域的拓展,如其将“求仁”之路分解为“尽心”“知性”“知天”的可行步骤,并开创了“仁政”概念意在勾连现实政治以弘其道。荀子则尝试使儒学兼容于战国时期国皆求“强”,人皆逐“利”的普遍期望,批判地吸纳了其时流行的法术刑名等学,使其在境界论上与孟子殊途同归,客观上化解了二者在人性论上的冲突,又推动了早期儒学向秦汉以降登入庙堂的兼综之学转变,为其成为更适于此后皇权政治的官学探开了最初的通路。总之,上述孟荀所作的种种改变或尝试无论其结果如何,皆可视作早期儒学顺时因类的基本弘道理念的实践,而延续中夹杂着变革,授业重心从修养心性拓展至政治实践,既顺应战国实用主义抬头的学术形势又坚持对形上世界的关注,或许应当是孔子至孟荀之间早期儒学弘道理念的大致变迁状况。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弘道理念”即是在先秦儒学视域下,孔子及其后继者为实现其“修己安人”的理想所做的种种理论探索与实践调整。
②“顺时因类”见于《礼记·月令》“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笔者借用于本文中,“顺时”主要指巧妙顺应、利用时代思潮助推儒学发展,“因类”则主要指因弘道对象不同,在顺应时代思潮大趋向的同时,也需依据客体不同所做的精确调整,如面对春秋贵族是则着重于“道”论对突破天人障壁的理论作用。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99,205,89.
[2]周学熙.《论语·八佾》“祭神如神在”新诠释[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82-87.
[3]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5.
[4]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04.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14-315.
Construction and Changes of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of Confucianism During Pre-Qin Period
ZHOU Xuexi
(School of Marxism Aba Normal College,Wenchuan,Sichuan 623002)
Abstract: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of natural tendency in early Confucianism by Confucius,and hi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philosophy of Zhou Dynasty guided by him.Mencius and Xun Zi of the Warring States still implemented this spirit in their knowledge impartment.However,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wngrad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continuous change of academic trend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theory adjustment made by Mencius failed to break the original intention—realm theory framework,withoutmuch achievements.And the original Confucianism was expanded as comprehensive study by Xun Zi.The process accompanied with revolution,and the teaching impartment expanded from mental cultivation to political practice,which adapted to the academic trend of pragmatism ris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adhered to the focus on metaphysical world.This should be the appropriate changes conditions of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of Confucianism from Confucius to Mencius and Xun Zi.
Key words: Confucius;Mencius;Xun Zi;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7-0041-07
收稿日期: 2019-03-09
基金项目: 阿坝师范学院校级科研基金一般资助项目(ASB18-12)。
作者简介: 周学熙(1991-),男,汉族,助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早期儒学研究。
(责任编辑:冯起国)
标签:孔子论文; 孟子论文; 荀子论文; 弘道论文; 阿坝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