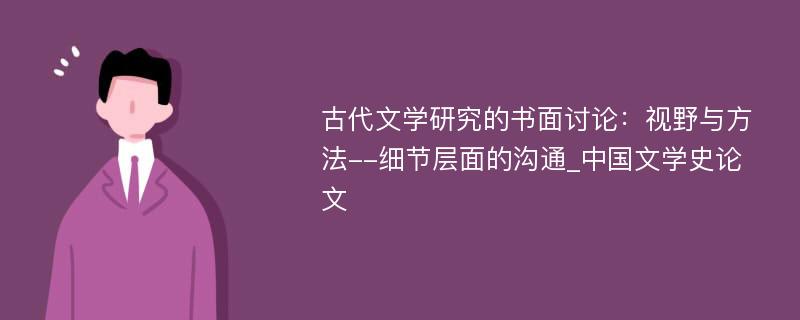
“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笔谈——走向细节层面的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层面论文,视野论文,古代文学论文,细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人在介绍国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套话出现的频率最高。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这一有着明显中国本位意识的实用主义,有时也使国人在面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时,自觉不自觉都会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常识性错误;而期待中的借鉴与启发,则往往变得空洞散漫甚至可有可无。所以,有必要从海内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所产生的学术背景,审视其或同或异的立场、方法、目的以及交流的可能性。
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步的,也就是说它的初衷是为了传授古代文学的知识。出于这样的目的,在文学史书写中必然突出大家名作,并以此为坐标,构建文学史的演进线索与价值评判体系,进而将其强化为公论共识。在中国,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主要都是作为教材而编写的。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兴起时,西方的文学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德国学者H·R·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走向接受美学》的第一章开篇就声称:“在我们时代,文学史日益落入声名狼藉的境地。”“文学史在大学课程表中已明确地消失了。”(《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时至今日,作为一种著作体例,文学史或许没有也不会绝迹,但与教学的疏离,肯定会使其有不同的面貌。
据说哈佛大学例外地保留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但作为针对本科生的课程,是以文本介绍为主,有关文学史的背景知识只是非常概括非常粗线条的(详参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现代中国》第十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不可能与中国大学里长达两年的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相提并论的。所以,新近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译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虽然主编者也提到了教学的需要,但主要还是为了一般的“非专业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及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而写作的。这样的学术指向,与以教学经验为基础、以教学对象为预想读者群体、以教学效果为目标的文学史书写,显然是不相同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孙康宜就说:“相比于一般的文学史,我们还不一定会把经典化(cannonization)看得那么重。……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给普通读者看,又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可能就不会那么注重作家个体,而会更注重一种倾向(tendency)或者一种潮流(trend)。”(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因此,在这部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小说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如《搜神记》、《世说新语》等都没有专门的介绍。相反,对其他一些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的作品,书中却予以较为突出的介绍。比如此书虽然别出心裁地以专节评述了宋代笔记,但对洪迈《夷坚志》却只字未提,而着重介绍的是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欧阳修的《归田录》等。即使是被论及的作品,在讨论的深度上也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如在讨论“三言”时,真正展开论述的只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种“偏颇”有时并非全是由于篇幅所限造成的。我并不是说这样撰写有什么不可以,毕竟历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无论怎样展开论述,也只能举一反三。不过,如果是以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为己任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更多地考虑论述对象的基本价值、地位,考虑历史叙述的周密与完整,考虑评价的分寸乃至使用的笔墨等。从实际教学的角度说,如果一个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缺乏基本的了解时,就对他们大谈“倾向”、“潮流”,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当然,文学史学科的著述方式、体例也是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转折。“重写文学史”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也陆续出版了许多体现当时研究水平的文学史新著。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着眼历史分期(“三古七段双视角”说),并据此突出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提出“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并据此强调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与价值。然而,坦率地说,这两部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更充分地展示的是中国文学史家在宏观上把握历史脉络的追求与能力,而在历史脉络依托的细节方面,却没有更为丰富的发现与揭示。我以为,这才是文学史研究更应努力的方向,也是最见出研究者独到眼光的地方。多年前,我曾撰文提倡个性化的文学史书写(《文学没有“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谈片》,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缀玉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看来,这种个性化不单是与众不同的表述,更应该是对历史细节与众不同的发掘与阐释。
如果说《剑桥中国文学史》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我以为首先就是这一点。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在讨论“晚明文学文化”时,有这样一段论述:
论及晚明小说创作惊人的增长速度时,我们也面临了在其它文类中所见到的那些同样的趋势。融合了编选、编辑、创造性写作的文学活动,使得小说能够独立发展。没有其它文类的这些活动,小说不可能兴旺发达。从这个意义说,小说的兴起是二次开发的结果。1566年,致仕官员、藏书家谈恺以前所未有的壮举,编辑、整理、出版了《太平广记》……《太平广记》的出版,为晚明众多著名故事、传说提供了素材,讲述浪漫故事、神秘故事的唐传奇也重新得到广泛传播,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太平广记》还激发了按主题重新编纂文言故事选本的兴盛,从前那些罕见的材料进而能够被人广泛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21—122页)这一段话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晚明小说的繁荣是“二次开发的结果”;也提到了一个以往研究者不太重视的细节,即《太平广记》在当时的编辑出版及其意义。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晚明小说编创的实际状况,就可以认同,这确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也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细节的探究,显然比泛泛地讨论晚明商品经济对文学思潮的影响要来得更实在些。
不言而喻,也恰恰在这样的细节,有讨论的空间。田晓菲曾指出,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于众手,每个学者都很优秀,但全书缺乏连续性和整体性,有些章节甚至自相矛盾(田晓菲、程相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与此相比,《剑桥中国文学史》确实努力贯彻了核心论题与整体观念,但由于此书各章节出于不同学者之手,依然存在着上述缺失、不平衡。在具体论述中,也同样存在前后矛盾或不一致之处。比如在讨论明代小说的发展与传播时,书中认为“普通民众是白话小说的主要读者的说法,只需通过调查现存的小说版本就能轻易将其推翻”,“在晚明,无论谁创作了小说,精英士大夫无疑是读者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25页);而在讨论清代小说时,又转而强调《儒林外史》、《石头记》是例外,“这些小说很少为同时代的读者所读到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标志了重要的历史变化,因为长期以来,白话章回小说都是跟口头的说书传统以及稍晚出现的商业出版联系在一起的,并因此从众多文类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30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恰恰出现在全书最为重视的“文学文化”(literature culture)的整体观念之下。也许,除了不同撰者观点可能有的分歧外,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本身都不是单一的。而只有通过对细节的深入研讨,我们才能发现其中深层的差别。
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还有一个根本的属性是与中国本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不同的,那就是前者从属于汉学或中国学的范畴。从根本上说,汉学的学术指向是以认识中国为目的,法国汉学家若瑟·佛莱什(José Frèches)在长文《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中就指出:“汉学史基本上就是西方对中国关注的历史。”“汉学研究的高潮将来会依然与大众对于中国事件的兴趣相联系。”(原载巴黎1975年出版的《我知道什么?》丛书第1610号,《汉学》,中译文载《汉学研究》第十三集,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174页)显然,这种关注与认识是建立在一种成熟的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审视基础上的,除了新鲜感引发的妙思奇见,也难免由陌生感导致某种误读、偏见。
最近几年,有关汉学的争论较为激烈,有的研究者特别强调汉学与所谓“汉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提出“由于缺乏学科批判意识造成的‘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已成为一个敏感紧迫的问题”(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汉学研究》第十四集,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汉学心态”、“伪汉学”等,也受到了质疑。也许,对古代文学而言,问题还并没有这么严重。而且,与早期的汉学研究有所不同,现在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他们多半是在中国(包括港台)完成大学学业的,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孙康宜及田晓菲、商伟等多位撰者。这一研究队伍构成的改变,使汉学在内部形成了一种纠偏正误的机制,并促进传统的汉学日益向国际化发展。需要警惕的倒是,这种所谓的国际化也可能使汉学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居高临下、涵盖一切的假象,而至少在目前,汉学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
基于汉学的基本性质,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把古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标本,必然重在介绍与比较;而中国本土的研究,则将古代文学视为文学遗产,重在阐释与评价。比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的分期上,作了许多可贵的努力,时有卓见。但是,孙康宜也曾谈到:“我们决定把1400年当作一个分水岭,主要是因为《剑桥文学史》系列中已出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史,如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史,大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而且学习英国文学的也都知道,140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新的文学史可能吗》)固然,她也努力说明了1400年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问题是,这样的理由,并不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在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段也能找到,甚至可能找到更为充分的理由。与其他国别文学史保持某种时序上的一致,只有一个理由才是无法辩驳的,而这样做的目的或客观效果,是为了便于比较。
这样的比较,在具体论述中更是随处可见,比如在论及西门庆在一场性事中精尽人亡时,作者说“这无疑是世界文学所有性场景中最为怪诞的一幕”(《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34页);在谈到科举制度扼杀人才时,作者说“其暗昧与压迫使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世界”(同前,第263页)。在我看来,这些比较,与其说是一种确切的判断,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性表述。无论如何,海外的研究者,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也为了向异域的读者说明,自然而然地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作比较,总体上还是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把握的。
同样是为了介绍与比较,海外学者还会突出基本文献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评价。如《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突出地评介了《东京梦华录》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通常只作旁证材料使用的书。此书的撰者写道:“这五部著作之所以无比珍贵,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至为详切的都市生活与风俗的细节。”(《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册,第587页)显然,这也是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所以,撰者还据此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主要的节庆(同前,第585页)。中国的文学史家更加关注的可能不是它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与风俗细节,而是它们为什么怎样提供了这些细节。
还有一点也必须指出,由于非母语文献的搜集、阅读毕竟不如使用母语那么快捷,海外汉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时,经常通过精读有限的文本,扬长避短,在中国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颇有意味的现象,而他们也善于将这种阅读的印象转化为一种学术思路与判断。比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讨论“笔记与小说”时,作者称笔记常见的随意的编排“赋予了笔记一种不可预料性,这也是它的部分魅力之所在”(上册,第506页)。这种所谓的“不可预料性”并非笔记作者有意安排的,因此往往不会为中国学者所留意,但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这首先可能是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而作为客观存在的效果,未必没有探讨的价值。
综上可知,由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与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学科属性与学术指向,这些不同最终都可能体现到对历史细节问题的认知上。也就是说,在细节问题上,我们有可能找到超越上述种种不同的、饶有趣味的对话方式与场域。
向细节层次的推进,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之初,西学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理论方法上的影响最大。人们习惯说,我们用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了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在理论方法的引进、尝试方面,也是如此。十几年的时间,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叙事学等,纷至沓来,但是,脱离了固有的学术理路与相应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如今,我们更应该审视的也许就是中外学者对历史细节的不同认识与解读。
从自身的学术发展来看,我以为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应转向细节。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曾提出:“鲜活的小说史应该从细节上展示小说文体成长与小说创作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种细节指文本所包含的所有具有历史演变性质的构成要素。……一旦小说史深入到小说文本构成的细节中去,必将呈现出更为真实、可靠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前因后果。”如果这种细节还包括所谓“文学文化”的诸多层面,其学术内涵更难以估量。宇文所安就说过,文学史“学者们的努力,丰富了我们在很多细节方面的知识”,而他自己也“喜欢探察文学史上的一些蛛丝马迹,它们提醒我们过去的人做出的价值判断和现在如何不同”(宇文所安《史中有史》,《读书》2008年第5、6期)。别忘了,日本也是海外汉学的重镇,在细节上由小见大,也是日本学者的强项。这表明,海外学者的精读文本与关注个案,正与注重细节的学术路径殊途同归。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多次提到《剑桥中国文学史》,并不是在对此书作书评,而只是借此引出一些讨论的话题。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面对海外研究成果,不应只是简单的借鉴或利用,而应努力展开真正的对话。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宇文所安如下的观点:“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虽然它们并不来自西方,也不来自中国。……谈到对知识的整理和思考,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有太多的关心和焦虑。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把多样性的‘中国’和多样性的‘西方’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和挑选,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自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