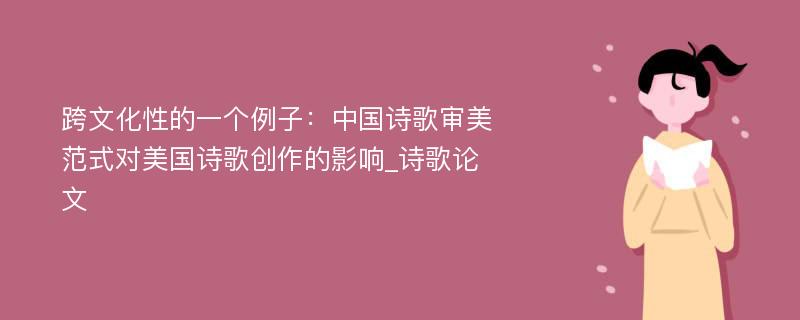
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例证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间性是文学间性的重要构成形态之一,也是比较文论的前沿性研究热点之一。本文拟从文化间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几个典型例证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来揭示中国诗歌艺术风格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的整体性影响。
一
文学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感性而复杂的多维意义世界。文学文本与意义的生成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文本内部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中心论则认为,作者在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参照甚至模仿,作者的创作不是绝对的独创。法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丽丝托娃把这种文本参照现象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译“文本间性”)。这一理论提出后,文论研究的关注点不再仅仅是作者与其作品间的关系,而是转向了对文本的多学科分析,特别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
另一方面,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一译“主体间性”)理论,俄苏学者巴赫金提出了“对话理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他们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学术角度将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扭转为“主体—对象主体”关系。人不再把自己简单地看作是世界的征服者,而是要与对象主体进行对话。这种哲学思想对文学理论的直接影响就是读者中心论的兴起。
近来,有学者将文本间性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间性”的观点。这是一种“间性的间性”,是联结两大理论的桥梁,即由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综合、互动而构成的复合间性。由于它兼备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双重特质,因此更便于我们考察文学文本和意义的生成机制。其中,文化间性作为文学间性的一种重要构成形态,体现了从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
文化间性是一种隐型间性。它所涉及的层面不是语言的层面,而是更为深刻的、超越的层面,即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对另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在文化间性的众多研究课题中,中国诗歌艺术风格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的整体性影响始终是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中国诗学精神对现代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些个别的诗人身上,而是体现在整体性的文学潮流之中。尽管中国文化和诗学的审美范式并不是美国现代诗歌的主流影响因素,但在几代美国诗人的文本中都能找到中国思想和诗学的影响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
经过浪漫主义运动之后,英语诗歌以其体裁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而著称于世,不仅有史诗和长篇叙事诗,而且还有十四行诗、抒情诗、自由诗、散文诗等。但是,英语诗歌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初却面临着穷途末路的尴尬局面: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功能已被小说所取代;典雅古朴、讲究韵律的十四行诗由于英语的发展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而成为文学史中的记忆;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科技术语和数字、代码逐步充斥着生活语言,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语言与20世纪的社会话语格格不入,这给诗歌带来了形式和语言的双重危机。此外,美国重要诗人狄金森和惠特曼在19世纪末相继逝世,后继乏人。这样,历来作为英美两国文化标志的诗歌即将失去在文坛的统治地位,其形式和语言的根基也随之发生了动摇。
庞德于1934年发表了其散文集《创新》(Make It New),认为一场艺术革新运动势在必 行。[1]从美国诗歌创作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场艺术革新运动首先意味着诗歌审美范式 的转换。
当一个民族需要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是其主流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会给双方带来新的生机。20世纪是西方文明进行反思求变的时代,其中就美国诗歌而言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诗歌运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美国诗歌的意象主义时期,其领军人物就是庞德;50年代开始是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而此次运动与解 构主义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历史背景造就了美国诗人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 。安东尼·依斯何普(Antony Easthope)在阐释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与美国诸批评家的评论重点时说:
在阿诺德式的与美国人强调的重点之中,文学研读累积了一种传统的人文主义,而这 可以远远追溯到浪漫主义及文艺复兴时期。一般认为研读文学可以令你成为一个更好的 人,可以发展你的“想像力”,这样,你可以凭想像力进入他人的经验之中,由此学会 尊重真理以及推崇公义。[2]
正是由于在欧美传统中存在这种对文学的信念,即肯定其道德力量的信念,美国诗人才会把文学作品视为修炼自己品格的媒介,同时也视之为寻求自我的媒介。这就为中国诗歌艺术风格在美国诗歌亟需范式转型时进入美国诗人的视阈并逐渐对其创作实践发生深远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从文化间性的角度看,作者主体与读者主体通过文本进行对话交往,如果读者开始自己的写作而转变为新的文本的作者,那么前文本与当下文本之间就必然会形成指涉关系。也就是说,阅读积累对于创作实践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中国诗歌对美国诗人的影响就发生在美国诗人们对中国诗歌的阅读接受过程之中。这些美国诗人主要是通过两种英文文本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诗歌艺术:一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本;另一种是关于中国文化和诗学的英文著述或汉语著述的英译本。甚至一些经典化的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庞德等诗人之手,已经转化为美国英语诗歌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的意象派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起因于庞德在1915年出版的著名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一译《华夏集》)。这是一个将意译的诗歌文本视为创作作品并随之被经典化的典型范例。许多美国诗人把这些诗奉为英诗传统的经典之作,视之为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三
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在1965年之前曾总结了中国诗学文化对美国诗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波及欧美三代诗人:
第一代:庞德;里尔克(R.M.Rilke);阿波里奈尔(G.Apollinaire);玄姆(F.Jammes) ,马拉美(S.Mallarme);巴斯特纳(B.Pasternak);马恰度(A.Machado)。这些都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成名的年轻诗人。
第二代:雷克思罗斯;杜丽特;卡明斯(e.e.cummings)。他们是一战后崛起的诗人。
第三代:勒弗朵夫(Denise Levertov);克利里(Robert Creeley);罗伯特·邓肯;劳伦斯·弗林格;金斯伯格;史奈德等。这些是在30—40年AI写作作的诗人,他们继承了前人已采用的中国诗歌的话语范式。
庞德是一位创新意识极强的诗人。他曾学习过汉语,翻译过唐诗,也研读过日本的和歌和俳句。他希望借助翻译借鉴外国诗歌来丰富和改造美国诗歌,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他在中国文字和诗歌中领略了形与义、景与情融合为一体的奥妙,在东方文化中感悟到了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审美意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象这个核心审美范畴,建构了意象主义的诗学理论。
庞德的诗作《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是意象派诗歌的开山之作:
人群中这些面庞的悠然出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作品篇幅很短,但已经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诗学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来加以对照: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断肠人在天涯
首先,这首中国诗具有一个显著的语言特点,即句子结构的不完整性。藤、树、鸦、桥、水、居所、路、风、马、夕阳,这些叠加在一起的象征荒凉、忧愁的意象,是以一 系列名词的罗列形式呈现的;庞德的诗里也没有使用动词,而是完全由一系列名词排列 而成,造成不同意象的叠加,这样的结构在以往的英语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庞德自己 分析说:“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 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4]诗中匆忙而喧嚣的人群、湿漉漉的深色 树枝等意象,在这里也是为了铺陈。正如马致远将枯藤、古道、瘦马等意象用来比拟断 肠人的情感体验一样,庞德的许多花瓣也是为了比拟那些美丽女人和可爱儿童的面庞。 更为有趣的是,枯藤等意象与断肠人的心情是一致的,而花瓣不仅与黑色树枝形成了对 比关系,而且与那些面庞具有呼应的、一致的关系。花瓣既有美感,同时也具有神秘感 。因此,二者不仅在语言形式和比较手法方面旗鼓相当,而且在审美趣味方面也具有很 多的相似性。
中国诗歌所独具的“意象叠加”的意境传统、“缘情说”的创作理念、“兴”的艺术 手法,甚至连汉诗句式结构上的名词连缀形式,都在庞德的这首小诗中得到了完美的展 现。
四
关于哲理思想入诗的问题,也不难找到中国诗学扭转和推动美国诗歌发展方向的例子。早在诗歌的浪漫主义时期,英国诗人济慈(Keats,1795—1821)在其诗学论述中极力 主张诗只表现感受,以创造“纯美”的诗作,而决不能表达任何思想。[5]这种有失偏 颇的艺术主张把审美感受与理想思考割裂开来,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题材和构思的视域 。由于济慈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其诗学思想也一度影响了一 批英美诗人的创作。美国的爱伦·坡(Allen Poe,1809—1849)就极力追求超验世界的 美,反对诗歌关涉真理和教谕。这种主张致使象征主义诗歌脱离了社会现实,滑向了“ 纯诗”的道路。[6]
但是,当中国诗歌的文化艺术特色对美国的诗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哲理思想居然成为美国诗歌的一道风景线——在此仅举雷克思罗斯在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之园园之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为例。其中,他把《老子·第六章》和《诗经·国风·绿衣》稍加改写后融入此诗的第一段,用来描写诗人住在远东日本乡下的经验与感受:
稻田里的刚刚Young rice plants are just being
插了秧。茶园的树丛
Transplanted.Tea bushes are
低而密集。茄子 Low and compact.Eggplants are
仍在小小的棚架之下。 Still under their little tents.
古筝音调的草地。三味线 K'oto meadows,samisen
风情的湖泊,山之鼓;水之笛 Lakes,mountain drums;water flutes
整夜在月光中飞落。
Falling all night in moonlight.
候鸟们在许多屋顶上Migrating birds twitter on
吱吱娇啭。杜鹃花开了。 The roofs.Azaleas bloom,
夏日开始。一个六十多岁 summer opens.A man of
的男人,仍旧穿过林木蔚蔚 Sixty years,still wandering
的群山徜徉,采摘 Through wooded hills,gathering
蘑菇,弯卷的蕨芽 Mushrooms,bracken fiddle necks
和竹笋,倾听 And bamboo shoots,listening
在他脑海深处逐渐消失
Deep in his mind to music
于遥远时空的音乐。
Lost far off in space and time.
谷神不死。
The valley's soul is deathless.
是谓玄牝。 It is called the dark woman.
玄牝之门 The dark woman is the gate
是谓天地根。 To the root of heaven and earth.
绵绵若存。If you draw her out like floss
用之不勤。 She is inexhaustible.
不用费力就可拥有。 She is possessed without effort.
绿兮衣兮
It was a green jacket,a green
绿衣黄里Jacket with a yellow lining.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When will the heartbreak stop?
绿兮衣兮
It was a green jacket,a green
绿衣黄里 Jacket with a yellow skirt.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When will the heartbreak go?
常青的松林在
The evergreen pines grow more
春天将尽时变得更绿 Green as Spring draws to an end.
嫩黄的稻秧在蓝的水中生长。 Yellow rice blades in blue water.
诗中不乏极具东方色彩的意象,乍一看还真像是出自某个中国诗人之手。稻田、茶园、草地、湖泊、山色、水影、夜色、花鸟,这些夏日景象的描绘,不同意象的叠加,构成了一个幽雅而朦胧的艺术境界,具有中国诗歌审美取向的含蓄美。而十三弦古筝的草地,三味线之湖,山之鼓,水笛声,静中有动,“整夜在月光中飞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诗的境界。候鸟、杜鹃花标志着夏天的开始,一个老农民的形象出现了,于是画面忽然动了起来,一组采摘的镜头构成了田园风光纪录片的蒙太奇,而且更为奇妙的是,读者仿佛还能听到音乐的配音。种种艺术形象真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外,从这里还能看出作者对中国诗学所独有的艺术手法“兴”的模仿。我们知道,“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被纯熟地运用。“赋”为直陈,“比”为譬喻,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学中均有运用,唯独“兴”是最具汉民族特色的国粹。例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所谓“兴”的创作手法,就是两组意象在语言上形成排偶的形式,但同时在内容上又 具有摹拟的关系。傅修延认为:“‘兴’不仅见于《诗经》,东周谣谚中‘原田每每’ 与‘凤皇与飞’等便是兴象;《易经》的‘鸿渐于陆,夫征不复’(《渐·九三》)和‘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等也属‘兴’的发端。” [7]英文在字面上不容易做到排偶,但雷克思罗斯的这首诗先描绘大自然的景色,然后 才出现六十多岁男人的形象,这种谋篇布局的策略或多或少地模仿了“兴”的方法。而 且,诗人在状物写景时还运用了视觉与听觉通感的手法:草地的景色有如十三弦古筝的 音调;湖泊看上去如同三味线弹奏的乐曲一样优美迷人;山的雄伟峻秀令人想起隆隆的 鼓声,水的情调就像长笛的音色一样空灵婉转。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老子的道家哲理 出现了。“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等句,出自东方哲学经典《老 子·第六章》。谷神,指生养之神,一说为虚空博大、变化无穷的道。玄,原义为深黑 色,牝,指兽类的雌性;玄牝则指玄妙的母性,即孚育和生养天地万物的母体——具有 无限神奇的造物能力的道。
雷克思罗斯把玄牝理解为黑女人,显然是受到了他所接触的《老子》英译本的影响。老子“道”的概念,指的是天地混沌状态时的元气,是世界的原创机制,是宇宙的本质和实质。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8]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人们对世界创始机制的理解则体现在《圣经·旧约全书》的第一章<创世纪>中:是万能 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天地和世上的万物。估计是译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于自己的理解,按 照字面意义把“玄牝”译成了“the dark woman”。或许译者根本就没有理解“玄牝” 即指“道”的造物能力,或者是他感觉“道”不能译为“上帝”而又找不到合适的译法 。总之,译本的问题已是不可考了,而雷克思罗斯对“玄牝”涵义的理解终归尚欠透彻 。
按照读者中心论的观点,读者的活动不再是单纯的阅读接受,而且还要与作者及人物进行对话交往,对文本做出反应;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展开阅读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终极意义。翻译理论的功能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译者应当考虑接受对象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条件而选择适当的语体来进行目的语的写作。虽然该诗中 对老子哲理的理解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交往,雷克思罗 斯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其实已属相当不易了。
总之,这首诗的题材和格调很像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和形式都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特别是借鉴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意象叠加”的意境追求、“缘情说”的创作理念、“兴”的艺术手法、“哲理入诗”的审美范式,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汉诗的句式结构,是美国诗歌吸收和转化中国思想文化和诗歌艺术特色的绝好例证。
五
在文学间性的构成形态中,文化间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既基于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隐型间性。它既涉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又引发对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两方面的重新阐释。根据上面的个案分析不难看出,现代美国诗歌在整体的文学潮流上与中国诗学精神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诗人自觉地将中国诗歌的艺术风格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借鉴,从中汲取精神哲思和艺术手法的养料,提升自己的内在情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行人生阅历、阅读积累、文学能力、情感体验的整体综合把握,充分地调动了文化间性的种种功能。这种不同文化、不同诗歌审美范式相互交流的艺术实践,特别是中国诗歌的艺术风格对美国诗歌的创作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