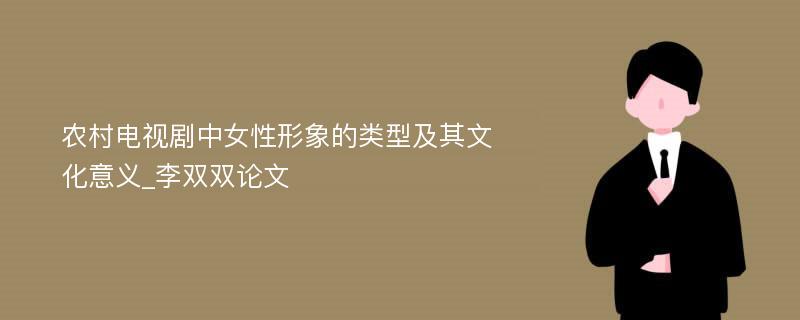
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及其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中论文,题材论文,意义论文,形象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4-0151-10
由于广大农村和农民在中国历史及现实中的重要地位,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直备受创作者和观众的重视。“1978年5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单本剧——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三家亲》。”[1](P218)这部电视剧既揭开了新时期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帷幕,也成为其后众多农村题材电视剧问世的先声。其后的30多年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随着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农村、农民地位的变化及党和国家对农政策的调整而几经浮沉,有过硕果累累、反响热烈的辉煌历史,也经历了“九亿农民八部戏”的惨淡经营时期。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过诸多艰难,但出于对现实的关注,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从未放弃过表现地域辽阔的农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而乡村女性作为乡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众多农村剧青睐的表现对象。综观新时期以来30余年的农村剧创作,我们发现,她们基本不脱苦难女性、女强人、道德女性和落后女性这四类范畴。这些面貌不同、性情各异的女性,构成了乡土世界灿烂夺目的另类风景,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变迁。
一、苦难女性:伦理乡村和现代城市的牺牲品
由于女性身上特有的柔弱、忍让、服从等特质,女性往往成为历史和现实苦难最大和最直接的承受者,农村剧中也不乏这样的乡村女性“受难者”形象。她们往往是爱情、婚姻悲剧的主角,其身心承受双重的迫害与痛苦。在传统的伦理乡村世界中,她们是封建伦理祭坛上的祭品;进入现代都市后,她们又常常充当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男性的消费品。
1.传统伦理乡村中的牺牲者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农村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塑造了为数众多的苦难女性形象。她们多是受传统伦理迫害、束缚的乡村女性。此类剧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是美丽、柔弱的年轻乡村女性,她们对爱情、婚姻都饱含着美好的期待,但这种期待在故事开场不久便会被外来因素彻底打碎,她们从此都会陷入苦难的命运之中,失去了梦想中的爱情和自由。《喜鹊泪》中的喜鹊、《山月儿》中的山月儿、《白色山岗》中的青草、《篱笆·女人和狗》中的枣花与枣花娘,都是传统伦理乡村中的牺牲者。1982年的农村剧《喜鹊泪》是80年代初期为数不多的悲剧作品之一。剧中的农村姑娘喜鹊,虽有心仪的对象,却最终在父亲的逼迫下跳进买卖婚姻的深渊,绝望的喜鹊在抗争无望的情况下含泪自尽。尽管作品将喜鹊的悲剧归结于十年内乱时期国家实行的愚民政策,但封建主义的思想和伦理道德却是逼死喜鹊的最大凶手。另一部颇具代表意义的作品是《白色山岗》:年轻的放羊汉田三月为了报答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老支书,答应在老支书死后照顾支书年轻貌美的妻子李青草。但三月最终无法抗拒青草的引诱和内心的欲望,与青草发生了野合。之后田三月陷入仁义礼俗和情欲的挣扎之中无法自拔,为了所谓的“仁义道德”,三月最终亲手掐死了自己深爱的青草,酿成了两人的悲剧。该剧在道德、欲望、伦理的纠缠中揭示了文化桎梏的锁链是如何难以挣脱,又是如何扼杀了一对年轻人的正常欲求、爱情和生命。《篱笆·女人和狗》中的枣花虽与小庚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无法抗拒父母之命,嫁给了葛家的三儿子铜锁。婚后生活不幸的枣花出于“孝道”选择了一忍再忍。她一次次鼓起勇气准备离婚,又一次次屈服于公公和母亲的哀求。正如学者李宗刚所言:“在民间所规范好的婚姻秩序中,女性所恪守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面对婚姻的不幸,‘熬’是女性唯一的选择。”[2]虽然在外力的推动下,枣花最终离婚成功并嫁给小庚,却再次陷入了小庚为她编织的夫权的大网中。同样,枣花娘与茂源老汉作为老一辈农民的代表,也深陷传统伦理宗法之中无法自拔——虽然彼此相爱,却始终被礼法阻隔;虽然深知不能结合的痛苦,却依然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儿女身上。枣花娘的失足落水而死,其实是死于封建礼法的泥淖,正如茂源老汉所控诉的那样:“这不是天灾,是人祸。”“篱笆”、“古船”、“井”、“网”,这些象征性的物象组成了一个个寓言,象征着强大的封建传统伦理对女性的沉重压抑和束缚。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束缚桎梏这些乡村女性的文化伦理,具体体现在婚姻或家庭中的男性身上。相比这些女性的柔弱善良,剧中的男性往往是粗暴野蛮、心胸狭窄、冷酷狠毒、自私自利的。他们在剧中被设计成女性不幸命运的直接制造者:喜鹊的悲剧来源于封建家长的逼迫;枣花第一段婚姻的悲剧源于前夫葛铜锁的虐待和不务正业,第二次婚姻的不幸则源于小庚对她的控制和猜疑;山月儿的悲剧在于丈夫田大把她当作单纯的生育机器以及第二任丈夫牛二的心胸狭隘和对她的猜疑……总而言之,这些女性的生活极不完满,她们在家庭或婚姻中的地位十分低下,无论是在父亲还是在丈夫面前,她们都没有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她们要么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随意占有,要么被视为单纯的生育工具任意处置,其正常的情感需求和人格权益都被忽视和践踏了。
面对这种密不透风、摧残人性的文化桎梏,被桎梏者也有过或强烈或微弱的反抗。《喜鹊泪》中的喜鹊不惜以死相逼;山月儿无法忍受丈夫让她“借种生子”的安排,决计出逃;枣花一次又一次出走。但面对强大的封建礼俗,这些反抗又显得如此微弱和不堪一击。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封建伦理道德丑恶的一面,还有其温情脉脉的一面。喜鹊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枣花面对的是含辛茹苦的母亲和恩重如山的公公。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乡村价值体系在此显示出其在文化道德与善恶评判上的两难处境。从人格道德上来说,那些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者并非十足的恶人,有的甚至是慈祥的乡村长者或正义善良的正人君子。正因如此,主人公的抗争行动便愈显艰难。她们一方面要顾念这种伦理亲情,另一方面又要反抗这种伦理亲情,在顾念与反抗之间挣扎徘徊的反抗举动往往是不彻底的,或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主人公的这种犹豫挣扎也表明这种普遍性的乡村伦理亲情已经内化为他们文化人格和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时时制约着她们的抗争行动,让她们的生命无法独立自主,她们的反抗更是无法彻底。所以,当喜鹊无法争取到自己的爱情、而又无法彻底反叛自己的父亲时,只能以自杀这种惨烈的方式离开人世;枣花一次次屈服于母亲的眼泪和公公的恩情,一次次地重复着:“娘(爹),您老人家别生气,俺听您老人家的”;当第二任丈夫小庚以疼爱她的名义将她锁在家中,软弱的枣花也选择了屈服于丈夫的“疼爱”和“怜惜”。她们最终无力摆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只能为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剧人生加上形象的悲情注脚。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生命的悲剧性凋零,引发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促发观众对阻遏乡村社会前进的传统心理积弊进行思考。
2.由乡入城:乡村女性的堕落与无奈
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乡村女性走出了传统的伦理乡村,进入她们渴望的现代都市,暂时摆脱了陈腐的乡村传统和乡土伦理的束缚与桎梏。但来到城市之后,更大的苦难正静静地等待着她们。都市带给她们的,不是繁华和荣耀,而依然是无尽的屈辱和苦难。《生存之民工》中的王家慧,渴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为了这个理想,她委身发廊老板陈佑良,但怀有身孕的家慧在失去性的交换价值之后被陈佑良赶出家门,流浪街头。倾盆大雨中,家慧在一处破屋中艰难地生下了孩子。当她抱着孩子去找陈佑良时,再一次遭到了殴打。为了生存,家慧投身发廊,沦为男性的性工具。《山城棒棒军》里的王家英到歌舞厅做了三陪小姐;《城市的星空》中的农村女孩乔小央为了筹集给男友治病的钱,同样出入歌舞厅做了小姐……在老舍先生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骆驼祥子》中,年迈的车夫曾不无悲愤地评论他们悲惨无奈的底层人生:“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而多年以后,乡下女性依然要靠着最原始的身体资本谋生,身体在这里成了女性的一种交易工具,女性靠身体来获得生存的机会,来满足自己对城市的渴望和物质的欲求。而女性身体资本使用价值的短暂和不断贬值,也预示了靠卖身生存的女性最终的必然悲剧。
如果说乡下女性在城市里出卖身体完全出于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求,那么对有些女性来说是有失公平的。许多乡下女性进入城市时,怀揣的是美好的寄托和理想。她们也渴望在城市里经历美好的爱情,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城市男性却利用了她们对城市的向往,对她们进行欺骗和玩弄。《民工》中的李平,进城后先后遭到两个城市男性的玩弄和抛弃。李平决心把感情托付给跟自己同样出身的农村人,却被玩弄她的梁超英无耻地说出她和自己同居并打过胎的秘密,被赶出家门的李平只能再次选择将自己放逐。《我是农民》中的黄英子,被城市豪华奢侈的物质生活吸引,并在祝可一的计谋下失身。在金钱的诱惑和对婚姻的期盼中,黄英子搬进了祝可一为她提供的公寓,做了祝可一的隐身情人。在她宫外孕生命垂危之际,祝可一却正在打着另一个女人的主意。对这些曾经纯朴天真的乡下女孩来说,她们渴望得到城里人的爱情,但爱情对于她们,只能是一个遥远而可笑的梦想。因为城市看中的,并不是她们纯真的爱情,而是她们青春的肉体。在城市男性的眼中,她们不过是他们拈花惹草时的一个猎物和目标。
城市的罪恶不仅让乡村女性迷失了身体,也让她们迷失了曾经纯洁无瑕的灵魂。乡村女性的由乡入城,跟大多数进城的乡村男性一样,是受着城市现代化的吸引,渴望摆脱乡村单调乏味的人生,脱离传统乡村伦理的束缚。但由于其身份的先天弱势,她们承受的依然是城市加诸她们身上的苦难。她们的身体被城市占有,她们的灵魂在城市里迷失,没有爱情,没有归宿。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家慧和李平们在城市空间中的无处遁逃,看到了乔小央和黄英子们被骗后的自甘堕落。她们的不幸,是乡村文化和乡下人在城市里的悲剧处境的一个缩影,归根结底源于乡村之于城市的先在弱势,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而产生的一个恶果。按照李佐军先生的观点,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有机复合”[3](P46-47)。“二元经济结构”指的是“一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不同质的相对独立运行的产业主体子系统(或单元),其中一元以现代技术武装的、商品化程度高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部门为代表,一元以传统手工技术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式的乡村农业部门为代表”。这两个本质不同的“元”分别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文明时代。“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一国内存在着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子系统(或单元),即一元是具有现代生活概念的发达城市地区,一元是条件相对恶劣的、拥有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有传统生活观念的落后农村地区。进入新时期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格局依然制约着进城的农民,城市因占有经济上的优势而顺势构建了它的文化优势,对农民表露出不可一世的自傲心理和强烈的排斥情绪。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乡村女性,只是承载着乡村弱势地位的一个典型符号和鲜明表征。
从传统的伦理乡村到现代化的都市空间,乡村女性的悲剧一刻也没有停止。她们楚楚可怜的“受难者”形象,其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在时代中的嬗变也引发了人们对乡村现实和乡村女性命运的理性反思。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代农村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伦理乡村在逐渐远去,传统文化伦理下的女性受难者形象逐渐消失,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剧表现更多的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而她们追求经济独立与精神自由之路的艰辛,也表明乡村女性“向城求生”的道路依然漫长。
二、女人不是月亮:乡村社会中的女强人
并非所有农村剧中的乡村女性都是苦难的被动承受者,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很多农村题材电视剧也塑造了许多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如《李小娥分家》、《女人不是月亮》、《城市的星空》、《当家的女人》、《插树岭》、《天高地厚》、《圣水湖畔》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她们的独立意识已经觉醒,她们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以女性的自尊、坚强和聪明能干赢得了男性的敬佩,并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叙事模式,开创了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中“女强男弱”的新型人物关系。
1.扣儿和山杏:超越苦难的坚强女性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剧中出现的乡村女性大多是传统伦理乡村中的牺牲者,那么到90年代以后,受难的乡村女性依然存在,只是此时的女性,不再像喜鹊、山月儿这样被动地承受苦难,也不再像枣花那样无奈地被笼罩在男权的大网中,而是学会了用女性的坚强和独立来抗击苦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事业上的成就和辉煌弥补了个人生活的苦难和缺憾。扣儿(《女人不是月亮》)、胡山杏(《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李香叶(《颖河故事》)、耿志茹(《一亩三分地》)、黑玉(《金鲤鱼》)等90年代以后农村剧中的主人公,都是此类超越了生活苦难的坚强独立的乡村女性形象。
《女人不是月亮》中,美丽纯真的山村女孩扣儿不满封建婚姻的束缚,毅然逃婚,离家出走,追寻自己的爱情和梦想。当她发现昔日的恋人田牛已经无法与自己进行精神上的沟通时,她再次逃婚出走。如果说扣儿第一次逃婚走出纽哥的家反抗不自主的婚姻,是她作为“人”的思想的觉醒;那么她第二次逃婚走出恋人田牛的“金屋”,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则是她作为现代女性独立意识和抗争思想的升华。“扣儿”这个名字看似随意,但却巧妙而又自然地蕴含着创作者的深意:它是乡村女性遭受封建束缚的代名词和缩影,纽哥、田牛、曹四夫妇、赵鬼等人,都是束缚扣儿的无形的“纽”,而扣儿以出走的方式宣告了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并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和最后的成就避免了“娜拉”出走后“不是回来就是堕落”的悲剧结局。
如果说扣儿一开始便懂得反抗命运,那么胡山杏、李香叶、黑玉们则是经历了痛苦的磨难之后才醒悟到女性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中国的许多农村女性一样,她们一开始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所以饱尝了男性带给她们的欺骗、背叛等身心的双重磨难。突然的噩运和打击终止了她们千篇一律的庸常生活,她们在苦难的磨砺下进发了原先被压抑的坚强和韧性,在抗争和奋斗中寻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柔弱的山杏为摆脱噩梦般的婚姻勇敢地站到了法庭上,宣布挣脱婚姻的枷锁;坚强的李香叶走出婚姻的不幸,创办企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黑玉在被丈夫抛弃后勇敢地走出挫折,带领村民们绑扎笤帚并出口韩国、日本,使家乡成为远近闻名的笤帚专业村,又凭着自己的努力办起了学校和妇女扫盲班,使流传的“金鲤鱼”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这些女性的奋斗史形象地说明了乡村女性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与喜鹊、山月儿等乡村女性的悲剧相比,扣儿、山杏们先悲后喜的命运处理无疑更符合观众的欣赏心理。她们一步步超越父权和夫权的束缚,由男性的附庸蜕变为真正自立自强的个体生命,并以事业的成功证明了女性的生命价值。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创作者对身处苦难之中的乡村女性的期待。扣儿、山杏、黑玉、耿志茹们从苦难中崛起并最终超越苦难的经历无疑充当了当代中国妇女解放和妇女独立的最佳教材,在男权思想相对严重的乡村来说,无疑更具现实指涉意义。
2.从李淑霞到张菊香:电视剧中的当代李双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电影,如《李双双》、《小白旗的风波》、《槐树庄》等塑造了李双双、叶俊英、郭大娘等非常经典的乡村女干部、女强人形象,大公无私、敢于和一切违反集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的李双双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与乡村电影遥相呼应,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女干部、女强人形象。1981年,根据郑九蝉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能媳妇》便塑造了一个“当代李双双”的形象。剧中的女主人公李淑霞,未出嫁时便已是远近闻名的铁姑娘。这个合村的女队长发誓“三年不改变合村面貌不出嫁”,结果说到做到,用三年时间使娘家合村成为了富裕村。之后她嫁给了田家屯的青年田宝,婚前提的一个条件就是“往后我要参加工作你可别干涉”。李淑霞过门三天便被选为田家屯的队长,她排除工作和家庭中的重重阻力,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李淑霞的泼辣果敢、公正无私的个性与品质,可与李双双相提并论。
2004年的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的张菊香也被观众称为“当代的李双双”。和李淑霞一样,张菊香泼辣能干,是家庭各项事务的实际掌控者。她在结婚前便提出婚后当家的要求,婚后独掌家政大权,将家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全家发家致富。当选村干部后,张菊香同样以其果敢和魄力排除障碍,实现了全村共同致富的理想和目标,其胸怀和才智远胜于普通男性。
在塑造此类乡村女强人形象时,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普遍采用了一种“女高男低”的人物关系模式。女主人公往往个性成熟稳重、泼辣能干、目光长远,不仅在能力和地位上高于身边的其他男性,而且在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上也远比一般男性开明进步。如李淑霞不仅要与丈夫田宝的封建思想和大男子主义斗争,还要顾及与田家其他男性长辈之间的关系,要与自私的大伯斗智斗勇;张菊香也要在家里的几个男人之间周旋,既要安抚自私小气爱吃醋的丈夫李二柱,又要摆平固执守旧的公爹。而这些男性在作品中的作用便是不断给女性从事的事业设置种种障碍,如田宝在春种期间不顾李淑霞的规定私自进城揽活,并在伯父的指使下偷拿其他农场的草料,被李淑霞处罚时更是大闹会场;李二柱不仅不支持菊香的养殖事业,反而在竞争对手的挑唆下迷上赌博,无端猜疑菊香,差点给菊香的养殖事业带来灭顶之灾。而这些女强人在个人生活上也会存在某种缺憾,比如李淑霞为了送还田宝偷的草料,在路上不慎流产;张菊香同样失去了腹中胎儿,婚姻也岌岌可危,并最终和二柱离婚。当然,这些女强人最终会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挽回不利局面,并让其他男性刮目相看,心悦诚服:李淑霞完成了预定目标,迫使田宝兑现承诺大头朝下走了三圈;张菊香的豁达大度感动了公爹和大伯哥,并使李二柱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双双式的女性形象在新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出现,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她们在社会、家庭中占据的主导地位隐喻着乡村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作为对前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村女性形象的反拨,这类女性形象迎合了时代和社会对“男女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价值期待,也是对当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的一种想象性超越。
从十七年时期的李双双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李淑霞,再到新世纪之初的张菊香,其共同点在于她们都是泼辣能干的女干部、女强人。与前两者相比,新世纪之初出现的张菊香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如果说前两者与其他人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公与私之间的话,那么张菊香与其他人的矛盾冲突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上。李双双和李淑霞的形象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她们的泼辣能干和大公无私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与她们稍显虚饰和拔高的“崇高”相比,张菊香发家致富的初衷更多的是为了让家庭摆脱贫困,让个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她致富之后回报乡亲和社会的无私举动,则是一个乡村女强人朴素而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体现。所以,同为时代背景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张菊香显然比李淑霞更为真实,更具生活气息。
3.吴秋香和李月春:另类的乡村女强人
《雪野》中的吴秋香是80年代中期农村剧中出现的堪与现在的张菊香相媲美的女强人形象。吴秋香是一个热情、泼辣、勇敢的乡村女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她办养鸡场、开大车店,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自始至终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被迫嫁给老实木讷的齐来福后还敢去野地里与钟木匠私会;她敢于冒着被人说闲话的危险公开发布征婚启事。但是,从钟木匠到陈文彬,再到刘中志和林大个子,吴秋香身边的这些男性似乎都有着品德上的致命缺陷,一直到剧情结束,吴秋香的感情生活依然彷徨无着,女性能力和道德上的强势与男性形象的苍白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家的女人》中的李月春,也是一个另类的女强人形象。她18岁入党,在村里干了多年的主任,形成了说一不二、事事包办的个性,尽管已经出嫁多年,却一直是娘家实际的当家人。和吴秋香一样,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却喜欢青梅竹马的石岩,但她一直恪守道德,守在瘫痪的丈夫身边,尽心尽意伺候了他十几年。丈夫去世后,她本可以嫁给石岩,却为了提拔乡长而刻意疏远石岩以避免政治影响。当石岩赌气另娶他人之后,她才追悔莫及失声痛哭。而她提拔副乡长的事情最终落了空,在村主任的竞选中也败给了侄媳张菊香。这个个性独特的女强人形象同样令人难忘。
吴秋香和李月春这两个经历完全不同的女强人,却因为相似的个性和结局而具有了某种相似性。如果说李双双式的女强人形象被赋予了诸多社会意识形态的色彩,那么,吴秋香们的出现,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化反思的力度。应该说,吴秋香和李月春都是不乏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悲剧在于其虽然获得了个体的独立,但其个人生活却始终存在极大的缺憾。她们在个人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始终无法拥有期望中的美满人生。这些另类女强人事业的成功与个人情感的挫败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对比。如果说吴秋香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是因其“肯定妇女自身的价值,尊重人的本性和感情”,而“理想的价值观总会与传统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因而导致“妇女的觉醒往往带有悲剧意味”,那么李月春面对恋人石岩的情感表白却几次回绝的举动同样表明“封建主义幽灵还在人们头脑中徘徊”[4](P35)。作品结局中吴秋香在雪地中茫然伫立的身影和李月春的孤独失落,都为她们争强好胜的一生抹上了一丝感伤的色彩,也提醒着人们,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真正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
三、乡村世界的道德楷模:温柔宽厚的道德型乡村女性
温柔、贤淑、宽容、忍让、深明大义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贤妻良母,向来是中国文艺作品中层出不穷的女性形象。与能力和智慧超群却泼辣、独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女强人相比,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似乎更符合男性对传统理想女性的想象。在更具现代性的女强人形象不断成熟丰满的同时,另一类颇具传统女性美德的道德型女性形象也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渐渐浮出水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水乡一家人》中,有一个叫淑贤的好媳妇,便是一位集贤惠、孝顺、忠贞、忍让等诸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贤妻典范。尽管丈夫早逝,但她依然竭尽所能、不计回报地侍奉婆婆。“淑贤”这个极具传统意味的名字便暗含着创作者对女性传统美德的期待和向往。与大儿媳带娣、三儿媳爱娜的贪婪、冷漠、自私相比,淑贤的宽容和大度更能唤起人们对女性传统美德的赞美和响应。而《山道弯弯》中的大嫂金竹、《泥土》中的媳妇刘素梅、《篱笆·女人和狗》中的老大媳妇马莲,都是善良勤劳、隐忍大度、任劳任怨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的最大特点便是极富牺牲精神,往往为他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幸福,她们身上荟萃着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如金竹在丈夫去世后,为了小叔子的幸福自愿把丈夫留下的矿工名额让给小叔子,在小叔子受伤后又不顾周围的流言蜚语照顾他,体现出一个长嫂的无私奉献精神;身为家中长媳的马莲任劳任怨,对公公、丈夫的坏脾气甚至打骂都悉数忍受,从来不加辩驳、反抗。她们是传统的贤妻、孝媳,她们的传统美德无疑值得肯定和赞扬,但创作者在赞美她们的传统美德时,却往往有意忽略了其对封建专制男权的默认和服从。如马莲在遭受丈夫打骂后,面对丈夫破天荒的道歉,马莲受宠若惊地表示:“我有错,你才发脾气。”女性的宽容和忍耐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男权的膨胀,贤良淑德的女性便有可能变成封建男权统治下的牺牲者。譬如枣花,她也完全可以归类到贤妻孝媳的行列,但她毫无原则的忍耐和退让却将自己困在了丈夫为她编织的夫权的大网中。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创作者注意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温柔贤淑、逆来顺受式的贤妻孝媳形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型的慈母形象。《希望的田野》中的老姐姐、《美丽的田野》中的七娘、《母亲是条河》中的周翠、《老娘泪》中的程大娘等,以她们伟大的母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将女性和母性的传统美德提升到极致。她们以女性独有的坚韧品性和博大胸怀,含辛茹苦养大子女、弟妹,并以自身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影响着子女、弟妹们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她们都是乡土人格的典型代表和乡土道德的象征。如《希望的田野》中的老姐姐在父母去世后将弟弟徐大地抚养成人,为了弟弟嫁给了与自己条件并不匹配的丈夫,但因为丈夫善待自己和弟弟,所以老姐姐不仅不觉得委屈,反而以感恩的心情对待丈夫。在弟弟担任乡党委书记一职后,老姐姐一再告诫家人不要给弟弟的工作添麻烦。在家人的利益与弟弟的工作之间,老姐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弟弟。在病重弥留之际,老姐姐欣慰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并有所出息,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的父母,而弟弟工作后给她的296捆钱她至死分文未动。老姐姐如同神话原型中的“地母”形象,坚韧温厚而又朴实无华,其完美的乡土人格使其成为乡土道德的化身。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为了突出道德性女性的伟大,作品在情节设置上往往采用一种“苦情”模式,比如往往让这些女性年少守寡,让她们独自承担生活的苦难,有的甚至还要承担丈夫留下的“麻烦”。如七娘(《美丽的田野》)曾是养子李长顺父亲的童养媳,虽然没有嫁给他,但七娘却将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留下的孩子养大成人;周翠(《母亲是条河》)在丈夫死后,不仅要独力抚养自己的两个女儿,还在“情敌”叶秀走投无路之时,接纳了丈夫与其婚外所生的孩子,并视如己出。当然,她们的生命中也会出现其他优秀男性的仰慕和追求,但她们最终会因种种原因与其失之交臂,如七娘与老支书八路国、周翠与孙师傅都有过一段情感的纠葛,但最终都没有走到一起。周翠与孙师傅甚至已经订好了婚期,但在孙师傅的哥哥去世后,她为了孙师傅嫂侄的幸福和利益而牺牲了自己后半生的依靠。当积劳成疾、头发花白的母亲出现在学有所成的养子面前时,她的人生已如一盏枯灯,这样的情景让母爱的奉献和牺牲更加令人动容。也正因如此,这些伟大的女性往往晚景凄凉,人生不无遗憾。她们在获得道德上的肯定和赞美的同时,也让人感叹其颇具凄凉意味的结局。
当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以另一种形式补偿这些道德型女性的奉献和牺牲,并以这种补偿肯定和赞美她们的道德立场:去世的七娘享受到儿子和村民八抬大轿送葬的殊荣;风烛残年的周翠成为养子宝军最大的牵挂,甚至为了她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而专程回国;程大娘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唤回了失足的儿子,并让儿子在全村人面前跪地谢罪,挽回了程家的清白声誉。道德型女性的义举发挥了极其强大的道德影响力,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也完成了对乡村女性秉持的传统道德的弘扬,顺理成章地将她们树立为女性道德的楷模。
道德型女性形象的塑造秉承的多是中国传统苦情戏的戏剧模式。女性承受的苦难越多,牺牲越大,其形象便会愈加突出和感人,其道德影响力便愈加强大。但是,这一塑造模式也凸显出创作者的思维定势和创作误区:女性一定要牺牲自己正常的情感需求和健全的家庭生活才能彰显出其人格和道德的伟大吗?含辛茹苦的妻子和母亲必须要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才能功德圆满么?诚然,对于有着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观众而言,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容易被普遍接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作者让周翠为了养子宝军的成才,不惜牺牲两个亲生女儿的幸福;让七娘为了子女牺牲了自己与八路国的情感,这又何尝不是对善良柔弱的女性施加的另一种“暴力”?又何尝不是对男性价值体系的一种迎合与妥协?从这一意义上说,道德型女性形象的坚韧、奉献和牺牲大多无关女性个体的生命价值。也就是说,她们得到了传统男性话语的称赞,失去的却是女性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正如一些论者所质疑的那样:“如果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女性形象,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是否有着按捺不住的疑问?诚然,无私、宽容、牺牲等品德可以是社会美德,但是用这些词语习惯性地来评价女性时,它实际上已经纳入男性价值系统的伦理道德评价范畴,而非仅仅是社会价值评价。因为这些传统美德几乎全都是指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由于这些伟大的传统女性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家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劳心劳力中,当她们完成了养儿育女的既定使命之后,剩下的人生岁月的空白不能不让人感到女性生命价值的极大落空。这些富于传统美德的农村女性的选择常常是非自主性的。”[5]而从对女性命运进行深层人性观照的角度而言,“女性的个性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迷失了的自我回归本我的过程,也是自我回归于人的过程。如果离开了这样的一个价值标尺,那所有的美德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因此,传统性别话语的复归和传统女性形象的出现,也表明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中现代意识的部分缺失。如何塑造既有道德影响力又有健全的生命价值和人生追求的乡村女性形象,是创作者应该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问题。
四、需要“教育”和“改造”的落后女性:民间乡土生活的真实呈现
如果说道德型乡村女性是乡土大地上令人景仰的圣母,是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乡情伦理的化身,那么处在另一个极端的便是那些粗俗落后、愚昧野蛮、更具民间乡土气息的世俗女性。她们身上带有各种性格或道德上的缺陷,缺乏道德型乡村女性温柔贤淑、深明大义、忍让牺牲的品德,她们不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因此她们可以划归到需要“教育”和“改造”的“落后”女性群体中。
1.面目可憎的农村“长舌妇”形象
乡村社会,因其历史的久远和长期封闭滞涩的生活状态而累积了大量的陈旧积习和观念。数千年的乡村传统文化的制约,贫困、落后、封闭的生存环境的逼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生存经验和本能,使中国农民形成了愚昧、狭隘、固执、守旧、嫉妒、仇富等种种丑陋的农民劣根性,乡村生活的一成不变和单调乏味,更让谣言、闲话找到了滋生的土壤。村头、树下、井边、门口,这些农民尤其是乡村女人时常聚居的空间成为了谣言和闲话的发源地。女人们一边洗着衣服、纳着鞋底、打着毛衣,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听、传播、制造他人的消息是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常见的情形,也因此塑造了一种面目可憎的“长舌妇”形象。她们喜欢聚众扎堆,传播谣言,无事生非,挑拨邻里矛盾,借此虚度着无聊的人生。与他人有关的闲言碎语成为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的调味剂,填补了乡村女性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也给谣言的当事人带来了巨大伤害。
《雪野》中爱说闲话的大婶和爱吃醋的大娘是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出现较早的“长舌妇”形象,她们的存在让行事一向大胆泼辣的吴秋香也有所忌惮,怕被说闲话。而《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更是将此类乡村女性琐碎无聊的人生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展现出来。“蛐蛐叫夜蛙叫河,一波未平又一波。舌头煽风风煽浪,快嘴鸭子风轮车,陈规陋习是没影的锁,闲言碎语是扑灯的蛾……”《古船·女人和网》以插曲的形式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落后村社文化进行了形象的描绘和批判。剧中以胖嫂为典型,她和村中其他无所事事的女人热衷于在井台、村口等公共场所传播花边新闻,制造流言蜚语,似乎老葛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躲不开她们打探的眼神和夸张的嘴巴。枣花娘的意外落水身亡、枣花与小庚的婚姻悲剧,都与她们制造的流言不无关系。《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有个孙大彪子,不仅热衷于打探和传播他人隐私,更因和村长夫妇联手设计拆散了山杏和玉生而亲身参与了胡山杏的婚姻悲剧。无独有偶,《当家的女人》中的白面团也是此类面目可憎的农村妇女形象:她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先是趁张菊香家乱成一团的空当偷走菊香的两只兔子,更因目睹了李月春和石岩的“私情”而变得有恃无恐;继而蓄意挑拨菊香和二柱的关系,使夫妻俩心生隔阂;故意让李月春知道大柱和马寡妇的情感进展,导致李月春与菊香大闹一场;更热衷于传播李月春的闲话,让石岩心生嫌隙,最终导致李月春和石岩分手……白面团们传递的闲言碎语制造了许多“无事生非的悲剧”,“点缀”着乡村世界无聊、空虚的生活。农村“长舌妇”这一独特形象的出现,与乡村世界闭塞守旧的生活环境和由此生成的愚顽无知的村社文化息息相关。借助“长舌妇”形象,农村剧对这种落后的村社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和批判,传递出创作者对中国乡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文化反思。
2.令人爱恨交加的“泼妇”形象
跟农村“长舌妇”形象类似,精明自私、蛮不讲理的“泼妇”形象也是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常见的一类角色。她们常因一点小事便撒泼耍赖、吵架骂街,有的甚至因自私、懒惰、嫉妒、争风吃醋等原因而铸成大错,给他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些乡村女性个性的尖酸刻薄、无赖虚荣不仅是农民劣根性的一种体现,更折射出乡村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和依赖男性的现实。如《乡村爱情2》中的谢大脚,随着与长贵感情的确定,一改第一部中的泼辣形象,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泼妇”,动辄上演争风吃醋、撒泼打架的戏码:暗恋她的王大拿到象牙山投资,被她光着脚提着铁凳子追打;长贵穿了件新衣服到她那儿显摆,不想却将她激怒,衣服被撕了个稀巴烂。《种啥得啥》中李相平的嫂子桂风也是典型的“泼妇+妒妇”,不仅语言粗俗,而且自私霸道、蛮不讲理,婚后多年还要跟婆婆索要彩礼,对丈夫也动辄撒泼吃醋、无理取闹;该剧中的另一个农村女性许玉英亦是虚荣懒惰,对家人不管不问,对婆婆恶言相向,却梦想不劳而获,几乎将女性的所有缺点集于一身。谢大脚、桂风和许玉英们的“泼”和“妒”,除了传统文化积弊的影响,也源于她们对男性的强烈依赖和对自我的不自信,因此她们要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于男性身上,希望借助“泼”和“妒”的手段来抓住男性。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桂风无理取闹的吃醋行为让丈夫离她而去;谢大脚与长贵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除去这些个体形象,农村题材电视剧中那些尖酸刻薄、不求上进的乡村女性常常作为一个丰富、生动、感性的群体形象集体出现,如《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一群农村妇女,泼辣粗俗,虚荣懒惰,天天聚在一起打麻赌博,荒废正业,村干部们组织抓赌,她们却与干部们“斗智斗勇”,不肯收心戒赌;《刘老根》中的大辣椒、满桌子等中年妇女没事便聚在一起彼此炫耀和攻击……这些乡村女性的粗俗落后,与其封闭的生活环境、过低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不无关系。
上述女性当然不是上文提到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值得同情的柔弱的乡村女性,但她们却因更贴近乡村生活而显得无比鲜活真实。当然,她们的“恶”、“泼”、“醋”、“懒”等种种恶习在剧中往往会受到正面力量的打压和制止,其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得到逐渐改造:如唯恐天下不乱的胖嫂通风报信让葛家老大去草丛捉奸,却发现在草丛中谈恋爱的正是自己的女儿,以致在乡亲们面前颜面尽失(《篱笆·女人和狗》);孙大彪子在山杏出逃之后巧妙地掩护了她(《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许玉英在受到诸多教训后最终洗心革面回归家庭(《种啥得啥》)。这些落后女性的转变也体现出创作者改造落后女性的美好心愿。与毫无瑕疵、处处克己奉礼的道德型“圣母”形象相比,这些性情泼辣、言行粗俗、举止随意的女性形象常常缺少道德底线,但她们身上的世俗气息却也是民间乡土生活的常态,因而也更加生动真实。因此,尽管此类乡村女性的自私落后需要加以批判和改造,但从尊重个体生命需求的角度来看,这类女性形象反而能带给我们别样的启示。
综观30多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对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沿着政治、经济和道德这三个维度展开,其核心叙事动机在于追溯和描绘乡村女性争取政治、经济乃至思想观念独立自主的历程。乡村女性形象建构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时代意义与文化意蕴,而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也随着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而发生巨变,乡村女性形象也因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剧中常见的是传统伦理乡村中的苦难女性形象;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女强人形象占据主流,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乡村女性形象开始浮出水面;面对世纪之交的社会浮躁,道德型乡村女性形象则满足了人们在道德失范现实下的道德想象和寄托;出于创作者改造农村的想象,落后女性形象的出现呼应了对落后乡村进行改造的现实需求。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农村女性问题都在农村剧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无论是被送上乡村传统伦理祭坛的柔弱女性,还是独立自主、特立独行的女强人;无论是鞠躬尽瘁、默默奉献的道德型女性,还是需要“教育”和“改造”的落后女性,这些活跃于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无一不是乡村历史和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她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各异的心路历程和迥然有别的人生命运无疑能够引发观众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思,也“显示出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观众对乡村女性的不同程度的社会价值期待”[6]。正是借助这些乡村女性形象在时代中的审美衍变,通过对她们的婚恋情感、人生命运及未来出路的展示和思考,农村题材电视剧完成了对乡村传统、乡村现实和乡村文化的探索与考察,完整地勾勒出一幅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对于农村女性形象建构承担着远远大于它自身的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7]。这些栩栩如生、风貌迥异、内涵丰厚的女性角色,为电视荧屏的人物长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形象,大大拓宽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表现空间,见证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成就与魅力,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上述女性形象所承载的审美特质和文化反思,已经超越了农村题材电视剧这一单一的类型范畴,而可以推衍到其他的题材类型和艺术样式。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能塑造出更为别具一格的乡村女性形象。
标签:李双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