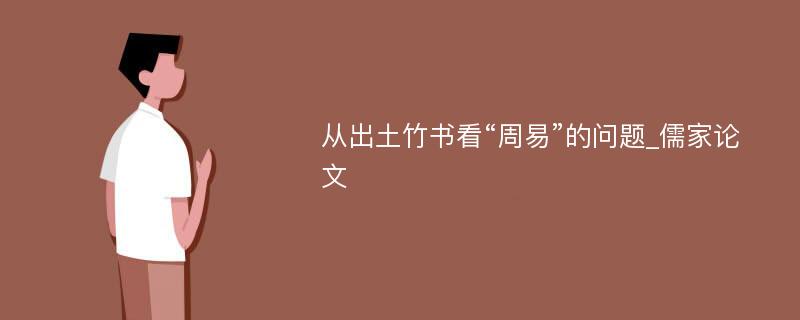
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竹书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0)04-0008-13
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有关先秦古籍的竹简、帛书纷纷出土,分外引人注意,已引起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相信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价具有较大的帮助。就出土竹简《易》书或与《易》相关的简书来看,从古至今已经有几次颇为重大的发现,它们都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与资料来源。
一、《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事因王充《论衡·正说》篇中的有关叙述而起。《论衡·正说》:“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同篇又说:“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
《论衡·正说》篇所言“秦燔《诗》、《书》”的说法,多见史载,《史》、《汉》皆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之言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对秦始皇的这番秦言,主要是针对民间学术和诸儒的妄议而发的,维护的是强秦的既独统治利益。秦燔《诗》、《书》、百家语者,乃燔烧民间此类书籍;秦博士所职及皇家所藏图书,则不在燔烧之列。秦所藏图书殆毁于项羽焚秦之时。不过据《史记》秦燔《诗》、《书》及“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两点,一般认为《易》因本卜筮之书而得不燔,此说可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而《史记·儒林列传》:“乃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土,六艺从此缺焉。”“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汉书·儒林传》亦云:“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六学”即“六艺”。“六学从此缺矣”,有多种理解,从《易》来看,或说《易》因卜筮之书不焚,其他五经皆焚;或说《易经》因卜筮之书不焚,而《易传》及诸说《易》之文章,同其他五经、百家语皆在焚烧之列。[1]前一说,在《论衡·正说》篇中可以得到旁证:“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吏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此引一段话第一、二句有点费解,可能有误字,不过大意是清楚的。王充云秦“尽烧五经”,联系它文,当指《诗》、《书》、《礼》、《乐》、《春秋》,《易》因卜筮之书不焚。而后一种推论,持说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史》、《汉》皆言《易传》曾经孔子之手整理或他亲自创作,经过几百年的传播,《易传》已具有经典的意味。《史》、《汉》系列易学的传承线索比较分明,与其他五经的传承显有较大的区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因此,《易传》及说《易》之作是否列入“百家语”的范围而予以烧焚,应当审慎考虑。而只要《易经》不在禁绝之列,则随其传播、应用,传说之学必然兴盛、流衍。马王堆帛书有大量《易》书,这些《易》书当有不少传自先秦,有些亦有可能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被传抄过,因此《易经》及其《传》在传《易》诸学派之间,比较可能是自由传播的,不存在禁绝的问题;即使有禁令,亦当是虽禁而实未禁。马王堆帛书《易传》自身表明的研《易》诸家有孔子、子贡、缪和师、昭力师、缪和、昭力、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平等人、皆其证。
顺便指出,李学勤先生认为:“昭力的昭,如所周知是楚氏,楚同姓昭、屈、景三族之一。缪和的缪,通穆,也可能是楚氏。……两篇(《缪和》、《昭力》)以缪和、昭力冠首命题,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楚人作品。”[2]王葆玹认为:“帛书中的缪和其人显然即是荀子的再传弟子穆生。”[3]王博对缪和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缪和》中提到的缪和或即是穆生,而穆生也同时是《缪称训》的作者。”[4]
不过《史记》、《汉书》所记与申公相关的缪《或穆》生有二人,一为申公同学,一为申公弟子。《汉书·楚元王传》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此穆生即申公同学,鲁人,年岁可能长于申公,二人俱为荀子再传弟子。鲁穆生善《诗》,习《易》,能以《易》理“见机而作”,以微知彰。《楚元王传》云:“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酒醴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穆生察几微之动而预知吉凶,后楚王戊果“与吴通谋”,起兵作乱。而穆生离开楚王戊之后是否立即投到了淮南王刘安的门下啜食残羹?史书未言。但从穆生的智慧与性格来看,不当刚离狼窝又入虎口。淮南王刘安封于文帝十六年,自杀于武帝元狩元年,在位共四十二年。《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后一直阴密谋反,“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终致杀身之祸。因此,穆生不太可能托身淮南王刘安门下以寄生糊口。至于刘安门下是否还有其他穆生,或谁作《缪称训》,因问题不在讨论之列,故不议。既然穆生不太可能投入淮南王门下,那么他离开楚王之后,是否远游到了长沙,而作帛书《易·缪和》?衡量时间上的差异(楚王戊继位在文帝前元6年,帛书下葬年代为前元12年),及缪和在帛书中自称为弟子这一身份来看,此种可能性是很难成立的。如此,则又是不是鲁穆生年轻时的学《易》作品?穆生年轻时与白生、申公、楚元王习《诗》于浮丘伯,习《易》的可能性是有的,因古从在精研一经(或一书)的同时常兼读诸书,但谓此鲁穆生即为缪和,恐流于推测、附会而已矣。而帛书《缪和》中的缪和只是六位问《易》的弟子之一,没有可靠证据说明该篇为缪和所作;相反容易说明此篇帛书更可能成于其弟子辈之手。又,帛书缪和是不是《缪称训》的作者(所谓“缪生”)?衡量证据的多少与可信的程度,实不敢妄断。
《史》、《汉》所记还有另一缪生,是谓兰陵缪生,乃申公弟子。《史记·儒林列传》云:“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汉书·儒林列传》所叙亦同《史记》。兰陵缪生并不就是鲁穆生。兰陵与鲁地望有别,而“缪”与“穆”两字史载有异,是此二氏本来相别乎?当然,缪可通穆,但字音上的相通并非必定姓氏上的相同。帛书《缪和》之“缪”正与兰陵缪生之“缪”相同,且兰陵为楚故县,因而即可谓此兰陵缪生作《缪和》篇么?兰陵缪生当系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耻之而归鲁教授时期的百余名弟子之一。学成,缪生为《诗》博士,后官至长沙内史,与《缪和》易书的下葬年代已差有年矣。如果《淮南子·缪称训》亦为某一缪生所作的话,那么我们可知的就有四位缪(或穆)生,帛书《缪和》篇之缪和,申公同学鲁穆生及《缪称训》的作者所谓缪生,三人皆通习《周易》,而作为申公弟子的兰陵缪生于《易》是否熟习,则未尝确知。总之应把四位缪(或穆)生分别开来,一为帛书缪生,一为鲁穆生,一为兰陵缪生,一为淮南缪生。当然四位缪(或穆)生从其地域看,皆与楚密切相关,但帛书缪生(名和)必定出自荀门么?实难推定。不应把四位缪(或穆)生滚作一团。
回过头来再论暴秦是否焚《易》的问题,在史书及帛书中有些补证。《汉书·艺文志》易类记有汉初几家《易》书,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从先秦到两汉的易学传承头绪比较复杂,秦帝或未曾焚烧诸研《易》之书。而从逻辑上推论,设若《易》(《经》)因卜筮之书而不焚,可以任由民间传播、研习,则此间学习者必甚夥众;而既然研《经》不已,则说《易》之作前后衍生、相传,不可免矣。因此《周易》经传大体皆在未禁之列,这也是易学昌明,到汉代跃居五经之首的原因。帛书《要》篇云:“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廖名春认为“‘於’当通‘疏’”,不当作“阏塞不通”解。[5]“疏”训“失”。“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两句正相对为意,可从。但《要》这两句话是在什么时代说的,尚难肯定。如果认为是汉初的创作,则“《周易》未失”一句表明《周易》经传的传播未经秦火。
《论衡·正说》云:“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秦之”,“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逸《礼》、《尚书》各一篇具体指什么,今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只就《易》来说,所益逸《易》一篇,《正说》并没有指明。又所谓得逸《易》一篇,并云“《礼》、《易》篇数亦始足,”,可知未得此逸篇之前,官方《周易》或正统派《周易》所据的传本原当有一个固定的篇数;而得此逸篇之后,当合乎《周易经传》十二篇本或当时师传所云的流行说法。扬雄《法言·问神篇》云:“或曰:《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问神篇》所云“《易》损其一”的记载与《论衡·正说》相一致,所缺一篇当即是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佚《易》一篇,推敲《正说》“《礼》、《易》篇数亦始足”之语即可知。因此,不当认为河内女子得佚《易》一篇后,仍阙《杂卦》一篇。(注:王葆玹认为河内女子发现的逸《易》乃《说卦》,而《法言·问神》篇所云“《易》损其一”的一篇乃指《杂卦》,在西汉末年补入,“极有可能是王莽时的创举”。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93-395。)[3]那么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篇到底是什么?是《说卦》三篇,《序卦》或《杂卦》么?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黄晖《论衡校释》注解《正说篇》上述一段,引《经义丛抄》徐养原云:“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大誓》,唯《礼》无闻。”所谓以他书考之,不知考之何书,这是后人“《说卦》三篇后得说”的先导之一。不过《隋书·经籍志》早已有如此看法,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论衡·正说》云孝宣帝时得逸《易》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云得《说卦》三篇,不但指明了篇名,也说明了篇数。但两种说法之间的不一致是颇为明显的。于是为撮合二者,抹平裂痕,故有《说卦》一篇变为三篇的说法,三篇者《说卦》、《序卦》、《杂卦》也。(注:郭沫若云:“《论衡》所说的‘一篇’,《隋》说为‘三篇’,好像不相符,其实只是证明《说卦》、《序卦》、《杂卦》的三种在初本是合成一组,后来分成了三下罢了。”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6]今观《易传·说卦》以下三篇,大体各有其内在的中心内容和编联方式,而谓此三篇本为一篇,实淤塞不通,不足取论。又,到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时,《说卦》以下三篇本为一篇如可成立,那么《淮南子·缪称》引《序卦》文来推断,则《说卦》以下三篇在汉初皆存,何来“得逸《易》一篇”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序”,今人一般理解为动词,有“叙”、“编系”、“作”等义。《史记正义》则云:“序,《易·序卦》也。”依此,则上句当逗点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云云。如此,《易》十翼《史记》唯缺《杂卦》一篇未叙。孔子时,《易传》六《或九》篇是否已全备?已不得确知。不过史迁的叙述表明了《序卦》、《说卦》乃先秦之作,当初并未将其合为一篇。《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亦表明《说卦》、《序卦》、《杂卦》三篇皆当是先秦作品,且未见将《说卦》以下三篇合为一篇的蛛丝马迹。《淮南子·缪称》:“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此即引《序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两引文辞有不同而语义相同,且《缪称》直接称“《易》曰”,可知《序卦》必出自于先秦。张岱年先生即有此论[7]。我颇为同意这一观点。这样,加上后得的一篇《杂卦》,《易十翼》其实都传自先秦。
何以见得后得的一篇《易》书即是《杂卦》而非《说卦》呢?首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言先秦有所谓《说卦》一篇,亦可间接说明《说卦》在当时似已流行。李镜池认为“《史记》不特没有‘《说卦》’二字,连‘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一句也是宣帝时京房等插入”的看法,[8]除了浮想臆断之外,一无是处。其次,马王堆帛书《易之义》已包括了《说卦》前三章内容,说明《说卦》的成立至少已有较早的渊源,而直谓《说卦》作于焦京之后,河内女子所发一篇逸《易》即是《说卦》的观点,已失之武断。其三,《说卦》的许多内容已散见于子、史诸书。《说卦》的八卦诸象说,多已见于《左传》、《国语》及《彖》、《象》、《文言》、《系辞》,而八卦的时空分布说亦有悠久的渊源。(注:刘大钧云:“在《周易大传》几篇中,当以《说卦》篇为最早。”刘大钧《周易大传我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9]《说卦》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说卦》“帝出乎震”一段文字的要义,就是以四时八方与八卦相配合,并进行易学的解说的。实际上仍然是阴阳家学说与易学的一次结合,也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八卦的一次相互配合。[10]其渊源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以及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是难以分开的。《汉书·魏相传》云:
(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秦之,曰:“……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
魏相,武帝至宣帝时人。上引文乃魏相上秦宣帝之言。《魏相传》云相“少学《易》”,又说“相明《易经》,有师法”,可知魏相的《易》学颇有渊源和成法。魏相秦文把阴阳五行思想与八风、八卦配属起来,亦当有渊源与成法,《传》云“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秦之”即是明证。《明堂月令》或谓即《礼记·月令》,刘向《别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属《明堂阴阳记》的一篇。《月令》是阴阳五行系统的扩展,然并未纳入八卦方位。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至武帝时,阴阳家们早已把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这些因素统合起来,而在此系统中颇为容易显现的“八位”一环亦非常容易与八卦配合起来,不应该武断地否定阴阳五行与八卦方位早已有机结合的那种可能性。(注:朱伯崐:“(《说卦》)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朱伯崐《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5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1月北京第1版。)[11]
《易阴阳》不知何书?顾名思义及兼察魏相所言,可知是《易》学与阴阳家理论相结合的作品。因此《易阴阳》一书当不缺少八卦与阴阳、四时(甚或五行)相配合的内容。这样看来《易阴阳》确有同于《易·说卦》“帝出乎震”章的内容,而成为当时的流行观点之一矣。但《易阴阳》并不就是《说卦》,甚至基本上不同于《说卦》,不然当时的学者就会已如是指出了。那么到底《说卦》出自何时?是宣帝时吗?恐不应当如此推测。细察《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文字与思想尚较为原始。文中特别强调“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等内容,可见其时尚处八卦与四时八节八方相配合的初创阶段。因此,《说卦》必当出于《易阴阳》一书之前,而为先秦作品。此外《说卦》在西汉时被人引用多次,见于《汉纪》、《汉书》之中,[12]因此,以《说卦》必定出于汉宣帝之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说卦》在汉初仍然流行,那么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一篇逸《书》就只能是《杂卦》了。《杂卦》虽然晚得,但因为是发老屋所得竹简,故其制作必定在先秦,而有可能匿迹于秦颁禁书令之时。
对于《易传》还需要指明的是,其一《易十翼》的名称当自后起,《汉书·艺文志》正式有“十篇”之说,而《史记》则只叙有六篇《或九篇》。《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该文开篇即云:“《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易大传》并非就是《易传》,二句皆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传》出现,因而不太可能是二名混用。但《集解》及颜师古注引张晏的话说:“《大传》谓《易·系辞》。”《易大传》即是《易·系辞传》,今人亦信之颇笃。然《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记刘向对曰:“……《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此句不见于今本《易·系辞》,亦不见于《易传》,帛书《易》也无此句话。看来,《易大传》可能别为一书,虽与《系辞》有些语句相同,但究竟不是《系辞传》。
其二仔细考察司马迁在不同地方对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记载,用字都准确一致,然则否定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史记》只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而《汉书》更云孔子作《易传》(亦示后人毁谤孔子与《易》有干系的把柄),以帛书《易》观之,否定孔子与《易》有很深关系的看法,已经完全错了。
其三比较《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易》六传的编排顺序与今本距离颇大,而《汉书·艺文志》所记十篇较合于今传本顺序,试列表如下:
今传本
彖传(上,下) 象传(上,下) 文言 系辞(下,下) 说卦
序卦
《汉书艺文志》
彖(2) 象(2)系辞(2)
文言(2)
(说卦)(1) 序卦(1)杂卦
《史记·孔子世家》 序(1) 彖(1) 系(1) 象(1) 说卦(1)
文言(1)
杂卦(1)
《汉书·艺文志》所记《易传》篇目顺序不但与今传本基本相同,而且篇文的分解亦相同,表明《易传》经过汉儒的章句解析,已经成熟定型了。而《史记》论研易或“正《易传》”,以《序》传列为诸传之首,颇有道理,不同的《序》传表明有不同的传本、不同的经文编排卦次以及不同的易学传承流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或《儒林列传》所云易学之传递脉胳,当是孔门易学之嫡传,未尝不可信也!帛书《易经》的排列顺序与今本颇为不同,更强调八经卦相重的有序组合,黄寿祺、张善文归纳其组织原则为:“上卦为纲,下卦为目。”[13]诚有见地。帛《易》,与楚地《易》学传承颇有干系。以帛书反证孔门《易》之嫡传,则把《序卦》传列为诸传之首,以见与他家的分别,及作为自家的标识来看,是十分必要的。而《序》传不在着重阐明今传本《易经》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孔颖达《周易·序卦正义》)的组织原则,而在于着重阐明如此组织所蕴含的道理,通过此顺序而来的道理而有效地规范了孔门嫡传《易经》的编排顺序。孔子尚德义而后其祝卜的言行(帛书《易·要》),正与此相一致。
总之,从出土材料和世传文献相结合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其中《杂卦》篇是否必定传自孔门,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虑;而《说卦》、《序卦》二篇按《史记》的记载则与孔子本人有较大干系,虽然二篇未必就是孔子研《易》亲手之作。又,“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此篇当即是《杂卦》,说《杂卦》后得可,但说《杂卦》出自汉初传《易》家之手不可;而把《论衡》云“得逸《易》一篇”,一分为三,云“得逸《易》三篇”,也当是错误的。
二、晋汲冢竹书《易》述论
西晋汲冢出土竹书,《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晋书·卫瓘传》、《晋书·荀勖传》、《晋书·束晰传》、荀勖《穆天子传序》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等皆有记载。《荀勖传》说:“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祕书。”《中经》,由魏祕书郎郑默始制,荀勖因之更著《中经新簿》。汲冢竹书即列于《新簿》丁部(《隋书》卷三十二《经籍一》)。
竹简出自何墓,诸书记载不一。《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见《晋书·卫瓘传》)皆言汲冢为魏襄王墓,王隐《晋书·束晰传》言汲冢为魏安厘王墓,唐修《晋书·束晰传》或言汲冢为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注:《晋书》卷五十一《束晰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竹简出自何墓,诸书记载不一。除此之外,汲冢竹书何时出土,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太康元年说,有太康二年说,和咸宁五年说。)诸书言冢冢为魏王墓,当有所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竹简)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国,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戍,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位,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独记魏哀王之二十年”之“哀王”二字,竹简原文当作“今王”,下文云“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可知。但“今王”真的是指“哀王”吗?竹书《纪年篇》并未直接点明为哀王纪年。《史记·魏世家》“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句,《集解》云:“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和峤所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与杜预在秘府所见简文原本一致。而裴骃《集解》又据《世本》判断《史记》之误,认为“无哀王”,进而断定《纪年》所谓“今王”实即“魏襄王”,(注:朱希祖认为杜预把“今王”当作“哀王”有误,“哀王”实为“襄王”。朱希祖《汲冢书考_·汲冢书来历考第一》附《魏哀王魏令王考》,中华书局,1960年。)[14]论据是坚实的。不过《索隐》云:“《系本》(《世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工甚明,盖无足疑。而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纪年》出自先秦魏王墓,《世本》传自先秦,魏有无“哀王”,当以此为据,而谓“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殊不足论。《春秋左传正义》亦从《史记》之说,云:“《史记·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位;十九年卒,子安厘王立。哀王是安厘王之祖,故安厘王之冢埋哀王之书。”是不辨行简《纪年》原文,而直以《史记》裁断出土竹书,误矣。比较诸书记载,杜预最详,汲冢竹简《纪年》所记事件年代当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但是《纪年》终结的年代并非即是汲冢人葬的年代,汲冢墓入葬于公元前299年之后是可以断定的。这样汲冢墓到底是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呢?比较可靠的推测当然是以靠近竹简《纪年》终结的时间为妥,荀勖《穆天子传序》即如是云:“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对于此点,李学勤先生论证道:“1975年末,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小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编年记》一书,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今’三十年的史事。此‘今’指秦始皇,其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墓主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鉴定其骨骼约年四十至四十五岁,可知他应即卒于始皇三十年。这个例子和汲冢的《纪年》相似,从之可以推论,汲冢的墓主很可能死于魏襄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的时候。假如冢确为王墓,那就只能是襄王的墓,不会是更晚五十多年的安厘王的墓。”[2]据此汲冢很可能是公元前296年或此后不久入葬的魏襄王墓,宽泛说来即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这样汲冢竹书皆当是战国中期或此前的作品。
汲冢竹书颇丰,《晋书·束晰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束晰传》说“得竹书数十车”,又说“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晋书·武帝纪》云“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祕府”,卫恒《四体书势》说“得篆书十余万言”。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春秋左传正义》云:“《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据《束晰传》,其中的竹简《易》书有《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师春》一篇。与《易》或有关系的竹书有《琐语》、《穆天子传》。此外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又说“别有《阴阳说》”,《阴阳说》不见于《晋书·束晰传》,但亦是当时《易》书一篇。
《易经》二篇,王隐《晋书·束晰传》称“《周易》上下经二卷”。此《易经》二篇与今传本上下经同,杜预《集解后序》云:“《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唐修《晋书·束晰传》也云:“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可见汲冢竹书《易经》与汉晋儒家正传的《易经》本子是相同的,亦与汉中古文经相同。《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如此,今传本《易经》的定本早已流行于战国中期矣。马王堆帛书《易经》卦爻辞与今传本略有不同,差别不大;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是在八经卦的两组顺序基础上相重合的结果,与今传本“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序卦》原则颇有差别。因此从汲冢竹书《易经》、刘向所见中古文《易经》到今传本《易经》近属同一易学传统,其卦序排列相同;而帛书《易经》当属另一易学传统,或系前者的交通。
不过,有学者认为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在今传本《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基础上改编拟定的,恐只是一种比较可能的推测而已。从今传本被史载为孔子编定的儒家正统易学本子来看,设想帛书《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起源晚于今传本《易经》的排定是合理的。由于春秋战国传《易》诸家多矣,因而帛书卦序未必晚于今本《易经》的确定。今传本和帛书本《易经》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都非常有规则,当反映了两派传《易》学者的不同玩《易》标准。今传本《易经》的标准显现于《序卦》传中,正是由于《序卦传》的存在,使从孔子到两汉,儒家正宗的易学传统延绵不绝,不自扰乱。而帛书《易经》的卦序传统,是否可以在秦汉之际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不当以两本卦序的比较,轻易否定这种提问的必要。
《易繇阴阳卦》二篇,《晋书·束晰传》云:“《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王隐《束晰传》,谓“有《易卦》,似《连山》,《归藏》”。王隐所说的《易卦》,是否即是唐修《晋书》所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尚不得而知。唐修《晋书》言《易繇阴阳卦》二篇,王隐所著《束晰传》对《易卦》未言篇数,一般应看作一种。唐修《束晰传》说《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大体相同,繇辞不同。而汲冢《易经》,汉中古文《易经》、帛书《易经》、今传本《易经》、阜阳汉初竹简《易经》[15],其繇辞基本相同。由此可以判断《易繇阴阳卦》二篇当是另一系统的《易》书,这一《易》书是否即是《连山》、《归藏》的传本?颇难断定。不过相传从上古流传到后代的卜筮之书有三卜、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不反对与三易之说相关。因此,把《易繇阴阳卦》二篇与《连山》、《归藏》联系起来尚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能的推测。[2]而王隐《束晰传》说汲冢竹书中有一种简书“似《连山》、《归藏》”,则《易繇阴阳卦》二篇当与《连山》、《归藏》的传本相关,而《易繇阴阳卦》颇有可能即是《易卦》,二者当属异名同谓。
《连山》、《归藏》,《汉书·艺文志》未录,《隋志》亦无之,后儒多疑其为晋隋间的伪作。不过“自孔子降而至始皇时,《连山》、《归藏》又尚无恙也”[16]。《隋书·经籍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桓谭《新论》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说:“《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金楼子·立言》引杜子春云:“今《归藏》先坤后乾,则知是殷易知矣。”《礼记·礼运》郑玄注亦云“其书存者有《归藏》”的话。“《连山》八万言”的说法,黄宗炎已力驳之。总之《归藏》汉时可能仍尚存,至三国晋初时损失惨重,隋尚存其遗,所以《隋志》说《归藏》“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隋志》又说:“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此即是列于易学诸书之首的“《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由前面的引文可知,此十三卷《归藏》已注入了非常多的水份,当合于“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的评价。此点与当今相继发现的卜筮简书情况相一致。晋《中经》即荀勖所著《中经新簿》。荀勖,汲冢竹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荀勖未言《易繇阴阳卦》或他篇竹简《易》书似《中经》《归藏》,则竹简《易》未必基本合于当时《归藏》。于是,王隐所见《归藏》其来源如何,也是颇有疑问的。郭沫若说:“《易繇阴阳卦》,又有《归藏易》的名称。《隋书·经籍志》上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但晋的《中经》所著录的都是汲冢的出品。《晋书·荀勖传》上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述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此可以知道所谓《归藏易》不外是由荀勖对于《易繇阴阳卦》所赋予的拟名。……荀勖得到了《易繇阴阳卦》,便任意把它拟定为《归藏》罢了。”[6]郭氏此说太过于奇巧,不可过分信任,但也说明不应该把《易繇阴阳卦》(或《易卦》)简书与《归藏》直接等同起来。虽然今传本《归藏》有许多地方颇为值得怀疑,但是这并不反对它有许多材料来源颇为悠久古远的看法。[17][18][2][15]且惟其因为如此,才可能发现《归藏》与简帛书《易》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总之,有关《归藏》的真伪,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应该把问题简化为只通过比较简帛《易》与今存本《归藏》有相近或相一致之处,即断定《归藏》本身在制作、传统的问题上不伪。
回过头来反观王隐《束晰传》“有《易卦》,似《连山》、《归藏》”之语,可知当时《连山》、《归藏》已相混淆,而《易卦》并不即是《连山》、《归藏》。或许王隐所见《连山》、《归藏》是经过多次辑录或由其他卜筮材料编纂而成的。因此对于此篇简书当依唐修《晋书·束晰传》所云,其性质与《周易》大体相同(“与《周易》略同”),不过爻辞比较不同而已。《易繇阴阳卦》当为另一学派易学经书,或系与孔门《易》并传之《易》书。这是春秋战国易学发达,流派纷呈的又一个例证。
《卦下易经》,《晋书·束晰传》云:“《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李学勤先生指出,《卦下易经》这个题目或当分成两载读:
卦下
易经
《易经》是大题,《卦下》是小题。这是古人标题法之一。如此依今人习惯,当断读为《易经·卦下》。[2]依此读,可以推论《易》(或《周易》)已被尊称为“经”了,这与郭店楚简提供的相关信息较一致。郭店简的入葬时间与汲冢简基本同时或略早(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的墓葬年代约当战国中期偏晚的时候[19]),可互相证明。有《卦下》,则当有《卦上》,《卦上》、《卦下》相补充配合,就是一篇完整的《说卦》文章。不过,《卦下易经》只是“似《说卦》而异”,而不是《说卦》的一部分,所以《卦下易经》与今传本《说卦》只是在性质上相似或相同,而在具体卦象论上则有较多的差异。又《说卦》前三章见于帛书《易之义》篇中,于是《说卦》原来的样子也需要论证。今本《说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乃前三章,通论象位结构的义理本原,第二部分即四章至十章综论八卦诸象,末八章即第三部分分论八卦诸象。其中第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分隔较大,并且出现于帛书《易之义》中,证明《说卦》前三章与后面诸章是经过一次拼接组合起来的。《说卦》还有许多象例已见于《左传》、《国语》及《易·彖》、《象》、《文言》、《系辞》等书,[20]说明《说卦》可能曾综合前人象例而成。又《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骋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其时《易象》已成篇。今《周易》有《象传》,当可省称为《易·象》。如此,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即是今传《周易·象传》否?如果不是,那么《易·象》有可能与《卦下》、《易经》、《说卦》三书性质相同,但有时间先后的差异,而《说卦》的成立不得晚于战国末期。然则《说卦》前三章与帛书《易之义》的关系怎样?我认为二者各异传而分流,不应该简单地认为谁抄谁。审帛书同于《说卦》前三章之文,在《易之义》篇中与前后文不相接而独立为一段落,正是供人挪动文本的内在依据,由此也可以说明《易之义》也许是重组抄作之文。(注:以上论述是建立在《卦下易经》可分读为《卦下易经》的基础上的。但是否应如此分读,还是一个问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杜预云《彖》、《象》、《文言》、《系辞》四篇,恐是省文,乃以《易十翼》前四传概括而言《易》十传,这种方法古书多见其例。依此则《阴阳说》当不与通行本《易传》相同,此正是杜预言“别有《阴阳说》”之义。今出土帛书《易之义》开篇即云:“子曰:易之义谁(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21]是《阴阳说》与《易之义》相关之证。《易之义》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第六幅帛书易传中的第三篇。它紧接帛书《系辞》,另起一行,顶端有墨钉标志。篇末有篇题,并记有字数,由于字迹模糊,释写者尚未识出。今拟篇题,乃摘取首句三字而成,未必允当。此篇首句即云“易之义唯阴与阳”,又全篇文章与阴阳、刚柔概念相关紧密,乃或亦可称之为“易阴阳义”类题目。(注:廖名春云:“所谓《易之义》应称之为《衷》,《衷》才是这一篇佚书的书名。”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1997年第2期。)[22]如此,则与杜预说汲冢竹简有《阴阳说》一篇正相配合。杜预所记《阴阳说》,不见《晋书·束晰传》,可能表明《束晰传》并未把全部易书标名出来,不当以为《阴阳说》必定同于《束晰传》所列的某一部分。汲冢竹书,史载有“数十车”,“十余万言”,《束晰传》所列竹书可能并非其全。《阴阳说》对于先秦阴阳思想的流布及其与易的关系,当有重大的意义,惜其重佚,后世学者只好空自喟叹。
《晋书·束晰传》:“《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公孙段与邵陟论易”,表明二人的关系密切,且对《易》有较深的研究。而《公孙段》二篇,性质类似帛书《缪和》、《昭力》以及《系辞》等篇。[2]再次表明,先秦除有孔子一派儒生研易外,他家研易者实不在少数。
《师春》一篇,《晋书·束晰传》说它“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师春》是竹简原有的标题,此标题与“书《左传》诸卜筮”并无字面上的关系,因此才有所谓“‘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的推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变云:“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杜预《后序》所云比《束晰传》更为详细。《后序》说“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表明《师春》一篇是完整有序地照抄照录了《左传》原有的卜筮文字,包括龟卜与《易》筮两方面的神事;不仅如此,《师春》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一定的疏解,而文义又同于《左氏传》。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师春或许与左氏(左丘明)有较密切的关系,是左氏后学乎?无可确知。而《左传》当是战国早中期的作品,竹简完全可以证明。而今人说刘歆把《师春》割裂编入《左传》(注:郭沫若说。李镜池已驳之。)[6][23],颠倒古书源流之序,殊不足论。
《师春》,宋代尚存。宋仁宗嘉佑年间,苏询编定六家谥法,采及《师春》。北宋末,黄伯思校雠秘阁所藏《师春》五篇,事见所著《东观余论》卷下《校定<师春>书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汲冢师春》一卷。宋人所见《师春》多云“诸国世次”、“律吕谥法”、“卦变杂事”等内容,与杜预所云有较大差异。
竹书《琐语》记“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晋书·束晰传》),似看不出与《易》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不过这类竹书许多记载着以《易》进行占卜的结果,当今出土楚简多见其例。《穆天子传》卷五则有一条筮例与《易》有关:
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絺紵三十箧。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
穆天子狩猎于苹泽,先以《易》问天意。筮史狐□筮得一卦,遇讼。讼,坎下乾上。逢公占曰有“薮泽苍苍”之象,此象例不见《说卦》。今联系《说卦》及《左传》易象例,勉强解之,坎,陷也,有水象,所谓“薮泽”也;乾,天也,天之正色,苍苍然,所谓“苍苍”也。讼九五爻得其中正,又遇天子求筮,所以说“其中□,宜其正公”。《讼》之繇,“薮泽苍苍”,又“宜其正公”,正是“畋猎则获”之意。所以这一次占筮是大吉大利的。这也是穆天子为什么要赏赐逢公及筮史的原因。
此筮例,当属于卦占,不属于爻占。卦占比较便于占说,逢公以意逆之,可谓于天人两不偏失。在《周易》,九五爻得其中正,往往吉辞。讼九五爻辞云:“讼,元吉。”可知此爻亦一卦之主,又与天子求筮相合,所以穆天子就非常高兴了。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穆天子传》此筮例不是用的《周易》筮法,那么当时诸《易》的架设理论基础当有相互一致的地方,如卦象的相近,爻位的相通等。从逢公所占之辞来看,与《周易》有较大差别,因而我比较相信此便不是用的《周易》筮法。《左传》筮例,往往先用它《易》,然后才及《周易》,似乎在当时《周易》尚未占据正统地位。《周易》属于流传民间而影响颇大的新兴易学。《易》筮有一定的法则,一般由筮史来做。但解释的好坏或其意向,往往与释占者密切相关。《左传》易筮尤见分晓,而此则筮例已发其端。此外,由于当时卜筮之学甚浓,说易者当甚众,而能理解易筮的人则更不在少数。从此例到《左》、《国》,可以知其大概。而《易》为卜筮之学,其所由来者远矣。
附记:本文的写作,陈伟先生及业师萧汉明教授提供了部分资料;本文的修改,得到了刘大钧、陈鼓应先生的批评和指正。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0-08-02
标签:儒家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易经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汉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易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