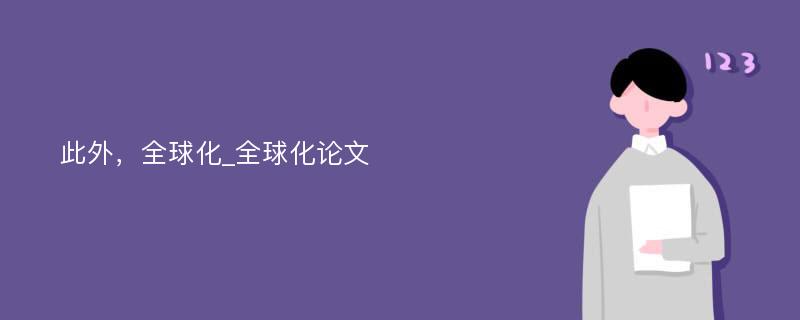
再说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无可回避
全球化作为历史事实,以及如何面对全球化,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一种是以“全球化”之名,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之实,获狭隘民族主义私利之行径;另一种是符合文化发展本性的全球化,指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与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这种全球化,即使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我赞成后一种对全球化的理解与概括。
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是难以避免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方面都是如此。地球上不同的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的文化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差异再大,也很难避免互相之间发生联系和影响,尤其是在现代。学界一般认为,语言和文化的扩散存在两种模式:一为人口扩张,即人口迁徙模式;一为文化传播模式,即人群间有文化传播、基因交流却有限,如英语(文化)在当今各国之普及。不同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及文化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交融,虽然有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方面的因素,但就人类本性而言,文化的互相联系、交融、影响、作用,才具有根本性。
宏观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地球上的人类,虽然是分散居住和生活的,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相通、需要相通、必然相通的。人类文化具有某种天生的弥散性,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所挡不住的,尤其在当今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海关、国界对于互联网起不了拦截作用。上万年前秘鲁人发现的马铃薯和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最终成为全球的食品;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又传遍世界供全球人使用;喝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有习俗而风靡全世界;莎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激动着世界各大洲的读者;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汉代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汉唐通往大食、大秦丝绸之路的打通;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分裂;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成;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大面积扩张;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推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期电视直播、电子文化、网络媒介创造的信息快速通道,信息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留下的脚印。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全球化是极其缓慢的,从资本主义时代起则变得十分迅速,而在信息时代,出现了加速度和全方位的电子传播。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全球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即“文”的方式和“武”的方式,而且二者常常有交叉,“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文”的方式
所谓“文”的方式,是指通过和平友好的交往、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价值共识、共享,达到融通、融合。譬如,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把先进的汉文化带到西藏,无疑也会把藏族的优秀文化带到内地;中国与西域各民族,与西方及海外各民族、各国家,通过丝绸之路(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互相通商,进行文化交流,这都是“文”的方式。在汉代,西域各国贵族子弟经常到长安学习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优秀文化、各种发明创造,传到西域、西方和海外;西域各民族、西方和海外各国的优秀文化,也传到中国,例如胡琴、琵琶,都是来自西域。史载,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中国传到西方的,除丝和丝绸之外,还有漆、钢铁、凿井术、炼钢术等等。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29—97年)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大加赞赏,称之为优良的卓越的产品。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等。张骞带回《摩诃兜勒》乐曲,乐府因之而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和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1世纪中叶传到天山一带。到唐代,中外交往更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与外国交通路线,重要的就有七条。陆路五条:(1)自营州(河北昌黎)入安东道;(2)自夏州(陕西横山)通大同云中道;(3)自中受降城入回鹘道;(4)自安西入西域道;(5)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两条:(1)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2)自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即大食国)。当时中国航海已经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中国瓷器最受世界各民族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三彩、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婆罗洲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1](P113)。
以“文”的方式相互传播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眼镜。13世纪末,眼镜出现于中国并很快传到欧洲。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大约是公元1260年)写道:“中国老人为了清晰地阅读而戴着眼镜。”14世纪,中国绅士愿用一匹好马换一副眼镜。将眼镜从中国引入欧洲是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并且逐渐普遍使用。16世纪,眼镜在西班牙顺利传播。1730年,英国人制成双钩于耳的眼镜。但眼镜在英国的传播历程颇坎坷,牧师们说:“企图用眼镜来恢复衰退的视力,是对仁慈的上帝之恶意挑衅。”这使人想起中国清代初建铁路时,也曾遭到朝廷大臣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怪物破坏了祖宗的风水。清朝大臣与英国牧师乃有异曲同工之妙[2]。现在,西方和日本制作眼镜的先进技术又不断回传到中国。从小小眼镜,可以见到全球化的蛛丝马迹。
再如马镫。马镫虽小,作用很大,它使骑士和战马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犹如眼镜,它是一种媒介。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讯息。它给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掌握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没有马镫,就不会有蒙古大帝国,不会有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越过喀尔巴阡山,挺进高加索,征服乌克兰,直逼匈牙利。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5 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在西方,马镫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 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3] 小小马镫的传播同样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证明。
再举一例:悉尼歌剧院。它的设计者伍重(Jorn Utzon),丹麦建筑师,1957年为澳大利亚设计悉尼歌剧院而闻名环宇,2003年获得了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那年他85岁。伍重得奖的评语是:“伍重是一位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建筑师,这历史包含了玛雅、中国和日本、伊斯兰以及他自身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精神。”早在学生时代,伍重就热衷中国文化,后又进一步涉猎有关中国建筑的著述。他比较中西建筑特点时认为,在西方,重力是朝向墙体;而在东方,重力是直接朝向地面的,他概括为“屋顶与平台”,这一空间意象是他悉尼歌剧院设计思想来源之一。悉尼歌剧院的空间意象正是强化了的巨大“平台”和“平台”上的“屋顶”。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该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颁布为官书。据说,伍重在悉尼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本《营造法式》。1958年,在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中标的第二年,伍重旅差途中曾来中国,会见过梁思成,请教过有关《营造法式》的一些问题[4]。由此我们找到了“文化交融”、 “全球化”的又一例证。
“武”的方式
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相处,亲切交流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但是,有的则有矛盾、冲突,甚至会发生战争。所谓“武”的方式,主要是说战争。战争的破坏性,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战争带给人类的另一种东西,即强制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融。有时候是很残忍地施行这种交流和交融,伴随着血和泪,例如满族入关,建立大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西方列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如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割地(割让香港等)、赔款、划租界、行治外法权、强开内河航运、强开商埠、强建教堂等等。但另一面,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带来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促进新一轮的西学东进——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书籍、学术文化正是在此之后,如严复所译《天演论》。中国某些人士(包括官方和民间)大办洋务,开各种工厂、企业、公司,如船厂、煤矿、铁厂、枪炮制造厂,建新式海军,购买现代化舰艇等等。它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世纪的中国一部分人接触外界事物之后,自觉地睁开了眼;还有一部分人的眼,是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开的。他们认识到必须变革,必须开放交流,必须接受新文化。“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5](P319),“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6](P432),“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6](P243)。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7](P96)。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留学生容闳,从1847年起在美国留学八年,中西对照,使他更加感到清王朝之黑暗腐败。经过长时期的积蓄,于是有后来的“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有为《公车上书》中提出必须“破除旧习,更新大政”;梁启超在《论不法之害》一文中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岂能服膺!”
“武”的方式,除了真刀真枪的厮杀,也包括不见刀枪的特殊的战争,即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二者常常交织在一起。而且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战争”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占了下风。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另一个吃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它们在许许多多强制性的行为中,也在无声无息的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并且遵循“取优”的规律,运行、变化、发展。通过这种融合、“取优”,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搏斗、交融,尽管常常伴随着血泪,但最终结果是从窄狭走向更广阔的融合与发展。
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心理
面对全球化,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敞开胸怀,“拿来送去”;一种是闭关锁国,不进不出。中华民族的汉、唐时代,是取前一种态度,成为世界的第一等大国、强国,文化高度繁荣,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诸多商业往来、文化交往。唐朝国都长安,除外国友好使者外,还有许许多多“外籍人士”(商人和各种文化人)居住;中国也派往国外许多使者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人员,还有出国留学者。而到了明清时代,则取后一种态度。自明代初期起,就实行“海禁”(又称“洋禁”)政策,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只允许“朝贡贸易”。这与同期的西方相比,政策恰恰相反:哥伦布出海,是受鼓励的,而且规定许多奖励政策。中国明朝海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的、政治思想的、军事的等等。就军事来说,据说是为了防倭寇。明代永乐时,海禁尺度有所放宽(但绝未解除),永乐皇帝还派郑和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不是进行海上贸易,而是显示大明国威,顶多属于“朝贡贸易”之类。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曾解海禁,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的彻底的落实,因此清代总体说仍然没有开放,而且越到后来越禁锢。闭关锁国的结果,使中国成了世界上的“夜郎国民”,中国几乎被甩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仍然是封闭的。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了某种封闭心理,这其中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面对外来文化,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我们”失去了什么。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常常简单地把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看作是“文化占领”,常常以“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等观念来看待文化交往。这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如果超越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也许会接纳和认可不同文化由隔膜、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的新成果,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会从由文化碰撞融会而产生的新文化中受益。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也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两者都沾了个“信”字,但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二者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它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的,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儿;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又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账”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发展起来,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更有益处。
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研究者要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提倡社会学者应当进行“跨文化”研究。而要进行“跨文化”研究,就必须改进研究者“心态”,克服偏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 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8] 扩展开来说,不止是社会学研究领域,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所有领域,都应该克服这种偏见,改进自己的“心态”。这个观点正与上面所言“超越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谋而合。而且在费先生看来,不止是“心态”,以往的某些“思路”也应改变和超越:“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种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8]
正确的“心态”、“思路”是怎样的呢?费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即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判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共存、共荣,价值共识、共享,达到多元世界的“和而不同”。“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8] 当然,在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心理、“心态”、“思路”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另一面,即不要失去民族性。
文化的全球化当然是一个十分长远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对文化前景的推想和瞻望。文化全球化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已有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即使全球化,也必须保持文化、特别是文学本性所要求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多元化。这是文化和文学艺术全球化问题的特殊性。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民族性、多样性、多元性。总之,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是文学艺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歌德曾说:“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这也是说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性的问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爱心,但是爱国和民族自爱,绝不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前者可以同时是开放的,好客的,喜欢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善于学习和吸收他国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慷慨把自己的好东西奉献给别人的;后者则常常采取闭关锁国和民族封闭主义,甚至奉行民族利己主义。我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如果通过交流、对话、融通,达到全球化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全球化使人受益,不应惧怕这种全球化,更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全球化。我们应该奉行民族开放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这样的全球化,让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美学在这样的全球化氛围中发展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