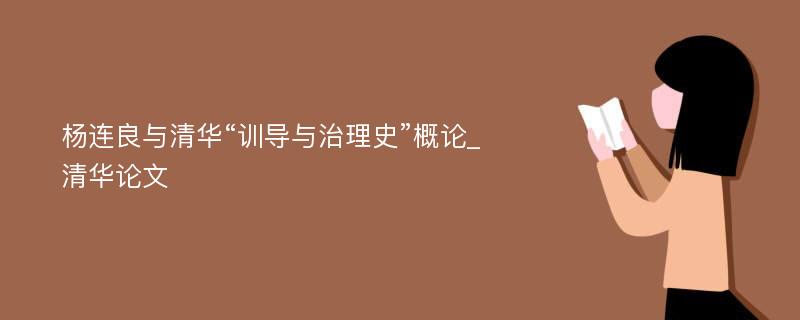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学派论文,之学论文,杨联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45[2010]04-0013-07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史学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种史学流派迭出。随着“国学研究院”的兴办,聚集在清华大学的一批史界学人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及共同的工作学习环境,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旨趣及研究方法,形成“清华学派”。在清华求学的杨联陞接受了系统的史学教育,深受其惠,并且作为清华史学的海外传人,将“会通史学”输送到国际汉学界。本文拟对杨联陞的史学特色进行考察,以进一步印证“清华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派别的合理性,来阐释“会通史学”作为一种健康的史学研究路数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
一、“清华学派”及其特征
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提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①背景有二:一是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及知识分子的研究渐成学术热点,且方兴未艾;第二点则更为直接,是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及复兴为契机,②一些学人,特别是与清华相关的学人,试图追寻“老清华”的学术轨迹及学术精神,以期重续三四十年代清华学术尤其是“国学研究院”之辉煌。
继“老清华人”王瑶于1988年提出“清华中文系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后,徐葆耕、胡伟希、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刘超等人又一步从定义、学理及史实等各个方面充实了清华学派的内涵。③如徐葆耕先生发挥冯友兰先生的“疑古”说,将清华学派的提法引入清华史学。张岱年先生也以亲身经历之感受认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清华哲学系称为“清华学派”是有事实根据的。④胡伟希先生则进一步区分了狭义及广义上的“清华学派”。他认为狭义上的清华学派专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以清华哲学系为中坚的哲学派别,广义的清华学派泛指此一断限内整个清华大学文科为代表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北京大学的刘超则将清华学派的外延扩展到整个清华,并不仅限于文科。因为这一指称“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尺规。”
何兆武、李伯重等先生基于学理及概念上对“清华学派”的分析更有代表性。何先生对于“清华学派”持“疑似”存在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通常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之下”,又自然地使清华学人产生“某些共同的情趣和风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称之为“清华学派”。⑤李伯重先生与何先生看法相近,但进一步从概念上严谨地分析了“清华学派”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依照《辞海》的解释,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在此意义上“清华学派”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西方有关“学派”(school)一词的解释与此不同。如霍恩比(A.S.Hornb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1997年版的解释为:“Group of writers,thinkers,etc.,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而《美国传统辞典》2003年版的解释是:“A group of people,especially philosophers,artists,or writers,whose thought,work,or style demonstrates a common origin or influence or unifying belief”,即“拥有相同理论或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群体。李伯重先生更倾向于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清华学人虽各人研究领域及治学风格各有不同,但“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⑥而其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正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清华学派”这一概念下,学界对于“清华学派”的主要特色及体现的学术精神的看法则比较一致,大体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表征则是以“通才教育”为主的办学模式及以“精英培养”为中心的教育理念。⑦具体而言,王瑶先生认为,清华学派兼有“京派”的乾嘉遗风及“海派”的宏观理论之长,微观与宏观结合,力图找出历史现象背后的“时代及社会的原因”。何兆武先生则进一步将“清华学派”的共同情趣及风貌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著名史学家、旅美清华学人何柄棣先生对此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认为清华实施的是“人文通才教育”,而历史系中“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⑧。他甚至强调指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做到这三个“并重”,且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事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此时也正好是本文的主人公杨联陞先生就读期间。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之下,清华的学术精神及维系命脉则是陈寅恪祭王国维文中所写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二、杨联陞与清华
从杨联陞1933年入学到1937年毕业,正是清华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正值清华的鼎盛时期。“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虽是民间选婿的玩笑之词,却也从侧面说明了清华在京城高校里的独立一帜及清华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
人生中处处充满意外。1933年杨联陞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被保送师大、燕京,又同时考取北大中文及清华经济二系。如果说最终选择清华只是遵从家长意愿并非其初衷的话,那么四年的清华生活应该说让他充满了对这一幸运选择的感恩之情。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⑨杨联陞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直至晚年,这种情愫仍时时萦绕其心,“每因长夜怀师友,更假余年念清华”⑩。此时的清华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物质条件,在社会各界包括京城其它高校资金捉襟见肘、争薪讨薪风潮不断的情况下,唯有清华仰赖美国退还的“超收庚款”,得以继续发展。特别是1933年后,退款倍增,清华经费更为充裕。在此基础上,自然环境优美的“水木清华”所有硬件设施的配套如“四大工程”(11)都可比肩美国大学。(12)青年时代的杨联陞正是在环境如此优越的清华园里激情“斗牛”、勤奋“开矿”。(13)另一方面,清华的历任主事者尤其是1926年出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更是利用清华得天独厚的资金优势,倡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手笔选聘了诸多名师,并进一步确立“教授治校”为中心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优良的物质条件、美式教育下的民主治校之风,师生间督励之惠,同学间的砥励共学,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都为清华师生提供了发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宽松氛围。由此,清华一向坚持的“通识教育”得以有保障地顺利开展。而以经济为专业的杨联陞也才有机会选修了许多文史学系的课程,最终成为专业的历史学家。
早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甫一成立,其教学便注重“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只是更为偏重西方文化。直到1923年校长曹云祥延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张彭春推行课程改革,加强了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关怀,并于1925年成立了以吴宓为主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立意即在于培养学生对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及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通彻了解。(14)杨联陞后来回忆清华国学院的盛况曾有一首“人文社会学院献词”,很好地概括了清华几位导师各有特色又“五星”“互影”的师资阵容。
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人文社会学,理工亦科技。真善自千秋,精美方成器。(15)
杨联陞入学之时,国学院已于1929年停办,几位大师除陈寅恪、李济外亦飘零星散,但国学院之遗风却在清华很好地传承下来。此时梁启超的“新史学”早已浸入学界,影响深远,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所进行的改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史学”的影子。“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16),鼓励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吸收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并特别延请到擅长理论及历史哲学的雷海宗主持中国通史的讲授。王国维先生也一向认为学无新旧,无中西,更无有用与无用之分。(17)这种为学态度正与清华学风不谋而合。加之深厚的哲学素养及严谨朴实的考据学风都对确立清华国学院的治学传统起到了奠基作用。而这一传统的最好继承者莫过于陈寅恪。不惟如此,杨联陞更有幸在日后与几位大师有亲授之缘。如赵元任及李济先生,杨联陞虽没能在清华校园中亲炙其为学风采,但在赴美之后因缘际会,常侍二位先生左右,学术往来甚为密切,也算补偿了他在清华未能得其真传之憾。
杨联陞早年即酷爱文史之学,自幼年直至16岁一直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曾因背诵经书史籍劳力过甚而大病一场。进入师大附中之时,即已对文史、考古及社会人类学等有所认知,并认为“学问忌执贵通”,其博学之潜质已隐然可见。(18)及至清华就读期间,更是如鱼得水,徜徉于诸位文史名家的课堂,进一步激发了对于文史的兴趣。虽从家长之命选了经济系,但除必修诸课,选课多为文史学类。如朱自清的国文、雷海宗的通史秦汉史、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俞平伯的词、闻一多的楚辞、张荫麟的学术史、杨树达的说文解字、唐兰的古文字学、王力的中国音韵史、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浦薛凤的政治学,此外还包括必修的叶公超先生的英文及随钱稻孙先生学习日语,甚至在毕业后还特地向萧公权先生学诗。勤奋刻苦的学习加上优良的天赋使得杨联陞很快在学生中甚至学界崭露头脚。(19)雷海宗先生的秦汉史课上,“教到王莽就说同学对东汉有兴趣的可看杨君的《东汉的豪族》”(20),而那一篇正好是张荫麟先生请杨联陞为他编著的高中本国史的长编所写的一部分,后来还写过魏晋到唐初两篇(吴晗给他写过明初两篇)。张荫麟对杨联陞“特相赏识”,邀杨“常去其家”。陶希圣也曾回忆道,“我的课在清华设在历史系,杨联陞却是经济系生来选此课,由此自修且自成一家”(21)。而当时学界翘楚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课上,选修的人不少,包括汪篯、何炳棣等人,杨联陞的论文得到了最高分。其晚年所写的《一字诗怀师友》,细腻传神地表现了其在清华这个学术熔炉里所得到的师友督励之惠。
一院一斋一念旧,一歌一咏一怀新,一花一鸟一世界,一缘一会一天真。一点一圈一只眼(法眼,包万象也),一抬一搦一钳锤(要经过大炉,老师对学生,一手抬,一手搦),一刀一断一猫儿(南泉斩猫),一性一佛一狗子(人问:狗子还有佛性无?曰:无;亦可说有)。(22)
应该说清华的系统教育为杨联陞得以“博雅通人”之名立足于国际汉学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便是以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教学的五十年间,他也是尽力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知识,研究领域上起先秦,下迨清末,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23)其指导的论文包括宗教、美术、教育、政治、音乐、科学史、哲学等系学生。加之通晓数国语言,“学术触觉灵敏,常能贯通各方面的知识……凡中外学人讨论中国学术问题,他发现谬论,必直言批驳,不留情面,为国际间公认的汉学批评名家”(24),被誉为“东方伯希和”。其学术传人余英时对此更有直接的体认: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25)
而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更是以“少年辈第一人”(26)期许杨联陞,在为其《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所撰导言中指出:
杨联陞的学问是出于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27)
正像戴密微所指出的那样,杨联陞往往能够掌握“浩博的资料”,同时进行“精密的分析”,用杨联陞自己的话就是“训诂治史”,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综合性的结论”。也就是说杨联陞的“通”并非“横通”之通(28)而应是既博且精,博雅之中有精致的训诂之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会通”之学。
三、由“训诂”而“会通”
杨联陞自谓其治学的基本立场是“训诂治史”。也就是要求治史者“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对于史料中的歧漏错谬,则需要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及各种方法加以严格考证、确切理解,所有的史学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展开。1962年3月杨联陞被邀请到法国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作了四次演讲,题为“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开篇第一讲即强调汉学家须通训诂:
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它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29)
杨联陞还在后面的第四讲用了五六页的篇幅追溯了“均”与“和”两个重要概念在各个时代的应用。他首先质疑了《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原简可能有所错乱,“均”与“安”应倒置。其后通过整理“均”与“和”两字在各个时代的意义,用以说明在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均”与“和”这两个相关观念的应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训诂学在其学术研究中的基础作用。而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我一向以为中文一字多义(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语文与思想关系甚密,有人说: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很难了彻古代思想。(30)
而对于训诂学的重要工具学科——语言学,杨联陞也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并一直对其保持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将语言学知识作为切入历史的最主要的路径。在语言学上赵元任对杨联陞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杨联陞1933年考入清华时,赵元任已经去了中央研究院,后来又去了美国定居,但1941年杨联陞得到当时任教于哈佛的贾德纳先生的帮助入读哈佛大学时,其与赵元任先生的“学缘”即紧密联系在一起。杨很快成为赵府中的常客,且作为唯一的讲师协助赵先生开办美国陆军特训班,其对语言的兴趣进一步得到发掘。两人于1947年合编了《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再版多次,两人共同制定的汉语课程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沿用。二人感情至深,“岂仅师生谊,浑同父子缘”(31)。之后杨联陞的著作中有很多涉及语言学方面的,或是与语言学有关的史学著作,如《汉语否定词杂谈》、《中国语文札记》、《〈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等。对于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杨联陞形象地比喻为“传统说的经学与小学的关系,要通经学不得不通小学”(32)。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注意历史上及史书里的各种语言现象,不然就要闹很多的笑话,出很多的错误。(33)
正是运用语言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杨联陞纠正了中外学界对某些史籍中字词理解中的许多谬误。如奴隶的“隶”字,一些西方汉学家经常弄错,径直将之翻译为“Slave”,事实上,并非一定是奴隶,如“徒隶”就是受了徒刑,罚做若干年限苦工的人,但与终身为奴隶的人大不相同。另一个文法方面的例子则是如何解释甲骨文中的卜辞“雨不雨”。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这是个选择问句,即“下雨不下雨呢?”杨联陞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句法,甚为晚出。事实上“雨不雨”是两个问句,即“下雨吗?不下雨吗?”而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陈没有注意到句法结构古文言与今天白话文有很大不同。
杨联陞认为阐明历史与语言关系的最好的例子是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34)傅氏指出古文字和古书中,很多时候性就是生,命就是令,意思相通。性命是动词也是名词,该书前半部都在分析这四个字的关系,是训诂学上一大贡献。
必须指出的,杨联陞主张的“训诂治史”绝不仅仅是训诂和考证,他紧守“训诂考据”关口,无非是提醒治史者应注意审查和运用史料的复杂性而已。因为正像余英时所说那样:“杨先生考证精到而取材广博,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考证学家;他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35)。这一方面当然与杨联陞在清华及美国哈佛大学所受到的社会科学的训练有关,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杨联陞早年即服膺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的治史路数。
杨联陞这一治史的基本立场与陈寅恪先生有密切关系。杨联陞曾选修陈寅恪的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36)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也是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陈寅恪的学识之渊博,学术工具之齐全,考证之精细绵密,考证又往往服务于大的史学目的,都使杨联陞对其钦佩不已。因而往往于陈先生课前,在教员休息室“侍谈”,并在课后步送先生回寓,甚至造寓晋谒。终其一生,杨联陞都对陈寅恪执师礼甚恭。甚至中美两国音讯隔绝时期,杨联陞一直关注陈先生的生活及学术研究,其出版的《再生缘》等著作,杨联陞也是想尽办法,辗转寻获;其课堂讲授,也往往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为重要参考资料。尽管论私交来说,可能还不如与赵元任及胡适等人更为亲密,但其对陈寅恪学术的仰望之情,对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敬畏,始终使陈寅恪在杨联陞的学术生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其训诂治史的立场也正好与陈寅恪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精义相通,即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
更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大书如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单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陈寅恪先生也正是在评价沈的这篇文章时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37)。
陈寅恪先生这一评述,想必杨联陞早在清华读书时即已看到,杨的几部著作也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治史路数。如《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分别追溯“报”、“保”、“包”三字的起源,并详细搜罗了其在各个时代演变出来的语义,注重分析其在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及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认为三个字都可用一个“信”字来贯通:“报”,人们报答祖宗乃依于对先人的信仰;“保”字,是要我们对所保的后代有可信性;而“包”字,是人对社会人群的信实。而“信”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可以说正是“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一部社会史的典范之作,是为陈寅恪先生这句名言所作的精彩注脚。另一部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也是一部在经济史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对中国历史有关货币和银行的约300个左右的关键词着重作了记述和分析,脉络分明地叙述了历史上货币与信贷的演变,并时时注意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背景。同样精彩立意的文章还有《国史探微》及《中国制度史研究》中收录的几篇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史的一般性通论之作,都是在具体考证的训诂学基础上得出了综合性的结论。其他单篇文章如《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及《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等也无一不是广泛运用社会科学于史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精彩之作。难怪周一良也把杨联陞与陈寅恪先生并提,认为他很好地发扬了寅恪先生的治史风格。
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古代和现代……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38)
正像林聪标在杨联陞1985年到新亚书院讲学时所说的,“近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是由乾嘉史学因缘发展而成,由札记考证、名物训诂而进以贯通史事,探究风俗典章,进而蔚为大观。但十九、二十世纪中西交通发达,西洋史学的绵延扩大由考古史者所发扬,每以博闻广问、记诵考索为根本,自不免与乾嘉以降的史法史识相互为用,而援引壮大。尤有进者,当代社会学、经济学之发达也直接塑造了民国以来史学研究的风尚。在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的开拓下,于民国初年熏陶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史学家,杨联陞则为其中的代表人物。”(39)
应该说,杨联陞的这种“以小见大”、“观微知著”的治学风格的养成,不排除有其“天赋才能”,但更多地还与他在清华所受到的通才教育有关,由历史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佛学、禅宗、博弈、绘艺、俗曲等,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魅力,更成为杨联陞等人终身追随的目标。如对于陶希圣称赞他“博学多闻而自成一家言,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杨联陞惶恐不安,认为“‘自成大师’四字,我实在不敢当。如教我隋唐史的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我再活二、三十年也未必能到。”(40)尤其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然成风之时,杨联陞原有的治学倾向得到更好的发挥。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互相结合,相互阐发,广泛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律学等各学科知识,在博雅的基础上,坚持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认可。
四、余论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作为清华学术精神之灵魂,更是深深影响了包括杨联陞在内的几代清华学人。因为唯有具备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人才有可能真正发前人之所未发,想前人之不敢想,才能真有创新和真知灼见,也才能真正成为第一流的学人,成就第一流的学术成果。正如1965年初秋,清华毕业生、亦是杨联陞的同学及终身密友的林家翘自麻省理工大学到芝加哥作学术演讲时,曾对何炳棣说:“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41)而杨联陞也正是凭借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始终站在国际汉学的研究前沿,因而被同行们——包括傲慢的日本汉学家——视为国际汉学界的第一人。(42)对此,杨联陞深表不安,提议以“第一线”替代“第一人”的提法。这与林先生的观点亦有相通之义。
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43)
反之,如不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但容易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局限,即便是在学术研究中,也不免因循前人,甚者更会抄袭伪造学术成果而混迹学界。对此,杨联陞深恶痛绝,其日记中多次对于诸如此类的人和事,表达愤慨之词。(44)此种精神一方面力图捍卫学术独立自由之权力,另一方面更表现出对其自身学术的高度自信。所以当1968年杨联陞得知他终身景仰的老师陈寅恪在文革中遭受攻击时,不禁失声痛哭;而当1956年费正清领导的东亚研究中心试图以近现代中国学研究取代东亚系及哈佛燕京学社中的传统汉学研究之时,杨联陞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收稿日期:2010-01-17
注释:
①这个提法是由1943级毕业生王瑶在1988年“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有一个鲜明特色的学派。”(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②建国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中重新建系最早的是1983年的外文系,然后是1985年的中文系、1993年的历史系、1999年社会学系,其他几个系则都在2000年之后。由此可见,对于清华学派的学术研究,其时间段正好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各系重建时间相合。
③胡伟希:《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葆耕:《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陈平原:《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天涯》2006年第2期。
④张岱年:《回忆清华哲学系——清华学派简述》,《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
⑤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读书》1997年第8期。
⑥李伯重:《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⑦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天涯》2006年第2期。
⑧转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⑩杨联陞日记,1985年12月9日。
(11)四大工程指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科学馆,其营造工程师及建筑选材都及尽一时之选,甚至被外界批评过于豪华浪费及洋化。(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2页)
(12)“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这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和设备都最好。”(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3)当时清华园里的流行词汇。“斗牛”指在体育馆中健身,“开矿”指在图书馆中用功读书。
(14)吴宓提到国学研究院设立的立意在于:“(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15)杨联陞日记,1987年2月27日。
(1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7)王国维:《〈国学从刊〉序》,《观堂别集》卷4《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18)“联陞自入中学,即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象,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尤堪宝贵,学问忌执贵通。”(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
(19)刘子健教授曾回忆,“杨先生带着旧学根基,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而后再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学,可是却有好几位历史系教授赏识他。抗战前一年,我刚入学,他是四年级,无缘拜识,但早有人遥指着他向我说,那位杨君真是大才,不但是学生领袖之一,并且已有学术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货》上。本科学生,如此出人头地,向所未有,难得之极。”(刘子健:《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先生》,《历史月刊》1991年第37期。)杨联陞于清华就读四年所发表学术文章主要有:《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庭的生产》分别刊于《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5、6期;《东汉的豪族》、《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分别刊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1937年第12卷第1期及1937年第12卷第3期;《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五胡乱华前胡族的内徙》、《汉末“黄巾之乱”的一个新考察》、《“管氏有三归”的确解》分别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11月13日及1937年1月15日。
(20)(21)陶希圣:《序》,Lien-sheng Yang,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Shih-Hjo Publisher,1982..p.iv.
(22)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1页。
(23)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收于《书生本色——周一良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4)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2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6)杨联陞:《杨联陞自传》,载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页。
(27)参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8)有关杨先生之“通”非“横通”之通,可参见李弘祺:《海滨拾贝壳的学者——怀念杨联陞教授》,《历史月刊》1991年第36期。
(29)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30)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1)1982年3月10日《挽元任先生》:“新年劳枉驾,蓬门欲泪连。岂仅师生谊,浑同父子缘。方期重侍饮,未料遽长眠。宝婺星相接,同升极乐天。”(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7-278页)
(32)(33)杨联陞:《历史与语言》,《大陆杂志》第37卷第1、2期合刊。
(34)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4页。
(3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36)有关杨联陞所选陈寅恪先生的课,有何炳棣及周一良两人的回忆可以佐证。何炳棣回忆1936-1937年他选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课时,“班上有高我一级的杨联陞”,而杨联陞说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时,周一良、俞大纲两位曾来旁听,对照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的回忆,他是在1935年的秋天旁听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的。故此可说明,杨联陞不但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至少还选修了“魏晋南北朝史”,从学陈寅恪长达三年之久。
(37)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3期。文末附《陈寅恪先生来函》。
(38)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书生本色——周一良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9)林聪标:《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40)陶希圣:《序》,Lien-sheng Yang,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Shih-Hjo Publisher,1982.p.v.
(4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42)杨联陞日记,1953年4月29日。“cleaves谈Ford给奖学金情形,彼甚表不满。(因学文学及语言者均未得)又言叶理馁曾告彼日本学者中有人以余已是当代汉学家第一人,余说此语绝对言过其实,前辈尚多。自己根基亦浅,气象未宏,安敢僭妄至此耶。”
(43)杨联陞1963年9月10日给周法高的信,收于周法高:《汉学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27页。
(44)杨联陞日记,1977年1月6日、1970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