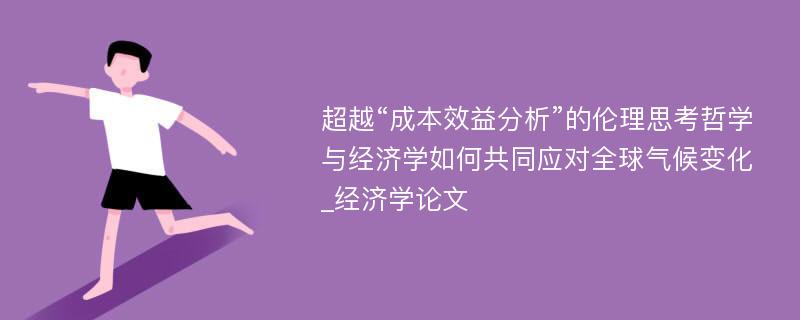
超越“成本—收益分析”的伦理学考量——哲学、经济学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气候变化论文,收益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2-0005-09
方旭东(以下简称方):您好,布鲁姆教授,很高兴能向您请教有关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气候日益频繁,“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①这个议题也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举世期待的联合国第15次气候变化会议(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COP 15)于2009年12月7-1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最终却因为与会国分歧太大,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从而给世人心中投下长长的阴影。可以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任重而道远。您知道,我本人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近年来对气候变化问题也非常关注。到牛津访学之后,有机会对这方面文献集中加以研读。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这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科学方面,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四次评估报告;在经济学方面,2007年出笼的《斯泰恩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是同类著作当中篇幅最大同时也是影响最广的;在政治学方面,有安东尼·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②;在伦理学方面,也已出现了像《气候变化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这样的普及型小册子。我还发现,在伦理学学者中,您是比较早涉猎这方面问题的,十几年前您就出版过一本书《全球气候变暖代价评估》(Counting the Cost of Global Worming) (London:The White Horse Press,1992),《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在2008年6月号上还刊登了您的一篇文章《气候变化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顺便说一句,《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环球科学》在2008年7月号上载有此文的摘译。
约翰·布鲁姆(以下简称约翰):是的,我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一直都很感兴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品,我也做过相关的几次讲演。2007年4月,我应邀到圣—安德鲁斯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做“诺克斯讲座”(Knox Lecture),我讲的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何以需要伦理学?”(Climate Change:Why Economics Requires Ethics?)2009年9月,我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做“罗斯蒙讲座”(Roseman Lecture),我讲的就是“气候变化的伦理学”(Ethics of Climate Change),跟刊登在《科学美国人》上的那篇文章相比,这个演讲更加专业一些,有比较详细的论证。此外,我还打算在下学期为研究生开设一门课程,暂名为“气候变化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s)。
方:我注意到,与一般的道德哲学研究者不同,您对气候变化的伦理思考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比较多地运用了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手段。这当然跟您个人的治学经历有关,您最初就是从经济学转入伦理学研究的,正如您的大作《从经济学出发的伦理学》③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除此之外,我想知道,您认为在处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究竟可以从经济学家哪里学到什么?
约翰:我一向认为,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应该互相学习,因为他们彼此都能从对方那里获得教益。在处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不妨以经济学家为友。这首先是基于某种策略的考量。你知道,很不幸,没有多少人把我们这些道德哲学家的话当一回事,因此,如果我们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就应当与那些有权势的人交朋友。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有权势的人就是那些经济学家。我认识到这一点,是我去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参加《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的发布会。当时我看到,英国两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左一右,就坐在斯特恩的身旁。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对斯特恩的话真的听进去了。我之所以认为我们有可能影响经济学家,是因为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斯特恩本人在内都认识到这一点。《斯特恩报告》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一点:它一上来就讨论这项工作的伦理基础。很多经济学理论就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我们哲学家必须让经济学家去完成这种应用。无论我们从气候变化的伦理学中引出什么结论,其中大部分都将不得不通过经济体系去执行。所以,我力主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为友。不过,哲学家要想影响经济学家,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就是,道德哲学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致说来,经济学家所做的是“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他们感兴趣的是,比如,实行“烟尘排放税”(carbon tax)会带来哪些好处,又要付出什么代价。这倒不是问题,因为很多道德哲学家其实也是这样思考的——认为某事应当做,是因为利大于弊。这些哲学家是所谓“目的论者”(teleologists),以往他们被不确切地称作“效果论者”(consequentialist)。很自然地,这种“目的论伦理学”(teleological ethics)与经济学方法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哲学家要与经济学家结盟的第二个理由。
方:的确,如您所言,“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常用的手段。不过,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应用“成本—收益分析”,似乎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在这里,成本或代价主要由当代人付出,而收益则主要由后代子孙享用。现在科学家们说,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因此,缓解气候变化一个重要举措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排放温室气体——开车,用电,购买高能耗生产或运输的产品——所有这些活动都产生促使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要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上作出一定牺牲。比如,我们将不得不减少出行,我们将不得不减少吃肉;甚至从整个生活方式上,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享受人生的观念,一切从俭。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生者必须作出牺牲,以有利于那些一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活着的人。如果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显然,就某个个体乃至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收益几乎为零,而付出的成本可能无比高昂。在这里,经济学家顶多只能告诉我们成本有多大,收益有多大,以及什么人承受,什么人受益,至于为什么这一代人要为另一代人作出牺牲,“成本—收益理论”并不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我想,在一些人的收益与另外一些人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在一代人的利益与另一代人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是伦理学家要操心的问题。
约翰:是的,对于气候变化,我们应当做的不只是对成本收益进行权衡这样的事,虽然它部分的是这样。假设你计算出通宵聚会给你和你的朋友带来的收益要超过给你邻居带来彻夜不得安眠的伤害,它不能推出你应当举行聚会。同样地,设想一个工业项目,它在不远的将来会带来收益,但排放的温室气体在此后数十年对人构成伤害,即使收益大于成本,也不能让这个项目上马。因为它在道德上可能是错的,从中受益者不应当将代价强加给那些未受益者。不过,即便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不能完全回答对于气候变化我们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它也是解答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经济学拥有管用的手段去权衡复杂情况下的成本收益。因此,经济学可以为伦理学效力。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在根据他的伦理立场行事,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而已。
方:您的意思是说,在对气候变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经济学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伦理前提。如此说来,经济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争论,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彼此的伦理观念之争?如果是这样,这倒为我们观察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论争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前面你提到《斯特恩报告》,据我了解,这个报告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在经济学界也引起了激烈争论。④报告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采用了综合的、国际的和长期的视角,尤其是报告采用了几乎为零的“贴现率”(discount rate),这为赞同者和批评者提供了依据。斯特恩小组主动征询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Robert Solow)、斯狄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意见,都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赞赏,认为报告采用低贴现率,重视代际公平,具有经济学理性。英国国内的不少学术研究机构如廷达尔(Tyndall)中心和皇家科学院,也积极予以肯定。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斯特恩报告》的分析方法和假设条件均存在问题。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并非一定是绝对悲观的。对未来经济损失采用过低的贴现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斯特恩报告》采用的经济学分析模型,不仅过于简化,而且长时间系列简单外推,在方法上也是危险的。因为即使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确定的,人类社会也会不断适应气候变化,增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报告》中,最坏的不利影响延续了二百年而人类没有有效适应,这是不可思议的。剑桥大学的达斯古珀塔(Partha Dasgupta)教授批评《斯特恩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他指出,《斯特恩报告》模型参数设定了近乎为零的极低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0%以上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根本不现实。因为,目前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其储蓄率也只有45%左右,而美国等国家的储蓄率甚至为负。当前世界市场贴现率多在10%,甚至更高;即使是社会公益投资所采用的社会贴现率,也多在5%或更高;因为资金的使用也有机会成本。如果调整贴现率,则结论就会发生逆转。⑤曾任总统经济顾问的耶鲁大学教授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则质疑说,常规经济学分析显示,最优减排路径应该是开始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但《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立即大幅度削减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那意味着,当代人必须立即承受巨额的经济代价。然而,牺牲当代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对后代人也是不利的,因为当代人不能为后代储蓄更多的资产,包括金融、知识、技术等。可以看到,无论是《斯特恩报告》的批评者还是赞同者,这些经济学家在评论时都特别提到了事关“代际平等”(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或“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just)的贴现率问题。表面上,“贴现率”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外行不太明白的经济学名词,可是,如果从您提供的角度分析,那么,它的设定其实反映了其背后经济学家不同的伦理立场。是这样的吗?
约翰:没错。让我从“贴现”(discount)说起。你知道,经济学家通常对未来商品实行贴现。这里所说的商品是指人们所消费的物品与服务,诸如自行车、食物、银行服务,等等。为何要对未来商品进行贴现?根本上是因为商品具有“递减的边际效益”,你拥有的商品越多,再增添的商品对你的价值就越低。比如,在你的房子里有一间浴室,这对你的生活是一项巨大改善;如果再来一间浴室,好是好,但对生活的改变不是那么大。只要存在经济增长,未来人类总是比现在的我们富裕。而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得到某些物品时,这些物品给他带来的好处要比它们带给那些没有他那么富裕的人的好处少一些。在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的预测方案中,世界经济都被认为将继续增长。这就是说,未来人均拥有商品的数量将比现在多。这意味着,商品与服务送到他们手中,是送到了比较富裕的人手中。假设这商品是食物,比较富裕的人就好比是已经吃饱了的人,即使你再给他们多一些食物,他们从中获益相对较小。商品可用的时间离现在越远,其贴现也就越多。贴现率记录商品价值随时间而减少的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物品对未来人类的福利的贡献相对于现在为小。
除了边际效益递减这个原因,还有一个纯粹伦理的原因,使得一些人认为要对到达相对较富者那里的商品予以贴现。按照一种所谓“优先主义”(prioritarianism)的伦理学说,到达一位富人那里的收益(我的意思是指在个体幸福上的一种增量),比起到达一位穷人那里的同样收益,应当被分配较少的社会价值。不过,按照另一种伦理学说,即所谓“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种收益,无论谁得到它,其价值都是一样的。社会只管致力于追求人们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而不论这个总量在人群中是如何分配的。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对未来商品予以贴现,而在一个较长时段(比如一百年),不同的贴现率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相去甚远。以距离现在一个世纪的1吨谷物为例,如果你采用6%的贴现率(约等于诺德豪斯所采用的贴现率),其价值仅相当于今天2.5公斤的谷物。毫不奇怪,诺德豪斯最后得出结论说,现在为将来做牺牲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牺牲对于未来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如果你采用1.4%的贴现率(约等于斯特恩采用的贴现率),一个世纪前的1吨谷物,其价值则相当于今天250公斤的谷物——这是前者的100倍。
贴现率应当是多少?什么决定未来拥有的商品的价值随时间流逝而递减的速度?我认为,它首先取决于一些非伦理因素,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是衡量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未来要比现在富裕多少。因此,它决定了未来人们从增加的物品中所获之收益比起现在人们从同样物品中所获的究竟要少多少。快的增长率生成高的贴现率。贴现率也取决于一个伦理因素。对于那些比我们富的未来人类,其收益的价值与我们的相比应如何估计?如果优先主义是对的,那么,我们将对那些相对较不宽裕的人的福利予以优先考虑。也就是说,未来人类收益的价值比起我们的就应当少一些,因为未来人类比我们富。相反,如果功利主义是对的,未来人类收益的价值就跟我们的一样。优先主义因此走向一个相对较高的贴现率,而功利主义则走向一个相对较低的贴现率。
方:您的说法让我对“优先主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颇有感慨。就其本质而言,“优先主义”赋予穷人的收益更多价值,它因此要求那些相对较富的人应当考虑为那些比自己穷的人作出一定的牺牲。然而,正是这种思路使它对于未来商品采取了一个较高的贴现率,从而对当代人在气候变化上的努力评价消极。本来,在讨论全球南北差距时,优先主义者比起功利主义者通常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更多一些。现在,不无讽刺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功利主义者而不是优先主义者对发达国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约翰:是的,优先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之争在这个语境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几乎令人心酸的换位。优先主义与功利主义在贴现率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不同经济收入人群收益的价值分配上。而在不同时代人群收益的价值分配上,则存在另一个分歧,也对贴现率的设定发生影响。有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应当依时间远近对未来人类予以不同程度的关心,即要对那些生活时代离我们更近的人比那些更远的人给予更多关注。如果这些哲学家是对的,那么,未来幸福,只因其在未来才降临,就应被贴现。这个立场被称为“纯贴现”(pure discounting)。它意味着,对于一百年后某个十岁儿童的夭折应当看得比当下某个十岁儿童的夭折要轻一些。相反的观点是,我们对不同时段应予同样看待,主张某项损害发生的日期对其价值不应发生任何影响。“纯贴现”导致一个相对较高的贴现率,而不计时间远近一视同仁的观点(temporal impartiality)则导致一个相对较低的贴现率。因此,要决定正确的贴现率,经济学家至少得回答两个伦理问题:我们是接受优先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我们是采纳纯贴现还是不计时间远近一视同仁?我的看法是:优先主义是错的,我们应当不计时间之远近而一视同仁。
方:用这两个伦理问题去检视《斯特恩报告》,不难看出,他的回答都是倾向于低贴现的。所以,最后他得出了在别人看来过低的贴现率1.4%。而与这个数字相连的是他对控制气候变化行动的信心,他在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世界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控制气候变化。在决定贴现率时,伦理考量无可避免。不过,那些批评斯特恩的经济学家似乎认为不需要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伦理判断的基础上,他们甚至因斯特恩这样做而谴责他傲慢。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说明,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怎样,我想,有关贴现率的争论将促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杂关系,这也许是气候变化给经济学带来的众多挑战之一。其实,气候变化不仅给经济学,也给其他相关科学带来了一系列难题。而第一个麻烦也许就是,迄今为止,科学对气候变化的所有结论似乎都还不具备“一锤定音”的性质。最近的“气候门”事件⑥,将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再一次摆到世人面前。“气候门”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调查,但这一事件无疑已使科学家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事后,一些科学家做了反击,另外一些科学家则进行了反思。德国汉堡普朗克研究所的一位气候学家即对《明镜周刊》网站表示,这一事件暴露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原本应该得到思考:“我们科学界对待不确定性,甚至错误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同公众的关系是不是有问题?那些邮件里有一些词句很不好。气候怀疑论者完全可以利用它们来混淆视听。”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关于气候变暖问题就存在主流派与怀疑派之争,怀疑派质疑主流派所说的“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并提出自然周期说。“气候门”的出现似乎为怀疑派提供了一件有利的武器。如果主流派是对的,那么,现在的无所作为将导致环境、经济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果怀疑派是对的,那么,主流派所主张的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将是一个巨大的决策错误——这些钱如果用于经济复苏,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更迫切的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有点像下赌注,而且这个赌注是空前巨大的。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约翰:气候变化的原因与结果是极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气候将如何变化,我们也不知道气候的一些变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在我们做决定时该如何应对所有这种不确定性呢?我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来对治它,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任何特别的预防理论或类似的东西。我们久负盛名的决策理论教我们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并且我认为决策理论能像它解决别的问题一样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能够得到有力的(虽然并非毫无争议的)证明。我们应当将“预期效益”(expected utility)最大化。为了说明这个理论,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如果一种治疗感冒的药丸有 5%的可能置你于死地,即便它很可能治愈你的感冒,你会服用它吗?你不会。这个例子说明,你会去做任何具有极大预期效益的事。在决定如何行动时,各选项的预期效益是考虑的重点。“预期效益”理论告诉我们,人们重点考虑的东西不必然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你去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报告,那里都在说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比如,他们说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地球将变暖2-3℃(最近这个数字又修改为4-5℃)。其实,如果我们遇到的只是这么多升温,结果也许是可以控制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当考虑那些更小可能的情况。多数研究显示,地球变暖8℃以上有超过5%的可能,变暖10℃以上也有百分之几的可能。“IPCC”的报告显示的是对气候变化较低的估计。不管怎样,为气温上升10℃以上的可能性分配一个百分点还是合情合理的。升温10℃是什么概念呢?地球上一次那么热是2000万年以前。一个那样热的地球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经验。至于另一个比较,2万年以前,那时地球还只比现在冷5℃,数千米的冰层覆盖在加拿大上面。变暖10℃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可能糟透了。如此一来,即使乘以小的可能系数,严重暖化的可能性在预期效益中也比所有那些有关最可能发生什么的预测要重要得多。
方:那么,科学家需要正视这些极端的可能。如此说来,怀疑论者在气候变暖问题上抱有一种不负责任的侥幸。即便从“预期效益”理论来看,怀疑论者的立场也不可取。就算人类现在花数以千亿计的美元来缓解气候变化最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这个代价也值,因为它好比人类为自己买了一个“保险”。事实上,游离于气候变化主流派和怀疑论者之外的物理海洋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尔·温施就持“保险”这种视角。他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预测固然有不确定性,但不妨从“保险”角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⑦换句话说,就算我们死后没有洪水滔天,我们现在为后代子孙打造诺亚方舟也并非荒唐之举。现在我的担心倒是,如果你的说法成立,那么,全球面临的就不是控制2℃的问题,而是预防10℃的问题。我想,如果地球真的变暖10℃,大概人类早就灭绝了吧?其实,用不着10℃,从1906年到2005年这一百年间,地表平均升温不过0.74℃,可是,看看近几年全球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真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应当考虑更坏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将统计数据放到一边,转而讨论更糟糕的情况。按照您说的“预期效益”理论,升温10℃,从而人类灭绝,这是一种微小的可能,但它却很可能占据了我们预期效益计算的中心位置,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那么,假设人类真的灭绝了,这事有多严重?我的意思是,人类存在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我想知道,作为伦理学家,您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噢,我的天,如果人类灭绝或人口减少到极点,这在各个方面都很糟糕。首先,如果真的灭绝了,这是对我们这个物种的摧毁。其次,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亿人将英年早逝。最后,大批潜在的人类将不复存在;如果我们阻止了气候变化,他们本当降临人世。如果人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或者相反是一件坏事,那么,人类灭绝或人口狂减将是一件极其严重的坏事,或相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多人本能地认为人类的存在既不好也不坏。我把这称之为“中立直觉”(intuition of neutrality)。我们意识到一个人的存在也许对他人有好的或坏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认为就其自身而言是好还是坏。例如,我们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其生命中将享受的好处构成生养一个人的理由。如果一对夫妇决定不要孩子,我们或许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孩子将对人类有限的资源提出要求,从而使他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对父母有了孩子,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将过得更好。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在阻止一个将享受其美好生活的人出生这件事上做了什么不一样的坏事。再来比较这样两个世界:同一群人生活在其中,且每个人的幸福在其中也完全一样。我们的直觉将是:这两个世界谁也不比谁更好。这里我们已经将对一个人他人的好坏影响因素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考虑一个人自己所享受到的好处。我们的直觉认为,这件事既不好也不坏。这种直觉或许有局限。我们可能会承认,一个活着非常痛苦的人的存在是一件坏事,而一个生命质量极高的人的存在是一件好事。然而,就一个特定的生命质量范围内,我们认为身处其中的人的生命既不好也不坏。这就是中立直觉。
如果“中立直觉”是对的,那么,我们对于有关灭绝的代价问题可以作出一个快速回答,那就是:它既不好也不坏。然而,我要说,这种直觉实际上是错的。具体的论证很复杂,这里我只做一个简单说明。“中立直觉”是从价值中立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存在,认为它比起不存在既不好也不坏。假如我们把这理解为是说这个人的存在与不存在一样好,我们就得到一种我称之为“强的中立直觉”(strong intuition of neutrality)。你会发现,矛盾立刻暴露出来。因为这个直觉假定在某个幸福水平上某人的存在与不存在是一样好,而在不同的(比如说较低的)幸福水平上其存在与不存在也一样好。由于“与……一样好”这种关系是传递性的,因此,某人在某个幸福水平上的存在与他在较低水平上的存在一样好。而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对一个人来说,过得好就是比过得不好要强。“中立直觉”还要过头一点,为了证明某人的存在与不存在一样好,它需要假定只有一个幸福水平,然而,较高幸福水平上的存在比起不存在要好,而较低幸福水平上的存在比起不存在则要糟糕。综合起来,结论是我们必须放弃“中立直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人类的存在既不好也不坏。所以,灭绝不是一件“价值中立”(neutral value)的事。至少,总体说来不是那么回事。未来人类没有降临人世这件事要么好要么坏,两者必居其一。很可能你认为人类灭绝是一件糟糕透了的事。也许未来人类将过着一种跟我们一样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将把他们的生活也看成一件好事,因此灭绝就是一件坏事。然而,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表示怀疑,我们自身生活的善是否足以说明如果我们从未出生世界就会比较糟糕。也许大多数人是这样看的。但我不知道这样想的根据是什么。
有关人的价值问题,是所谓“人口伦理学”(population ethics)处理的内容。然而,人口伦理学是众所周知没有结果的。在如何评估人口狂减的坏处上,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共识。按照某些观点,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事。我想,这是为哲学准备的一个“硬活儿”。
方:在人口伦理学上缺乏共识,我想,可以理解为价值的不确定性。然而,形势迫人,在气候变化面前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我们必须决定,就像各国政府首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必须就是否达成有约束性的全球缓解协议进行表决。既然我们都同意,人类灭绝或人口狂减的可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这个事件造成可怕后果的可能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事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占据了我们预期效益计算的中心位置。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种价值的不确定性而拿出一个行动意见。我记得,前面我们在讨论处理科学的不确定性时,您提及“预期效益”理论,那么,在处理价值的不确定性时,“预期效益”理论是否同样奏效呢?
约翰:我们是可以像运用“预期效益”理论对待一般的不确定性那样来对待这种价值不确定性。比如,假设我们并不知道中立水平,我们不知道灭绝有多糟糕,但每个可能的中立水平附着于某个特殊的糟糕程度。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应当把可能性归因于不同的中立水平,这些中立水平依次告诉我们灭绝的各种糟糕程度的概率。这样我们只要做一种预期效益计算。但中立水平的整个想法只是我的价值理论的一部分。顺便说,这个价值理论我得自经济学家布莱克贝(Blackorby)、波赛特(Bossert)以及唐纳森(Donaldson)等人。可是也有一些人不相信我的理论,例如某些“平均功利主义者”(average utilitarians)。这些人认为,我们应当将人的幸福的平均水平予以最大化。预期效益理论的应用因此就遇到麻烦。因为,如果不同价值成为一种预期效益计算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价值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可以比较。简言之,它们必须是“共同基数”(co-cardinal)。这是什么意思无关紧要。可是我完全看不出在平均功利主义和我的理论——一种“整体功利主义”(total utilitarianism)之间建立可比性如何可行。在平均功利主义看来,价值是由幸福水平(尤其是平均水平)所赋予的。而在整体功利主义看来,价值是由幸福水平乘以人数所赋予的。这样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无从比较。你知道,我们不能指望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当我们拥有不可比较的价值理论,对于气候变化我们该如何行动呢?我想,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问题。假如“我们”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那么答案也许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必须承认,有时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认知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一定有什么事是我们应当做的。然而,我们无权做此假设。我们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当我们必须做决定时,有时我们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实上,甚至我们在不是做某项具体决定时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即使当我们无法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行动。(而如何行动,我认为可能存在合理的要求。)假设“我们”是指哲学家。在这个僵局中哲学家应当做什么呢?回答是我们应当继续辩论。记住我们都是民主进程中的参与者,正是这个进程解决意见分歧。民主进程也包括理性的辩论,而不只是投票,有时理性的辩论驱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与某些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并不假装超然于局外而做最后的裁决。我们每个人应当做的就是,尽己所能为我们所信从的价值理论创造最佳实例。我想,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气候变化的伦理学的意义所在。说到各自信从的价值理论,你作为来自东方中国的哲学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一定有某种不同于西方的智慧吧?对此我很感兴趣。
方:的确,在气候变化这样重大的全球问题面前,中西哲学家理应互通声气,彼此协作。以我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我认为中国哲学是能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作出自己的贡献的。前面我们谈到当代人为未来世代做牺牲的合理性证明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用西方的经济理性很难加以辩护,因为经济理性对人性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人是自私的,人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观念,如何能想象本性自私的人类肯为他人,哪怕是自己的后代,牺牲自己当前的巨大利益呢?这也许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对人类能否缓解气候变化持悲观态度的一个原因。而中国哲学的主流对人性对自我的理解则是另外一幅图景:人只是血缘链条中的一环,上有父母祖先,下有子孙后代。而从根本上说,人类都是一家人,有共同的父母、天地,这就是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哲学以亲情为原则处理整个社会乃至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儿女孝顺父母与父母为儿女谋幸福都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中国的皇帝、官员与人民之间不是西方这种公务员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给予了也许让西方人觉得过多的关怀与照顾,甚至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就包含了对自己子女的爱,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是所谓传宗接代。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摆脱这种意识。即使是融入西方社会的华人,其家庭感举世公认是最强的。所以在中国,父母省吃俭用,然后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拿来给成年子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社会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相反,不为子女存钱的家长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可想而知,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而作出重大牺牲以缓解气候变化,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有一位中国学者叫梁漱溟,在比较东西哲学与文化时说,西方人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账都算得清清楚楚,而中国人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是不算账的。所谓算账,我想,就是你前面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功利主义这些东西,即使是主张立刻采取有力措施减排的斯特恩也不例外,他的证明方式是对政府晓之以“利”——早投入比晚投入收益更大。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服世人,有一个根本的困难:无论如何,付出成本的和取得收益的不是同一群人,也就是说,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不对等关系。正如你指出的,有关贴现率的分歧实际上是伦理立场的分歧。优先主义与功利主义虽然不同,但都是不把未来世代的价值看得比当代更高。而如果未来世代的价值不高于当代的价值,要说服当代人作出牺牲,总是存在有人不同意的可能,事实上,美国民众在对奥巴马减排计划上,反对与赞成之声一直势均力敌。反观中国,则情况大为不同,几乎举国一致赞成大规模减排,除了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我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在这件事上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绿色”、“低碳”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不仅是人类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一大转向,同时也必然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我们应该到了反省美国所代表的那种超前消费、高消费、多消费的生活方式的时刻。正如那部反映气候变化的纪录片《愚蠢的年代》(The Age of Stupid)标题所显示的,我们也许需要对文明与愚昧重新加以定义,而一贯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反对自私用智、无限榨取自然的中国哲学,无疑有很多智慧的珍宝值得我们探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⑧
约翰:真希望你所说的东方中国的哲学理念和智慧能被更多的西方学者和大众所接受,这可能需要人类共同去努力。
(附记:这个对话稿是根据两位作者2009年6月—12月间在牛津的几次谈话整理而成,原对话用英语进行,事后由作者之一方旭东作了翻译和一些编辑上的技术处理。)
注释:
①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第一条“定义”中,“气候变化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到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资料来源:UNFCCC官方网站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②该书的中译本已于200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③John Broome,Ethics out of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该书的中译本《伦理的经济学诠释》已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④潘家华:《气候变化引发经济论争》,载《绿叶》,2007(2)。
⑤达斯古珀塔的结论是:《斯特恩报告》作者所提出的对气候变化即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主张是其有关代际平等观点的题中本有之义,但得不到作者所强调的有关气候的新事实多少支持。评论全文见:http://www.econ.cam.ac uk/faculty/dasgupta/STERN.pdf
⑥来自俄罗斯的黑客于2009年11月17日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传了一张“东英吉利大学”(East Anglia University)气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的文件,随后多达16兆的这些科学家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被公开在网上。10天(11月27日)后,“东英吉利大学”发表声明,确认本校服务器被入侵,上千封电子邮件和3000多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被盗载。“CRU”是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全球领先机构,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被曝光的一些邮件显示,这个世界著名的权威气候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可能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以便支持碳排放愈演愈烈的结论。邮件在网上公开后,一时舆论哗然,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作“气候门”。12月4日,来自哈佛大学等多所名校的25位美国科学家发表公开信,称这些邮件的内容无法动摇全球变暖的现有结论,决策者和公众应该明了控制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一些国家的民意出现微妙变化,美国媒体12月8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45%受访者认同气候变化问题主流科学家的看法,这一数字在两年前为56%。
⑦转引自《走出气候门》,载《汕头经济报》,2009-12-09。
⑧可参:“How Confucianism could curb global warming:China openly debates the role of Eastern thought in sustainability”,by James Miller,from the June 26,2009 edition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http://www.csmonitor.com/2009/0626/p09s01-coo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