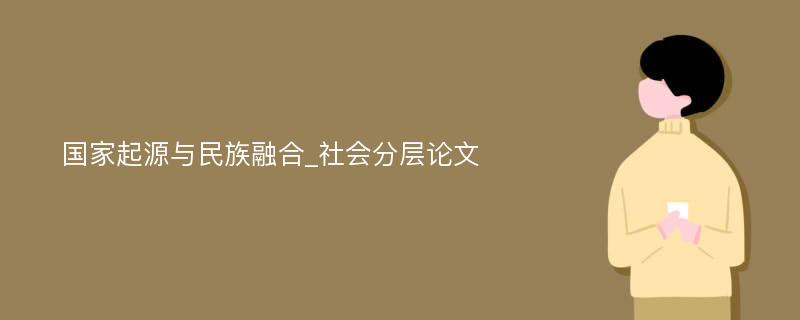
国家起源与民族聚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苏联民族过程理论认为,民族发展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民族分化和民族聚合两种过程;民族分化是前阶级社会民族过程的主要内容,而从原始社会解体开始,民族聚合过程便占了主导地位。[①a]这是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论点。国家起源是可被多种视角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杨堃先生曾把国家产生的物质条件归结为四种:1.有利的地理环境;2.相当多的人口数量;3.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民族关系。[②a]其中第4种是一个独特的见解,却未引起足够注意。但当我们把这种见解结合民族过程考察时,却发现国家是一个民族聚合过程的产物。[③a]应该说,这个发现是有意义的。本文旨在陈述这个发现,以期丰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一、国家产生的一般机理
在找出国家起源与民族聚合过程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依据已有的研究对国家起源的一般机理作出概括。
国家起源研究,若从最早留下有关论述的柏拉图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把这一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的研究基于两个基础:一是由他们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二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进化论所支配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出现。前者保证了整体研究方法的科学,后者为研究找到了可资论证的依据。正是这两点使他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臆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其论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并不标示这一问题研究的终结,相反,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世界整体科学水平的提高,《起源》发表100多年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更大发展。这些研究视域宽、层次深,且学说众多、观点纷呈。国家起源虽然只是社会政治系统的演化变迁,但人们的研究已触及到了与之有关的经济过程、政治技术、社会规范、心理模式和地理环境等各个领域。与之相应,所谓“征服论”、“战争论”、“进化论”、“冲突论”、“融合论”等各种学说也纷纷涌现。我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也依据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
既有研究是继续研究的基础,国家产生一般机理的概括也必须以已有的成果作出。
(一)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标志
“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①b]这是恩格斯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这里,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但当代的有关研究表明,用“社会分层”来概括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似乎更准确。“社会分层”指的是“根据财产、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垄断把社会集团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种姓、阶级和阶层。”[②b]社会分层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隐伏着社会冲突的根源。所以只有存在社会分层才会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威胁,才有在政治上建立国家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社会分层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分化,但又不限于阶级分化。因为种族、民族、宗教、职业和种姓等也都可以成为社会分层的内容,这些分层的存在同样也是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罗马国家的形成时提到的平民和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③b]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④b]但却是对立的社会分层,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的社会地位,而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国家的建立。
其实,把社会分层看作国家产生的基础也是当代国家起源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如“冲突论”的代表人物莫顿·弗里德认为,国家是为了通过运用强制性的机构来维持经济分层而出现的,一旦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出现了社会分层,这个社会内部就存在着不稳定。因此,分化了的社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大大加强以前就已存在的统治机构,这个强有力的机构是国家。[⑤b]此外,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将社会分层作为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说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分层包括着阶级对立和冲突的内容,且在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对立已是社会分层的主要内容。用社会分层表述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是对阶级斗争说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取代。
国家是前国家社会的政治机构演进的结果,但演进到哪一步才算出现国家了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提出了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准:“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①c]现在看来,“第二个不同点”是正确的,而“第一点”则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中外学者看法几近一致。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氏族组织和国家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氏族组织在内的血缘团体在国家社会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作为国家组织的不同层次长久地存在。所不同者仅在于氏族部落已不是独立的社会实体,而是包容在国家之内,成为国家的不同组织了。按地区划分国民是在国家社会内逐渐完成的过程。实际上,即使恩格斯本人也更看重“公共权力”这个标准,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②c]
关于“公共权力”的具体涵义,恩格斯讲:“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③c]也即“公共权力”是一个实施强制行为的暴力机关。此外,“公共权力”还应是一个能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这是近年来人们较多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不少学者在其国家定义的表述中也突出了这一点。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把国家定义为“管理机构集中化、专门化的社会。”[④c]魏特福称国家为“专职人员的政体。”[⑤c]我国也有学者把酋邦和国家在政治技术上的区别看做是否“形式化”或“专门化”。[⑥c]所以,完整地看,国家形成的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则具有强制性和专门化两个特点。
(二)国家形成的途径
国家形成的标志虽一样,但形成的途径则不同。这是必然的。大千世界,人类所居之处自然环境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形成国家的途径也必然不一样。然而下述几种国家形成模式却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这即是恩格斯所讲的三种模式加上灌溉(或治水)模式和贸易模式。
恩格斯所讲的三种模式分别是指雅典模式、罗马模式和德意志模式。他对这三种模式的总结是:“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的。”[⑦c]
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些是与这三种模式契合或比较契合的。如以弗里德和怀特等为代表的“冲突论”或“进化论”者主张,国家最初是作为解决社会内部由经济分层引起的冲突的强制性机构而发展起来的。这显然与雅典模式一致,也贴近罗马模式。而奥本海默和冈普洛维茨的“征服论”则认为,征服者在被征服地区强加统治是国家的开端,阶级分化和国家产生于一个社会被另一个社会所征服。[①d]这显然又是德意志模式的不同表述。
灌溉模式以美国人魏特福的论述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东方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大规模的灌溉起了主导作用,因为这种灌溉要求一个特殊的管理集团来组织大批的劳动力。这个管理集团要具有监督、管理、计划、防务等各种功能,因此必须是专职的,而且是专制的,国家即由此建立起来。[②d]这个观点因被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激烈批判,但其所叙理论和西亚、埃及等早期国家的形成的确有相合之处。此外,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夏朝国家的建立直接导源于大禹治水。从尧时开始的大洪水要求中原地区的各部落必须联合,并服从统一的调动指挥,禹作为统一治水的指挥者而成为王朝领袖,因治水而形成的部落联盟机构也因此发展成为国家。可见,国家作为一种最高社会管理机构,从某些早期社会最迫切的灌溉或治水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开始,进入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同样出于社会统一管理而进入国家的另一渠道是贸易。哈斯曾把贸易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亨利·赖特和格雷戈理·约翰逊提出的地区内部贸易途径:由于人口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日用品和食物量的不断增长,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分工和交换。在解决这种地区内部的贸易管理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管理阶层。这个阶层不断分化后,社会在组织方面就达到了国家水平。这是对伊朗西南部国家形成的概括。另一种是威廉·拉思杰揭示的地区之间的贸易途径:由于相邻地区生活资源的不同,出现了一个中心贸易系统。控制了这个贸易系统的管理人员由于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实现了对民众的统治,并支撑起一个国家水平的权力机构。这是对中美洲低地国家形成的概括。[③d]从贸易途径进入国家的事例不多。
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三种共有现象
上述国家形成的一般机理表明,世界各地形成国家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但在步入这些不同途径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下述三点是至为明显的:
(一)最早的国家都出现在自然条件良好的经济发达地区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已被公认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根据最早的文字材料和其它考古发现,苏美尔建国之时已有了犁耕,有了大麦和小麦的种植,有山羊、绵羊、牛、驴等家畜的饲养和以冶金(金、银、铜)及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④d]反映埃及城邦国家产生时期的涅伽达文化说明,当时的尼罗河谷地的居民已开始在河谷两岸挖渠道,筑堤坝,从事人工灌溉农业。我国夏朝的建立约在B·C·21世纪,但远在建国之前的龙山文化,甚至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了成熟的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⑤d]《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正说明夏国建立与农业的关系。此外,印度、地中海沿岸和美洲早期文明地区的历史也都反映出国家形成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国家起源期间都有频繁的民族流动
这一点因研究国家起源者鲜少提出,故需把最早出现国家的几个地区的情况一一列出。
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的河流平原地形决定了这里容易形成民族聚集和流动。创造这一地区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并非土著,而他们却也未能成为这里永久的居民。“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斗争的历史。”[①e]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段话已把问题说清了。
古埃及:古代埃及三面沙漠,一面临海,有着良好的自然保护屏障。但优良的环境也并没能使这里的民族保持纯一。直接导出埃及文明的巴达里文化说明,建立国家前夕的埃及人已有“不同来源的混种”。古埃及文化具有古代非洲民族文化的特征,也有古代西亚文化来源的特点。
黄河流域:我国夏朝建立之前的黄河流域曾是一个不同部落集团你来我往、流动频繁的地区。黄帝、炎帝、蚩尤、太昊、少昊等部落的长期征伐,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最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②e]
古代印度:标示古印度跨入最早文明行列的是“哈拉巴文化”。这种起自B·C·2050年持续700年左右的文化的兴衰已无法得到说明,而能够得到清楚说明的下一阶段的印度文明则是由来自西北方向的雅利安民族所建。这个外来民族经过长期战争征服了原有居民,在几个世纪之内,先后使他们成为印度河流域和恒河上游地区的统治者,并于B·C·9世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雅典:雅典国家所处爱琴海文明区域,恩格斯所述的雅典远不是这一区域最早的国家。爱琴海地区最早的国家出现在B·C·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而正是在此之前的200年左右时间里,这一地区出现了一次移民运动,新来者是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一批印欧人。稍晚于此的从迈锡尼文明中产生的国家也是另一部分新移民所建。更晚于此的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经过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冲洗的。因为在此之前所经历的“荷马时代”,即各部落大规模征战的时代,与B·C·12世纪由多利亚人南移推动的另一次民族迁徙有直接的关系。
罗马:罗马国家建立之前的民族流动更为明显。从B·C·二千纪初直到B·C·6世纪这里就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民族流动:1,B·C·二千纪初,包括拉丁人在内的一批印欧人由东北方向移入。2,B·C·1200至B·C·1000年第二批印欧人移入,包括萨宾人、萨莫奈人等部落。3,B·C·11世纪,来自小亚细亚的伊达拉里亚人渡河而入。4,B·C·一千纪到B·C·7世纪,包括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内的地中海先进国家的民族移入。频繁的民族流动,使这一地区有了相当程度的民族融合。所以,“王政时期”的七个王中既可以有拉丁人、萨宾人,又可以有伊达拉里亚人。罗马国家实际上建立在民族聚合正在完成但又尚未完成时期。所以,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纠合在一起。“平民”和“罗马人民”的冲突既含有阶级冲突,又含有氏族部落成员同被征服但尚未被溶合于内的其它社会成员的民族冲突。罗马国家的建立则是这种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
德意志:在恩格斯所讲的三个模式中,德意志国家的建立就是民族征服的结果。这已是最激烈的民族流动的表现,在此无须赘言了。
古代美洲: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是殖民主义入侵之前最大的美洲国家,而建立这一国家的阿兹特克人则是13世纪以前才由北方来到墨西哥盆地,逐步征服和吸附当地的民族后建立国家的。中央安第斯山地区印加国家的建立也是一个典型的由征服其它民族而建立国家的事例。印加人是花了几个世纪的功夫才把自己的势力推及到整个安第斯山沿海某些山区的。这种征服过程自然也是民族迁徙的过程。
可以看到,所有最早进入国家的地区,在国家形成之前或形成期间,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和迁徙。这是一种十分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
(三)频繁的战争
民族流动与战争是形影相随的,凡有民族流动的地方必伴随有频繁的战争。这可说是一条规律了。浏览这一时期的史迹,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的记录往往成为主要内容;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文化中的刀剑弓矢与累累尸骨的交叠也已向人们作了最明白的昭示。在氏族社会,“凡是部落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①f]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很贴切的。
当我们把国家起源过程中的这三种共有现象作了上述排列之后,不由会惊异地发现,这三点恰好展示的是一种民族聚合现象:趋利避害、向往最好的生存环境,驱使不同民族向不多的几个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于是发生民族流动;因聚集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得不到解决,于是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是古代民族交往的最普遍形式,也是打开民族壁垒实现民族聚合的主要途径。战争以表面冲突的形式反映着民族聚合的内容,而国家也正是在这种聚合进程产生的剧烈社会震荡中发生的。
三、民族交往与社会分层
民族聚合以民族交往始。对于前国家社会来说,这种交往一般限于三种形式:交换、战争及出于利用和抗御自然的联合。其中,战争最为普遍,但其余两种也并不罕见,只是影响不及战争罢了。这三种交往虽形式不同,但却从不同方面共同营造了国家。
先看它们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社会分层的发生与交换和战争有直接的关系,而和出于利用和抗御自然的联合关系不甚明显。
(一)交换与社会分层
前已谈到,社会分层是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强调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因为造成社会冲突而导致国家建立的主要是阶级冲突,而交换又与阶级的出现关系至为密切。
什么是阶级?最权威的定义为列宁所下:“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g]从列宁这个定义可知,阶级不仅是经济关系上处于对立的集团,而且也包括由于分工不同而在经济关系上处于并列的集团。如奴隶和奴隶主是对立阶级,而农民、手工业者则是并列的阶级。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分工的出现也便意味着阶级的出现,但这只能就社会内部的分工而言,而实际上,真正的社会分工最初是在社会之间,即氏族部落之间。恩格斯讲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实际也即是民族大分工。民族之间的分工不是阶级的出现,但却造就了阶级产生的催化物——交换。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交换的出现,不管是社会内部的,还是社会之间的。民族之间的交换是通过三种形式促进社会阶级形成的:
1.由民族之间的交换内化为民族内部的交换。这个过程是同相互交换的民族聚合为一个民族同时完成的;而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由交换形成的民族关系便内化成了阶级关系。但这种聚合的实现在前国家社会决不会由交换单独完成。在战争作为民族交往主要形式的时代,交换只能作为聚合过程的一种辅助因素。所以,尽管有人可以把中美洲国家起源的途径归入贸易模式,但却无从抹刹国家形成过程中残酷的战争史实。
2.民族之间的交换既能促进民族内部生产力的提高,又能刺激生产关系的分化,从而促进阶级分化。正如马克思所讲:劳动产品“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②g]交换从来就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族际交换的发生必然刺激族内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刺激阶级的形成。恩格斯讲的第一次大分工造成了社会第一次大分裂,即分裂为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③g]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3.交换过程本身也造就阶级分化。起初,民族间的交换由各自的首领进行,交换的物品为氏族部落的公有财产。当私有财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后,这些首领便把交换变成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从而成为剥削阶级。
(二)战争与社会分层
战争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人类社会集团之间发生的一切暴力冲突。这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定义,恩格斯在《起源》中对于战争的记述也出于此义。狭义,即由克劳塞维茨所提出又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首肯的公式: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由阶级矛盾和政治利益冲突所引起。本文取广义,以便于叙述。由此,战争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即在于下述三点:
1.战争造就最早的对立阶级。自民族产生以来,最初的战争都只能是民族之间的战争。道理很简单,民族,即氏族部落内部公有、平等,无发生战争的条件。但在民族之间因接触而发生暴力冲突则十分自然:为争夺食物、生存地域或妇女。起初,因民族人口稀少,接触不多,战争的频度不高,规模不大;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将对方驱逐、杀死、将财物或妇女掠为己有。“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决不能以它的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④g]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民族人口增加、规模增大、民族间的接触也日益增多,战争的频度和规模开始加大。由于这时民族内部有了一定剩余产品,为使用无偿劳动力创造了条件,所以战争各方便将战俘变为奴隶,无偿占有他们的劳动。于是一部分以剥削奴隶为生的氏族贵族发展起来,与战俘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立阶级:奴隶主和奴隶。由此来看,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起源于民族对立,而且在战俘尚未被同化于征服民族以前,阶级对立也便是民族对立。
2.战争刺激财富的聚敛,促进了社会分化。当战俘被变为奴隶以后,不仅把一种民族关系内化为阶级关系,更重要地还在于激化了社会内部的分化。恩格斯讲:“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创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背景。”[①h]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公有制原则的被破坏,在一部分氏族贵族因使用奴隶而加速富有的同时,另一部分,也是大部分氏族成员则因不同的原因而沦于贫困,由此逐渐形成社会阶级的梯次结构:奴隶主、平民和奴隶等。这一点在《起源》中叙述是很清楚的。
3.战争还可成为其它社会分层的原因。如瓦尔那,即种姓制度是印度特有的社会分层制度,而它的起源则是印度雅利安人对土著达罗毗荼人的征服。“瓦尔那”(Varna)原义为“色”,原是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时用于区分白肤色的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黑色土著居民的用语。起初只有“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之分。“达萨”即被征服的土著人奴隶。只是后来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才在雅利安人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等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但土著居民仍然被作为最下等的种姓首陀罗而存在。[②h]这是战争对社会分层留下的深刻烙印。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因战争而导致的由民族因素构成的社会分层也时时可见。如匈奴国家即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包括匈奴、东胡、楼烦、白羊、丁灵、月氏、乌孙和西域各族等。但处于统治地位的则是匈奴民族,他们之中的显贵氏族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则又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在匈奴之外的其它民族则分别处于或奴隶或附庸的不同等次。[③h]这种社会分层也是源于匈奴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战争和征服。
至此可以看出,民族交往的交换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社会分层的形成,由此奠定了国家形成的基础。
四、民族交往与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
与社会分层不同,在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方面,民族交往的各种形式都起着作用,而且这些作用更为明显和直接。
(一)交换与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
个别的、小规模的交换不会对政治制度发生影响,但当它发展成决定民族生活的主要经济形式之后,其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便如“贸易论”者所揭示的了。其大致过程即如上引赖特和拉思杰等人所述,由于交换而产生了贸易管理,在此过程中一些管理人员由于掌握了基本生活资料而形成专权,并进而建立起国家权力机构。
(二)民族联合与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
民族联合的缘由除了战争之外便是出于对自然的利用和抗御了,而通常又是出于大规模的农业灌溉和抗御洪水。前者即如“灌溉论”者援引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例,后者即如我国学者援引的大禹治水之例。在强大的自然压力面前,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合作,于是出现了民族间的联合,联合起来的群体必须统一行动,因此出现了集权;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需要分工协作,于是出现了专门的职能部门。而当这些集权和职能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扩展和正规化以后,作为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便出现了。
(三)战争与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
如果说,交换和联合在促进公共权力机关的设立方面仅是某些地方的局部现象的话,那么战争在这方面的作用则可说是各地的共有现象了。因为即便被认为是由于贸易和灌溉而产生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战争的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在这些地方,应该说战争与贸易或灌溉等一同促进了国家的建立。概括地说,战争是通过下述几点促成国家机构的建立的:
1.促成相邻族体的联合,使前国家政治系统开始跨出氏族结构。氏族和与此前后的队群和部落是前国家社会的普遍社会组织形式,它只适应于小规模的民族社会;而在战争频仍的原始社会末期,无论是防卫自己还是进攻别人都需要有共同利益的族体走向联合。正如恩格斯所讲:由于战争,“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①i]这种族体的联合,恩格斯称之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有亲属部落的联盟,也有非亲属部落的联盟。它的特殊点在于各组成部落之间的平等联盟关系。但实际上,除了部落联盟之外,“酋邦”也是这种族体联合的形式。酋邦的形成或经过部落之间的征服,或经过部落联盟的演化。所以,不论酋邦还是部落联盟,都是族体的联合或增大。这种联合或增大都是与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同步而行的。这为社会冲突的发生增添了更大的可能,也为维持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提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
2.战争使政治机构趋向军事化、专门化。与不断发生的战争和族体联合相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上的军事化。恩格斯将其称作军事民主制,认为每个进入国家的文化民族都曾经历过军事民主制时代,如雅典的“荷马时代”,罗马的“王政时代”等。由于酋邦社会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不宜再提“军事民主制”。的确,恩格斯讲到的军事民主制是和部落联盟对应的制度,这种制度都有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军事首长三种机构。而这些在酋邦那里只剩下后两种或最后一种了,已没有多少“民主”色彩。但无论如何军事制度的痕迹十分浓厚,酋长也即是战时的军事首长。这和恩格斯讲的部落联盟没有不同。部落联盟和酋邦都可以成为国家的过渡形态。前者因民主制度较浓,可以使过渡后的国家呈现共和的体制,如雅典和罗马;而后者因民主制度消褪则可能走上专制了。
军事化政治机构的特点有两条:一是集权,二是强制,这也正是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关所需要的性质;部落联盟和酋邦军事化政治机构的出现也正是从这两点上为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专门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又一特征,而它的出现也必然是由军事化机构凝固化以后的产物;并且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这种机构也向它所需要的方向分化,从而成为专门化的另一渠道。
3.军事征服后对异族的统治需要强制和机构的专门化。恩格斯对德意志国家形成的叙述为此提供了具体事例:“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①j]恩格斯在这里仅提到了军事首长向王权的转化,但却是最具本质的转化。因为只有王权才最深刻地体现着集权和强制,体现着国家和前国家政治机构的区别,其下属政权机构的专门化也只有随着王权的确立才能确立和扩展。
总之,战争对国家机构建立的促进在于促使族体之间的联合,在于带有军事色彩的政治机构的创立和扩展。至于这种机构如何最终完成向国家的转化,则是各种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或通过政治改革,或通过对外征服,已不再具有同一性了。
完成了上述分析,国家起源于民族聚合过程的立论便可清晰了:当人类在其分化阶段完成了不同民族的孕育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变化开始缓缓流动,而农业最早发生地区展示的良好生存环境驱使他们纷纷向这些地区汇集。于是,民族过程的聚合阶段到来了。民族聚合的大门是由民族之间的交换、联合战争和出于对抗和利用自然的联合打开的。而在这扇大门打开的同时,民族之间的交换、联合和战争也造就了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层和军事化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和组织基础。国家起源于民族聚合,在于这种聚合带来的社会冲突和为解决冲突引发的政治变革。民族聚合过程带来了由民族碰撞激发起来的社会震荡,也创造了平息这种震荡的工具——国家。
注释:
[①a] (苏)勃罗姆列伊、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
[②a] 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
[③a] 本文“民族”取泛义,即为民族学所研究的“ethnos”,包括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
[①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8页。
[②b] 吴泽霖总纂:《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③b] 德文populus Romanus在汉文中有不同译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译作“罗马人民”,《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译作“罗马公社”;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为“罗马民族”。
[④b] 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叙,“罗马人民”和“平民”的区别在于:前者处于氏族、库里亚(胞族)和部落之内,而后者则在这些组织之外,二者因此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但这种区别不全在于经济关系,不能算是真正的阶级关系。
[⑤b] Morton.Fri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P225,1967.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6—167页。
[②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14页。
[③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7页。
[④c] (美)乔纳森·哈斯著、罗林平等译:《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⑤c] K.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P239,1957.
[⑥c] 谢维扬:《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
[⑦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5—166页。
[①d] (美)乔纳森·哈斯著、罗林平等译:《史前国家的演进》,第4、48页。
[②d] K.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b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P18.
[③d] (美)乔纳森·哈斯著、罗林平等译:《史前国家的演进》,第124—127页。
[④d] 本节材料除另注外,均取诸《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古代社会》(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⑤d]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e]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②e]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f]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94页。
[①g]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页。
[②g]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5页。
[③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57页。
[④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54页。
[①h]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4页。
[②h]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2页。
[③h] 参见林斡《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载《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0页。
[①j]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