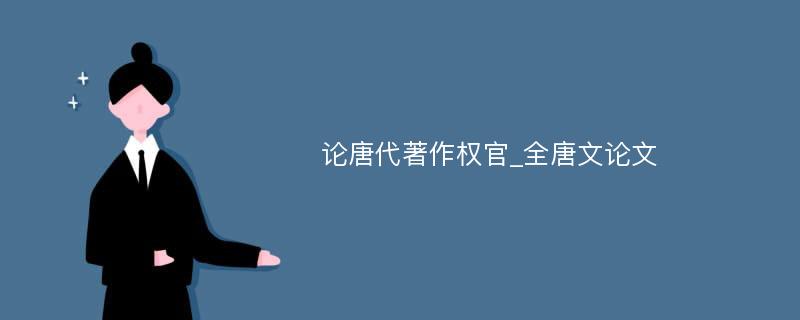
唐代著作郎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著作论文,郎官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6)03—0105—07
唐代的著作郎官隶属秘书省,虽与尚书省郎官隶属不同的省,但与尚书省郎官一样都属于清官。“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四品以下、八品已上清官。……五品谓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赞善大夫,太子洗马,国子博士,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率府郎将”。[1]33 (《唐六典》卷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郎官在唐代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象征,一般不能轻易地授予。《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乾曜之男洁白其父曰:‘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2]3235 (《旧唐书》卷一百六)著作郎虽属于五品清官,却是人所艳羡的一个职位。许敬宗在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3]633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由此可见,不论是尚书省郎官还是秘书省的著作郎官,在唐代都享有较高的声誉。著作郎在唐代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职能,虽然唐代的秘书省“别立史官”,[4]3205 (《全唐文》卷卷三百十六)但仍“多以著作郎领带其职”,[4]3205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史馆别立之后,昔日的著作郎所掌,“唯碑志、祭祝之文在焉”,[4]3205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然以其能综群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国,转为郎官,经纬斯文,昭宣有政,或上迁秘书少监,或擢拜中书舍人,固不易其任也”。[4]3205 (《全唐文·著作郎厅壁记》卷三百十六)著作郎由于其才华出众,故当中不少人升迁至更重要的职位,参与治国方针策略的制定,对唐代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从著作郎官的设置沿革,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任命及弊端与其文化意义三个方面对其加以探讨,以期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一、著作郎官的设置及其沿革
著作郎一职在汉代有其实而无其名,“著作郎: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5]736 (《通典》卷二十六)直至“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隶中书省,专掌国史”,[5]736 (《通典》卷二十六)到“晋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5]736 (《通典》卷二十六)于是“改隶秘书,后别自置省,(谓之著作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5]736 (《通典》卷二十六)其后宋、齐与晋同。
著作佐郎一职亦始于魏,“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属中书。晋佐著作郎八人,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秘书监自调补之”,[5]736 (《通典》卷二十六)而“晋制,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初,以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废矣。宋、齐以来,遂迁‘佐’于下,谓之著作佐郎,亦掌国史,集注起居。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其职,冠制与大著作同。陈氏为令、仆子起家之选。后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齐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后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缀国录,属春官之外史。隋于秘书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炀帝加佐郎为十二人”。(《通典》卷二十六)[5]737
唐因隋制,改隋代的著作曹曰著作局,“大唐为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开元二十六年,减佐郎二员)亦属秘书省。(自宋以后,国史悉属秘书)龙朔二年,改著作郎为司文郎中,佐郎为司文郎,咸亨初复旧。初,著作郎掌修国史及制碑颂之属,分判局事,佐郎贰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实无其任,其任尽在史馆矣。其属官有校书郎二人,后魏著作省置校书郎,北齐著作亦置校书郎二人,隋亦同,掌雠校书籍,若本局无书,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减一人,掌同校书)”。(《通典》卷二十六)[5]737
唐代著作局除设置著作郎和著作佐郎外,尚有属官“书令史一人,书史二人,校书郎二人,正字二人,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1]301—302 (《唐六典》卷十),著作郎官品为从五品上,佐郎为从六品上。唐初,著作郎们的主要职责为修撰国史,但自“贞观二十三年闰十二月,置史馆于门下省,宰臣监史,自是著作罢史任”。[6]1123 (《唐会要》卷六十五)故其职能转为“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1]302 (《唐六典》卷十)由于“贞观初,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以他官兼领”,[1]281 (《唐六典》卷九)所以大多数著作郎官仍旧参与史书的修撰。如“初唐八史”和国史的修撰者有不少为著作郎,“(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元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邱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6]1091 (《唐会要》卷六十三)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为《晋书》修撰的主要人员。唐代的著作郎官参与国史的修撰、撰写碑志等,对唐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唐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职责及其弊端
唐代的著作郎官与尚书省等郎官一样有职事官和赠官之分。职事官即担任著作郎官并履行其修撰的职责;赠官则为赠与其职而未必履行其职责的一种方式,即非职事官。著作郎官选拔和任命的方式与其他的官职选拔相类。综观唐代的著作郎,其任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科举入第,这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唐代大部分著作郎的选拔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如皮日休“咸通八年登进士,授著作佐郎”[4]3697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第二贬官,即由官阶高的官位贬为著作郎,如“舒元舆为刑部员外郎,太和五年贬为秘书省著作郎,仍分司东都”[7]5744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第三征召,即征辟那些有才学、有德行、有声誉的隐士,入朝为著作郎,如阳城,“陕虢观察使李泌闻其名,亲诣其里访之,与语甚悦。泌为宰相,荐为著作郎。德宗令长安县尉杨宁赍束帛诣夏县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辞让。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后诏,赐帛五十匹。寻迁谏议大夫”[2]5132 (《旧唐书》一百九十二)。再如李渤,“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遂家东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九年,以著作郎征之”[2]4437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第四推荐,即通过在朝的师长、友人等推荐入为著作郎,如崔沔“姚、卢时在政事,遽荐沔有史才,转为著作郎”,[2]4928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因有史才而被举荐为著作郎;第五荫补,即通过祖辈或者父辈资历而入仕的方式。如路应“应,字从众,以荫为著作郎”[3]4624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第六敕赠,敕赠为一种偶然的方式,取决于帝王的喜怒爱好,也受得官者自身资质的影响。如杜审言本为著作佐郎,后诏赠为著作郎。
不论是职事官还是赠官,著作郎的选拔任命总体标准是一致的,即以文、行取人。这种方式与魏晋六朝品评人物的方式相近,即通过品藻人物的才能和德行来鉴定一个人,然而著作郎的授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唐代普遍实行的取士方式获得,所以较之魏晋六朝人物品鉴的“九品中正制”还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著作郎官的授予资格,可以通过排列分析几例授官的诏令得知。
李峤《授崔融著作郎制》:
鸾台:具官崔融,长才广度,赡学多闻,词丽杨、班,行高曾、史。外台美其方正,中省推其良直,永言司典,尤俟得人。载笔西垣,既藉微婉;紬文东观,更资博通:宜著作之庭,兼践记言之地。可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官。(《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二)[4]2488
苏颋《授吴兢著作郎制》:
黄门:朝议大夫守谏议大夫上柱国兼修国史吴兢,服言行,贯穿典籍,蕴良史之才,擅巨儒之义。顷专笔削,仍侍轩阶,而官之正名,礼不以讳,宜著书于麟阁,复载籍于鸿都。可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馀如故,主者施行。(《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一)[4]2542
苏颋《授胡皓著作郎制》:
黄门: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上柱国金城县开国子杜元逞,久登位事,早负声实,择言以法,饰吏以文,清方蕴其素心,断割成其利器。用才可任,惜太官之滞留;备物惟殷,当御府之关综:宜膺宠命,式副佥选。可殿中少监,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一)[4]2542
孙逖《授司马利宾等著作郎制》:
敕:朝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司马利宾等,或富于学业,或精于吏能,公清为洁已之资,词赋有成名之美。举其同术,宜并拜于轩墀;甄其异用,俾分官于儒馆。可依前件。(《全唐文》卷三百九)[4]3137
宪宗《授李渤秘书省著作郎诏》:
前左拾遗内供奉李渤,隐居求志,殚见洽闻,尝致弓旌之招,尚怀林壑之恋。如闻肄其素业,成此新书,词章典雅,谋议深远。献于阙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恩,用清旧议。可授秘书省著作郎。(《全唐文》卷六十)[4]646
由以上五个授官制可以看出著作郎官授予者的共同点,其一为“赡学多闻”、“清为洁已之资,词赋有成名之美”即文学才华出众;其二为“久登位事,早负声实,择言以法,饰吏以文,清方蕴其素心”即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品行高尚,声名远播,在当时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甚至为名播一方的隐者,如李渤“前左拾遗内供奉李渤,隐居求志,殚见洽闻,尝致弓旌之招,尚怀林壑之恋”。德宗时的阳城也为曾为隐者,因有德行而被征召。这些不仅与唐代一贯的铨选标准,即“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5]360 (《通典》卷十五)相一致,而且更加突出“德”与“才”的要求。秘书省是唐代重要的文化机构,著作郎是秘书省里的重要官员,对于这些官员的严格选拔,可以看出唐代对于文化审慎与尊崇的态度。
唐代著作郎的职责在于“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4]3204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但是唐代的著作郎官职责因“贞观初,诏梁国文昭公、郑国文贞公统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亲垂笔削,与《春秋》合符,……因是开馆于内,别立史官”,[4]3204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虽然“多以著作郎领带其职”,[4]3204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但其主要职责还是“唯碑志、祭祝之文在焉”。[4]3204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唐代著作郎的职责由掌修史而变为掌碑志、祭祝之文,这个转变不仅表明了唐代对于修史的格外重视,同时也表明了唐代学术分科的细致,分工的细化及应用公文的多样性,而且也凸现了唐人“重生厚死”的生命观念。建寺立碑是唐代对死者的一种重要的纪念方式,如“贞观三年十二月一日诏:‘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伐。誓牧登陑,曾无宁岁,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为事条以闻。’仍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记铭功业。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宏济寺,宗正卿李百药为碑铭;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著作郎许敬宗为碑铭。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起居郎褚遂良为碑铭;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著作郎虞世南为碑铭;破窦建德于氾水,立等慈寺,秘书监颜师古为碑铭;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昭福寺,中书侍郎岑文本为碑铭。已上并贞观四年五月建造毕”。[6]849 (《唐会要》卷四十八)唐太宗令著作郎许敬宗、虞世南分别为普济寺和昭觉寺撰写碑铭,以纪念在大唐帝国建立之初而捐躯的将士,体现了对这种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肯定。
唐代的著作郎官阶为从五品上,官阶不高亦不低,位置却很重要。著作郎因“以其能综群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国,转为郎官,经纬斯文,昭宣有政,或上迁秘书少监,或擢拜中书舍人”。[4]3205 (《全唐文》卷三百十六)通过不同方式入仕的著作郎官,其文化修养和道德质量也表现为良莠不一。故有些著作郎官升至宰相;有些一生著述不休,留下大量的著作;而有些则滥竽充数,居其位而不谋其职。陆长源在《上宰相书》中直陈不讳“且尚书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光禄不供酒,卫尉不供幕,秘书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虚设,禄俸枉请”[4]5184 (《全唐文》卷五百十)极言庸官之弊。
造成著作郎官泛滥及其弊病存在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是由于皇帝的滥加滥赠;二是著作郎官自身才不称职;第三则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武则天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批削贬亲李唐的官员,大量任命自己的亲信,其中著作郎官的滥赠也在其中。
“天授二年二月十五日,十道使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魏州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盖天后收人望也。故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脱校书郎。试官自此始也。”(《唐会要》卷六十七)[6]1180
大量的试官和滥官造就了唐代的冗官,著作郎当中亦不免有滥竽充数的庸官。如著作郎杨安期,就因为才职不称而被弹劾。盛唐时期的张鷟在其《著作郎杨安期学艺浅钝文词疏野凡修书不堪行用御史弹才不称职官失其人掌选侍郎崔彦既亏清鉴并请贬退》奏章中就弹劾杨安期,“安期才无半古,学未全今,性无异于朽材,文有同于敝帚。画虎为犬,疏拙有余;刻凤为鸱,庸才何甚?文词蹇钝,理路乖疏,终取笑于牛毛,徒自矜于鸡口。崔彦位参藻镜,职掌权衡,未分麟鹿之殊,莫辨枭鸾之异。投鼠尸于玉府,有秽奇珍;掷鱼目于珠丛,深轻宝物。躄士之追蹇兔,罕见成功;盲人之配瞎驴,自然俱败。选曹简要,秘局清高。理须放还,以俟来哲”。[4]1764 (《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三)郎官须是有素行且才望高者, 这是唐人对于郎官一贯的要求,不仅选拔严格,更是不可滥赠。故玄宗时的李林甫被拒授郎官在情理之中。文宗时,盐铁判官姚勖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但是
“制出,令勖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勖检校礼部郎中。翌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嗣复对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勖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出为陕虢观察使。”(《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2]4379
韦温宁愿接受出官的惩罚,也不改变与降低其对于郎官选拔与任命的标准,郎官在唐人心目中作为清选,且不可随意动摇其铨选标准的事实由此可见一斑。
政局动荡黑暗也使著作郎的设置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白居易就曾尖锐地指出这样的社会弊病“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刘辟肆乱心,杀人正纷纷。其嫂曰庾氏,弃绝不为亲。从史萌逆节,隐心潜负恩。其佐曰孔戡,舍去不为宾。凡此士与女,其道天下闻。常恐国史上,但记凤与麟。贤者不为名,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辈,身死名亦沦”,[8]4660 (《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四)白居易处在政治黑暗,政局不稳的中唐后期,这个时期许多制度一再受到破坏,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制度破坏造成的恶劣表现之一就是一些身居其位的官员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白居易对当时不能尽其才的著作郎樊宗师婉言相劝“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8]4660 (《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四)建议樊宗师发挥自己的才能,编书修撰,以备后来。
另外,著作郎官的选拔和任命的标准中有着明显的文学因素,这与中国历代重文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一致的。如唐宪宗《追赠甄济秘书少监制》中,对于甄济的品评为“存树风节,谓之立名,殁加褒饰,所以诱善。故朝散大夫试秘书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济,昔以文雅,见称当时,尝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坚贞之正性,不履危机;睹逆乱之潜萌,不从胁污。义声可传于竹帛,显赠示贲于松楸。藩方上陈,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奖忠魂。可赠秘书少监。”[4]621 (《全唐文》卷五十七)甄济因文雅称于时,所以被辟召,又因行为坚贞,不从胁污,有义声被追赠为秘书少监。秘书少监为秘书省的高级长官,官阶为从四品上。从著作郎到秘书少监,官阶升了三级,而把“文雅”作为其入仕的起点,由文而推及其行,跟自孔子以来认为诗文创作跟德行一致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诗》、《书》、《礼》也。此三者,先王典法,临文教学,读之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背文诵,但记其揖让周旋,执而行之,故言执也。举此三者,则六艺可知”。(《论语注疏》卷七)[9]2483
唐人对于著作郎的要求和期待同样充满文学的意味,“著作之司,艺文之府,既藉贤良,实资英俊。自非干宝赡学,无以措其锋颖;孙盛宏词,讵可尘其简牍?”。[4]1764 (《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三)唐代的部分著作郎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例如,杜审言。史传记载“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大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3]5735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审言因其才华,而拜受著作佐郎,卒后,还追赠著作郎,无不跟他的文学才华相关。《全唐诗》保留大量曾任著作郎的诗人与儒、释、道诗人交游唱和的作品,说明唐代历史上的著作郎是社会文化圈中的活跃分子。例如,在一系列的赠送诗歌《咏主人壁上画鹤,寄乔主簿崔著作》、《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中,保留了曾任著作郎的崔融与初唐大诗人陈子昂密切交游的事实;无可的《奉和段著作山居呈诸同志三首次本韵》一诗说明段著作郎与僧无可过从密切的事实;《同李著作纵题尘外上人院》一诗更表明了诗僧皎然与著作郎李纵共同切磋诗艺术的文学佳话,僧俗两界的诗人对著作郎及其创作都有着高度的评价。元稹的《和乐天赠樊著作》“君为著作诗,志激词且温。璨然光扬者,皆以义烈闻”,[8]4459 (《全唐诗》卷三九七)认为著作郎的著作皆以“义烈闻”,热情地赞颂了著作郎的职责所具有的社会影响。
三、唐代著作郎官的文化意义
唐代著作郎官跟其他职官一样,不仅承担社会职责,体现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在唐代文化发展史上也承担相应的文化角色。这是由它所担任的职责与此职责所蕴涵着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神所决定的,而这种特有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天命观。
著作郎官职自设置以来一直主要掌修史,但是到唐代,著作郎官的主要职责发生了变化。初唐的著作郎大都曾参与初唐八史的修撰,后来设置了史馆,其职责才发生转变,自“贞观二十三年闰十二月,置史馆于门下省,宰臣监史,自是著作罢史任”。[6]1123 (《唐会要》卷六十五)由此著作郎的职责转为“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1]302 (《唐六典》卷十)由修史转到撰碑志祝文,著作郎官职能角色的转变,表明唐人不仅仅对过去历史的重视,而且更为关注现在和自身的状态,尊重个体的生命意义。
碑志及其祝祭文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特殊的作用,祝文与祭文内容和形式既表现了对死者的尊重和哀挽,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天的崇敬与敬畏,以及祈求“天人合一”与天地共存的和谐生存状态。碑志的作用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诔碑》中有全面的论述。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文心雕龙》卷第十二)[10]61
追求不朽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执著与热爱的一种表现,用不朽的金石来替代短暂有限的生命。“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赤诚地表达了追求与金石一样不朽生命的感情与愿望。这样的方式跟自古以来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追求不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9]1979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以镌刻金石追求不朽的方式,是“不朽”的生命观在特定时代里的特定表现。
著作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撰写碑文,然后交付工匠刊刻于金石之上。通过这样的方式,逝者的生平事迹便能通过碑石铭文的记载流芳百世,以延续短暂有限的生命,达到“不朽”的目的。这也是唐代大量的墓志铭传世的原因之一。唐代的墓志铭不仅数量之多,涉及的人物也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同时还包括僧、尼、道士、女冠、妓女、宫女等特殊的社会阶层,真实勾勒唐代各个阶层人士的生活状态,使我们在千年之后仍然能够了解这些人当时的生活境况,从而达到了其追求与金石同“不朽”的目标。
综上所述,唐代著作郎官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儒家气质的群体,其所担负著述修史与碑志、祭祝职责表明了唐代注重历史、崇尚文化、尊重个体的时代特质及唐人重生厚死的生命观念,反映了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家的文教思想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6—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