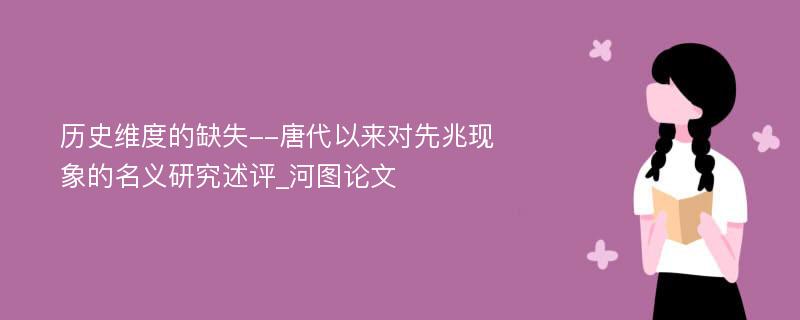
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谶纬论文,维度论文,述评论文,缺失论文,名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究竟什么是谶纬?谶纬是一是二?概括唐代以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可分为“谶纬有别”和“谶纬无别”两种(以下简称“有别”、“无别”)。① 两种观点都各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有唐以来“有别”的观点,历史悠久,可谓切理厌情。从概念和词义而言,谶和纬毕竟不是一种东西。至于后人混淆谶纬(或以“纬”称“谶”),则需要仔细考察其演变之具体情状。但是主张此一观点的论者,未能对谶、纬之演变纠结以及互辞之状况作出翔实的历史描述。而清代兴起的“无别”的观点(与“有别”说并行于世),提出汉代以来谶、纬互称以及存世谶纬佚文中谶、纬纠结无明显区别这两类证据,的确击中了“有别”论者的软肋。② 但是他们这两类证据,看上去言之凿凿,其实均可怀疑:(一)东汉后期以后确实存在谶、纬互称的现象。但是第一,谶、纬互辞现象是与“谶纬”思潮之兴起共生的呢,还是它经过了一个时段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③ 第二,也许是因为思辨尚不够严谨规范,汉代人常常会混同使用一些内涵相关的概念。谶、纬以外,比如辞、赋,在汉人那里也有混称的现象④,而在今天看来,很难说楚辞体和汉赋体是同一种文体。那么,谶、纬互称是否也类似辞、赋互称呢?或是汉人缘于某种目的有意混淆呢?若缺乏历史实感地泛泛地以谶、纬互辞现象来证明谶、纬本无分别,就不能令人信服。(二)是谶纬文献问题。今天所依据的谶纬文献,是唐宋类书以及有关的经、史、子、集中引录的片段文字,以及明代以后的辑佚著作,其中实有很多疑问。如:不少谶纬佚文原始(或早期)出处的冠名并不一致,这些佚文当如何具体安置?许多佚文在原始出处只称“纬(谶)书曰”或“某经纬(谶)曰”,当具体辑入哪一篇?同样一段佚文,不同的早期出处甚至有隶属于不同经之纬(谶)的情况,该怎样处理?实际上,不少谶纬佚文的安置,是出自辑佚者的主观判断。更有甚者,有的辑佚著作(比如最早辑佚谶纬的《古微书》)还有把非谶纬文字当作谶纬佚文辑录的情形⑤。根据这样不一定完全可靠的谶纬佚文,来证实谶、纬原本无别,总会令人起疑。
总之,“有别”说者的观点切理厌情,但他们未能对谶纬之源起、演变作出详细考察;“无别”说者提出了不少史料证据,但他们对相关文献的认识和使用都存在较大问题,也同样没有翔实的历史梳理。两种观点,都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
二
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强力反拨“有别”之说,以广征博引的史料,充分暴露了“有别”说证据的薄弱。“有别”说论证不足,已无需再述。“无别”说其实也同样存在致命缺陷,因其对现当代学界影响更大,须认真辨正。下面即以“无别”论者中成就最大、论证最专博的陈槃为例,略作申说。
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是在其四年前论文《谶纬释名》基础上充实而成,专述“无别”之义。因其史料征引详博,似乎已将“谶纬是一非二”之结论做成了定论。但是,此文的论证,实有两点严重问题:
(一)史料使用不当
有两种表现:一是把互不相干的几条材料撮录在一起比附说事,而不顾每一条材料本身究竟是何含义。今完整照录陈文的一组材料于下:
《东观汉记·郊祀志》:“谨按《河》《洛》谶书。”
《杨震碑》:“明《尚书》欧阳,《河》《洛》图纬。”
《后汉书·儒林景鸾传》:“兼受《河》《洛》图纬。”
王蕃《浑天说》:“末世之儒,增减《河》《洛》,窃作谶纬。”(《晋书·天文志》引)
《东观汉记·郊祀志》一条,是群臣劝刘秀封禅:“三十二年(即中元元年,56),群臣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谨按《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上东巡狩至泰山。有司复奏:‘《河》《洛》图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前后凡三十六事。………’”司马彪《祭祀志》记载更明确:“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⑥。感此文,乃诏松(梁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这两条史料所称谓的“《河》《洛》谶书”、“《河》《洛》图记”、“《河》《洛》谶文”其含义十分清楚,就是指《河》《洛》谶。
《杨震碑》一条,本作“明《尚书》欧阳,《河》《洛》纬度”⑦,而陈文将后句误引作“《河》《洛》图纬”“纬度”是与天象相关的词语,这个“纬”乃是指“星纬”,一般指五行星。因此,碑文所谓“《河》《洛》绢度”,是《河》、《洛》和星纬之义,不仅指《河》《洛》谶⑧。
《景鸾传》一条,《后汉书》原作:“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馀万言。”可知景鸾所习,《诗》、《易》、《礼》而外,尚有《河》《洛》、风角杂书、月令,则此所谓“《河》《洛》图纬”,是指《河》《洛》及其他谶纬书。
王蕃《浑天说》一条,陈文原注“《晋书·天文志》引”是错误的,《晋志》并无此语。此语乃出自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原文作:“末世之儒,多妄穿凿。补增《河》《洛》,窃作谶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氏将两两对句节引作三个单句,并将“补增”误引作“增减”,于是造成所谓“增减《河》《洛》而窃作谶纬,是谓谶纬有由《河》《洛》出者”(《河》《洛》本即谶,如此表述殊为不辞)之义,以便与河洛出谶之说牵合,以证谶、纬无别。实际上,王蕃之原文,“补增《河》《洛》,窃作谶纬”本是对句,分述两事,并没有“改造《河》《洛》以成谶纬”之义。
可见,陈文罗列的一组四条史料中,所云“《河》《洛》谶书”、“《河》《洛》纬度”、“《河》《洛》图纬”、“补增《河》《洛》,窃作谶纬”,均各有其具体含义。其中只有《东观汉记》“《河》《洛》谶书”是指《河》《洛》谶,其他三条均指《河》《洛》和其他谶纬书。这恰好说明:《河图》、《洛书》是谶类而非纬类(与今人的一般看法一致)。陈氏因为四者共同的“《河》《洛》+谶书(或纬度、图纬、谶纬)”的语辞方式(甚至有妄改原文之处),便得出《河图》《洛书》既可称谶亦可称纬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陈文史料使用不当的第二个表现是,把一段很长的材料剪裁节引,以造成前后连接互释的可能。如其引《后汉书·曹褒传》,引文原样如下(引文中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以见其删节之状):
(明)帝问:“制礼乐云何?”(褒父)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璇玑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讬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每见图书,中心恧焉。”……(章帝)章和元年……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以为百五十篇。
陈氏如此剪接原文之后,得出结论:“按诏书前引《尚书璇玑钤》及《帝命验》说,下云‘《五经》谶记之文’,是以《尚书纬》之《璇玑钤》及《帝命验》为《五经》谶记之类也。”但是,详案上段引文之全文,实包含明帝与曹充、章帝与曹褒两段不相干的故事。陈氏引文“帝善之”以前部分,讲的是明帝接受曹充建议,将太乐改为“太予乐”;而“(章帝)元和二年”之后部分,讲的是章帝敕命曹褒重新全面制订汉礼。即使要考证“《五经》谶记之文”与上述帝臣引述谶纬书之关系,也还涉及不到明帝和曹充。陈氏所以还是把明帝、曹充一段引出来,目的就是要加强其结论的可信度。此其一。其二,在章帝和曹褒的部分,在“中心恧焉”和“(章帝)章和元年”之间,陈氏省略了大段原文。这段省略掉的文字,记述章帝两下诏书倡导改定礼制;曹褒体会圣意,两次上疏,建议重定汉礼;还有章帝召问班固“改定礼制之宜”的记载。之后才是章帝“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令曹褒重定汉礼。完整阅读原文便可知道,章帝前引《河图》、《尚书璇玑钤》、《帝命验》之语,其目的(意义)仅在于为重定汉礼之行为寻找理论或思想的根据,而与重定汉礼之内容没有必然联系。不过,经过陈氏的省略剪接,就会造成《璇玑钤》等就是后文的“《五经》谶记”之错判。其三,章帝正式敕令曹褒重定汉礼的诏令,全文为:“此制(按指叔孙通《汉仪》)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陈氏省略了“此制散略,多不合经”八个关键字;又,“撰次……以为百五十篇”句,全文为:“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陈氏省略了中间说明新定汉礼之内容的文字。这两处有意的省略,都不过是要隐去“经”而突显“《五经》谶记”,以便更顺畅地把“《五经》谶记”与遥远前文的《璇玑钤》、《帝命验》牵合起来而已。
(二)陈文的结论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以偏概全
汉代确有谶、纬互辞之现象,但是基本出现在东汉中期以后。这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又经历了一段时期之后的事。也就是说,因于其时政治文化环境,经与谶、与纬不断融通,从前的明晰界限已经渐趋模糊了。东汉中期以后出现谶、纬互辞现象。并不意味着谶、纬从来都是可以互辞的⑨。陈文之例证,基本都是东汉后期至三国乃至更后时期的史料。其中属于两汉之际和东汉初年的,只关乎苏竟、薛汉、张纯三人;而这三条史料的解读,实可斟酌。先照录陈氏引文于下:
《后汉书·苏竟传》曰:善图纬。……与(刘)龚书,晓之曰:……图谶之占,众变之验。
《儒林薛汉传》曰:尤善说灾异谶纬,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
《张纯传》曰:乃案七经谶。
《后汉书·苏竟传》一条,所谓“图纬”、“图谶”究为何义?范史的叙述并不明确。考《苏竟传》,于开头简要记述苏竞“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之后,其后的主要内容就是载录苏竞《与刘龚书》全文。这封书信的核心内容,是具细分析各种星象之表征,说明其“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的谶验意义,以此劝说刘龚不当拥兵抵抗刘秀。而所谓“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云云,就是紧接在星象论析之后的话。依此推测,则此所谓“图谶之占”,最可能是指“星占”。由此回推范史之所谓“善图纬”,极可能是说苏竟擅长“星占”之学。⑩ 也就是说,《苏竟传》中所谓“图纬”、“图谶”,大抵都是指“星纬”、“星占”。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证成陈文谶等于纬的结论。因为,“纬”本有指称星辰(主要指五行星)之义,此处的“纬”并非指纬书,而是“星纬”;而星相术本来即是图谶的一个组成部分。
《儒林薛汉传》一条,“善说灾异谶纬”是指薛汉的才学,“受诏校定图谶”是说薛汉的工作,本为二事,由此并不能必然得出“纬”等同于“谶”的结论。
《张纯传》一条,所谓“七经谶”之称,根据陋见,典籍中仅此一见(11),绝无仅有,殊可奇怪。并且,“七经谶”究竟指什么,了无旁证,尚待考查。
三
以上大略揭示了迄今谶纬名义之研究的缺欠。基于此,本文认为,今天研究谶纬名义、判断谶纬同异之问题,应当充分考量以下三点:
(一)谶、纬本义为何?词义又是怎样演变的?汉代人在语言实践中如何使用它们?
这是因为,汉代人最初为文本命名(或谶或纬),一定是依照字之本义而称谓的(后来称谓混乱,是另一回事,其演变过程也很复杂,俟另文详考)。汉代人在习惯上一般如何使用这两个字,才是判断谶、纬异同的最根本而有效的依据;而不是像陈槃那样,主要依靠罗列一些经过择选和解释之后可以“互辞”的材料来做判断。
先把存世的唐前字书中有谶、纬二字之释义的材料集中于下:
《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纬,织衡丝也。…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
《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
《仓颉篇》:“谶书,《河》、《洛》书也。”(12)“谶,验也。”(13)
《三苍》:“谶,秘密书也,出河、洛。”(14)
《广雅·释诂》:“谶,证验也”;又其《释言》:“纬,横也。”
《玉篇·言部》:“谶,言也,验也”;又其《糸部》:“纬,横织丝。经,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
“谶”、“纬”二字不见于《尔雅》。由《说文》、《释名》以下之释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谶”的基本内涵是“验”(证验),而“纬”的含义从来都是与“经”相配的。即使从二者都可指谓书籍这一点来看,也是各有所指——“谶”特指“证验之书”,具体说就是“河、洛所出书”,其内容特点是“证验”、“纤微”、“秘密”,原本与经无关。“纬”则指与“经”直接相关、阐释“经”的书(所谓“反覆围绕以成经”)。至于后汉有以谶附经、以谶证经之事(15),那是当时学人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有意而为(《白虎通》即是代表),在时间上也是比较靠后的事,因而它并不能成为谶、纬本无分别的有效证据。
再看“谶”、“纬”二字在西汉(含)以前实际的使用情况。
根据陋见,“谶”字似不见于今存之先秦典籍(16),较早出处盖为汉初贾谊《鵩鸟赋》:“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这个“谶”字之义,明显是谶书、谶语;其内容也很清楚,就是征验(根据某种征象而预言未来)之类。此外,西汉时期其他典籍中有“谶”字的材料,仅见于史部数条:
(秦缪公卧病)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史记·赵世家》)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汉书·哀帝纪》)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壄。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汉书·翟方进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汉书·王莽传上》)
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汉书·王莽传下》)
这些“谶”字之含义鲜明而一致,就是征兆预言之类。与贾谊所谓“谶”,内涵完全相同。
以下是西汉(含)以前典籍中使用“纬”字的情况: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郑玄注:“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杜预注:“嫠,寡妇也。织者常苦纬少,寡妇所宜忧。”)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
《诗·大雅·皇矣》“比于文王”《毛传》:“经纬天地曰文。”(以上经部)
《国语·周语下》:“天六地五(韦昭注: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
《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之罘刻石》:“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史记·礼书》:“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
《史记·天官书》:“紫宫、房心、权衡、成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张守节《正义》:“五星行,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也。”)
《汉书·律历志上》:“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又:“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又:“三辰之合于三统……五星之合于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
《汉书·律历志下》:“土、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是为镇星小周。”
《汉书·礼乐志》载《安世房中歌》第二章:“清思呦呦,经纬冥冥。”(颜师古注:“经纬,谓经纬天地。”)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惟泰元》:“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
《汉书·五行志上》:“《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引京房《易传》:“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纬。”(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有所破坏,绝匹帛之属也。”又引晋灼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丝因风暴乱不端理也。”)
《汉书·李寻传》:“五经六纬(按均指星宿,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尊术显士。”
《汉书·扬雄传》载《法言》序目:“神心曶怳,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谊、礼。譔《问神》第五。”
《汉书·王莽传》载元始五年诏策:“钦承神祗,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以上史部)
《管子·五行》:“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曰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
《庄子·寓言》:“(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成玄英《疏》:“上下为经,傍通曰纬。”)
《荀子·劝学》:“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荀子·解蔽》:“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
《淮南子·地形训》:“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
《淮南子·要略》:“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
《说苑,正谏》:“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纬以成帷幕。”
《太玄·玄测序》:“经则有南有北,纬则有西有东。”
《太玄·应》:“一从一横,经纬陈也。”
《太玄·玄莹》:“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经纬交错,邪正以分。”又:“立天之经曰阴与阳,形地之纬曰从与横。……阴阳曰合其判,从横曰纬其经。……阳不阴无与合其施,经不纬无以成其谊。”(以上子部)
《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王逸注:“纬繣,乖戾也。”《玉篇·糸部》:“繣,乖戾也。”宋·钱杲之《离骚集传》:“纬,织丝也。繣,结碍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纬繣,如纬丝之繣结,乖戾不就绪也。”)(以上集部)
从以上粗略检索的史料看,西汉以前的“纬”字使用,其含义有:“织物的横线”——这是本义;“组织(治理)”、“伦理”、“星宿”、“地理方向上的东西向”——这是衍生义。明显可见,在西汉(含)以前的语言应用中,“谶”和“纬”之义涵不同,界域分明。一直到汉末曹魏时期,“纬”字的常见含义仍大抵如此:
《周礼·春官·龟人》郑玄注:“东龟、南龟长前后,在阳,象经也;西龟、北龟长左右,在阴,象纬也。”
《礼记·间传》郑玄注:“黑经白纬曰纤。”
《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星谓五纬,辰谓日月。”
荀悦《申鉴·政体》:“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
孔融《喻邴原书》:“国之将陨,嫠不恤纬;家之将亡,缇萦跋涉。”
曹植《文帝诔》:“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吁嗟,万国悲伤。”
徐幹《中论·务本》:“择善而从曰比,经纬天地曰文。”
嵇康《声无哀乐论》:“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
与此同时,东汉后期,“纬”字的含义也明显有了新的拓展。如:
蔡邕《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妙旨。居则玩其辞,动则察其变。云物不显,必考其占。故能独见前识,以先神意。”
荀悦《申鉴·俗嫌》:“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
郑玄《起废疾》:“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
《郑志》卷中:“张逸问:《礼注》曰‘书说’,书说,何书也?答曰:《尚书纬》也。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
《李子材铭》在“游心典谟”之下以“七经”与“群纬”对称,则“纬”当指书籍;续以“察其变”、“考其占”、“见前识以先神意”云云,则“纬”之所指当是谶验一类书籍。《申鉴·俗嫌》径称“纬书”,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纬书”称谓。郑玄答张逸问,直呼“尚书纬”,且郑注《三礼》多引“《孝经说》”、“《易说》”等等,依此答问,则都是“图谶”之书;其《起废疾》更说纬书乃孔子所作,以高尚其价值。凡此种种,都可证东汉后期用“纬”称呼谶书,已经比较流行了。
(二)从历史维度考量经、谶、纬三者的演变纠结关系,是理解谶、纬名义的枢纽
根据上文对西汉以前“谶”、“纬”之字源、字用的粗略考察,谶、纬之内涵及其与经的原本关系,已经略显端倪:谶自谶,纬自纬;纬以解经,谶与经本无关联。谶、纬与经三者开始纠结混淆,乃是东汉(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事。
而无论是“有别”论者,还是“无别”论者,都缺乏历时的翔实具体的考察。即使那些持论比较平实客观的学者,也莫不表现出历史思维的缺失。如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
纬含广狭二义。纬书之广义的解释,是泛指当时所产生的一切讲术数占验的书而言,所以每每将“谶”、“图”、“候”等字与“纬”字配合而成为“谶纬”、“图纬”、“纬候”等名词。纬书之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七纬”而言。……谶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谶”是和广义的“纬”一样地泛指当时一切讲术数占验的文字。但非文字的口说,如《史记·秦本纪》所载的“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也可以称为谶。……至于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当时所谓“河图”、“洛书”而言。(《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此说较之各执一词的“有别”、“无别”论者,显得比较平妥。但仍是以论代史,说法并不清晰准确。更为谨慎稳妥的结论,是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解说·关于〈河图〉、〈洛书〉》之说:
从总体上看纬书,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谶类和纬类二类。所谓谶类,即预言未来书的一类,在纬书中大半指天文占之类,同时也包括例如古帝王传说之类的史事谶。纬类则与此不同,它是解释经文的一类,《七经》纬即属此类。但是依据这种分类,两类条数就依各纬的不同而相异,不仅《河图》、《洛书》中有相当于纬类者,同时《七经》纬中也有许多天文占之类。从纬书整体看,可以说两类的条数大略各占一半。由于纬书本来具有预言书的性质,因此谶类占的分量可能稍微多一点。……这样形成的谶类和纬类,很难说从开始就被冠之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纬书名,而且它作为纬书被冠以纬书名,又作为纬书被整理,都可能是西汉末以后的事情。……纬书得到某种程度的整理,并具备了纬书的形式,大概是在东汉的郗萌时。《隋书·经籍志》在纬书的后序中记:“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17),谓之《春秋灾异》。”被称为《春秋灾异》的纬,仍有一些疑点,但至少说明在整理纬书的当时,是将谶类包括在内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安居、中村将所有谶纬遗文区分为“谶类”、“纬类”而不论其篇名为何,并且怀疑今存的篇名乃是后人整理谶纬时所加,可能更为客观而接近于实际。但他们同样是只做静态的理性分析,而不论谶、纬之历史演变,还是未能彻察真相。
有鉴于此,今天探讨谶、纬名义及其性质之问题,尤应突出历史维度,弄清楚谶、纬之本然状态及其发展演变情状,才可能接近实情。
(三)以存世谶纬佚文为依据来讨论谶、纬名义,不一定能够获得准确结论
上文已经谈及,存世谶纬佚文零散错乱而游移不定,难以呈现汉代谶、纬文献的原貌。如果完全根据谶纬佚文来研判汉代谶纬的名义、性质和状态,可能不会得到准确的认识。
比较而言,更值得信任的是《隋书·经籍志》和《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所记录的谶纬书目。尽管陈槃对这两份书目有所怀疑(18),但是作为今天可见最早的明确的谶纬书目,还是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陈氏所以不相信初唐史臣的书目,乃由于他主张谶纬无别,这两份书目不能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直接而可靠有效的证据说明这两份书目有问题,仅凭推论来做出判断,还是不足以否定其可靠性。初唐史臣辑录书目,必有根据,定非妄为。后人如果根据需要(而不是有效可靠的证据)而随意怀疑古代典籍(尤其是史志这样的典籍)的可靠性,那就不是严谨科学的态度,今天的研究也便无法开展。
《隋志》和李贤的两份书目,虽然其范围大小、书目多寡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所谓“七纬”,均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这七种经典之纬。第二,谶、纬本来有别。而这两个基点,是今天研究谶纬所应坚持的。
本文认为,谶、纬“有别”还是“无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的。泛泛谈论有别、无别,企图以一种观点概括谶、纬之名义,是永远都会缠夹不清的。谶、纬本来的状貌,就是“谶自谶,纬自纬”。谶起源甚早,根据它“神秘应验”的非理性的基本特性看,即使像刘师培《谶纬论》所说“起源太古”也并不为过(只是刘氏并未区分谶与纬);而纬则必然产生在经之后,无论其内容在今天看来多么不合科学不合逻辑,它在最初都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对经的理性阐释和发挥。所以,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的看法,可能最接近实际:
盖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论语》、《孝经》而外,无复别出。……若谶之依附《六经》者,惟《论语》有谶八卷,馀皆别自为书,与纬体制迥别。……窃意纬书当起于西京之季,而图谶则自古有之。……要之,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后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于经义。(《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二,中国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印行《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
经、谶、纬三者原本各具义域,至于后来走向混融纠结,乃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择其要者概说如下:
第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文化传统,是谶、纬与经学交融的思想基础。学人往往会把阴阳五行思想归结到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实际上,此种思想的起源和基本成型要远早于此。仅从儒家经典而言,《周易》古经的核心理念便是阴阳,《尚书·洪范》是五行思想的最早最系统阐释,《左传》、《国语》中记录比较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之实例非止一端。阴阳五行实际是我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原型”思想之一。阴阳五行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天人之学,带有神秘和预示的性质。正是由于神秘和预言特性,它便成为不同人群因于各种利益需要而经常使用的思想,因此也具有了极强的实用价值,历代久盛不衰。汉代兴盛的儒学,本来与阴阳五行思想就具有水乳关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评述儒家,即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之语。学人研究儒家,往往更多关注其“明教化”一面,而忽视其“顺阴阳”一面,是偏颇的。谶纬之学,与阴阳五行、与儒学交融,有着深刻的学理上的渊源。
第二,汉武帝之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话语权,先秦以来的图谶之学若想生存并获得一定地位,就必须与儒学牵合,并为政治所用,此乃必然之趋势。不言而喻,此种思想的转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期即有作为预言的谶语流行。这类预言谶语,本甚粗陋而神秘。其后经过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融合,拥有了比较明确的学理内涵,成为“符命”一类谶语,为当权者所重视。汉代以后,更受到今文经学的强力制约,逐步与经学融合,谶与经、纬便纠结在一起了。
第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新儒学思想的极大成功,加速了谶、纬与经学的交融。四库馆臣说“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以今天残存的《春秋繁露》核之,此说其实不无道理。卢文弨曾云:“此书(指《春秋繁露》)之大旨在乎仁义,仁义本乎阴阳。”(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附录《春秋繁露考证》之《四库馆(奏进书后)》卢氏案语)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乃是董仲舒的思想基础和核心,也是现当代学人的共识。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例言》指出“西汉书有两体”,一为“注经体”,一为“说经体”。《春秋繁露》属于后者,是“依经以旉义”的著作。因此,无论其思想之因缘,还是其著述之方式,都与谶纬书有思理相通之处。只不过,后世谶、纬纠结,又零散无统,后世学者已经很难把《春秋繁露》和征验预言为主要特征的谶纬书联系起来了。而从历史思想演变的角度看,宣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董子思想的集大成功,无疑会加速谶、纬、经的融合进程。
第四,谶语预言在两汉之际的政权更替中,发挥了实际而有效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它巨大的现实力量。正缘乎此,王莽才于始建国元年(9)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中》),刘秀也于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刘秀对图谶的态度。作为开创刘汉王朝中兴局面的帝王,他使图谶之学按照自己的意志定型,并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化。在此种情势下,谶、纬与经融合,实为必然之趋势。
注释:
① 历代学者论谶纬名义之史料甚夥,可于下列三书了解其梗概:(一)姜忠奎:《纬史论微》卷第一,黄曙辉、印晓峰据1935年石印本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二)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中国台湾编译馆,1991年;(三)钟肇鹏:《谶纬论略·谶纬的起源和形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谶、纬无别”之观点,可以陈槃两篇论文《谶纬释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4年)、《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同上第二十一本第一分,1948年)为代表。
③ 顾颉刚说:“(谶和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汉代学术史略·谶纬的造作》,东方出版社,1996年)陈槃也以为“谶纬之类,先有《河图》《洛书》,然后有由此而出之谶,然后始有纬。”这样叙述恐怕导致谶、纬相分别,故紧接着又说:“但名义虽有先后之不同,而实质则一而已矣。”(《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谶纬先后说》)既已先后别之,复以异名冠之,何以“没有分别”、“实质则一”?因为缺乏历史考察,终不能令人释疑。
④ 参见拙著《西汉文学思想史》第二章第二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参见拙文《谶纬文献及其辑佚问题例说》,文载《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
⑥ 《太平御览》卷五三六引录司马彪《续汉书》:“《河图会昌符》云:‘汉大兴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功。’”
⑦ 见[宋]洪适《隶释》卷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明]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三二《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四三《石刻文字十九·太尉杨震碑》(以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同。
⑧ 按:说杨震“明《河》《洛》纬度”,仅见于《杨震碑》。其他史籍如《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资治通鉴》等,均只载其家传、师传《欧阳尚书》,不曾说他还擅长“《河》《洛》纬度”。并且,《后汉书》等史籍传杨震,都说他“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当世儒者称为“关西孔子”;淡泊名利,数十年不应征辟,五十岁之后才入仕;在朝期间,虽遍任三公,但廉洁不谋私利,多次上疏批评外戚内宠,引据《书》、《诗》、《春秋》、《易》、《论语》这样纯正的经典,而完全不见他引用谶纬书。凡此种种,均可表明:杨震乃是一个醇儒。《杨震碑》“明《河》《洛》纬度”之说,甚可奇怪。
⑨ 关于汉代谶、纬之分合纠结状况,作者另撰《汉代谶、纬分合演变考》一文专论。
⑩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条:“苏竞、杨厚、郎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规切时政也。”可为旁证。
(11) 其后《通志》卷一○八,《玉海》卷六三、卷九五、卷一一一,《册府元龟》卷五六三,《渊鉴类函》卷一六○均有“七经谶”之称,但都是引述《后汉书·张纯传》。
(12) 《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引。
(13) [清]顾震福辑:《小学钩沈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01册。
(14) [清]任大椿辑、[清]王念孙校正:《小学钩沈》,《续修四库全书》第201册。
(15) 参见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论谶亦附经》所举出的材料。
(16) 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卷二、冯惟讷《古诗纪》卷四、梅鼎祚《古乐苑》卷三○均引录传为帝舜所作之《南风操》,中有句“有黄龙兮自出于河,负书图兮委蛇罗沙,案图观谶兮闵天嗟嗟,击石拊韶兮沦幽洞微”云云(三书文字略异)。此作乃后人伪造,不足为据。
(17) 郗萌,《后汉书》无传。据《晋书·天文志上》“《宣夜之书》云: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及《隋书·经籍志·子部》“梁有《秦灾异》一卷,后汉中郎郗萌撰”,可知郗萌当是东汉的星象灾异学者。然其具体的生活年代不明,《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依此,则郗萌当活动于东汉前期;而此处所引《隋志》则云“汉末”。或以为班固所说,当为另一郗萌。
(18) 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谶纬互辞考》:“以三十六篇为纬,《隋志》以前,未有闻焉。三十六纬之篇目,李贤以前,亦未有闻焉。……《隋志》以下,以三十六篇为七纬非谶之说,实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