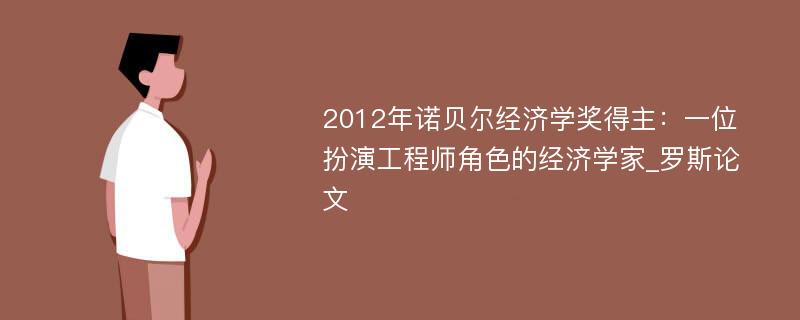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扮演工程师角色的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主论文,经济学家论文,角色论文,工程师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伊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又译沙普利)和埃尔文·罗斯(Alvin E.Roth)是谁?这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很多人的疑惑。的确,对国内经济学爱好者及学生来说,这两人有些冷门,不是大众所追逐的学术明星。
相较而言,夏普利还算有名,因为“夏普利值”(the Shapley value)是众多博弈论爱好者和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夏普利作为博弈论(尤其是合作博弈)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出现在博弈论教材中。但就罗斯而言,除了少数实验经济学爱好者,国内很少有人知晓。人们更多地看重观点(即思想),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一看到数学符号,立马就跳过去,更别说那些严谨的证明和设计了。从而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观点的辩论,而不是证据和逻辑的交锋。这看似刺激,但实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罗斯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家要试图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仅在意念上帮助社会,在媒体上耍嘴皮子,更重要的是设计出能够改进人们福利的机制。
罗斯和夏普利:博弈论的缘分
夏普利获奖,一点也不意外。早在纳什获奖之前,呼声更高的就是夏普利。在纳什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同时,夏普利于1953年发表了著名论文《n人博弈的值》,奠定了合作博弈的基石。他解决了合作博弈的一个关键难题,即“夏普利值”。有了这个解,合作博弈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建模。然而,合作博弈的确存在一个弱点,就是必须得有个保证协议落实的超然机构。
与夏普利相比,罗斯的学术生涯比较普通,而且罗斯也没有像夏普利那样有很高的获奖呼声。但罗斯完成了一个经济学家帮助社会改进自身不足的任务。这种参与是直接介入机制设计之中,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运行系统。
夏普利的思想被罗斯所挖掘,罗斯看重其在研究分配方面的巨大潜力。合作博弈中,之所以协议难以达成和实施,皆因利益分配之困难。利益分配不均,大概是所有合作无法成立的关键。要解决合作的稳定性问题,利益分配必须公正。“夏普利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核心点在于,事后的利益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前的禀赋,还要看事中的贡献,即每个人所得,取决于各自对联盟的边际贡献。但夏普利只是给出证明,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20世纪70年代,罗斯发表了两篇论文,开始探索“夏普利值”的应用,比如在公共工程建设中,如何让各利益方分摊成本。正是这种对“夏普利值”的大胆应用,使合作博弈得以焕发生机。
罗斯为了让夏普利的思想更生动地展示出来,开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设计符合谈判博弈要求的程序,并邀请志愿者参与游戏。罗斯设计出一个双彩票的博弈游戏。这个游戏中两类彩票分别代表大奖和小奖,游戏参与人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获得大奖,也可能获得小奖。结果显示,协议均值落在等概率协议点(各50%)和等期望价值协议点(75%和25%)中间,即参与人期望货币收益相等。这就意味着公平成了博弈的一个聚点。这个公平分配的聚点如何形成?罗斯发现其中涉及几个主要因素:信息是否成为共同知识、参与人的风险偏好分布、预期和声誉、时间因素等。
这种研究有意义吗?假如三个人分一个蛋糕,无论按照纳什的理论预测,还是按照夏普利的理论预测,其结果都可能是趋近公平的分配。而问题在于,按照纳什的思路,这个公平分配来自每个人的策略,即每个人虽心怀鬼胎,却最终达成了一个公平分配方案。这有点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按照夏普利的思路,三个人之间可能会出现两两结盟,甚至三人合作达成公平分配协议,从而实现一个公平分配结果。其中,纳什和夏普利都忽略的关键问题是,公平分配结果很可能来自某种社会规范的影响。罗斯称之为信息的共同知识,即参与人相互都知道自己和彼此的行为规范,从而可能达成某种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合作博弈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后来为费尔(Fehr)等人进一步发挥,指出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有限理性的人,这种参与人理智和情感并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偏好。这才是社会中不同个体以及群体之间能够形成合作的关键。当然,这是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市场设计:社会工程师的意义
罗斯和夏普利的缘分,在另一个舞台上缔结得更深,那就是市场设计。在1962年,夏普利和戴维·盖尔在《美国数学月报》上发表《高校招生和婚姻的稳定性》一文。他们观察到,美国学校招生过程中,存在一些资源浪费现象。假如有两个大学,甲和乙;有两个申请的学生张三和李四。张三喜欢甲,李四喜欢乙。有效的资源配置是张三读甲大学,李四读乙大学。问题是大学录取采取优先接受程序,张三觉得自己有优势,同时申请了甲和乙,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甲和乙都给张三发了录取通知;李四申请了乙,同时申请了一个其他国家的丙大学保底,乙给李四发了等待通知,但丙给李四发了录取通知。那么李四是等待还是去读丙大学?显然,如果张三一直拖着不决定,李四就不得不选择丙大学,最后乙大学无法录取李四。从大学和申请人的角度看,都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夏普利和盖尔发明了一种递延接受程序(the deferred acceptance procedure),这种程序要求张三和李四都填报甲和乙,但必须给自己的偏好排序,这样张三申请时就表明了甲、乙顺序,李四表明了乙、甲顺序。甲按照这种程序,只考虑最偏好自己的,仅录取张三,乙则录取李四。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
罗斯决定运用递延接受程序,重新设计美国医师劳动市场。1999年,他和皮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美国医师匹配市场的重新设计》一文。这一成果改变了美国医师的就业状况,大大提高了这类劳动市场的配置效率。
美国各医院为了争夺优秀学生,经常采取不正当竞争,导致劳动市场混乱。后来建立了美国国家住院医师选拔计划(National Resident Match Program,NRMP),该计划每年公布全美各医疗机构的医师需求数量和岗位,学生向该计划提出申请,并完成与医院岗位的匹配。但这个计划有两个弱点,一是与高校录取的资源浪费类似,采取优先验收程序,同样会导致这类问题;二是无法解决学生夫妻的申请难题。对此,罗斯等人基于递延接受程序,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资源浪费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夫妻的难题。该计划依赖一个集中的登记结算中心(清算屋),学生向该中心提出申请,但必须标明偏好序,中心把偏好序信息传入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按照最偏好原则选实习医师;如果没有选满,那么就依次选第二偏好的学生,如此类推,直到供求至匹配位置。罗斯这个新计划的推行,大大改变了美国住院医师的就业状况。
罗斯和凯格尔合作,专门比较分析了递延接受市场机制和优先匹配机制的有效性,发现前者明显稳定。他们还找到了相关的证据,比如在英国,爱丁堡和卡迪夫采用了前者,伯明翰、纽卡斯尔和谢菲尔德采用后者,但前者取得了成功,后者则没有。
罗斯把这种市场设计思路运用到很多其他领域,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以肾脏捐赠为例。假如有甲、乙、丙三个家庭,各自亲人愿意为家里的患者捐赠肾脏,但都存在排异性,无法实现捐赠,怎么办?罗斯发明了一个基于递延接受程序的机制,称作“首位交易循环链”(Top Trading Cycles and Chains,TTCC)机制,可以让三个家庭各自进行交换,这样就实现了匹配。这个匹配同样通过一个登记结算中心来实现,大大提高了肾脏移植的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结算中心按照等级将患者和捐赠者排序,患者按紧急程度排,捐赠者按匹配程度排,最急需的患者寻找最匹配的捐赠者,一旦配对成功,就剔除,然后依次继续,最后所有患者都与各自的捐赠者配对成功。显然,这种市场机制比家庭和医院各自单独搜寻的效果要好很多。
经济学家能否成为工程师
2002年,罗斯写了一篇论文《经济学家作为工程师:博弈论、实验和计算机作为设计经济学的工具》,发表在《计量经济学》第70卷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总结了迄今经济学家参与市场设计的几个重要案例,并阐述了这一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原理。这篇文章可能使一些人不禁又回到早年攻击贝克尔的老问题上:经济学又帝国主义了吗?其实不然。
罗斯既不是兰格的计算机乌托邦的追随者,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罗斯所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都基于市场非有效这一前提。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任凭“看不见的手”兴风作浪,很可能无法实现应有的效率。基于此,经济学家有责任介入市场之中,真正认识市场的不足,然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试图改进市场的运行机制,从而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
罗斯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脚踏实地,做一些对市场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纸上谈兵。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只手可以是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某种组织;社会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的,因为我们的理性都有限,所以只能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活动中,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大概就是罗斯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