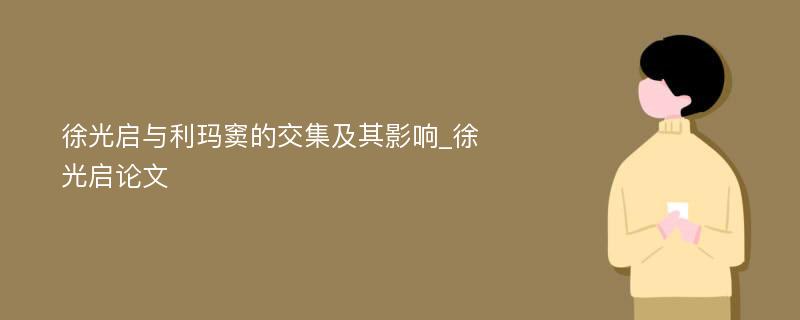
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游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玛窦论文,徐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5-0071-10
徐光启是明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是晚明诡谲多变政局中的要角,而且还由于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具有多方面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尤令人惊叹和不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大官僚、大文人和大科学家,居然也同样是一个信仰十分虔诚、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献身于上帝的基督徒。我们认为,这应与其长时间地与来华欧洲教士接触和交往有重要关系。据考,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识郭居静始,至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病逝,其间近40年,与其接触交往的欧西教士多达20余人。其中有多人与其朝夕相处,交往甚深,如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等。①而利玛窦则是诸人之中交往最深者,也是对徐氏一生影响最大的欧洲人。以往有诸多中西前辈学者和当下时贤对徐、利之交往进行过较深的探讨。中国学者如徐宗泽、席泽宗、方豪、罗光、梁家勉、胡道静、朱维铮、郭熹微、古伟瀛、李天纲等,国外学者则有裴德生、谢和耐(Jacques Gemet)、邓恩(George H.Dunne)、卜正民(Timothy Brook)、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余蓓荷(Monica Ubelhor)、Gregory Blue、Joseph de la Serviere及日人安部力等。徐秋鑫先生和孙尚杨先生甚至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及《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专书研究。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已具备深度。然我们手头仍有几份中西文献资料,上述研究并无采撷,故史实尚有缺憾。因此,本文拟系统钩沉徐光启与利玛窦西学交游之实况,并借此分析西学交游对于徐光启完成身份角色转变、构建西学知识体系、深化神学修养体验以及形成相关著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疏漏与外行之处,尚望方家批评。
一、徐、利二人之交往
(一)相闻与相见(1599-1603)
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光启首次听闻利玛窦之名。据晚清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述:徐光启“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②。而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则称:
昔游岭嵩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③
正如徐光启自述,其首次接触西学,乃1595年客居岭南时瞻仰天主圣像一事。至于真正知晓西人利玛窦,待到“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之后。检视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早期刊刻、流转、收藏过程可知,自1584年至1600年约有四种版本。一为1584年肇庆知府王泮之肇庆刊印本;二为1595-1598年间应天巡抚赵可怀苏州摹刻本;三为1599年改任湖广参政王泮之南京修订本;四即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南京刻印本。其中第一、三种主要流转于达官贵人、文人士子的私相授受中,第二、四种流播较为广泛。④徐光启很难识见肇庆刊印本及南京修订本,而相对容易看到流转广泛的第二、四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因是之故,徐坦言“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由此可知,萧若瑟所谓“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当为赏析赵可怀版世界地图一事。至1600年再次寓目吴中明版舆图,前后已然两次闻听利玛窦之名了。
至于萧若瑟所谓“南京问道”,时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据晚明来华教士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禅学、玄学及三教等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事,竟无着落,心终不安。万历庚子,至南都见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梦,如见圆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盖天主预启以三位一体、降生妙义。⑤
其时西人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亦称:
庚子(1600),再入南都,知利玛窦先生来自大西,传天主教,因往候,略闻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⑥
此事在利玛窦1605年的信中也有记录:
他(徐光启)曾向我说,他在南京和我会面,仅仅听见我讲恭敬唯一的天主,他回家忽然得一梦。梦中看见一座大庙,其中有三间小圣堂,在第一圣堂中间有一老人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父,在第二间圣堂中又见一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子。在第三间圣堂中,则无所见。⑦
李杕《徐文定公行实》:
庚子抵白下,遇利子玛窦。……逮闻利子言天地有主宰,万物不能生。人间祸福,皆一主宰掌握。人负气以活,具形体,秉灵性,形必归灰,而灵性永无泯灭。善其生则获祜,恶其生则罹殃,失毫谬千,攸关重要。公恍然,为之低徊久之。⑧
这一次见面时间不长,应该是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南京寓所获聆利氏讲道,但对徐氏影响不小。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再次来到南京,想拜谒利玛窦。《徐文定公行实》称:“秋,复至石城,因与利子有旧,往访不遇。”⑨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亦载:
癸卯(1603),(徐光启)瞻拜天主像。因以利子刚译《实义》及《教要》诸书送阅。公持归邸舍,彻夜不寐,读之,欣喜不已。⑩
按《实义》为《天主实义》,《教要》为《天主教要》,均为利玛窦新译之书。这一次拜访,虽未见利氏之面,但获利氏之书,对徐光启产生更大影响。
(二)入京后徐、利交往日密(1604-1605)
万历三十一年冬,徐光启入京参加会试,第二次见到利玛窦。
癸卯冬,则吴下徐太史先生来。太史既自精心,长于文笔,与旅人辈(指传教士)交游颇久,私计得与对译。于时以计偕至,及春荐南宫,选为庶常,然方读中秘书,时得晤言,多咨论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未遑此土苴之业也。(11)
癸卯冬,即万历三十一年冬,徐光启具体进京的时间应是1603年年底或1604年1月间。徐光启到达北京后,与利玛窦交往颇多。柏应理《徐光启行略》称:
赴京会试,即登甲榜,入翰林。其时利子在都城,构堂行教。公虽备员讲幄,时获朝廷顾问,必且日与弥撒,未尝间缺。(12)
可以看出,徐氏进京后与利玛窦的交往更加紧密。故《徐文定公行实》称:“公馆京邸,与利子交益密。”(13)为了方便与利玛窦交往,徐光启还在利的“住宅附近租一房屋”(14)居住读书,以便于向利玛窦请教。徐氏《跋〈二十五言〉》云:
余亦以间从游请益,获闻大旨也,则余向所叹服者,是乃糟粕煨烬,又是糟粕煨烬之万分之一耳。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诸凡情感诱慕,即无论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绝不萌诸其心,务期扫除净洁,以求所谓体受归全者。间尝反复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盖是其书传中所无有而教法中所大诫也。启生平善疑,至是若披云然,了无可疑;时亦能作解,至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请事焉。间请其所译书数种,受而卒业,其从国中携来诸经书盈箧,未及译,不可得读也。(15)
此跋语作于万历三十二年冬至日,西历为1604年12月21日,徐光启在北京留居已近一年。据茅元仪《与徐玄扈赞善书》称:“徐光启每布衣徒步,晤于(利氏)邸舍,讲究静谧,承问冲虚。”(16)当时利玛窦“赍贡入燕,居礼宾之馆”。按利玛窦当北京后,初居四夷馆,后赐宅于京城西南宣武门内之东,继建教堂于其宅左。(17)《利玛窦中国札记》记徐光启到达北京后,“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18)。利玛窦1605年的信亦称:“他常来望弥撒,办告解,领圣体。”(19)由《跋〈二十五言〉》语知,徐氏先向利玛窦“从游请益,获闻大旨”,认为“其学无所不窥”。但徐光启毕竟粗通天学,理解不深,加之“生平善疑”,故而“反复送难”,最终“了无可疑”、“服膺请事”,并“请其所译书数种,受而卒业”。即与利玛窦的交游,最终促使徐光启服膺西学,而其本身的西学修养也渐趋深化。可徐光启因读哪些译著“受而卒业”呢?经查,利玛窦此前所译书皆为《西国记法》、《交友论》、《天主实义》、《四元行论》、《二十五言》等数种哲学、伦理学书籍,故此时徐氏所读译书盖为前述书。但正如跋语所言“诸经书盈箧,未及译,不可得读也”,有关神学著述,徐光启不可能多有涉猎,故才会出现反复问难“其书传中所无有而教法中所大诫”之事发生。总之,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二年这一年中,通过与利玛窦的交游,终于信服西学,捐弃“向所叹服”。徐光启虽未明言其向所叹服是什么,但可知为传统士大夫所好之儒释之类,甚至认为“向所叹服是乃糟粕煨烬,又是糟粕煨烬之万分之一耳”,故知此时徐光启这一次与利氏之交游,对徐光启为学改变影响之大。故徐光启十分推重利玛窦于西学东传的功绩。其《景教堂碑记》言:
我中国之知有天主也,自利子玛窦之来宾始也。其以像设经典入献大廷,赐食大官,与士大夫交酬问答,因而传播其书,兴起有众也,自万历庚子利子之入都门始也。其庄严祠宇,崇奉圣像,使闻风企踵者瞻仰依归也,自万历辛亥利子之赐茔授室始也。利子以九万里孤踪,结知明主,以微言至论,倡秉彝之好,海内实脩之士波荡从之。(20)
徐光启认为利玛窦等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妙者”(21)。
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光启在京期间还是不断地向利玛窦学习。1605年5月10日利玛窦致高斯塔神父书云:
他把从我们这里所听见的好事和有益的事,或是关于圣教道理,或是关于西方科学,凡可以加重我们声誉的,他都笔录下来,预备编辑成书,他已经开始听我们讲授逻辑学和几何学,但他不能继续听讲,因为不愿意耽误他再升一级。(22)
则1604年徐光启多读《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等哲学、伦理学译著,而1605年徐光启已转向学习圣教道理和西方科学之书,前后已略有差异。徐光启其时也认为“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23)。以利玛窦致高斯塔神父信比对,可知徐光启的西学认识已渐次转移,即由西人“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之至大者,转入象数之学,即“先生(按即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24)。
(三)合作译书(1606-1607)
由于徐光启在学习西学方面的成绩及与利玛窦之间的密切关系,故双方决定合作翻译西书,首选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撰于1607年的《译几何原本引》述此事甚详:
客秋,乃询西庠举业,余以格物实义应。及谈几何家之说,余为述此书之精,且陈翻译之难,及向来中缀状。先生曰: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耳。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先生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先生勤,余不敢承以怠,迄今春首,其最要者前六卷,获卒业矣。(25)
利玛窦1608年3月6日在北京的信称:
(去年),这位绅士(徐光启)和我一起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译成中文。……徐进士还为这部书撰写了一篇文辞典雅的序文,由他亲手书写刻本付印。(26)
利玛窦还称:
徐保禄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来他学到的一切东西。一年之内,他们就用清晰而优美中文体裁出版一套很像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27)
“客秋”,指的是万历三十四年秋,为1606年7-9月;“春首”则是指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即1607年2-3月。如满打满算的话,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译的二人合作方式前后持续了8个多月的时间。翻译6卷《几何原本》,如此大的工作量,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得以完成,一方面反映了利玛窦本身的中文能力很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徐、利二人工作之勤奋及配合之密切。
《几何原本》译出之后,利、徐又合作翻译《测量法义》一书,也是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徐光启《题测量法义》:
西泰子(利玛窦)之译测量诸法也,十年矣。法而系之义也,自岁丁未始也。曷待乎?于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28)
丁未,即1607年。可知《测量法义》应是在译完《几何原本》后于当年又翻译了这本书。
这一段时间,由口授笔译之缘故,徐、利二人基本上应该是天天都在一起,所谓“朝夕相处,殆无虚日”(29),即应指此者。而这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使徐光启在西学的学习上获得更大的提高,即李杕所言:“问道之余,讲求西法。利子口译,公则笔之。天文、地理、形性、水利诸学,罔不探究。而推算历学,尤加意焉。”(30)
二、徐光启在西学方面受利玛窦之影响
由于利玛窦对徐光启的倚重及与徐光启其人西学交游的深入,徐光启受利玛窦西学方面的影响也日趋多元。所谓科学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主要体现在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筑造铳台等诸层面。
第一,利玛窦对徐光启的影响,首先集中于地理学、天文学知识上。《利玛窦中国札记》称:
利玛窦神父开始时是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他最初教的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固执地维护从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错误的人,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31)
徐光启也是如此,他因“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32)。赵可怀、吴中明所刻世界地图两次冲击着徐光启的精神世界(33),这至少应为徐光启“南京问道”的重要起因。其《致友书》:
西泰诸书,致多奇妙,如天文一节,是其最精要者,而翻译之功,计非岁月不可。用是未暇,以待他日图之耳。(34)
1605年,徐光启作《题万国二圜图序》,认同利玛窦所说“天地圆体”说,以为“西泰子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35)。可见此时徐光启已完全接受西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徐光启由于受利玛窦影响,“天文、地理……罔不探究”(36)。崇祯四年(1631)、崇祯五年(1632)他向皇帝进呈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两卷和星座图表一张,这两卷书及星座图表就是汤若望、罗雅谷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37)崇祯六年(1633),作《赤道南北两总呈图叙》称:“今予独依西儒汤先生法,为图四种,一曰《见界星总图》,一曰《赤道两总星图》,一曰《黄道两总星图》,一曰《黄道二十分星图》,业已进上,公之海寓,似无遗义。”(38)据利玛窦笔记,《浑盖通宪图说》这部实用天文学书是李之藻和徐光启两人合撰。但据该书之李之藻序,是书应是由李之藻个人完成。梁家勉先生认为徐光启可能参与了是书的商订。(39)这些均可反映徐光启在学习西方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阮元《畴人传》称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推崇,尽得其术”,又称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40)这无疑与利玛窦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联。
第二,徐光启曾向利玛窦学习几何及测量之术,因而翻译《几何原本》,作《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其《刻几何原本序》称: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传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以故极精其说,而与不佞游久,讲谭余晷时时相及之,因请其象数诸书,更以华文,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遂共翻其要,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41)
1605年5月10日利玛窦致高斯塔神父书言徐光启开始学习逻辑学和几何学,但因怕耽误升级,故中有所挫。(42)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后,为明《几何原本》之用,遂于1607年译著《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以解释《几何原本》,而其意义也在于水利等实用,其《测量法义》序:
西泰子之译测量诸法也,十年矣,法而系之义也。……数易见也,小数易解也,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利巨,为急务也,故先之。(43)
其目的在于“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利巨”,体现徐光启注重应用几何学。《勾股义》序亦如是:
自余从西泰子译得《测量法义》,不揣复作勾股诸义,即此法底里洞然,于以通变施用,如伐材于林、挹水于泽,若思而在,当为之抚掌一快已。方今历象之学,或岁月可缓,纷论众务,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然而欲寻禹绩,恐此法终不可废也。(44)
徐光启从利氏学习几何学后,“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盖精于几何,得之有本”(45)。
第三,徐光启之西方水利知识,应初得自于利玛窦。前述徐光启的几何学和测量知识已略言几何与测量的大用在于治水、治田。《泰西水法》序亦曰:
昔与利先生游,尝为我言:“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深明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焉者,何也?身被主上礼遇隆恩,思得当以报。顾已久谢人间事矣,筋力之用无所可效。有所闻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私愿以此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特恐羁旅孤踪,有言不信耳。”余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骤闻若言则唐子之见故人也,就而请益,辄为余说其大指,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畴昔所及。值余衔恤归言别,则以其友熊先生来谓余:“昨所言水法不获竟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讫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多募巧工,从受其法,器成,既又人人亟赏之。余因笔记其说,实不文,抑六载成言。亦以此竟利先生之志也。(46)
很明显,翻译《泰西水法》是利玛窦最先提出的。徐光启受其影响,原准备同利氏合作翻译,但由于利氏去世,遂与熊三拔合作完成。曹于忭《泰西水法序》亦称:
太史玄扈徐公轸念民隐,举凡农事之可兴,靡不採萝。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修共共终厥志,而器械成于熊君有纲。
郑以伟序亦称:“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先生之志而传之者也。”(47)
柏应理《徐光启行略》称徐光启同偕利子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详究星象、历数等书。(48)此说有误。《泰西水法》利玛窦应未参与翻译,而应是熊三拔与徐光启合作完成。但此书的翻译最先可能是由利玛窦提出,但他没有实现。故称“亦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
第四,徐光启的西方历法知识,也同样初得自于利玛窦。《明史·徐光启传》称:“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尽其术。”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各疏》称:
臣等昔年曾遇西洋利玛窦,与之讲论天地原始,七政运行,并及其形体之大小远近,与夫度数之顺逆迟疾,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其确然不易之理,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臣等自后每闻交食,即以其法验之,与该监推算不无异同,而大率与天相合。(49)
《刻〈同文算指〉序》(万历四十二年,1614):
既又相与从西国利先生游,论道之隙,时时及于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象数之学亦皆溯源承流,根附叶著,上穷九天,旁该万事,在于西国胶庠之中亦数年而学成者也。吾辈既不及睹唐之十经,观利公与同事诸先生所言历法诸事,即其数学精妙,比于汉、唐之世十百倍之,因而造席请益。(50)
徐光启《〈简平仪说〉序》(万历三十九年,1611):
余以为诸君子之书成,其裨益世道者未易悉数,若星历一事,究竟其学必胜郭守敬数倍。其最小者是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叹,偶为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未及详其所谓故也。(51)
《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同样认为如此:
万历间归化陪臣利玛窦等数辈,观光入觐,所携历法等书尤为精密,其所预推交食,时刻分秒,无不悉验。……若地之经度惟利玛窦诸陪臣始言之,亦惟彼能测验施用之。故交食时刻,非用此经度,则不能必合也。其他精微的确,种种敻异,与制作仪器,皆非思力所及。(52)
在向利玛窦学习的诸种西方学问中,西方历法知识应是徐氏的最强项,故李杕称:“问道之余讲求西法,天文、地理、形性、水利诸学,罔不探究,而推算历法尤加意焉。”崇祯二年(1629)五月乙酉朔日食,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历)》推算三分有奇,《回回(历)》推算五分有奇。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53)可知,向利玛窦学习西方历算知识后的徐光启之历算水准已远远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历算家。(54)
第五,徐光启还向利玛窦学习西洋军事科学知识,制造火器及筑造铳台等。《明史·徐光启传》称“从西洋人利玛窦学……火器,尽其术。”万历三十二年(1605),徐光启进京向利玛窦学习西学后,就已注重近世火器等攻守器具,其万历三十二年《拟上安边御虏疏》称:“攻守器具最利者,则无如近世之火器。”(55)
天启元年(1621)四月二十六,徐光启上疏要求依照西学铸造铳台,以铳护城,其《谨申一得保万全疏》称:
欲以有捍卫胜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56)
兵部尚书崔景荣天启元年五月上疏称:“少詹事徐光启疏请速立敌台,其法亦自西洋传来。一台之设,可挡数万之兵。”(57)
五月初九,徐光启再上《台铳事宜疏》,要求采用利玛窦筑台造铳的方法:
然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本法。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邱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此皆人之当议者也。(58)
其中“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这些话语明确表明徐光启早在万历中期就已经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铸造铳台的军事知识,而真正实用则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以后。
又徐光启《钦奉明旨录前疏疏》称:
古来兵法,至近世而一变为火器也。今有西洋炮,即又一大变矣。此炮之用,实自臣始。(58)
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亦称:
职少受业于先师徐文定公之门,素与大西洋诸陪臣游,先师有未竟之志,职隐忍不言,是为不弟。故不嫌越俎,冒昧空诶,约以二言曰:战守惟火器为第一,火器有以西洋神威为第一。先师练兵昌平,始议购西铳,建敌台,同志我存李囧卿总理都城十六门军需,亦首议取西人西铳。两先生岂漫然为此,盖灼见此铳之利。(59)
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习了“建敌台”之法,而且已掌握了西铳之“法式”。如果说将佛郎机铳引进到明朝军队王阳明为第一人的话,那么,将西洋大炮使用到明朝对外战争中则徐光启为第一人。
三、徐光启在神学方面受利玛窦之影响
在神学方面,徐光启接受了基督教,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天主教徒,利玛窦对其影响也是很大的。
首先,由于利玛窦的影响,促成徐光启的最终受洗。徐光启1599年初闻利玛窦之名,1600年于南京向利玛窦问道,1603年即皈依天主教:
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着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保禄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父,跟他谈及过去所曾听说过一些的基督教。……当时他可能只获知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原理。(60)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亦称徐光启:
尝潜心考究生死大事,惜儒书未道其详,旁参二氏九流之书,亦不得其真解。仰观俯察,抚今思古,颇多疑团。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于利公所言,天地万物必有一无上真主,化育生成,而为人类之大父大君;人魂不死不灭,在生敬主为善,则永归天乡,与天神为伍;否则沉沦地狱,与魔鬼同群。(61)
又徐光启《跋〈二十五言〉》:
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62)
如此,则徐光启虽因见天主圣像、世界地图等西方器物,但真正引起其疑问和好奇的,当还是生死和灵魂问题。而“南京问道”也给予徐光启心灵的启迪,以致《利玛窦中国札记》载:
好像是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启明,圣三位一体的神异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63)
而对于徐光启的皈依,利玛窦的著述却起着主导作用。《利玛窦中国札记》记1603年罗如望为徐光启讲道情形:
他把基督教教义的一份纲要,还有利玛窦神父教义问答的一个抄本带回家去;那是还没有刊行的一个文本。他非常喜爱这两部书,以致他通宵读它们……他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回家后又捎来两封信,信中他极清楚地表明他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有多么深。(64)
这两种书,一是《天主实义》,一是《天主教要》。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云:
罗子因以利子刚译《实义》及《教要》诸书送阅。公持归邸舍,彻夜不寐,读之欣喜无已。遂曰:我平生善议,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辩,至此而无可辩,即立志原受教。待旦复入堂求教。(65)
由上可知,徐光启入教依然深受利氏著述的影响。而徐光启受洗前仅与利玛窦、郭居静和罗如望三位神父有所接触,加之南京问道和阅读著述的直接、间接影响,徐光启终于皈依天主教。即利玛窦的极大影响,无疑为徐光启最终入教的重要机缘。
其次,利玛窦见证了徐光启的信仰历程及信教之虔诚。在利玛窦的视野中,徐利虽相识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可《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交游要人中并未提及徐光启;而《利玛窦书信集》中,1602年9月2日《利氏致龙华民神父书》曰:
《天主实义》用中文撰写,已经过一位大官文豪,也是我们的朋友润色一番。(66)
罗渔译此句时加按语曰:“即徐进士光启”。我们以为此处为译者之误。徐氏此时并未成进士,也未为官,因此不可能称为大官文豪,故知此人非徐光启。同书直至1605年2月,利玛窦方在致马塞利神父的书信中首次提及徐光启高中进士(67),而此时已过去约一年时间了。也即徐光启首次出现于利玛窦书信中当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此后1605年5月10日《利氏致父书》(68)、1605年5月10日《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69)、1607年10月18日《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70)、1608年3月6日《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71)、1608年3月8日《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72)、1608年8月22日《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73),几乎年年书信中皆提及徐光启,可见徐光启在利玛窦视野中、在天主教传教中渐趋重要。1605年5月10日《利氏致父书》中,利玛窦视徐光启为新教友;而同日《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徐光启被利玛窦称为“似乎已经是久已进教的老教友”(74)。甚至视其为“中国圣教的坚固柱石”:
几天以前,我在谈道时,说到天主有时在梦中示人秘密,他才把他的梦告诉我。可见是天主选了他作中国圣教的坚固柱石,因此愿意用一奇迹来教导他。(75)
1607年、1608年,徐光启作为“卓越的教友”被利玛窦提及其父受洗及遵循天主教葬礼葬父事。(76)由“新教友——老教友——圣教柱石——卓越教友”称谓的层层递进可知:徐光启在利玛窦视野和中国天主教事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这也完整地描绘了徐光启的天路历程。
徐光启1604年到达北京后,据利玛窦称:
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有人说,保禄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流泪不止。(77)
后徐光启成功使得父亲、妻子受洗入教,(78)妻子亦成为北京第一位奉教的妇女。(79)1604年,徐光启为《二十五言》作序时,《利玛窦中国札记》即称其对基督教信仰的崇奉:
利玛窦神父还就各种道德问题和控制灵魂的罪恶倾向的问题写过二十五篇短文。……神父们的朋友保禄也写了一篇序和一篇跋……尤以他们的朋友保禄的赞许为然,他在其中乘机颂扬基督教的原则说,他不仅赞同它们而且已经接受它们成为了教徒。(80)
1605年5月10日利玛窦致信罗马,同年称颂徐光启信仰的坚贞:
他天资聪明,学问和文章也出众。他在我们住宅附近租一房屋,每天足不出户,他看到我所著的和所印的中文书甚受人的重视,他便常常催我多写书,说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传教和建立教会的方法。可是他也知我的时间少得可怜。最后,他请我用中文写出我在主日和节日向教友所讲的道理,这一点我也做不到。于是他只好在我讲道时,自己作记录。(81)
再次,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徐光启的神学修养日趋深厚。利玛窦对于徐光启的神学影响,主要集中于上帝说、三一论和灵魂说。徐光启“南京问道”时,两人就探讨上帝说和灵魂说。《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3记:
(徐光启)尝潜心考究生死大事,惜儒书未道其详,旁参二氏九流之书,亦不得其真解。仰观俯察,抚今思古,颇多疑团。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于利公所言,天地万物必有一无上真主,化育生成,而为人类之大父大君。人魂不死不灭,在生敬主为善,则永归天乡,与天神为伍;否则沉沦地狱,与魔鬼同群。(82)
同时,因“南京问道”,徐光启接触三一论。《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万历庚子,至南都见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梦,如见圆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盖天主预启以三位一体、降生妙义。然尚未知其解也。(83)
当然如前所说,徐光启最为关注生死和灵魂之事,也正因此才向利玛窦“南京问道”。徐光启受洗后,进京日夕与利玛窦相处,在北京的教堂中,受利玛窦神学思想影响更深。伏若望(Joao Froes)《徐保禄进士行实》:
他经常来这里做忏悔和领圣餐,非常虔诚,热泪盈眶,在场人无不为之感动。每项布道会他也都前来协助,并对布道会充满好奇。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会非常坦诚地提问,就像一个学校里的小学生。
伏若望还称:
保禄进士在与众人一起聆听弥撒时,其真诚的神态尤为出众。他在我们神父们的住所旁边租了房子,并开辟了一个专门供他使用的门。他经常通过此门来参加弥撒。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教堂成了他家的神像龛。(84)
利玛窦在京期间经常就许多神学问题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文人进行对话。其《畸人十篇》“大部分是连续不断的评论,是一种以对死亡的反复沉思作为维持人生的正当秩序的方法”(85);而第三篇《常念死侯利行为祥》、第四篇《常念死侯备死后审》即为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对话。两者主要论及死亡与最后审判,旁涉灵魂事。利玛窦认为常念死侯,有五大益,即以敛心检身,而脱身后大凶也;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以轻财货功名富贵也;以攻伐我倨傲心也;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徐光启闻后,即曰:
此皆忠厚语,果大补于世教也。今而后,吾知所为备于死矣。世俗之备于死也,特求坚厚棺椁、卜吉宅兆耳,孰论身后天台下严审乎!(85)
徐光启因诵读利氏著作,更加关注灵魂学说和最后审判。徐光启不仅经常学习利玛窦的各种神学著作,在北京时期更有三四年时间两人长时间接触相处,并有经常性的对话。利玛窦的神学思想及作为中国天主教传教会领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徐光启,使其敬佩服膺。柏应理称:
公服膺利子之教,欲笔其像供奉之。利师不许,遂法利师之行,亦终身不绘一像。(86)
此足说明,利玛窦这位引领其进入基督教世界的“导师”在其心中具有的崇高地位。
这一切不仅对徐光启对于上帝、灵魂等天主教教理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促使徐光启入教以后的后半生始终如一地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一位天主教徒的美德。邓恩称:“徐光启与利玛窦的精神境界颇为相似,均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完美和谐的气质、准确的判断力、毫不动摇的信仰、真挚的谦恭。”(87)
最后,徐光启不仅注重加强神学修养,同时也积极加入天主教的宣教事业。伏若望《徐保禄进士实录》称:
有时神父们因前往妇女教徒家中主持弥撒而缺席教堂中的弥撒,徐保禄便决定学着帮助她们,他学得非常勤奋刻苦。在拉丁词语的发言方面尤其花了力气,这些辞汇因为比较长,所以对他来说有困难,有些字母很难发音,特别是对于一个如此年纪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是他通过努力克服了所有困难,定期致力于对她们的帮助。这引起了所有人对他的崇敬。(88)
徐光启努力学习拉丁文,协助神父给女教友主持弥撒。
尤其在对教会的保护和发展上,徐光启更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曾德昭《大中国志》:
保禄博士(徐光启)已从京城回到自己的家乡,由于他的出现,做事更加便利,减少了传道和教化百姓所发生的危险。因此施洗礼的人数不断增加,神父不得不写信请求协助,要求给他派一名伴侣,有时曾有三人。保禄博士为了扩建那座教堂,几乎把它全部推倒,重建了一座新的,所以直到今天他仍然有许多基督徒。(89)
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录》中保存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
在一次教难中,皇帝命令驱逐所有的神父。保禄进士得知神父被围困后,想办法营救他。
徐保禄一生对教会拥有热情,即使在其生病和临终之时也如此。在他病重期间,他还设法使神父再次进入南京。为此,他给一位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大官写信,将神父置于他的保护之下。
保禄进士总是以其真诚向人们表现他灵魂的善良,让人们看到《圣经》的推广、教会的发展。
由于这种对上帝的和蔼可亲、忠实和虔诚的品行激发他更大的愿望,他要了解欧洲教会的事情,特别是教宗和耶稣会总会长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管理修会、教会的基本情况、教会向外的扩张,等等。
他得知我们的神圣信仰在交趾支那王国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后,非常欣慰和高兴,而交趾王国中发生的教难也让他感到难过。为了安慰和鼓舞交趾王国的教徒们,他亲笔写了一封长信,心中蕴含的精神足以使该国教徒重新坚定信仰。
他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教会,不仅以与官员打交道之便利而保护教徒,而且还向皇帝表明立场。由于皇帝命令驱逐神父们,他便将一些神父藏于自己家中,并通过关系,将另一些神父藏于朋友家中。神父们撤离北京后,他代替神父们尽可能地为那里的教徒提供精神上的需求,决心做一个古希腊基督教教父亚大纳亚那样的人。
他不仅对自己家乡和自己国家中的教会有这样的热忱,而且也非常关心帝国以外的教会的发展情况,他始终都非常希望将我们的天主教义带到朝鲜去。他请皇帝派他带人前往朝鲜,主要目的是趁机带神父前往,以便将福音的种子散播在朝鲜王国。
他对教会事务密切关注,给予好的建议帮助教会发展,用他的权利保护教会。他编撰了很多著作并将这些著作作为教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手段。他将一生都奉献给教会事业,其主要目的一直是使福音得到传播。他经常用自己的钱出书,并在帝国内传播这些书,以便让所有人都对我们的教义的真理有所认识。(90)
上述“经常用自己的钱出书”,大抵就是指徐光启自己完成的一些宗教著作,如《圣教规诫箴赞》,以四字一句,对天主最高礼赞,将耶稣降生、十诫三德、教主爱人之义发挥尽致,充分显示其宗教认识及投入。(91)这些宗教著作也正是徐光启为宣教所作,也即徐光启不仅随着自身神学修养的提升从而坚定了天路历程,也以类似传道员的身份参与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这无疑又证明了徐光启本人的信仰之坚定。而这与启迪并促成其天学历程的利玛窦应有着重要的关联。
注释:
①汤开建、张中鹏:《徐光启与明末来华欧洲传教士交游考》,提交于“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07-11-08。
②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三《徐光启奉教》,第88页,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86-8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因第二种版本乃苏州勒石,第四种意在流播,故知。参见(明)吴中明:《跋〈山海舆地全图〉》,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⑩[意大利]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见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213-214、537页,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
⑥(12)[比利时]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536、539页,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版。
⑦《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第290页,罗渔译,台北光启、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⑧⑨(清)李杕:《徐文定公行实》,见宋浩杰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0、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1)[意大利]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8页。
(13)(清)李杕:《徐文定公行实》,见宋浩杰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2页。
(14)(19)《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90、266页。
(15)(21)《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86-87、66页。
(16)(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六十九《与徐玄扈赞善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9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影印明崇祯刻本。
(17)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14-515页,1605年8月27日,利玛窦迁入他们新购买的一所房子,并准备修建教堂。以前是靠租赁旧屋居住,且无地建教堂,故赐宅之说为虚。1604年与利氏会见还应在旧屋。
(18)[意大利]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9页,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徐光启集》卷十二《景教堂碑记》,第531页。
(22)(26)《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90、356页。
(23)(27)《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16-517、517页。
(24)(28)《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75、82页。
(25)[意大利]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8页。
(29)(30)(清)李杕撰:《徐文定公行实》,见宋浩杰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2、232页。
(31)《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3页。
(32)(35)(38)(41)(43)(44)《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86、63、7、75、82、83页。
(33)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详情参考洪煨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见刘梦溪:《20世纪学术经典》之《洪煨莲、杨联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4)《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牍二》,第504页。
(36)(清)李杕撰:《徐文定公行实》,宋浩杰:《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1页。
(37)[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第13章,第204页,余三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9)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87页。
(40)(45)(清)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二《徐光启传》,彭卫国、王原华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
(42)《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90页。
(46)(50)(51)《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62、79、72页。
(47)曹于忭《泰西水法序》及郑以伟序,均转引自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99-100页。
(48)[比利时]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544页。
(49)《徐光启集》卷七《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第344页。
(52)《徐光启集》卷七《治历疏稿一》,第330页。
(53)(清)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二《徐光启传》。
(54)《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55)《徐光启集》卷一《论说筹议》,第5页。
(56)(58)《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第175-176、188页。
(57)[比利时]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545页。
(58)(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钦奉明旨录前疏疏一》,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未刊本。
(59)(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
(60)《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67-468页。
(61)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三《徐光启奉教》,第88页。
(62)《徐光启集》卷二《序跋》,第86页。
(63)(64)(77)(7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68、469、489、491页。
(65)[比利时]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538页。
(66)《利氏致龙华民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61页。
(67)《利氏致罗马马塞利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66页。
(68)《利氏致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83页。
(69)(71)(74)(75)(76)《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90、290、290、290、356页。
(70)(72)(73)《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327、365、385页。
(78)《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91页;也可参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341页。
(80)(8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4、487页。
(81)《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90-291页。
(82)《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三《徐光启奉教》,第88页。
(83)[意大利]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见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213-214页。
(84)[葡萄牙]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1634)》,董少新译,载《澳门历史研究》第6辑,2007年。
(85)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459-461页。
(86)[比利时]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547页。
(87)[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第6章,第81页。
(88)(90)[葡萄牙]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1634)》。
(89)[葡萄牙]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74页,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1)古伟瀛:《由理起信-徐光启的宗教信仰》,“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07-11-08。
标签:徐光启论文; 利玛窦论文; 利玛窦中国札记论文; 历史论文; 几何原本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