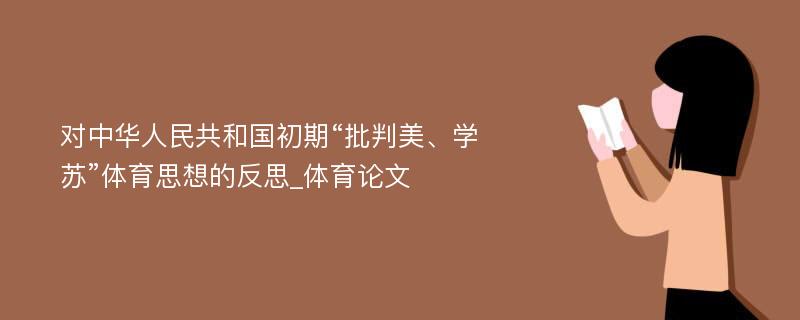
对建国初期“批美学苏”体育思想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想论文,建国初期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09)07-0005-03
我国建国初期,在体育思想发展进程中,曾经历过一段“批美学苏”的特殊历史时期。今天人们往往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这一历史时期,将其看成是“左”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对“批美学苏”体育思想进行历史、客观、辨正的分析和评价,使其恢复本来面目,并从中把握共和国体育思想传承与演进的逻辑线索。
1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世界上形成了以前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垒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选择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制度的构建、外交策略的选择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以前前苏联为样板、向前前苏联学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建国初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又严重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前前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而不能向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找[1]。”同时,在仿照前前苏联模式,以前苏联为样板构建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须清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影响。
作为文化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在以什么样的体育思想为主导、构建什么样的体育组织、如何发展体育运动等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就体育思想而言,当时面临着“破”与“立”的双重任务。“破”就是基于对旧体育本质的认识,即30年来中国体育理论、制度、方法、作风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一套[2]必须从思想上予以清算,消除体育思想的崇美倾向;“立”就是建立一套为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人民的、大众的体育运动服务的体育思想体系。“立”的途径就是以前苏联为样板,仿照和借鉴前苏联模式,具体办法就是大力宣传前苏联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积极组织出国访问交流,邀请前苏联体育代表团来中国进行技术示范,邀请前苏联体育专家来讲学,大量翻译和出版前苏联体育理论和体育技术方面的书籍,吸收前苏联体育的基础理论、体育管理、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国防体育的思想和观念。
2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的内容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的贯彻是在“破”与“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其中,“破”的过程主要集中在思想领域,而“立”的过程则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展开的。
“批美”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循的逻辑路径是:旧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它和美国体育是什么关系?美国体育的本质是什么?旧体育和我们要建立的新体育是什么关系?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在当时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其逻辑结论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对于旧体育本质的概括,其基本基调是反动的、没落的、为少数人服务的。过去,反动统治下的体育,是为少数人服务、供少数人玩赏而与广大人民相脱离[3]。对于旧体育和美国体育的关系,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旧中国的体育学人有四分之三是留美归来的;二是旧中国的体育思想、体育组织和体育方法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一套[2]。关于美国体育的本质,徐英超指出:美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国家,它的组织、经济、军事、教育等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体育自然也一样,不能设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体育,对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的人民会是合适和有益处的。国民党反动派是美帝国主义、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因此,他们搞体育是为了讨好美国主子,有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为他们少数人直接服务[2]。在充分揭露旧体育的本质及与美国体育的关系后,人们认识到,旧体育与新体育是对立关系,是水火不容的,必须深入批判旧体育,清除旧体育的流毒和影响,清算体育思想中的“崇美”倾向。我们“建设新体育,是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3],因此,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残余的东西,都必须加以严格的批判和改造,借以了解过去的错误,挖出它的根源,扫清新中国新体育建设的障碍[3]。在体育思想“批美”的进程中,许多体育界颇负声望的学者和官员,通过他们留美的经历或对美国体育的了解,积极参与进来,对美国体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其代表人物有徐英超、马约翰、吴蕴瑞、苏竞存、凌治镛、马启华、陈镇华、马钧、管玉姗、梁兆安等。
“学苏”的过程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而且表现在实践层面,它是通过对前苏联体育思想、体育组织和体育运动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学习和吸收来全面整合提升体育思想的。
在体育思想上向前苏联学习,和在其他方面向前苏联学习一样,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力推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前苏联创造了新文化,应该成为我们肩上新文化的范例[1]。”刘少奇也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前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前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前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4]。”朱德同志说:“要学习前苏联体育方面的好经验。”[5]
当时,对我国体育工作者来说,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学习前苏联体育的问题,即对前苏联体育的本质特征进行正确而全面的把握。因此,创刊不久的《新体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前苏联社会主义体育的本质特征:“前苏联的体育运动是为了加强劳动人民的健康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力量,是劳动人民走向高度生产劳动的准备,是协助以共产主义教育苏维埃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建设家,有组织有训练不屈不挠的勇敢的人们、坚牢意志的人们、社会主义国家强有力的爱国者、争取列宁——斯大林不朽事业的战士”。“前苏联的人民体育事业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前苏联的体育已成为苏联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苏联的体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苏联的每个体育工作者及运动员都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承担祖国的生产建设,保卫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像这样怀有目标的体育事业,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从来没有的。”[6]其次,通过广泛宣传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体育取得的伟大成就来鼓舞和激发人们的斗志,坚定奋斗的目标。牟作云在《今日前苏联的体育》一文中,不仅回顾了苏联体育的发展历程、宣传了成就,而且强调了苏联体育伟大成就的取得根源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7]。前苏联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体育团体,百万人民有规律地进行着体育活动;苏联运动员在和欧洲及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竞赛里,……保持了前苏联在运动上的光荣。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成功的基石,保证了我国体育运动不断向前进。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和前苏联政府的关切和帮助,所有这些成功是不会实现的[6]。第三,在前苏联体育思想和体育理论主导下,创立了新中国体育理论的学科体系。其总体特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并依据教育学原理来指导。具体表现为:第一,从阶级性、工具性方面来界定体育的社会性质和生活职能;第二,强调体育的国家性、统一性和人民性;第三,突出了体育和其他社会现象的不同之处是发展人的体质,并确定体育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第四,重视教学过程以及运动技能技巧的传授[8]。
3 对“批美学苏”体育思想的评价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兴起于1949年,终结于1959年,与中苏的友好关系十年繁荣的“蜜月”期相始终。这一历史过程留下了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3.1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唯一选择。“特定时空条件”从内向外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批美学苏”体育思想是全方位地消除崇美思想、学习前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9月刘少奇在北平高干会议上提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前苏联。毛泽东也认为,前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其二,全方位地消除崇美思想、学习前苏联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客观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承认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全面封锁我们,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双方的敌对情绪。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条件和可能向美国学习。而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方面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其三,全方位地消除崇美思想、学习苏联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建设的新中国,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建立人民民主、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欲达此目标,必须“批美学苏”。
3.2 在“批美学苏”体育思想主导下,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批美学苏”体育思想是“破”与“立”辩证互动过程,对于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来说,“破”的作用是“隐形的”,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认识和观念上,而“立”的作用则是“隐形和显形”兼备的,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
1950年8月28日到11月28日,新中国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应邀访苏,对前苏联体育运动的组织领导、干部培训以及学校体育等作了较为系统的参观和学习,并参观了全苏田径运动大会、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大学、中央体育研究院以及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的工厂、学校及公共体育宫的体育活动[8]。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是1950年12月24日由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体育学校部部长罗曼诺夫率领的体育代表团。由此拉开了中苏体育交流的序幕。当然,中国体育无论是理论水平、组织能力还是竞技能力都是相当落后的,中苏体育交流的内容主要是向前苏联学习。在培养我国体育科研人才方面,前苏联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从1954年起,中央体育学院先后聘请了10位专家担任研究生导师招收了215名两年制研究生和34名体育理论研究生,到1957年,上海体育学院也聘请苏联专家,培养了59名研究生[8]。为了尽快提高我国运动训练水平,1955年底到1956年初,苏联选派了12名教练在我国国家队执教,他们和以后陆续来华的苏联和东欧教练员系统地介绍了先进的训练理论和方法,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有的已接近和达到了世界水平,为中国以后形成的一批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8]。
3.3 “批美学苏”体育思想的贯彻过程,得到了前苏联体育界和前苏联人民的无私帮助,谱写了中苏传统友谊的篇章。长达10年的向前苏联学习的过程,不仅使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更得到了前苏联体育界和人民的全力帮助与支持,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下面一个事例即可略见一斑。1953年9月13日至10月26日,苏联国家体操队应邀来华访问表演,全团共30人,都是苏联运动健将,集中了苏联体操界的精华。他们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南京、上海、广州和汉口7个城市表演了20多场,观众人数达50多万,参观学习的体育工作者达6000余人。期间,他们还进行了示范练习,召开了学术报告会、座谈会等,给我国带来了现代体操运动的新信息和先进的训练经验。随苏联体操队观摩学习的中国运动员如饥似渴地学习,苏联教练也倾囊相助,他们在火车上讲课,在行李车上练鞍马,使中国运动员在短时间内掌握了一些较难的技术动作。在中苏表演赛中,虽然中国运动员水平很低,但苏联队中的世界冠军却给了他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当时中国最好的体操器械,除鞍马外全部不合格,苏联队访华结束时,将其全套器械送给了中国,成了我国制造国产体操器械的样板。此外,苏联队留下的《前苏联体操运动员等级大纲图解》成了我国以后训练和比赛的大纲[8]。
3.4 如何看待“批美学苏”体育思想存在的局限性。显然,受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批美学苏”体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有将“批美学苏”体育思想意识形态化、照搬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和迷信前苏联经验等问题。应该说,上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缠绕在一起的,也不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应该历史、客观、辨证地对待这些问题。
关于将“批美学苏”体育思想意识形态化问题是指把“一边倒”的政治口号与“学习前苏联经验”混为一谈,把学习欧美等国家比较成熟的体育理论和体育实践等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表现得并不严重,和“文革”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从一些学者的“批美”文章中可看到,他们也承认美国体育中关于技术、生理方面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按照今天的说法,我们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不应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当时,不仅无法认同,而且在实践操作上也无可能性。我国同美国体育交往的历史是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以后的事情了。
关于照搬前苏联发展模式和迷信前苏联经验问题,今天有些人往往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认为是幼稚的和无条件的照搬。实际上,历史事实远非如此。其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严重缺乏,有些领域尚处于空白状态,前苏联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移植”。其二,我们在学习前苏联经验时,也注意同本国实际的结合问题。中央曾就加强向前苏联和其他国家学习的组织工作时提出: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其三,学习前苏联,也要“以苏为鉴”。当时前苏联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已显露出来,这也促使我们反思。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这种思想更加明确。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当然,在宣传前苏联经验时,为了强化人们“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心理期待,夸大了前苏联经验,形成很不好的学风。有些人对前苏联经验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认为只要是前苏联经验,什么都是好的。
收稿日期:2009-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