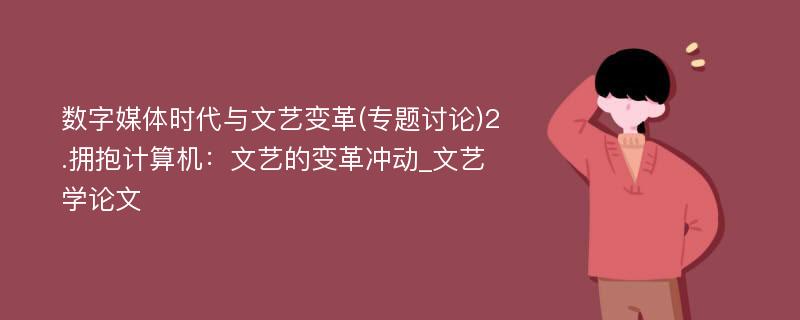
数字媒介时代与文艺学的转型(专题讨论)——2.拥抱电脑:文艺学的转型冲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媒介论文,冲动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者连同相应的史论在中国经常合称为“文艺学”)是在书面媒体兴起并占据传播领域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日益关注崭露头角的电子媒体。如果说书面媒体根据社会身份规定不同的专门化类型的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建构分化性知识社区的话,电子媒体则引导人们分享相同的信息空间,相对忽略其父子关系、隶属关系或别的基于社会身份的关系。以此为背景,文艺学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在不同程度上放下自己的高贵身段,关注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电子媒体至今业已经历了以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为主要依托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文艺学面临着广播所刻意培育的听觉文化、电视所推波助澜的视听文化的挑战,因此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外延,以至于在不少方面和艺术学重叠。在第二阶段,文艺学面临着日新月异、充满魅力的信息科技的挑战,一次次产生弃旧图新、拥抱计算机的冲动,以至于在许多领域与信息科学交叉。数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口头媒体的对话特性、书面媒体的沉思特性,消除了以模拟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使观众变得被动的负面影响,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推动当代文艺学的转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媒体下文艺学转型问题,我们应先读一读美国学者、评论家瑞安(Marie-Laure Ryan)为论文集《赛博空间文本性:计算机技术与文学理论》所写的导言。瑞安试图根据电脑的作用对计算技术衍生的话语和文本的新形式加以区分。她认为,电脑的作用有三种类型:作为作者或合作者;作为传输媒体;作为表演空间。在20世纪70-80年代,当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应用的首选课题时,计算机对文学的潜在价值一般被视为文本的生产。这种生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因素被排除在外。计算机产生的文学是人与机器合作的成果,其中,计算机可以起三种作用:为人类合作者输出可以翻译成文学语言的蓝本;在与用户的实况对话中产生文本;对于人所写的文本进行不同的操作。人类合作者相应地充当后处理者、合作处理者与前处理者。作为例证,可以举出Tale-Spin之类可以生产故事概要的古典人工智能程序、Eliza之类可以生产对话文本的可选性人工智能程序,以及用于随机生成词语组合的各种数据库。在谈到作为传输媒体的计算机时,瑞安认为,相关文本根本不是写作的新形式,而是对业已确立的文本的电子补充。属于这一类的,有数字化印刷文本、通过电脑网络进行的异步通信(电子邮件及帖子)、树状小说与合作文学、《地点》之类万维网肥皂剧。不过,她也指出,电脑虽然主要是作为传输通道而起作用,但绝非一种被动的媒体,而是正在培育新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它们可能导致电子文本及其印刷对应物之间的有意义的风格与实用的差别。例如,《地点》追踪加州海滨五个住户的日常生活,由五个作家分别负责撰写其日记。访客登录网站后不仅可以观看插图、了解过去情节,而且可以给人物发送电子邮件,提出对其生活的忠告,或者向作家提出如何发展其情节的建议。这些作家/人物要负责答复其戏迷的邮件。这种相互作用打破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传统边界,创造了一种在作家与读者之间进行适度合作的可能性。就作为表演空间的计算机而言,瑞安指出,此处文本不能从电子环境中分离,因为它旨在探索其硬件和软件支持的特性,如流动的视觉显示、交互运算法则、随机化能力,以及一种潜在地将文本激活的程序的运转变成独一无二的演出的实时操作模式。属于这一类的有超文本、电脑游戏(包括多用户网络游戏与面向对象的多用户网络游戏)、用户参与型虚拟交互剧、具备人工生命特性的诗歌机器或赛博文本(cybertext)等。它们都拥有迥异于传统作品的特性。例如,在最为乌托邦的形式中,交互剧将是充分自治的产品,其中,用户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驱动将人物人格化。脚本将允许用户选择在任何时候做什么、说什么与想什么,他们可以影响情节的发展方向,但它其实是由系统控制的,因此,每种选择将产生在美学上令人愉悦的、在叙述上是精致形式的戏剧行为。这类产品如能获得成功,将实现消灭作者、人物、演员与观众之区别的古老梦想[1]。
瑞安关于计算机在文本生产中所起作用的分类,实际上对应于文艺学因计算机应用而萌生的三种转型冲动。
第一种转型冲动与程序设计有密切关系。程序本质上是文本,它与传统文本的区别不仅在于所使用的是专门的人工语言,而且还可以被执行并产生变化,某些时候甚至仿佛有自己的意志。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德拉尼(Paul Delany)在《计算机与文学评论:从格列姆到控制论文本性》[2]等文章中谈到,MIT教授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在1963年发明了人工智能程序Eliza(根据萧伯纳《皮格马瑞翁》女主人公Eliza Doolittle命名)。它在人机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效果不仅使文学家向往新型交互写作,而且让文艺学研究者憧憬善解人意的数字助手。他们将计算机视同于犹太教法师用黏土制作的机器人格列姆(golem),只要获得指令(正如在格列姆的口中放入写有神圣文本的纸片那样)就醒来干活,任务完成就进入休眠(正如格列姆一旦口中的纸片被拿走就丧失生命那样)。这些人相信,长于计算的机器将弥补人脑之不足,从而为文学主张的证明、文学作品价值的判别、文学史公案的析疑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以计算机辅助文学研究为契机,文艺学将实现面向计量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的转型,从而超越人类情感的束缚、记忆的局限、功利的纠缠。从那时以来,他们确实在建构作品索引、确定作品归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文学系的两位教师就利用用词习惯统计技术戳穿了英国某出版商伪称新发现莎士比亚遗著的骗局),但从整体上说,这种转型带来的更多是失望,因为计算机至今尚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擅长阅读文本、阐释理论、发现人类所未能洞悉的意义模式。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前景。至少在互联网上,可以应用相关技术开发文艺学自动答疑系统,并实现文艺作品智能推荐、文艺活动的智能追踪、文艺档案的智能保存,等等。
第二种转型冲动与网络建设息息相关。将电脑的用途由计算转向媒体的观念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1962年8月,美国科学家立克里德(J.C.R.Licklider)与克拉克(W.Clark)合写备忘录《在线人机通信》,提出建造“巨型网络”(galactic network)的设想。这是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的观念前导。上述想法发端时不过是“星星之火”,但不到二十年即成燎原之势。当世界范围内计算机彼此连接成为网络之际,文艺学领域又萌生了新的转型冲动。其心理诱因之一是将伴随数字媒体而诞生的赛博空间当成传统社会规范鞭长莫及的乐土。人们讴歌网络文学的自由特性,向往网络写作的强大魅力。这种冲动由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共鸣而变得分外强烈。传统文艺学一度青睐的“结构”衰落了,被“网络”——既无层次又无中心、纵横交错的连接所取代。作品不再不朽,甚至也不再是定型的,而是任何一个人依其所喜、依其所能而发挥的命题,是像雪貂一样四处跑的语义材料,从网络角度看则是基于包交换的信息流。与此相适应,文艺学转型要求将注意力由书页转移到网页,网络文学理所当然地占据了视野的中心。文艺理论工作者、文艺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资深学者与新锐稚子一样发帖子、建主页、开博客,力求在众声喧哗中发出个人之“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很自然地呼唤网络文艺学(主体是网络文学理论、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史)的诞生。相关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不过,也有若干因素可能使上述努力遇到挫折。例如,号称无中心的互联网实际上是有中心的,美国至今仍不放弃对根服务器的控制权,美国文化至今仍在网上占据主导地位,多元化或多声部在许多场合仅仅是表面现象;各国传统的伦理、法制与商业势力正在迅速向互联网扩展,过去常被人们当成数字媒体特点的某些现象(如没有把关人)正在丧失其意义;网络文学至今没有显示出足以与非网络文学相区别的充分的新颖性(坊间仍然将它们印出来卖,写手们多半以此为乐,读者似乎也将网络文学的印本当成了真身),网络文学研究所运用的基本还是其他类型文学研究所常见的观念、术语与命题。建立“网络文艺学”的目标,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种转型冲动来自旨在探索计算机本身潜力的创造。这种创造同样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MIT研究生作为业余消遣开发游戏“空间大战”(1962),哈佛大学硕士纳尔逊(T.H.Nelson)提出“超文本”的理念(1965),都在这一时期。1981年,纳尔逊用超文本形式写作了有关超文本的《文学机器》,这本书可以看成对他用毕生精力开发的在线超文本出版系统以及所进行的超文本文学实验的理论阐释。1991年,美国雅达利公司实验室劳雷尔(Brenda Laurel)出版了《作为剧院的计算机》,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计算机作为表演空间的意义。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专家默里(J.H.Murray)出版《全息面板之上的哈姆雷特》,挪威伯根大学教师阿塞斯(Espen J.Aaresth)出版《赛博文本:透视各态历经文学》,丰富了这一理念的内涵。将计算机看成表演空间,一方面意味着人可以进入计算机(在现阶段当然要借助某种程序或诉诸某种化身),不仅在其中亮相,而且能够施展才华、大显身手;另一方面,意味着作品本身是因人的参与而产生变化的数码戏剧。无所不包的网络是全球意识的物理化身,是超越国家和空间的界线的基础设施。它不只是文学在世界各地传播时所搭乘的“新型马车”,而且是文学赖以展示自身魅力与变化的舞台,甚至是文学自身安身立命的家室。传统文艺学一度看重的“主体”因此式微了,网民既不像笛卡尔那样“我思故我在”,也不像荣格所说的那样更换面具,而是“我变故我在”——流动的自我成为人的本质。这一点与将计算机当成数字助手或数字媒体无疑有着明显的不同。也许可以说,文艺学因引入数字助手而产生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开发计算机辅助文学研究的新手段,因引入数字媒体而产生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开拓网络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因引入数字表演空间而产生的转型主要表现为造就赛博文本研究的新范式。
从理论上说,计算机辅助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现代主义理论的支配下进行的,网络文学研究深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赛博文本研究则以探索体现信息科技、信息艺术发展趋势的创新理论为旨归。若加比较的话,第一种取向将计算机(程序)当成文艺学研究者手中听话又能干的工具;第二种取向将计算机(网络)当成文艺学研究者搜集材料、发表意见迅速又自由的途径;第三种取向将计算机(空间)当成文艺学研究者探索人们如何在赛博家园生活、通过赛博文本进行表演的依托。由于“表演”在学科分类上是文艺学与艺术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赛博”(cyber)本身来源于信息科学(控制论),因此,第三种取向代表了文艺学、艺术学与信息科学三者的重合,21世纪以来的学术新作有不少以“互联网艺术”(Internet Art)为题行世。这种趋势同创作实践中网络文学日益多媒体化、国民经济体系中网络游戏产业实力日益增长是一致的。当然,这种取向同样面临种种障碍。例如,缺乏对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足够了解至今仍是文艺学研究者的拦路虎,“为计算机而计算机”蕴藏着丧失文艺学应有的人文关怀的危险,将赛博空间当成“家室”可能招致“网瘾”之讥,过分强调赛博文本的特殊性难以传统文艺学对话,等等。
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半个世纪以来,因计算机应用而产生的文艺学转型,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在成果形态上,从印刷品、单行电子出版物到网络电子出版物;在理论形态上,从沿用传统理论术语解释新的文学现象,到汲取信息科技新词阐述传统文学历史,以至于从数码文学的新鲜经验中提炼崭新的学术范畴;在社会形态上,从印刷文化所哺育的老一辈学者接受电脑培训以便实现“换笔”,到以计算机从事写作的中年学者将上网当成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自幼就用Logo之类语言学习编程的新一代人在赛博空间中与智能代理“共舞”。当然,更为深刻的是对于上述形态转变具备指导意义的观念转变——诗与数学、信息科技与文学/艺术研究完全可以是一家。不论转型对文艺学意味着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或别的什么,但有一条是肯定的,计算机与网络的应用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