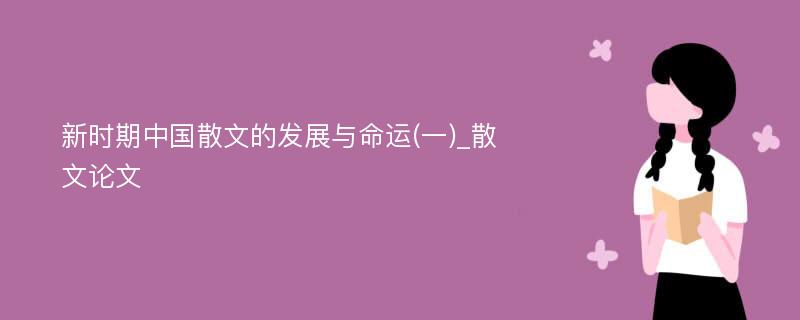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散文远远未能如诗歌和小说那样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兴趣,与小说和诗歌的中心地位相比,散文处于边缘位置。可以说,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研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具体说来,这表现在研究观念的陈旧、研究模式的老化及研究队伍的弱化等方面。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衡定散文优劣的标尺主要还是情、理、形、神,知、智、意、趣,较少出现新的散文理论标准;又如,研究者探讨的方式主要还停留在经验和感想层面,未能上升到学理和理论高度;再如,具体的散文作家,作品分析远胜于宏观地把握与概括,以至于出现散文研究“见木不见林”的倾向;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往往是就散文而研究散文,未能站在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散文进行探讨。与诗歌和小说研究的高歌猛进、激扬奋发不同,散文研究更多的是低徊浅唱、疲惫松软。
当然,散文研究如此这般的境况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第一,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滞后。作为一种文体,新时期的诗歌与小说一直处于不断革新状态,观念与文体总在超越传统和自身。在诗歌领域,朦胧诗、寻根诗、寻根后诗都是对以往诗歌传统的根本性超越;在小说领域更是推陈出新,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后先锋小说等层出不穷、波推浪涌。相比而言,散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质,一直处于既定模式之中难有根本性超越。以致人们对散文的发展深怀忧虑,有人甚至提出散文“消亡论”,从中可见人们对新时期散文滞后的强烈不满。显然,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对一个没有多少变动的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其意义很值得怀疑。第二,散文概念和理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长期以来,诗歌和小说研究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从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固定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理论的发展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强有力的支点和依据。然而,散文可供参照的理论却较少,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而深入的散文理论,散文的概念、范畴、内涵、外延、价值和本体等都较为模糊,未能得以确认。这就必然导致散文研究有着经验化、随想性的不足。第三,散文研究者素质的低弱。尽管新时期已经出现几本散文研究著作,有的研究者也做了不少拓荒工作,并表现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文化功底,但总体而言,散文研究队伍远没有诗歌和小说研究队伍整齐和壮大,其理论修养与学术功底也不可同日而语。看来,让一支装备不良、素质低弱的“军队”去攻破散文这个坚固“堡垒”,那是非常困难的。
新时期散文研究的落后状态直接导致三个恶果,一是它难以成为创作的借鉴与指导,从而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处于相当的盲目和随意状态;二是不能正确估价新时期散文的成就与局限,以致出现研究者的“迷失症”;三是限制了一般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读者或是对散文不屑一顾,或是迷失于其中难以进行理性判定。
新时期中国散文已走过20多个年头,尽管它的成就远不能与诗歌和小说相提并论,但它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散文一改附属地位,由边缘而向中心移动,成为热得发紫的文学样式。显然,在世纪之交,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做出宏观而公正的评价,展望其发展前景,是一件必要而又颇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用“新时期、后新时期、后后新时期”而用“新时期”来概括这几十年的散文,主要有两点考虑:其一,尽管在不同的时域里散文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本质上说,这几十年的散文具有总体一致的启蒙性特征;其二,“新时期”这一概念更为完整和清晰,足以概括这个时期的散文发展与走势。
文化散文——继承与深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它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狭义上,它就是指与政治、社会和道德相区别的精神、心理、人格和审美方式。本文使用的是狭义文化。从此意义上说,文化散文更多的是带有文化内蕴,内含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意趣。1990年,有的学者指出,“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文化散文”。(注:佘树森:《九0年散文琐谈》,转引佘树森、 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大致说来,“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散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政治、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切入进行的文明批判,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散文;二是从文化角度展现人的精神、心理、生活和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文化散文。比较而言,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意识形态散文为主潮,而文化散文则处于边缘地位。
到新时期,尤其到1985年以后,这一对比关系发生了调换,就是说,意识形态散文相对弱化,而文化散文则空前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大概有四。一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业已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比较和平的生活,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关系有所松动,那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已被打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以其自身的文学性方能获得其长久的生命力。三是作家的学者化呼声很高,一些学者步入作家行列,这就带来了散文的文化化。四是读者文化品位的提高也要求散文承载更大的信息量,做到更入情合理,有着更高的品位与境界。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散文家,他们有冰心、萧乾、柯灵、孙犁、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黄裳、余光中、林非、宗璞、余秋雨、张晓风、贾平凹、张炜、周涛、林清玄、张承志、史铁生、韩小蕙、王小波、素素、郑云云、伍立扬、王开林、刘鸿伏、祝勇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兴盛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的影响。在新时期文化散文家中,有的就是当年活跃于文坛的散文大家,如冰心、孙犁、钱钟书,那些中青年散文家也都是喝过中国现代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并且,从中国现代作家那里都可找到他们的师承或源头。比如,汪曾祺直接师承沈从文,废名;贾平凹在《四月十七日寄友人书》中“曾惊叹过三十年代的作家,深感到他们了不起,后越是学习他们的作品,越觉得他们都是从两个方面来修养自己的,一方面他们的古典文学水平极高,一方面又都精通西方的东西”。张中行和黄裳又分明得益于周作人的文化散文。林非、张炜与鲁迅的文化散文关系密切。
那么,新时期文化散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深化了现代文化散文呢?
首先,对人性、人情进行了深度的开掘。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散文比较重视表现人的阶级性,而对人的非阶级性则关注不够,当年鲁迅和梁实秋那场笔战就很能说明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化散文弥补了这一不足。比如,林语堂、丰子恺的文化散文较多关注普通人性,即衣、食、住、行和真、善、美、爱等,如林语堂的《论躺在床上》,丰子恺的《放生》、《素食之后》都属此类作品。
到了新时期,探讨共通的人性和人情成为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作家逐渐认识到衣、食、住、行、性、爱、美、趣味等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如郑云云的《住房心情》、伍立扬的《悲欣交织说口腹——饮食文化随笔》等都是自觉探讨人性的基本方面。另外,亲情、夫妻和友朋之爱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一个母题,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苏晨的《老伴》、林非的《离别》、宗璞的《哭小弟》、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这些作品与鲁迅的《藤野先生》、冰心的《南归》、朱自清的《背影》都有内在的联系,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文化散文中关于人情至美的母题。这些作品较前或许在观念上没有太多的突破,但在抒情的真挚、描写的细腻、叙事的方式和感人的深度上都有超越。
事实上,“爱”作为人类永恒的母题,它世世代代为人抒写,然而它又是常写常新,总是不老,看来,问题的关键既是写什么,更是怎么写。比如林非的《离别》让人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它们都写父(母)子之爱,然而写法又明显不同。一是在叙事方式上,《背影》是从儿子的视角用直叙的方式,表达离别前父亲的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而《离别》则通过父亲的视角运用倒叙回味的方式,描写父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离别》中,儿子出国前父母的准备和机场送别时的千叮万嘱都被省略了,作品是从儿子离别后产生的空荡写起。“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真可惜自己的眼睛无法跟他拐弯”,尽管儿子多少次回头告别,但母亲肖凤却自语自问说,“为什么不再回头瞧我们一眼?”父母回到家里,“推开门,觉得阴凄凄的,冷飕飕的”,尽管时令正值盛夏。此时,“往日的欢乐都到哪儿去了?”肖凤的心更是高悬着,她“走进儿子的小屋子里,轻轻抚摸着他写字的桌子,抚摸着他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其实,离别前和离别中的伤情固然强烈,而离别后的伤怀往往更深厚,尤其对父母来说更是如此。那么大的空间需要用思念去填充、回味和想望,从而产生较大的艺术张力。二是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离别》较《背影》更节制。《背影》中写了两次流泪,一次是看到家道衰落,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二次是离别时父亲为我准备一切,后又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里,“我的眼泪又来了”。而《离别》也写了两次流泪,一次是儿子的身影消失后泪水溢满眼眶,但强忍着,没有让它流下来;二次是母亲回到家中,看到儿子的用品,抚摸着儿子早晨留下的体温,“眼泪终于掉下来”。这种通过节制后的感情更为感人,它在最该表达的时候一涌而出,既表达出作为学者作家的父母之克制力,又表现出内在情感的深度和流程,这里,《离别》比《背影》的情感表达又胜了一筹。三是在细节的描写上,《离别》比《背影》更扣人心弦。父亲送走儿子,“觉得自己的眼眶里正涌着泪水,绝对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震颤,泪水会掉下来”。这是何等细微的体味,这仿佛是人走在一根发丝上,又好像早晨的露珠滚在草叶上,让你的心也为之震颤。
与此相关,倡导人性向善也成为许多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在这些散文中,“善”不仅成为个人的一种修为,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自己避免受到异化和污染。在表达方式上,新时期文化散文比较注重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1989年,冰心写了《我喜爱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作家与小猫、小狗间的亲近。张炜也酷爱小动物,在他的散文中屡屡写到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他的向善之心,也表达了对那些残忍者的咀咒。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张炜的散文《圣华金的小狐》。在张炜笔下,小狐已不是狡猾放荡的野兽,而是周身充满灵性与美的象征,它的灵目,它的秀鼻,它的软毛,它的长须,它的大耳,都透出生命的光泽。然而,就是如此可爱的小生灵,“到本世纪末,它们可能灭绝”,而灭绝小狐的罪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作者表达了对人类残暴性的痛恨之情,“这样的一双目光,一张脸庞,令人心动。可是更多的时候,人类已经在残酷的追逐和杀戮中失去了感动的能力。对于死亡、流血、可怕的变故和异类的伤痛,已经变得相当漠然”,“圣华金小狐,还有其它无数的可爱生灵,都将在残酷的时间和命运的戕害和淘洗下,消失终结”。作者最后还警示说,面对小狐的眼睛,人类“都应该长长的反省”,“人类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面前,应该全面地检点自己的行为,追索自己的品质”。面对人性的异化,张炜的呼喊是沙哑的,滴着血的,从中可见某种绝望。在另一篇散文《老人》里,张炜关注的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里的动物比小狐幸运得多,它们与美丽的花朵一起聚集在两位栖身山中的老人身边,做着美丽的梦。老人从动物身上获得欢乐,而动物也得到老人的饲养和呵护。有趣的是,作者对动物进行了拟人化描写,它们之间甚至它们与老人之间都可以进行交流。我认为,作者对动物如此富有爱心,无疑希望人类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修成一颗善良仁慈之心。在丰子恺笔下的动物是可爱而温情的,但在张炜笔下的动物则可以与人类交流、亲爱和会通,换言之,张炜笔下的动物与人已难分彼此和高下,而是荣辱与共、合为一体了。更重要的是,张炜站在人性异化的角度来审视动物,对人类的命运深怀忧患。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将自己看成是大自然的精灵,万物的主宰,而将动物看成野兽,而在张炜看来,动物与人都是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共生共长共灭,从心性上看,动物并不比人类来的残酷与可怕。
还有一位以动物为参照呼吁善心的散文家值得注意,她就是唐敏。在《心中的大自然》中,唐敏写到鹰,写到虎。对鹰,孩子时的“我”是充满敬佩与热爱的,然而,有一次,它却被一个战士击落,因为这个战士说,他的班长眼睛瞎了,而鹰脑是治眼最好的药。作者虽没有张炜的愤怒,但对人类的残暴深为不满,对人类的至上观念也表示怀疑。对虎,“我”一直天然地怀有恐惧,然而,有一次,在山里,我一人与老虎突然相遇,相距仅仅五米。老虎竟然看了我二秒钟后悠然离去了。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在作者看来,老虎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宣讲的那样“凶猛残忍”,而是多么善意啊,它完全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
琦君曾写过《人鼠之间》和《黑人与小猫》二篇散文,表达了她的慈爱善心。尤其是《人鼠之间》更是不可多得。在一般人笔下的动物都是可爱的,对可爱者行善施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人见人恨、人见人恶的老鼠,作者也同样能给以善待,那就难得了。作者这样写道,“我本来对小动物都非常的喜爱,猫狗自不必说,就连人见人厌的过街老鼠,我也无心杀害。尤其是对于眼前这只楚楚依人,饥肠辘辘的小老鼠,越发动了怜悯之念”。这里,琦君做法的正误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她宅府仁厚,有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她似乎要让日益变得功利、偏狭和凶残的人类清醒:葆有一颗善心是多么重要啊!
在人性日益受到异化的今天,新时期的文化散文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作品呼吁人类要有一颗善心,对人,甚至对动物都应该如此。残酷与凶暴不是先天性的,它是后天被异化的,找回善心,保住本性,这样,人类才能有健康与幸福。
讲究趣味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重大收获。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化散文中,林语堂和丰子恺的散文非常注重“趣味”,林语堂曾写了《论趣味》,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鼓吹趣味是不能无所顾忌的。到新时期,趣味已成为许多散文作家的追求,比较典型的是贾平凹、董桥和伍立扬。董桥写过《说品味》、《听那立体的乡愁》、《满抽屉的寂寞》、《文章似酒》;贾平凹写过《丑石》、《五味巷》、《酒》、《灵渠》、《闲人》、《美食家》、《红狐》、《狐石》、《坐佛》;伍立扬写过《文字灵幻》、《寂寞》、《水月镜花》、《诗酒年华》、《诗与水墨韵味》、《梦中得句之趣》、《悲欣交织说口腹》,仅仅从文章的题目即可见出作者的审美趣味:这是对生活和艺术中真、美和趣味的无边欣悦与崇尚。为了表达“趣味”之妙,作者往往运笔自如,行云流水,妙语连珠,有时真似如有神助一般。这是中国文化散文中重“性灵”的一脉。只是与林语堂等人有所不同,董桥散文中有一种“怪味”,贾平凹散文多了一股“鬼气”,而伍立扬散文则将林语堂的绅士风度加以发挥,增添了如许华美。这是明显的深化与发展。
其次,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上,对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西方自由、民主、科学和平等思想的支撑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此时,先驱们非常坚执,决不容许反对面的意见,带着明显的霸气。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从根部腐坏,必须进行彻底的“换血”,而西方文化则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鲁迅将中国旧文化概括为“吃人”二字,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对西方文化进行全面吸收;郭沫若则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热情洋溢的将滚滚的工业烟柱比喻为美丽的花朵。应该说,将西方文明的优秀部分注入衰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中,使之起死回生,这是必要的,但这一批先驱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即是将西方文化神化了。这就势必带来中国现代散文的主导倾向,即对西方文明的赞美甚至崇拜之情。
当然,中国现代散文对西方文化也不是完全认同的,其中也有疏离,这主要表现在那些文化散文上。鲁迅的《朝花夕拾》、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冰心的《寄小读者》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与皈依,更应注意的是,林语堂在他的“两脚蹋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思想指导下,确是创作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文化散文。但总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确实存在这样的不足:往往偏向的而不是中正的对待中西文化。
新时期的文化散文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或是过于依恋中国传统文化,或是过于信仰西方文化。但与现代文化散文相比,许多新时期文化散文对这一倾向都有新的超越,这些散文往往站在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表现了比较健康成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倾向。这类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他们包括余秋雨、张中行、季羡林、林非、王小波等人。
余秋雨在散文《笔墨祭》中谈到中国的毛笔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尽管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其中也内涵着美与人格,但世界文化的发展已不容许中国人仍手握毛笔慢悠悠的爬行,新的世界和新的文化已是人们对这种毛笔文化进行美的祭奠的时候了。他这样概括毛笔文化的局限,“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牲,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整体上,它应该淡远了”。显然,这是针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说的。如果不站在世界科技的高速发展中审视,余秋雨或许还沉迷于毛笔文化的“美”中不能自拔。同样,在《西湖梦》中,余秋雨还对“梅妻鹤子”的“隐逸文化”人格进行批判,认为这样就会使中国“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站在西方竞争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的隐逸文化也确实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如果不改变中国人的文化结构,中国将永远被甩在世界的后面。只是余秋雨的分析还欠深入,他没有看到“毛笔文化”和“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的正面意义,也没有看到造成中国这种“柔性哲学”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更没有看到世界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柔性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是清除而是继承与发展。这是余秋雨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存在的误区。
比较而言,林非的文化散文要清醒得多。在《旧金山印象》中,作者一面惊异于物质文明发展的速度之快,一面又感到这种物质文明存在着与人性和人类发展相悖的地方。作者这样写道:“从挖掘洞穴的原始人,到建造摩天大楼的现代人,其间的进步实在太惊人了,人的创造力量实在是太无穷无尽了。然而当人们将各种最流线型高楼大厦汇集在一起之后,却也同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失掉阳光的环境,多少重复了洞穴中那种阴暗的气氛”。这是一个对中西文化有深切理解的学者的眼光,合情合理、深入透彻。这里让我们想起新时期文化散文有的过于强调“桃花园式”的生活环境,甚至崇尚原始式的洞穴式生活方式,有的过于沉迷于都市生活的钢铁结构中,这两种生活理想都是有问题的,都缺乏现代的理性精神,都带有感觉和情绪化的倾向。可以设想,如果人类完全舍弃物质文明的便利条件和优秀成果而追求远古的自然风光和情调,或一味跟随现代物质文明的疯狂发展不顾人类的精神家园,那怎会产生健康的人格和人类的幸福生活呢?用桃花园式的文化理想来反拨现代都市文明的异化是有价值的,让人类享受符合人性发展的现代文明也是不错的,而如果非理性地顾此失彼则永远难以超越人类倍爱异化的困境。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健全是新时期文化散文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余秋雨曾说,“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与体魄总是矛盾,深邃与青春总是无缘,学术与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注: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张炜曾这样给知识分子下定义,“没有关怀力,判断力,在民族发展和转变的关键时刻毫不动心,漠然处之,甚至尾随污浊,即便有再多的学问,能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吗?”。(注:张炜:《纯美的注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显然,在张炜看来,健全今天的知识分子人格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关注的核心,知识分子成为余氏透视中国文化、审视自身的一个聚光点。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王国维成为作者的剖析对象,虽然一个王朝业已覆灭,而被传统文化同化又不能自拔的旧式知识分子王国维却“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与那个朝代一同逝去了。
史铁生是一个孤独者,他在那篇《我与地坛》的文化散文中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进行的心灵探险的心路历程,在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中,史铁生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感悟,那就是人在与万物的和谐中体会真、善、美,美好的生命就是在自然的秩序中倾听上帝无言的声音。史铁生似乎对厚重的历史和纷乱的文明碎片不感兴趣,而是穿透它们,直接走进人生、生命之中,用心灵和智慧去感悟永恒与永生。
王小波的散文也在探讨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精神品质,只是他比余秋雨和史铁生多了一份明晰、一份超脱。在王小波这里《我的精神家园》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理性的批判与整合上,在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和科学精神的基本原则上,王小波以一个“浪漫的骑士”对中西文化展开无情的批判。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作家,他不禁反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蔑视封建伦理道德,而且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使”角色。如果充当一个诚恳的“信使”还不坏,问题是“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指马寅初,笔者注)相比”。由此可见,保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重要。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往往不是理想主义和从众意识,而是自己的身份与独立人格。在《椰子树和平等》中,王小波指出“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就是“有人聪明有人笨”。这里,王小波提出了一个存在论问题,即人本质上的悲剧性。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文化往往用这样的方法去消除这种不平等,即“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或“一旦聪明人和傻子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子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如此把握我们的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令人感到悲凉自心底升起,从中可见作品的深刻性。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化散文还未能解决好中西文化互补融合的问题,那么,新时期中国文化散文则在此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些作家能够站在20世纪学术研究的最高点思考文化和人类的发展命运,自觉而理性地对待文化和人类面临的异化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与对策。同时,新时期文化散文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即从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等角度,来反思中西文化,尤其反思知识分子的健全发展。这可以说是较前的一次深化。
再次,文体模式的演进与突破。长期以来,散文这一文体一直以其短小精粹为特色,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杂感、通讯、小品文、散文诗、书话都是如此。即使是随笔也往往篇幅不大。散文似乎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体式,以短小的篇幅快速地反映自身及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从而带来了散文气魄小、承载量不大的文体模式。这一模式自有其优点,自然、活泼、灵性而快捷,容易表达诗意和情感。中国现代散文一直以这一模式为主导,形成了与小说不同的别一种风格。
新时期的较长时间里,散文创作都是遵循着现代以来短小精悍的散文传统,只是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出现了较长篇幅、较大容量的“大散文”,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化散文”。为了与篇幅较短、容量较小的文化散文相区别,我们将这类散文称之为“大文化散文”。此类散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余秋雨、史铁生、周涛、张承志、素素、祝勇等。这种划分定义方法既可突现此类散文“大”和“文化”的特点,又可与非文化散文,与一般的文化散文区别开来。使其更明晰、更准确。
“大文化散文”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呢?一是自由度大。短小的篇幅固然有其特长,但它也有明显的短处,那就是较难承载大的容量,这就限制了散文只能选取较小的题材。对那些较大的题材,作家也只能有所选择,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久而久之,散文甚至形成了“形散神不散”、“叙事——抒情——说理”的模式。到新时期中后期,客观形势的变化、诗歌与小说的变新、文化寻根的推动、散文作家和理论家的呼吁,终于使这一传统散文模式有所松动,“大文化散文”应运而生。这种散文体式打破了既定的散文模式,完全以自由的心态进行创作,在题材上注意把握大的文化命题,在叙事、抒情和议论上都舒展自由,以内心的展示为依据。这里余秋雨和周涛比较有代表性。余秋雨以学术论文随笔的形式展开,他往往选中一个大的文化命题而后多角度多侧面阐发,行文如江河纵流,不择地势,浩浩荡荡。这类文章往往都很长,万字、甚至长可达到数万字。《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抱愧山西》、《十万进士》等都是这样。周涛则以多个单篇组合而成长篇的方式成文,表面看来,这些单篇间的联系往往并不密切,但其内在精神却不无关联。如长篇文化散文《吉木萨尔纪事》、《蠕动的屋脊》、《伊犁秋天的札记》、《游牧长城》等就是这样。这种文体极有助于作家自由挥洒,纵横驰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二是忧患意识强。这类散文与一般性文化散文如汪曾琪、贾平凹、孙犁等的散文不同,它们更多的是站在民族文化、中西文化和人类文化的高度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理想,这类散文的理想性强、参与意识强,往往具有较强的启蒙性质。余秋雨站在文明和文化的中心焦虑地呼唤知识分子人格健全与发展;周涛以边地文化的倡导者迫切希望中华文明不要遗忘边陲文化的“美”;史铁生用自己的心灵默默的又是忧心忡忡的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素素对东北久远的文化细心考察,希望尽快找回失去或即将失去的文明记忆;祝勇面对老北京文化精神的日益衰落发出忧心如焚的寻问。这种忧患具有一种弥漫和辐射作用,使其散文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和悲感意味。三是理论色彩浓厚。“大文化散文”与一般文化散文比较,明显增强了说理的成分与逻辑的力量,有时议论推陈铺排,如山海涌来。有的善于引经据典,以增强自己的论点的说服力。还有的运用思考的力量层层递进。浓郁的理性力量使得此类散文可信性强,并有着大气磅薄的深刻力量。余秋雨的散文充满历史史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益的,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作品过于沉重,有呆板和概念化的倾向,好为人师和贵族化优越感。对周涛散文的理性有的学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注: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这一评价是相当准确和中肯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大文化散文”并不是无源之水,平地而生的,它有中西文化散文作为深厚的背景。比如英法随笔的影响是明显的。另外,中国现代文化散文中,梁遇春和林语堂的文体对其影响最大。林语堂的文化散文《机器与精神》和《中国文化之精神》都是属于“大文化散文”的范畴,无论在精神实质还是文体形式上都是如此。只是林氏带有明显的绅士风度,不显过于沉重忧患罢了。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林、梁毕竟还属个别,而且他们远没有余秋雨等人来得自由与自觉,也未形成巨大的声势。
总之,新时期中国文化散文是一个可喜的收获,虽然在总体格局上仍未脱离现代中国文化散文传统,但在广度与深度上显然有较大的开拓与深化,某些地方还有明显的突破。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文化散文并不因与传统的紧密联系而减损其成就与价值,可以说,从艺术水准和感染力的深度来说,文化散文最有生命力,它对新时期散文的贡献也最大,这是其他散文体式都不可比拟的。
(未完待续)
标签: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余秋雨论文; 张炜论文; 新时期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背影论文; 王小波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