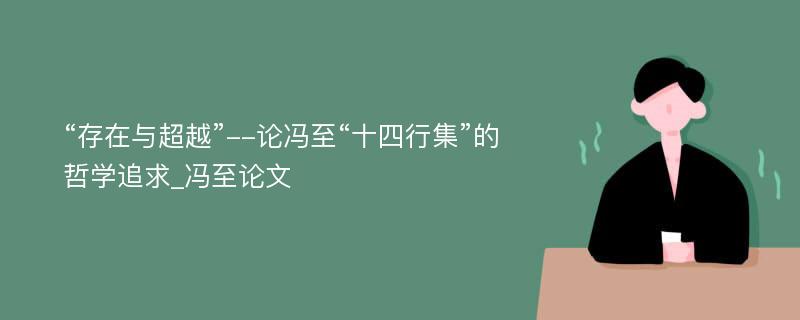
“存在与超越”——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学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与论文,哲学论文,四行论文,论冯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2-0059-05
冯至的《十四行集》实质上隶属于那种“共名”状态下的独立化书写。抗日战争的风 云把作家们纳入一个共同的“抗日文学”的旗帜之下,原本多样化的写作因而获得了一 个共同的主题。但个别作家和诗人并未被“共名”的潮流裹挟而去,他们对战争状态下 万物的冥想为他们提供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可能。他们不像其他大多数作者那样 急切地去为抗战奔走呼喊,而是继续坚持着用自我生命对自然与现实进行体验,用艺术 的眼光沉思世间所有的一切。他们并非不关心战争,也并非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他 们只是变换了关注的角度。这部分作者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共名”状态下或许显得 不合时宜,然而,当我们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站在中国文学历史演进的高度,便不 能不佩服他们对生活所具有的洞察力和对艺术的远见卓识,他们在艺术上探索的成就至 今尤为人力所不逮。冯至的《十四行集》便是这群“另类”作家所留下的一个生动的个 案。
对生活的关注与凝思是《十四行集》哲理意蕴的来源。战争把冯至逼到昆明的乡下, 使往日那种逃脱都市的喧嚣与回归自然的愿望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竟得以实现。这一切 使冯至对生命万物的静谧观照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在对“我为什么住在乡下”这一问题 作出回答时曾表示,住在乡下能“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 的原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 处”[1]。根据海德格尔这一理论,冯至在昆明乡下的生存确实可以更确凿接近事物的 本质,发掘事物本身所透射出来的哲学意义。
对于这一诗学特征,李广田曾作出极高评价,“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 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 是最好的诗人”[2]。“在平凡中发现最深的东西”构成了《十四行集》的哲理色彩。 具体而言,《十四行集》在哲学意义上的追索与冯至所受的存在主义影响深深关联。
然而,存在主义是个意义模糊的哲学命题,要对其作出明晰的阐释几乎不可能。就连 许多存在主义大师自身对这个概念的确定性也表示质疑。海德格尔如是说,“‘存在’ 概念乃是最晦暗不明的。……‘存在’是自明的概念……然而这种平常是可理解性,恰 恰表明它的不可理解性……”[3]。这是否说明追问《十四行集》中的哲学意义成为不 可能了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言说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十四行”的策略:
……每天都有人——通常是一位知识妇女,但也可能是门房,或者电车售票员——问 我何谓存在主义。没有人因为我回避这个问题而表示惊讶。我说这个问题太难也太长, 无法诠解。人们能做的只是设法阐明它的要旨,而不是形成定义。[4]
马塞尔的这一策略适用于我们对《十四行集》的解读。实际上,冯至对存在主义的接 受也正是所谓“要旨”性质的哲学理念。固然冯至对存在主义有过较为系统的阅读,但 因其本身“不善于逻辑思维”,在选择阅读的对象上还是有所偏向的。像里尔克、基尔 克郭尔、尼采等充满诗意的哲学性本文,冯至怀有极大的热情。而对于那些晦涩艰深的 著作,他则只是涉猎,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或所爱好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要旨”[5] 性质的哲思。
透过诗歌本文的表层,《十四行集》给予我们哲学意义上追问的回答正是上述的一些 存在主义的思绪。但不仅仅如此,其时,冯至还自觉接受了诗哲歌德“蜕变论”的影响 ,以图对自己的实际生活有所指导。这样一来,《十四行集》的内蕴便显得繁密而丰厚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将《十四行集》中的哲学理念进行如下命名:死亡的先行;生命 的承担;沟通的隐喻;蜕变的具化。
一、死亡的先行
对生命的关注是冯至哲学理念中最常见的命题。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深刻地意识 到死亡是生命的界限。这种对生命的有限性的自觉,对冯至并没有产生虚无主义与悲观 主义的影响。这一清醒达观的态度可说是冯至早年生命意识中主体情绪的延续。但这一 时期的冯至因为哲学上的自觉,对生命本体存在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向宇宙存在的拓延, 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
无疑,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死亡是既定的,是生命向另外一个超验世界挺进的界限。 冯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主张把死亡纳入到人的现存之中,即根据不确定的但已 知的死亡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冯至在诗中对此有过明示,“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 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十四 行集.二》)。这与海德格尔“先行到死”的观点颇为相近,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一 种走向死亡的存在,人的现存与死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关系。死亡进入并存在于人的现 存之中,而人的现存也在经常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探讨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命获 得了另外一种性质,“即使在生命过程中死亡就已经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6]。冯至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解来诠释死亡的,他对死亡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海德格尔更加 深入。冯至把死亡纳入生命过程的同时,把死亡视为生命最辉煌的顶点。他主张人类应 乐观地对待死亡,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现存而努力,使自己的生命丰饶,以便在人生 的最后时刻领略生命最完美的东西。《十四行集》的第一首诗作《我们准备着》把这一 观念进行了具象化的处理: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 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 一次危险,//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 现。
在诗中,死亡成了现存的一种预设。人类已意识到死亡的可能。因而,在走向死亡的 存在中,人们应当达观地努力地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彗星 的出现,狂风乍起”,死亡的不确定性告诫人们死亡的实现随时都有可能,只有有“准 备”的人,才能担当起生命的重负。像那些小昆虫一样,它们结束了自己的现存,但它 们终究“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生命在此已达到了无可比拟的 辉煌。生与死这一对矛盾在这样的境界中获得了统一,人类对死亡的支配在努力求生存 的过程中获得实现。这种思想的另一重要理论来源是里尔克,“在里尔克那里,死亡是 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出现的”[6]。在里尔克 看来,死亡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高峰性体验。作为冯至的精神导师,里尔克对死亡的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施予了冯至一种单向度的传输,冯至在耄耋之年曾对此有过说明:“他( 里尔克)的世界对于我这个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是很生疏的,但是他许多关于 诗和生活的言论却像是对症下药,给我以极大的帮助。”[7]里尔克对于死亡有过意味 深长的描述,他说,“不要带否定意味来读解‘死亡’这个词语”,因为“如同月亮一 样,生活确实有不断规避我们的一面,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对它的完美性和 丰富性的充实”[8]。为一般人所恐惧和避之惟恐不及的死亡,里尔克却认定了是通向 完美生存的众妙之门。此时,我们再返观冯至的《我们准备着》一诗,就不难发现,冯 至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对里尔克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认同。
二、生命的承担
存在主义在强调人存在的荒诞的同时,也强调人应把人的在世这一事实承担起来,独 自担当起自己的命运。对此,萨特把它具象地表述为:“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 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 。”[9]在哲学的高度上,冯至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此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在《十四行 集》中,冯至用诗歌的形式对此进行了形象的阐释: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就是和我 们的用具的中间//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 陶泥,/它们都象风雨中的飞鸟//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好象自身也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 们生命的暂住。(《十四行集.二一》)
在这里,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端孤独无助的世界。个体生命之外的客观世界对于 人来说是那样的疏远与不可接近,就连与用具之间,“也有千里万里的距离”。而且, 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对人的存在而言,呈现的是一种愈来愈远的隔离态势,“铜炉在向 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连这些最简单的事物,人类都无法在本质上 予以把握。甚至,主体对自身的把握也存在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好像自身都不能自主 ”。这样的生存处境寓示了人类存在境遇的荒谬。面对存在的虚无,虽然有“微弱的灯 红”,但我们的存在也只是“暂住”而已。人类向何处去?在对基尔克郭尔的分析中, 冯至找到了答案,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方向:“人们不应该永远对 着虚无,要越过虚无,去寻求生存的本质、人的地位和价值。”[10]在虚无面前,人只 有承担起自己存在的责任,才可能越过虚无实现自己真实的生存。
里尔克在生命承担的哲学命题上的确施予了冯至启迪性的影响。1937年5月,冯至在为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本作序的时候写道:“(里尔克)告诉我们,人到 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花园里的那些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 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 单。……谁若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 当生活的种种问题,和我们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11]在里尔 克看来,人生之路艰难而恐怖,要达到一个人真实的存在,人只有独立起来,担当生活 中的责任。冯至领会并接受了里尔克这一生存观念的精髓,并进一步将其作为自己40年 代人生观的根本追求。
怎样“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冯至倡导在人的生存中实行一种严 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冯至曾对里尔克的艺术标准作出过如此的分析:“美和丑、善 和恶、贵和贱已经不是他取材的标准;他唯一的标准却是: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 严肃与滑稽。”[10]冯至将里尔克的艺术标准移置到生命哲学的范畴之中,作为人类实 现个体真实存在躬行的原则。冯至赞赏那些认真负责、严肃工作的人,并时常反省自己 ,“我不是常常不够认真不够严肃吗?”[7]他推崇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中提到的诗 人阿尔维斯,他在临死前还纠正修女一个单词上的错误。里尔克对阿尔维斯的分析也引 起了诗人的全身心关注,“他是一个诗人,他憎恨‘差不多’;或者也许这对于他只是 真理攸关;或者这使他不安,最后带走这个印象,世界是这样继续敷衍下去”,这种精 辟的人生见解“击中了”冯至的“要害”[7],为冯至的人生哲学提供了一种指南。
鉴于此,对于那些独自认真承担人生命运的人,冯至给予了推崇性的书写。他为鲁迅 、蔡元培、杜甫各写了一首诗,对他们执着人生的负责态度进行了肯定。在《十四行集 》第九首中,冯至描述了一个在前线经年作战的友人,回到城市后不为人所理解。冯至 为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你超越了他们,他们已不能/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 ”这是对抗战时期都市大众平庸、虚伪存在的一种反讽,而诗中的那位战士,因为对人 生的严肃负责,却获得了与杜甫、鲁迅等人在人生哲学层面同等的地位。
三、沟通的隐喻
冯至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强调生命个体对自己命运进行承担,但事实上,人一降生便置 身于一个群体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存在发生关系。因而,在处理个体与周围 存在者的关系时,冯至是主张交往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强调人存在的本 然的孤独,强调个人对命运的自我承担;一方面注重存在与存在之间的交流,倡扬相互 关怀。其实不然,在冯至的存在观中,人的本源性的孤独处境永不可更改,交流只是人 获得个体生命充实的手段而已。冯至的老师雅斯贝斯的实存哲学道出了“交往”的真谛 ,在他那里,交往成为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必要,“人只有在与其他的实存的精神交往中 才能达到他本然的自我”[6],“理性的运动不能在孤立的个人中发生,而只能在个人 与个人之间的交往中发生”[6]。这种“交往”理论成为冯至一种哲学上的精神资源, 他的诗也曾对此作出诠释。试看《十四行集》中的《威尼斯》:
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一个 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当 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等到了夜深静悄,/只看窗儿 关闭,/桥上也敛了人迹。
这是冯至“交往”观念的具象化描述,它像一个隐喻,展现着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交往使人的生命得到了充实与丰盈。 但正如前所述,交往并不能改变人孤独的本然性处境,“等到夜深静悄/只看窗儿关闭 ,/桥上也敛了人迹”,人的存在复归于无尽的孤独之中。
冯至的“交往”观念并不是仅限于实存之间的交往。他所倡导的交往打破了生与死的 界限,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结构上的差距。如同里尔克所说:“真正的生命形象穿越两个 区域,最伟大的循环之血涌过二者:既无此岸也无彼岸,惟有伟大的统一。”[9]这种 敞开性的存在扩展了冯至交往对象的界域,此在与彼在的界限随之消失。《十四行集》 中的第十七首《原野上的小路》书写人与人(不论生者还是死者)在这条小路上不尽的关 联;第二十首《有多少面容》书写在一个无限的生命空间里,存在者之间的交流随时可 能发生。这些诗作是对冯至敞开性交往观念的一种形象化表述。我们再来看一首充分表 现了生命体验中沟通与交流的诗,《十四行集·十六》: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 上交错的蹊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 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 棵松树,/是某某城市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 径,/化成平原上行人的生命。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眺望的远景有我们的生命化成,而条条道路与道道流水,阵阵 清风与片片流云,这些互相关联的事物又化成我们的生命。人化为物,物化为人,生命 与生命互相呼应,生命与万物融合为一。沟通与交流无处不在。这种交流具有无限的延 展性与敞开性,“既无此岸也无彼岸”,趋向于“伟大的统一”。冯至曾谈到自己在蹊 径行走时的体验:“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 ,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13]这种关连意味着交流的存在 与可能,只不过在《十四行集》中,诗人把这种理念诗化了,使其具有玄远悠长的韵味 。
冯至的“交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人道主义色彩。雅斯贝斯提出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应是“爱的交往”,他认为人的存在“只能从爱中得到充实以及爱对于存在着的 东西是敞开的”[6]。具体到冯至的诗中,是写梵高的那首“十四行”。这首诗对梵高 的画作了一番描述,对画中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诗人比拟为“永不消溶的冰块”。 但在最后,诗人却向画家发出了这样的追问:“这中间你画了吊桥,/画了轻倩的船: 你可要/把些不幸者迎接过来?”这种追问,体现了诗人的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沟通的 隐喻与人存在之间的相互关怀在此获得了统一,融溶在一起。
四、蜕变的具化
歌德给予冯至的影响并不亚于里尔克等存在主义诗人或哲学家。从冯至大量的研究歌 德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在哲学层面上,歌德至少有三种哲学理念给予冯至较深的震动 。具体而言,即否定精神、蜕变论、向外又向内的生存态度。其中尤以蜕变论之思想影 响最深。冯至自己也承认,“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 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 诗句,都颇有同感”[13]。“抛弃旧我迎来新吾”,冯至的言论已触及到歌德“蜕变论 ”的精神实质。歌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是由一个“原型”演化而来的,它们一 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不断得到进化与提高,并以此解释动物、矿物甚至人的生长和 发展。冯至对此深表认同,他在第十三首《歌德》中写道: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 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了一切的 意义:“死和变。”
生命在不断的蜕变中完成了从有限到无限的突破。这种蜕变是一种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蜕变中生命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养分而丰盈。这正如冯至对歌德的阐释:“死只是走向 更高的生命的过程。由于死而获得新生,抛却过去而展开将来。”[22]冯至的一些诗句 为这种蜕变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如第二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第三首《有加利树》:
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生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
但蜕变并非轻易可以完成。“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 要用前一段痛苦的死亡换取后一段愉快的新生”[13]。从低级到高级的每一次演进都必 须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各种痛苦。因而,冯至强调人的坚韧与生生不息的工作精神。他倡 扬人们具有歌德那种“一分一秒”都不曾停息的工作态度,惟其如此,才能有“随时随 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的蜕变结果。他把富有蜕变精神的“有加利树”视为自己的导师 ,“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诗人愿意 像有加利树那样在凋零里不断生长,以获得生命的丰满。
蜕变论这一观点与冯至所倡导的对人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蜕变 论要求人们不断向前变化,向更高阶段演进;对人生的承担需要人们认真严肃的工作, 对自己的生命全面负责。它们的最终指归均是使人生获得圆满丰润。在抗战时代人类精 神陷入危机的背景下,蜕变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对个体生命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号 召人们只争朝夕地工作奋斗,它告诫我们:“一切必须化为无有,如果他们要在存在中 凝滞。”[13]
《十四行集》是冯至的诗学探索达到顶峰趋于成熟时的作品。朱自清曾将其誉为中国 新诗发展的“中年”[14]。综观20世纪的中国诗歌发展史,《十四行集》的存在是颇为 “孤独”的,然而,正是其空前而又绝后的姿态证明了其自身地位的独特性。冯至在诗 中表现出的对人的存在与蜕变的思考,至今对我们尤有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1-02-20
标签:冯至论文; 里尔克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十四行集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死亡论文; 歌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