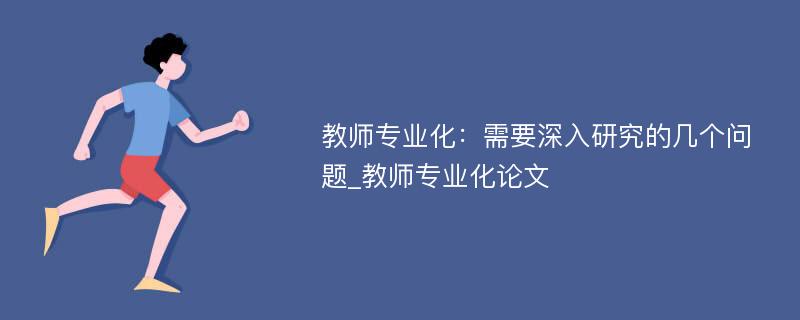
教师专业化:亟需更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更深入论文,亟需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教师行业专业化程度的认定
对于教师行业是否为一种专业,以及对教师是否为专业人员,一直是许多学者与社会大众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有以完全专业视之者,也有仅视之为半专业或准专业者,更有不认为其为专业者。[1] 事实上,他们主要都以已有的或自设的专业标准来评量教师行业专业化程度。在教师行业“现在被视为专业或强烈要求成为一个专业”[2] 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人仍认为目前教师至少是‘半专业’ (semi-profession),如果努力进行专业化,是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全专业’(full-profession)。”[3] 这也是此间学界中的一个主流观点。
的确,关于教师的专业属性已有两项重要举措:其一是1955年世界教师组织联合会(WCOTP)曾以“教师的专业地位”为大会主题,并且认为教师工作属于专业范畴;其二是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明示,“教师职业必须被视为专业”。这两项举措(特别是后者)常被那些视教师行业为专业的学者作为主要依据。然而,他们忽视了教师专业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努力目标,而并非是对教师实际工作情况与条件的描述。换言之,如果就“应然”的观点来看,教师应被视为专业人员;如果就“实然”的观点来看,教师现在只能被称为半专业人员。[4] 可见,教师工作应为专业,诚属确论,[5] 而“教师不仅是一种行业,更是一种专业”[6] 恐怕还称不上一个科学的命题。
问题还在于教师工作为何应为专业?有论者称:“随着对人的认识,对儿童成长认识的逐渐深刻”,我们深深感到教师“应该是专业人员”。[7] 看来,这一说法有点笼统。已有的研究结果已显示,“赞成者大多持着教育事业对社会贡献之重要性、教师资历提升与教师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等观点”。[8] 在这些观点中,又以教师作用的重要性为先。那么,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呢?我们不妨藉由两个案例来看这个问题。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国外研究似乎表明,学生成绩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乃是非学校因素(比如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家庭背景),而不是学校和教师的参与(详见科尔曼等人的报告, 1966年;詹克斯等人的报告,1972年)。然而,此后的研究(布罗菲等,1986年)却证明,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学生只有与他们共同工作,并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而不是试图绕过他们工作,才能够取得进步。因此,便开始形成一个重大的变革原则:“有效的学校学习需要良好的教学,良好的教学需要在指导学生学习中能作出决断的专业化人员”(波特等,1988年)。[9] 有意思的是,这一研究结果最近又因为哈努谢的研究报告而面临挑战。
哈努谢从《科尔曼报告》(1966年)问世后30年间的有关研究中选出了最重要的90项,并针对其中377个“功能预测推估”进行后设(meta)检视,在1997年发表了题为《学校资源对学童学习成效影响力评估:最新资料补充》一文。在此文中,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教学资源呈现稳定的增长,然而,学生的学习成效并未随之改善。具体地说,行政投入、设备、师生比、教师教育程度、教学经验、教师薪资和生均教育成本支出等项目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在统计上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准。[10] 学校/教师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作用,于是又成为一个问题。
在对影响学校教学成果的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后,王埃泰尔和瓦尔贝格(1993年)却别具一格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影响学习的28个变量按其作用之大小可分为三类:
·作用最大的变量包括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动力和行为;课堂管理、课堂环境和师生互动;家长在家中的鼓励与对学习的支持。
·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点的变量包括学校素质,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决策方式,社会影响,校外同龄群体。
·影响最小的变量包括不少决策者目前正不遗余力地进行的教育结构的调整。[11]
主要由《科尔曼报告》引发的家庭与学校/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孰大孰小的争论,在这一综合考察中,已变为学生、学校/教师和家长各自有哪些与学生学业成绩有关的特点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最大、一般和最小。
此外,与教师作用的重要性直接有关的,则是在国内外教育界都广泛存在的一个诉求即应“以学生为中心”。一段时间以来,“以学生为中心”甚至被视为针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一个新理念。但是《德洛尔报告》却阐明了“牢牢记住教师是学习的中心这一点是有多么重要”。[12] 我国有论者对“以学生为中心”已明确地提出了质疑:“以学生为中心”这一命题有忽视教师的作用之嫌。在他看来,“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情景,教师的教学自主程度应有所不同,学生的学习自主程度亦会有所变化”。[13] 对此我们已有较详细的阐释,[14] 这里不再赘述。
上述两个案例多少可以表明,作为教师行业应是专业的主要依据,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尚需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进一步予以支持或修正。
不言而喻,教师行业为何应为专业更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论证。教师工作领域复杂吗?其复杂性为教师所知吗?其复杂性为他人所知吗?这便是又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国外,研究人员发现,教师每小时作出与工作有关的重大决定为30个,师生互动每日达1,500次(在一个有20—40名学生的班级中)。根据这一事实,有学者得出如下结论:医生所遇到的可以与教师所遇到的复杂情况相比拟的只有一次,即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之后的医院急诊室中。
在这样复杂不定的情境中,了解情况、作出决策的能力,在教学中就像在其它专业领域中一样至关紧要、困难重重而且颇具挑战性。[15] 这种研究是足以借鉴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厘清教育事业之专业性质及其相关概念乃为教育从业者所需,或许在概念澄清之后,教师能对自己的工作及权力有合理之期望并寻求务实的改良策略。”[16] 在这一厘清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更加重视的路径之一,就是深入地而非一般化地探究教师行业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二、对教师专业标准的界定
对于“教师行业是否为一种专业”、“教师是否为专业人员”这样的问题,还有“另类”的回答。例如,有论者指出:“要想了解一种职业‘是否’符合专业标准,不如探讨这种职业在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中,达到‘何种程度’。”[17] 至于教师是不是专业人员,在有的论者看来,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而是在如何使教师专业化的重点上”。[18] 即便如此,似仍须以理想的教师形象为标的,亦即仍然不能回避教师专业标准问题。
在界定教师专业标准上,国内外学界和教育主管教育部门都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在国外,桑德斯(1933年)是“第一个有系统的分析专业的社会科学家”;[19] 对于专业标准有深入探讨的,是利伯曼(1956年)[20] 和美国教育学会(N·E·A·,1984年)等;(注:关于利伯曼在其《教育专业》(1956年)中提出的8个专业标准,可详见《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8页,以及台湾《现代教育》,1992年4月,7卷2期,第17页。)较为大众所接受的专业特征是由《国际教师工作与教师教育百科全书》(1987年)所界说的;(注:关于美国教育学会在1984年提出的8项专业标准,可详见张兰畹和吕锤卿的《中英国民小学教师在职进修制度之比较》,载于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和师范教育学会主编的《国际比较师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台湾师大书苑1992年,第774页。)较为通俗的关于专业标准的表述是“专业化教师,即工资高,训练有素,有能力和愿意继续学习,有工作动力,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对学生、家长和社会有责任心的教师”。[21] 这里仅是若干有代表性的界定。
在我国,对教师专业标准进行认真思考的学者已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看法。例如,杨深坑等认为,教师专业社会化是指“教师在专业社会化的生涯中,习得一切教育专门知识技巧,内化专业伦理信条,表现专业责任、专业自主性、专业服务态度等,成为教师专业行列中一份子的过程。”[22] 吴康宁认为:“所谓教师的职业社会化,是指通过内化教师职业价值、获取教师职业手段、认同教师职业规范以及形成教师职业性格而不断‘成为’教师的过程”。[23] 再者,便是大家可能并不生疏的我国官方文本中(1999年)提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应具有的6项标准。
当我们对林林总总的教师专业标准作一审视时,不难看到已解决的问题与留下的问题几乎同样多。归纳起来,“留下的问题”大致上有以下两类。
首先是专业标准有待细化。专业标准现在有点大而无当,其结果是给人们提供了创造的空间,却也提供了误释的机会(两者都不是有意的)。前者可以举教师专业伦理为例。诸如过去提倡并得到广泛体认的“蜡烛精神”(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而今是否已经过时等问题的讨论,就是值得肯定的。这种讨论有可能使原本宏大的专业伦理标准更人性化、更具体化,说到底将更伦理化,当然也更具可操作性。后者可以举教师的专业知识为例。此间论者一般都认为,教师应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即一般文化知识、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教育学科的知识。持此论者还指出,教师的知识结构不能再局限于“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的传统模式,而应包括科学与人文的基本知识、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一至两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和技能,以及教育类学科知识。[24] 平心而论,论者们达成的这种一致并非尽如人意,因为典型的传统模式未将“一般文化知识”排除在外,所以也就没有被超越可言;况且,典型的传统模式很在意的三个知识“板块”(一般文化知识、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科知识,亦被称为普通文化知识、专门知识与专业知识)之构成比率,现在也未被涉及,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就更无踪影了;即使具体到“教育学科类知识”,典型的传统模式在不断加以调整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比例,现在也语焉不详。
至于在西方国家自1970年代兴起的对教师专业自主的研究,在我国现尚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时间差”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专业标准的“粗放式”界定不无关系。
其次是专业标准有待矮化。专业标准现在有点要求过高。几年前,笔者曾经追问对教师必备素质的要求是否已经过高?指出,赞成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及能力,但不同意教师应成为心理卫生工作者的主张;赞成教师应积极参与课程及教学的研究,但不同意将“教师即研究者”作为教师所必备的一个素质。[25] 近年来,有些论者仍热衷于给教师“加冕”,如“学者型教师”、“专家型教师”、“研究型教师”、“智慧型教师”、“反思型教师”等,这是对教师要求过高的再现。难怪有学者撰文予以批评,其主旨十分简明(“教师就是教师”)。过高要求的又一例证,便是师德应有“底线”的主张最近备受非议。这就是说,不顾教师的工作特点和自身条件的要求即为过高。专业标准过高,往往还是教师被要求承担新的角色或履行新的任务,却又未受到应有的培训和未拥有必要的工作条件之产物。这一点,托尔斯顿·胡森早在1979年就有明示。[26] 现在看来,胡森担忧的现象已在多处发生。例如,美国新近“有些州对教师规定了更高的标准,并且进行许多评估,但却限制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时间;而另一些州正在对中学的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改革,但并没有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补充性支持”。[27] 就我国而言,目前正在实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育信息化等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应引以为戒,并牢记胡森的告诫。
对上述案例,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根据社会学的观点,关于教师专业标准的各种界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角色期望的范畴,而在现实生活中,被期望的角色行为与实际的角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便是角色期望的“不清晰”。[2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教师专业标准更加清晰和适切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三、对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的辨析
自1960年代末美国学者傅乐(Fuller,1969年)以其编制的著名的《教师关注问卷》揭开了教师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以来,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已成为一个蓬勃的研究领域。[29] 可以被用来说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的依据的,在1994年已有这样一段文字:“综观1970年代迄今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教师在不同的生涯发展阶段中,将会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识、能力和教学技术,并有不同的需求、感受和态度;表现不同的行为和特质。而这些转变会依循一定的模式和形态,呈现可预测的发展阶段(Burden,1982年)。”[30]
作为已有的研究之总结,我们应该提及英国教育社会学家班克斯(Olive Banks)。她在其《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对西方新近的教师社会化研究结论作了归纳。[31] 嗣后,台湾已故的著名教育社会学家林清江对此作了阐释,[32] 吴康宁对此已作了应用。[33] 这里将林清江的阐释摘录于后:
(1)师资养成教育时期,是培育成熟教师观念的重要阶段。
(2)成功的师范生的表现与成功的专业行为表现,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关系。
(3)师范教育机构的“教育水准”与“学生态度改变”两者之间,具有直接关系,但这些新态度的维持时间很短。
(4)教师任教数月后,教师态度与学校同事的相似性,便高于其与受教学校的相似性。
(5)任教学校显然比受教学校,更为教师社会化的重要影响机构。任教学校的校长、同事及学生,都是教师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6)师范教育中所培养的教师角色观念,常与课堂中的实际事实不一致。
(7)教师角色的不明确,会影响教师在课堂中所表现的行为。
(8)教学团体的次级文化与教师的社会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的依据和8项结论,可谓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点。但是,我们不应低估教师社会化过程的复杂性。教师社会化“显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历程,绝对无法藉用单纯的、单一因素的参考架构便能得到充分而周全的理解”。[34] 教师专业发展在理解上的难点至少可概括为两个。
首先,应凸显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哪些阶段?
教师专业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在国内外学界似都未达成初步的共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变为“应凸显教师专业发展的哪些阶段”?研究文献显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起始阶段”、“教育见习与实习阶段”及“入职阶段”近几十年来在境外已日益受到关注。这并非偶然。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起始阶段”从何时算起,虽然在国内外都尚未有定论,但一般都承认在接受正规的师范教育之前形成的各种个人经验乃是影响教师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在个人经验中,有一些是有益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也有一些是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而且其中有些经验还不易得到改变。有论者甚至认为,最完美的职前师范教育仍无法与个人的主观经验相抗衡。[35]
关注“教育见习与实习阶段”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容易界定”之外,更主要的是这种活动具有课堂学习所难以取得的效果。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实证研究业已证实,教育实习对实习生的教学观、儿童观和教师职业观有积极的影响。前几年的资料显示:美国有51个州中已经有46个把教育实习列为中小学教师资格的申请要件。[36] 然而,“教育见习与实习阶段”往往却因经营不善而在实际功能上适得其反,[37] 充其量也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因此,怎样组织这一阶段才是问题的关键。
至于“入职阶段”的重要性,则在第45届国际教育会议(1996年9月30日—10月5日,日内瓦)的建议中已有简要的说明:“应对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给予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最初担任的职位和从事的工作将对其以后的培训和职业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应在他们任教初期就实行监护制度与专业指导。”[38]
显然,凸显上述三个阶段,丝毫也不意味着今天就必须使之从“预期职业社会化阶段”和“继续职业社会化阶段”中剥离出来单列为三个阶段,更不意味着它们一定比其它阶段更重要,而只是藉此想说,这三个阶段因长期被“淹没”在“预期职业社会化阶段”和“继续职业社会化阶段”中而未得到足够研究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次,教师专业发展中是否存在“危机阶段”?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所奉持的基本观念和立场是:每一个教师都是在不断的成长与发展中,后一发展阶段通常比前一发展阶段要成熟。最近,有论者归纳另外一些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后发现,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教师是能够不断追求自我实现和专业成长的人,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很多教师可能会遭遇挫折、沮丧而停滞不前,需要多方面的帮助。这一阶段,现在被称为“职业挫折阶段”、“重新估价时期”、“危机期”和“厌倦期”等。[39] 这一发现颇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此类研究至今在我国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
目前,此类研究固然要关注“危机”的成因与对策等,但首先需要研究的还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着“危机阶段”吗?诚然,社会学中的角色冲突理论,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假设。在美国开展改革的系统中工作的教师“经常发现他们自己的专业发展需要与学校或学区的专业发展需要不同”,[40] 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然而,归根结蒂是要在这方面对我国开展实证研究,以更具说服力。
除上述两个“理解上”的难点之外,还有“应用上”的难点。例如,是否应该为教师专业发展各阶段制定相应的专业标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之不同如何让教师把握?对入职后处于不同的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师,是否应设计内容、方式上不同的培训方案?如此等等。当然,就此而进行的研究也不是没有,但能称得上相当坚实可靠的解释毕竟还远远不够。
可以预期,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将随着教师专业发展在“理解上”和“应用上”的难点之解决而逐渐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标签:教师专业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