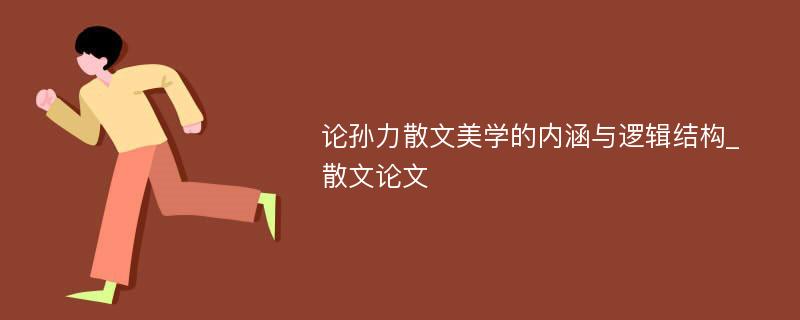
论孙犁散文美学的内涵和逻辑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散文论文,内涵论文,逻辑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犁之所以在晚年成就了一位“真正的散文大师”(黄秋耘语)①,与他一生都是创作与理论、评论并重,晚年很好地实现了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探讨的良性互动不无关系。孙犁关于散文美学的论述,深深植根于自己痛切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散文创作实践所孕育,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现代散文的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提炼了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欧阳修、鲁迅散文的精华,从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从孙犁晚年对中国古代、现代散文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述看,他是认同传统的“大散文”观的。他晚年所写的《晚华集》、《曲终集》等十部散文集,除了记事、写人、抒情、记游文字,还有序跋、书简、读书记、书衣文录、评论、杂谈等形式。他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一文中,指出:“散文是我们祖国主要的文学遗产,古代作家的主要著作,也是散文。”“散文的大部分,都是应用文,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是很多的。”②这就表明:孙犁在观察和研究散文的时候,襟怀和视野是十分宽阔的,是以实际人生为大背景的,是不囿于单纯的文学意识的。这一视野的可贵在于:它的取得,使孙犁在进行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研究之时,避免了单纯就文体论文体之弊,而将散文写作活动与实际人生从根本上打通,站在了人生整体、时代与历史文化的制高点上。散文创作要“质胜于文”,正是他坚持“大散文”观,即以人的整个实际生存为依据的广义散文观,所必然会有的一种审美价值取向。那么,在散文问题上,孙犁是否不具备自觉的文学意识,将文学散文与一般的“文章”混为一谈呢?则又不然。
我们看到,孙犁在认同广义散文观念的同时,又十分强调散文作为文学体裁的艺术与审美特点,而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又是以通常所谓的“狭义散文”为其着眼点的。孙犁有一个十分新颖的见解: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惟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外国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历代散文名家,所作均属寥寥。即以韩柳欧苏而论,他们的文集中,按广义的散文算,还常常敌不过他们所写的诗词。在散文中,又搀杂着很大一部分碑文、墓志之类的应酬文字。”③显然,在此,他又是以“狭义散文”即文学散文的眼光看问题的。他发现:“历史上,很少有职业的散文作家”;“所以,我们的课本上,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篇。”④文学散文眼光的贯彻,必将使作家们所写的一般性应酬文字、学术性文字淡出孙犁这里所说的“散文”范畴。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孙犁深入地考察、研究了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美学特征,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实质。他深刻指出:“散文不能多产,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⑤(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此,“题材难遇”是最主要的原因:“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这些内容,是不能凭空设想,随意捏造的。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⑥按上述标准看,鲁迅一生所写的散文,就是《朝花夕拾》集所收10篇,及收入杂文集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阿金》等很少几篇;孙犁晚年所写的狭义散文,其数量约占《耕堂劫后十种》总篇数的五分之一。
或问:孙犁的广义散文即“大散文”观,岂不与上述看法相悖吗?
答曰:看似抵牾分张,实则两虑而一致。
众所周知,在各种文体之间,在文学体裁与日常应用性的文章体裁之间,都存在着模糊性、过渡性、交叉性,会出现亦彼亦此、难分彼此的状况。对于散文这一文体大类来说,情况更是这样。如前所述,散文的大部分是应用文,就这部分散文而论,写起来可以不具备文学性,同样也可以具备文学性——问题的焦点在于作者的艺术修养的有无高下,看其能否将某些应用文写成“美文”。对于这样一些尚有待于在写作实践中去判定其是否具备文学性的应用性文字,与其将其逐出散文领域,毋宁将它纳入散文的版图。为孙犁激赏的《出师表》、《陈情表》、《陇冈阡表》,其文体不就是古人章奏之一体的“表”吗?而司马迁脍炙人口的《报任安书》,不也是作为应用文的书信吗?可见,以灵活、宽泛而又包容的态度看待散文,认同一种“大散文”观,是符合中国散文史的实际的;这样做,为文学散文的兴盛,预留了广阔的地盘。如果某些应用性的散文篇章,写得毫无文学意味,那它们就没有进入文学散文的“入场券”。在此,表面上的标准是宽容、流动的,内骨子的标准却自马虎不得。这正是中国人在对待散文文体时,所体现的一种传统性的人文智慧。
有的散文理论家认为“表现自我”是散文的文体特质,有的狭隘地将抒情散文作为狭义散文。孙犁指出:“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⑦这就有力地批评了那种一味强调散文要“表现自我”和狭隘地突出散文的抒情特征,要“净化散文”的观点。
那么,孙犁心目中的狭义散文到底是什么样的散文呢?
概括言之,他心目中的“狭义散文”,就是他在《散文的虚与实》一文中论述“散文不能多产”时,所说的以“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为题材的散文。不言而喻,这类强调亲身经历的散文,可以是记人、记事、写景的,也可以是抒情的,其内含比单一的抒情要广泛得多。同时,三个“亲身”的强调,分明将叙事的因素包括了进去,这便使狭义散文的根基变成了复合性的、可生发性的,不让抒情一途独专其美。如此看来,孙犁也是讲“狭义散文”的,但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要比当代一些散文理论宽阔得多。“狭”而能“广”,正是“狭义散文”沟通、烛照与统摄“广义散文”的内在机制。
总括起来说,认同“大散文”观,可以极大地开拓散文领域,开凿实际人生通向文学散文的宽阔通道,消除人为地设置的文体障碍,同时,为应用性文字向文学散文的跨越预留了地盘。另一方面,划分出狭义散文,便于突出散文的塔尖,有助于集中地概括文学散文的审美特质,从而,如上所说,对广义散文进行烛照、渗透与统摄。“万物负阴而抱阳”,⑧狭义散文与广义散文的关系,亦当如是观。
孙犁用对中国散文审美创造规律的总结与阐发,激活了他对散文的整体研究,并以之为轴心,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散文理论框架。
1982年,孙犁在《〈孙犁散文选〉序》中指出,散文的“道理”有三:一、要质胜于文;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三、文字、文章要自然。⑨1983年,孙犁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强调:“应该从历史上,找出散文创作成败得失的一些规律”;他简要分析了散文史上千古传诵的“三表”(《出师表》《陈情表》《陇冈阡表》),指出“从我们熟读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凡是长时期被人称诵的名篇,都是感情真实,文字朴实之作”,“就散文的规律而言,真诚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⑩同样的意思,在同篇中他又以“感情的真挚和文字的朴素无华”来表述。1984年,他在书信中说“我以为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二曰含蓄”。(11)1985年,孙犁在一篇评论中,强调“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12)1986年,他在文学书简中指出:“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作为对“避虚就实”的补充,他说“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如《兰亭序》,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13)1992年,孙犁在致《美文》主编贾平凹的信中说:“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语法修辞。”(14)——以上,是我们对于孙犁有关散文创作规律论述的摘要。可以看出,孙犁对于散文创作规律问题的看法,前后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在美学理论的论域下,显得更加趋于严整、深刻。笔者在反复梳理、归纳、整合孙犁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初步勾勒了其散文美学理论的逻辑框架:
总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
美学理想或境界:自然(包括情理兼备)
襟怀:所见者大要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
中心范畴:真情实感
语言美质:朴实 含蓄 简练
基本功:语法修辞取材者微一细节的真实以上所列各项,在整体逻辑框架中,分属不同的层次,而又相互勾连、渗透,浑然有机,构成一体。本节所要论述的,是作为孙犁散文美学的逻辑基点和中心范畴之“真情实感”。
如上所述,孙犁是将“真情实感”置于散文创作规律的首要位置的。这是作为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真实性”这一美学范畴——在散文文体上的具体体现。一般而言,小说、戏剧将人物形象的塑造,诗歌将意象、意境的营造提到了文体的首位,这方面的成就往往成为对它们进行审美创造衡量的尺度。散文文体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孙犁所说,它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有其“更直接的现实性”(15)。这一点,使散文丧失了如同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可以自由地展开艺术想象(虚构)、运用更多的艺术技巧的可能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将对一切文学体裁普遍适用的美学要求——“真实性”浓缩简化为“真情实感”用于散文,一方面既与小说、诗歌的“形象”“典型”“意象”“意境”有所区别,又将散文的日常性、应用性提升到了艺术与审美的层次。要之,散文文体的日常性、单纯性,决定了其美学尺度不可能像小说、诗歌的美学尺度那样多变与复杂。在小说,无论是其理论或实践,它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关系,一直很难把握。而不能虚构,使散文避免了这层烦难。面对一篇散文,有社会经验的读者,不难凭直觉判断其有无真情实感。因之,将“真情实感”作散文基本的审美特质和要求,可谓:顺理成章,固当如此。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孙犁提出的上述命题,其内涵却是异常丰富、深邃的。
为何要标举“真情实感”?归纳孙犁的说法,一是为了“取信”于读者,二是为了感动读者。历史一再证明,内容虚假的散文,是没有读者的。孙犁指出:“文章能取信于当世,方能取信于后代。”“文章要感人肺腑,出于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不会是阿斗。你有几分真诚,读者就会感受到几分真诚,丝毫作不得假。”(16)这就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讲清了“真情实感”于散文的重要性。
与上述命题相关联的另一问题是:散文在题材上要实。孙犁指出:“我……以为散文还应该写得实一些。即取材要实,表现手法也要实。就是写实际的事情,用实际的笔墨。”(17)“散文要眼见为实……处处有根据”。(18)他将“中国散文写作”最主要之点,归结为“避虚就实”。(19)这样,就使“真情实感”有了着落。孙犁的这一命题,具有现实针对性。建国至今,散文领域,一直存在着“凭空设想”、“随意捏造”的作品。
那么,怎样才算写出了“真情实感”呢?孙犁指出:“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20)这就为读者对散文的阅读感受提供了一条理性的参考尺度。孙犁举《陈情表》的例子说:“李密当时的处境,尤其困难,如果他不说真情实话,能够瞒过司马氏的耳目?”(21)正因为《陈情表》坦诚地写出了作者的复杂处境、尴尬身份、矛盾痛苦的思想与心情,以及与家庭、政局的关系,感人至深,才使这篇散文成为千古名篇。
在孙犁看来,“真情实感”并不是一个纯理论(文艺学、美学)问题,而更主要地是关乎政治文化制度、社会实践和个体生存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22)他从历史上看到人类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以及文人并不理想的生存环境,痛切地认识到说真话之难,屡屡为之感叹唏嘘。他又指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因为是私人信件,并非公开流布的文字,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真心话,才成为千古绝唱。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说了些真心话,透露了出去,就招来了大祸害。有鉴于此,致使文人执笔,左顾右盼,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23)谈到日记这一形式时,孙犁指出:“(它)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24)出于怕招祸的心理,孙犁在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后,将不少书信烧毁了。他晚年在散文中如实叙写了亲身经历的一些人事,尽管下笔时注意分寸,竟也得罪了若干朋友。按道理讲,一位作家将他一生中心灵最受震撼的事件,最受感动的事情、场景写下来,这既是他应有的创作冲动,又是读者的殷切期望。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的主客观原因,这方面的作品在历史上的数量并不太多。常见的情况是,不少散文作家执笔为文时,往往颇费踌躇,自觉不自觉地挑选那些与是非、利害关系不甚大的题材写。说透了,这种做法,是作家在安全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这两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之间寻找平衡点。在这种情况下,固然散文作品也可能写出“真情实感”,但从个体的生存整体看,此种“真情实感”毕竟是经过过滤的,残缺不全的。
社会环境、生存条件包括文坛状况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在探讨文学各大文体的理论包括美学理论时,不应该孤立地就文体谈文体。除了客观条件,散文作家要在作品中写出“真情实感”,还与自身的思想意识、人格修养和创作用心有关,这是主观上的前提。作家如果以追名逐利为务,将创作看作晋身之阶,那么,他只能追风逐潮,写出内容虚假的散文。在这方面,孙犁律己甚严,他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为人愚执,好直感实言,虽吃过好多苦头,十年动乱中,且因此几至于死,然终不知悔。”(25)
有论者认为,“‘真情实感’说到底只是作家职业道德的伦理规范,而非审美规范”,赞同用“真实性”替代“真情实感”而作为散文的本质特征之一。(26)判“真情实感”只是“伦理规范”而非“审美规范”的论断,似有不妥。因为,我们所说的“真情实感”,并非普通人日常形态的“真情实感”,而是与散文作者、作家,与散文创作的审美过程,与作为文学文本的散文作品相联系的“真情实感”。它在创作主体与社会现实(题材)建立审美关系的过程中产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由日常型态向艺术型态和美感型态的升华;我们能因为它里面包含着伦理观念,就要把它逐出“审美”的大门吗?“美与善连”(孙犁语),人的意识的各种成分构成一个整体,要人为地将某些美学观念完全与伦理规范截然划分,痛快倒是痛快,可惜解释不了创作的实际问题。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心理机制有别,他们的审美意识与伦理意识之间,在更高的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潜移默化的,难分难解的;人格与文格之间,除了相互统一的一面,如孙犁所说,还有相互提高的一面。古代散文名篇不必说,我们能说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朱自清的《背影》所表现的“真情实感”,不正表征了一种美学尺度,显示了散文文体基本的审美特质吗?
如上所述,散文文体由于其本身的日常性、应用性、写实性所限制,它无法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更为全面地体现艺术的本质(如艺术虚构、想象的自由驰骋,多种艺术方法、技巧包括愈出愈奇的艺术方法与技巧的运用),也不可能在诸如形象、典型的塑造,人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揭示,意象和意境的营造,戏剧冲突的描写等方面与别的文体媲美。也就是说,散文的日常性、应用性与写实性,与艺术的假定性、超越性发生了背离,它只能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与“剥夺”(如艺术虚构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的情况下,在艺术与审美上另辟蹊径。这样,就像上文已经论证过的,像孙犁所反复揭示的:“真情实感”便成了文学散文这一文体最基本的艺术与美学特质。这才是散文在艺术和美学上的主要目标。这符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散文“易学而难工”的道理。既然像小说、诗歌、戏剧所凭借的不少审美之途被堵塞了,散文文体似乎被注定了只能通过“真情实感”和文字这两条途径进入艺术与审美之畛域。学者陈平原有见于此,曾指出:“散文应该立足的是文字,不是情感与想像。”(27)
细究起来,各体文体对文学语言运用的取径和要求是区别不小的。诗的语言要求高度精炼、富于节奏感,长于“比兴”和“取象”;小说语言,涉及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复杂得多;戏剧语言,则除了附加的说明文字,全是人物对话,舞台表演性决定了它在更高的程度上必须更为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剧情,并与动作融为一体。适应着这种不同的取径和需要,人们创立了“诗学”、“小说叙事学”、“戏剧理论”等专门学科,使之成为一种学问。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对散文语言的运用,多有探讨,可惜往往比较零碎,琐细,多限于字、句的技巧性分析,缺乏整体性的提炼、统摄,从而很难上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在散文语言研究方面,与同时代的其他散文作家相比,孙犁得天独厚,具有相当的综合优势:一、他从小对语言敏感,包括对家人、老师的语言和京剧唱词都很敏感;二、私淑鲁迅,在思想、情感、文字上,都有所师承;三、创作上基本上以小说和散文为两大主要文体,而其小说无论长、中、短篇,都是“散文化小说”,这积淀为全面、深厚的艺术素养,特别是散文写作的基本功,包括记事、写人的技能和语言功力;四、中晚年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史古籍,受到了古代汉语的深度熏陶;五、晚途,专攻散文一体,歌哭、献身于斯,饱蘸着生命的汁液,写出了异彩纷呈的十部散文集子,同时钻研中国古代散文名家的生平、思想、作品,深味其文字,并且研读了中国古代文论若干名著,从中获益匪浅;六、一生分心于美学理论的学习与探究,具有较浓厚的美学意识。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安定,得享遐龄,有在这方面探讨的兴趣,遂使他在散文语言研究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些古代散文家、文论家,并不逊色多少。
在这方面,孙犁的中心论点是:散文的文字要“朴实”。以“朴实”的要求为最根本、最重要,与之并列的是“含蓄”与“简练”。在散文文体的第二个美学特征的方位上,这三个方面,又构成了一个相互生发、渗透、补充的整体。以下,我们依次论述这三个要点。
一、朴实。如上文所述,孙犁将文字朴实视为散文的规律之一。他曾指出:“我写文章从来不选择华丽的词,如果光选华丽的词,就过犹不及。炉火纯青,就是去掉烟气,只有火。这需要阅历,要写得自然。”(28)其实,“朴”是道家道论和审美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道”的一种属性,其含义与“质”“素”“天”“真”“淡”“无为”相近相通;所谓文字朴实,就是发自内心,本色自然,蔑弃雕饰浮夸。孙犁的气质近于道家,受道家哲学、美学的影响较深。他以诚临文,明乎创作要表现真情实感,决不能颠倒宾主,以词藻华丽为务:“一心去寻找漂亮的形容词句,只追求俏皮华丽,堆砌起来,结果把要表现的事物蒙蔽、埋葬了。”(29)孙犁洞悉华丽词藻对事物的本真(“质”“朴”“神”)之遮蔽作用。这正是他深邃的审美目光的表现。《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元好问也有“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名句。实际上,文字朴实是以“真情实感”为前提的,而“真情实感”又须以朴实的文字来表达。在谈到散文语言的重要性时,他指明:“……当然语言文字也与作者的真情实感紧紧相关。”(30)这就说明:对于孙犁所提炼和反复推阐的散文美学的这两大要点而言,一失而俱失,相得而益彰。
孙犁强调,文字的朴实,“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的素质”,(31)他所举的例子,是司马迁、班固和韩柳的散文。
二、含蓄。如果说文学作为艺术,在艺术和审美构成上应该具有含蓄的特征,那么散文文体由其自身的日常性、应用性所可能带来的过分清楚与直白,则需要在文字运用上格外注意含蓄,以便通过这一必要而且可能的途径来消解和提升,从而获得文学的艺术特性。孙犁曾将“感发”与“含蓄”作为散文的二个规律。“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32)这说的实为“真情实感”问题,情郁于中,感发于外,归于真实。“朴”有本真、内敛之义,故而,“含蓄”与“朴实”相需为用,在审美取向上是一致的。关于“含蓄”,孙犁说:“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谈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33)“散文如果描写过细,表露无余,虽便于读者领会,能畅作者之所言,但一览之后,没有回味的余地,这在任何艺术,都不是善法。”(34)显然,标举“含蓄”,孙犁正是为了坚持散文的艺术和审美特质的,是为了指向“贵玄远,求其神韵”(35)的审美境界的。
三、简练。孙犁曾指出:“我国文学一贯提倡短小,以简练为贵,这是我们祖国文学很好的传统。”(36)“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37)在他看来,正是文体自身的性质,决定了“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要求它在文字上“讲究漂亮”,(38)要求作家具备行文简练的艺术功力。孙犁将“文字简净,叙述明快,结构也不拖拉”视为“散文的基本功夫”,(39)其中后二点从表达方式和结构着眼,但实质上都无不与“文字简净”相关,是其实际展开。为求简练,孙犁提出要将语言看做“黄金之锻”,千锤百炼。实现文字简练的途径主要有:力戒“描写过细,表露无余”;叙事“以简要为主”,不要节外生枝;游记“要眼见为实,文献引用不要太多”;“要对口语加番洗炼的功夫。好像淘米,洗去泥沙;好像炼钢,取出精华”,“洗去那些不确实、紊乱的成分”;(40)“抒情也要有所控制”;(41)考证文字,“需要简明、具体”,“并读着有兴味”。(42)文字上做到“简练”了,散文在形体必显得“短小”。孙犁曾将“形体要求短小”作为中国散文的文体特点之一。可见,散文的文体特征与审美特征,是相需为用,相互支撑的。
朴实、含蓄、简练,孙犁对于散文文字所要求的这三个方面,是通于“真情实感”这一大前提的,是以他崇尚的“自然”这一美学境界为指归的,是三位一体、难分难解的;不过,三者之中,实又以“朴实”为基点。孙犁的这些论述,包蕴着浓郁的审美意识,如他说:“文字的简练朴实,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的素质,不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43)
散文作家要做到文字的朴实、含蓄、简洁,必须在文字运用方面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方面孙犁有两点看法,值得注意。一、讲究修辞语法。他指出:“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44)“语言是一种艺术,除去自然的素质,它还要求修辞。”(45)不言而喻,“修辞语法”正是获得文字表现能力的手段。孙犁强调:“有词不一定有诚,而只有真诚,才能使辞感动听者,达到修辞的目的。”(46)他深知,修辞学作为一门学问,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体会学习。他十分赞赏欧阳修的散文:“在文章的最关键处,他常常变换语法,使他的文章和道理,给人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47)孙犁的散文名篇,适应文章中的具体场所和语境,出色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婉转等修辞手法,强化了文字的表现力。二、重视细节真实。孙犁严肃地批评一位朋友为他所写的记事文多有细节失实之处:“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48)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为现实主义小说家普遍重视,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散文为其直接写实即不能虚构的性质所决定,不可能也无必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这样,它退而求其次,讲究细节真实。将细节描写的重要性(关乎整体真实)与真情实感在散文美学中加以突出的强调,正是孙犁在散文理论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他总结了传记写作的特点,曾将“大节与细节并重”作为一大原则。
与细节描写并立而又相互交织的另一命题是:“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免人所共知的大事。”(49)在此,关键在于“人不经心”这四个字。人不经心我经心,捕捉、选择习见的小事,从中开掘开思想意义,发现和提炼艺术意味,这正是散文作家应该具备的眼光。他多次强调上述命题,如说:“最好是多记些无关重要的小事,从中表现出他为人做事的个性来。”(50)通过记小事来表现人物的个性,乃至反映时代风云、习尚。正像孙犁所说,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欧阳修“主要的经验,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51)他的上述命题,将艺术“以小见大”的特性,具体、明确、恰当地落实于散文文体。在散文创作中,娴熟地表现出这一功力,其实是很难的。他在《谈美》一文中,指出:“艺术家的特异功能,不在于反映,而在于创造。不在于揭示众口之所称为美者、善者,是在能于事物隐微之处,人所经常见到而不注意之处,再现美、善;于复杂、矛盾的性格中,提炼美、善。”(52)可见,发现事物的“隐微之处”,并对之进行艺术开掘、审美观照,是艺术家的“特异功能”,而由于散文文体受到了“取材要实”等限制,在这一审美构成和审美机制上自然应更加强调。进一步说,善于发现和阐释“事物隐微之处”,正是道家哲学和美学的优势,孙犁擅长于此,一个重要成因是受到了道德哲学和美学的深深沾溉。
在散文美学境界的取向上,孙犁标举“自然”。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美学追求,统摄、涵盖了散文创作的各个环节,包括作家的艺术素质、创作用心,文本的审美构成和美学效果。“取材要实”,写“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不然“就会不自然”;(53)文字,要自然,“出于真诚”;(54)技巧以“顺应自然为主导”,“如果游离于艺术的自然行进之外,只是作为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其价值就很有限了”;(55)叙述上,“应求自然”。(56)上文曾提到孙犁的基本美学命题:“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究其实,这是受了中国传统的道家崇尚“自然”的美学观深度熏陶和滋养的结果。诚然,在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中国作家的审美早已发生了现代转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念和手法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在散文领域,也有所谓“新潮散文”的出现,并有相应的理论探索。但有几点,似须注意:一、正如学者楼肇明指出的,“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于其它文类”,它对自身传统的反叛不像其它文类“那么强烈和激烈”,“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呈阶梯性前进。(57)因此,孙犁侧重于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更多地从古代散文总结中国散文美学,并非没有现实意义。西方的、现代性的散文创作经验,总得与中国的东西相融合。如果说,孙犁晚年的散文美学,缺乏应有的开放性,这倒是事实。这与他中晚年对国外的散文创作没有较多接触有关。二、一些理论家谈创作,制造“主义”,牵强附会,玄奥莫测;一些作家谈创作,反倒不能从实际出发。这种情况决定了,探寻在散文美学的建树方面迥出众流者,似乎只有瞩望孙犁这位在散文创作上获得了大师般的成就,又在理论探索上深有素养、久有志趣、且能实现创作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另辟蹊径的散文大家。众声喧哗是好事,但需要冷静,沉淀,审辨。三、孙犁的散文美学,有他对众多分支体裁如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游记写作要点深入把握的支撑,故而显得根基牢固,毫无空泛之弊。他对中国古代散文各种体制的写作要点,均下过一番钻研的功夫,并参照古代名家的论述,含英咀华,作为创作和研究的修养。他明确要求,散文作者“首先应该涉猎中国散文的丰富遗产,知道有多少体制,明白各种体制的作用,各类文章的写特要点。”(58)他对传记一体写作要领的论述,尤其精辟、深刻,许多观点发人之所未发,整体性极强。其要点是“四并重”(记言记行、大节细节、优点缺点、客观主观并重)和“五忌”(恩怨感情用事、用无根材料、轻易给活人立传、作者直接表态、用文学手法)。(59)还有游记,他提出游记之作,“不在其游,而在其思”的命题(60)。真可谓:无所不窥,用力甚勤,惨淡经营。
总之,孙犁晚年的散文美学,内容丰富深邃,造诣很深,在当代文学史上,异彩纷呈,引人注目。它既被包容于作家整体的美学理论,又具备自身潜在的、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它以“真情实感”为逻辑基点和中心范畴,以“真情实感”和“文字朴实”为两大主干,以语法修辞,细节真实和写“人不经心的小事”为艺术和审美的基本功,以各分支体裁的写作要领为依托,以“自然”为审美取向和美学境界之追求,以现实主义为总体的创作原则,从而构成一个浑然的有机整体。
注释:
①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②(15)(16)(25)(30)(41)(51)(53)(58)孙犁:《远道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4,132,196,137-138,207,136,138,139页。
③④⑤⑥(12)(19)(37)(38)(39)(45)(54)孙犁:《陋巷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7-228,228,228-229,275,228,264,229,278,205,205,190页。
⑦孙犁:《澹定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⑧《老子·四十二章》。
⑨⑩(11)(13)(20)(21)(22)(23)(32)(33)(34)(35)(47)(52)(59)孙犁:《孙犁选集·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207-208,214,217,207,207,208,208,214,214,214-215,97,441,96,231-234页。
(14)(44)孙犁:《曲终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6页。
(17)(49)(50)孙犁:《无为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1,260页。
(18)(28)孙犁:《尺泽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7页。
(24)孙犁:《秀露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26)楼肇明:《序:沙盘·平面图和当代散文研究的整体性思维》,见梁向阳:《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27)陈平原:《散文的四个问题》,见江力琼虎主编:《中国散文论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9)(36)(40)孙犁:《孙犁文集4·理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72,69页。
(31)(43)(46)(56)(60)孙犁:《老荒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2,46,238,133页。
(42)孙犁:《芸斋书简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48)孙犁:《如云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57)楼肇明:《〈世界散文经典〉序》,见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