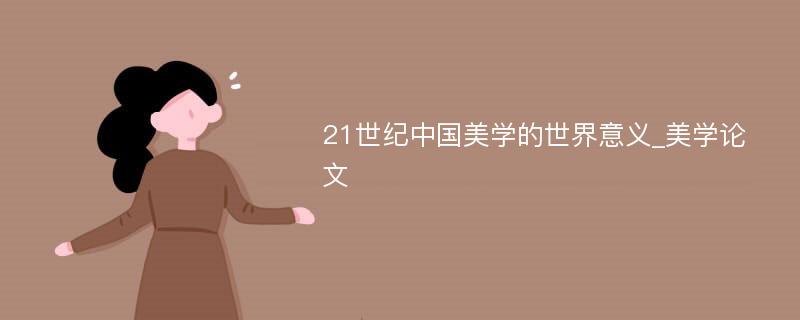
中国美学在21世纪的世界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性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4)05-0106-05
“西方”通常都被人们看成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美学的最初发源地。所以,20世纪的许多亚洲学者,往往在西学东渐的大势所趋之下,倾向于按照西方美学传统的基本模式来考察各种美学问题。但实际上,亚洲各国也有它们自己的与西方很为不同的美学传统。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美学传统的比较性考察,探讨中国美学在21世纪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一
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美学传统之间的鲜明反差,深深地植根于它们在哲理精神方面的根本区别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地体现出“认知理性”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哲学传统则主要地体现出“人为情理”的基本精神。[1]P(33-56)因此,它们总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和解释人与世界之间的种种根本性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与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
基于认知理性的哲理精神及其蕴含的主客二分倾向,西方美学家们总是倾向于把“美”首先看成是外部世界中客观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某种令人愉悦的属性,同时把“人”首先看成是能够通过感性或理性的认知活动去感知或观照美的客观对象的“审美”主体。例如,亚里士多德主张,“美的主要形式就在于秩序、均衡和体积上的大小,这些在数理科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美涉及到一种认知的功能,因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的。”正是置身于这样一种传统之中,鲍姆加通才会把美学明确地定义为“感性认识学”,也就是所谓的Aesthetica;这一名称最清楚不过地打上了西方哲学传统认知理性精神的深刻烙印。康德和黑格尔尽管已经注意到了美与人的存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仍然坚持认为,美在本质上是人的某种主体状态在外界事物中的“对象化”表现,即所谓美是“道德感的象征”或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与此相应,西方美学家们也总是将“艺术”首先看成是人们认知外界客观事物的一种特定方式,特别强调它的认知功能,甚至根据艺术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真理性关系来衡量和评价其价值意义。有关艺术的“模仿说”之所以能够在西方美学史上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例如,柏拉图强调好的艺术“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亚里士多德则把“美的艺术”称之为”模仿”的艺术,并且主张:“艺术在本质上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态,其中就包含着真正的推理进程。”康德一方面认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另一方面又宣称:“天才就是典范性的创造力,是主体自由地运用其认知诸机能的天赋才能。”黑格尔也坚持认为:“艺术的本质功能就是以艺术的感性方式揭示‘真理’。”诚然,许多西方哲学家也经常提及并且探讨了艺术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不过,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艺术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关系却显然在本质上优先于前者,因而也受到了更多的强调。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认知理性的哲理精神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美学家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审美关系的界定和探讨。
相比之下,基于人为情理的哲理精神及其蕴含的天人合一倾向,中国美学传统并不只是把“美”看成是外界事物自身具有的某种令人愉悦的客观属性,而是首先将“美”看成是人的存在本身在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统一中所达到的某种自由状态或方式(“道”)。因此,对人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仅仅通过认知活动去感知或观照外部世界中美的客观事物,而是通过人为情理的活动去美化人自身的存在、使人的存在达到美的层面或境界。例如,在儒家美学中,孔子就反复主张:“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荀子则将美明确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人为活动(“伪”)之间的有机结合,认为“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易传》强调“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同样也把美归结为君子修身养性、建功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弘大事业。道家美学通常都把美视为人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存在中实现的与天地自然的素朴而和谐的统一。庄子明确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换句话说,天地之大美就在于它们那种“道法自然”的“无为”特征;因此,人们如果能够体悟天地自然的这种无为本性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同样以“无为”作为自己的存在范式,当然也就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禅宗美学特别重视美与人的情感之“心”的内在关联,主张“无情无佛种”,认为每个人都能在日用伦常中通过实现“自性”而成佛致美。简言之,中国美学传统的三大主要思潮,都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人的存在状态自身的美之上,而不是放在外部世界客观事物的美之上。
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中国美学传统同样强调了艺术在人为活动中、乃至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表现人的情感志向的本质功能和重要意义,却很少涉及艺术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功能。早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尚书·尧典》中,就出现了一句名言:“诗言志”。孔子也指出:“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明确地把音乐归之于仁人之情的抒发表现;这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把音乐看作是数的比例和谐的观念迥异。此外,孔子还特别要求弟子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从而充分地凸显了艺术在个体道德完善和社会政治管理方面的积极功能。古代儒家的另一部典籍《乐记》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主张“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另一方面,道家和禅宗美学更为关注艺术在表现人们的自然情性、实现个体精神自由方面的积极作用。庄子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审视艺术的本质功能,认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禅宗美学则特别强调直觉(顿悟)在艺术与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认为艺术与审美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而是在于最终指向人类生活和精神自由的基本原则。它所主张的人们在“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的日常践履中实现“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与审美和艺术内在相通的自由生存方式;所以,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才会出现“以禅喻诗”或是“以诗解禅”的种种现象。
进一步看,中西哲学传统也总是从截然不同的视点出发,去理解真、善、美之间的相互关系。[2]P(323-338)一般来说,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真”主要是指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本身以及人们对它的真理认识;“善”则经常意指着“德性”,这些善的德性一方面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又在根本上建立在真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而“美”作为客观事物令人愉悦的感性属性,则往往在地位上从属于“真”和“善”。因此,在理性精神的主导作用下,西方哲学传统往往倾向于把沉思真理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或是道德实践的生活(柏拉图和康德)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而很少会把感性审美的生活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传统从人为情理的基本精神出发,更倾向于把真善美三者都看成是人的形而上存在的三个构成维度,即把“真”看作是人们情感生活的一种“真诚”状态,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状态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内在统一;把“善”看作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善良”状态,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状态充分实现人的真诚情性;最后则把“美”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境界以一种感性——情感的和谐方式达到“真”与“善”的有机统一。例如,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做到“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尽美尽善”(《论语·八佾》),以此作为自身存在的理想范式;孟子强调:“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明确主张“美”包含着比“善”和“信”更丰富的内容,是“善”和“信”的进一步扩展充实,所以在人的存在中是一种比“善”和“信”更高的理想境界。道家美学高度评价“美”与“真”在人的存在中的直接而素朴的统一,同样也把这种统一视为人的存在的最高理想境界。因此,庄子明确指出:“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禅宗美学则把佛性本身看作是人生最高的美的境界,主张“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坛经》),认为人们在日常的感性生活中就可以“即性成佛”。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美学”往往被看成是一门有关“感性认识”的科学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学”则首先被看成是一种有关“人自身美的存在”的哲学;这一点可以清楚地表明分别建基在两种不同哲理精神之上的中西美学传统之间的深度差异。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西方美学传统的基本模式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美学传统,势必会导致对后者的严重误读乃至致命扭曲。
二
毫无疑问,由于相对缺失认知理性的哲理精神,中国美学传统无论在理解人的本性和审美活动方面,还是在解释美和艺术的本质功能方面,都存在某些片面甚至严重的缺陷。因此,当代中国美学要想发扬光大并且丰富自身,就必须像20世纪那样持续地、更深入地向西方美学学习。不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美学毕竟具有西方美学相对缺失的人为情理精神,它也依然拥有不少明显的优点长处,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富有说服力、很有价值的深刻洞见。因此,尽管目前在国际美学界,西方美学的理论结构和话语关联仍然占据着主导强势的地位,但中国美学却仍然能够在21世纪的跨文化美学对话中扮演一个富于建构性的自立角色,甚至发挥出其特定的世界性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定义人的本质。众所周知,在人的本质与美和艺术的本质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诚然,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经典定义,人在本质上首先是“理性的动物”;不过,这一定义本身却存在着某种片面性,不足以充分揭示人的全部本质。这是因为,除了理性之外,在人的本质中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根本性的因素,诸如实践、感性、本能、情感、意志等等;它们和理性的因素一样,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审美活动中,这些非理性的因素甚至较之理性的因素具有更深刻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美学传统特别强调实践和情感因素在人的存在中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人首先和源初地是“人为情理的动物”(即能够从事特定的人为活动、拥有属人情感的动物),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为”和“情性”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是两个关键性的范畴,意指实践活动和自然情感(如喜、怒、哀、乐、爱等)构成了人生存在的实质性内容,以至于只有当这些自然情感能够在人为践履活动中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时,人们才能使自己的存在成为本真性的人的存在,才能真正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也正是在这一哲理基础之上,中国美学传统提出了上述那些有关美和艺术的原创性卓越观念,它们在21世纪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实际上,流行艺术、行为艺术、时尚、设计、健美、旅游等等活动日益渗透进和深刻影响着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表明,这些不是认知——理性的、而是实践——感性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正在成为21世纪人的整体性存在的内在构成要素。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如果我们仍然坚执西方哲学传统的认知理性精神,仅仅把人视为一种“理性的动物”,并且由此出发仅仅把美看成是审美观照的客观对象、把审美活动看成是某种与活泼的现实人生不相关涉的静态行为,显然就远远不够了。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人,哪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首先都是美和艺术的积极创造者和审美活动的内在参与者,而远远不是消极被动的欣赏者和旁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像各种实践-感性的活动本来就与人的形而上存在内在相关一样,审美活动也应该在当代人类的生活中具有能动的、本质的重要意义,而不再是某种仅仅从属于理性的、可有可无的人类活动。在这方面,中国美学传统的人为情理精神无疑能够为21世纪人类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灵感和启示,使之真正成为所谓的“实践中的美学”,并且深入探讨上述那些崭新的审美现象及其在当代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看,更重要的也许是中国美学传统的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美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自身的一种自由和谐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真与善以及所有那些属人的本质因素(其中也包括此前为中国传统哲学长期忽视的理性因素),都应该内在地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按照这个观念,美不仅仅是在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中具有单纯审美的意义,而且更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形而上的哲理意义;人也不仅仅是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首先是人自身的美的存在的创造者。事实上,客观对象和艺术作品的美原本就是与人自身美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当人自身的存在首先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达到了美的境界的时候,人才有可能一方面在外部世界中创造出客观的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在内心世界中产生主观的审美心理活动。换句话说,人自身美的存在在本质上构成了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得以产生的形而上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美学传统的上述洞见,将会大大拓宽和扩展21世纪人类美学的理论视界和研究内容,尤其是使其远远超出西方美学传统一方面偏重于研究美的事物和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另一方面偏重于研究审美心理的主观机制的有限范围,从而将其真正提升到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层面。显而易见,如果21世纪的人类美学能够从“美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这一中国美学的深刻启示出发,深入探讨人类能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使自己的存在达到美的境界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它必然会对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诚然,19世纪以来,某些西方哲学思潮也在这些方面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洞见。例如,马克思哲学充分肯定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的本质以及对于美的创造的决定性作用;尼采和海德格尔不仅强调了某些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存在中、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明确要求赋予审美和艺术活动以人生存在的形而上意味,提出了“审美的形而上学”、美和艺术是“此在”本身的“敞开”和“澄明”等观念,甚至明确要求人的存在本身也应该成为审美性的或艺术化的,主张赋予人自身的形而上存在以美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们显然与中国美学传统存在着某些潜在的相通之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哲学思潮毕竟是在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架构之中建构自身的,并且在批判超越后者的认知理性精神时分别体现出实践——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基本精神,它们依旧在不同程度上维系和保持着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人与自然的张力甚至冲突。因此,比较地看,中国美学传统基于其独特的“人为情理”精神,更为注重人的存在的包容性内在和谐的哲理倾向,仍然具有其自身的特定优势,可以对21世纪的人类美学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或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美学传统提出的种种观念,对于21世纪人类美学的发展就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很明显,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在跨文化的美学对话进程中,来自任何美学传统的任何深刻洞见都是不可或缺的,都不应该被边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内在的结合点,以使所有那些来自不同美学传统的深刻洞见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需要全世界的美学家共同合作,付出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
目前,人类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各种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方面,正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问题,诸如环境保护、生态危机、经济发展不平衡、种族冲突和社会政治冲突、乃至恐怖主义等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视点看,所有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种族问题或是伦理问题,而且同时也是美学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危及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谐统一,破坏着人类自身美的存在的形而上根基。21世纪的人类美学应该而且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积极的实践作用,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关键转折点上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美学家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既在理论上让美学成为一种有关“人自身美的存在”的哲学,又在实践中让人的存在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成为一种美的存在。
收稿日期:2004-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