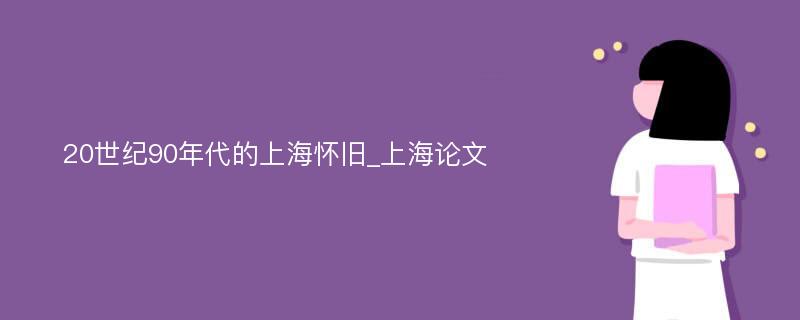
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以来这个一直受着“进步”叙事和时间神话支配的国家里,九十年代发生了有趣的“时光倒流”现象。时髦咖啡馆以“一九三一”命名,旧上海月份牌和旧照片的流行,旧建筑的修复,有关上海怀旧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以及“老上海怀旧馆”的出现等现象,形成了“上海怀旧”的潮流。一九九四年,《上海文化》创刊,二○○一年推出“想象上海”栏目。《上海文学》开辟“记忆·时间”与“上海辞典”栏目。二○○二年,上海大学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档案里的上海》和反映旧上海风情的《城市记忆》丛书出版,《追忆——档案里的故事》、《外滩万国建筑群》等电视专题片拍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放《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主题展》。一九九八年创刊的《万象》杂志,则直接借用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一份刊物的名字。《上海文化》创刊号上《重建上海都市形象》等文一开始便将“怀旧”作为“重塑”上海的一种策略。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带动了上海大规模的街区改造,各种以“怀旧”为营销手段的消费场所开始流行,新天地、衡山路、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区等在怀旧风的吹拂下应运而生,借助“怀旧”赋予城市独特的性格和文化内涵,通过记忆,对其进行想象和规划。
在海外中国学以及台港文化和学术机构助推下,“上海行动”里应外合,联合上演了一幕声色艳丽的“双城记”。像日本的“脱亚入欧”一样,上海借道香港,把自己的记忆写在了“家国之外”,巧妙地回避了“尴尬和耻辱”。上海老诗人赵丽宏在《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中写道:“我住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人的尴尬和耻辱,和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一墙之隔便是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的地方,陈独秀的居所近在咫尺,陈在这里编辑《新青年》杂志。同一街区是京剧大师梅兰芳隐居的地方,抗战八年,他蓄须明志,拒绝在日军占领下演出。不远处是著名的繁华之地“大世界”,当年日本占领上海后武装游行,一位名叫杨剑萍的中国青年,高喊着“中国万岁”,从大世界楼顶跳下,以身殉国。杨是大世界的霓虹灯修理工。诗人提问:“如今的上海人,有谁还记得他?”
上海装载着现代中国的发生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上海记忆”显然经过了删减。在“建筑博物馆”和买办家族的巍峨华丽后面,《建国方略》和《新青年》的悠远回声被过滤掉了;类殖民地的“繁华”掩去了民族主义志士的鲜血和呐喊;正在上演的暧昧的“双城记”里似乎已没有了“尴尬和耻辱”的角色。“乡愁”(怀旧)作为现代性的修辞,密布玄机,因此有必要检省一下“上海想象”的文学建构。
八十年代,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带动示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动了一场“重写”。这次“重写”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地图。通过“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被供奉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圣坛上,大有取代曾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之势。
一九九三年,王安忆以中篇小说《“文革”轶事》发出了强烈的“怀旧”信号。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一部直接向张爱玲致敬的作品。《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长诗。王安忆借用这个题目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悲剧故事。王琦瑶近乎凝固的日常生活穿越了无尽的动乱和荒唐。这是一部张爱玲式的“反传奇”作品。
二○○○年,李欧梵《上海摩登》中文版的出版把“上海怀旧”推向了高潮。李欧梵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那个Light,Heat,Power的世界”,表达了对于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的热情礼赞。“上海摩登”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学(文化)叙事,是一段没有民族主体的文化记忆。在《上海的世界主义》一文中,李将三十年代的上海描绘为“一个世界主义城市”。李感叹,上海这种殖民地的繁荣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如花凋零”,尤其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他怀着浓重的乡愁,重新描绘三十年代的“都市风景线”及其震惊体验。
陈丹燕以惊艳的笔调讲述上海往事而著称,其作品包括《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旧事》、《慢船去中国》等。《慢船去中国》是一部“寻根小说”,叙述一个为美国洋行服务的买办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成员王简妮,费尽心机到美国留学,继承了祖辈的买办事业。通过美国格林教授对这个家族历史的书写,王简妮的个人奋斗进入了家族历史的谱系。格林教授在他的书中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总结东方的买办:他们是世界主义,他们不为民族工作,而是为先进的文明工作。他们推动古老的东方国家走向西方世界。在东西方的沟通中,他们像一道从高处向低处的大河上的水闸,控制着高处的西方文明向低处的东方流动的速度。王简妮毫不讳言买办往昔的辉煌与鸦片贸易等罪恶的关系。因为倚洋自重和极端势利,王简妮被中国同事称为“买办王”。《上海的金枝玉叶》叙述了大资本家女儿戴西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怀旧潮流中,二十年代戴西全家坐在大房子前的合影重新出现在有关旧上海的书里,出现在为白领办的铜版纸的杂志上。戴西年轻的时候随父亲从澳大利亚回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却一直使用英语,人们以为她是外国人。书中这样写道:“而当时要是有人以为你是外国人,就是对你最高的评价。”怀旧态度包含着一种(身份)认同障碍,包含着重建与过去的对话关系的企图。怀旧情绪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赖于某些新的文化力量和新的文化记忆机制的存在。
“上海怀旧”的兴起和上海浦东开发有关。一九九○年,国家启动上海浦东开发,以上海为龙头,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而其重要契机是,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叙事崩溃,冷战结束,“历史终结”,新的激进的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政府提出“与国际接轨”,导致意识形态转型和时空转换。上海空间的重组,必须放到冷战结束后这种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格局剧烈重构的过程之中来加以理解。在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条通往三十年代的记忆走廊被打开了。
上海曾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这是一个多元、异质的空间。上海既是一座殖民城市,又是一座充满革命记忆的城市。它既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也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怀旧是一种社会集体行为,是一种选择和认同。对旧上海的记忆实际上是对新上海的一种想象。而记忆也是一种斗争。记忆同时包含着遗忘。九十年代“上海怀旧”突出上海的“世界主义”特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忆则被覆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甚至被指为民族主义的虚构。著名的四明公所事件的有关记忆和叙述,文明和暴力也发生了倒置。在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中,发生在法租界的四明公所事件被描述为文明与落后的冲突。而在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国人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一书中,则是一方面中国人据理抗争,一方面法国人暴力镇压。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法国人使用暴力,但慑于中国人的顽强抗争而妥协。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妥协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使用武力,任何目的都可以达到。结果,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法国人违背承诺,通过暴力达到了目的。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是这样叙述的:“但贴邻的英国人则对这个办法极不以为然,以为大失外国人的面子。他们以为只要稍为用一些武力,则目的哪有达不到的道理(十九世纪终了时,法国人已违背了这次诺言,仍旧造了一条直穿过这义冢地的马路,将反抗的宁波人开枪打死十二名)。”(《出卖上海滩》,霍塞著,越裔译,上海书店二○○○年版,64页)
卫慧的《上海宝贝》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加入了“上海怀旧”的潮流,同时,它也揭示了“上海怀旧”的根本性质。卫慧是一位宣言“身体写作”的作家。《上海宝贝》不仅是欲望叙事的样本,而且也是一幅权力分布的隐形地图。《上海宝贝》体现了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霞飞路等上海文物,而且德国男人马克也被“上海宝贝”像CK牌内裤一样当做品牌来使用。“上海宝贝”的身体通过不断交换而获得增值。“上海宝贝”和王简妮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她们的身体却界定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海宝贝”一方面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上等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却像妓女一样卖身白种男人。《上海宝贝》是这样描写她们的:“她们脸上有种婊子似的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做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八百万女性中的佼佼者。”
韩少功在《暗示·地图》中指出: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遥远,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地图。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地理概念的主要并不是交通工具,而是财富和权力。远在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出现以前,上海和伦敦、巴黎的距离就比它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距离更近。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是一个人口、财富和权力加速集中的过程。如果说三十年代与上海毗邻的是东京、巴黎、伦敦、纽约这些国际都市的话,那么,革命则改变了这种地理关系。一九四九年后的上海作为工业城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由于回归主权国家和被纳入到国家工业化过程之中,上海失掉了它的“特色”和“国际性”。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如何重塑“世界大都会”的辉煌?上海成为国际港口,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有关,在鸦片战争前,其国内贸易的地位就已经超过广州。但上海真正的兴起与繁荣,却与西方的入侵有关,同时离不开中国的内战和动乱。上海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太平天国起义。持续多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摧毁了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江南古老的中心城市,使财富和人口向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转移,并因此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界限。因此,上海与中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关系。中国越混乱,上海就越繁荣。上海越浮华,中国就越凋敝。同时,上海越“国际化”,它离中国就越遥远。
“上海怀旧”普遍将上海的失落归咎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上海的毁灭却是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九三三年,新中华杂志社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孙百刚在这一题目下写道:“尖锐的对照,极端的膨胀,这些都是趋向毁灭的表现。”管见微对“上海的将来”的看法是:“大减价、绑票、暗杀、共产党的标语、法西斯蒂的传单、各帝国主义者的兵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这些显示着‘上海的现在’。从这些推展开,便是‘上海的将来’了。换句话说,上海的将来,只有在各派混战中而告灭亡。”郑学稼预言:“这虽不是必呈的现象,至少也得为龟蓍式而科学化的预言:上海繁华的寿命,要在一九三六年——军缩条约失效之日——正寝了。”“当太平洋怒潮掀起时,即使上海变为一九一四年的瑞士,仍免不了使诗人高咏‘百代豪华付劫灰’了。”(《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辑,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侵入了上海租界,用暴力摧毁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租界的特权,并且在日本的示范下,西方国家最终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西方和东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伤记忆”,西方的奥斯维辛和东方的古拉格。但这种“创伤记忆”又是与其叙事的中断有关。在中国现代,存在着西方殖民侵略和“文革”互为创伤的两种记忆。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上海租界”这段曾经苦涩的记忆转化成为消费主义上海的一种时髦,一种引以为荣的文化符号和资源。
“上海怀旧”波及大陆、台港和海外华人学者,它为何如此强烈地袭来?“上海怀旧”以“摩登”、“国际化”为中心,上海为何被如此记忆?“上海怀旧”被看做是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历史和性格,然而,“上海怀旧”不应仅在城市文化视域内讨论,“上海怀旧”不是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记忆。“上海怀旧”和九十年代“告别革命”、“与国际接轨”,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五四记忆”与“上海记忆”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另外,中国现代文化的“创伤记忆”由何而来?“上海摩登”能够提供成功的修复吗?最后,还有一个“谁的记忆”的问题。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台港精英和大陆新贵在为这种记忆授权的同时扮演了什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