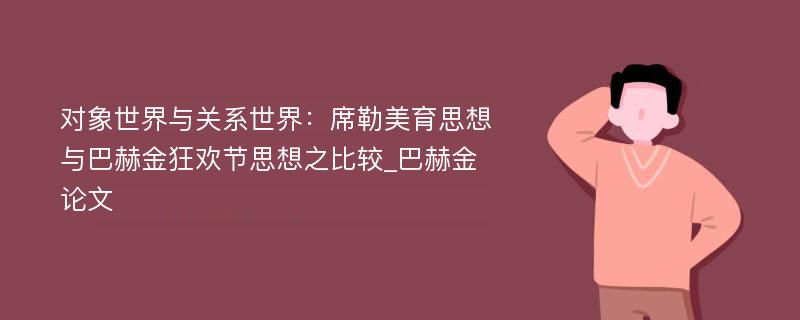
对象世界与关系世界——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与巴赫金狂欢化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巴赫论文,思想论文,世界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60(2002)02-0013-06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可以说是美学史上划时代的理论著作,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1]席勒的这部著作中把美的作用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赋予美以弥合人性本身的分裂、国家和个人的分裂的重要作用,有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他联系拉伯雷的《巨人传》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它们的狂欢节世界感受基础(也可以说是诙谐文化)和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狂欢化世界感受也有着其突出的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和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更为深刻的不同之处,前者在于它们共同的审美乌托邦色彩(或者说人性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者则源于二者不同的哲学基础。正如18世纪的所有美学,席勒的美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哲学思考基础上的,主要是康德的哲学;而巴赫金的哲学基础要更广泛一些,有德国哲学的影响,也有宗教哲学的,后者正是我们这篇论文想着重指出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巴赫金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而深刻的注意,比如他的狂欢化思想,似乎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处找到理论上的呼应,但其实,狂欢化思想和巴赫金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他的宗教倾向)也值得关注。这里主要不是一种明显的神学上的理论传承,而是越过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的思想上的和宗教的联系,所以称之为宗教倾向。狂欢化理论想建立的这个世界可以称为关系世界,以区别于席勒的对象的世界。
1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
18世纪的一个特点是,哲学不是去反映和描绘生活,而是信仰理性思维的自发的独创,建立在康德哲学基础上的席勒美学也有着相似的对理性思维的自信和推崇。在审美教育思想中,席勒虽然是从当时的社会性格的危机本身出发,但还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人性本身的结构分析上,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本身有能力扬弃自身的矛盾,创造出一个审美状态,保证人性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理性状态。为此,席勒分别从当时的现实和人性本身的抽象结构两方面出发,论证审美教育的可行性。
席勒首先从当时德国的现实出发,对时代进行了批评,席勒认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把它的自然国家改造为道德国家,成熟的民族来自成熟的个人,即从自然性格转化为道德性格的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产生第三种性格,“它开辟了从纯粹力量统治过度到法则的统治的道路,它不会阻碍道德性格的发展,反而会充当不可见的道德性的感性保证”[2]。它像一个支柱,使社会能从自然状态转化为道德状态的同时,不会产生观念和物质的分裂,保护人的生存。而当时,“时代精神在乖戾和粗野之间,在非自然和纯自然之间,在迷信和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摇摆不定”[2],时代的性格说明了人的危机,文化本身给人性带来了创伤,如人的碎片化,国家和个人的触目惊心的矛盾等(统治者“把人类混同于纯属知行的恶劣制品,最后他就使人类从眼前完全消失了”[2],而被统治者则冷淡地接受法律)。在席勒看来,国家要建立在一种更好的人性基础之上,“政治方面的一切改善都应该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2],但人性的进步不是那么容易的,摆脱自然状态和粗野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除此以外,人们还面临着自由的非正当运动由此导致的对个体的奴役;而对自由的恐惧则往往驱使人们或者陷入人性的软弱,处于一种被习俗奴役的状态,或者逃向自然状态的野蛮,最后只能由盲目的强力来收拾残局。理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面对这种盲目的力量,席勒因此呼吁,“你要敢于成为有智慧的人”,“经过心灵而通向头脑的道路必须打通”,“如果真理要在与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么它本身必须先变成力量,并在现象世界中提出一种冲动充当代理人”。[2]人们必须寻找一种使人性高尚化的工具,美的艺术就是国家所没有的工具,人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问题是,席勒认为,当时的审美文化是以牺牲性格的力量为代价而换来的,美和自由相互躲避,因此,必须提出一个美的纯粹理性概念,换句话说就是,美必须作为人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表现出来。
此后,席勒从抽象人性出发的从人性的纯粹一般概念中来推导出美的普遍观念,经过抽象,他区分人性中的人格和状态,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形式冲动),说明只有以美和艺术为对象的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人从单纯的生命开始,为的是以形式终结;他成为个体比成为人格时间要早,他是从限制出发走向无限的”[2]。为此只要应该有人性存在,就应该有美存在,否则人就不可能从有限的感性走向无限和理性。他说,“理性首先是随着使人的感性依赖性变得无限而开始的……理性在人身上被识别出来是通过对绝对的东西(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的要求的,而因为人的自然生命的任何个别的状态都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因而这种要求就迫使人完全离开他的自然生命,并从一种受限制的现实上升到观念。”[2]与此同时,感性的人想摆脱自己的规定性,必须或者丧失已经有的被动规定,或者“本身早已包含他应该向之过渡的主动规定”,前者是不能丧失的,因为这是质料,“因此,他必定本身早已包含着主动规定,他必定是同时受动地和主动地被规定地,这就是说,他必定成为审美的人”[2]。审美心境是自然的赠品,对人来说,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完成从命运到对象的角色转化,人才能成为理性的人,能够掌握自然,而不是被自然掌握。
席勒的审美理论的前提是人的理性自足,是从抽象人性立场上对人性的高尚化的设计。他说:“真理并不像现实或事物感性存在那样,能够从外界来接受,它是思维能力自主地和自由地产生出来地,而这种自主性和自由恰恰是我们在感性的人那里找不到的”[2]。因此,席勒靠牺牲心灵的统一性来挽救心灵的独立性,“因为假如心灵本身不是分裂的,假如心灵本身不是对立的,那么心灵怎么可能从自身之中同时取得不活动和活动的基础呢”[2],他把人的精神设定为有限的精神,而且同时受到感性和理性限定,或者说质料和形式的冲动。在先验哲学家看来,只需要把精神和这两种冲动区分开,这样,精神的绝对统一性就保护下来了,而且,无论是人被哪种冲动驱使,精神都是主动的。但这个精神来自何方?既不是感官感觉,也不是身内与之对立的意志,“只有向那种意识到自我的人才可以要求理性,这就是要求意志的绝对一贯和包罗万象”,精神的实质就是理性,理性来自人的自我意识。席勒甚至认为,“在此以前他还不是人,也就不能期待他会有人性的行为”,“只要有了自我意识,同时又有了自我意识的永不改变的统一性,这就足以给一切为了人的东西和应该通过人而生成的东西,给人的认识和行动,确定统一性的法则了”[2]。当感觉和自我意识天然的产生出来后,“感性冲动随着生活经验(随着个体的开始)而觉醒,理性冲动随着法则的经验(随着人格性的开始)而觉醒……在两种冲动都获得了存在以后,人的人性才建立起来……而两种必然性的对立就成了自由的根源”[2]。审美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它为思维力创造了自由,使思维力能按照它自己的法则来表现自己”[2]。席勒说,“我们必须把在审美心境中归还给人的能力看作是一切馈赠中的最高礼物,即人性的馈赠”,美是我们的第二创造者。美“使人能够按照本性,从自己本身出发来创造他所愿望的东西——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人能够成为他应该是的东西”[2],使人能从自然状态藉审美状态[“实在的和主动的可规定性的状态”[2]]过渡到逻辑及道德状态(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
我们看到,正是从人性的完整性和高尚化出发,席勒对当时的时代性格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国家和个人应该相互负责,尤其是人性本身。人身上的能力是相互对立的,而理性的勇气正在于面对这些矛盾和对立,在各种冲动的斗争中赢得理性的胜利,并一定是经过美的胜利得来的。问题是,从人性本身的完善出发的审美乌托邦,最后却只能落实在国家对人的规划上。抽象人性不能使国家进化,相反,只有国家有能力来改造人性。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再进一步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审美乌托邦的实践带来的恰恰是审美的失落。无怪乎哈贝马斯对席勒的艺术观的理解是,“艺术本身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教化过程与个体无关,涉及到的是民族和集体生活语境”[1],因为“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用自由的国家代替必然的国家的民族那里,才能找到性格的整体性”[2]。说到底,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还是理性的专断论的产物,具有康德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幻相的特征,席勒借理性之手将美和艺术提高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位,与此同时,他勾画出来的是抽象、静止和封闭的人性。
2 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
如果说“在世界文学中,在其内部存在着两种看待世界的观点,即严肃的和诙谐的看待世界的观点的作品”[3],那么理论上同样如此。因此,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严肃的,那么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则是笑的,诙谐的。狂欢化理论的现实基础是和官方的、教会的思想相对立的民间诙谐思想,它的美学观念是怪诞现实主义。狂欢化艺术是对物质——肉体根基本身的深刻的肯定,有着摆脱了为抽象理论服务的怪诞形象和诙谐风格,因此它是欢快、解放、再生的。
巴赫金从拉拍雷的文学创作入手,说明,拉伯雷所有形象的独特性或者说他的特殊的“非文学性”就在于他和中世纪民间文化的深刻联系,巴赫金认为,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才能揭开他的众多形象之谜。因此,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的导言和第一章中,巴赫金集中对狂欢化理论或者说诙谐文化进行了阐述,说明了中世纪诙谐文化的哲学内涵和拉伯雷的作品与之的深刻联系。
巴赫金把民间诙谐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诙谐的广场表演);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尤其是第一种形式,其实就是诙谐文化的源头,后面的两种形式都来源于它,它主要具有一种历史性和双重关系性。巴赫金认为,这些仪式——演出形式(以诙谐因素组成)“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3]。需要注意的是,巴赫金认为,这种诙谐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在阶级和国家制度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从官方的方式转变过来的,而且也会随着历史而变化成官方的或日常化的方式。他说,“所有的诙谐形式……都转化到非官方角度的地位上,经过一定的重新认识、复杂化和深入化,逐渐变成表现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民间文化的基本形式”[3],而在此之前,它和严肃的方式都同样是“官方的”。从17世纪下半叶以来,“民间文化的种种狂欢节仪式——演出形式逐渐狭隘化、庸化和贫乏化。一方面,节日生活被国家化,逐渐变成歌舞升平的东西,另一方面,节日生活被日常化,即退居个人、家庭和室内的日常生活……那种特殊的狂欢节世界感受及其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开始变成为一般的节日情绪”[3]。如果说从纵向的角度看,狂欢化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那么它的仪式和相关艺术本身则包含着一种双重关系。狂欢化包含了诙谐的真理,但它并不排斥严肃性,事实上,狂欢节仪式上的第二种生活正是以严肃的生活为前提的,如果说日常的等级的生活是对象的世界,是人试图通过抽象理论来掌握对象的过程,那么,狂欢节就是人暂时阻断对象世界,参与到关系世界中的一次生动的事件。马丁·布伯用“我与你”来形容这一暂时告别对象关系的关系事件,他赞颂它的精神性,以此对比经验世界(即我与它,它可说是关系世界)的物质性和因果性,这种活动就是人的真性活动。在文明的进程中,人注定要从我与你的关系中分化出来,进入我与它的关系,“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它’,此乃我们命运中不堪忍受的怫郁”[1]不仅如此,“人越来越多……以‘学习知识’这一间接手段来取代直接经验,把对‘它’之世界的直接‘利用’简化为专业性‘利用’”[4]。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生活了,而人的真性生活本身实际被悬置,被阻碍。布伯认为,“当关系事件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个别之‘它’因为步入关系事件而能够成为‘你’”[4]。这种关系世界又分三种境界: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与人类相关联的人生;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其中前者在语言之外,中间的见于语言中,后者不可言喻,但创生语言。如果说对布伯来说,后者是最吸引他的境界,那么显而易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间的境界,即与人相关联之人生,在语言中生存的人生。对巴赫金而言,布伯的理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人的这种二重性的真实处境,人不得不徘徊于“我与它”和“我与你”(经验世界和关系世界)之间,这既是人生的悲哀,也是人生的伟大。另外,布伯的人格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赫金的思想。布伯认为,人性具有两极,或者是“我与它”之中的经验与利用之主体,或者是“我与你”之中的无规定性之主体,是人格,而“人各之存在依赖于他进入与其他人格的关系”[1]。巴赫金的所有理论包括狂欢化理论都是在关系中定义人的存在,人在和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己,建构起自我意识。他说,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地特殊形式……(这)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整个狂欢节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3]可以说,巴赫金发现,在狂欢节中人在和他人的关系中能达到一种“我与你”的境界,而且这种节日中表现的肉体的感性体验使这种乌托邦呈现出完整人解放人的意义,这和席勒等理性主义者所期望的人的完整性是多么不同。后者是以抽象理论来限定人,高尚化人,同时却蔑视人的物质存在,把人的存在理性化,静止化和唯一化;而前者认为抽象理论恰恰把人“物化”了,是在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存在,狂欢节和狂欢化艺术就是人利用诙谐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念的反抗和摆脱,是完整的人的回归和再生,精神和肉体、个体和全民获得统一,物质——肉体的因素获胜,人的第二本性(“深刻的、坚不可摧的乐观主义”[3])获胜,这使人在对立的意义上重新获得经验的世界和关系的世界。
3 共同的人性理想上的对立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审美乌托邦理想,国家、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进步都需要人性的进步为前提,而人性的高尚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审美教育,通过艺术和美,人性完成从野蛮状态到道德状态的过渡。总之,人如果想脱离感性王国,到达理性王国,就一定要经过审美王国。哈贝马斯认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甚至对直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1]其实,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更是一种人性乌托邦构想,目的是人性的完整和自由,也就是理性的人,而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侧重的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达到这个目标,是对席勒的审美乌托邦或者说人性乌托邦的社会实践。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核心也是人。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3],“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全民的感受”,“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9]。诙谐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它和自由以及非官方民间真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它可以战胜面对秘密、世界和权力的恐惧,揭示出关于世界和权力的真理,它与谎言和溢美之词以及虚伪对立,它和笑、骂人话、赌咒、怪诞形象关系紧密。从这种独特的世界感受中演化出诙谐的美学风格,即怪诞现实主义,表现出贬低化、物质化和创造性等特点,如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怪诞现实主义。很明显,狂欢化理论也是一种对人性和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这一点和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相似,而且狂欢化理论同样关注艺术和美,事实上,正是对《巨人传》的怪诞形象的美学特点的分析,使巴赫金能追溯到它的民间文化的根基,或者说是中世纪的狂欢节。但是理论所设定的对立面上,巴赫金和席勒的思想是决然不同的。席勒崇尚理性的世界,他所耿耿于怀的是人最先处于的自然的野蛮状态,和由这一状态所带来的人性中的感性冲动;而巴赫金所有理论的出发点则于对抽象理论,或者说对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反感,因为它把人给物化,或者说对象化了。他的早期哲学思想中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和陈述,而这一点,包括他的行为哲学,都贯穿在了他的狂欢化理论。
在对抽象理论的反感和对现代人类危机的诊断上,巴赫金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注:在早期哲学里,巴赫金认为在人身上出现了自己的涵义和自己的存在的分裂,或是文化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的分离,因为理论主义排斥真实的个人和历史的自我的活动。他指出,“一般意义上的人并不存在,只有我和一个特别具体的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可以指我的密友,我的同时代的人(社会的人)以及过去和未来的真实的人类(历史的人类)川世界作为事件并不由完成了的静止的事物组成,相反只有通过创造性的人类实践价值创造的持续过程,世界才向我们展现”。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也抗议了理想主义哲学,认为它们忽视了具体的人类活动却执着于从人类生存的真正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抽象出枯燥乏味的理论。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因此正是要把这种错误的存在于人类的外界的盲目的冲动归于人类自身的清醒的控制之下。理想主义只有通过结束人类自身的隔离状态,通过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才能最终被战胜。从米歇尔·伽狄勒的分析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巴赫金在对现代人类危机的诊断和出路的设计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相似处。)[5]。巴赫金在《论行为哲学》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富有参与精神的思考者因此而对现代哲学深表不满,这就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对于参与性的意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在于:它试图这样来建构自己的世界,使特定的、具体历史现实的行为在其中获得地位,使不断追求不断行为的意识在其中能有所遵循。”[6]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可见一斑。
但在出路的构想上,他们又显示出很大的差别,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哲学还是理性主义的,而巴赫金的思想里带有很强烈的宗教意味。如果说马克思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和世界的关系的话,巴赫金则更注重个体的生命历程,个体和世界的关系。狂欢化就是个体和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关系模式,这里,个体和世界是统一的,是欢快的,是作为个人和世界的日常的等级的关系的对立面存在的,应该说,就是因为存在着对象化的人和世界的关系,狂欢节的这种人和世界的关系世界才获得它的意义。
这种区别在植根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席勒美学那里找不到的,因为归根到底,席勒的审美教育的目的是最后只出现一个理性的世界,理性的人,而感性的,审美的人都只是过渡,是通向理性目的的前导,席勒眼中的理想世界是单一的、对象世界。狂欢节式的这种关系世界的意义恰在于它同时面临着日常的对象世界而存在,人可以一次次走进这个关系世界,又不得不一次次退出这个世界,回到对象世界,重新面对日常的等级的生活。这并非表明了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或者说明了巴赫金对人类社会出路的不乐观。对于笔者来说,巴赫金的这一世界的朴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正在于,它从来没有试图垄断人和世界的关系,对于个体而言,这代表了一种选择的权力,是排斥了理性的独断的对人本身的尊重,因而是人性化的乌托邦。人可以同时过着两种或更多的生活,应该给他选择的自由,让他随时可以进入不同于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另—个世界,改变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在第二个世界里,他剥下假面,放弃等级,赞扬肉体,诅咒上帝、国家,戏谑生活中一切沉重的严肃的东西,却不担心受到惩罚。
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二元对立的对象世界,那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是以事件定义存在的关系世界(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以理性和感性的对立为基础来构造人性的矛盾和发展的,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还有人格和状态,国家和个人等。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提出了所谓狂欢化的世界感受,以一个事件中显示的乌托邦召唤沉迷于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中的人们);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代表了追求人性完整的严肃的理性思考的话,那么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就提出了一种诙谐的真理;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思想含有一种静止的、分裂的、矛盾的人性观,那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是对建构的人、外在化的人、肉体的人、死而复生的人的最高赞美;如果说席勒的审美思想是代表了启蒙时代的对理性和个体的过于自信,那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是对理性的独断论和专制体的怀疑和批判。
4 对象世界和关系世界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席勒的对象世界的出发点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人,理性自足的人,为了展现他的异乎寻常的创造力,必须把人性分裂为人格和状态,感性和理性冲动,在它们的斗争中找到一种协调的因素,美,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时代性格到抽象人性的一系列矛盾;同样可以说,席勒是在个人和国家的背离的基础上来构想他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从出现危机的民族的时代性格出发,他反过来追究提升人性的可能性,以美和艺术作为工具,阐发了在以美和艺术为对象的游戏冲动的帮助下,人怎么才能协调好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把自己从自然的状态提升到理性的状态,从感性的王国进发到理性的王国。
席勒审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批判理性,康德限制了理性活动的范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把理性的能力抬到了极高的位置,因为它具有先验的、整合感性知性等活动的综合判断功能,换句话说,理性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人的真正的天赋神权。席勒在康德理性批评的基础上,从人性的完善角度展开了对美和艺术的先验哲学论证,寻找和抽象出了美的纯粹的理性概念,美是活的形象,它是形式性和实在性的统一,是感性冲动和理想冲动的统一,甚至,只有人在面对美和艺术时,当他被游戏冲动驱使时,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此基础上,席勒创造性的提出了审美王国,以及这一王国对人性从感性王国进化到理性王国的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从人性的完善基础上的合理推理,其实是对人性的理性独断,它不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考察美,而是从理性的权力上规定美,限定美,是用生活去印证纯粹理性概念的美学历程,因此,这是一种理性的,先验的乌托邦冲动,是想象的王国。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只会加深对象世界的分裂状态,理性和感性,个人和国家,生活和艺术……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理性自足的个体是虚构的,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重任,这正是抽象理论的前提和阿革硫斯之踵。理性在这个框架内只看见了一个世界,就是对象的世界,而没有发现另外还有一个世界,更真实,更完整,更具反叛性,也更难用理性的方式理解或消解。这是一个永远会存在也是永远无法被理性接纳的一个世界,它和人的双重本性紧密联系,经常被理性否认和忽略,也总在人类社会中流传,被人们所享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双重性的人,面向关系的人,他不承认和对象的唯一性的关系,背弃抽象理论的教导却在日常的体制化的生活中学会了如何截断它的统治,狂欢节和狂欢化艺术就是这样的一种暂时脱离严肃生活的方式;比起高高在上的严肃真理,它信奉诙谐的真理,能战胜自己对严肃真理的恐惧,在快乐中抛弃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抽象理论中的自我、分裂的自我,而在社会的、全民的、非官方的节日中展示另一个自我,和世界融为一体的自我、肉体的自我、完全外在化的自我。狂欢化的人是有着双重人性的人,却比坚守单一人性的人更完整,更真实,更快乐。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关系的世界,是马丁·布伯倡导的“我与你”的世界,应该说更深层的是对人的生存的宗教意味上的思考,即这种思考不是面对理论和制度,而是面对个体的人和世界的关系。巴赫金在现实中寻找无限性本质的可能,而不是像席勒那样,回到理论中抽象出本质的现实基础。这首先是一种行动,是人的负责的事件,它善于从现实存在中汲取存在的本质性说法,然后回到艺术中寻找它的美学上的特征。这是进入世界的举动,是进入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不像理性的对象世界那样高高在上而是谦恭的宗教的姿态。我们难道不能说,创造一种关系状态比提出一种理想化的理论要有价值的多,因为后者恰恰远离了真实的关系世界,远离了现实中的人性,发现不了人的双重的生存状态,相反,它在对象世界里创造抽象理论,则创造的越多,人性就越狭窄单一,人和世界的关系也越对立,人就越远离真实的存在。
收稿日期:2001-12-20
标签:巴赫金论文; 席勒论文; 人性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乌托邦论文; 巨人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