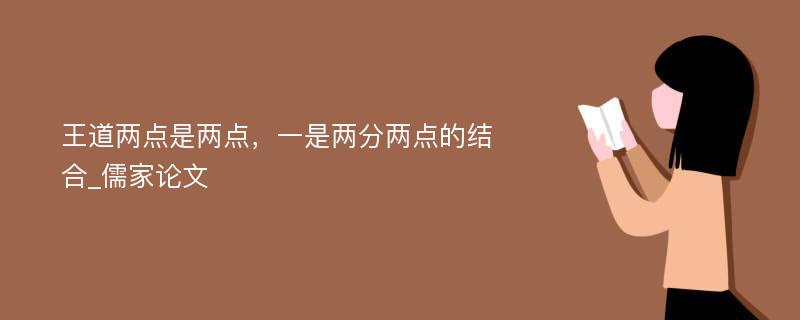
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是理性的最高抽象,又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命脉。
“王”是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同时又代表着以专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以及与这种秩序相对应的观念体系。
道与王是什么关系?就我拜读过的论著,特别是新儒家,十分强调儒家的道与王是二分的,道是社会的独立的理性系统,对王起着规范、牵制和制约的作用。就一隅而论,足以成理;然全面考察,则多偏颇。我认为道与王的关系,如本文题目所示,是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的有机组合关系,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相辅,以合为主。这不限于儒家,而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干。
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定位问题。试论一、二。
一、道、王相对二分
从历史考察,作为思想文化概念的道从一开始就与王胶着在一起,很难真正进行二分。不过又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两者在一些地方的确又分为二。学者多论儒家的道、王二分,应该说这是不全面的。就先秦诸子而论,这是共同的议题,问题的提出又早于诸子。
早在政治理念萌发之时已蕴含王、道二分。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第一篇政治文诰《盘庚》,已有政治理念的端倪。盘庚虽然以上帝(《盘庚》篇中又称“天”)化身来发号施令,但同时也还讲“德”、“重民”等。盘庚反来复去强调他自己一切遵奉“德”、事事“积德”,“不敢动用非德”。显然,德已经悄悄站在王之旁成为一个政治理念准则。殷周之变,大大促进了政治理念的发展。周武王、周公等用“以德配天”和“天以德择主”的认识方式,解释了夏、商、周的历史之变,德与王的二分更为明朗化。在后来的发展中,为什么在“德”之旁生出来了一个“道”,而且又后来居上?依我看,主要原因是,德是一个附属于天神的人事性观念,在春秋战国思想文化转型中,要突破天神的束缚,张扬理性的形而上学,“德”显然是不能适应的,需要创立新的观念,“道”正是适应这一思潮的要求而被张扬起来。(“道”并没有取代“德”,而是与“德”并存,容纳了“德”,并赋予“德”以新的内容。道与德连袂,于是又创造了“道德”这一概念。这个问题另述。)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道”是有关宇宙(天、地、人)理论体系的一字性凝结和概括,同时又是真、善、美和智慧的最高体现。道的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超越任何具体事物和个人的一种存在,即使是权力无限的君主也难于驾驭。西周时期的天子大致还能驾驭“德”,并给予界定。随着“道”的发展,君王们也一直在设法占有它、支配它,或让它适应自己,这点下面再论。不过“道”作为一种观念系统,也是无法改变的、无可奈何的事实。这不仅表现在道、王相对二分,而且“道”对于王还具有某种超越性。大致而言,有如下几点:
其一,道、王二系。道所表达的是知识、道理和价值合理性系统;王所代表的是秩序、制度和权力系统。道、王二分在诸子之前已经有相当明朗、清晰的认识。“先王之道”、“先王之制”、“王道”等观念出现及其超现实君主的性格已经表达了道、王二系这层意思。晋国丕郑论“义”高于君,把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晋献公得丽姬,生奚齐,欲废太子申生。大臣荀息惟命是从,并讲了如下的道理:“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二之有?”丕郑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从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国语·晋语一》)丕郑把义与君分为二系,义高于君,从义不从君。诸子之兴,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知识体系,在道、王二系问题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各家各派理论体系不同,论述的方式和侧重点也有差异。
儒家主要是把宗法道德理性与王权分为二系。所谓宗法道德理性,是指崇尚亲亲、尊尊,把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人伦道德体系视为道的体现,并以人伦道德为中心整合、治理社会。王所表示的主要社会权利系统。前贤、时贤对儒家的道、王之分论述详备,此不赘言。我这里只说几句儒家“道”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时下,很多人著文,称儒家学的核心是“人学”,或“成人之学”。依我之见,这种说法太宽泛了,还应接着往下说。所谓“下”,就是具体化、历史化。如果说儒家的核心是“人学”,其“人”并不是独立、自主、自由的人,而是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中心网络化、社会化的“等级人”。这种“等级人”的关系是由“三纲五常”维系的。我所说的宗法道德理性,其中心内容就是“三纲五常”。在儒家的理论中,“三纲五常”既被天命化,又被本体化,同时还是天人统一秩序的具体体现。儒学是“人学”,还是“等级人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容另文讨论。
法家主要是把法制(或“法治”)理性与王权分为二系。所谓法制理性,指法是道的体现,是人类的“公”,因此要尚法,依法治国。法家在哲学上受道家影响最为直接,慎到是把法与道结合起来的最早代表人物,其后《管子》中的法家著作、韩非等都把道视为法的本体,法原于道。所有的法家都认为,法理(法哲学)以及体现法理的法、律、令等,都具有规律性和一般性。法要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性、遵事理、量可能,因此常常用“道”、“常”、“则”、“节”、“度”、“数”、“理”、“时”、“序”等概念来表达天道、历史、人情、事理与法的内在的统一和规律。这种统一和规律体现了自然、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因此法制理性超越王本身。法家对王的定义则主要是从权势着眼,谁有最高权势谁就是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君所以尊者,令。”(《北堂书钞》卷四十五引《申子》)“势者,胜众之资。”(《韩非子·八经》)“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管子·法法》)法家是主君主专制最力的一派,同时也是最富政治理性的一派。现实的君主同法制理性分为二系是法家的一个重要命题。
道家主要是把自然理性与王分为二系。所谓自然理性,是指以自然为本,凡属自然的均是合理的,自然而然,崇尚自然。它与王的关系,大体又分为两派:一派以庄子为代表,另一是黄老派。庄子一派认为道与王是对立的,道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王,但王在道面前是等而下之的卑物。这种思想在老子那里已经有经典性的表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其中已包含对王权的鄙视。庄子沿着这一路线对君王们进行了猛烈的鞭挞(有些篇例外),指斥君主们是一批盗贼,“窃国者为诸侯”;君主又以名利挑动人欲,破坏了人们的自然生活,是搅乱人心的祸首。人们都称颂尧舜,在庄子看来,恰恰是尧舜把天下引向万丈深渊。体现自然理性的是那些“真人”、“至人”、“体道者”、“圣人”、“神人”等;帝王系列的人物,如黄帝、尧、舜等等,大抵是离道者。黄老派与庄学相反,是积极主张的一派。有的学者称黄老派为“道法家”,是很贴切的。“道生法”(《法经·道法》)把问题说的十分清楚。道、法一系,法本于道。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则主要是有权势,“衔命者,君之尊也。”(《管子·形势》)“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经法·论》)“主上执六分(按:指君臣在权力结构中不同地位的六种情况)以生杀,以赏【信】,以必伐(罚)。”(《经法·六分》)庄学与黄老派对政治的态度上尽管有很大差异,但都崇尚自然理性。自然理性与君王是二分的。
墨家主要是把社会公正理性与王分为二系。所谓社会公正理性,指的是以社会为本位,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此作为社会的公“义”。公义与“一人一义”的私义是对立的,公义高于私义。公义原于天,出于圣。天是有意志的天神;圣人是天意的体现。这种社会的公正理性高于王,规范王。王作为“政长”系统的首脑应实行公义;如果违反公义,不败则亡。
阴阳家主要表现在五德终始的历史理性与王的二分。阴阳家的学说很庞杂,这里只谈邹衍的五德终始历史理性问题。五德终始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按五德依次循环,二是相应地把政治分为五种类型(或五种模式)。在五德终始的历史理论中虽然混杂着神秘色彩,但在当时又是最富于理性的历史理论。它向人们揭示,没有不亡的朝代,没有不变的政治格局。历史之变是不可抗拒的,只有善于适应历史者才能获得胜利。在这个历史理性面前,一个朝代是有限的,具体的王更是短暂的。
道、王二系是诸子的共同话题,也是整个思想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道作为政治理性,源于认识;王则源于社会政治运动。道、王二系在理论上完成了政治理性与王的二分。由此引伸出,政治理性不是王的私有品,也不是王所能垄断的;它是人类认识范畴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社会价值问题。从认识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认识行列中来。先秦诸子“横议”政治,以及其后士人关切、评品政治,甚至平民、布衣上书议政,应该说都是以道、王二系为依据的。
其二,道高于君。这一理论概括最早是荀子提出的,但这层意思在“道”的理论化过程一开始就萌发了。道高于君不是儒家所独有,各家各派大抵都有类似的主张,是时代的通识,连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的法家也在其中。《管子》中的法家派著作一方面提出君主是“生法者”;另一方面又提出,法一旦制定出来就成为超越君主的一般,要高悬在君主的头上,也必须遵守。这如同工匠能成规矩而不能成方圆那样,方圆高于工匠;法一旦制定出来也高于君主。韩非在《解老》中说:“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对君主也是一样,道是胜败存亡的依据,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要“因道”。道高于君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表现在“君道”的抽象超越了具体的君王。社会角色的规范和抽象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制约、自我提高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商、西周时期虽然政治理性在君主之旁已悄然兴起,但人们还不能对神秘的“天子”作出更多的规范,因为他是崇拜的对象。随着周天子的式微、疑天思潮的泛滥和以“道”为中心的理性的兴起,“王”无疑还受到人们的膜拜,但已从神坛请下来变成认识对象。诸子百家有关“先王之道”、“王道”、“圣王之道”、“君道”等等理论,集中体现了对君主认识和抽象的成果。它具有提高君主的作用,又是一种政治理想。在这种一般和理想面前,一个个的君主都变成等而下之的具体存在。一般高于具体,这是人类创造的通则,是社会完善的必由之路。君道超越君主是政治理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表现在道的形而上内容远远超越了君主。道的形而上学内容有不同层次,具体而论,有“天道”、“地道”、“人道”,这些都已远远超越了具体的君主;统而言之,道是有关天地人的统一性(又可称之为宇宙体系或宇宙秩序,以及天地万物本源和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论,其超越君主的意义更不待言。在这些形而上的理论体系中,君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网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还没有明确给君主留下位置,当然在另外的论述中,又把道、天、地、王并称为四“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天为阳,地为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序卦》)显然,君主只是整个宇宙生成系统的一环。这类宇宙理论体系的道,无疑是高于君主的。
道高于君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个核心命题,同时又凝结为政治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精神和价值准则。在这个大纛下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政治多彩剧。
其三,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君臣之间本来是主奴、主仆关系,在春秋以前盛行的是绝对、盲目服从,诸如“君命无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君命,天也”(《左传》定公四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国语·晋语》九)等等观念,在君臣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此后也一直流行)。“道”的凸起,道高于君,引起了君臣关系的变化。高扬“道”的人认为,要把“道”视为君臣关系的第一纽带。在这股思潮发展中,孔子进一步提出“以道事君”(《论语·先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以道事君表示,臣是道义的承担者,为道义而仕;在道义面前,臣与君平等。如果道与君之间发生矛盾,则要以道为上。孔子温和地提出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孟子增加了刚烈的大丈夫精神,“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荀子更明确地提出“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刘劭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申鉴·杂言》)为实现道,在是非和道义问题上,臣要有“格君心之非”的责任和勇气;在行动上要敢于进行争、谏、辅、拂;还要有为道舍身的精神。黄宗羲说:“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中也,况以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于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明夷待访录·原臣》)如果王实在不可救药,儒家还主张实行革命,取而代之,但这只有圣人才可以做。
墨子同样主张以道义事君。墨子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墨子·贵义》)墨子主张言行一致,下边两个故事说明在行动上是以道义为重的。墨子派弟子高石子去事卫君,卫君待之甚厚,设之以卿位,致之以厚禄。高石子上朝堂上尽言墨家一套主张,卫君听而不行。高石子愤然离去,见到墨子说:“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於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墨子回答说:“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墨子·耕柱》)宁为狂而不失道,何等豪迈!越王通过墨子的弟子公尚过转请墨子到越共商国事,还以五百里地预封墨子。墨子听后说道:“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墨子·鲁问》)墨子把道义看的比权势、禄位更重,虽然许多诸侯争相聘请,大多因政见不合而拒仕;宁肯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折道义。
法家对问题的看法与儒、墨家有别。他们在君尊臣卑这个问题上无疑比其他派别更为突出,更强调主令臣从,但同时又主张君臣在法面前应平等以待,对法要“共立”、“共操”、“共守”、“公执”,要以法为公,尚公而抑私。所谓“私”,内容很多,这里不去讨论,其中有一点对君臣是共同的,法之外都是“私”。君主在法之外行惠,与施暴一样,都是对法的破坏,都属于“私”。法是既成的规定,面对法,更强调执行,而不主张法之外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对臣下进谏持分析和慎重的态度,不像其它家那么张扬。不过法家还是有限提倡进谏的,但要以法、以公、以功业为准则。所谓忠臣、谏臣,对上要“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对下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韩非子·奸劫弑臣》)“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管子·君臣上》)如果在法和功业问题上与君发生矛盾,同样不能盲从,“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为也。”(《管子·君臣上》)“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韩非子·难一》)法家以对法的态度和执行情况,对君臣进行了品分,《管子·七臣七主》便把君臣分成七类。法家也是主张以道事君的。
道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较为特殊。庄学一派尊道而排斥君,出世而鄙视君,甚至走到无君的地步。黄老派则积极主治,在思想上兼收法、儒,主张以道事君。《经法》中黄帝和大臣力黑之间的论治突出的是道。《淮南子》对臣以道事君,君以道纳谏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西汉时期著名的主黄老的大臣汲黯面折汉武帝,从一个例子说明黄老派是坚持以道事君的。
在理论上诸子的主流应该说都是主张以道事君的,对从道不从君观点也都或多或少进行了论述。至于具体人在实践上如何,则另当别论。
其四,以道品分君主,明君要以道为上,在道面前应有勇气低下高贵的头。春秋以前,君王主要是崇拜的对象,不能自由认识。此后,随着理性的发展,自由认识范围的扩大,君主逐渐变成认识对象。对君主的认识包括许多内容,其中重要一项是以道为标准品分君主。各家各派品分标准尽管不一样,大致说来分为“好”、“中”、“坏”三种。所谓好,就是“圣王”、“明主”、“有道之君”等等;坏,即“乱主”、“暴君”、“不肖之主”、“亡国之君”、“无道之君”等等。好、坏之间还有多品,可通称为“庸主”。按韩非的说法,好的和坏的都是千年不一出的,绝大多数是庸主。孟子也说五百年才出一个合格的王。当时的思想家把现实的君主放在道面前衡量时,几乎得出了一个大体相同的结论,一句话,都不合格。孟子与梁惠王对话后,指斥梁惠王“不仁哉!”(《孟子·尽心下》)又说:“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认为没有一个合格的,都是“乱其教,繁其刑”之辈(《荀子·在宥》),又说:“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荀子·王霸》)即使像法家这样的君主专制的讴歌者,对当时的君主也大有微词,“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商君书·修权》)道高于君和以道品分君主在当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并凝成一种稳定的政治文化,即形成了社会的普遍观念和政治价值准则。在这股劲风面前,许多君王战战兢兢,如不自己,在理性面前能低下高贵的头,程度不同的矫正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淮南子·修务训》记述魏文侯故事,魏文侯便深明道义重于权势,他说:“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齐威王以虚心纳谏著称,他曾下令:“群臣吏民,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广义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战国时期形成一种礼贤下士的政治风气,这同士张扬道有很大关系,君主们因重道而尊士,甚至与士人“分庭亢礼”。君主屈权而重道成为一种美德,即使在以后君主专制极度膨胀时期也时时有之,《申鉴·杂言上》说:“在上有屈乎?曰:在上以义屈,以义申。高祖虽能申威于秦项,而屈于商山四公;光武能申于莽,而屈于强项令。”这一类例子说明有些清醒的君主是尊重政治理性的。
道、王二分是相对的,道对王起着整合作用,同时又为王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得道即能王天下。
二、得道而得天下
人类思想发展史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凡属社会存在的重要现象,人们都要设法为它编织相应的合理与合法的理论,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同,也使人们的心理得到平衡。君主是社会生活中一种最重要的存在,所以关于君主合理与合法的问题,是人类思维最古老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中国古代,任何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总是莫如君主合理性问题最为重要和突出;在诸多现象的合理性理论中,君主合理性理论又居于主导地位。商以前史料阙如,难以论说。就殷周时期而言,那些最早的文献有关君主合理与合法的论述最为突出。当时君主合理与合法性的观念与理论,是以天命为中心而展开的,简言之,即君权神授。随着春秋战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君主合理与合法性问题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看法,但影响最大的、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有道而王”。
先秦诸子以道论王的合理性最力者应属道家,尽管在道家那里,与淳朴的自然相比,王是等而下之者,不过在理论上用道论述王的合理性是由道家开其先河的。老子最早提出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十六章》)庄子对君主的合理性问题进一步从道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人们俗说的君主,甚至包括唐尧虞舜,都属盗贼之类。只有真正体悟了“道”的人才配作君主。“君原于天而成于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谓也,天德而已。”(《庄子·天地》)“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让王》)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相对落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君权神授观念,不过当面对实际时,也突出了道。孔子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不仕无道之君,已经包含了以道作为认同君主与否的内容。孟子在一些地方大讲君权神授,在另一些地方又把道的意义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以受于人;如其道,则尧受舜之天下,不以为暴。”(《孟子·滕文公下》)其标志是民的背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子对道更加张扬,他说:“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荀子·强国》)三种威有三种不同的结果,前者王,中者危,后者亡。儒家以道义为标准对君主进行品分,最理想的是圣王,最坏的是暴主,如桀纣之主失去了合理性,可以对他进行“革命”。《逸周书》各篇的创作时代前后不一,其中《殷祝》篇就其文气而言应属战国之作。文中有一段商汤灭夏之后所说的话,完全是以“道”作为合理性的依据。“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贾谊在《新书·修政语下》引述了这段话,但按在姜太公头上。接着还有一段话论述了道与兴亡的关系,“故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行弗得而长也。故与道者,万世之宝也。”
法家对君主合理性问题的认识,究其原,也归结为道。慎到说过这样的名言:“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为天下”、“为国”是天子、国君合理性的前提;如果为自己,把天下、国家变成囊中物,那就违反了立天子、国君的初衷。《管子》中法家派的著作论述王的合法性十分注重“道”、“德”的意义和作用。《君臣上》说:“明君重道德而轻其国也,故君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王天下不是王的个人行为,不是以王为主体,而是道高于王,王是道的肩荷者和执行者。有道是有国的前提。又说:“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君臣下》说:“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也。”“德”、“威”是合法性的两大支柱。又说:“神圣者王,仁义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重令》认为威、兵、德、令四者兼俱才能王天下,这四者可简化为德、威两项。《霸言》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版法解》:“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君臣上》还提出君民一体:“与民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这同儒家的看法如出一辙。连韩非这样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者也把道视为合理性的依据,“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解老》)秦始皇是法家的崇尚者,他对自己的合理性有一系列的论述,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法家也非常注重用“道”作为合理性的依据。
《吕氏春秋》中许多篇对君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述。合法性的支点是君主要顺民、惠民,得到民的拥护。“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凡王也者,究苦之救也。”(《慎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恃君》),为民而置君、而置天子。“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长。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顺民》)顺民、惠民是道的体现。各家各派都主张圣人为王,这与得道而为王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因为圣人是道的人格化。
天命而王与得道而王,有路线的不同,前者崇神性,是从神那里寻求合理与合法性;后者崇理性,是以人的自我完善、功业、德政作为合理与合法的依据。崇尚神性更多表现为依赖;崇尚理性更多表现为主观能动的创造。春秋战国时代,是竞争和角力的时代,更需要从社会现实中寻求力量,应该说这是“得道而王”思潮大兴的历史条件。“国将亡,听于神;将兴,听于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句话可谓两条不同路线最早和最简洁的表述。就实而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割断神的脐带,即使在春秋战国理性大发扬的时期,道也没有与天命一刀两断,但侧重点是大不一样的。
道是理性的抽象,不能用感官直接感觉,对此老子已有论述,韩非在《解老》中更明确的指出,道是“不可闻见”的。但是道并不是不可知的,只要仔细观察它的功能,用抽象的思维方法是完全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也是可以论说的。下面一些各派交叉使用的词组:如“闻道”、“通于大道”、“知道”、“安道”、“得道”、“守道”、“体道”、“因道”等等,即是证明。
道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这是时代的共识,君主们也不例外。君主有明、暗之分,其区别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知道和遵道,“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也。(《管子·君臣上》)君主如何知“道”,除自己体悟外,还要通过尊师、用贤、纳谏等方式来获得。
为政之要在行道。只有行道才能把握住政治的总体。春秋战国以降,只要稍稍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政治不只是一个社会权力问题,还须要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即从“道”的高度来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坐而论道”。圣君、明主要通天道、地道、人道,并付诸实践,简而言之,即“法天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政治功能的影响至深,一方面,它赋予政治以视野广阔,登高望远,居高临下的长处;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具有全能的性质,而王权则是全能的核心。
得道而王,一方面表明道具有超越王的意义,王要向道靠拢,要体认道;另一方面,道又是王的合理性依据,道、王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王可以得道,这为王占有道开了通途。
三、王对道的占有
道就其本始意义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王的权威并立的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权威,然而中国由来已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不能容许这种精神权威无限发展和扩充的,不容许“道”在王之外超然独立。王能支配社会,无疑也要设法支配“道”;另一方面,当时思想家们创立的这个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塑造政治和改造政治,然而政治的主角是君主,于是思想家们又纷纷把实现“道”的使命交给了君主。上述两种趋势的结合,“道”即使没有完全被王吃掉,也大体被王占有。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王之道的构建和神化。先王这个词最早见于《盘庚》篇,它一出现就具有神圣和权威的意义。从西周以降,先王或先王之道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丰富的政治范畴。先王既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又是一个抽象概念。所谓具体,是说在位之王称其先祖为先王。所谓抽象,是说“先王”这个概念已超越具体的王,成为一个泛称。
在春秋以前,“先王”这个概念主要是作为行为主体来使用的,当然在先王的行为中同时也凝结了丰富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到春秋时期这些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被抽象为“先王之道”,这个词最早见于《论语》。先王和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言没有太大的区分,细致考究,先王更多指主体及其行为,先王之道则指先王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与先王之道相类的要领还有许多,诸如“先王之法”、“先王之训”、“先王之命”、“先王遗训”、“先王之教”、“先王之令”、“先王之法制”等。
在历史的滚动中,人们赋予先王和先王之道无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先王与上帝是对应、互通关系。有关上帝选立先王,先王配上帝、祀上帝的记载多多,无须征引。还有另一类资料,把事情倒过来,上帝是由先王创立的,《国语·周语上》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之”云云,显然,先王的地位比上帝还要显赫。众多的史料表明,祭祀上帝与祭祀先王的规格大体是相同的,尊先王如同尊上帝。
先王还有“成百物”的作用,《国语·郑语》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先王与造物主同列。
先王之道既包括制度,更深藏着精神。其精神是什么,这要依各家各派的学说而定。大致说来,先王之道就是自己所倡导的道或学说,正如韩非所指出的:“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先王注我。
儒、墨等以先王为旗帜,事事以先王为法。儒家的巨子荀虽曾提出“法后王”,其实他所说的后王就是三代之王,与孔、孟提倡的“法先王”没有原则的区别。他们把自己的主张还原为先王之道,同时又把先王神圣化,使先王变成一种绝对的权威,并凌驾于现实的政治权威之上。由法先王而提出的复古,在理论上有迂腐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又树立了一个超越现实君主的历史权威和精神权威,人们可以举起先王的旗帜对现实的君王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和批判。
法家对先王与儒、墨有所不同。儒、墨把先王当旗帜,法家把先王视为工具,有时作为自己理论的注脚,有时又视如敝屣。为了给自己的法治理论寻求历史依据,他们把先王变成实行法治的楷模。“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先王以三者(按:指目、耳、虑)为不足,故合已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有度》)“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安危》)先王俨然是自己的祖师爷。当讲到历史之变和变法时,先王都成为过去。“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是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商君书·六法》)“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这些话是温文尔雅的婉词,更为激烈的则是“不法古”、“废先王之教”、“无先王之书”等之类的摈弃之言!在与儒、墨争辩时,批评儒、墨借先王张扬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认为先王不复生,死无对证,虚构而不实,是一种文字游戏,“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韩非子·五蠹》)在法家看来,先王只能为现实的君主所用,决不允许先王变为高于现实君主的权威,不能成为批评和制约现实君主的口实。
其二,王道的构建和神化。王道比先王之道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个要领中,道是依附于王的,是王之道。王道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篇。洪范九畴的第五畴为“皇极”。皇,就是君主;极就是法则。文中关于王道的论述常常被后人引用。这段文字极为重要,摘录如下: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皇极”这一“畴”专论王道,在另外八“畴”中也有涉及。诸如王道的原自问题、王道内容、王道的作用、王道的意义等等,均有论述。庞朴先生在《原道》一文“王道”一节中已有精彩的分析。为了本文的需要,吸取庞朴的高见,另外也略有修正和补充,条析如下。
首先说王道的原自问题。从《洪范》整篇看,王道原于天(上帝)而成于王。箕子对话之始就告诉武王,“洪范九畴”是上帝赐予夏禹的。然而在具体的叙述中又说:“皇建其有极”,意思是说,王要建立为王的最高法则。王道原于天,又成于王,表明王是天的化身,王道是王的护身符。
其次,王道的政治内容简要而极高,第一项是要赐给臣民“五福”。何谓五福?文中没有交代,不过《洪范》的第九畴所讲的“五福”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一些注家认为前后的“五福”是一个内容。勿庸多说,这是极高度要求,也是极其伟大的事业。第二项是讲王要以身作则,才能使臣民心服。第三项讲刑罚要有度。第四项讲要用“有能有为”之人,尊敬“高明”之人。
再次,王道“荡荡”、“平平”、“正直”,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所谓“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王与臣民要共同遵守。《墨子·兼爱下》引这段文字说明文王、武王之德;晋国大臣祁奚“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左传》襄公三年)也引这段文字表彰其公而无私的精神。把社会道德准则附在王道名义下,王道与社会道德一体化了。
复次,王道还规定,王既是绝对的权威,又是民之父母。“惟辟(君主)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上下、贵贱截然相分。然而这个作威作福的君王又恰恰是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臣民对君王的指令在行动上必须绝对遵从,“是训是行”;在情感上还要完全投入君王的怀抱,“以近天子之光”。君王对臣民的权力支配和情感支配结合在一起,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王道是上承天,下理民的通则;既有超越具体王的一面,又有王占有道一面,可以说是王与道的混合体。以至同一段文字中,王道与王是不分的,混而为一。
这里附带说一下“王道”这一概念发生的时间问题。近期有几位学者著文论证《洪范》是殷周之际的作品,如果可信的话,那么,王最先与道结缘,“王道”要先于“天道”、“人道”等等概念。然而现存的西周、春秋文献以及金文,除《洪范》外,直到《左传》和《墨子》再引用这段文字,没有第二处使用“王道”这一概念。难道它像桂林的独秀山,一兀突起?这显然与社会思想发展不相宜,颇有可疑之处。这里暂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王道”不是继“天道”之后的衍生物。
战国时期,“天道”虽然是一个通用词,不过使用频率并不高。随着王、霸之争,王道大抵为儒家所倡导,或成为儒家的代称。赵烈侯改革,儒法并用,儒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史记·赵世家》)商鞅以“帝道”、“王道”进说秦孝公,秦孝公昏昏欲睡;说之以“霸道”,虚心聆听,数日不倦。王道、霸道之分,即是儒、法之分。
对王道在理论上作出更深论述的要属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有一段极著名的话: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事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在董仲舒之前,有关道贯通天、地、人和王通天、地、人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概括为“王道通三”,仍不失为一个创造。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综合。在他以前,王、王道、天道、地道、人道虽然已经常常混通,但还没有达到一体的程度。董仲舒通过对“王”字形的解析巧妙地把几者“混通”为一体,真可谓聪明之极。
把天德性化,君主的德性要随天,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但把两者一体化,以致连帝王的喜怒哀乐都源于天之四时,是董仲舒的又一发明,“天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
以往虽然也讲天与王的功能是相通的,但认为天的功能更为重要,天制约王。董仲舒进而突出了王的功能,“人主立于生杀者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王与天“共持变化之势”,这种提法是前所未有的,是董仲舒的新创造。
以往是以王对应天地、比拟天地,董仲舒则把天地、人主一体化,“天地人主一也”,天与王合二而一。
董仲舒对“王”是一种哲学释义。许慎的《说文解字》完全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其后2000年没有人提出异议。这里附带说一句,把一种思想变为字书或辞书的解词,说明这种思想已成为社会的公识,甚至成为整个民族的体认标准。董仲舒的著作在汉代以后逐渐被冷落,《说文解字》却一直是小学中的权威之作。董仲舒的著作对王的神圣化的理论通过《说文解字》普及到整个社会。由此想到,小学、训诂之作是研究思想史,特别是研究思想社会化、定型化不可忽视的资料。
在董仲舒这里,王道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王之道,它几乎把整个的“道”纳入了王道。王道内容的扩张,同时也标志着王的功能的进一步的扩张。
儒家一直高扬王道的大旗。王道作为一种观念,无疑同具体的王是有别的。人们不仅希望王实行王道,还常常用王道作为批判某些具体王的理论武器,宋代理学家甚至以王道为准则对三代以后的所有帝王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乍然看去,确有大丈夫浩然之气和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然而稍稍留意,有两点颇耐人寻味,其一,对三代君王的歌颂备至;其二,对宋朝的君主们寄予了深情的希望和期盼,不只比窿尧舜,甚至抑尧舜而扬宋君。从理论上看,他们,把三代以下、宋朝以前的历史都否定、抛弃,唯独宋是继三代之后的“圣朝”,对此,并没有讲出任何道理;明明知道宋朝积历代之弊,还作如是说,显然违背他们的思想逻辑。这种批判历史,屈从现实的现象,如果是为了“生存”,后人应予以理解,然而这也恰恰说明传统士人学理的非一贯性和人格的双重性。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理学家在张扬王道的同时,又以最精巧的理论、从更高的意义上肯定了君王制度。天理、王道、三纲一体化就是明证。这里不是苛求理学家,而是要同当代新儒家辩明一个事实,即宋代的理学家是不是君主制度的最忠贞的维护者?如果这是理学家理论的大前提(理论的和事实的),那么,在估价理学家的所谓“人格独立”等等之类的问题时,就应该有分寸。严格的说,君主专制制度与人格独立在理论上是不相容的。
我们不能忽视王道论的某些批判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被王制所限;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
其三,圣王之道的构建和神化。关于圣与王的关系问题,另文详述,这里只简单叙述与本题有关的几个问题。圣与王本来不同,圣是在王之旁生出来的一个代表知识和道德体系的人。然而有无限权力的王是不能容忍圣的无限扩展的;另一方面,祈求把圣人所代表的知识和道德付诸实现的思想家们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样一来,王与圣的结合成为必然之势。两者的结合最先体现在“圣王”这个词上。“圣王”一词在《左传》中仅一见,载于文公六年。《老子》、《论语》中未见,而《墨子》中则连篇皆是。其后几乎无人不谈圣王。圣王是贯通客体、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主宰着一切;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权力最合理的握有者。圣王是一个极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是对王的提高,但也可以说是王对圣的占有。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可质疑。
其四,王、道一体,道出于王。先秦诸子把圣人、君子视为道之原,同时又认为先王、圣王也是道之原。这在理论上为现实的王与道一体化,以及道源于现实的王原铺平了道路。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视为与道同体、自己生道的君主。秦始皇宣布自己“体道行德”,实现了王、道一体化。“体道”这个词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荀子说:“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解蔽》)韩非提出“体道”是君主有国、保身之本。(见《解老》)秦始皇的“体道”便是由此而来。秦始皇不仅体道,又是圣王,他颁布的制度、命令是“圣制”、“圣意”、“圣志”,永垂万世。先秦诸子创造的巍巍高尚的“道”一下子变成了秦始皇的囊中之物。秦朝虽然很快垮台了,秦始皇的思想却流传给后世。其后,贾谊提出“君也者,道之所出也。”(《新书·大政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道、王道、王混为一体。李觏竟说出这样的话:“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李觏集·佚文》)李觏的看法虽不是理论的主流,不过在许多时候是事实。对王来说,既要搞朕即国家,又要搞朕即道。
宋、明理学家高扬道统的大旗,道统俨然独立于王之外。然而恰恰在把道统说得神乎其神的同时,却又把这个神圣的道敬献给帝王,这一点在谥号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诸如“应道”、“法道”、“继道”、“合道”、“同道”、“循道”、“备道”、“建道”、“行道”、“章道”、“弘道”、“体道”、“崇道”、“立道”、“凝道”、“明道”、“达道”、“履道”、“隆道”、“契道”、“阐道”、“守道”等词,在谥号中居于前列。汉语词汇实在太丰富了,在这里,都说明一个问题:帝王是道的体现者。
这里再说几句作为观念的“王”。作为观念的“王”,其中已包含着“道”,先王、圣王、王道等在某些地方都可以简化为一个“王”字。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有道之王。王成为道的化身,此时希冀王就是希冀道,维护王就是维护道。
王对道的占有,或者说道依附于王,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甚至包括一些具有异端性质的人,都没有从“王道”等大框框中走出来。只要还崇拜“王道”等,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被王制和王的观念所锢,而且所说的道也是为王服务的。
四、道的王权主义精神
王对道的占有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在思想史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们在阐发、高扬“道”的观念过程中,一直向“道”注入王权主义精神。进而言之,道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忽视。只要稍稍留意观察,这一事实应该说是昭然的。这里我只谈三点:
其一,道对王的定位及其王权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
宇宙结构说有多种多样,但都遵循天人合一这一总思路。《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结构和秩序的一环,“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前边已经讨论过,天人合一的重心是天王合一。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无疑有其历史认识意义,然而这个恢宏结构真正能把握的部分是其下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主体就是贵贱等级制度。王则是等级之纽。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宇宙万物之用,即所谓的体用不二。细致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道、天道、地道、人道、天理、心性、礼仪、刑法、道德等等无疑是有区别的,但从更抽象的意义说又混而为一体。无论是“体”或“用”,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其主旨都是为君主体制服务的。有人会说,这未免把深奥的哲学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如果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还原为社会历史问题,有时就是相当“简单”的。把“简单”的社会历史问题深奥化,固然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反过来,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还原为“简单”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体用”问题如果落实在社会历史中,难道不是为君主制度辩护吗?
道所蕴含的规律性思维方式及其揭示的规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有说不尽的话题,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最实际的,应该说是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王权至上论。
其二,道的纲常化及其王权主义精神。中国是一个宗法—王权社会,从有文献记载开始,有关伦理纲常的内容就十分突出。伦理纲常向来与政治就是一体的。伦理纲常是儒家的主题自不待言,墨家以及法家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倡导的。在道家中,庄学对纲常投以鄙视的眼光,其他派别,特别是黄老派对纲常是十分重视的。
把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很早就开始了。春秋以前是神化,随着道的兴起,又开始道化(依然保留着神性)。伦理纲常的细目很多,其中最核心的是“三纲”。董仲舒做了一件影响千古的大事,这就是把伦理纲常概括为“三纲五常”,并把它形而上学化,即道化和神化。理学家们的思维具有极强的形而上学性,内部的分歧也多多,不过其中有一点是高度统一的,那就是条条认识道路都通向三纲五常,都把三纲五常形而上学化,并与形而上学中最高范畴一体化,构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张载说:“人伦,天理也。”(《张子语录下》)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札》)又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朱文公集·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陆九渊说:“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典常,谓之彝伦,盖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头换面。”(《陆九渊集·与王顺伯》)在理学家那里,人伦与道可以说是同实异名。人伦法则也就是宇宙法则,三纲五常“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朱文公集·与陈同甫》)“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陆九渊集·与朱元晦三》)。
儒家所论的伦理纲常无疑比具体的君主更有普遍意义,甚至经常高举纲常的大旗批判某些君主,有时还走到“革命”的地步。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而是从更高的层次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用形而上学论证了君主制度是永恒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纲常对王的规范和批判意义,同时也不宜忽视这种规范和批判的归结点是对王权制度的肯定。我们的新儒家朋友对此实在有点漠视,或视而不见,真不知其可也!
其三,道施化万物的中介是圣王。道化万物,主宰万物,又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依据。道的作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在。然而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独立自主地施化,在许多情况下,圣王、圣人是道施化万物,特别是施化人类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甚至没有圣王、圣人,道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讲,圣王、圣人之所以为圣王、圣人,就在于体道。圣王、圣人是道的人格化。此处只强调一点,把圣王、圣人作为道施化万物的中介,圣王之制也因此而被神圣化。只要翻开我们老祖宗的著述,有一点是普遍的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对圣王之体的崇拜,只要圣王出世或实行圣王之制,就会把人类带入极乐太平世界。圣王无疑不同于一般的王,但只有王才有可能成为圣王,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在理学家眼里,三代以下无圣王,也无圣制,可是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他们对大宋的万岁爷几乎都颂扬为圣或期待成圣。应该说这同他们的理想曲不大合拍;如果按他们的逻辑推下去,宋朝的万岁爷都应该靠边站。可是他们没有按逻辑往下走,这中除了现实问题外(我决没有意思让理学家都上断头台),在理论上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道需要通过王来实现,现实的王有可能成为圣王。儒者角色是帝王之师,要设法格君心之非,帮助王成为圣王。这种精神固然有其珍贵的地方,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不仅没有离开王制,而是以肯定王制为前提的,毫无疑问也肯定了王权主义。
以往学者对道的论述,特别是新儒家,大抵多强调道的理性规范和批判意义,强调其理性的独立性及其与王的二元关系,对道的王权主义精神很少论及。就历史实际而言,我认为这类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忽略了主要的历史事实。其实,无论怎样抽象的思想,它都有一定的历史内容;抛开历史内容,只能是灰色的、无生命的东西,或者是文字游戏而已。
道、王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是有机组合关系,同时也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从这种范式中走出来。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比具体内容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不可不察!
标签:儒家论文; 法家论文; 君主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文化论文; 墨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管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中国法制史论文; 道德论文; 墨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