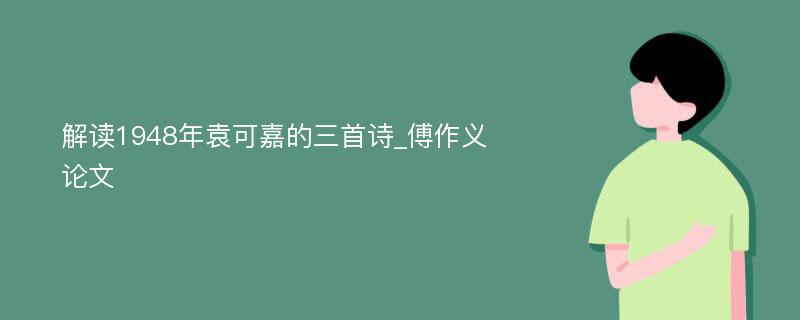
读袁可嘉一九四八年《诗三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九论文,诗三首论文,袁可论文,四八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可嘉先生《诗三首》,指的是他发表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21期上的《诗三首》,计:一,《香港》,二,《北平》,三,《时感》。
《新路》是一批教授、学者主办的刊物,以时事政论为主,其倾向当时即引起注意,因为据说他们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左翼指他们实际上是为垂死的蒋家王朝帮忙,则刊物的立场自然是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但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查封了,可见国民党并不认为这个刊物站在他们那一边)。
与另一自由主义刊物,政治上中间偏左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主编)相似,这个《新路》不是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筹备期间,他们曾邀知名记者、作家、书评家萧乾参加,萧一度应允,却并未到职就退出了,但在1949年后中共领导的审查和批判运动中,萧乾还是不断检讨才得过关,并且成为影响他后半生的“历史污点”之一。
袁可嘉在该刊发表的诗作,且其中涉及政治敏感点,在1948年末直到1949年初,先就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遭到左翼学生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抨击。袁可嘉在那里供职到1950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这是用其所长于英译了,或许他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会比留在高校要减少些吧,不得其详。
在漫长的“文革”之后,袁可嘉在1978年写的《断章(一)》说:
我是哭着来的,
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来的,
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现在袁先生归去了,我相信他是笑着归去的。我也相信他个人是明明白白归去的。
然而六十年前留下的这桩小小的诗案,还是值得我们后来者重新一读,加以澄清,让读者对真相能够明明白白。尘埃落定,透过时代的沧桑,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少受一时一地偏见的遮蔽了。
我不是诗评家,也不是当代史学者,我只是凭一己的常识,对这三首诗,尽可能试作一次政治解读。限于手头的资讯不足,我想,如有有心人能再以诗人在那前后发表的其他文章相参照(如《“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批评与民主》、《我的文学观》、《诗与民主》等),也许会更接近他诗义的内涵。
第一首《香港》和第二首《北平》,应是与他后来经常被各种选集选用的代表作《上海》、《南京》属于同一系列。
《香港》,从诗中“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来看,在今天也不失为“政治正确”的;然而说“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居然把“革命家”和“暴发户”相提并论,又说“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这不是说革命家也只是“破船片”吗?至于“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作为一首涉及政治的诗,不能不联系政治背景来看:当时,由于内战日益临近决战,原先作为中间力量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一些知名人士,为国民党所不容,于是由中共统战部门护送到香港暂住,1948年中共发布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核心的“五一”节口号,吸引了更多的人。有些知名人士当时就在香港发表了拥护中共主张的声明。而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文委在香港主办并向内地秘密发行的“大众文艺丛刊”,则在批判胡风及其文学友人的同时,又发表郭沫若的时文《斥反动文艺》,点名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今天即使从共产党的立场来检讨,这也是不顾大局的一种左倾盲动和关门主义表现。大家知道,袁可嘉与朱光潜、沈从文都有师生之谊,关系密切,朱光潜主编的商务版《文学杂志》和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都是袁可嘉经常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的地方。以意逆志,他在写《香港》一诗时,心头或不免掠过暗影。诗人都是敏感的,我们不排除袁可嘉从郭沫若檄文的火药味中,预见了“明日的风暴”对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展示的不祥前景。
但袁可嘉虽不是象牙塔里的诗人,毕竟还是书斋中的学者,而并非政客或政治家,他在概括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时的几句诗,便显得晦涩难懂,如“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就不知何指,也许是诗人词不达意,也许是由我不了解的当时某个历史细节引申出来。从下面紧接着的“洋绅士修养有素,竟不觉汗颜/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以及随后的“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来看,又似乎是说港英当局默契地给“革命家”和“被革命家”提供了“演双簧”的舞台,或者索性就是说给“革命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因为号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家”就是在帝国主义治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吧(那么,“被革命家”就是指的港英当局,然则是他们在和“革命家”搭台“唱双簧”了)?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惑,可以算是“诗无达诂”的结果。也可以说,这首诗看来写得匆忙,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佳境。
下面,暂时跳过第二首《北平》,先来看看第三首《时感》。我们记得,在1948年初,穆旦发表了他的《时感四首》,便曾经一度引起争议。通观袁可嘉的诗作,虽然也有不少“感时伤世”的篇章,但径直题为“时感”的只此一首,该是寄托着他对时世由衷的忧患之感吧?
全诗3段,各6行。是由他置身其间的文化教育圈子的现象有感而发的,但小气候离不开大气候,他的感伤也触及整个中国的形势。要知道,时为1948年,而在不久前的1947年,在国统区“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即毛泽东誉为“第二条战线”的配合下,中共的军队已在内战战场上转入全线反攻;12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时已将内战初期所提的被动的“自卫战争”改称主动的“人民解放战争”,动员群众的口号也不再是一年前策略性的“反对内战”,而是支援前线,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了。
袁可嘉一介文人,从来没有投身于政治,更不曾置身于革命队伍。但他是一个原始语义上的爱国者,又因其个人的文化教养,具有朴素的人道情怀,因此,他是反对内战的,无论内战的责任谁属。这在他于1947年7月发表的《号外三章·三》(《九叶之树常青》,王圣思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写得明明白白:
当然要咒诅,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
你们拿枪杆在死人身上划地图;
你争面,他占线,我们岂只能装糊涂,
伴随地名肉团子般任你们吞吞吐吐?
一种自私化生为两型无耻,
我们能报效的却只是一种死:——
冬夜远地的战争传来如闷鼓,
城市抱紧人畜为你们底自信受苦。
这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剿匪戡乱”和拥护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两种声音之外,的确是曾有的另一种声音,但因它主要发自基层没有话语权的弱势者,所以在当时就淹没在非杨即墨的喧哗中了。而如袁可嘉这样不知瞻前顾后发出的仅仅是叹息而已,却也难免“第三条道路”之嫌,如后来毛泽东指责的夷齐之阻拦武王伐纣的义师,如今的战争已是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它,乃至腹诽它,不就是反对革命吗?
其实,袁可嘉这首“号外”诗,大概也正是写于1947年“五·二○”学潮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前后。而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当时的宣传口径意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为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而像袁诗这样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等量齐观,谴责为同样是制造军民大规模死亡灾难的暴力,在左翼评论家那里,显然是通不过的。
袁可嘉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切身地感受到政治进入校园给他造成的压力。他是敬业的,要把课上好,把论文写好,无如周围已经缺少读书的气氛。青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胜于关心个人的学业,在教师间,学生间,甚至在整个文化教育界,已因不同的政治态度而逐渐分化得壁垒分明。在袁可嘉看来,这里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怀疑和诅咒,透露了可耻且可怕的反智倾向。可能有些左翼同学表露出对他的不屑,认为他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一套(翻看他那时的文章,也的确尽是在谈论克罗齐、艾略特),于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捡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填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这里描述的场景,经历过二三十年后那场文化浩劫的人们并不陌生:不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先有所谓“立场”,由之派生观点;在文化领域大反“封资修”,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彻底反对,而灌输以某种教条。当时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在革命战争的狂飙中,有类似后来红卫兵式的表现,不足怪,可以理解。而面对这些激情压倒理性和常识的年轻学生,袁可嘉无奈地发出嗟叹,就像是重复胡适当年说的,不要让马克思牛克思牵着鼻子走,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诗人认为北平是传播文化的中心,尤其从“五四”以来是新文化的中心,如上的遭遇更让他痛心。不仅由于学术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挤压,他分明预感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浩劫,但他却以知识者的坚守自勉:“总得有人奋力振作”,“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读过这首《时感》,回头来再读《诗三首·三》的《北平》,就易于索解了。
诗一开头说北平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份美景,“生命不强”是消受不了的,这是从来未经人道的一语。继之他说: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而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猛地飞出一脚将沉睡的大小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沉沉,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智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而复得的爱人。
在这里,诗人把他个人对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爱,升华为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新浪潮”的爱,如油与蜜不可分了。
下面,结束这首“十四行”的最后三行,就是包含着当时为人所诟病的那句涉及傅作义的诗。虽然为此让袁可嘉长期背着一个政治包袱,但看来,诗人对这首诗是不能忘情也不忍割爱的。这首诗在收入蓝棣之编选的《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时,据作者手稿(自然是得到作者同意的)排印,这么一段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在五四之春
所发出的追求科学民主的宏大呼声!
这三行诗与前面的诗行是血脉贯通的,归结到“五四”,也是水到渠成的。说它不是后来的改稿而是最初的手稿,也说得过去。
然而当年《新路》上的发表稿则是: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按:傅宜生即傅作义,当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匪”者指的是共产党。袁可嘉在此时此地歌颂傅作义为“将军队里的将军”,自然惹来一片骂声,左翼学生不但在北大民主墙上贴壁报,还在自办的文学诗歌刊物上抨击“无耻之尤的袁可嘉”,对于迂阔的诗人来说,也许这竟是始料所不及的。探讨袁可嘉为什么会这样写,近于“诛心”,可能在嗣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组织”和“群众”会向诗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据此可以对他在当时国内形势下的政治立场作出审查和判断。但时过境迁,这一层作业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然而,从常识出发,我以为,袁可嘉与傅作义不沾亲不带故,他也不会藉此攀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特别是在中共军队势如破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政界的许多人都在各作打算,各寻后路,而诗人能以一句“颂诗”求得什么功利呢?
就诗论诗,袁可嘉是扯来傅作义作一个比喻:比喻古城北平,比喻热爱北平的文化和文化北平的人,能像傅作义守城一样坚守文化和理性。当然,在这里,诗人是把守护北平及其文化遗产的安全对傅作义寄予厚望的,因为他认为傅是“将军队里的将军”。历史地看,傅作义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当得起这句颂词的。如果客观地估计其后他作为守城一方,在和平解决北平归属问题,因而使八百年故都北京城的人民生命财产、不可复制的历史建筑和宝贵文物,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致毁于战火,这个贡献是够大的,而傅作义为此也绝非没有付出代价。倘超越于党派意识之上,对于傅作义,以及像他一样的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将领”,对于他们的功勋立传赋诗加以歌颂,许多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直到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中共在正式文件中评价了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及其所辖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绩。片面的历史叙述也在开始改正。相信对于抗战后的内战,人们也将以新思维来对待。
袁可嘉这位醉心于学术,且偏于知性的现代诗人,即以他这曾引起争议的《诗三首》为例,在艺术上如何考量是另一问题,而在现代诗史上,它却是表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文化良知,并且见微知著,实际对后来发生的与反智、愚昧和迷信互为因果的例如“文革”这样的浩劫,发出了超前的预警。近年人们常常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在今天,也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诗人袁可嘉早在1948年就作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跟风、不随波逐流的表率。他的警句“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值得我们永远记住,永远讽诵。
2009年10月18日,北京
(这是作者10月末在袁可嘉诗歌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附] 袁可嘉《诗三首》
(一)香港
在无路的海上你铺出一条路,
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
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
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
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
洋绅士修养有素,毫不觉汗颜,
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
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
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
港口无须纳税,出口不必受查检,
香港总督最懂买卖,盗窃之流
从不被处徒刑,只是罚钱,罚钱,罚钱,
拆穿西洋镜,委实也呒啥希罕,
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
(二)北平
有人说你是活着的死人,我替你不平,
试打开任何一个角落,别处那有这份美景?
公园的黄昏,北海的午夜,景山的早晨,
生命不强,那里消受得了那么多美的浸淫?
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思想的新浪潮都打你的摇篮起身,
踉踉跄跄地大步而去,穿越紧裹的夜心,
猛地飞出一脚将沉睡的大小灵魂踢醒。
不过你一旦沉醉,酣睡沉沉,也着实让人担心,
一向是理性的旗手,如今也自困于反智的迷信,
我来自南方,爱你像爱我失而复得的爱人。
总愿你突破一时的眩惑,返求朴质的真身,
至勇者都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
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
(三)时感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伏案写作,
当汇来的稿金换不回寄去的稿纸;
当人们已不再关心你在说些什么,
只问你摇着呐喊的党派的旗帜;
当异己的才能已是洗不清的罪恶,
捡起同党的唾沫恍如闪烁的珠子?
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时候埋头苦读,
当智识分子齐口同声的将智识咒诅;
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疑心课本有毒,
在黑板与他们间的先生更是不可救药的书蠹;
在洋装书、线装书都像烟毒般一齐摆脱,
然后填鸭似的吞下漂亮而空洞的天书?
正因为包围我们的是空前的耻辱,
传播文化的中心竟时刻宣布学术的死讯,
在普遍的沉沦里总得有人奋力振作,
击溃愚昧者对于愚昧万能的迷信,
突破合围而来的时代的黑色地狱,
持一星微光,伫候劫后人类智慧的大黎明。
(刊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1卷21期)
标签:傅作义论文; 北平论文; 袁可嘉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香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