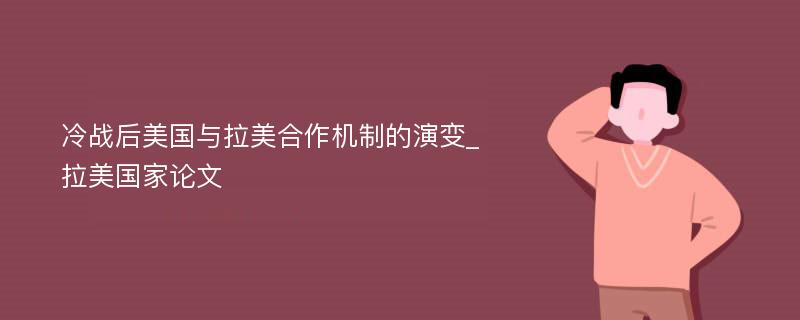
冷战后美国与拉美合作机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月20—22日,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除古巴外的34个美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加强民主和促进安全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冷战结束后,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及相关的部长会议增多,成为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而冷战时期相当活跃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和国际会议在冷战后却处于沉寂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冷战后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合作机制开始发生变化。
一、冷战时期美拉联盟机制的兴衰
美拉之间总体的合作机制最早始于19世纪末。1890年4月,在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赖恩的倡议下,第一届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和17个拉美国家参加了大会,并决定成立“美洲各共和国国际联盟”(注:在1901年第4届泛美会议上改名为泛美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注:在1902年第二届泛美会议上改名为“美洲各国国际事务局。)。此后,泛美会议共召开过9届(注:1948年第九届泛美会议后被“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取代。),成为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最早和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之一。
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加剧,为了同苏联相对抗,美国同拉美国家结成军事政治同盟。美拉联盟是这一时期双方合作的主要机制。1947年8月,美国和19个拉丁美洲国家(注:这19个拉丁美洲国家为:南美10国: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和厄瓜多尔;中美5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巴拿马;加勒比3国: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以及北美的墨西哥。另有一个中美国家尼加拉瓜因国内政变,新政府尚未获得承认而未能与会,但会后批准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也是缔约国之一。)的外交部长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维护大陆和平与安全的美洲国家会议”,并于9月2日签署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简称里约热内卢条约),规定“任何一国对美洲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因而,每一缔约国承诺行使其……固有权力以援助应付攻击”。(注:《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20页。)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是联盟的正式协商机构。1948年3月,第九届泛美会议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美国和全部20个拉美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成立了取代泛美联盟的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外长协商会议、理事会和泛美联盟等。此后,美洲国家组织的外长会议和国际会议就成了美拉合作的主要机制。此外,从1952年到1955年6月,美国还通过个别谈判的方式同12个拉丁美洲国家(注:这12个国家按缔约顺序依次为:厄瓜多尔、秘鲁、巴西、古巴、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危地马拉。)缔结了双边军事互助协定,从而建立了与拉美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50、60年代是美拉联盟机制的兴盛时期。在朝鲜战争中,所有拉美国家都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其中哥伦比亚还派军队直接追随美国参加了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基本上都站在了美国一边,许多国家还采取具体行动响应肯尼迪政府禁止运送攻击性武器进入古巴的封锁令,从而给赫鲁晓夫以“出乎意料的沉重一击”(肯尼迪语)。1961年,肯尼迪政府推出“争取联盟计划”受到拉美国家的欢迎,促进了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此外,美国还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压力乃至军事干涉,对拉美各国进行控制。1954年6月和1961年4月,美国分别对危地马拉和古巴进行武装干涉,1965年4月对多米尼加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1962年1月,在第8届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上,又迫使大会通过了制裁古巴并把古巴政府挤出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
然而,从6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削弱和军事霸权地位的动摇,以及拉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交独立性的增强,美拉联盟机制迅速衰落。据统计,在美洲国家组织各机构中,1948-1960年间,美国关于“冷战”问题的提案有20%遭到反对,到了1961-1974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3.3%;而涉及政治、法律和安全问题的提案,遭到反对的比例则由30%上升到72.2%。(注:曹琳:“美洲国家组织的现状和前景”,《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3期,第25页。)1979年6月,美国卡特政府提出建立一支泛美和平部队,用以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提案,遭到美洲国家组织第17次外长会议的否决。1989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巴拿马的武装干涉。1977年,巴西宣布废除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从法律上解除了与美国的“自动联盟”关系。菲格雷多总统还明确表示:“巴西和美国不会再出现任何形式的联盟。”(注:肖枫:“论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页。)另外,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美国作为阿根廷的盟友公然支持英国,对阿根廷中止出售武器并进行经济制裁。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根廷和其它拉美国家对美国和美拉联盟的信任,加深了美国与拉美国家间的鸿沟,凸显了美拉联盟作为美拉合作机制的局限性。作为二战后美拉合作的主要机制,美拉联盟到70、80年代实际上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在冷战联盟框架下,美拉合作机制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以里约热内卢条约为主要合作机制的美拉联盟的建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盟建立后,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渗透”的旗号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在50、60年代,“反苏、反共”甚至成了美拉联盟存在与进行合作的政治基础。1954年3月,在美国主导下,加拉加斯美洲国家会议通过了《团结一致维护美洲国家政治完整以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宣言(通称“反共宣言”),凸显了这一时期美拉合作机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次,以军事、政治合作为重点。这一时期的美拉联盟就性质来说是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合作也只是围绕着军事和安全事务进行。再者,各个主体在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拉美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力较弱,而美国是战后的超级大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远非拉美诸国可比。因而美国在合作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合作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因而必然遭到拉美国家的反对,从而在美拉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冲突的相互交织,也是这一时期美拉合作机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二、冷战后的美拉合作及新机制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拉之间的冷战联盟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美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战略,继续把拉美国家纳入以它为首的一种新体系内,以适应新时期的美拉合作。
1990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向拉美国家外交使团提出以贸易、投资和债务为“三大支柱”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简称“美洲倡议”),宣布要与拉美国家发展“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提议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受到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美洲倡议”标志着美拉之间开始从强调安全合作转向强调经济合作。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就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2月,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协定上签字。经过三国议会的批准,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作为建立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使冷战后美拉经济合作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1994年12月,克林顿政府发起并在迈阿密举行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会的34国(不包括古巴)领导人就实现美洲经济一体化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民主和保持美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两个文件,决定立即开始规划美洲自由贸易区,在2005年前建立一个包括整个美洲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次会议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经济问题被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表明在冷战后的美拉合作中,经贸问题已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其次,在这次会议中,美国和拉美国家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并在实施的时间表上顺利达成共识,与冷战时期美拉之间激烈冲突形成鲜明对照。此次首脑会议是西半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引起了美洲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曾于1956年和1967年召开过两次。其后的30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也由当时的20个增加到战后的33个。这次会议是冷战结束后召开的首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被认为是美国与拉美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标志。
自1994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后,直到1998年,美洲34国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举行了4次贸易部长会议和多次副部长会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8年4月,34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汇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圣地亚哥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正式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关税,最终建立一个包括全美洲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从构想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此外,这次会议还在教育、禁毒、反恐怖、反腐败、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次会议决定,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将于2001年上半年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它标志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已经机制化,并成为冷战后美拉合作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拉之间在经贸合作上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在安全领域也加强了合作。1995年9月,美国防部长发表《泛美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新时期美拉战略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巩固西半球的民主体制,对付任何拉美国家的民主政府所受到的“威胁”;增强本地区防务合作的透明度,建立信任措施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合作,打击贩毒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扩大与拉美国家的军事合作,以增强美拉在维和及“人道主义干预”等领域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能力等。(注:美国国防部1995年9月《泛美安全战略》报告。)为此,美国防部长佩里多次出访拉美国家,共同协商加强美洲国家安全合作问题。
1995年7月,在佩里的倡议下,美洲34个国家(古巴未被邀请)的国防部长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首次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会议就美洲地区的安全、西半球的安全合作以及军队在冷战后的新使命和新作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大会一致认为,毒品交易、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已经构成了拉美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威胁。各国承诺将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军事情报的交流,逐步建立互信机制,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国际维和活动。这是历史上美洲国家军事领导人第一次聚集在一起探讨问题。1996年10月,第2次国防部长会议在阿根廷的巴里洛切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军队参与扫毒斗争和军费开支等本地区的棘手问题,通过了增加军费开支透明度的声明,并形成了召开美洲国家国防部长年度会议的制度。到目前为止,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已召开了5次,冷战后的美拉安全合作机制基本形成。
2001年初,小布什当选美国新总统,2月16日对墨西哥进行了正式访问,开始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活动。以前新总统出访大多先去语言文化更为接近、又与美国同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这次小布什首选墨西哥乃是美国新总统外交的一次不小的变化。4月20日出席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呼吁在2005年底前建立从阿拉斯加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并强调坚持民主和人权原则)。这些信息清楚地表明,美新总统对加强与拉美“后院”的合作给予了重视。
冷战后的10年,作为美拉军事联盟的主要活动机制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很少活动。美洲国家组织自1990年接纳加拿大作为正式成员国以来,也鲜有较大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冷战时期的活跃。相反,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连续召开两届后,已经实现了机制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等新的合作机制在冷战后也活动频繁。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冷战后10年的发展演变,以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为主要内容的美拉合作新机制已逐渐取代美拉联盟而成了冷战后美拉合作的新机制。
三、冷战后美拉合作新机制的特点
冷战结束10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深刻的调整与变革,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美洲大陆,以经贸合作和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美拉合作新机制已基本形成,其主要特点是:
(一)合作重点由军事和安全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冷战后,经济领域的竞争大大加强。为了应付欧盟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挑战,美国仍然需要一个追随自己的西半球,把拉美国家的经济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之中,以增强它在经济领域同对手抗衡的能力;而拉美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债务等方面,也对美国有所依赖。在实践上,老布什的“美洲倡议”和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都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欢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则体现了美洲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实际合作。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拉美政策有两个重点,一是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二是建立以“巩固民主体制”为核心的泛美安全体制。其中第一点又是重中之重。1994年和1998年的两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都把经贸问题作为首要议题,最近的第三届首脑会议表明,经贸问题在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仍然是美国对拉美外交的重点。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和副部长会议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频繁活动,更加体现出经贸问题在冷战后美拉合作中的突出地位。
(二)推广美国“民主模式”的力度加强。进入9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基本完成了从军政权到文人政府的转变,但美国认为仍有必要向拉美国家推广其“民主模式”,从体制上保证美洲的安全与稳定。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提出了要在西半球“巩固民主体制”,建立西半球“民主共同体”;在实践上则联合盟国对古巴和海地施加政治军事压力,最终迫使海地“恢复了民主体制”。在1994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除了自由贸易区问题之外,“加强民主”也被列入了大会的议程,是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还以不实行民主体制为借口,把古巴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借以对古施压,1996年10月,第2次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明确地把“维护代议制民主”作为“巩固地区安全的基础”。今年4月,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又以“未实行民主选举”为由把古巴拒之门外,并达成了“把‘非民主国家’排除出美洲自由贸易组织”的决议,凸显了“民主”在美拉合作机制中的地位。
(三)“建立伙伴关系”代替联盟型的合作模式。早在1990年3月,老布什总统就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寻求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成熟伙伴关系”。1997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访问墨西哥期间,呼吁美拉之间要以共同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和共同未来为基础,塑造“走向21世纪”的“美拉合作伙伴关系”。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等机制下,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四)合作范围更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安全、反毒、环境、移民等多个领域。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除重点讨论了经济问题外,还就教育、禁毒、反恐怖、反腐败、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达成了不少共识。在美国和拉美国家举行的几次美洲扫毒会议上,许多拉美国家都表现出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并通过了《卡塔赫纳协议》和《圣安东尼奥宣言》等协议和宣言,表示要在扫毒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冷战后美拉合作机制虽取得了某些进展,但远非一帆风顺。在第一次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大多数拉美国家明确表示,反对在西半球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安全合作机构和机制。在第二次国防部长会议上,广大拉美国家否决了美国关于建立多国反毒部队和在巴拿马建立美洲地区空中交通控制中心的建议。由于美国通过合作控制拉美国家的目标没有变化,并且不时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今后美拉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仍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