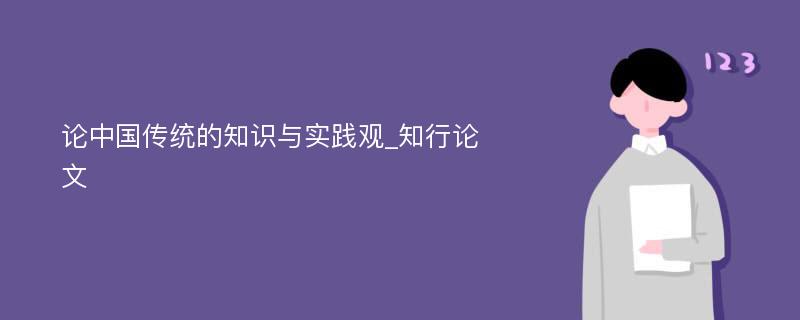
中国传统知行观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知行观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5)04~0005~06 在传统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与实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知行观。哲学家通过知行观研讨,弘扬事实求是哲学精神,形成重行的优良传统。 一、知行观释义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一个特有的话题,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这种提法。知行观涵盖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但不能等号,因为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知”,一个是“行”。“知”关涉知识论或认识论,而“行”则关涉实践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开始,世界就被二重化了,以为有一个超越的理念世界,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现象世界。按照这种世界观,知识源于理念世界,仿佛有一本“无字天书”,等待有缘人去读。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其实就是研究“无字天书”的读法,故而成为一个单独的话题。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和实践论分别是两个话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知识论为主题;而《实践理性批判》,则以实践论为主题。由于中国哲学家不认同二重化世界观,自然不会把知识论当中单独的哲学话题,而开辟了知行观论域。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误区。例如,有的研究者常常习惯于用研究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家的知行观;有的研究者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同中国哲学家的知行观简单地加以比较、对勘,专挑中国哲学的不是;还有的研究者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只把古代哲学家的知行观当作批判的对象,而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同情的理解。采用这些方法,显然不能揭示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和实质。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实际出发,研究知行之辨的特点、途径以及其现代理论价值。 知行观论域显然比知识论宽,其中既有“知”,又有“行”,并且把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知”?中国哲学家的看法与西方哲学家不一样。在中国哲学家眼里,“知”并不是对“无字天书”的解读,只是找到“行”的导向。对“行”的方法、路线、目标有清楚的了解,那就叫做“知”。西方哲学所讲“知”通常是狭义的,限制在事实知识的范围内,一般指科学知识;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是广义的,既包含着关于事实的“知”,也包含着关于价值的“知”,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单单是关于对或错的问题,还有一个得当与否的问题。由于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涵盖价值判断,不可能选择西方哲学中那种主客二分的理路。用从客观到主观的思路,可以解释关于事实的知识如何形成,但解释不了关于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不受客体性原则的限制。倘若脱离了主体性原则,根本就谈不上价值。价值的知识不能完全归结于客观事实,因其同作出价值判断的主体有密切关系。由于主体不同,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可能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在猫的眼中,鱼是最具食用价值的美味;但在狗的眼中就不一样了。狗对鱼毫无兴趣,总会想找根骨头啃。 中国哲学家通常把“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做“见闻知识”,也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外一种叫做“天德良知”,也就是关于价值的知识。知行观既涉及价值之知,也涉及事实之知,复杂性超过了单纯的知识论。中国哲学家探讨知行观,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在“见闻之知”,而在“天德良知”。关于“见闻之知”,他们通常会用经验论来解释;至于“天德良知”,往往会用先验论来解释。例如,张载认为,“天德良知”来自“大心”,与“闻见之知”无关。 中国哲学中的“行”,是指人的所有行为实践的总和。从字面上看,“行”由“彳”和“亍”两个字合并而成,意思就是“走在路上”。引申开来,“行”包含着践履、行动、探索、活动等意思。“行”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对于目的性的清楚的了解和定位,那就是“知”。所以,在中国哲学中,“知”离不开“行”,“行”也离不开“知”。中国哲学家往往把“知”和“行”相提并论,以“知”为契入点,以“行”为归宿点。中国哲学家特别关切知对于行的有用性,对“纯粹理性”的兴趣,显然不像西方哲学家那么浓。 西方哲学家特别重视“知”,而不管其是否有用,从而形成“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家眼里,“知”就是“知”,何必与“行”挂钩?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让我知道一个恒星的道理,叫我做波斯王都不干。”为什么要知道那个恒星的道理呢?赫拉克利特不抱任何实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哲学起于好奇”的说法,适用于西方哲学家,不适用于中国哲学家。如果让中国哲学家在“当波斯王”和“知道恒星的道理”之间做出选择,恐怕都会选择前者。“当波斯王”有多实惠,而“知道恒星的道理”有什么用处呢?追问“知”有什么用,这是中国式的提问方式,不是西方式的提问方式。欧几里得几何学认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这套说法都是抽象的学理,并不跟任何具体的生产活动相联系,也不同任何效用相联系。西方学者编写《植物学概论》,特别注意分类和命名。中国哲学家不会认同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或许会问:仅仅知道的植物叫什么名,有何用处?关键在于了解每种植物有什么用处。王充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论衡·超奇》)中国学者不会热心于编写什么《植物学概论》,却肯用心编写大部头的《本草纲目》,把每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写得清清楚楚。 探讨知行观是实事求是哲学精神的具体展开。所谓“实事”,指的是人干的事儿;人干的事儿,用一个字来说,都叫做“行”。所谓“是”,其中就有“知”的意思。“知识”这个词是外来语,来自于佛教,在古汉语中没有出现,“是”也有“对”的意思,不仅关涉知识论域,同时也关涉价值论域。“是”还有“真理”的意思。“真理”也不是本土词汇,也自于佛教。在佛教传入之前,古人关于真理的表述,只用一个“是”字。“是”有“正确”、“真理”、“知识”、“对”、“恰当”等诸多意思。从“用”的角度看,“是”最主要的意思为“恰当”,为“恰到好处”,能带来实践效果。何谓“是”?何谓“非”?实践效果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在中国哲学中,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于中国哲学中知行观的提法,毛泽东也表示认同。他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关系》。“认识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而“知与行”,则是中国哲学话语。《实践论》既是接着马列讲的,也是接着中国哲学的传统讲的,并且把两方面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二、重行传统肇端 中国哲学重行传统发端于原创时期,也就是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儒、墨、道三家在许多问题看法不一致,存在着分歧。但在重行这一点上,在务实的诉求上,观点上大体一致,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出明确的务实诉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把“知”落实到“行”的层面上,才可算有真学问。“知”作为学问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操作能力,并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文字。例如。怎样才算掌握了《诗经》中的真学问呢?孔子指出,仅仅把三百篇诗都背得滚瓜烂熟,也不算数,关键在于能否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真正懂得诗学的人,不是那种只会背诵诗句的书呆子,而是那些能够把诗句变成施政技巧的高手。他善于从诗句中提炼出一种施政的理念,“授之以政”;他善于运用诗句做外交辞令,“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在古代,学习诗歌不完全是一种文学上的享受,也是一种外交技巧的训练。在外交的场合下,谁能够恰当地引经据典,谁方显出使者有文化品位。孔子并不要求学生背死书本,而是要求学以致用。他以好学习闻名于世,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每事问”(《八佾》)、“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听其言观其行”(《公冶长》)、“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的这些名言警句对于中国人培养好学务实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经常被人们引用。 对于儒家重行的诉求,荀子讲得更透彻。他认为任何知识都来自经验,来自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人是认识主体,有认知能力;物是被知的对象,具有可以被人所知的道理。知识的形成过程就是“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同上)。荀子特别强调的是:人的知识和才能必须与客观事物相符合。他说:“所以知之者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正名》)人的智慧和才能一点也不能脱离客观事物,倘若脱离了客观事物,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其中包括关于道德价值的知识)。基于经验论原则,他对行高度重视。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荀子采取层层推进的论达方式,把“行”置于最高档次。荀子把“行”视为检验“知”的标准,视为求知的目的,认为“知”必须服务于“行”,“行”比“知”更为重要。如果脱离了“行”,“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大学》继承荀子重行的思想,进一步把“行”明确地界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四大实践活动。 墨家也有十分强烈的务实诉求,主张“取名以实”。“名”是指关于知识的文字或语言的表述,而“实”是指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名副其实,才算有学问;徒有其名,没有其实,不算有学问。举个例子说,有视觉障碍的人没有关于黑白的学问,不是说他不会说黑或白两个字,而是说他没有能力把黑的物件同白的物件区别开来。墨家特别看重行,特别看重效果。墨翟主张“以名取实”,把客观事实摆在首位,强调认识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他指出,看一个人是否有真学问,不能只听他怎样说,更重要的是看他怎样做,看他言行是否一致。“言足以复行者常(同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同尚)。不足以举行而常(同尚)之,是谓荡口也。”(《墨子·耕柱》)他讨厌言行不一、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人,把这种只会说空话的人叫做“荡口”。用现在的话说,就耍嘴皮子。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墨翟的经验论认识路线,并且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墨经》指出,认识能力是人本身固有的才能,“知,材也。”(《经上》)《经说上》进一步解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意思是说,一个人有认识能力,并不等于说就有知识。他必须同实际事物相接触,在认识过程中获取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经上》强调“知,接也。”展开来说,“知也者,以其过(同遇)物,而貌之,若见。”用眼睛看东西,必须实际去看,才会获取知识;如果闭着眼睛,什么知识也得不到。 墨家求知范围,比儒家还宽,不单从书本上求知,还要从生产实践中求知。墨翟既是“知”的高手,也是“行”的高手。据韩非子,墨子制做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都不会落到地上。墨子可以算得上最早制作风筝的高手。不过,现在用纸糊风筝比制作木鸢要容易得多。墨家认为,“行”是人的本质特征,“赖其力而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必须学会“强力以从事”,把知识化为一种生存能力。 人们对于道家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家只在那里“坐而论道”,其实不然。道家的务实诉求,不在儒墨两家之下。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明确地反对人们把“道”只当成言说的话题,要求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时时刻刻都以“道”为指导原则。这就是说,“行道”比“论道”重要得多。老子反对坐而论道,提出“绝学无忧”、“绝圣弃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一系列论断。道家并不把“道”仅仅当成认识对象,而是当成实践对象。行道的关键,不在于嘴的功夫,而在于能否在行为实践中自觉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由此反映出,道家也是务实的学派。道家也十分讲究做事的效率,尤其是行政的效率。老子有句名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应该像煎小鱼儿一样,需要小心谨慎,不可胡乱折腾。在煎小鱼儿时,只煎一面而不翻个行吗?这一面就煎糊了,那一面还生着呢!所以,你得有所作为,你得翻个。但是,你总翻个,非把鱼翻碎了不可,也会事与愿违,跟不翻个的效果是一样的,仍然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意思是说,执政者推出政策,要恰如其分,要恰当其时;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折腾。不知道里根从哪里学到了老子这句话,竟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了,给他的施政理念增加了几分道家的色彩,并且收到很好效果。有些美国人说,近年来的几届总统,哪一个都不如里根。为什么里根时代被人看成是政治、经济发展得都比较好的时期呢?可能同他吸收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智慧有关。庄子用寓言的方式表达了重行的诉求,这个寓言故事就是庖丁解牛。这则寓言只讲庖丁是怎么做的,没有讲庖丁是怎么说的。庖丁只干不说。他在“行”中体现出“由技进于道”的高超,把解牛当成一种艺术的享受。被庖丁所解之牛霍然倒地,庖丁提刀而立,踌躇满志。道家主张“悟道”、“行道”,要求人们把“道”体现在行为实践中,至于“道”的语言表述,并不重要。“道”是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是向什么人学习得来的。庄子笔下的庖丁,有高超的解牛技术,但绝不会写什么《牛体解刨学》,无意向他人传授解牛之道。 三、重行传统弘扬 在汉代初年,重行的传统虽一度受到冷落,但没有中断。董仲舒对重行传统重视不够,有重视书本知识而轻视实际操作的倾向。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儒家留下的文化典籍上。他读书颇专心,一般不会走出书斋,留下“三年不窥园”的典故,为后世读书人乐道,视为专心读书的楷模。他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书呆子。在董仲舒的引领下,皓首穷经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些儒生只想在故纸堆里套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把读经书看得过重,有一种忽视实践、忽视实行的倾向。不过,这种重知不重行倾向,并不代表中国哲学的主导诉求。 总的来看,重行的传统在汉代以后依然得到延续。许多哲学家都对重行传统表示认同。扬雄(前53~18)认为,学习和掌握知识,乃是人有别于禽兽的一种特质。他说:“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法言·学行》)如果一个人不肯学习,那就跟动物还有什么两样?他强调,“学”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书本知识,还应当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新知识。如果一个人善于学习和掌握有用的知识,他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不善于学习和掌握有用的知识,只是死扣书本,他将变得越来越愚蠢。扬雄说:“多闻见而识乎正道者,至识也;多闻见而识乎邪道者,迷识也。”(《法言·寡见》)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行为践履,不能只在埋首于故纸堆;应当学行并重,“强学而力行。”(《学行》)刘向(约前77-前6)也认为,学习应当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目见、耳闻、足践、手辨等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后项都比前项重要:“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说苑·政理》)最后一项是“手辨”,即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实际动手操作,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东汉初期的王充,他进一步发展了重行的思想,把“行”提到了首要的位置。他认为,人的一些知识都来源于“行”,来源于经验。一个人学问的大小,不在于他掌握多少书本知识,而看他有没有做事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动手做事的能力,在王充看来同学舌的鹦鹉没有什么两样。鹦鹉能学人说话,但不懂话的意思,更不能照着话中的意思做事。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绝不能像鹦鹉一样光说不练。人的知识既来自书本,也来自实践,后者更为重要。王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劳动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论衡·程材》)齐都、襄邑等地方的姑娘们那双擅长刺绣或织锦的巧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常年累月的实践中练出来的。如果在实践中坚持长期地、刻苦地练习,笨姑娘也会练出一双灵巧的手;反之,不肯参加实践,再聪明的人就连最简单的事也做不好。由此可见,真知识、真本领都来自实践,而不是仅靠读书就能够获得的。他把理论学说比作弓矢,强调“学贵能用”。射出的箭能射中目标,才算是好射手;能用理论学说解决实际问题,才算有真才实学。人们掌握知识,不是为了卖弄,而是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化知识为能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知学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用学知指导行。他的这句话同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近似,但比培根早说了一千多年。 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中重行的传统,在禅宗那里也得到了发扬。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跟印度佛教的路数不一样。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印度佛教把“知”看得很重,要求信徒用心读佛教经典,从佛经中领悟佛性。读佛经是成佛的必由之路,如果不读佛经,那还算什么和尚!可是禅宗和尚偏偏不看重读佛经,并且有自己的理由。慧能指出,佛性根本就不在佛经里面,而在人的本心之中。因此,你无论读多少经书,而不向本心探求,仍然不能悟得佛性,永远也成不了佛。怎样才能成佛呢,按照禅宗观点,不能走向外的路线,只能走内求的路线,通过生活实践悟出心中的佛性,顿悟成佛。顿悟跟读多少佛经,没有必然联系。想通过读佛经成佛,那是枉然,因为佛经中并没有佛性;利根人不读佛经,或许听到一两句话佛经上的话,便突然开悟,立地成佛。在禅宗眼里,生活实践就是宗教实践,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悟出“佛无所不在”的道理,那你就成佛了,不必在经书里讨生活。 禅宗虽然号称为禅宗,其实并不主张坐禅修行。坐禅是指和尚打坐修行,原本是和尚必不可少的功课。可是在禅宗看来,做此种功课毫无必要,仅靠坐禅并不能成佛。成佛是悟出来的,不是坐出来的。有位著名的禅师,名叫马祖道一。他看到有位和尚坐禅,便在他身边拿一块砖磨。 坐禅的和尚好奇地问:“您磨砖干什么呢?” 马祖道一回答:“我要用砖磨出一面镜子。” 坐禅的和尚被逗笑了:“镜子是用铜磨出来的,磨砖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 马祖道一抓住机锋,立刻反问一句:“我磨砖不能够磨出镜子,难道你坐禅能够坐成佛吗?” 在这段公案中,马祖道一的意思是,成佛与否并不取决于如何坐禅修行有多么用心,也不取决于能背诵佛经的数量,全看你能否从内心处领悟到佛性。这种领悟,不需要采用单独的宗教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就可以完成,在“行”中就可以完成。禅宗既不主张坐禅,也不主张读佛经,贯彻了一条“行中求佛”的中国式路径。《六祖坛经》故意把慧能描写成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慧能自述,我虽然不认识佛经上的字,但对佛经中讲的道理,比那些识字的人,领悟得更到位。禅宗主张顿悟成佛、行中得知,反对一味地在佛经中讨生活。如果谁指望从佛经中学到佛性,他就像米箩筐中的饿死人,就像被水淹死的渴死汉。如果你只坐在米箩筐里,却不肯张开嘴吃饭,怎么会不饿死呢?如果你泡在水中,却不肯张嘴喝一口,怎么会不渴死呢?吃饭、喝水这都是我所参与“行”啊,倘若缺少了行,怎么会有收获呢?禅宗用“骑驴找驴”讽刺那些向外求佛的人。佛性本来在你心中,你不知向内求,偏偏向外求,同骑驴找驴有什么两样?印度佛教修行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做“观”,也就是读佛经;另一条叫做“止”,也就是坐禅。禅宗把这两条都否决了。禅宗和尚既不念佛经,也不打坐,把佛教的修行方式全都颠覆了。那么,和尚干什么事情呢?回到生活实践中去!你可以担水砍柴,在劳动实践中领悟到“担水砍柴,无法妙道”;你可舞枪弄棒,在习武实践中领悟庄严佛性。在少林寺里,和尚们整天舞枪弄棒,以此为修行手段,竟练就一身好武艺。 四、知行之辨 从先秦到汉唐,哲学家已经把重行思想家讲到位了,形成中国哲学重行的传统。不过,关于知行关系的深入研讨,却出现在宋代以后。知行之辩是宋明理学家十分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知和行毕竟是两个要素,两个要素就存在一个关系问题,需要判定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对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理家的看法不一致,大体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叫做“知先行后”说,提出者是程颐。他认为知在先,行在后。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理由是:知是行的先导,倘若没有知,行也就无从谈起。比如,你首先得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事,这就是知;知道想干什么事,然后你才能去干那件事,这才是行。他举个例说,我想从洛阳到京师,也就是从洛阳到开封,第一步是确立目标,而确立目标属于知,可见知在先;然后你还得选择怎么去京师的办法,徒步走呢?还是坐车去?这也属于“知”的范围。有了这些“知”,然后才可以成“行”。在汉语中,“知”字可以做两种解释:可以解释为“知觉”,也可以解释为“知识”。如果把“知”仅仅解释为“知觉”的话,“知先行后”说不算错误。在清醒的情况下,人的任何活动都受到知觉的支配,都是有意识的活动。如果把“知”解释为“知识”,“知先行后”说恐怕有先验论之嫌。此说没有揭示知识源于实践的道理,显然对行的重视程度不够。 朱熹修正了先师的意见,提出第二种看法,叫做“知轻行重”说。在“知觉”的意义上,他不否认知先行后;但在“知识”的意义上,他有所补充。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故当以致知为先;论其轻重,则当以行为重。”(《朱文公文集》卷十五)朱熹已经对“知先行后”命题做了淡化处理,强调知识和行动构成相辅相成关系。他认为行在重要程度上超了知,重申了重行传统。“行重知轻”说还有“知行相须”的意思,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知行关系同眼睛和双脚之间的关系相似。没有眼睛看路,脚不知道往哪里走;没有脚走路,光用眼睛看,也是无济于事。眼睛和双脚“相须为用”,才是最佳配置。实际上,知与行密不可分:没有离开知的行,也没有离开行的知。他的妙喻是: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鸟的两个翅膀中,其中一个如同知,而另一个如同行。只有两个翅膀同时起作用,鸟才飞得起来。在车的两个轮子中,如果只有一个轮子动,另一个轮子不动,那车子也就走不了。康德说:“概念无经验则空,经验无概念则盲。”朱熹关于知行相须的看法,同康德的说法有些相似。朱熹提出“知轻行重、知行相须”的观点,已经把知行关系拉近了,并且把行的重要性突出出来了,但是毕竟没有否定知先行后说。对知先行后说的直接否定,来自于陆王派,来自于王阳明。 王阳明提出第三种意见,叫做“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的意思是说,知行没有先后之别,知是“一念发动处”,而“一念发动处”也就是行了。知行不过是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知离不开行,行离不开知。王阳明常用的例证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个人见到美的颜色,这叫做“知”;而有喜爱美的颜色的心情,油然而生,那就是“行”了。在这里,知和行同时发生,没有先后之分,可见构成“合一”关系。王阳明所说的“知”,有模糊性,并没有把“知觉”与“知识”区别开来;所说的“行”,也有模糊性,没有把生理活动与行为践履区别开来。他强调知行合一,固然有弘扬重行传统意思,但无法同先验论划清界限。“知行合一”说中的“知”,有时用来指“见闻之知”,有时用来指“天德良知”。如果是指“天德良知”,“知行合一”说强调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原则,倒是可以成立的。价值判断的主体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来说,价值判断的确有先验性。如果用来指“见闻之知”,“知行合一”说就难以站得住脚了:倘若没有见闻,没有经验,怎么可能会有“知”呢? “知行合一”说还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把知和行等同起来。把知和行做截然的划分,固然是一种理论偏向;但是把二者等同起来,恐怕也是一种理论偏向。倘若把知行等同起来,可以把重心转向行,也可以把重心转向知。王阳明尚能重心放在“行”这一方面,发扬重行传统,肯在“事上磨练”,干出一番事业,为后人称道;可是阳明后学却把重心转向“知”这一方面,偏离了重行传统。他们只会在方寸上做文章,竟成了一群无用的废人。明朝灭亡后,有这样两句诗很流行:“平时袖手谈性命,临危一死报君恩。”就是对阳明后学的讽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拿不出真本事,只有送死的份儿。在血的教训面前,必须重新审视“知行合一”说,力求用新理论取而代之。新理论的提出者就是王夫之。 大明王朝被清朝取代之后,王夫之作为前朝遗民,痛定思痛,觉得“知行合一”说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矫正,遂提出第四种意见,叫做“行先知后”说。他所说的“知”,只有“知识”的意思,没有“知觉”的意思;而且是狭义的,仅指“见闻之知”。他不认同先验论,始终坚持经验论立场。他提出“行先知后”说,一方面针对“知行合一”说而言,反对把知行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是“知先行后”的反命题,强调“行”的首要性。王夫之指出,行具有知不可替代的品格,“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四书训义》卷二)他只承认知行之间存在着“兼”的关系,但反对把“兼”夸大为“合”。如果像王阳明把“兼”换成“合”,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消行以归知”,把“行”的首要位置给取消了。王夫之不但重新把“行”置于首要位置,还明确地把“行”界定为实践。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张子正蒙注·至当篇注》)把实践的概念引入知行观讨论,毛泽东并不是第一人,在毛泽东以前,在王夫之那里,就出现了“实践”的提法。我们有理由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王夫之行先知后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和王夫之都是湖南人,都是湖南人的骄傲,他们之间存在思想联系毫不奇怪。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观点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说法是相通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哲学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还同中国固有哲学中的优良思想传统相结合。通过毛泽东的阐发,中国哲学知行观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有用的、活的思想武器,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实事求是这样一种反对教条主义的利器。我们不能做某种教条的信徒,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定不移地把行放在首位,贯彻通过行获取知的认识路线。行先知后的知行观为实事求是精神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历史已经证明:当我们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我们的事业就顺畅发展;当我们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