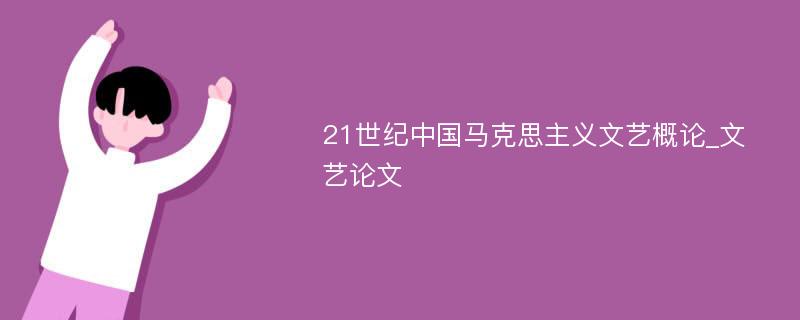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是由现实形势和理论进程所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随着时代的步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持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张力结构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展现出独特的面貌。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文艺理论运动的格局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获得了自己的特有身份,而且为人类文艺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理论界和批评界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逻辑结构和形态体系上描述得更加清晰。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举世无双的辉煌,也遭遇了大起大落的波折。相当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被冷落和边缘化的,代之而起的则是现当代西方文论肆无忌惮地称霸文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艺理论至今仍陷在这个泥潭里,动弹不得。这种“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理论诉求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非但没有带来中国文论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反而造成理论和创作不可遏止的混乱与低迷。教训再一次表明,“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1]文艺创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正能量,文艺理论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轨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近些年来,中国文艺确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实践和新问题,亟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给以透彻的解释。如果我们把文艺创作理解为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叙事化组织与特殊把握的话,那么,处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巨变期的文学艺术,对文艺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也是必然的。而在诸多种文艺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疑比其他文艺理论更具阐释力和科学性。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了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党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繁荣文艺的意见,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探索创造,为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添砖加瓦。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这是一个庄严的号召,一项重要的理论指示。随后,习近平又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谈到:“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联系到这些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是包括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内的。既然要立足国情和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那么,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境界的任务,也应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应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呢? 显然这需要从“三个关键词”的解释来加以说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理论规定的三个必备角度和条件。这三个关键词,本身并没有特殊性,但是将它们有机地连在一起,并用来界定一种文艺学说,那就有了形态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离开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没有意义的,离开本土化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缺乏个性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的理论,它是严整的整体。它要走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要求,要切合各国的国情,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生机,充满活力。 “21世纪”和“当代”这两个概念,在界定使用上是可以通用的,它们都指具体的时段。21世纪与以往世纪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大幅调整,地区冲突蔓延加剧,科技和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文化需求空前高涨。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的卓尔不群的东西。中国的文艺形势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时代特征带来的变化对文艺理论建构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的”概念,是就空间和地域而言的,当然也具有主体身份之成分。“中国的”表明这种理论不是“西方”,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从本土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是同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原创精神有着血肉联系的。它反对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照抄照转,也反对闭门造车、复古因袭。它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揭示出新的特点和范畴,提炼和总结出我国文艺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历史表明,文艺理论的正确道路从来都是深埋于国情土壤之中的,要把它找寻出来,就得从深入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淬炼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洋教条和土教条、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强调文艺理论是“中国的”,并不是不需要学习外国的。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4]我们“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5]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本质属性的规定,用以同其他学派和学说相区别。文艺理论研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个需要理直气壮进一步去正视的问题。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6]曾几何时,文论界弥散着“马克思主义过去的思想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文体统治,我们致力于文体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专制式的思想统治”[7]的论调,这同文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应是“浇上了一些折中主义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理应“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8]“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9]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来讲,也是如此。它对中国文艺学建设起着引领性和主导性作用,绝对有资格和资质在其体系中发挥灵魂和基础的作用。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果忘掉这个“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故意寻找别的学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海德格尔或弗洛伊德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在学理上是难以站住脚的。我们应该扭转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割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完全否定辨证唯物主义,肆意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旧哲学的复辟,反对在它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或建议用人本主义本体论、世界观来取代它的位置。[10]这种倾向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表示,它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这样,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词结合在一起来修饰的文艺学,就注定是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并且全方位地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未来。 那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先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何不同呢?如果我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从本质上看问题,那就不难发现,“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它们是一派相承、与时俱进的。应该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一个过程,它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停滞不前。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其中就包括着从内涵与形态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意思。所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主要是一种理论侧重点和形态转变上的区别,是发展不同阶段和特征的区别,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当然,用“中国的”和“中国化”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是应当承认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认为,一般来讲,“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所继承和化用,中间是有丰富和发展的,但与“中国的”相比,后者则更强调其原创和更新的因素。“中国化”注重原有理论同本土实践的结合,“中国的”强调的则是这种结合中的升华和生发,产生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传播”、“融入”、“结合”、“提升”、“波折”和“再提升”的过程。先是使它在中国被了解、被具体化,接着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之带上中国特点,继而使自身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并努力创造出一些新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想指出,到了当今的时代,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良性互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当逐步从“中国化”阶段迈向“中国的”阶段,从而实现一次文艺理论境界的大幅度升迁与飞跃。或者说,我们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实现文论的民族化形式,而且还要有自己的理论贡献、理论创造,有更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东西。质言之,就是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文艺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文艺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说汉语,让它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新实践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化”和“中国的”虽一字之差,但它们的创造性和含金量是不同的。“中国化”与“中国的”两者之间,固然有内在的血脉关联,但彼此确有理论生长状况与形貌内涵上的差别,后者应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更高层级的理论升华。这种升华,过去就曾经有过。譬如,毛泽东文艺思想,就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发展到新阶段也做了有力的铺垫和推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可以说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诞生提供了雏形,做出了示范。由此可见,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具备了条件和基础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分?哪些成分能成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哪些需要加以改革、补充和创造?如何把握和呈现新的时代精神、用何种叙事形式来讲述中国的经验?叙述的历史动力和价值取向是什么?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领导权的建设?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新的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究竟该有怎样的文艺和文化理想?等等。这些问题,都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和契机,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核心主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任意为之。与此同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要充满理论自觉和自信,相信“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11]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绩,与世界舞台上的任何相关学说相比,都是不逊色的。目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规律?又有哪个国家能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只有中国走在这些方面的前列。我们研读一下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贡献了许多智慧。《意见》在六个主标题下,把具体“意见”归纳为25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领导文艺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些经验和思想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是做好今后文艺工作的必要原则。 这里重点说一说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中心的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它对当今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影响,预示和展现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基本趋向,令我们从中窥见“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胚胎、萌芽和蓝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话》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受到腐蚀和疏离的情况下讲的,它把当代文艺创作和理论领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12]在这点上《讲话》是很突出的。它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氛围,提出的所有命题都不回避矛盾,极具理论现实感;它始终跳动着民族精神的脉搏,自主而自信地揭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论碰撞与建设中站住脚的根基作用;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它活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谱系中具有赓续和推进的双重效应。理论创新一般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讲话》迎着困难上,认准了历史唯物论文艺观的宗旨,认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认准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真实期待,以现实依据为起点,以历史根由为逻辑,以人民主体价值为取向,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和中国文艺现实发展两个维度的交集中聚焦思考,从宏观的战略高度谋划布局,对一系列尖锐问题都给出了科学解答,切切实实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大地提升了一步。 《讲话》集中讨论并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时期的文艺状况有清醒的认知,通篇充满了对中国精神和中国元素的发掘,发出的是典型的中国声音,体现的是地道的中国气派。《讲话》说了许多新话,提出许多新命题、新判断。有些内容,表面上看是常规的,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由于它紧密结合时代新状况,直面变化了的新形势,因之依然给人以拨乱反正的强烈的新鲜感。例如,《讲话》定义“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认为只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认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3]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不仅头一次划清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文艺属性差别的界限,而且通过“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的逻辑阐释,通过呼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拆除“心”墙,做到“身入”、“心入”、“情入”,这样就把“文艺为人民”这个老命题提到了更高的层次,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阐释,为人民美学观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14]综合上述因素,我们有理由说,《讲话》确实推动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一个现成的、固定的学说,它可能会有多种形态,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造。这是当今有担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但最主要和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从文艺理论发展的逻辑和文艺运动的实际来看,我认为最主要和最根本要解决的是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阐释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阐释清楚未来的文艺创作怎么无愧于时代、能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的轴心。它们之间虽有内在关联,但彼此是不同的论域。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骨架的“脊柱”。 《讲话》总体上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它谈文艺如何不沾染铜臭气、不当市场奴隶,又能在市场上受欢迎,要处理好艺术生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谈互联网环境和互联网思维境况下文艺如何去拓展与更新;谈文艺作品怎样挣脱“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妨碍与桎梏;谈文艺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谈文艺怎样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并把人民作为主体来加以表现;谈文艺创作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谈要把文艺问题“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谈“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谈怎样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谈制约文艺创作“高峰”的因素是哪些,“高峰”作品的出现如何成为可能;谈“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谈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带来文艺形态、类型、观念的哪些变化;谈如何加强对近些年出现的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文艺人才和群体的团结、吸引和正面引导力度,等等。这些,严格说来都是从上述那两个最主要、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中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一方面给“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开拓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让我们看清了今后文艺理论建设在思想性诉求、价值观维护、历史意识张扬、中国风格建立以及保持主流态势和理论话语权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任务。这些挑战和任务,对当代文艺学建设来说都是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感的课题。而在这两个最主要、最根本问题方面,我们文论界的研究一直是做得很不够的。 这种不够,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迷信西方文论,往往陷在所谓“文本”、“叙事”、“审美”或“文学性”上“兜圈子”、“打转转”;二是疏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深度开掘,随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同各式各样西方学说“融合”、“拼组”、“嫁接”,把文艺理论搞成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人学”、“美学”或“玄学”。结果,丢弃了理论参与和指导当代文艺现实“塑造”的功能。结果,“唯启蒙论”盛行,“唯个性论”铺张,“唯艺术论”泛滥。[15]因之,我认为根据现实需求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反思和批判研究中构造一个合理的文论框架,积极回应一系列与之相悖的观点和意见,对其理论的体系架构、基本概念、关键范畴及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形成大致的轮廓,并合理处理好同历史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当前整个文艺理论格局当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才能树立起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过程中,发挥原创精神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问题,是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这不意味着从零开始。在文论建设上,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不赞成把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一页一页地掀掉。同时,我们又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个在批判和实践中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行道路的发展的学说。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就需要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遗产加以继承、清理和光大。只有对上世纪进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论历史进行合理的确证,严肃辨析文论史上的一系列误导、误判甚或恶意曲解的思潮,正本清源,扫除障碍,返本开新,才能筑牢“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根基。也就是说,在宏观的大目标下,只有把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细化,骨头一块一块地啃,饭一口一口地吃,这样才能避免空疏、空洞、空泛和大而化之的毛病。 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上,亦应如此。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只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它才能成为活的存在,其精髓才不会被遮蔽和消解。“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对当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系列流行概念、范畴和潮流加以厘清,并找出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根脉,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与范式。 以“人民性”为例。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DNA,因为它的思想内核与根本使命,是要随着时代进步不断给广大人民群众争得更多更大的审美享受和艺术权利。人民群众应成为文艺的服务对象、力量之源和行为主体,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说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民”的结构和成分会日益多样,其范围会不断扩展,功能和作用也会与时移动。我们只有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才会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提到新的时代高度,才会同非社会主义的文艺做本质的区别。这同照顾人民需求的多样性和批判性是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反而正是这一点开辟了人民需求的新视野和新天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是考虑并兼顾到新时代“人民”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才使得“人民”的内涵得以落实,“人民”内涵的演化得以体现。此外,我们也必须看到,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在近二三十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由于受到抽象“人性论”和“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文艺创作不再关注大众的生活和感情,很少顺应人民的意愿,而是病态地同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扭结在一起,文艺的“人民性”也因此变了味儿。这个时候,我们在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过程中,厘清人民文艺的脉络,规范“人民性”的内涵和外延,重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具有了针对性极强的现实理论意义。 无疑,学科的本质是学术和学理,没有学术和学理的学科,终究是不完整、不完善的。建设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特有功能。 历史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扭转多年来文艺理论建设总是跟在西方文论后面走,把别人的学说视为圭臬或将自家理论视为别人的学说延伸的被动局面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机与活力,改变长期以来被冷落、被扭曲、被污名状态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通过合理转化本民族和国外优秀文化遗产,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论话语方式,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尊严和阐释能力的时候了。那种认为“文艺理论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办?似乎没有新的出路,只能看是否能坚持一条路走到黑”[16]的焦虑,是大可不必的。 总之,我们要防止“告别理论”的倾向,重建我们的文艺理论理想,加强文艺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总体质量和水平的跃升,用接地气的、充满创造力的、系统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形态,去占据文艺理论多元坐标系的中心地盘。这是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