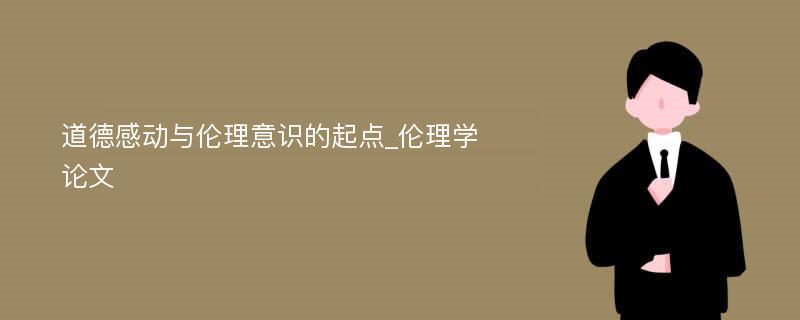
道德感动与伦理意识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道德论文,意识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鲁迅:《一件小事》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朱自清:《背影》
这两段文字,出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学作品。它们反映出,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常常会为身边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和事所感动。什么是感动?我们为什么会感动?我们往往因为什么东西而感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感动的哲学伦理学意义何在?尽管我们常常感动,但似乎鲜有人对感动、特别是道德感动这一情感现象的哲学本质和伦理学意义,进行深入的和概念上的系统分析和讨论。在本文中,我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某种探讨,旨在阐发道德感动作为极其重要的道德情感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德性伦理学的本质,有着怎样的哲学意义。
二、从底线伦理的困难说起
我们知道,道德哲学所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伦理学的本质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又被归结为关于道德意识之起源和边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国内谈得较多的是“底线伦理”。例如,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就在一篇名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的文章中提倡建立道德底线,并将这一底线视为“社会的基准线”和“水平线”。在这一意义上,何教授认为:“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何怀宏,第420页)①这种底线伦理的说法,和西方现代伦理学主流将伦理学的本质理解为规范型的律令性伦理是一致的。传统德性伦理学的现代复兴先驱、著名英国女哲学家安丝康(G.E.M.Anscombe),就曾因此将现代伦理学的本质归结为“伦理学的神圣律法概念”(divine law conception of ethics)。(Anscombe,p.1)
在我看来,按照这种要求建立的底线伦理学,在哲学上假设了两个未经论证的前提,一个是存在论上的,一个是知识论上的。前者假设世上有某种或某些先天存在着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规则,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后者假设我们人类出于某种机能和功能,能够认识、发现并正确地实践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和规则。坦率地说,主流伦理学说大多在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上或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关于这个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参见Scheler,1973,pp.45-81)由于着重点和篇幅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能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指出,立基于其上的所谓底线伦理学在具体的道德伦理实践中,至少会遇到与上述前提相关联的三个基本难题;倘若底线伦理学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三个难题,那么它在理论上至少就是有疑问的或不周全的。
第一个难题很简单:我们大概很难找到这样的普遍道德底线。可能有人马上就会说:“不应撒谎”、“不应杀人”明显就是这样的一些道德底线,它们在基督教的“十戒”、佛教的“八正道”以及儒家的基本信条中均可找到。这话固然不错,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些戒律作为底线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和普世皆准的,像善意的谎言是否应当被允许就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cf.Kant,pp.63-67)还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同属一个宗教文化传统,但双方关于死刑是否应当废除的问题也是争得不可开交。
即使我们撇开第一个难题不论,承认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底线规范,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机制,例如通过民主对话和平等协商,我们达到了某些我们以为可以成为道德底线的规范,但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难题,即人们对于这些道德底线的解释也可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尤其是会发生在争执各方对于基础价值的理解方面以及涉及到基本权益的时候。如果没有关于基本价值的理解和权益方面的冲突,也许人们还能达成对于某个抽象概念的共识,例如关于人权和人道,我们可以原则上一致同意;可是在具体解释和实行规范的时候就不行了,依旧难免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样一来,所谓“规范”的力度或效率就会下降,规范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从而最终导致道德评判的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些空洞的概念还会沦为某些有权有势者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
第三个难题更为严重:虽然这样的一些底线规范也许有助于维护人类公共生活的秩序,但却无法推动人类道德水准的改善和提高。我们的道德生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仅是一个求生存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求“好的生活”的问题。(cf.Aristotle,pp.1-18)底线伦理学只求大家能平安相处,不相互冲突和伤害,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其基本原则是正义和公平。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混同,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混淆,这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误区。正是由于这一混淆和失误,我们看到,法律成了道德的最后底线。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道德沦丧的年代,人们就会不仅仅以不违反法律作为道德的标杆,甚至可能认为即使违反法律,但只要不被发现、定罪,就是道德的或者至少不是不道德的。这样下去,其结果必然是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道德底线也随之越来越低,而且人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去钻法律的空子,以至最后道德规范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只要有法律就够了。这在实际上是否认了人有道德完善和道德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总而言之,以上就是当今比较流行的底线伦理学或者规范伦理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绕开这些难题,奢谈什么“底线伦理”、“普世伦理”,只能陷入哲学上的空洞的概念游戏和实践中的一厢情愿。
同时,这三个难题也暴露出我们在对道德哲学基础的传统思考方面的缺陷和误区。道德是否一定要具有律令式的规范性?是否一定要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这些问题也许是需要认真思考与讨论的。天主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孔汉思(Hans Kueng),就企图从上述的立场出发来建立未来世界的全球性“普世伦理”。而在我看来,全球伦理作为普遍性、强规范性的律令式的规范伦理和底线伦理,是不可能且不必要的;但作为具有“弱规范性的”或者说作为“范导性的” “示范伦理”,则是可能和必要的。②
三、道德感动之为道德意识的起点
前面讲的是我对当今伦理学主流理解的一个质疑,这是负面的批评。下面我将从我们的日常道德生活的角度,从正面来谈谈我所设想的我们的道德意识如何起源和构成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道德评判和道德提升的伦理力量在生活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这将是本文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道德意识是有关善恶的道德评判。那么,我们的道德意识的起源是什么?学者们常常从形上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文化乃至生物遗传的角度来谈论道德意识的起源。我在这里不想谈那么深远,只想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就是“道德感动”。我们时常都会或者有可能为一些人、一些事所感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感动?“感动”像“善”、“仁”、“义务”、“责任”、“诚实”、“公正”等等一样,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吗?如果是,“感动”的意义将如何界定和描述?
什么是道德感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某些事件、被某些人的行为所感动,这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严格说来,并非所有的感动都是道德感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道德感动与美学感动。但无论道德感动还是美学感动,都无疑是一种价值感动,是一种由“好东西”所激发的感动。应该说,这种感动的存在就是价值本身存在的见证。因为我们这里探讨的重点是道德感动,所以我们也许会说,“感动”这一现象的存在说明道德怀疑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立场站不住,因为无论道德怀疑主义还是道德虚无主义,都企图对道德存在本身发出质疑。而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伦理道德不仅是应该而且是必需的,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容讨论的问题。让我们扪心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被感动过?如果我们被感动过,那么一般说来,我们一定是由于一些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动。不错,因为感动是一种情感现象,我们常常难免会犯错,出现虚假的感动。但正如我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尽管虚假的感动有各种情形,但这些都不能否定或者至少不足以否定,道德感动作为道德德性或道德价值之见证这一基本的特性。而且,道德感动就其本质而言,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现象。也许有人会说,几乎不可能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件事情所感动,但我想说的是,在所有的时间、不被任何事物所感动的人也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在逻辑上得出结论:只要有一些人或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一些事所感动和不断地被感动,那就说明道德的存在是明明白白、不可质疑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将道德“感动”作为我们的伦理意识以及我们研究人的道德本性的一个起点和人的道德意识的明证。而一旦这样看,道德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可能既不在于从规范上去提出应当如何生活,也不在于从形上学的角度去先验地断言人性的善恶,亦不在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去描述道德意识的远古起源,甚至不在于从生物遗传的角度去探寻道德的基因,而是在于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具体感动事件中来看待我们的道德意识的本质。
尽管我们在概念上区分了道德感动与美学感动,但在中文的日常语境中,当我们说“感动”的时候,主要指的是道德感动。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里,“感动”由“感”和“动”两个字组成。“感”主要指的是“感觉”、“感情”、“感触”,泛指人的情感和情绪。但在更深一层的语言、历史、文化层面上,“感”字还指向某种与人相关、但又常常超越于人的“感应”、“交感”、“感通”等等。“动”一般说的是“运动”、“活动”、“行动”,但和“感”字联系在一起,说的大概就是人在价值活动的交感、情绪感应中所引发或激发出的具有道德意义的“行动”,或者至少是有趋向于道德行为的“冲动”的过程。所以,在《说文解字》中,“感”被解读为“动人心也”(许慎,第222页)。除了“感动”之外,我们日常所讲的诸如“同情”、“心安”、“恻隐”、“羞耻”、“惭愧”、“内疚”、“罪恶感”、“怨恨”、“义愤”等等,大概都可以归入“道德感动”的范畴之列。这样说来,我们也许还需要区分出广义的和狭义的道德感动。广义的道德感动指的是所有具有道德见证力的、能激发出我们的道德评判和道德意识的情感,其中既包括积极正面的也包括消极负面的情感。但从狭义上讲,也许只有那些能促进和激发人的道德向上的情感,即有积极正面意义的情感,才属于道德感动。
在中西方哲学史上,应当说道德感动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其在道德伦理学上的意义,很早就引起了圣贤睿哲的重视和思考,比如孔子讲的“心安”、“耻”,孟子讲的“怜悯”、“恻隐”、“不忍人之心”,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又如休谟、尼采、舍勒、斯特劳森、司洛特(M.Slote)等人分析探讨的“同情”、“义愤”、“怨恨”、“感通”等等,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道德感动的范围。感动的发生首先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让我们深深感动的往往不是那些英雄伟业,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成千上万的平常人、平常事,这些才是我们道德意识的“源头活水”。比如开篇所引述的鲁迅写的“一件小事”、朱自清写的“背影”,这些都是在我们周遭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再如汶川、玉树大地震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感动?它们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道德力量?这就是我要分析的。在我看来,道德感动不仅仅是一种感动,同时也是一种判断。不是先对之有一种感觉、情感,然后再对它加以判断;道德感动本身就已经蕴含着一种判断在内,道德感动同时就是一种道德判断。而且,这里牵涉的是双重的判断。当我们被一个行为所感动的时候,我们不仅肯定了这一行为,对之给予一个道德赞赏的判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道德感动同时也显现出或见证了这一道德赞赏的根据。也就是说,道德感动自身可能不一定是一个道德行为,但它的确是道德德性的一种见证,③而且它还是引发新的道德行为的一种力量,它往往诱导、激励、推动、促进后续的道德行为的产生。这样,道德感动的道德判断和见证功能就使得感动者自己和他人的道德行为发生或至少有可能发生。
我们在这里也许还需要区别道德感动和情绪激动,因为这两者常常交织缠绕,一同发生。在我看来,道德感动具有伦理特性,而情绪激动一般只有生理特征。情绪激动往往只是道德感动的一种外在的生理表达形式。情绪激动并不一定保证有道德感动。陈嘉映说,和激动相比,感动似乎处在一个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参见陈嘉映,第182-183页),这话很对。在道德感动这里,有着更多的传统积淀和文化参与。或者也许可以这样讲,常常因为我们的道德感动,所以才情绪激动。也就是说,虽然两者之间或许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有时有情绪激动而无道德感动,有时则有道德感动而无情绪激动,但在多数情况下,道德感动伴随有情绪激动,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一个需要注意区别的是虚假的感动和真实的感动。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人为了特殊的目的而制造出虚假的感动,这些感动常常也能制造出激动的效果。在我看来,虚假的感动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为虚拟事实的编排和想象而引发出来的感动,例如我们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听一个故事,可能被虚拟故事中的情节感动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知道情形是假的,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动。另一种则是伪装出来的感动,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由当事人伪装出来的感动,比如某些表演者或骗子的行为。比较这两种虚假的感动,应当说,只有后一种感动才不是真实的感动,而在前一种感动中,感动本身还是真实的,只是它为之所动的对象是虚假的。例如我们被故事中的爱情所感动:虽然故事是虚假的,但它所反映见证的爱情价值却绝不是虚假的——爱情本身是人类生活和心灵中的美好价值和情感,我们为它而感动,这是对虚假事实的真实感动。而且,我还想说,即便是真正虚假的感动,依然对我们的道德评判有意义,只是这种意义不是积极正面的而是消极负面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我们可能因为无知而一时受骗,为一些人造作出来的虚假行为所感动;但是只要我们知道了被蒙骗的真相,我们马上会感到反感、厌恶乃至愤怒,这就是一种具有负面意义的“感动”情况。如前所述,这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道德感动。所以,正面的感动是道德行为和道德德性的见证,而厌恶作为负面的感动,则是不道德行为和不道德德性的见证。
四、道德感动之为道德哲学的重要范畴的几个特征
下面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按照这样理解的“道德感动”,它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建构过程中的本质机制是什么?或者说,作为道德哲学的重要范畴,它可能有哪些基本的特征?
首先,我想引用英国当代哲学家斯特劳森的一个观点来说明道德感动的第一个本质性机制,即道德感动的“亲身性”。斯特劳森认为,情感反应作为一个特定的言语过程,牵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间、第一和第二人称之间的一个对应性的或对话性的行为交往过程。它一定是一个我你关系,是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所以,一旦我们引进第三人称,即引入一个客观的第三者的判断,就会取消原初的对应性特质而导致对话情景的消隐。(cf.Strawson,p.9)将这一说法应用到理解“道德感动”的伦理学本质上,我们大概可以说,“道德感动”一定具有某种亲身性,也就是说,一定要身临其境才会有感动。这种亲身介入虽然不必然要求情感主体的当下在场,但至少要求我们设想自己当下在场。所以,我想把这种道德感动的当下在场和亲身介入的特征称为道德的“亲身性”。按照这一理解,感动一定要有一种对应、响应、对话的形式,即呈现一种互动影响的关系状态;它似乎不太会是一种客观观察或理论论辩的过程。它强调身临其境,而且要求不断地身临其境,将心比心,在设身处地的情境中激发或启动我们的道德自我与道德意识。换句话说,正是在这样那样的道德感动中,一种强烈的道德自我感和自我意识才会出现。所以,“亲身性”应该是道德感动的第一个本质特征。
其次,道德感动在其根本上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论推论。也就是说,道德感动是一个非逻辑、非对象化的过程。与推论、论理过程不同,道德感动作为一种情绪状态,是一种感应、感染和传染的东西。④在某种道德情境中,有时我们心里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就会动起来;正因为这样,道德意识就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培养,我们的道德感就会越来越强,以至于在社群中慢慢形成为风范和习惯。但这里我还想说,虽然道德感动作为一种情绪状态具有非逻辑、非对象化的特征,但它并非完全不可琢磨。在道德感动的瞬间,图像、影像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道德感动的现象学分析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意识的培养生成过程也许更是一个图像化、影像化的过程,因为我们大概很少会为一个抽象的道德理念、一条普遍的道德规则所感动,但往往会为一个个具体的道德形象、道德故事所感动,为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的行为所感动,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图像、影像的形式出现的。
第三,道德感动不是一个理论思辨行为,它在本质机制上与行动有关。在道德感动中,我们也许不一定马上付诸行动,但至少有要行动的冲动。所以,感而不动大概就不是真的感动。
第四,道德感动既有个别性,又有公共性。一方面,道德感动是在一个个别性、亲身性的情景中发生,每一个感动都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说,每一份感动又都隐含着公共性,蕴含着一种感动者所认同的具有公共性的道德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道德感动是道德德性的见证。从表面上看,人们是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被深深地感动(正面意义)或产生愤怒(负面意义)的,但这种个别的感动或愤怒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因为感动者所认同的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我们的”价值得到了弘扬或者遭到了侵犯。例如,斯特劳森曾指出,虽然诸如“愤恨”之类的道德情感的发生是出于对个别行为的反应,但真正引起这些反应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而是涉及到行为的本质,即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共认可的道德价值。在这里,侵犯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或权益,而是大家共同认可或默认的一种价值。(cf.Strawson,pp.14-15)⑤同理,道德感动是这样的一种对行为的赞许,这里赞许的不仅仅是个别的行为,更是那行为背后所见证的、公共认可和崇尚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品性。当然,这里的“公共性”更多的是与历史、传统、文化、风俗相关,而非与神性的天条或先验的律则相联。
五、道德感动与儒家伦理的传统
尽管在中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对道德感动这一现象予以重视的证据,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从提出的年代、所重视的程度来看,还是从论述的数量而言,道德感动都无疑在中国人的伦理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一种主流的核心位置。⑥
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传统中,应当说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的情绪感动现象与道德德性、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情绪感动常常被表述为自然阴阳交感以及感应、感通的一种现象和方式。按照这种说法,浩瀚宇宙中的日月山川、自然万物之发生运作,甚至包括历史朝代的兴盛衰亡、个人生活和生命的变迁起伏,无一不是由阴与阳这两种基本力量的此消彼长、相摩互荡所决定。这种以阴阳冲突与和合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式的中国哲学的传统宇宙观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道德德性或善恶之质常常通过身体的感觉和人心的感受,即喜怒哀乐、饥渴痛痒等,而得到见证和验证。例如,我们中国人日常语言中所讲的“感天动地”或“天怒人怨”等等,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用情感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赞赏还是反对自然和人事行为中善举与恶行的古老传统。
中国人在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对“感”,即“感觉”、“感情”、“感动”、“感通”、“感应”的思考和重视,大概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和《易传》年代。我们知道,《周易》古经由64卦象和其卦辞、爻辞组成,分上下两经,一般认为从乾、坤两卦始,以既济、未济两卦终。正因如此,传统解释强调乾(天)坤(地)两卦在整个易学体系中的龙头地位,并用此两卦象来诠释《易经》的基本精神。不过,也有解释者更看重下经的首卦咸卦,认为这才是真正体现《易经》精神的根本。⑦按照《易传》的经典解释,“咸,感也”(高亨,第269页)。许慎的《说文解字》更进一步将“咸”解为“皆”与“悉”,取其相互间“详尽获悉”之义。(参见许慎,第32、74、314页)因此,“咸”之卦象所体现的乃是天地之“感悉”,圣人、人心之“感悉”与山泽之“感悉”的情状。东晋高僧慧远曾因此得出“易以感为体”的结论。(参见余嘉锡,第240页)这一结论也为后世具有创新精神的儒者所接受和弘扬。例如明末的李贽,就曾明确宣称“天下之道,感应而已”(《李贽文集》第7卷,第169页);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则更进一步提出:“咸之为道,固神化之极致也”,“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王夫之,第277、903-904页)。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将“咸”卦在《易经》整个体系中的地位拔高到超过甚至替代“乾”、“坤”的解释,但也一直认为,传统《易经》解释中对下经首卦或整个《易经》体系的中位卦即“咸/恒”卦地位的忽视或重视不足,是导致先秦中国哲学传统中一些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在后世缺失和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强调“乾”“坤”在整个《易经》体系中的龙头地位和强调“咸”、“恒”的枢纽核心位置,并不必然构成《易经》哲学思想理解上的矛盾;相反,如果我们沿循儒家传统中对“咸”卦之为天地和合、阴阳交感的“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的“人之道”的基本解释,配合儒家天人合一的阴阳大化宇宙论中的天地人三才感应贯通的说法,就会发现这种对“咸”卦中心地位的强调,恰恰显现出儒家仁学体系中“立人极”之终极关怀。
下面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易经》咸卦之卦象以及彖传对咸卦卦辞的解读。咸卦的卦象兑上艮下,卦辞说:“咸:亨。利贞。取女吉”(高亨,第289页)。彖传对卦名、卦象与卦义的解曰: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同上)
按照这一解释,“咸”卦说的是天地万物男女之间的亨通感应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通过亨通感应化育万物众生并在这种亨通感应之中显现大德。这也就是说,天地之大道和大德通过感通、感应、感悉、感动、感情、感悟浸润渗透,进入世间人事,化育我们的道德人生,使我们从此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人(仁)。因此,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易经》彖传咸卦的解读中,已经包含了儒家哲学本根论与伦理学的全部要义。
这一将天地人事之感应感通与道德人心之情感感动关联在一起的做法,不仅贯穿在以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易经》及其《易传》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理论的传统中,而且也集中表现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文艺理论的传统中。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有了“诗言志”的说法。这一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在2000年前的《毛诗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发挥。第一,按照《毛诗序》作者的说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十三经注疏》,第269-270页)。这也就是说,诗作为“志之所之”者,主要通过抒发内心情感、感动的方式言说自身,而且,除了诗赋之外,还有“嗟叹”、“歌咏”、“舞蹈”作为抒情言志的方式。第二,《毛诗序》还指出,诗乐作为抒情感动不仅言说个人之志,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批判和道德教化的功能。一方面,诗乐之音作为抒情感动,呈现或者见证着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之顺和与乖失,所以,“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同上,第270页)另一方面,正因为诗乐尤其是民间诗乐的这种政治、社会和道德的见证作用,作为抒情感动的诗歌,同时也就有了“讽刺”、“风化”的功能。“风”首先是一种中国上古诗歌的体裁,是产生于当时各诸侯国且在民间流行的民歌体诗歌,与“雅”、“颂”相对。但显然,《毛诗序》似乎更强调由于诗歌的抒情感动而来的“风”的“风化”与“讽刺”作用。“风化”讲的是“上以风化下”,而“讽刺”则讲的是“下以风刺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诗教”的由来。“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感鬼神,莫近于诗。”(同上,第269-270页)在上的统治者可以发挥诗的感动作用教化民众,激励、培养良好美德,改变社会风俗,即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同上,第270页)。在下的平民百姓则可以“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通过诗的感动作用“以风刺上”,从而使“闻之者足以戒”,并进而“正得失”(同上,第270-271页)。
应该说,这种以《易经》与《诗经》为代表的将人类情感尤其是道德感动作为人类道德德性之见证与道德化育之起点的上古中国思想传统,在随后兴起并在过去2000多年中作为中土主流意识形态出现的、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中,得到了有意识和有系统的展开和发扬光大。这中间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孔子和弟子宰我之间关于“三年之丧”的道德根据的争辩。(参见《论语·阳货》)其中,宰我至少提出了两个论据来反驳“三年之丧”的传统礼法。第一是从行为之后果的角度来反驳,即“三年之丧”的实践势必导致礼乐崩坏的恶果;第二是以“旧没新升”、“钻燧改火”为喻来阐述行事不应拘泥于旧法,而应合乎时宜或与时俱进的道理。严格说来,宰我的这两点辩驳,并非完全背离夫子之道,但明显惹得老师不太高兴。不过老师并没有直接反驳弟子的论点和原则,而是换了一个角度,提出了“心安之为仁”的原则,这与宰我所认同的“后果”原则、“时宜”原则明显不同。也许孔子并不完全反对“后果”与“时宜”原则,但他更关注的明显是要回归礼俗之源头和基础,强调“心安”这一道德情感在日常的道德德性之培育与道德行为之评判过程中的优先与根本地位。在孔子反驳宰我所说的“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与“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同上)这两句话中,孔子提出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古礼”的原则,即“天下之通丧也”,一个是“亲爱”原则,即“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而在孔子这里,这两个原则高度统一,统一的根基就在于出自“父母之怀”的“亲情之爱”。应当说,孔子的这一将礼教、礼仪、礼俗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归结到人心感通、感动、感情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上接了《易经》、《诗经》所传承下来的中国上古伦理思想的古老传统,而且往下还开启了自曾参、子思、孟子到宋明理学,再到现代新儒家的中国伦理思想和哲学的主流意识。例如在中国儒学的传统中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所倡导的“心性之学”,在我看来,其要义无非就是这里所讲的作为道德情感的“人心感通”和“人心感动”。孟子将孔子的“心安”之说具体发展为“不忍人之心”,又称“恻隐之心”;不仅如此,孟子还将这种“不忍人之心”与人类的道德人心之本联系起来,与另外三种道德情感并称为人类的先天道德人心之四端,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参见《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这四种人类固有的先天道德情感乃是人类道德本心或本性的最好见证,也是区别于人类与非人的禽兽的最后界限所在。当然,作为“端倪”,这些道德情感的存在只是展现出人类成善成仁的可能性,它们还需要长期地被“养之”、“充之”,这也就是儒家后来所讲的终身学习、修养和道德成长过程。假若我们不善保养,忽视、漠视甚至残害这些作为道德本性之见证与端倪的道德情感,我们就会在道德上日趋麻木、冷漠、无动于衷,就会沦入如宋代大儒程颢所说的“麻木不仁”的境地。(cf.Chan,p.530)
六、儒家伦理之为情感本位的德性伦理
沿着道德感通和道德感动这一主流线索,来理解和把握中国伦理哲学、尤其是儒家伦理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伦理哲学传统,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儒家伦理传统在未来全球伦理中的独特位置。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的理念相近于德性伦理学,它的理论所强调的主要是如何培养和练就做一个善人和好人即二人君子的品德和品性,而不是寻求一整套理论理性的体系规则来判定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不该做。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的主流中,德性伦理学的基本形式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讲伦理学所寻求的目标无非是人的生活的幸福,也就是说,为人类寻求一种好的生活,而人的生活的好坏又是由有机生活本身的内在理性和本质目的所决定的。诸道德德性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是帮助我们达到和实现这种内在理性的本质生活目的所必不可少的卓越品德和条件,所以幸福生活、理性生活与德性生活是基本一致的。(cf.Aristotle,Book I,pp.1-18;Book X,pp.162-171)按照这一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方面是德性伦理学,另一方面又是目的论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伦理学。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内在理性生活的本质目的性,所以他对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似乎显得重视不够。而在我看来,以及根据本文上述的简要梳理,在人类哲学史上、尤其是在道德哲学的思考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也许可以视为最早赋予道德情感、即我在前面所分析的道德感动以实质性地位的伦理学理论。虽然同为德性伦理,但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目的论的假设不同,儒家伦理似乎更加强调“道德感动”的本然地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倾向于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定位为本质主义的德性伦理学,而将儒家的德性伦理学称之为情感本位的德性伦理学。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伦理学作为情感本位的德性伦理学,与西方近现代规则伦理学背景下的情感主义伦理学(Emotivism),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知道,情感主义伦理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大概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休谟指出,道德探究主要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也不可能是一个理性规则的问题;就其本性而言,价值问题是一个情感问题,所以不可能有普遍律则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也就是说,道德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为我们真正提供判断一个行为之好坏善恶的规则判准。(cf.Hume,Book Ⅱ & Book Ⅲ)这样,以休谟为开端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就势必走向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和困境。儒家的德性伦理虽然会认同休谟伦理学对情感在伦理学基础中的重要地位的承认和提升,但它有可能避开休谟式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相对主义结论及困境。⑧因为在我看来,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在规则伦理学范围内的争执,也就是说,道德的相对性或绝对性,是在说明道德规则之实践应用时的相对和绝对,即是在判定某个道德行为之道德性质时才会出现的困境。休谟式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张是,因为道德情感是主观的,而且会经常出错,所以不可能在普遍规则的意义上判定某个行为的道德善恶性质,从而道德知识不能声称具有像科学知识那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但在德性伦理学的背景框架下,道德情感的作用应该不会像在休谟式的情感主义伦理学那样,引向道德相对主义的结论,因为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普世规则或律令的认定和实施,而是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品格、德性的培育和塑造。这恰恰就是道德感动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人格和品德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次感动和不断感动中,不断地培育和生长起来。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在哲学上突破西方伦理情感主义的局限和困境,或者至少看到沿着这条道路有突破这一困境的希望。⑨
具体说来,我们知道,伴随着道德感动而来的道德判断具有双重判断的功能。第一个判断是判定这个行为的好坏,而第二个判断则是判定这个行为背后所见证的品质、品格的道德性质。按照情感主义的思路,我们很可能被一个虚假的行为所欺骗而感动。但按照德性伦理的观点,即使我们被一个虚假的道德行为欺骗了,这个虚伪行为所关联、见证的德性一般说来却极可能是货真价实的。这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种虚假的联系,但这个德性本身却是真实不虚的;我们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这个德性以及我们对这个德性所体现的道德价值的认可而不是其它。其它方面可能有错,即我们在实际经验生活中,经常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认错或弄错究竟是谁拥有这个德性,这个行为是否真正体现这一德性,等等;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一德性之为德性本身却不会有错。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感动所告诉我们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某个行为所感动,例如关公刮骨疗毒。关公面对刮骨剧痛,坦然镇定,谈笑风生,这一行为使我们闻之感动。休谟式的情感主义者可能会说,的确我们有很多人会感动,但我们的感动只能是我们的主观赞成或赞赏而已,不能构成普遍的道德律,即要求所有的人在相同情形下都照行。而且,我们还可能出错,可能被关公所骗。也就是说,关公很可能实际上是个骗子或魔术师,当时使用了某种技法,蒙骗周围的士兵乃至后人并使之感动。⑩但倘若更深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里的感动如前所述,实际上牵涉双重判断。感动的第一层判断是:关公的行为让我们感动。按照休谟式的情感主义的说法,这的确是一个个别的主观判断,也可能有误解或被误导。但伴随着感动的第二层判断则是:虽然关公刮骨疗毒的行为是让我们感动的直接原因,但这一“感动”的真正理由或根据却在于:关公刮骨疗毒这一行为所以让我们“感动”,乃是因为“勇敢”、“镇定”这些道德德性借此向世人明证或展现出来。如同我在前面所述,我们的第一层感动完全可能有误,但这种知识论或认知层面上的可能有误,丝毫不会影响“勇敢”、“镇定”之为感动我们的道德德性这一特质。这也就是说,真正“感动”我们的不是关公刮骨疗毒这一偶然的个别事实或事件,而是其明证或见证的道德德性。在这里,关公刮骨疗毒的事实可能有误、有诈,但“勇敢”、“镇定”之为感动我们的道德德性,则确凿无疑。
对道德感动之本质的这一把握,在我看来,恰恰正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特色。前面提到,宋代大儒程颢在解释孔子的“仁”时,曾经提出了一个“麻木不仁”的概念。“麻木”就是身体没有感觉了,这样就把“仁”理解为一种心灵、心体的感觉、情感。孟子的“四端”说则更突出地将人的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发端起源。在儒家看来,我们不是生而为人的,我们是成长为人的;道德修养使人成为人,使人和禽兽区分开来。所以说道德行为是从道德感动开始的。这样就回答了“伦理道德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哲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作为情感本位的德性伦理,儒家坚持道德不在于外在的加强义务、命令或律则般的普遍性规范,而是在于和源自于生活中人心的感受和感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让我们感动的不是“规条”、概念、律令,而是“品性”或“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各种律令形式的规范伦理或底线伦理都难以成功。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这些伦理学都过于强调了规条、规范的束缚作用、防范作用、底线作用,而忽略了伦理道德之人心教化、范导和感动的本性及特质。关于道德感动的以上分析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到,道德伦理的本性首先是示范而不是规范。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中,不是森严普效的道德律令、规条,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灵活现的道德感动,在引导、激发着我们去做好人、做好事,引导我们走向人性和生命的完善和圆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很需要理解和诠释儒家伦理学的原始价值和积极意涵。
注释:
①应当指出,何教授针对当今社会普遍道德沦丧、道德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盛行的情形大声疾呼,提倡普遍主义的道德底线伦理,有着相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何教授也注意到,底线伦理“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解、关怀和同情……”(何怀宏,第422页)但是,何教授试图从这种关切、同情、恻隐之类的“良心”出发,去建立作为日常道德社会生活的普世底线或规范律令的做法,在理论上隐含着根本的缺陷,因为这难以摆脱道德主观主义的立场。
②关于我对孔汉思立场的批评,见《道德金律与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王庆节,第302-311页)
③关于这一点,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何以见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个例子:村子里的人愤怒了,将通奸的恋人捆绑沉入水塘。在这个例子里,从情感分析的角度看,无疑会出现多种情形,即有人愤怒、有人同情、有人不忍……这里涉及的不是对一个单一道德事件的评判,而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大多是因为感到维系家庭完整的忠贞价值遭到侵害;同情的人之所以同情,多少是因为在其中看到了男女之间的真情真爱;而不忍的人之所以不忍,乃是对生命价值遭遇侵犯感到惋惜。当然,一般说来,通奸破坏了他人本来完整的家庭,的确有值得谴责之处。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通奸所破坏的是一个不值得保留的婚姻、一个充满压迫和压抑的婚姻、一个无趣而又强扭在一起的婚姻,此时它难道没有值得同情之处吗?在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对传统家庭的背叛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廊桥遗梦》中的男女主人翁短短几个日夜炽热的婚外恋情,难道没有值得同情之处吗?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这里同情的不是对家庭价值的破坏,而是男女之间相爱的真情真性。还有,被捆绑沉入水塘的恋人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不忍?这里引起不忍的不是他们破坏别人家庭的行为,而是即便有这种行为,他们的生命和身体也不该遭受如此残暴的对待。这也就是说,在感动的这一刻,感动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和事,感受到的是此时此刻对方所受到的折磨;感动者并没有想要将这一行为作为一个标准来理性地校验或证明它是否符合或归属某个普遍道德律令。因此,道德感动首先不是关于某个具体行为对错的判准,而是某些道德德性显现的当下见证。这样说来,对待同一件事情,周遭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感受的角度、氛围可能是不同的。
④舍勒曾经分析过这种情绪感染与传染的特征。(cf.Scheler,1992,pp.54-58)
⑤另外,舍勒也持相似的观点。(cf.ibid,1994,pp.40-42)
⑥例如,李泽厚就曾强调儒家以亲子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仁学”,其本质乃是一种“情感本体论”。(参见李泽厚,第18-22页)蒙培元也将儒学的历史解读为一部以情感哲学为主体的历史。(参见蒙培元)
⑦下面关于《易经·咸卦》经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解释线索,参照了张再林的《咸卦考》。(见张再林等编著,第32-66页)
⑧严格说来,休谟的情感哲学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休谟式情感主义伦理学(Emotivism)也许并不完全等同。但由于本文不是关于休谟情感哲学的专门讨论,故不考察这一细节。
⑨在当代哲学中,艾耶尔对休谟式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有经典表述。(cf.Ayer,pp.102-112)麦金泰尔则对这一哲学立场进行了有力批评。(cf.MacIntyre,pp.1-35)
⑩《三国演义》中更恰当的例子也许是:赵子龙坡上浴血救幼主,刘玄德马前摔子得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