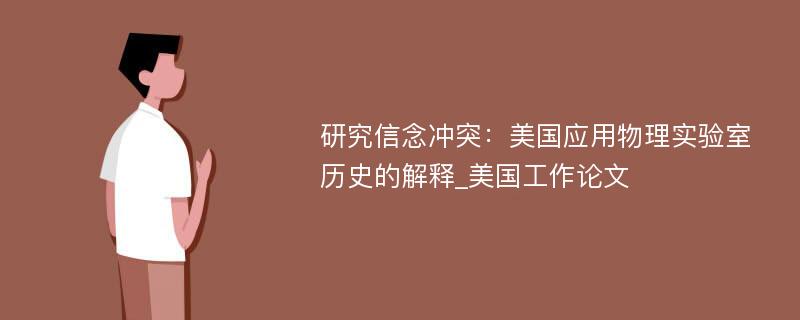
研究信念的冲突:对美国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历史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信念论文,实验室论文,冲突论文,物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4)03-0118-03
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纯科学信念”(pure-science ideal)和“应用科学信念”(applied-science ideal)的冲突。这种信念冲突作为深层的文化因素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本文通过考察美国应用物理实验室(Applied Physical Laboratory,简称APL)的发展史,来说明这种研究信念冲突的历史影响。这种分析将对讨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成立和美国科学发展的模式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1]
一 “纯科学信念”与“应用科学信念”的冲突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存在“纯科学信念”与“应用科学信念”的冲突,到19世纪80年代,这种冲突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已经变得明确而公开化。分别为这两种信念奠定话语基础的是亨利·罗兰(Henry Rowland)和罗伯特·瑟斯顿(Robert Thurston)。
这两种研究信念都旨在说明“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前者后来被称为“科学”,后者后来被称为“技术”)的关系。“纯科学信念”认为,“纯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只不过是“纯科学”理论的直接应用,因此,“应用科学”从属于“纯科学”;“应用科学信念”认为,虽然“应用科学”会应用到“纯科学”知识,但后者要根据实际进行理论转换才能应用,而更重要的是,“应用科学”主要是工程师们运用科学方法(主要是培根归纳法)对实践进行研究而获得的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它并不附属于“纯科学”。以这两种信念为基础,研究人员衍生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学术地位的多种理解,比如,持“纯科学信念”的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是无功利的、自由的;大学应该是“纯科学”的基础阵地,等等。持“应用科学信念”的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指向应用,“应用科学”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和“纯科学”有同样重要的学术地位,等等。
19世纪末美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兰,在1883年至1893年间的多次演讲中,为“纯科学信念”奠定了话语基础。在《为纯科学辩护》的演讲中,他说,“现在,特别是在美国报纸上,把科学的应用(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与纯科学混同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人,他们盗用了以前的伟大思想中的一些点子并把它们照搬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而发了财,现在他们却常常甚至比那些伟大的思想的原创者还更受人称道……”他“厌倦看到我们的教授们因舍弃纯科学追求应用科学而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并坚持纯科学能在教育学上培养德性这样一种信念。
为“应用科学信念”奠定话语基础的人是在史蒂文斯技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担任机械工程教学工作并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1880年)第一位会长的工程师瑟斯顿。虽然他在弗吉尼亚力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承认,“19世纪史无前例的物质‘进步’是发明家和机械师们把物理科学的事实和规律应用于他们的生活的实用目的的结果。”但是,他更强调,“应用科学”是独立的研究、教学和实践的领域。在这次演讲中以及其它多次演讲中,他都强调,“工程研究人员应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创造了一批称作‘应用科学’的知识,而工程师们则在大学里学习这些知识,并在工作中实践它们。”[2]
以罗兰那类措辞为基础的“纯科学信念”和以瑟斯顿的那种措辞为基础的“应用科学信念”,这两种对立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在美国文化中一直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模式。本文将通过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的历史来加以说明。
二 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成立:万·布什与图夫的研究信念的冲突
应用物理实验室于1942年3月成立,它的前身是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下辖的T部,它是为了加快T部研制的近炸引信的生产与应用而成立的。从1940年开始,T部一直在研制一种无线电近炸引信,到1941年底研制成功。这种引信可用在防空飞弹上控制炸弹的引爆时间,从而大大提高攻击敌机的精确度。这对于海军的防空能力有重要的意义。正是为了指导这种引信的生产和使用,应用物理实验室才应运而生。在筹备阶段,就应用物理实验室是否有必要成立和采取什么样的运作方式、管理形式等问题上,万尼瓦尔·布什(V.Bush)和图夫(Tuve)及海军方面产生了分歧,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持不同的研究信念。
布什是一个持“应用研究信念”的人,[3]不过,本文认为,布什持的“应用科学信念”是相当保守的。布什曾这样区分“应用科学”与“工程”这两个概念:应用科学是在经济环节之外开展的、力图将“纯”知识转化为一种适合于应用的形式的研究;“工程”则是在经济环节中应用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的活动。利用这种区分,布什把与工业生产(经济环节)相连的“生产工程”(即由实验室样机向大规模工业生产转化的过程)排除在“应用科学”的范围之外,这表明布什想极力维护“研究”的纯正“学术”传统。本文认为,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布什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都采用了将研究(Research)、开发(Development)与生产工程(Production engineering)相分离的科研组织模式。这两个研究组织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只负责研究开发工作,而不负责生产工程中的技术问题的研究和指导。布什认为,生产和使用是工业和军方的事情。照这种思维模式,布什认为,T部设计和开发出近炸引信的可实用样品,这是OSRD的“学术”研究人员的工作范围,而至于它的生产和使用中的技术问题则是公司与军方的事。因此T部在实验室中试制出了引信就算大功告成,以后的工作应该转交给公司和军方去做。但负责T部的图夫持较激进而实用的“应用科学信念”。他说,“应该打破这种将学院研究人员与他们的更有实力的军方和工业伙伴分离开来的界限,研究和开发的价值就体现在所研发的产品的实际应用当中,因此跟踪引信进入到工厂生产和战场使用过程中,这完全是实验室研制工作的一部分。”图夫的这种意见表明他与布什分别所持的研究信念的冲突。[4]在这种分歧中,海军是否认识到引信的价值以及它持什么样的研究信念就成为关键的因素。海军一贯所持的实用主义研究倾向和近炸引信的重要战略价值决定了海军倾向支持图夫的方案。这样,1942年3月,海军对OSRD拨款200万,用来资助近炸引信向大规模生产转化的工作。布什和图夫达成妥协,布什同意图夫成立应用物理实验室来负责近炸引信的后期研制工作,包括生产和使用中的技术指导;作为交换条件,图夫必须向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的指挥办公室汇报工作,并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托管应用物理实验室。这种妥协既照顾了布什等人的“学术”研究的观念又照顾了图夫的激进的应用研究的观念,而海军的资助则是分歧得到解决的关键因素。
为了组织引信的生产,图夫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他建立了内部报告制度,使他能全面了解引信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其次,图夫分派了许多参与过引信设计的研究人员到各生产线上对批量生产引信进行技术指导;再次,为了保证军队正确使用这种引信,图夫指派几个该实验室的专家到海军中对引信进行宣传并向海军官兵教授使用近炸引信的有关技术。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图夫建立了一个由实验室全程控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的模式,正是这个经验使得即使到了战后,应用物理实验室在导弹研制项目中仍试图坚持这种控制权,拒绝把生产工程的控制权交给克莱克斯(Kellex)公司负责。
三 战后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民用化过程:多种研究信念的冲突
二战即将结束,战时的科研组织开始从军用转向民用。这时,应用物理实验室面临着是解散还是寻找新的资助伙伴以继续存在的生存选择。布什认为,战时的科研与开发局和国防研究委员会都只是为战时服务的临时机构,和平时期的研究人员不应该受到军方的应用观念的限制,以致把“研究”的目的指向军事应用。总之,布什所坚持的“学院文化”式的保守的“应用科学信念”使他非常警惕科学研究的自由所受到的威胁,他反感来自任何利益方面对研究自由的控制,不管这种利益是经济的(这一点从他把“应用科学”定义在经济环节之外可以看出来)还是政府(包括军方)的。因此,1944年9月,他宣布将解散战时科研与开发局。他推荐应用物理实验室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机构。和布什的保守观念相反,图夫的“应用科学信念”是激进的。他积极倡导军事研究性质的“应用研究”,极力想扭转研究人员对军事研究的反感态度。他甚至认为,“公众、国会、军方和研究人员将决定未来人们是否愿意为这项工作提供机会,决定对这项工作所持的观念的性质,甚至决定着它将获得的资金数量。”他说,“国家安全已不再只是军方的事情,因而有必要使民众意识到他们对国防所肩负的责任和重大意义,并为他们履行这种责任提供多条途径。”因此图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长期由军方资助的组织——“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RBNS)”,而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战时组织模式将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就该实验室的将来而言,他说“我们试图保存的并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即APL,笔者注),而是一个有着更广泛的基础的,即与全国许多研究组织和群体相连的、实现技术的应用的、囊括一切的模式。”显然,图夫的重点并不在于维持实验室本身,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着更广泛的科研组织的支持作为基础的永久性军事研究组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鲍曼(Isaiah Bowman)则另有打算。他持“纯科学信念”,比布什更激进地维护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副报告中,鲍曼领导的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鲍曼的“纯科学信念”。报告声称,“虽然一些工业科学家也从事‘纯研究’,但大学才真正地在过去是,而且也将继续是从事纯研究的中心”;“美国的‘应用科学’已发展得很好了,但‘纯科学’却落后于欧洲。”基于这种“纯科学信念”,鲍曼这样为应用物理实验室设计未来。他打算在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一个新的系,称为“合作研究院”(ICR),以该院的名义接收实验室作为该系的一个最大分部,但并不是以大学的名义来接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作为大学的教工。也就是说,不是把它当作大学的一个教学科研单位。鲍曼认为,应用物理实验室是不能承担教学任务的,因为就该实验室曾编写的那些技术指南来看,它们只适合用来做生产和使用的技术指导,而不适合教学。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应用物理实验室所进行的研制项目是一个被海军列为保密的项目(APL在1945年1月又开始执行海军资助的导弹研制计划),这令鲍曼很反感。他认为,海军对科研成果的保密妨碍了研究成果的共享,这使得该实验室的成员不能参与到大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中来。这突出地反映了海军对基础研究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与纯科学家对基础研究所持的纯“学术”态度之间的冲突。在科学家看来,基础研究是没有特定的实际用途的知识与活动,它虽然最终能作为技术的“资本”,但他们相信美国在开发军事技术上能快过任何国家,因而基础研究与国家安全并不直接相关。因此国家应该促进科研成果的公开与交流以促进基础研究,从而更好地发展和更自由地积累知识财富。而就海军而言,许多基础研究本身就与军用技术紧密联系,甚至有着直接的军事用途[5],为此海军对它所支持的研究项目进行了保密分级,有些研究成果几乎只有当事人知道。海军的这种做法使得科学家自由研究的信念极大受挫,引起许多科学家的不满。鲍曼因此认为,要是应用物理实验室仍然为军方工作,它就不可能实施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因而,鲍曼急于想断开实验室与海军的联系。另一方面,为了大学和实验室的经济利益,他想让该实验室与民用工业签订合同,靠出售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专利来获得利益。同时鲍曼要求应用物理实验室把研发与生产工程分离开来,要求找一个公司来负责导弹试验样品的设计和生产工程中的技术问题(鲍曼选择了Kellex公司)。鲍曼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应用物理实验室的研究更具学术性,而不必受“应用”所左右。同时,因为应用物理实验室并不属于大学的教师编制,只不过是一个校办产业,因而也就保证了大学的“学术”纯洁性。
实验室的新老两代成员都极力反对鲍曼把实验室对生产工程的控制权让与Kellex公司的做法,也反对鲍曼的歧视政策,因此积极谋求海军在战后对APL的资助。这样,由于各方面意见的不一致,实验室的前途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7年,海军的资助又一次对APL的前途和组织形式起了决定作用。1947年,海军迫切需要一些导弹布置在船上,哪怕只是一些实验样品。这再一次突出了悬而未决的应用物理实验室与海军、霍普金斯大学、Kellex公司的关系的问题。第三任实验室主任拉尔法·吉伯森(Ralph Gibson)和其大部分成员都认为不能与Kellex公司一起来分享实验室对导弹研发工作的控制权以及海军给予的利益;同时,作为技术专家和研究者,他们认为导弹不只是一件产品,而且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以此强调实验室工作有着与基础研究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强调“应用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应用科学信念”),他们不愿其他任何人来重写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不与Kellex公司合作,而由实验室自己来负责生产工程。他们也要求鲍曼把实验室当作大学的系部来接纳它。这个要求与鲍曼的将大学跟一切与导弹的生产相关的事务分开的打算相左,但鲍曼出于利益考虑也只好接受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验室的成员始终坚持了图夫所倡导的“应用科学信念”,坚持对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全面控制,这再次为它赢得了最佳的生存条件。而同时它也通过在和平时期重组一种民用与军用相结合的模式而获得了学者职业的地位,即它终于成为了大学的教学研究单位,而且后来它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成为实验室中惟一的一个不受保密限制的基础研究阵地,这又多少照顾了鲍曼的纯科学情结。
四 结语
本文从科学和技术共同体内部和外部的研究信念的冲突的角度来揭示美国的应用研究的组织模式的形成原因,这种视角有一定的编史学意义。以前,我们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探讨二者在科学和技术史中实际上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本文的研究则说明,我们更应该注意,在历史上,人们是怎样去理解二者的关系的,以及这种理解对科学技术的组织和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3-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