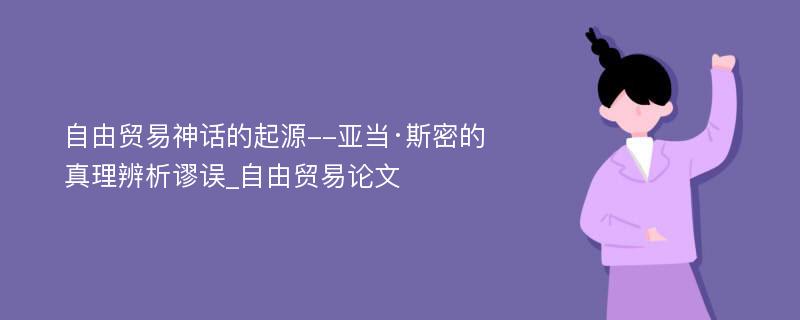
自由贸易神话的起源——亚当#183;斯密真相辨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起源论文,自由贸易论文,真相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33.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3—0141—17
大凡确立一种意识形态,必然要造神,亚当·斯密就是为确立自由贸易意识形态而打造的一方尊神。概而言之,流行的亚当·斯密神话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自由贸易论是由亚当·斯密首创的,正如他首创了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斯密是突兀而立的经济学巨人;
●由斯密首创的自由贸易论,连同其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其无比的科学性、革命性和雄辩性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接受;
●斯密的学说,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贸易论,有力地推动英国率先走上了一条增进国民财富的工业化道路;
●斯密学说不仅对英国是有效的,而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有遵循自由贸易论等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才能让世界实现持久的共同繁荣。
围绕亚当·斯密的造神运动至今一直在发展着。2006年10月29日晚,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宣布,斯密的头像将荣登20英镑钞票。次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当年《泰晤士报》刊登的讣告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如今亚当·斯密将成为20英镑钞票上的历史人物,他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地位从此不可动摇。……他撰写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用简称——引者按]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并认为个人私利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益。他的理论成为英国19世纪工业力量的奠基石。”① 神话不仅见诸报章,而且早已流布学界。例如,2001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严肃著作《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伟大思想家的生平与理念》,在其开篇“第一章:一切源自亚当”中便称:“1776年是一个先知预言的年份”,当年宣告了“政治自由和经营自由,二者相互协作开启了工业革命”;“《国富论》是全世界都聆听到的思想炮弹”,“是一份经济独立宣言”,“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斯密“写就了赢得繁荣和财富独立的普适性公式”,“正如乔治·华盛顿是新生国家之父,亚当·斯密是新创科学之父,他是财富科学之父”;等等。②
透过“斯密崇拜”的迷雾而深入历史,却可发现,斯密神话是通过歪曲历史、掩盖事实、高调兜售、反复灌输才编织起来的。有足够证据表明,亚当·斯密并无开拓性的创见,其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甚至阐述得比他更加周密和系统。只是当英国的产业发展还处在需要保护主义的阶段时,他人早熟的理论便注定无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即使到斯密去世的1790年,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尚未充分确立,自由贸易论之类的自由主义药方尚嫌超前,故而,就是斯密也还要等待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名满天下。与一炮打响的传说相反,《国富论》的出版不仅在斯密生前,而且在其死后初期,都未能为其作者带来一举走红的盛誉。可以肯定地说,远不是“英雄造时势”,即根本不是因为斯密学说而让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从而奠定了什么世界繁荣的基础。历史真相恰恰是“时势造英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势找英雄”,即英国偏偏是依靠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政策才率先确立了工业竞争优势,现实的需要此时呼唤相应的意识形态,于是,幸运的亚当·斯密就被拉出来梳妆打扮一番,人为打造的神像从此便成为服务强者利益的最佳工具。揭开自由贸易论确立阶段的这个历史盖子,将有助于从源头上打破弥漫在我们周围的自由贸易神话,从而清晰地透视这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原形。
缺乏创新缘何暴得大名
以为斯密天才般地创立了自由贸易理论,这种认识在西方,进而在整个世界,早已凝固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本新近的中文版西方著作言之凿凿地宣称:“自由贸易原则是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的。”③ 中国的教科书也称:“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雄辩地证明了自由贸易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从而建立了古典主义的贸易理论。”④ 而且,除了把自由贸易论的原创权归于斯密外,人们普遍认为,斯密还首创了支撑自由贸易论的那些基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比如,天赋自由、经济理性、追逐私利促进公益、放任自流、看不见的手、管制有害、劳动分工、贸易共荣,等等,据说都是由斯密首先提出的。在斯密著作中,尤其在《国富论》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到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只是它们纯由斯密转述而来。细究经济学说史可知,不管是自由贸易论,还是那些相关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实际上无一由斯密原创,它们本质上都是斯密之前时代的产物,在斯密时代都已成为学术常识。
在自由贸易论这个斯密似乎堪称鼻祖的领地,斯密不仅不是开风气之先的首创者,而且他也未必后来居上。即使按照偏于保守的估计,在亚当·斯密之前,至少有五位作者实为“自由贸易的完全的支持者”,至于倡导“更自由贸易”者,则人数起码还可翻倍。⑤ 据查,英国的经济学思潮在17世纪便呈现自由化的倾向,那些被斯密笼统地冠以“重商主义者”称号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在日益转向“重商自由主义”的立场。“多数重商主义者,至少从17世纪末期起,更应被称为自由贸易者,而非保护主义者。”⑥ 所以,有学者提醒道:“把向自由贸易的任何转变归因于斯密,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人所熟知,许多所谓重商主义文献已在反复讲述‘自由’的好处。”⑦ 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托马斯·孟……查尔斯·达文南特、尼古拉斯·巴尔本、乔赛亚·蔡尔德,特别是达德利·诺思爵士,已经提出了倡导外贸自由的理论,其阐述的明确和清晰程度一如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亚当·斯密。”⑧ 此外,比斯密早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其他人物,从威廉·配第到亨利·马丁,都“提出了赞成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普遍原理及部分理由”。⑨ 另外,人所共知,长期游历法国的斯密深受以佛朗索瓦·魁奈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在自由贸易问题上,重农学派也许真正是第一个主张无条件自由贸易的集团。”⑩
具体从学理上说,远在13世纪即有一位人称“米德尔顿的理查德”的欧洲大陆人提出了用以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初步模型。(11)“塞缪尔·福特里在1673年提出了亚当·斯密一个世纪以后才会提出的大致相同的内容,即自由贸易会让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12) 亨利·马丁、雅各布·范德林特、马修·戴克、乔赛亚·塔克等均早于斯密,探讨了要素禀赋和优势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交易之利弊等命题,塔克、戴克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比斯密更加自由化。尤其是马丁在1701年发表了坚定并系统地支持自由贸易的政论册子《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此书批评了贵金属主义论;认为不应对进口设置任何限制;强调由自由进口带来的竞争压力将最终让整体的英国经济受益;提出自由贸易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等等。(13) 贸易学说史家不止一次指出,“马丁在许多方面以比亚当·斯密更为深刻的推论阐述了自由贸易的逻辑”。(14) 再有,艾萨克·杰维斯1720年出版的《世界贸易体系或理论》对国际交换和支付作过深入分析,形成了首个国际经济总体平衡理论,得出了“全面呼吁普遍自由贸易”的结论。其理论被后人认为是“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正式体系之一,为自由贸易作了最有力的实际论证。”(15) 还有,德国人厄内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在其出版于1722—1723年的《论君主的财富》之第二、三卷中,已经阐述了利用比较优势条件、开展国际分工、进行互利交易的思想,而且据考证斯密了解此人著作,斯密有关分工的论述“有时甚至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样的”。(16) 此外,法国人诺埃尔·安托万·普吕什在其出版于1732—1750年间的《自然观察》之第六卷中,已经“提出了通常但是错误地被称作‘李嘉图模型’的谷物经济模型”,而且据考证斯密也是完全能够接触到该著作的。(17)
与自由贸易论关系密切的其他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同样也非斯密首创。关于天然自由理念,包括天赋贸易自由理念,且不论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古典哲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这方面的论述,至少在16、17世纪,西班牙和荷兰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已有系统理论。道理很简单,比英国领先一步赢得海上霸权的强国自然更为迫切地需要为海外征服权和和贸易权进行辩护。弗朗西斯科·德·费多礼亚于1557年宣称,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拥有自由通行等权利,这是得自天赋的“国家之法则”。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于1612年也认为,基于“国家之法则”,自由的国际商业交往天经地义,所有民族和国家都不应违背。雨果·格劳秀斯在《论海洋自由》(1608年)等近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之作中认定,所有人都有权从事相互间的自由贸易,并拥有通过“正义战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18) 德国法学家塞缪尔·普芬多夫于1660年也作过类似的表述。(19) 所以,约瑟夫·熊彼特指出,虽然斯密“认为自己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理由是他早在1749年就讲授了这一原则。”但实际上,“前人例如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都已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天赋自由原则”,“斯密的分析骨架师承于经院哲学和自然法哲学家,不仅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著作中有现成的这种骨架,而且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也向斯密作了传授。”(20)
关于经济理性、追逐私利促进公益等理念,查尔斯·达维南特在1695年就宣称,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存在着一条超越任何政府法规的法则,它本质上以个体的私利为基础。(21) 同样,强调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和谐的观点虽然被谬称为堪称“经济学核心矛盾”的“亚当·斯密悖论”(22),然而,“肯定无疑,关于市场上行为自私的个体可以促进公众利益这一想法早在17世纪的著作家那里就已相当普遍。”(23) 的确,达德利·诺思、路维斯·罗伯茨、亨利·帕克、理查德·堪布伦、乔塞亚·蔡尔德等在17世纪发表的著作,乔赛亚·塔克、詹姆斯·斯图尔特等人最迟至1760年代发表的著作都已提出,个人自发的谋利行为可以促进公共的福利;商人的行为虽然动机在于自利,但总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最有名者当数伯纳德·德·曼德维尔,他于1714年出版《蜜蜂的寓言:私人之恶,公众之福》,正如其书名所示,他认为对奢侈和自爱的追求会带来一个勤勉的社会和一个繁荣的经济。法国的皮埃尔·勒·佩桑·布阿吉尔贝尔写于1690—1710年间的作品同样已经提出,私利驱使下的个体虽然谋取个人利益,但客观上却在促进公益。(24) 据考证,曼德维尔和布阿吉尔贝尔本身还是受到了更早两位法国道德学家皮埃尔·尼古拉和让·多马的影响,斯密的观点与其十分相似(25),从中至少可见渊源之流长。
关于放任自流、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等理念,斯密亦非原创者。在17世纪,西欧的经济思想中已包含两股思潮,即在所谓的重商主义之外,还存在着自然法哲学思想,后者早已在呼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有名者就是法国所出现的经济自由派别,“放任自流”一词原即来自于法文laissez-faire et laissez-passer(自由生产、自由贸易)。布阿吉尔贝尔早于斯密揭示了市场通过价格所发挥的连接和协调买卖双方并使之竞争的功能,得出了经济繁荣并不太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普吕什也提出了斯密以后重复的观点,除讨论垄断是否可取、劳动分工有何意义之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甚至“看不见的手”这些观点都已出现。此人著作有英文译本,且为他人广泛转述。(26)“1749—1750年,产业上的天然自由思想并非仅仅限于斯密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在苏格兰同他直接交往的人们当中也很流行。大卫·休谟和詹姆斯·奥斯瓦尔德当时也就该问题有书信往来。”(27)“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统共只分别出现过一次,而且是指“自然法则的体系”,而非后人理解的“市场”。(28) 相反,有关市场价格机制的“英国渊源可谓举不胜举”。(29)“甚至重商主义文献中也包括了很多可以被恰当地视为放任自流思想之先声的东西。”(30) 一度担当斯密赞助人的凯姆斯勋爵在其1774年出版的著作中“显示出充分了解决定价格的诸多力量。”(31) 理查德·坎梯隆也对市场的自我调解机制作了非常清晰和成功的解释。“斯密之前的许多作者都已认识到在某些部门存在着自我调整的力量,……例如杰维斯和休谟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诺思、曼德维尔、乔赛亚·塔克关于国内市场、劳动和资本市场的看法。”(32) 所以,经济学说史家认定:“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坚持并没有像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有激进意义。”(33)
关于劳动分工理念,虽然《国富论》中以扣针为例论述劳动分工的第一章往往最为人传颂,然而,它不过在重复常识。“人们错误地把发现‘劳动分工’归功于亚当·斯密,可古希腊人都熟知将工作分给专门行当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我还没听说斯密之前有哪个经济学家没能对此有所观察并对其益处有所评论。”(34) 费尔南·布罗代尔也说过:劳动分工“这个旧概念远在亚当·斯密以前,已被威廉·配第、厄内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弗格森和贝卡里亚所指出。”(35) 的确,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写成,1690年出版)等著作中曾分别以织布、船运、制钟为例论述过专业化分工以及规模经济问题。斯密之前深入分析过分工问题的至少还有马丁(1701年)、曼德维尔(1714年)、亨利·马克斯韦尔(172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1729年)、塞缪尔·麦登(1737年,其所著《每周观察》见于斯密个人藏书)、弗朗西斯·哈奇森(1755年)、约瑟夫·哈里斯(1757年)、亚当·芬格森(1767年)、乔赛亚·塔克(除1774年出版物外,其另有两部著作论述分工问题,斯密拥有其中之一)。他们的探讨涉及专业化分工导致技能熟练、效率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改善、成本和价格降低、对劳动者综合要求减少、分工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此外,普吕什(其著作英文版问世于1739年,以“针”为例讨论分工问题),以及法国的《百科全书》(就以“扣针”为例论述分工之益处)等亦被认为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36) 斯密有关分工可能带来异化后果的论述则受到了法国哲学家卢梭的影响。(37) 再有,法国经济学家杜尔阁出版于1766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中已提出了十分完备的分工理论。(38)
以上从他人研究中勾勒出的史料清楚显示,通常归功于斯密的那些基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实际上均非斯密首创。即使不以《国富论》正式出版的1776年为界,就是按后经发现写于1763年的12000词的“国富论早期草稿”衡量,甚至再考虑更早的著作酝酿期,这一结论的总体有效性仍不容否定。正因如此,熊彼特评论道:虽然“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理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39) 雅各布·瓦伊纳也认为,“在经济分析的具体点上,一些前辈做得比斯密要好,斯密未能充分吸收休谟、重农学派和杜尔阁的某些真正有价值的分析性贡献”;“在每一个细节上,单独地看,斯密看来都有大量前辈。只有在很少细节上,他能与前辈中最好者具有同样的深刻性。”(40) 了解斯密之前经济学发展史的人对此感到毫不奇怪,因为“在[1620年代——引者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某种我们可以称为现代经济学的东西诞生了。这决不是斯密及其最密切盟友的一项发明,相反,它缓慢地浮现,在此过程中,市场分析的工具箱逐渐完备并日趋复杂。”(41) 作为佐证,请注意这几个事实:《国富论》出版之前,根据英国18世纪一位文献家所编订的书目,英国经济学领域发表于“1557—1663年间的作品接近2400部”,况且“一些相当著名的著作尚未列入其中”,仅这位文献家本人便收集了1500部书籍和小册子;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欧“在1662—1776年间已经拥有最高质量和兴致的贸易、商业和政治经济学作者”,“以后将成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持久核心的那些问题,随同由这些问题的方法、理论和政策而产生的大多数经久不息的对立观点(基本上至今仍未有定论并经常激烈争辩着),都可发现已在该阶段的著作中开始被人探讨”(42)。显然,斯密之前的两百年中,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已经存在高度发达、十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并不新鲜!
人们不禁要问,缺乏创新者缘何能够浪得虚名,就如取得创新者却何以未能名至实归?如果斯密拥有的盖世盛名不完全来自学术因素,那么,是什么样的非学术因素在起作用?看来,这倒是一个真正堪称“经济学核心矛盾”的“亚当·斯密悖论”。
在清理斯密与其前人自由贸易方面的思想渊源关系时,你不能不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反常”现象所震惊。既然亨利·马丁早于斯密75年就“在其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贡献方面甚至超过亚当·斯密”,为什么马丁未能脱颖而出?同样,既然在18世纪早期,卡尔就已触及比较优势概念,还有,普吕什已提出“李嘉图模型”,他们怎么就未获世人青睐呢?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真正的先行者不仅未能获得应有的名声,甚至还无一例外地几乎都被彻底埋没!继1701年初版后,“亨利·马丁的小册子在1720年重印过,因此不可能为其同代人完全忽视。但是,他的论辩看来未能引起任何见诸文字的讨论或反驳。”更有甚者,马丁此后长时间内居然“未被引证或者追随,直到在19世纪早期才被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从可能的湮没中拯救起来。”(43) 近至1983年,还有人在进一步证明马丁确为《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之作者这样的问题。(44) 一个“在前斯密作者里出类拔萃堪称异数”的自由贸易理论家不仅未能如斯密般名扬天下,反而差点被历史尘封,这是令人诧异更启人深思的问题。无独有偶,全面阐述了普遍自由贸易的“杰维斯的小册子很长时间内似乎几乎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以后虽曾获得一位收藏家的极高评价,但一直要过了两个世纪,即到1930年代,才由雅各布·瓦伊纳“充分地重新发现杰维斯的著作及其重要性。”然而,此等历史现象决非仅在英国偶然发生。最早在法文版著作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等重要思想的德国人卡尔居然也“被忽视了太长的时间”,也是在两个世纪之后才由经济史家重新挖掘出来,并被奉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45)
这几个自由贸易论的真正先驱,在英国和法国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仅未能受到追捧,反而几乎同被历史埋没。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即既然(政治)经济学涉及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按照斯密自己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46),那么,在这样的领域里,一个理论及其创造者,难道仅仅是具有原创性或者新颖性或者逻辑性或者科学性,而不切合当下现实的需要、不计及政策建议的后果,便可以成就功名吗?换句话说,与现实利益紧密挂钩的理论及其首创者,其废存和沉浮难道可以不受现实的影响或者选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几位自由贸易论先驱终究被淘汰,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理论太过超前于现实,而超前也就是不合时宜。毫不奇怪,“当英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舆论依然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思想时,杰维斯的小册子看来对其同代或后来者甚少或者没有影响。”同样,马丁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当时的政治圈和舆论界也自然只能“不受欢迎”、“简直被置之不理”,“不得不再等待几乎一个世纪才会获得人们坦然的赞赏。”进而言之,既然英法两国迟至18世纪都还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国家政策的基石,那么,超前的自由贸易论只会成为危及国家利益的异端邪说。这绝非夸大其词或者危言耸听,超前的自由贸易论的确曾被视为异端邪说。沃尔特·贝奇豪特在1895年便说过:“在现代英国人看来,‘自由贸易’是令人生厌的正统教条中的一条普遍真理,因而他难以充分地记得,一百年前它不过是不可想象的异端邪说。那个世界的全部商业法则都立足于保护主义的理论。”(47) 以此为背景,前述先驱屡被埋没的“反常”现象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足可让人悟出斯密成名背后的玄妙因缘。
现实需求选择理论工具
显而易见,在英国或其他国家尚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确立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之时,不管有多么完善合理的自由贸易理论,它也难免束之高阁甚至千夫所指的命运。反而言之,既然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赢得了综合的产业竞争优势,现实的需求便注定要催生或者挖掘出一套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不管它叫什么名号,也不管它是否原创。正是现实需求这样的大环境制造了一个神化的斯密幸运儿。这样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熊彼特的看法就是:“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但斯密的观点并非很特殊,而是当时流行的观点。”(48) 熊彼特称斯密与时代风尚完全一致,这是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中作出的判断,它道出了斯密名声鹊起与时代需求在宏观上的吻合性,这种吻合性在对比斯密与其自由贸易思想先驱者的不同命运时尤可清晰地观察到。
当然,在熊彼特的宏观大框架之内,如果具体深入历史细部,则尚应看到,斯密还是比熊彼特承认的要稍微超前于其时代。(49) 从《国富论》面世的1776年到斯密去世的179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总体上尚处于发动展开阶段,英国还未确立充分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依据新近的研究,必须承认,工业化是一个比曾经认为的要缓慢得多的过程。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显著的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分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50) 既然如此,现实需求应当不会一味地追捧自由贸易论,不管该理论由谁提出。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从而在微观上也彰显了斯密暴得大名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吻合性。与流行观点相反,斯密远不是随《国富论》的出版而一鸣惊人,不要说在他有生之年,就是在故去后的至少10年中,他都未能享有日后的盛誉。“《国富论》出版之后大约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开始出现清晰的证据,表明这部书在首要的经济思想家那里确立起权威。”(51)“有许多证据表明,虽然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后又生活了14年,但斯密经济学的胜利终其一生都没有到来。”(52) 很显然,历史还需要等待英国产业竞争优势充分确立之后才会把斯密转述的自由贸易论推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那种认为《国富论》立刻成功的观点一直是西方历史学持久不衰的陈词滥调之一,可是缺乏清晰的证据来证明之。”(53)
考察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迟到的成名过程,可以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实际上主要是英国当时的现实需求在物色和锻造意识形态工具。从发行数字看,《国富论》1776年的初版印数据推测不过500—1000册,近两年后出第二版,印500册,再过六年,即1784年始出第三版,印1000册,前三版跨越的10年里总发行2000—2500册。1786、1789、1791年,《国富论》第四、五、六版问世,总发行4750册。虽就初版发行量,出版商认为,“作为一本需要人们深入思考才能有所收益的书,其销路比我预料的要好”(54),但深入研究表明,公众对《国富论》的需求只是在斯密一生的最后五年中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55) 然而,即使是新近出版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也还在重复不实的陈词滥调,称《国富论》“很快就得到了成功,第一版的两卷本几乎一下子就告售罄了。该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为有利的热烈欢迎,而它的影响……那么巨大而又广泛”云云。对照《国富论》的有关发行数字,哪怕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无法给人以《国富论》不胫而走、斯密一举成名的印象。事实上,重弹不实老调的人随即也不得不承认,“确实,要使他的著作产生实践效果需要经历时间。……直到1820年代,英国的关税壁垒从来都没有实行过什么重大的削减。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定居法》直到1834年才撤销……”(56)
从最初的书评看,虽然绝大多数较有声望的刊物对《国富论》作出了反应,但所有评论家只是笼统地说,斯密的“主要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却并未指明斯密的观点与既有观点有何重要区别,也并未提到“哪些观点会对英国社会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即使是斯密的友人,包括休谟,在《国富论》出版后致作者的信件中固然对斯密给予了颇多的赞誉,但看来也是礼貌祝贺多于精当评判。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最初20年之前,许多人认真地探讨过他的论点,也没有证据可以支持那种依然通常的看法,好像斯密的著作‘与时代精神完全合拍’,同代人在不知不觉间实际上会成为他的‘信徒’”。(57) 在斯密余生,舆论界的此种反响平淡的状况未有改变。有研究者在考察了当时的主要刊物《每周评论》和《批评》的反应后得出结论,“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合理地断言,18世纪下叶的两份重要刊物到亚当·斯密去世的1790年都没有把他引为经济政策方面的可靠指导者。”甚至斯密家乡苏格兰的刊物《苏格兰人杂志》和《爱丁堡每周杂志》也并未“显示对斯密的任何特别兴趣”,它们没有“特别有心去支持自由贸易的说法”。(58) 可见,《国富论》的反响不过平平,更没有如想当然者认为的那样成为什么自由贸易论的旗帜。
事实上,斯密自己倒还颇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由贸易等自由经济思想不管在观念层面有多少优长,毕竟“过于超前于18世纪欧洲的实际政治和社会态度”(59),所以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说过:“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当指恢复至斯密思想中的天然自由状态——引者按],正如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荒唐。”(60) 他还在1780年的通信中坦陈:“我几乎忘记我是《国富论》的作者;……我疑心我现在几乎是我自己书的唯一主顾”;“报纸上刊登的对我讽刺的无数短文,你不值得花时间予以注意。但是,总的来说,攻击我的文章比我预料的还要少些。”(61) 斯密的这些话中也许有自谦和自嘲因素,但总归反映了大致的事实。
有一封对斯密的批评信至今值得注意,即《国富论》问世半年后出现的“波纳尔总督致亚当·斯密的信”。除例行的赞扬外,信件作者指出,斯密就英国的美洲政策和贸易限制措施所作的阐述经常过分纠缠于纯理论构想,以致无法看清自己著作的危险操作后果。波纳尔的结论是,斯密“很像一个未曾执业、茫然无策的庸医,手拿截肢手术刀跃跃欲试,却毫不精通回春之医术。”(62) 若将同代人对斯密的尖锐批评与日后自由贸易对弱势方带来的后果进行对照,无法不让人掩卷长叹。不过,应当指出,像这样高调的批评,就如高调的赞扬一样,在斯密的余生中还是罕见的,反响平淡才是总的基调。斯密去世时的情况可资证明。据考证,“斯密之死在英格兰,乃至在其家乡苏格兰,甚少引起关注。发表的讣告很少,而且并不恭敬。《年度档案》在其报道亡故消息的‘编年’栏目中,给了斯密12行文字,同栏中却把65行给予了梅厄·瑞,一位对气压计有兴趣的副军需官。”(63)“在爱丁堡,斯密的去世引起的震动,甚至还没有一个活跃的牧师的死引起的震动大,例如,30年后远没有斯密有名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死引起的震动就比斯密大。报纸上刊登的斯密讣告照例只有两小段文字”,难怪当时有人在信件中提到,“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死”。(64)
从实际政策面来看,斯密在世时的影响的确相当有限。财政大臣弗雷德里克·诺思为对美战争而就开征新税问题咨询于斯密,事后还以苏格兰海关专员一职给予报答,但有关政策动议与《国富论》中流行的批判政府管制、倡导自由贸易之类的观点简直是南辕北辙。故此,以自由主义经济教条论之,通常的结论是:《国富论》“所提论点在国内事务中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据明显缺乏”(65)。1783年,此书首次在下院被引用,但大臣“福克斯只是很随便地引用了斯密的话”,并未涉及斯密的核心观点。“其后,下院便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直到1787年罗伯特·桑顿先生为了替英法贸易条约辩护,才又援引了这本书。”而“在上院,直到1793年才有人提到这本书。”(66) 另外,即便从1780年代末期起斯密言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得到引用的频率在增高,但也应当知道一个对比性事实,即议会“18世纪的辩论充满了对约翰·洛克、大卫·休谟、格雷戈里·金、查尔斯·达维南特、乔赛亚·蔡尔德、威廉·配第、乔赛亚·塔克和阿瑟·扬经济学著作的引用。而且,与对这些作者的援引次数相比,对斯密援引的次数还是微不足道的。例如,18世纪的辩论中对斯密共提及40余次,但对亚瑟·扬却有数百次之多。事实上,与其他经济学权威相比,斯密不过排在可怜的第九、第十位。”(67) 对1776—1800年斯密在议会中被援引的专门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是在《国富论》出版之后25年,议会两院基本上对其信条漠不在乎,对其真理性抱怀疑态度,对其可应用性没有把握。”(68)
议员援引斯密开始增多的一个重要背景,恰恰是因为出现了两个与自由贸易相关的事件:一是国际形势趋紧使英国在1770年代末必须正视爱尔兰有关放松对其贸易压制的呼声;二是英国与法国于1786年订立了促进自由贸易的《伊顿条约》。研究表明,不是斯密的学说带来了这些推动自由贸易的事件,他当时的影响力远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相反,倒是这些事件为斯密的走运提供了推动力。当然,在爱尔兰问题上,《国富论》据推测影响过有关策论的提出者,斯密也确实为英国政府提供过咨询意见。然而,与斯密要求完全放开贸易管制的建议相比,最后出台的政策还是谨慎、节制和务实的,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受到了乔赛亚·塔克先生,而非亚当·斯密的引导。”(69) 实际从政者权衡利弊、折中极端的做法是毫不奇怪的。正如当时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斯密所言:“斯密博士,您站在教授的讲坛上当然可以像讲纯数学那样讲授自由贸易理论,但议员们却不得不一步步地慢慢来,因为他们要受到利害关系和优先次序的摩擦,行动必然受到阻碍。”(70) 况且,即使爱尔兰事件在指向“更自由的贸易”,它也“既没有确立《国富论》的权威,也没有激励人们更系统地研究该书。”至于《伊顿条约》,“似乎无法证明英法商约或者1780年代的其他任何外交举措受到斯密著作的一些引发或指导。”(71) 相反,主持1786年英法商约的威廉·伊顿虽然曾经赞扬过《国富论》,但还是称那些贸易定理“在纸上看来正确,在实践中不应被信任”。(72) 还有,“斯密本不会是他所处时代议会的首要经济学权威,可看起来只有随着英法谈判的成功,他才变成一个权威。”(73) 综而论之,“斯密作为政府顾问的时候并不成功”(74),正是现实形势的变化在抬高斯密,而非相反。
还可证明的是,在现实需求逐步抬举斯密的初期,主要是党派政治在起作用。应该说,在斯密之前的英国,党派利益就左右着贸易问题上所持的政策立场。“1680、90年代英国经济学领域自由贸易的早期支持者几乎肯定都以政治考虑为其动机。”(75) 经济学家因政治考虑而完全颠倒自己在贸易问题上的观点,这种例子也屡见不鲜。譬如,一般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的达维南特曾以现实政治利益为动机而倡导过自由贸易,故而被史学家称为“政治机会主义者”。同样,那位早已系统提出自由贸易论的马丁后来转向保护主义立场,“站在托利党一边反对与法国订立的贸易条约(1713年),他明显地象达维南特一样,非常关注政党政治。”(76) 18世纪下半叶起适值英国政坛托利党和辉格党角力争锋的一个高潮,随着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正开始酝酿着范式转型。因此,期望贸易领域乃至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构建完全在象牙塔里进行是不现实的,同样,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经济理论,尤其是贸易理论在出笼之后,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剪裁。
就在这一政治纷争中,一方面,斯密以其高度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姿态,包括对自由贸易的鼓吹,而赢得了当时执政的辉格派的注目。斯密不是不讲政治立场的。为了批判现有的经济管制,“斯密对于重商主义派追求自由、启蒙和进步的纲领闭口不言,足令人惊异。……在其对重农主义的讨论中,斯密又避而不谈谷物自由贸易的两次试验所遭遇的失败。”(77) 实际上,正如传记上两次明确提到的那样,“斯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员”。(78)“对于亚当·斯密的辉格急进派倾向,任何一位学者都不会怀疑”,“正是那些辉格急进派议员在1776—1800年间最为一贯地在提及斯密之名。”(79) 另一方面,辉格派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又对斯密学说进行着符合自己需要的改造。据考察,从1780年代到1800年,一本《国富论》日益被简化为一条单一的原则,即“所有贸易应当是自由的”。这种对斯密的改造也包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维护英国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而刻意剔除斯密学说中的政治自由主义内容,从而让原本的斯密形象,即“准法国的、准无神论的、准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家,被消解为关于经济自由的简单药方。”(80)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让双方都各取所需并且各得其所。“某些政客在议会公开地称颂《国富论》,由此而极大地帮助了斯密的事业”。例如,据考证,急进辉格派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威廉·皮特于1783年和1791年在议会中对斯密的援引和称赞便促进了斯密著作的再版和声誉的上升。(81) 不过,十分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下院最早提及斯密观点的福克斯私下曾说,他“没有读过这本书[《国富论》——引者按]”,且曾“对斯密及政治经济学本身表示了极端的轻蔑”;他“不相信自由贸易”。(82) 而“皮特内阁的实际经济理念更接近于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斯密的同代人,詹姆斯·斯图尔特,此人的著作强调有必要在货物与服务的交换中保持‘财富’的平衡”,毕竟当时“旧有的注重贸易平衡的重商主义观念依然存在。”(83) 但不管怎样,需要“打鬼”时,打造的“钟馗”终究是个可用的帮手。比如,“在英国围绕废除‘谷物法’的论辩中,斯密的名字就足以成为自由贸易益处的立论依据。”(84) 总之,斯密学说与辉格派政治的渊源关系无比密切,以致经济学说史家指出:“把《国富论》奉若《圣经》,认为其出版终结了经济学无知和重商主义偏见的中世纪,并开辟了经济进步、自由贸易、政府放任自流的新时代”,这是一种“对经济学史的辉格派解释”。(85)
斯密去世之后的十几年应当是斯密获得声誉的关键时期,因为1793年时,一位辉格党人,同时也接掌斯密在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职位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追忆斯密时,还在希望“到一定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学人将追随斯密的榜样,而仅仅过去10年,斯图尔特的学生就谈及与斯密名字相伴随的“迷信般崇拜”。对于这样的显著变化,不少研究者都坦诚:“有关斯密著作被神化的过程,我们的所知依然是惊奇地少。”(86) 然而,当把目光投向英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特别是考虑了上文指出的学说与政治互动的关系之后,则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获得某种答案。正如有人指出,“随着英国的工业优势到1800年时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我们可以期待,自由贸易已显现为英国制造商的最佳政策”;“英国的工业优势意味着强大的游说集团不仅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而把自由贸易视为扩大其私利的一个手段。”(87) 尤其是在“1815年以后,英国人已确信自己的霸权,开始废除原先本着重商主义精神而实行的一些限制,例如禁止出口机器和禁止工匠外迁的规定,以及某些重大关税壁垒和航海法。与此同时,他们以无可指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互惠的理由,力图说服别的国家也照样做。”(88) 显然,这里提及的1800—1815年间英国工业竞争优势的迅速确立,与亚当·斯密超级声誉的确立发生在一起,这绝非偶然。把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巩固为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已经水到渠成,而且已事关英国的根本国家利益。
斯密曾就给予爱尔兰自由贸易权利问题向英国政府高官上书,他说过:“我认为,即使爱尔兰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也不会使大英帝国的制造业遭受多大损失。爱尔兰没有可以与英格兰抗衡的技术与资本。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获得技术与资本,但要获得与英格兰完全相等的技术与资本,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89) 尽管斯密的建议并未被充分接受,但斯密对有关利害关系还是表达得足够明白:因为我强他弱,所以不仅不应当害怕自由贸易,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给予他人自由贸易权利,不是为了让他人由弱变强,而是因为自己可以巩固并扩大优势;在自由贸易格局中,落后者将难以改变与强者之间的相对力量对比。对于斯密包裹在自由贸易这一世界主义外衣下的利害算计,至少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已洞若观火:“威廉·皮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论可以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90) 当然,对于精明强干的政治家而言,某个“不是装装门面”,而是寄托了重要使命的对外谋利工具,在对内经营中则完全可以只是“装装门面”而已。皮特“他尊重作为学者的斯密,但并未让此人的思想妨碍自己去建立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91) 什么叫“内外有别”,什么叫“老谋深算”,借助李斯特等人的著作,看看英国政治家对斯密学说的宣传和利用就知道了。总之,以现实需求为基础,通过主流舆论的塑造,《国富论》“在19世纪成了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福音书,也成了英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文本象征。”(92)
意识形态化难免的弊病
斯密学说终于成为英国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大凡意识形态,除了其能为国家或集团利益服务的本能特点外,至少不免三个特点:一是抹杀他人的思想贡献,从而给人一种世上万般真理我皆具备,甚至由我独创的形象;二是面对复杂的问题,提出某个十分简单明快、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公式;三是出于现实需要,党同伐异,无视现有理论中的缺陷,又不宽容对现有理论的任何偏离。这些特点偏偏都可在斯密及其学说,以及其同党那里不难找到。
就抹杀他人的思想贡献而言,在斯密身上表现得大大超出通常所知的程度。如已考证,斯密在其著作中惯于掩盖对他人包括前人成果的援用。熊彼特指出,斯密“不很大方,从不像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93) 哈奇森指出:“斯密在《国富论》中只字不提这些前辈,例如配第、卡尔、塔克、加利亚尼、维里、杜尔阁、孔狄亚克、斯图尔特,只有一次提及坎梯隆,不管这样做是否充分的足够和恰当,对于20世纪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来说,如此对待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却是完全不够的和误导人的。”(94) 而且,斯密把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统统一锅端地扣上“重商主义”这顶帽子,并以其著作大半的篇幅攻击所谓幼稚荒唐的“重商主义管制”,造成了斯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一无可观的假象。“对于其前辈,即所谓‘重商主义体系’倡导者的理论和政策,斯密故意去败坏它们的声誉……斯密及其19世纪的追随者十分有效地贬低了17、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以致凯恩斯那代人从小就得到灌输,相信重商主义理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95) 一句话,“他的论点取得力量,靠的是完全漠视前代思想家和相反意见”。(96) 对于此种行径,从李斯特到熊彼特,已经多有揭露,甚至是按照自由主义路径创立了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斯密仰慕者”艾利·赫克歇尔都说,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描述不过是“高调的自由贸易宣传”(97) 而已。可惜,在褊狭的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充分地进入更加广泛的公众视野。
更有甚者,有人指出,“亚当·斯密借用了许多而未承认”(98),“即使按照他所处时代偏松的学术规范标准衡量也是缺乏学者风度的”。(99) 事实上,斯密对他人成就的掠美复加掩饰,在同时代便曾引起过批评和质疑。例一,斯图尔特“迟至1796年还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首要经济学权威”(100),当他于1780年去世时,其讣告的撰写者为其遭到的剽窃打抱不平,“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到亚当·斯密为剽窃者”。例二,当斯密与同代经济学家亚当·弗格森于1760、70年代关系恶化后,面对斯密对其的有关抄袭指控,弗格森有力地回击说,他与斯密一样不过是掏取了同样的法文材料!(101) 总而言之,部分地由于斯密对于前人成果有意无意地漠视、掩盖、贬低乃至歪曲,造成了日后人们对于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巨大成就的漠视和偏见,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对斯密的妄信,而放大了的斯密神像所产生的巨大阴影则进一步遮蔽了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成就的光芒。这种唯我独创的假象正好为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霸道铺垫了基础。(102)
其次,以简单化的公式去求解复杂问题,这在斯密对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执着倡导中表露无遗。斯密固然可谓一个综合胜于独创的集成者(103),然而,他在杂糅他人观点时不幸走了一条极端化、狭隘化、公式化、简单化的路子。可悲复可叹的是,这使他反而更易成为一面意识形态旗帜。简而言之,斯密吸收了曼德维尔私人之恶带来公众之善的观点,却抛弃了曼氏有关应当限制贸易的另外观点;他吸收了其老师哈奇森有关经济自由的思想,同样却抛弃了其关于限制贸易(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观点;他吸收了凯姆斯勋爵有关经济自由的思想,但抛弃了其有关限制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的思想;他吸收了达维南特、戴克、范德林特、加德纳等人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但基本抛弃了其赞成政府干预的思想;等等。这样的吸收和选择真有点匪夷所思。“‘诚实的’亚当·斯密犯有一系列学术罪行。他上下搜劫,寻觅支持‘自由市场’观点的所有东西,而对其他的一切则弃如敝屣。”(104) 难怪有人愤然指出:“一部著作要跻身伟大的行列,必须含有既正确又独创的思想,而如果把斯密的《国富论》与17、18世纪的文献作一细致比较,则可发现,凡其中正确者均非他所独创,而凡其所独创者则必定不正确。”(105)
不管如何,斯密诚可谓难得的简化高手。所以,虽然斯密之先辈和同代人绝大多数都是相当平衡、务实的,甚至还有像前代如威廉·配第、同代如詹姆斯·斯图尔特那样真正首创而又全面的大经济学家,但斯密学说却迥然不同。“现代经济学家发觉斯密的立论过于简单化,或许还太过情绪化和片面化。”(106) 可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学说毕竟像一幅漫画一样削繁就简、黑白分明,反而更易为不明就里、无意细究的大众甚至政客所理解和喜好。比如,史家承认,斯图尔特1767年出版的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没有像斯密的著作那样,采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迅速征服舆论”(107)“总是顾虑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以致被人认为“太过冗长繁琐和模棱两可”,加之其他个人因素,终于沦落为所在学科历史中“最为完美和杰出的失败者之一”。(108) 与之相反,斯密“他赢得了简明性、可读性、可信性,只是却损害了学术的诚实性。”(109) 应当说,这里反映的是植根于人性中的悲哀。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和纷繁复杂的现实,人们往往满足于并最终停留在一些浮光掠影且似是而非的“事实”、概念和原理上,旨在通过宣传而占据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更是需要简单明快的道理。于是,斯密以他在贸易等众多问题上较为极端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胜出,便不再显得奇怪难解了,更何况利益需要的现实大势已在流向他这一边。
不过,在指出了斯密身上利于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特点之后,也应当公正地指出,斯密虽不免若干取巧行为,但也不好说他就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投机之徒。出版《国富论》时,他本已功成名就,初版扉页上列出的头衔便有:“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前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也早已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声誉,虽然这种声誉与日后的盖世盛誉尚不可同日而语。从个性上看,斯密也还算个淡薄世利的君子。他“只喜欢书,不喜欢其他任何东西”(110) 耽于思考的乐趣,时有独自出神的毛病,迂阔并稍爱走极端,性格内向,终生未婚。他自己定位于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这样的角色,《国富论》不过是他构想的哲学体系中经济方面的部分应用而已。正是这样一个书生本色的斯密,才会对自己的已版著作反复修订,并在去世之前要求把自认为不成熟的16卷手稿付之一炬,也才会明知自由贸易时机远未成熟而简单化地为之反复说教。这样说,不过是想说明,对于他这样一个追求正常闻达的人而言,其身后的过誉终究是后世加诸头上的,故而,后世的时势与动机才更值得细察。
同样,也必须公正地说,虽然斯密总体上比起他的前人和同代人秉持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然而,斯密也还是比古典自由派确立之后人们通常对他的公式化要显得不那么走极端,特别是由于《国富论》本身的庞杂性,以及其中许多模棱两可的表述,“每一类可以想象的教条之痕迹,都可在《国富论》中找到,只有自己理论怪异的经济学家才无法援用此书来支持自己的特定目的。”(111) 故此,通观《国富论》,包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斯密还是设想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他提出了设置进口关税的几种“场合”,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二是“在国内对国内生产物课税的时候。在这场合,对外国同样产物课以同税额,似乎亦合理。”再如,斯密还设想了在贸易报复的情况下和向自由贸易逐步过渡的过程中,进口关税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此外,斯密也承认商人利益会有与公众利益相背离之时,故此相信政府在支持市场机制方面还是应当发挥某种重要作用,比如,政府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建立法治体系,从而让天然自由秩序运作得更加有效。(112) 还有,斯密基于“国防比富裕重要得多”的思想,毫无保留地支持“现代历史学家视为重商主义基石的‘航海法’”。(113) 有鉴于斯密的这些观点,下面这段评论还是不失公允的:“虽然斯密说过一些尚值得进一步解释的一边倒的言辞,但斯密并非教条式地倡导说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当撒手不管。他的论述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当时,从重商主义时期,甚至从中世纪,承接了太多的东西。他反对所有类型的垄断、独占团体、特权待遇,其强烈程度就如他反对试图通过限制贸易来促进国家繁荣的那种立法。他经常被冠以‘私利之布道者’,可是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私利在贸易和工业中所呈现的某些形式之反感,他也并不厌恶实际上可能带来益处的法律措施。”(114) 一句话,“就如对待卡尔·马克思一样,需要将亚当·斯密与其门徒区分开来。”(115)
然而,一个学说一旦上升为事关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它便会沿着新的轨道往前滑行,其原有的特点,包括出发点乃至优点,也包括其构思者曾经的意图、设想等等,都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从19世纪初叶开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便“致力于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的正统信仰,……其强调的重点和重新的解释遮蔽了[《国富论》——引者按]原本的内容。”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例如,“李嘉图把斯密那些颇为散漫的原理改造成一个让生产和分配与自由贸易相挂钩的体系,……在自由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关系。”(116) 还有的例子更是发人深省。例一,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派辉格党人”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豪纳拒绝出版《国富论》的注释本,因为他‘不愿在斯密著作产生充分效果之前去揭露其谬误。’”例二,斯密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于1833年在阐述为何要坚持斯密崇尚的“放任自流”原则时说得同样明白:“那个原则,如同其他负面性原则一样,还有工作要做,那主要是一种摧毁性的工作。我高兴地看到,它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此项任务。之后则它必须很快失效,待失效后,但愿灰烬归于沉寂,因为我对于死灰复燃心怀疑虑。”(117) 此话说得何等明白!显然,英国的这些经济学家是非常讲究服从现实需要的,为了现实需要——不管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或者其他的,可以先矫枉过正一下、隐瞒实情一下,需要的是先竖起有利于其时英国国家利益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大旗。
意识形态的确立除了要求自觉性之外,更需要高压的外部环境。斯密时代前后,英国从来都不缺这种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外部压力。且不说稍前哲学家洛克曾被监控、革职及流亡海外(118),就在斯密身边,他的老师哈奇森即被指讲课内容抵触官方教义而面临惩罚;他的好友休谟也因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被逐出苏格兰学术圈。(119) 休谟曾难以谋得教授职位,难以在生前出版著作,斯密自己便不敢如病中休谟所托出版其身后著作,斯密在通信中说:“我的一篇十分无害的悼念我的朋友休谟去世的文章却为我带来比对大不列颠整个贸易制度的猛烈攻击多十倍的辱骂。”(120) 19世纪的英国在扶植自由贸易学说时,丝毫不缺这种高压环境,而让人惊异的是,此等压力多强加在堪称19世纪古典自由派中最为头面的经济学家身上。
第一个受压者是罗伯特·托伦斯,这是一位对比较优势原理所作贡献不亚于李嘉图的一流经济学家,他实际上早于李嘉图(1817年),在1815年即已提出了比较优势思想,但是他一直受到相当的忽视,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从崇奉自由主义始,却以探究保护主义终。针对当时盛行的自由贸易论,甚至是单边自由贸易论,托伦斯逐渐发现,“一国可以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而使贸易条件变得对自己有利”,由此可以导出结论,“英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会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条件的相应恶化”,“国家繁荣所依据的贸易政策不应当立足于自由贸易,而应立足于对等互惠。”然而,英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通过投票,一致反对托伦斯的观点,并为这种“连道理的影子都没有”的“不负责任的观点”无比愤慨。须知,这个“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年的首次会议在李嘉图、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托伦斯主持的呢!(121) 如今,贸易学说史证明,“在所有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中,贸易条件说最为有力、漏洞最少,作为对自由贸易的限定,它依然是经济理论所承认的认同面最广、得到普遍接受的一项非议”,但是,“在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头脑中,非议自由贸易就是异端,托伦斯越出了那些框框,于是在将近一百年中成了一个被群体抛弃的贱民。”最早的《帕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对托伦斯的著作不屑一顾,称之为“缺乏恒久价值”,只是过了几十年,到英国自己的竞争力已经明显受到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之后的1913年,新版的词典才承认了托伦斯:“假如不能跻身第一流古典经济学家的行列,比如不能与李嘉图、西尼尔、约翰·穆勒齐名,也一定会因为其原创性、理论推理,以及所思考的经济命题的范围,而能跻身第二行列,与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比肩而立甚至超越他们。”可见,即使是参与奠定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重要基石而且也同样深切关注英国国家利益的大师,如若要动摇已上圣坛的教条,也会遭到激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情打击。(122)
更为知名的古典经济学大师约翰·穆勒也领教过这种党同伐异的高压态势。就在英国挟其如日中天的工业优势正图利用自由贸易武器拿下世界的1848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问世,书中成为此后数代学生教材的标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内容姑且按下不表,只谈引起争议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尽管此前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李斯特等都已提出过对自由贸易教义的此类非议,况且,幼稚产业保护论在英国甚至“可以至少一直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但是,是穆勒凭借其在古典自由派中的地位和声誉,首次“正式地将它纳入古典贸易理论之中”,并“赋予其学术的可信度”。穆勒这样指出:“单从政治经济的原理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保护性关税才站得住脚,这就是,临时性地设置这些关税,特别是在一个年轻并在崛起的国家里,借以使某一外来产业在国内生根,当然这一产业宜完全适合该国条件。一国在某一生产部门相对于另一国家的优势往往只是因为它动手更早。一方没有天生的优势,就如另一方也没有天生的劣势,有的只是所获技能和经验基础上的当下优势。”此论甫一发布,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抱怨迅速传到穆勒那里,称他的言论正在被保护主义分子曲解,用于辩护18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高关税。”所以,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英国19世纪自由贸易的急先锋理查德·科布顿临死时愤言:穆勒书中那段赞成产业保护的话“盖过了他其他著述可能带来的全部益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提到,穆勒的斗胆一言让“他的朋友谈起就愤怒,但比愤怒更多的是悲痛”,似乎哀叹穆勒的一世英名居然毁于不合时宜的一小段话。(123)
高压之下,穆勒不得不进行自律,他开始修饰自己的观点和言词,同时高调谴责任何总体上的保护政策,甚至还说出了日后被自由派广泛引用的话,即贸易保护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掠夺的一项系统性制度”。然而,非理性的批评声浪持续不断,弄得穆勒终于难以招架,他坦言:“我现在对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可人们如此经常地把我的观点引用于未曾设定的目的”。在私人通信中,穆勒依然坚持自己的原有观点,但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65年的第六版和1871年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版里,他被迫步步退让,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裹在很多婉转节制的措辞中。史家称:“最终,穆勒宣布撤回自己的观点,即进口保护是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恰当手段,尽管他从未抛弃过自己的信仰。”最后也是最好的收场当然是让及门弟子来做。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其“最首要的门徒约翰·E.坎斯”在1874、1878年都公开著文批评幼稚产业保护论,称之为“一位伟大作者的附带意见”,并提醒人们注意穆勒为自己观点所设定的“严格限制”。至此,一场剿灭异端思想的战斗终于完美结束。结果便是:“1848年之后的数十年中,穆勒对幼稚产业保护有节制的赞同未能取得经济学家们的较多支持。”这样,英国在自己工业竞争力节节强大的同时,牢牢抓住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压制了一个本来会让那些落后国家提前或进一步觉醒起来的思想成果。(124)
除了托伦斯和穆勒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托马斯·马尔萨斯也备受压力。虽然马尔萨斯总体上也认同自由贸易,但他从其关注民生的一贯立场出发,为农产品的供应安全问题作了额外的保险性考虑,认为如果粮食出口国在短缺年份不遵守自由出口的承诺,那么,进口国也有理由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设定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他表示支持“谷物法”这一横亘在英国自由贸易道路上的重要制度。于是,他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马尔萨斯在辉格党人那里迅速而且永久地失宠,证据是在1814年支持“谷物法”后,他被完全地逐出《爱丁堡评论》。此前,《爱丁堡评论》不仅高度称颂马尔萨斯,而且在经济问题上把他援引为某种权威。”(125) 用翻脸不认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见,在古典自由派学者和政客那里,自由贸易论虽被奉若神明,号称刀枪不入,但谁要是真的“在太岁头上动土”,那都是要严惩不贷的。
凡是涉及或者被认为涉及重大利益,出现上述种种情况都属正常现象,科学史上充斥了这样的可叹例子。自由贸易论既然成长为主流的官方学说和政策工具,在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走向无比的辉煌,并总体上有效地履行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但另一方面也首先需要走过一个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之类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化不管其起点如何,终究会妨碍真正自由的讨论,这种对自由的妨碍可以是有形的挞伐,也可以是长期的弄假成真、自我麻痹、沾沾自喜、自我内心过滤等等,所以意识形态在实现一段时期的正面功能后最终往往会回过头来损及自身。英国19世纪下叶实行几近单边主义的自由贸易后不久为何最后疲相毕露,又为何到1930年代英国重新拾起所谓的“新重商主义”,充分印证了意识形态化一定程度上的自损性。
然而,历史地看,当英国及其他随后崛起的国家赢得了总体的优势地位之后,巩固自由贸易这一意识形态无疑更多地为它们带来了滚滚利益。19世纪以后,发达世界借助自由贸易理论及其实践,总体上维持并扩大了其产业竞争优势和相对经济利益,这种状况至今未有本质改变。正因如此,作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从来都热衷于煽动“斯密崇拜”,把自由贸易论打扮成“价值中立”、“利益超脱”的普世主义“科学理论”,并广为散布自由贸易让英国率先赢得现代发展这一不实神话。与此同时,在自由贸易旗帜下,包括通过压制对自由贸易论的各种挑战,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落后国工业化的必要性、工业化过程中采用保护手段的正当性等等关键问题被边缘化或被作误导性探讨,落后国家的追赶步伐因此受到进一步的牵制。显而易见,对于尚处落后状态并试图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发展的国人而言,尤有必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保持清醒头脑,维护自身利益。就此而言,深究亚当·斯密及其经济学说之所以获得追捧的历史,辨析其中积非成是、以讹传讹的细节,仍然不失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考察》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泰晤士报》2006年10月30日,转见《参考消息》2006年11月1日,第4版。
②Mark Skousen,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伟大思想家的生平与理念》),New York and London:M.K.Sharpe,2001,pp.13—16。
③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6页。
④华民:《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⑤参见Jacob Viner,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贸易理论研究》),New York:Augustus Kelley,1937,pp.92。
⑥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重商主义:一套经济学语汇的形成》),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139。
⑦Salim 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神话》),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Inc.,1998,pp.169.
⑧Frank H.Knight,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6。
⑨Terence Wilmot 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86.
⑩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9页。
(11)参见Douglas A.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逆流而进:自由贸易学说史》),Prince 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20; 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43。
(12)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pp.101.
(13)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83—86,pp.233,pp.394,pp.402。
(14)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62.
(15)转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98页。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26—129。
(16)雅各布·瓦伊纳:“约翰·雷著《亚当·斯密传》指南”,载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 482、483页。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61—163; 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25。
(17)参见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25。
(18)参见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上述数人对天然自由及天赋贸易自由的论述,参见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21—24。
(2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78页。参见Jacob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亚当·斯密与放任自流”),in Douglas A.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经济学说史论文集》),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86; 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69—71。
(21)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49。
(22)马克斯·考森、肯那·泰勒:《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3)Lars 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重商主义》),Vol.1,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4。
(24)上述数人对追求个人私利有益于公众等问题的论述,参见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48,pp.65,pp.68—69.其中诺斯、塔克、斯图尔特的有关论述,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80,pp.235,pp.340。
(25)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00—103。
(26)参见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25—27。
(27)雷:《亚当·斯密传》,第35页。
(28)参见Lubasz Heinz," Adam Smith and the Free Market" (“亚当·斯密与自由市场”),in Stephen Copley and Kathryn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 s Wealth of Nation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新的跨学科论文》),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p.46。
(29)(31)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39.
(30)(32)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385; pp.398,pp.359.
(33)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Vol.1,pp.4.
(34)Gwydion M.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亚当·斯密:富而无国》),London:Athol Books,pp.9。
(35)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87页。
(36)有关分工问题上斯密前人的贡献,参见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4—29.有关卡尔及富兰克林的分工论及其对斯密的影响,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480—484页;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61—163,pp.403。
(37)参见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256。
(38)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309—310。
(3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0页。
(40)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257,pp.86.
(41)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Vol.1,pp.15.参见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pp.1—7.
(42)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9,pp.11,pp.239.参见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30—31。
(43)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57,pp.59,pp.62.
(44)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28.
(45)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29,pp.163.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482页。
(46)转见A.W.Bob Coats," Adam Smith and the Mercantile System" (“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制度”),in A.W.Bob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I: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英国和美国经济论集,第1卷:论经济思想史》),Routledge,1992,pp.141。
(47)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29,pp.389,pp.360.
(4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2页。
(49)有关斯密稍超前于时代风尚的观点,参见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对亚当·斯密的现代评估”),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I: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22。
(50)PP.J.Cain and A.G.Hopkins,"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The Old Colonial System,1688—1850" (“绅士资本主义与英国海外扩张,之一:旧的殖民体系,1688—1850年”),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9,No.4( Nov.,1986) ,pp.512。
(51)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pp.87.参见Jacob Viner," Adam Smith" (“亚当·斯密”),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254。
(52)(58)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39,pp.151—152.
(53)Richard F.Teichgraeber,Ⅲ," ' Less Aba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攻击我的文章比我预料的还要少些’:《国富论》在英国的接受过程,1776—90年”),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30,No.2( June,1987) ,pp.338。
(54)雷:《亚当·斯密传》,第258页。
(55)有关《国富论》发行情况的介绍和分析,参见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37—366。
(56)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6、124页。
(57)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39.
(59)(62)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37,pp.350.
(6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2页。(此引照原文新译)。
(61)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3、341、346页。
(63)Emma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亚当·斯密与保守经济学”),Economic History Review,XLV,1( 1992) ,pp.74。
(64)(66)雷:《亚当·斯密传》,第394页,第262、263页。
(65)Keith 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天然自由与放任自流:亚当·斯密如何成为自由贸易论者”),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 s Wealth of Nation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pp.23。
(67)Kirk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在议会中的作用”),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pp.510.参见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61—362; 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37。
(68)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pp.544.
(69)(72)(75)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44; pp.145,pp.153; pp.166.
(70)(78)雷:《亚当·斯密传》,第416页,第146、291页。
(71)(73)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58—359,pp.361; pp.362.
(74)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27.
(76)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49,pp.389.
(77)Hiram Cato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亚当·斯密的前工业化经济学”),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5,No.4( Dec.1985) ,pp.842。
(79)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60,pp.138;有关斯密对辉格派的吸引力,参见同书pp.156,pp.162,pp.173。
(80)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XLV,1( 1992) ,pp.93,pp.87.
(81)(87)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38,pp.161—162; pp.159,pp.173.
(82)雷:《亚当·斯密传》,第261—262页。
(83)John A.C.Conybeare,Trade War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贸易战:国际商业争夺的理论与实践》),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1。
(84)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 s Wealth of Nation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pp.28.
(85)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I: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20—121.
(86)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90" ,pp.365.
(88)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页。
(89)雷:《亚当·斯密传》,第321页。
(90)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91)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121.
(92)Tribe," Nation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 s Wealth of Nation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pp.23.
(9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77页。
(94)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372.
(95)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1: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19,pp.134.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90—294页。
(96)(99)(104)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35,pp.38,pp.38。
(97)转见Coats," Adam Smith and the Mercantile System"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I: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40。
(98)(100)(105)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200—201,pp.152,pp.3.
(101)参见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161—163.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60、422、4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79、280页。
(102)参见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64.
(103)参见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86。
(106)Viner," Adam Smith"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259.
(10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68页。
(108)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pp.338,pp.349—350.
(109)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58.
(110)雷:《亚当·斯密传》,第257、299页。
(111)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pp.92.
(112)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4、36、38、40等页。
(113)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1: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51.
(114)Knight,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pp.9.
(115)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1: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35.
(116)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 s Wealth of Nation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pp.28—29.
(117)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62,pp.166.
(118)参见Henry William Spiegel,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经济思想的成长》),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23。
(119)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13、23、112—114页。参见Coats," Adam Smith:The Modern Reappraisal" ,in Coats,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1: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pp.125。
(120)莫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46、27、278、280页。参见Williams,Adam Smith-Wealth without Nations,pp.19;雷:《亚当·斯密传》,第268、291页。
(121)参见Spiegel,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pp.347。
(122)(123)(124)本段引文和所涉细节,参见Irwin,Against the Tid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Chapter Seven,pp.87—115,pp.116—132,pp.116—132。
(125)Rashid,The Myth of Adam Smith,pp.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