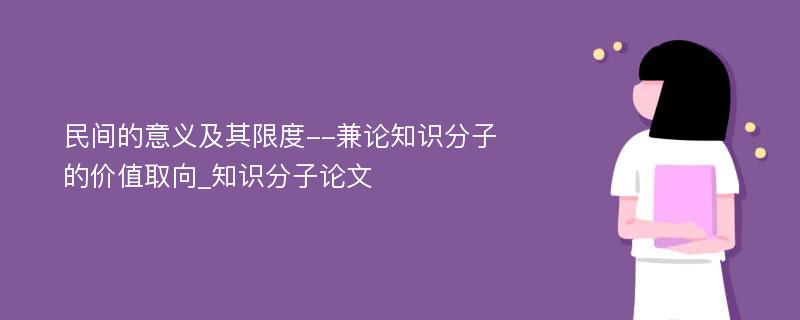
民间的意义及其限度——兼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限度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民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分天下”说
陈思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初发表的两篇论述自抗战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发展的长文中①,提出了一个“民间文化”的概念,这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内,引来了诸多关注的目光。关于民间的话题原本并不新鲜,只是在世纪末的今天重又提出来,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其实,关于民间文化在本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陈思和在早些时候的关于当代战争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对新时期创作的具体评价中,就已潜伏了这一思路。现在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理论化。他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史作出这样的归纳:自上世纪末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本土文化在庙堂与民间之间的封闭型自我循环系统在世纪之交被打破。中国的学术文化分裂为三,即由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在这“三分天下”的理论背景下,陈思和对自抗战至今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了新的解释。它的意义首先在于,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进入抗战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全能的方式,但在今天对抗战时期、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相对不足(如与五四与新时期相比)甚或严重匮乏(如对文革时期)的研究现状下,这种解释的意义就愈益明显了。另外,对于文学史中民间文化的思考还可以显示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它可以为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自身的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价值取向的思考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我认为,即使在上世纪末以前中国文化的封闭循环系统中,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因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也同样存在着,只是在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知识分子的道统连续不断地或聚集寄托于政权,或流散隐蓄于民间,而打破这一封闭系统的西方文化在百年来的大规模输入,是建立在强权压迫和显示本土文化落后与软弱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外来文化从一开始就将中华民族赶上了民族现代化的单行道,现代化便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随着末代皇朝的崩溃,传统文化结构分崩离析,中国历史似乎被永远抛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道。这样,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便成为讨论文化“三分天下”的巨大历史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以前人未有的专注目光考察民间文化在现代的沉浮,其意义显然就超出(也应该超出)了文学史的范畴,(在对文学史的具体论述中,陈思和一再提醒读者,其民间的概念限于文学史内部)它使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思不再继续囿于精英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精英文化传统内部,而是放宽眼界,在三种文化势力的分合演变与互动关系中,确立自身在当代文化结构中的角色地位及其界限。这本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决非我辈仅以一篇文章可以说得清楚,本文仅以“三分天下”的话题为起点,对民间文化在现代的意义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一点浅见,以期加入关于当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讨论,并供方家指正。
二、现代化背景下的三者互动
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基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正是由于西方思潮的输入,才在新的意义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价值取向问题;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全新境况,使得这一问题在知识分子的自身传统中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将知识者推置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三种因素在古代传统中是始终存在的,三者间一直处于不断对立、冲突和组合的关系之中。就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虽说在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甚至以道统的标准教育和改造君王,所谓“庙堂之上言理,则君子不得以势相夺”,但如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传统知识分子从道统角度的一种历史概括,或曰叙述。真正的以“道”统“政”,不过是孔子以来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其实,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真实处境,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所以,道与政的对立与冲突从未在中国古代中断过。另一方面,政治统治者既需要以道统作为权力的支撑,又需要知识者作为谋士直接参与政治运作;同时,又对知识分子予以严格控制,并始终置其于事实上的附庸地位,成为其统治工具。在将知识分子工具化这一态度上,与对民间文化的态度并无二致,统治者既有从“采风”到“顺天应命”的利用,又有从武装镇压到招安降顺的控制。
就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民间一直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保护薮,在政治恐怖的时代,民间文化接纳并蕴育着被高压政治击溃的精英文化;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民间又作为知识分子借以辅政议政的对象,他们往往借民间的反映表明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另一方面,民间又常常被知识者所鄙视,所谓“下里巴人”“引车卖浆者流”是也。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民间文化又多是沉默不语的,相对于前两种文化势力而言,“街谈巷语”虽然从未有过中断,但却从来被视同“风吹草动”般的“天籁”。只有当社会纲常失系,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之际,民间的声音才又喧嚣一时,而这种声音又会很快被前两者利用,或者自己落入早已设置好的套路之中,一段时间后很快又归于“平静”了。
这种一乱一治,一分一合的循环,到上世纪末终于被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所打破,中国历史被置于西方现代化的语境之下,这种处境被现代话语理论描述为历史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和边缘性的空间观,中国文化被置于落后软弱的地位并永远安排在现代化的线性发展轨道上。传统文化格局的分崩离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各种价值规范系统的大转换时代。而作为这种文化离散状态的始作俑者,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对旧制度的破坏中使自己与旧政治脱离,开始成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从西方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社会理论模式,一时主义纷飞,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多元化状态。虽然民间文化在本世纪初的多元化状态中也并未真正走向历史的前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它就再也不沉默了。在民族独立要求的压力下,诸种主义纷纷被意识形态化,继而纷纷付诸于实践化的努力,谁都相信自己的理想可以救国,并在各种社会势力中寻找政治依托,于是民间的力量被再一次结合进诸种理想的理论化和实践化的努力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里,中华民族就处在这样一种新旧意识形态转换的时代里。从文化大传统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下,中国社会由文化的多元状态向一元状态转化的时期,而多元时代的诸种意识形态,从渊源上看又都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与改制有关;现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后确立,从动态的观点看,也与知识分子将理想付诸现实的实践化过程有关。因而,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野”与“在朝”的关系,这“一元”曾经也是作为整体的多元化状态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是在与原来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对抗。
从这里可以看出,本世纪知识分子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既有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以此考察民间文化的遭遇就会发现,不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改造和利用,是视之为工具;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或肯定或批判,也会有将其工具化的可能,或者是为了维护精英文化传统,或者是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民间文化的意义呈现,都必定是消极的片面的。这时候,民间似乎是热闹的,它被人不断地提及、谈论;然而它又是沉寂的、默默无声的。只有当社会历史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下,比如战争时期,当现实矛盾的尖锐远非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所能左右和解决时,民间文化才会真正走向历史前台,才会体现出其辉煌的生命力。
三、民间的意义:第三者在场
在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从新的意义上肯定民间文化的作用,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尤其在今天,面对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的迅速变化,传统的价值规范面临着种种困窘。知识分子一面担负着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任务;一面对汹涌而至的商品大潮一时又不能从容应对,价值多元化与价值虚无化同时并存,知识分子一时感到失却了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应该怎样为社会提供合理的价值规范呢?
民间文化概念的提出,既可以成为知识分子借以进行文化批判的合理依托;又是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自我反思的新的维度。正如文学批评界正开始意识到的那样,自八十年代中期起,许多作家开始从民间的立场上,展开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审视与批判,对张炜、刘震云、刘玉堂等作家的创作,就可作如是观。在知识分子喟叹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重新审察民间这一文化领域,就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引入了一个第三者。本来,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总是脱不开与政治的二元关系,从为政治服务,按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改造自身,以致丧失自我;到与政治意识形态,疏离以至逃避,总是将自身的价值使命,投射于政治这一对象上,把现实政治作为确立主体意识的唯一客体。这种反思,大大地限制了思路的深入与拓展。而民间文化的引进,就为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社会批判确立了又一个客体,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追寻提供了另一种参照。
这第三种参照的确认,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在数量上多了一个自我观照的对象物。民间视角的出现,还应把它看成是价值多元化的突破口及其象征。二元的关系不是对立便是统一,而三元就是多元化的开始。何况,民间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存在,尽管它常常处于被工具化的境地而默默无语,但民间文化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自由自在的文化形态总会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意义。而当知识分子的生命力衰退时,同样又可以从民间这个丰富的价值资源中汲取养料。“民间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的种种欲望,与这原始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道德规范有时会扼杀人的生命力,而过分精致化的知识分子文化同样会妨害感性生命的张扬。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着一个难于回避的悖论:一方面,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汲取了西方民主与自主思想的他们来说,是有背于初衷的。他们积极引进西方思想,鼓吹各种主义,就是为了打碎传统中国文化定于一尊的死气沉沉的格局;而另一方面,救国的愿望,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课题又逼使他们纷纷将自己所信奉的主义付诸于实践:教育兴国、实业救国,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方略,其间有着种种的差别与对立,但在民族现代化的目标上是共同的。如果将理想与信仰仅仅停留在理论的状态,民族的独立与现代化就难于实现,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时代课题的急迫性所导致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因素。但是,意识形态化过程,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必然要跨出的一步。从这一意义说,这一个悖论也是落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宿命。
这样,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身份往往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新的意识形态模式的提供者,又是与政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当他们以自身的文化传统,用价值理性批判专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时,他们是在为民请命,是在相当程度上护卫了民间生活的感性生命力;但当他们那怕出于某种崇高的理想,将自己的信仰与理论意识形态化,并在实践中强行推及他人时,他们实际上又以形而上学的理论戕害民间感性生命,剥夺民间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权利,由此,作为社会阶层整体的知识分子便发生了一次次分化。
以民间文化的价值多元化作为参照,来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难于摆脱上述悖论和双重身份的原因,就会有新的启发。不难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处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但因囿于时代课题的外在逼迫,更囿于在价值取向的内在心理机制上缺乏多元并存的理性维度,在二元对立判断之外不容第三种价值的存在,如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因此,知识分子往往在双重身份之间往返轮回:刚刚从被迫害者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又立即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专制者的角色中;而民间在他们的眼里,也就从被高举着与专制抗争的旗帜,变成被鄙睨地丢弃的破衣烂衫,民间从来没有被当作二元对垒阵营中的第三者而予以严肃认真地对待。
民间文化概念的提出,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体现出它的价值,在这里,文学艺术的天地尤其显得广阔。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蒙、张辛欣等就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表现了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文化空间,继而有“寻根文学”的创作和近年来被冠予“新写实”之名的创作,在这一线索的演化中,将民间文化作为文艺创作题材与形象资源,似已成为某种共识,而将其作为多元化价值资源的创作,却还方兴未艾。从理论思维的层面来说,需待澄清的问题还有很多。民间文化既作为多种信仰、多种价值规范、多种生活方式的集聚,要想将其中的积极因素纳入文化的大传统,就需要精英文化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界说,而这又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绝对的存而不论与削足适履都不能使民间文化在文化新格局的构建中体现其真正的价值,由于民间的藏污纳垢的特点,区分甄别的任务就相当艰巨。如对民间文化形态中的宗教、气功、相术等现像,精英文化当何以处之?当理论的界说还很难做出时,文学艺术倒可以因其形象性和非功利等特征而率先予以表现。
四、民间的限度
民间既是价值多元化的资源所在,亦是藏污纳垢之地。说它是藏污纳垢,即使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难以完全成立,——因为这种判断,很可能被认为也很容易滑向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某种褊狭之见。它至少也应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这种描述可以提醒人们:虽然不能直接指出那些因素是完全有害的,因为在民间文化领域里,价值多元化呈现与有害因素往往交错杂陈,难以机械地割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守护民间文化的同时,利用人类至今依然还很有限的理性能力进行甄别是十分必要的,它是我们从民间获取多元化价值资源的前提。
就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来说,民间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小传统,它要在当代显现其意义,就必得与文化大传统取得沟通。不论知识分子基于何种前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过程,也就是将这一部分小传统接纳入大传统的过程。民间文化是一种自在的文化现实,其自不言说,自不会抒情,不论是赵树理、高晓声、刘玉堂,还是张炜、张承志、刘震云,不论他们与民间的关系如何,对民间采取何种态度,他们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对民间进行言说,并以言说的结果纳入文化大传统,至少在客观上已致此。也许他们的言说所取的价值标准既非来自政治意识形态,也非来自精英文化传统,而是完全来自民间,姑且谓之“民间标准”,而且它还是一种非模式化的标准,即始终以价值多元化为指归,而非以一种标准去规范另一种标准,但既经言说,就已经不再是完全原始意义上的民间文化状态了。我在这篇文章里对民间的言说,自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在对民间的意义作出充分估计的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它的自在自发性和消极性。民间文化作为一种自在自发的文化存在,它的积极意义主要是以自发的路径获得显现的、正如陈思和所说,“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民间文化会以其自由自在,充满生命力的方式得以张扬,体现在文革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民间隐形结构”就是极好的例子。但问题的另外一面是,正由于民间文化与原始的生命力相结合,因而它往往又是盲目的、粗鄙的。
由于其盲目性,它就极容易被理性或非理性所操纵,而一旦被操纵,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就常常会溢出理性的堤岸泛滥成灾,以至难于收拾。文革同样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民间普遍蕴藏着的原始欲望,以及民间宗教等因素,才轻而易举地导致了文革中政治生活上的广场短路,社会生活中的私欲横流,精神生活里的个人崇拜,而它恰恰是与文学中生动的民间美学因素同时出现的。同样,如果不囿于文本的限制,民间文化的这种两面性即使在近期某些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描绘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这群人有同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同样程度的实践化,必要时都可以以身殉教,事实上《心灵史》里就是这样描绘的。但是,如果其中有人仅仅不愿意将信仰全部落实于实践行为(犹如佛教徒中执“佛祖心中留”辈),群体将又何以处之?是强制其从众,还是自听其便?如果是前者,这种信仰就已经超越了信仰的边界,不啻为一种专制,而若再以民间标准解释之,也就是放弃了人类价值规范的基本通约性,因为被强制者同样身处民间。设问,哲合忍耶群落中曾否发生类似的事件呢?如有,张承志将怎样描述?他现在的描述是否已经作出了某种取舍?若没有,他的“忠实”描述,显然也不是为了将这一信仰加之于我们,而只是提供一种价值精神的参照,是一种价值提醒。
这种由于民间文化的盲目性而带来的后果,很容易导致另一种形态的专制,即群众专制。即使在社会文化的大空间里,它是以对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但在具体情景里,它却是以逼迫少数人自由的方式实现的。尤其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社会在商品化、都市化日益普遍的今天,逐渐被市民文化所取代时,民间文化的空间就日益被现代传媒、商业广告、衣食消费时尚所控制,现代文化专制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当这种专制性结合了民间既存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中的夸耀攀比与感官享乐的极端化倾向时,民间就不只显现出它的盲目,而且再加上一层粗鄙,这种粗鄙化的专制并不一定以强迫胁从,更多的倒是以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姿态出现的。
因此,在确认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意义的同时,意识到它的局限,其意义同样是不容低估的。这使我们能够在创导和建设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现代文化空间时,对民间文化本身包含的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保持一种警惕。
五、结语
从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上考察文化“三分天下”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三者中的哪一方,都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产生程度不一的作用,三者之间具有一种互动关系,其中以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化的作用相对比较特殊,因而,对这一文化主体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境遇的考察,是探寻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角色定位及其价值取向的起点。
在对自身传统的反思过程中,重新认识民间文化在本世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充分意识其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民间的存在为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确认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也是营建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新空间的价值资源。作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现实文化空间,民间体现出丰富的价值内涵,它不是知识分子凭借工具理性可以加以清理的,知识分子必须谨慎地守护民间这片广袤富饶的大地,哪怕出于某种崇高的理想而对之加以肢解和践踏,都会对其造成巨大的破坏,从而扼杀其生机,损害乃至取消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化建设所可能具有的巨大作用。同时,民间文化的局限也提醒知识分子在反思传统与探寻当代价值取向时,必须对民间所固有的盲目性与粗鄙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文化后果保持一种必要的警惕。知识分子作为建设文化新空间的主要担当者之一,既应具备多元价值的襟与视野,肯定和守护民间的多元价值资源,同时又必须不放弃以至今依然有限的价值理性对其谨慎地甄别、选择和批判。
以民间文化作为反思历史与追寻当代价值取向的新参照,知识分子必须摆脱本世纪以来的文化双重身份,跳出文化角色上的二极轮回。而在引入民间作为思维第三向度时,作为个体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的文化角色确立一种边界意识。简言之,从事社会科学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都应清醒地意识到各自在文化建构中与现实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位置关系,不论是侧重于实践化运作还是从事于价值批判,都必须在拥有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胸襟的前提下,坚执自己的理想操守,同时又不使自己的实践行为超越自己应有的文化角色边界,无论是谁,越界筑路的后果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1994.11.10
注释:
①见《民间的沉浮》,载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政治意识论文; 陈思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