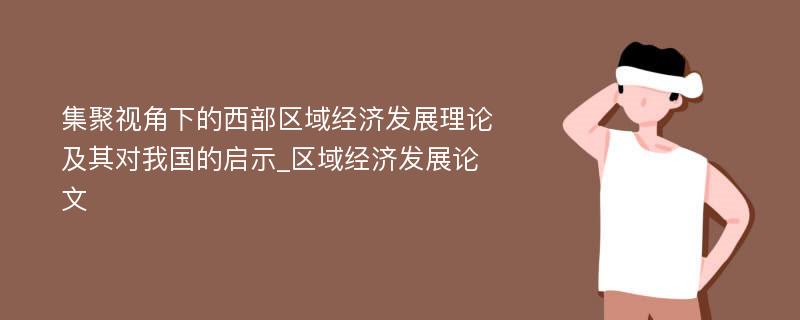
基于集聚视角的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启示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62(2010)07-0067-0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以产业集聚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也开始变得日益显现,并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政界、学界和工商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这种以集聚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现象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先后形成了交易成本学派、新制度学派、创新体系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尽管各个理论流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有所不同,但他们基本都是从区域中的柔质(flexible)和粘性(sticky)要素入手来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现象,这与以往以硬质(hard)和刚性(rigid)的投入-产出关系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如增长极理论、产业综合体实践)有着根本的区别。
尽管我国近年对于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推介和评述的文献已有不少,但多数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理论和案例进行的,而从整体区域发展思想转型的角度对现有理论流派的演进加以归纳和分析,并针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具体实践提出具有针对性建议的还为数寥寥。由于我国不仅整体上正处于内部工业化和外部全球化的双重进程之中,而且东、中、西等不同地区之间还处于差异相对较大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我国要实现整体现代化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系统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使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由主要依靠项目投资拉动逐步转变为以集群创新为根本动力。只有这样,我国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落后地区也才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因此,本文首先对基于集群的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有理论进行分类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介绍西方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方向和思路,最后是根据上述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提出的相关建议。
1 区域经济研究的主要流派
全球化是以资本、商品、服务、人口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然而,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如新古典经济学预期的那般消除甚至是缩小区域间差异。恰恰相反,全球化通过推动开放和促进竞争,使传统福特制(Fordist)生产方式面临解体后,经济要素获得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与空间上的重新集聚,从而导致各个地理层次(国际间、国家内)上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美国加州硅谷、意大利东北到中部地区、法国图卢兹科学城、德国巴登-乌腾伯格地区为代表的大批产业集群的诞生就是其重要体现。这些地域不仅是人口和各种其他经济要素的聚集区,而且通过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间在有限空间内的不断互动,为创新——这一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针对这些区域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西方学者分别从交易成本、制度以及创新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1 交易成本学派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大量生产女性服装的企业在洛杉矶地区的空间聚集吸引了美国地理学家Allen Scott的注意。他发现由于存在交易成本的原因,该行业中劳动分工与地理集聚之间具有因果关联。具体而言,企业间的劳动分工一方面可以将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有效地避免出现生产技术上的“锁定”效应,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也会增加上下游企业之间交易成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交易的频率高、性质复杂,而且无法通过企业管理加以内部化(williamson,1985)。而且这种成本往往随着交易企业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如交通运输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当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默契共识对交易的达成至关重要时,地理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缺乏相互了解会直接阻碍交易的进行。因此,相关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就成为减少此类交易成本的一个有效办法。随后,Chistopherson和Storper(1986)对加州好莱坞地区的媒体产业,以及其他学者对法国以及意大利产业集群(Holmes,1986)的研究,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尽管交易成本学派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它是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因此容易忽略促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和要素——制度与创新。事实上,交易成本的减少既不是集聚的唯一、甚至不是最为重要的动因,也不一定是集聚形成后的必然结果。在该学派学者后期的研究中,他们自己也逐渐发现集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创新的手段(Cooke和Morgan,1985)。也就是说,企业的自发聚集并不完全、或者并不主要是出于减少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的考虑,而是为了进一步的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同样,物理空间上的集聚最终是否能够带来交易成本的减少,乃至创新的发生,还有赖于除市场力量之外的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才流动、金融支持、研发活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构成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合理关系的区域治理结构和地方文化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新制度学派应运而生了。
1.2 新制度学派
区域经济研究中新制度学派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对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东北部到中部一带,即所谓“第三意大利”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崛起。Piore与Sable(1984)将其特点概括为灵活性(flexibility)加专业化(specialization)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以区别于福特制模式下以大规模流水线为典型代表的生产方式,并将这种产业模式和社会关系的兴起归因于该地区历史上所形成的以信任、合作为特点的文化传统。这种从某个地区特定的“软制度”着手,分析该地区经济结构与其之间的嵌入性(embededness)的方法(Polanyi,1992),已逐步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尤其是以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北卡罗莱纳州三角区为代表的等新工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的主流趋势之一(Harrison,1992),并以此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个意义上的制度,不仅仅包括成文的法律、规章和机构等显性制度的直接制约,还包括不成文的宗教、文化、习俗等隐性制度的深刻影响。新制度学派的核心就是将制度视为不断重复的社会实践过程,和在此基础上构成的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并通过这一视角对社会经济问题展开研究。
新制度学派的兴起颠覆了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线性(linear)发展观。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没有标准化的模式可供遵循,尽管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大体一致的,但是各个地方发展的具体路径却是因地制宜。小企业和灵活专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大企业和传统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完全替代。单个企业的规模大小,基于集成的一体化与基于分工的分散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经济体,都有可能是成功发展的方向。其次,企业之间的关联互动也没有所谓唯一最优的模式可供选择。一个抽象空间意义上并不完美的网络拓扑结构,有时却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实际运作却最为顺畅。而后者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可能会远远超出前者在结构上的不足。也就是说,新制度学派将区域发展的路径选择视作在该地区社会文化基础上内生的结果,也因此对其后区域发展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 创新体系学派
事实上,在交易成本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研究中,对于创新这一主题已有所涉及。如前者的代表人物Scott和Storper(1987)就曾提出,技术创新可以从劳动分工和产业集聚的角度加以解读,而Saxenian(1994)对于硅谷创新优势的阐述采用的也是以灵活专精为研究对象的新制度学派的方法。然而,创新体系学派与前述学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创新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它所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交易成本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分别只是从经济成本或历史文脉的角度对产业组织形态加以说明,并没有对产业的内容和性质加以进一步区分,如同样是具有灵活性与专业化特征的不同地区,却可以在技术创新表现上大相径庭。
创新体系学派有两个主要分支。一个是以北美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其主要关注硅谷、波士顿地区128公路等高新技术中心形成的原因,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对技术研发活动的孵化和孕育。然而,尽管这些研究表明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相关性,却并未清楚阐明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和因果关联。换句话说,世界上有很多研究性大学,但为什么偏偏是硅谷和128公路最终成为举世瞩目的高新科技产业基地?对此,部分学者注意到,一些特定的政策措施也是促进这些高新技术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比如,硅谷的诞生除了与大学毗邻之外,也与美国军事工业选择布局于西海岸密不可分(Markusen,2000)。然而,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政策因素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同样也存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为什么偏偏是硅谷?也就是说,以上经验研究都未能对高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规律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创新体系学派的另一个分支是欧洲以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的区域经济学家为主的研究群体,即GREMI(Groupement Européen des Milieux Innovateurs)所创立的方法,其关注的核心是创新的社会环境(milieu),也就是导致创新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或者说是在各个社会经济主体,如厂商、消费者、科研人员、政府官员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之间建立的有利于创新的网络关系。因此,GREMI不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与新制度学派对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有共通之处,认为人的行为与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往往是受到特定地域文化的限制,从而使区域经济研究的学科领域冲出了经济学以抽象理性(rationality)为前提的逻辑框架,而且就目的意义上的创新指向而言,GREMI对于创新环境,也就是马歇尔所说“集群中飘荡着行业秘密的空气”的研究,也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实现静态均衡(equilibrium)为目标的固有范式。然而,与马歇尔一样,GREMI未能阐明创新环境的运行机制与具体内容,也就未能在理论上将区域这一空间维度纳入对创新环境的研究。
2 区域经济研究和发展的新方向:相互依赖与创新孵化
鉴于交易成本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在视角和内容上的局限,以及创新体系学派在理论一般性上的不足,Nelson和Winter(1982)等人开创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率先对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现象作出了系统回答。他们认为:技术是沿着某种轨迹(trajectory)逐步发展起来的。创新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某个天才的伟大发现,而是在一定共识基础上创新主体之间相互学习和了解这一长期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创新是一系列相互影响的选择的结果,经济活动主体之间通过共享劳动力与人才市场、公共机构与制度、风俗习惯与传统价值观等不可移植(non- traded)因素而形成的相互依赖(inter- dependence)是创新所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过程。
演化经济学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创新过程给予了完整的理论阐述,而且发掘了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对于形成以创新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当创新,尤其是重大创新活动容易受到很多潜在变数的影响时,相互依赖对于主体规避风险、实现创新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增加,而这些条件只有在一定的区域空间范围内才有可能具备。对此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也有类似的分析(Romer,1990)。正是由于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使技术创新一定时期内也往往呈现出批量涌现的特点(Lundvall,1992)。换言之,这种不可移植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上的集聚,会帮助该范围内经济活动主体描绘出更高的创新轨迹,从而使他们能够以高端的竞争优势(如技术优势)而不是低端比较优势(如成本优势)立足于全球市场,并最终表现为区域间的专业化和差异化。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主体间的学习互动和相互依赖越普遍,经济区域化的趋势越明显,创新的动力也就越强大。
法国学者Maurice等人(1986)曾以德国制造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为例对这种相互依赖性作出了形象的说明。他们指出,德国技术工人从其学徒时起,接受的就不仅仅只是政府所提供的技术培训,而是走进了一个精装细作的生产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技术工人”的身份是受到尊重和崇尚的,他们也因此对自身的职业道路有着明确的预期,从而愿意利用终身持续的技术培训来不断地充实提高。在德国社会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高度协同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才是其制造业得以走向世界尖端的真正基石。沿着演化经济学所开辟的这条道路,一系列以区域内主体间“相互依赖性”为重点的新兴研究方向也应运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干中学”(learn by doing)和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的研究(张延,2009),以及跨学科研究中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析(王磊,2008),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在区域这一空间维度上孵化形成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对推动创新活动、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此外,演化经济学理论还通过阐述“相互依赖性”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演变,解释了区域经济的起伏兴衰。在某种技术诞生的初期,由于市场上几乎没有为其量身定做的零部件和技术人才,创新主体就必须自行打造和培养其所需要的产业链和人员储备。在这个同步演化的过程中,创新所需要的物理中间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都从起初通用性(generic)很高的要素,转变为与创新主体具有紧密联系的专用性(specific)很强的资产。随着基于创新的技术知识和行为规范成为这个范围内的行业共识,主体间相互依赖性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而使这一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建立起自身的影响范围,形成区域经济的崛起。而当技术走向成熟而变得易于模仿(如成为全行业标准),其物理资产和研发人员的专用程度下降,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开始由强转弱,于是在空间上就表现为生产活动的扩散,基于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也逐渐被基于成本考量的比较优势所替代,区域发展也会随之由兴盛走向衰退。
3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对于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回顾表明,近30年来区域经济的崛起不再是古典区位论中厂商最小化交通成本后,或者经典经济发展理论(如增长极)中经济政策下外生的空间结果,而是当代在全球化以及以垂直解体(vertical disintegration)为代表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post- Fordist)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经济生活所内生的一个基本过程(process),而这个过程的本质特征是主体间形成的相互依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新活动。这就决定了当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等“硬”性政策带动,转向取决于经济活动主体间的信任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协同行为。相应地,区域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也从线性的投入产出关系转变为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技术、制度和思想创新。换句话说,区域所蕴含的无形(intangible)社会关系,而不是承载的有形(tangible)物质投入,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研究所关注的热点和区域经济能否成功崛起的关键。
与上述好莱坞、第三意大利、硅谷等地区的成功经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意大利南部梅佐乔诺(Mezzogiorno)地区的区域发展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70年代该地区政府在拥有更大自主权的条件下,借助欧洲范围内的大量资金投入,广泛兴建了道路、机场、桥梁、市政和教育设施,寄望以此能带动该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Putnam(1993)在经过长达20年研究后,发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缺乏一种能动员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以形成协同力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由于该地区长期存在着畏惧新生事物和彼此间不信任的社会气氛,这使得希望借助资金投入和设立形式制度来发展经济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成为徒劳。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80年代的法国。当时由社会党执政的法国政府希望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在交通、通讯和教育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来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而忽视了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保守意识和文化,结果使得政策收效甚微。
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由着眼于“有形”要素投入向重视“无形”关系形成的转型,和世界范围内区域发展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表现为高度依赖于投资拉动。2000年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为35.3%,这一指标在2008年已达到43.5%。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全世界2008年平均水平仅为22.7%,其中发达国家为20.4%,发展中国家也只有28.2%(UNCTAD,2009)。而2009年全国范围内11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更有可能激发地方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加重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投资的依赖,而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上还是在环境资源上都是难以持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而后者是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度、政策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的(吴敬琏,2009)。正如《财经观察》评论所言,“中国经济不缺乏整体规划,缺乏的是对于经济规律与市场竞争的尊重与维护…振兴也绝非靠修路搭桥、拆迁卖地所能实现”(搜狐经济观察,2009)。
与单纯增加要素投入的方法相类似,区域发展实践中常常采用的另一项措施,是在形式上“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然而,这些“空降”的政策措施往往都因其难以获得本地区经济活动主体的认同,而最终无法在本地区产生同样的效果。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并不在于制定多少与此相关的规章条例,而是在于创新的精神深入人心,从而推动经济活动主体产生自觉的集体协同行为和相互依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我国要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局面,就不能通过中西部地区简单照搬东部发达地区“先进经验”,走高投入、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的老路。那样不仅将难以缩小与后者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而且还会对该中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应通过各种措施来引导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抬头望天”到“眼睛向下”,即从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指标的高歌猛进,转移到结合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确定相应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发掘和培育该地区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关系中有利于有利于强化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效应,有利于实现集体创新的方面。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并且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收稿日期:2010-03-03
标签: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