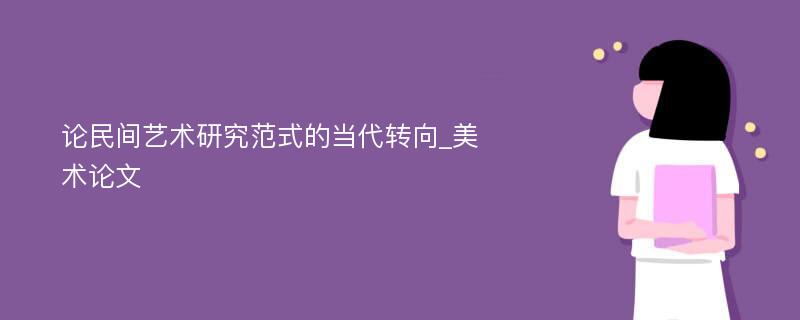
论民间美术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论文,民间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1)03-0048-03
一、从“文本”到“语境”
长期以来,民艺学界对于民间美术的研究,其主导性研究范式是对民间美术文本的研究,或是就作品的材质、造型、色彩等进行分析,或是就某一类民间美术的历史加以梳理,或是对某一图像的内涵进行解读等等。应该说,老一辈民艺学家如王树村、张道一、薄松年、李绵璐等,他们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民间美术文本的研究上,他们在民间美术文本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建构中国学派的民间美术理论体系,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研究范式逐渐显示出不足和问题。那就是,在研究民间美术时,往往将其从具体的时空中抽离出来,无视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很少考虑它与传承者、受众的复杂关系。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可能导致研究视野趋于狭隘,理论话题变得陈旧;另一方面也将导致民间美术的研究越来越脱离民众,现实意义趋于弱化。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批中青年民艺学者注意从单纯的文本研究中超越出来,进入具体的地域,在明确的语境中考察民间美术,并在文体写作、理论思考等方面表现出相一致的学术取向。整体上说,在语境中考察民间美术的研究范式,其不同以往的研究之处在于,强调在具体时空中观察民间美术,注意民间美术与传承主体、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的复杂关系,将民间美术的传承视为人们的文化演进和生活延续。因而,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意味着从静态的考察转向动态的考察,从单维的关注转向多维的关注。
什么是语境?按照哲学家的说法,“语境”有两种含义:其一,指话语、语句或语词的上下文,或前后关系、前言后语;其二,指话语或语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说明言语和文字符号所表现的说话人与周围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可扩展为事物的前后关系、境况,或者扩展到一个特定的“文本”、一种理论范式以及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可以看出,前者是一种狭义的语境,后者是一种广义的语境。这两种语境都决定着话语意义的生成。
民间美术研究的语境,包括时空、人、文化生态、历史传统、日常生活等要素。在研究中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关注,不仅有助于民艺学者拓宽研究视野和形成新的理论话题,而且有助于他们现实参与民间美术的保护与传承。
客观地说,民间美术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向,与其他学科的深刻影响密切有关,特别是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现象学、后现代文化批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理论和方法论,为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民间美术,是一种“大美术”概念,具体包括民间工艺、民间绘画、民间器具等造型对象。建立在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拟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成果为例,来观察民间美术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向,以发现这些学者在民间美术研究中共同的学术取向。
二、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的关键词
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就是将自己的研究活动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进行细致深入的田野考察,以观察和描述这一具体时空中民间美术的存在状况和各种变化。由此,民族志、传承人、文化生态、变迁、日常生活等,便成为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的关键词,也表明当代民艺学者的兴趣所在。
(一)民族志。由于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今民艺学界在民间美术研究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志调查和写作。对民间美术作民族志调查和写作,意味着将对象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之中,而不是将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的民间美术拼凑罗列在一起,建构一幅泛时间和泛地域概念的民间美术图景。事实上,民间美术总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中的民间美术,在制作方式、题材内容、形态特征以及相应的民俗风情等,都有一定的差异。因而,民族志调查,有助于民间美术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入程度。
对民间美术进行民族志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个别学者开始尝试,比如杨先让先生通过对黄河流域乡村中的炕围画、剪纸、木版画、布制品等民间美术的考察,撰写了《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艺考》一书,便是民族志调查的可贵尝试。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呼应。只是在90年代末以后,才有越来越多的民艺学者自觉地在语境中考察民间美术。由于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一直以来蕴藏着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所以也就成为民艺学者热衷调查的地域。比如靳之林对于表示中国本原文化“生命树”图式的解读,主要是结合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考察来进行的,并撰写了《生命之树》一书,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此后,乔晓光的《沿着河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郭庆丰的《纸人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5]和方李莉的《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6]等著作,是对黄河流域民间美术更为深入系统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著作在文体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像传统学术著作那样充斥着大量的艰涩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富有生活质感的民族志式的文体。这种民族志式的文体也表明作者对民间美术作整体观照的学术取向。
(二)传承人。在以文本为中心的民间美术研究范式中,民间美术的传承人常常是被忽略、被遗忘的。而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民间美术的传承人往往受到高度关注。传承人的人生阅历、师承关系、生活环境、性格特点等等,都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可以说,当今民艺学界对于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正日益显示出强劲的活力。
这是由于通过对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的记录和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民间美术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也有助于体察民间艺人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大历史之间的关系。比如郭庆丰的著作《生灵我意——人民艺术家周苹英个案调查》,不仅介绍了剪纸艺术家周苹英高超的剪纸技艺,而且深究了她的生活与性情对其技艺的影响,从而凸显了民间艺人的主体性。此外,王文章主编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也是将民间艺人置于中心地位。丛书对泥人世家、年画世家、风筝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剪纸大师、陶瓷大师、唐卡大师的成长环境、人生历程、师承关系、精湛技艺和所思所虑都进行了记录,用民间美术传承人的生活史来演绎民间美术的发展史,从而使民间艺人的叙述和追忆转化成了公共知识,完善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的内容体系。
(三)文化生态。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文化生态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的体系。这里的文化生态是指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种要素。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主要考察文化生态中各要素对民间美术的影响,以及民间美术对文化生态各要素的意义。
唐家路的著作《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提出民间艺术(该著作中主要指民间美术)的研究,要对其生活形态、信仰观念、伦理情感、传播媒介等各个方面加以关注,以便全面把握当代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从而表达了民艺学界对民间美术的文化生态进行研究的理论愿望。潘鲁生主编的《民间文化生态调查》丛书,可以说是对这一理论愿望的回应。该丛书分《锦绣衣裳》、《以食为天》、《民居宅院》、《车行舟进》、《农事器用》,记录了山东等地的民间服饰、民俗食品、民居建筑、民间舟舆、农业器具的存在状况,也记录了调查者对其造物思想、科学价值、文化内涵、审美理想等的考察和理论总结,为我们研究民间美术的文化生态提供了成功的研究范本。
(四)变迁。单纯以民间美术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范式,基本上将民间美术看做是与现代社会脱节的“遗留物”。这种研究基本上不关注民间美术的活态传承,也不注重从田野调查中获取材料。因而,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削弱了民间美术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体系中的合法性认同,而且削弱了研究活动本身的社会意义。事实上,现今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精英们想象中的田园牧歌生活,已被现代化、全球化的事实无情地摧毁,民间美术所依托的传统也出现松动甚至断裂。当今的民间美术,无论其功能还是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变迁”的概念进入到民艺学者的视野。
由于“变迁”概念的引入,学者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时,便会对民间美术的现状与历史加以比较,关注其实际功能、形态风貌、生产方式、市场空间、消费群体、传播媒介等的变化,并探寻影响其变化的力量。因而,“变迁”概念的引入,意味着民间美术的研究从历时研究转向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从静态的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考察。方李莉的著作《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调查》,便体现了作者“变迁”的研究视角。作者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发现,景德镇的民窑业在中国古代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支撑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并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其传统的制瓷手工技艺被现代化的技术所改造,与制瓷手工技艺相关的人文景观、文化传统、民俗风情也大量消失。而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景德镇家庭手工陶瓷作坊复兴起来,传统民窑的生产组织形式、行业分工方式、销售流通机构等也在重现。作者进而认为,景德镇民窑艺人的手工技艺和生活境遇的变迁,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11]此外,王海霞的《透视: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民间艺术》一书,也是“变迁”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对北方一些乡村的考察,发现正是民俗文化的变化才导致民间美术的变迁。比如由于人们居住方式的变化,才导致了炕头画的失落;由于人们厨房的革命,才有了灶王画的式微等等。因而认为,传承民间美术的前提,就是要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可以说,之所以用“变迁”的视角来透视语境中的民间美术,这是因为民间社会并不是一个与外界没有关系的封闭、自足的社会,而是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一起跌宕起伏的社会。
(五)日常生活。存在于人们各种生活场域中的民间美术,在为民众提供实用功能的同时,也构成人们生活美学的一部分。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以来,“生活世界”的学术意义也逐渐为中国的民艺学者所重视。王宁宇主编的《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一书,记述了关中地区木作工艺、传统制秤工艺、扎扫帚工艺、灯具制作等工艺的存在状况,注意到这类民间器具为农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调查者认为,这类民间器具因为与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所以成了一种文化资源。此外,李炎的《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以云南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工艺为调查对象,以观察这些工艺品在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情况。作者发现,尽管有些工艺品因为工业制品的冲击而淡出当地人的视野,而有些工艺品因为游客的关注和喜爱,也回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已成为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的又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三、结语
当代民艺学界对民间美术的研究,逐渐从以文本为中心,转向以语境为中心,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是中国民艺学界不断吸收国外艺术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发生的。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使得民艺学者更为珍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相关理念,创造性地转化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论。
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有助于洞察民间美术与传承人、文化生态、历史传统、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复杂关系,更好地把握民间美术真实的存在状况,也有助于民间美术研究获得更多的活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我们尚不能说民间美术的研究范式已经成功转型,而是仍处在尝试和探索阶段。正是因为这种日益占主流的研究范式还不成熟,所以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反思:当我们孜孜于田野调查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民间美术文本的研究能力正在退化?当我们满足于一个个个案的研究时,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丧失全局的视野?当我们借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时,艺术学的主体性是否正在弱化?……特别需要警醒的是,当一种研究范式为大多数学者所掌握,成为一种学术操作模式的时候,学者的学术研究很可能会沦为学匠式的重复劳动。
因而,民艺学者对于民间美术的研究,在注重语境研究的同时,也要注意提升文本研究的能力;在进行个案研究的时候,时刻要有“中国的”和“世界的”眼界;在借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时,要突显艺术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魅力。同时还要明白,学术研究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研究范式,学术研究的活力源泉之一便是研究范式的相互激荡和不断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