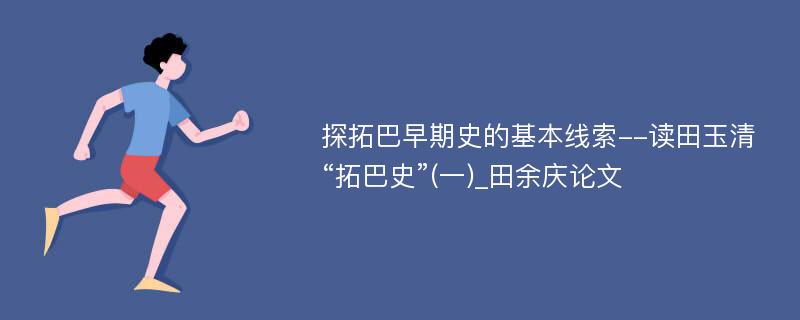
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跋论文,一书论文,线索论文,读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面世后,学界同人续有评骘,二三朋辈复加讨论。对北魏前期或魏晋以来北部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关系,此书所探可谓提纲挈领,值得反复回味。本文欲就田先生此番研究的背景与成就有所归约与申说,更欲就田先生提出的问题有所发挥与探讨,希望能有益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一项困难重重而意义深远的研究
有两种史家,一种是没有洞察力的史家,一种是有洞察力的史家,田先生是有洞察力的史家。有两种研究,一种是由简而繁穷其枝叶的研究,一种是举重若轻明其要津的研究,田先生的研究总是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约。有两种著述,一种是消除了许多问题的著述,一种是提出了许多问题的著述,田先生的《拓跋史探》,就是后一种著述。
此书所探乃拓跋早期历史(注:所谓拓跋早期历史,指天兴元年道武称帝以前的拓跋部族史,亦即田先生说的拓跋的“开国前史”。),诚如田先生所述,这是中古史上一个著名的“模糊区域”。而所谓“模糊”,一个重要的由头在于拓跋早期史料甚少又争议颇大。即就魏收书而言,《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元魏史》叙述了北魏国史的文本递嬗关系,其中有关拓跋早期历史的记载,源头多在道武帝时邓渊编纂的《国记》。而《国记》的可靠性向有三大疑问:一是拓跋部族早期并无文字,先世之事只有口耳相传之说,其中必多神话传奇之类,据此修成的《国记》自亦难为信史。二是道武帝开国规模而编修《国记》,本有浓厚的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之意,也就不免会据其现实要求而附会造作。三是《国记》在太武帝朝续修时又掀起过巨大波澜,主持修史的崔浩及连带诸臣因暴扬“国恶”而被族诛,其中违碍之处复经涂抹删改。因而拓跋早期史事,从其口述史的源头到成文史的最早两次编修,就已决定了其内容的扑朔迷离和疑团重重。近世史家精博者如吕思勉先生曾言:“拓跋氏之初,盖亦匈奴亡后北方鲜卑之南徙者。其后得志,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史事之真,为所蔽者久矣。然即其所造作之语而深思之,其中真迹,固犹可微窥也。”故吕先生一方面引《序纪》所述远祖迁徙之迹及神元以来史事,以证拓跋早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指出:《序纪》“云(成帝)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也;云大姓九十九者,与已为百姓也。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再传而至神元,凡八十一世,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究也;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于三皇五帝。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而世数及所统国数,无一非三、五、九之积,有是理乎?”(注:上引文皆见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上册第三章《西晋乱亡》第八节《鲜卑之兴》。)吕先生以三、五、九等数及“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为无理,固是不熟悉民族学材料的误断(注:在各族早期史诗或歌谣的叙事范型中,涉及数字时往往都有一套“定数”,我国古代则三、五、九等皆是这类定数的构成元素,直到现代如“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的“九”,亦是。故这类数字所指之数固非史实,但其在有关史诗歌谣中,却是无比真实的。);但以民族学家而精研民族史的马长寿先生,也说,《魏书·序纪》“本是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写成的。任何一种传说,其中必然是有真有伪。史学家能够下一番辨别真伪,留真去伪的工夫,拓跋鲜卑的原始真实面貌,仍然可以使它大致恢复起来。”(注:见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四章《拓跋鲜卑》一《拓跋鲜卑的起源和迁徙》。)除少数持论极端者外,吕先生和马先生这种观察角度虽有所不同,然对《序纪》内容皆有信有疑,在大量狐疑问视其为大体可靠,许多史实又难确证的看法;业已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拓跋早期史料上的模糊程度,以及欲治拓跋早期史的现代学者,在基础史料上所面临的僵局。
若仅仅是模糊,倒也罢了,因为模糊和未知的区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决无可能、也无须狂妄到要逐一去“以有涯济无涯”。问题在拓跋早期史这个模糊区域,对中古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必须将之纳入考察的视野。这种重要性,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北魏这个拓跋部所创建的北方王朝。要之,北魏一朝既是永嘉以来北方地区自乱而治的转折点,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具有关键的承前启后地位;也是自汉至唐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问题从纠结爆发至舒展缓和的关键时期;更是阿尔泰语系各族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的王朝,是北方草原部族与中华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座极其重要的界标。(注:我们这里说“北方草原部族”,当然不是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一书《序言》所说,“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草原地带”,亦即Eurasian Steppes上的所有部族,而只指中国北部的草原部族,具体兼指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突厥、蒙古语支各族而言。)而所有围绕着这三点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必须深入到道武帝以前拓跋部族的发展史中,来求得很大一部分解释的背景。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上述后一点,因为它不仅直接关联和说明着前两个态势,也是拓跋早期史及其研究极大地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史的部分。创建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部,实际上既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又统一了北方地区的草原部族;也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完全吸纳了北方草原部族因子的中国因素。换言之,拓跋部族及其所创建的北魏,不仅空前深切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东北亚这个世界史上著名的民族迁徙策源地中,各族存在、发展和相互关联的大势;而且也在北方草原部族中,成功地竖起了第一个扎根塞北而统治中原地区的样板,从而也无可避免地构成了影响和改变各部族传统迁徙格局和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因素。即此亦已可见,拓跋早期史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其族源和迁徙过程,还是部族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的变迁,或者诸部族间的相互关系格局,在说明其何得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巩固地统治了整个北方地区,亦即其何以成为永嘉乱后北方地区治乱盛衰消长的转折点和自汉至唐社会变迁的重要枢纽,乃至于其何能以草原部族而构成中国因素,从而影响了此后东北亚以及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关系和文明发展时,其价值和意义实在是不言而喻的。
但问题既若此之重要,史料又稀缺而可疑,要推进其研究的困难不言而喻。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另有一奇特之处,从近代史学兴起至今约百年之中,这块史学园地真似独得上天之眷顾而宗匠辈出,大师云集,一流学者聚集的密度及其各领域被深耕细耨的程度,堪称我国史坛之最。试想,在陈寅恪、马长寿、唐长孺、周一良等顶尖学者先后建树的一块块里程碑式的成果面前,一个后来的治史者,怎能不在高山仰止之下,油然而兴余生也晚之感呢?故尔直到近些年,北朝和北魏历史的研究(更不用说是拓跋早期史的研究了)给人的印象的确很容易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殆已网尽。连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填充前辈学者所搭骨架的工作,亦显賸义无多而须挖空心思,而留下来的问题则似暂无条件解决。看起来,除非在新资料的发现上另有机缘,抉发北魏历史特别是拓跋早期历史问题的前景,似乎已山穷水尽,难以为继了。
评论文字,历来为难,难就难在衡量的标杆难竖。我觉得上述几点,就是评介《拓跋史探》所含研究工作的几根最重要的标杆。除此之外,即便还有另外的标杆,也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竖立,那是后话,且先搁下。就基本面上总括说来,田先生这次选定的,实在是一项意义深远又困难重重的研究。说意义深远,是因为其不仅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或北魏一朝的研究,也关系到了整部中古史发展递嬗的枢纽和东北亚古代民族关系格局的转移。说困难,是其并没有多少新材料可据,旧史料又充满了疑团和问题:可资借鉴的杰出成果不少,仍足发挥和阐扬的余地不多。因而《拓跋史探》所收各文的研讨,不止是一如既往地体现了田先生过去开题运思的法眼和惯解难题的才华,更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史家在追求历史真谛时的无畏勇气和广阔胸襟。而田先生此番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固亦主要倚仗了他那田氏标牌式的识力和理论架构能力(注: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现象之间新的联系和因果链条既被建立,有关问题及其演变的脉络随之便被凸显,而与之相应的结构性理解或新的诠释体系,也就蕴含于中了。我以为这是田先生所示理论架构工作中最优美的部分。):更以令人吃惊的谙练程度,示范式地在解析拓跋史诸长期悬而未决之题时,融贯综用了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也正是因此,田先生此番对早期拓跋史的探讨,也再次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高度。
二、本书的主要贡献和启示
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最终结论有曰:“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这是在1986年,从中我们已看到田先生的目光投向了江北,投向了代北茫茫的草原。一晃十余年过去,到1998年,《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发表于《国学研究》第五卷,将届七十五高龄的田先生,围绕着道武帝时“子贵母死之制”和“离散部落之举”背后的现象和联系,深入探讨了神元以来君位传承及其常与“后族”关联的种种问题。到2000年第3至4期《中国史研究》连载《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长文,在前文所示后族问题常为乌桓问题的基础上,正面考察了拓跋与乌桓关系的各个侧面,及其对于拓跋早期发展史的意义。接着《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继前文对《序纪》内容的深入解读之后,揭出了拓跋部族从口述史到成文史,从部族史诗到王朝国史演变过程的种种窍要,这又为重新深入理解拓跋早期史料和北魏国史系统牵连的问题,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次年,田先生将此三文及相关诸文辑集成《拓跋史探》,在《前言》中开头便道:五胡十六国这个破坏性特强的时期的结束,归根到底是五胡之间及其主体部分与汉人之间关系发展和逐渐融合的结果,“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生催死的任务呢……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就这样,我们已亲身见证了魏晋南北朝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笔。上引《东晋门阀政治》结尾和《拓跋史探》开头的这些文字,十分清楚地把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与未来北方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与一个时期内南北全部历史运动主流部分的走向,也就与我们前面所述“整部中古史演变递嬗的枢纽和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格局的转移”,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代表,田先生此番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从君位传承与后族的关系、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入手,通过对一系列史实和问题的重新梳理,揭出了神元至道武帝百余年中,拓跋部发展过程所围绕的专制皇权的逐渐树立和族际关系的日趋融合这两大主题。同时又针对《序纪》这份拓跋早期史的基本史料,理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演变递嬗及相关问题的发展线索。于是,从自身社会形态到外部族际关系,又从基本问题到基本史料,田先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拉出了新的线索,拓展了新的方法,诠释了新的事实;也就搭起了新的研究框架,开辟了早期拓跋史研究较以往更为开阔的新前景。
以下先就前二文述其主要成就和启示。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乃是田先生此次研究早期拓跋史的核心文章,其他各文展开的种种问题,几乎都已包含其中。后来田先生把此文的构思写给《学林春秋》收录,就已表明了它在田先生心中的份量。而此文的成就,首先当然是出色地完成了“子贵母死”这一奇特制度来龙去脉的考察。可以说,这个史界长期不甚清楚的问题,至此已得到了确解或现时条件下的最优解。而能够弄清此制来龙去脉的关键,端赖田先生在隐微的记载后面,抉出了神元以来拓跋部君长传承往往母强子立的史实,并且理出了百余年来拓跋部君位传承常与后族相关这根重要线索,也正是在这根线索所代表的历史前提下,直到道武帝登位称帝,建立和巩固专制君主秩序时,也就有了强烈的必要,来抑制或预防母后和后族势强干政乃至于危及君位传承秩序,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子贵母死”之制的基本背景,并把此制与道武帝的“离散部落”之举,在同一线索和同一需要下,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又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离散部落”这个拓跋建国史上重大事件的认识。无庸置疑,对北朝史,对鲜卑拓跋部史,对一项具体的制度史研究来说,在有关研究已多年沉寂之后,就这些,已足构成相关学术史上的第一流成果了。
但文章至此虽已结束,田先生提出的问题却毋宁说刚刚开始。因为在材料稀少及其所含信息多已流失的情况下,“子贵母死”及“离散部落”这两个具体的事件,仍然是不足以承载拓跋部从部落联盟上升为专制国家这个基本历史过程的种种问题的。正如田先生后来指出的,问题一旦放到了“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下,就势不能不超越“子贵母死”及“离散部落”这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和举措;甚至也不能不超越神元以来拓跋部君位传承常与后族相关这根具体的线索,来进一步考虑与之关联的各种事件和现象。而这样一来,相应的研究也就势不能不从制度史或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进入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又从一般的历史学方法,发展为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等对象本身所要求的多种手段了。尤其是田先生在文中指出:神元至道武帝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两种继承秩序的激烈竞争”,是部落大人支持下的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与代表专制君主制方向的父死子继制的消长过程,而“皇后和母后干预继承秩序,在艰难的斗争中为父死子继制开辟道路,也是拓跋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此文《小结》中田先生又说:“子贵母死,出现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一个特定阶段……它的出现,符合拓跋部摆脱无序继承的纷扰以及巩固父子继承制度的需要;符合进一步消除强大外戚干预拓跋事务的需要;更为根本的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的需要。”很明显,在此文所观照的拓跋部从部落社会向专制国家演进这根总线索下,田先生再次敏锐地洞察了专制皇权的形成过程,乃从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浓缩了当时拓跋部族组织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而其焦点,则洵为君位传子秩序在君长与包括后族在内的各种贵族势力的关系架构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注:此文四《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述:时代、社会和历史的“诸多因素造就了道武帝拓跋珪,使他得以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国家皇帝角色演变,他势弱时不能不沿着旧有轨辙,引外家部族介入拓跋内部事务,平息诸父诸兄对君位的挑战;势强后却不能继续承受外家部族对拓跋君权的影响和控制,力求摆脱外家部族。”已经说明了拓跋部君位传子制发展过程的这个不限于母后和后族的关系格局。)这就提示和开辟了在此文基础上继续研究拓跋部专制皇权形成和社会演进过程的广阔道路。
因此,当我们今天回头再看田先生此文的贡献时,相较于前述具体成果,田先生的这些只是明确提出来,而并未在文中正面展开论述的线索和问题,当具有更为重大的影响和价值。因为把专制皇权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当时拓跋部族组织和社会形态变迁的一个缩影;又把君位传承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制的过渡和发展,作为当时拓跋部专制皇权形成和发展过程所汇聚的焦点,才真正升华了“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内涵,也明显构成了早期拓跋史研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新命题。(注: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所收《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可称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拓跋建国史的代表作。)而相较于君位传承常与母后和后族相关的线索, 君位传承常在君长与包括后族在内的诸部大人势力的关系格局中演进的线索,无疑也要更具有概括力和丰富的内涵。由此再观察和诠释拓跋部早期的种种记载,不待言,早期拓跋部族演进的许多史实和问题,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幅刷新。也正如我们在学术史上偶可见到的那样,无论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能够解决难题固然高明,但这个过程还能进而为研究提出新的命题,新的线索,并且示范新的方法和揭示新的事实。那么其贡献就只能用杰出二字才能形容了。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一文,既是上文提出的,后族问题就其部族背景而言往往是乌桓问题的深入展开,是拓跋早期发展史中的“乌桓因素”具体构成和影响的正面探讨;更是从拓跋与乌桓的关系出发,对当时代北地区以拓跋部为主导的部族关系,乃至于对后来北魏之所以能稳定地统一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背景的“宏观考察”。同时,此文也是一篇就米下锅,就有限材料之所及,对久已盘旋于田先生心头的论题作多角度多侧面探讨的文章,故其又头绪纷然而线索交错。不过要而论之,本文成就,首在于四:一是清理了拓跋早期发展过程与乌桓密切相关的大量事实,二是确立了神元帝以来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东西相向互动共存关系的人文地理格局,三是揭示了乌桓在拓跋部所主导的部落联盟内部新、旧人关系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四是理出了道武帝前,两种代北乌桓在趋异和趋同的复杂分化组合中相继融入拓跋部治下的线索。(注:“两种乌桓”,唐长孺先生称为汉以来作为东胡之乌桓和魏晋以来作为杂胡之乌桓,田先生称为“上谷以西乌桓”和“屠各乌桓”而合称之为“代北乌桓”。)也正由于部族之间这种密切关联的史实,势必要求拓跋史和乌桓史这两个以往联系不够的研究领域的通气接头。于是,正如田先生此文所示范的,各种乌桓史研究的成果,均被放到了拓跋史的视界之内,成了认识拓跋早期历史问题和解读魏收书《序纪》内容的重大因素;同样地,对拓跋史的深入研究,也相应构成了认识乌桓这个匈奴之后、鲜卑之前北方草原要角的大量历史问题的重要基础。(注:马长寿先生在《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收入《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前言》中指出:“每一族的历史,特别是少数族落的历史,必须放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然后才能理解各族历史的全貌。”田先生关于乌桓与拓跋关系的见解,完全符合马先生归结的这个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此,本文不仅在所涉论域大大推进了以往的认识,更开创了拓跋史、乌桓史研究及当时两族关系所代表的代北、塞北和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的新生面。
除具体解决的问题外,田先生此文时时观照的,正是拓跋早期史必然关涉的塞北和华北地区族际关系不断走向融合的主题。因为这一主题所包含的两大内容:一是北方地区民族关系从趋异走向趋同的过程,二是北方地区民族关系形成新的强势中心的过程,后来确都聚焦到了拓跋与乌桓的关系上。
纵观公元一至四世纪近三百年北方民族关系的大局(注:自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至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于牛川即代王位,为时近三百年。参日本内田吟风先生《匈奴西迁考》(收入余大钧等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北匈奴西迁年表》。),从匈奴衰落至鲜卑崛起,中间似有乌桓为塞上主角,而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势中心。这是此期北方草原各族得以一波又一波南下,其种种能量汇于其南部边缘而左冲右突,轻易就掀翻了刚刚统一了南方地区的西晋王朝的基本原因。同时这也是从华北到塞北,以往存留下来的匈奴余部、武力强悍而部落分散的乌桓、正在陆续抵达塞北地区的鲜卑,也包括汉人豪宗和羯胡等族在内,发生多中心杂胡化趋异现象,导致出五胡十六国乱局的基本背景。因而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北方地区的统一和这个乱局的结束,自必有赖于各族之间趋同势头的发展和足以阻遏北来各族浪潮冲击的新的强势中心的形成。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没有趋同的势头,强势中心就难以出现和巩固;而没有强势中心,也无法遏止北来部族的纷纷冲击和多中心趋异现象,难以保障和完成各族的消化和融合。因而魏晋以来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过程,不仅像许多学者反复强调和研究的那样,是以各族主体部分生活方式的逐渐农耕化和汉化(或合称封建化)为其基础的(注:这方面迄今最为优秀的代表作,仍是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所收《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而且也如田先生此文所示,是以集中代表和促进了这个势头的拓跋部大魏王朝的建立,以汉化过程中组织形态更加松散也变得越益孱弱了的乌桓等族,终于依附和融入了汉化过程中因专制体制的逐渐建立而不断强大起来的拓跋鲜卑,为其转折性标志的。
事实上,在魏晋以后北方民族关系不断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中,强势中心的形成显然已经上升为问题的主要方面,前秦的短暂统一便是一种徵象,一种呼唤。但无论是氐胡所建的前秦,还是慕容鲜卑统治的前燕等地区强权,统观五胡十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倏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都没有以本族为核心来融汇各部,形成巩固的族际联盟以为统治的中坚;相比之下,倒是长期发育于代北的拓跋鲜卑,自献帝以来已经形成了国族十姓间的巩固联盟,神元以来仍在以之为核心而不断聚散着更多的部落,从而逐渐具备了充当这个历史角色的资格。而真正使之从资格变成了现实的关键之一(另一个关键,当然是田先生“子贵母死”一文所示专制秩序的逐渐树立),便是神元以来不断伸缩和变化着的拓跋部落联盟内部,其族际关系正在越益走向融合的过程。而田先生此文着重讨论和提示的几个族际关系头绪:旧人和新人亦即拓跋国姓与部分乌桓部落和汉人之间的逐渐融合,两种乌桓的具体构成及其相继融入拓跋部治下的过程,拓跋部与鲜卑慕容部、匈奴贺兰部等其他内附诸姓渐趋融合的关系;显然已经勾出了拓跋联盟内部这个过程的基本轮廓。
由上可见,近三百年塞上民族关系主角终于由匈奴、乌桓让位于鲜卑的过程,不仅是整个北方地区和魏晋南北朝治乱盛衰的转折过程,也不仅是汉——唐社会历史和东北亚民族关系大局的转移过程,而且是拓跋部为核心的国族十姓联盟来到代北而逐渐走向专制君主秩序,又几经聚散而依附和融入了更多草原部落的建国过程。而代北地区拓跋和乌桓的关系,则同时催化和孕育了这个充满各种复杂反应的过程的最后一百年中,围绕拓跋部专制皇权逐渐树立和内外部族际关系不断融合而展开的两大主题,也牵扯和折射了其中的各种要素,因此又上演了许多由之着眼方可以豁然的历史活剧。而这些,也正是田先生此文及上文所不断谈到和反复提醒我们的内容。历史至此才可以重新研究,也才可以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上基于前人又超越前人。
在“子贵母死”和“共生关系”二文深入解读《序纪》,搭出新的研究框架后,《代歌、代纪和北魏国史》一文,正面探讨了《序纪》这份早期拓跋史基础材料的种种问题。其首先揭示了拓跋部和同期其他草原部落古老的口述史系统,直至他们进入中原后很久,仍在发挥重要记叙功能的事实;又理出了从拓跋口述史系统中的叙事歌谣,到道武帝开国规模时整理出《真人代歌》,再由邓渊等人据以编撰为《国记》,经国史之狱有所删削涂饰后,又转辗构成魏收书《序纪》蓝本的完整线索;然后又把邓渊之死和崔浩之狱相联考虑,讨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过程所赋予修史活动的种种沉重负担。总的看来,此文实际上是通过下列两个方面,重构了早期拓跋史研究的新史实或新材料。(注:学术史已无数次表明,在资料上,富于戏剧性的“藏宝再现故事”,实属旷世奇缘;而真正主导着研究的进展也真见史家功力的是,当讨论开始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下进行时,以往处在视野之外的大量事实才会浮现,许多旧的材料和史实从此增添了新的意义。)
一个方面,是田先生从此已经把《序纪》的解读,安放到了北方草原部落的口述史系统这个可称是惟一正确的基础上。因为在此基础上,就一定要意识到前文字时期,各族传承文明和体现传统的机制,会与其进入文字时期后,或与其周围早已拥有成文史传统的邻居迥然不同;也一定要考虑这个阶段上的部族,其史料出于口述史系统及巫术和习俗系统者,在比重和地位上显然要远远超过其有关史事进入周围文明区典籍系统的文字材料。由此就势必要问:如何来研究这些尚未进入或刚刚受到文字社会影响的部族史,怎样来建构这些部族的史料系统?如何区分这个主要由口述史所构成的系统本身的真实和“史实的真实”,怎样架起勾通这两种真实的桥梁?这就开启了以民族学或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于叙事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手段综合研究的广阔道路,也为祛除长期以来围绕《序纪》“真伪”问题而形成的重重迷雾,开启了一扇决定性的窗口。
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基础的稳固奠立,《序纪》及其研究的意义也才真正显示出来了。在以往北魏史或中古史学史对《序纪》的种种怀疑、辨析和研究中,有两个极大的问题很少被人提及。一是《序纪》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留存至今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草原部族“史前史”,也是公元4世纪以前欧亚草原各部族,借助邻族文字而留下来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口述史记录。二是《序纪》也是我国史籍所录北方草原部族族源和迁徙传闻中,特别是在《晋书》载记和《北齐书》、《周书》、《北史》所录北方有关族、姓源流的口述史遗存中,相对来说最为完整的一份。因而揭示《序纪》的史源与所本,探讨影响其成文过程的种种问题,辨析有关史实与记载之间的联系,对于北魏史和整个北朝史各领域的研究,对于揭示北方草原部族的源流、迁徙和发展过程,当然也对于进一步勾勒当时北方各草原部族口述史系统的状态来说,都具有远远超出早期拓跋史和中古史学史的基础意义。
此外,本文从邓渊之死来探讨拓跋国史系统与有关历史过程的连带关系,也是一个富于启示和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因为易代革命后的新王朝,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族王朝,其国史撰修过程在总结历史开辟未来时所可能具有的冲击力,及其所牵动的传统和现实因素,总是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尤其是对拓跋部来说,其口述史到成文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从部族社会走进专制国家的过程,因而其追本溯源的国史编修过程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所牵扯的君长和贵族大人及不同族姓之间的矛盾格局,所充斥的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实、脆弱与顽固的纠葛,及其这一切所潜藏着的爆炸性,都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国史系统本身的内容和形态,当然就更不必说是有关史官的命运了。
三、在“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之下
体察《拓跋史探》处理所涉问题的三个层面:凡各文直接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求得了确解或现时的最优解;而田先生从中所洞察的问题症结,又尤其令人有目光如炬烛照幽微豁然贯通之感;但在进一步将种种探索落实到“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之下时,亦即田先生此番研究相较于前人开辟最深创见最巨之处,则虽脉络头绪历历可数,思想火花缤纷灿烂,却也出现了若干不够连贯的缺环和歧误。我愿坦率指出,上面所述早期拓跋史研究的主题和线索,依田先生书中表述的理路,是确切无疑的,但在田先生的文中,却并不总是非常清楚的。这倒不一定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未必是“穷思立说”而高年精力难以久注之故,而恰恰是此番研究的问题重大而资料匮乏,几乎处处皆须在无路处开辟之所致。故田先生名书以“探”,屡屡强调所示各端“旨在探路”,除深愿引起共同探索外;也正是因为身为史家,自然深知凿空之艰,开辟之难,而既然选择了卓越,认准了不朽的事业,也就再无理由拒绝挫折。
以下试在田先生所示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下,就其必然要涉及而《拓跋史探》所收各文未能完全展开或有所歧误之处,择其要者略抒己见,希望能芟芟补补,让这条田先生新辟的探讨拓跋早期历史基本线索的道路更加通畅和坚实,并且以此告诉田先生:我们跟上来了。
一是起点问题。以君位传承秩序的确立来探讨专制皇权形成过程的种种问题,以此观照拓跋部落组织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正是田先生精识之所在。但要准确地勾勒相关的历史主题和线索,就一定要明确其演进的起点何在。就是说,神元帝前后拓跋部的君位传承秩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前提下演进的呢?
就民族学业已建立的一般顺序而言,既然是从部落社会走向专制皇权国家,就会有君位传承从推举制走向世袭制的发展过程。从各族酋长会议的机制来看,推举制通常都是要推出一位“兄弟”来做君长,其与兄弟相及之法有内在相通之处。在较为原始的婚姻关系中,“兄弟”正如“姐妹”,可以是群婚范围内的所有同性成员,也就只有当“兄弟”仅限于某一父祖的子孙时,兄终弟及才是私有制下父死子继的一种曲折的发展或过渡形式。具体到鲜卑拓跋部,其推举制向传子制的转折,是发生于献帝时期。理由一,是《后汉书·鲜卑传》:“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而据陈寅恪先生研究,献帝拓跋邻正是檀石槐辖下的西部大人之一。(注:《资治通鉴》卷七七《魏纪九》元帝景元二年胡注,以檀石槐所统西部大人推演为《序纪》中的宣帝推寅。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六篇《五胡种族问题》四《鲜卑》考其时期,断其当为亦号推寅的献帝拓跋邻。而田先生在“共生关系”一文六《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中,有一条脚注误以这条胡注为本指献帝,当改。)理由二,是《魏书·官氏志》:“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魏书·礼志一》载拓跋君长西向祭天的旧俗,须由宗室子弟七人陪祭; 《资治通鉴》一五五《梁纪十一》中大通四年则载北魏皇帝登位的“代都旧制”,须“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由此推断,献帝以来业已形成了宗室七姓共奉拓跋氏子孙为君的格局。(注: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第四章《拓跋鲜卑》二《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之形成》认为这是从较为原始的推举制,发展成了推举对象限于宗室八姓尤其是拓跋氏的世选制,但综诸处所载,我觉得马先生所概括的,也有可能是献帝令兄弟七人分领国人以前的情形,因为献帝既传子诘汾,其君位传承事实上已经是七姓共奉拓跋子弟为君,而已不再是君长从宗室八姓中推举出来的局面。)理由三,是《序纪》述拓跋君位传子,正自献帝传位其子诘汾始;且述圣武帝诘汾崩后其子力微立,神元帝力微崩后其子悉鹿立,章帝悉鹿崩后其弟绰立,平帝绰崩后兄子弗立,从此拓跋君位皆在神元子孙内部父子相继或兄弟相及。故献帝传位其子,实际上是揭开了拓跋君位传承以父子相继辅以兄弟相及的新纪元。
当然实际过程决非如此简单。从推举制到传子制,不啻是公天下到家天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折;是部落民主制遗存不断减弱而专制秩序因素逐渐增长、向后看的传统势力渐消而向前进的革新势力渐长的过程;是拓跋部落组织、社会形态和观念领域的一场革命,也就难免会有重重波折。《序纪》载献帝在世而传子诘汾,拟其挟七分国人的余威而强行传位于子,已自情况特殊;载诘汾、力微父子之际“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以致诘汾崩后,力微竟须隐名埋姓而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注:综《元和姓纂》六《源氏》、《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等处所载,诘汾另有长子匹孤率部远走河西。是圣武帝欲传子而崩,其情势危殆,似已不得保其众子矣。)又载力微欲传位其子沙漠汗,而诸大人谗杀之,力微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竟至事变而身死,直至章帝悉鹿立后,仍“诸部离叛,国内纷扰”。凡此种种父崩子立之间的国难,(注:《后汉书·鲜卑传》载檀石槐死后,其子和连代立,“众畔者半”;和连死后,兄子魁头立;魁头死,其弟步度根立。同样出现了传子制与国难纷乱相伴并常须借助于兄终弟及来曲折发展的现象。)表明献帝以来,传子制正在冲破传统的推举制,在代表新方向的君长与代表旧势力的部落大人间的激烈斗争中浴血前进,这就是当时拓跋君位传承制度演进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