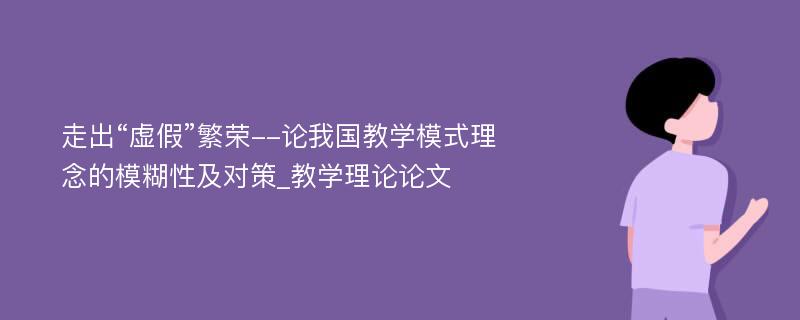
走出“假性”繁荣——浅论我国教学模式理念的模糊性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模式论文,对策论文,繁荣论文,性及论文,模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3)02-0054-04
一、我国教学模式理念的“模糊性”浅析
教学模式的产生,不外乎归纳和演绎这两种主要方式。演绎式是指建构者从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出发提出假设,设计出模式(即把假说转化成教学活动的指南,提出基本的操作策略和程序,以确保假说变成现实,从而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然后在实践中去验证假说,让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并最终确立起来。由归纳式生成的教学模式多半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经验的总结,是教学经验的规范化、理论提升。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建构的教学模式,它都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两面性,或者说教学模式是理论和实践的中介物。教学模式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中介物,首先,在理论层面,它理应是一个相对明晰的概念,并具相应的教学模式理论系统,用以反思旧模式,建构新模式;其次,在实践层面,教学模式应具有较为成熟的建构机制和推广机制,使得教学模式能真正为我国教育事业服务,从而为广大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所喜闻乐见。但是理想和现实并不一致。
1.理论层面:概念理解莫衷一是
“199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还没有收入‘教学模式’这个词条。这说明,‘教学模式’于此之前在我国还没有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为人们所认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教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问题,对教学模式的研究开始成为国内教学论研究的一个‘热点’。”[1]
“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模式,是1924年语文学家黎锦熙在《新著国文教学法》中首次提出的‘三段六步’(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呈开放姿态,模式五花八门,诸如发现式、问题式、三主式、自学式、领悟式,还有五步读法、三段训练法等等……”[2]
比较阅读以上的两段引文,我们不难发现,引文一是试图揭示教学模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国教学论中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从中我们得知,我国有意识的教学模式研究仅有短暂的历史;引文二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在我国的教学实践中,教学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短暂的理论史”与“悠久的实践史”,这构成了一种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教学模式理念的模糊性也源于此。
其一,由于教学模式理论尚处于建设阶段,因此,教学模式概念本身的内涵也还是一个研究课题,至目前为止,有相当多的人曾致力教学模式概念内涵的梳理和界定工作。正如前面的引文一所说,我国有意识的教学模式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这种研究是从学习国外的教学模式理论入手的。国外经典的教学模式理论当数美国著名的师范教育专家乔以斯和韦尔奠定下的教学模式理论。他们在代表作《教学模式》一书中给“教学模式”下的定义是:教学模式是一种可以用来设置课程(诸学科的长期教程)、设计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或其它场合的教学的计划或类型。[3]如今,这一西方的教学模式概念已为我国广大教学模式研究者所熟悉,并逐渐被归结为是“计划说”。在反思和借鉴“计划说”的基础上,我国理论界又出现了“结构说”和“程序说”。前者如“一定的教学思想或理论指导下为设计和组织教学而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它以简化的形式表达出来。”[4]后者如“教学过程的模式,简称教学模式。它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指导下,为完成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对构成教学的诸要素所设计的比较稳定的简化组合方式及其活动程序。”[5]当然,关于教学模式还有很多种说法。有研究者对类似的这些概念做了比较后得出:“国内学者的观点尽管角度不同,说法各异,但从教学模式归属角度看,不外乎以下六个方面,即教学理论、教学结构、教学设计、教学程序、教学范型、教学策略或方法等”。[1]显然,只要我国理论界还未出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教学模式定义,那么,关于教学模式概念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其二,由于我国教学模式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发展不同步,要建设教学模式理论就要梳理教学模式的实践史,所谓梳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给那些“可以”但尚未被冠以教学模式之名的教学经验冠以教学模式之名。那么,究竟在何种条件下特定的教学经验可以被冠以教学模式之名,或者说追加教学模式之名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正是因为教学模式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同的人就会以自己预设的教学模式概念去给他认为是教学模式的教学经验冠以教学模式之名。于是,教学模式实践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以及走过了怎样的一条道路这一问题就如同教学模式概念本身一样具有模糊性,在教学模式概念内涵还没有得到统一之前,对教学模式实践史的不懈的考察,会在无形中加剧教学模式概念的模糊性。
其三,在教学模式理论的建设期,对教学模式有着不同理解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不会停止以自己的标准去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教学模式,于是,这又在无形中加剧了教学模式概念的模糊性。在各类教育教学著作或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兴的“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各学科教学中发展起来的教学模式,譬如“小学语文整体性导读教学模式”、“指导、批改、讲评三步阶梯式教学模式”、“高中政治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有那么多“教学模式”诞生,说明了有很多人正致力于教学模式研究。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所潜在的隐患。仔细分析一下以上所列举的和我们平常看到过的教学模式,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大量所谓的“教学模式”都只是一种纯粹的教学程序或结构的描摹,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模式建构者对“教学模式”理解的简单化。一旦这些教学模式打出旗号,就有着传播和推广的可能,无论它们是否具有在实践中得到推广的潜力,它们所蕴含的教学模式理念却给他人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对“教学模式”的理解也许就是从这形形色色的具体的“教学模式”开始的。于是我们可以说,“想当然”的教学模式建构加剧了教学模式概念的不确定性。
2.实践层面:实施取向无所适从
除了我们上文中所分析的教学模式概念的不确定之外,我们还将看到由此而导致的教学模式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这从以下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来:[2]
“我以为语文教学无模式,也不应该有模式。教学内容是动态的,学生也一直在换,教师自己本身也在发展,所以很难用一种模式去套教学,一个教师不可能自始至终用一种模式去施教”。
“教学模式,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有一个好的教学模式,对一个学校,对一个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教育教学工作有一个预期目标,有一个衡量评比的体系,这比随意性的教学肯定要好”。
“模式是稳定结构,还是牢房”。
“要不要模式是一个悬念”。
“模式又是一柄‘双刃剑’,有经验的教师有模式意识,可能会使他的教学更快地走向成熟,但一旦津津乐道于所谓‘模式’,又可能是固步自封的开始。”
以上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一线教师和基层研究人员。简单归结一下,从中反映了人们看待教学模式的三种基本态度:支持、反对和中立。显然,这些态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源于不同主体对教学模式实施效果的考察和理解。而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又取决于人们在实施教学模式时所采取的基本取向:如果将教学模式作为一个“稳定结构”,一味地照搬,该教学模式就难免会沦落为“牢房”而遭人排斥;如果将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教学理念的载体或一种教学经验的升华而汲取其精华,该教学模式自然能够帮助广大教师改善和丰富教学,从而受到教师的青睐。由此,教学模式可能是个“功臣”,也可能成为“罪魁祸首”。就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人们兴建教学模式、评析教学模式的兴趣远远大于研究如何学习模式、实施模式的兴趣,这使得在众多学习借鉴教学模式的个案中,教学模式的不当使用要远远多于教学模式的恰当使用。于是教学模式就渐渐给人一种看起来很好用起来效果了了的感觉。这样一种氛围又会让那些尚未涉足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教师心生疑虑,无所适从。
教学模式实践层面上实施效果的参差不齐、实施取向的无所适从,首先是由于对教学模式缺乏理性统一的认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教学模式‘何许物也’尚且朦胧的窘境,不仅有碍教学模式在教学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而且会使人们失去对它应有的期待。”[7]教学模式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及人们对其褒贬不一的状况颇有“争鸣”的味道。很多时候,“百家争鸣”是繁荣的标志,我国教学模式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是否也是我国教学模式理论的福音呢?我们要不无遗憾地说,至少就目前来看,是弊大于利,是教学模式研究滞后的表现。
二、我国教学模式理念的“统一”化设想
乔以斯和韦尔的《教学模式》一书自1972年出版至今,一版再版,最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6版。在惊叹该书本身的畅销性之余,我们还应看到西方学者在教学模式研究中的孜孜以求。相比之下,我国教学模式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为了使我国教学模式能够真正发挥好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作用。我们得从我国教学模式的“统一”入手。
对于一个单一的是非问题,所谓“统一”认识,多半是以一条标准准确地告诉人们该接受什么和放弃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最为简单的“统一”方式,这种“统一”由于统一对象的平面化而平面化。但对于“教学模式”这类涉及面较广的、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所谓的“统一理念”就很难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而是需要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一系列筛选、整合和发展工作。在此,让我们以一种立体化的统一思路来为我国教学模式理念的“统一”勾勒一幅蓝图,由宏观至微观,设计这样三个层面:教学模式的价值和地位、教学模式的内涵和外延、教学模式的实施取向。
1.教学模式的地位和价值
在当前追求个性化与创新的时代,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模式”这样的字眼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另一方面,各类“教学模式”又层出不穷。前者是将“模式”这一原本中性的术语与“模式化”、“机械化”这些不良倾向联系在了一起,导致“教学模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者则简单地将树立“新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途径,功利色彩浓郁,导致“教学模式”泛滥。显然,出现这样两种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教学模式”的地位与价值。“统一”我国教学模式理念,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教学模式“连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服务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价值与地位,并以此作为教学模式建构、研究的终极取向。当教学模式得到恰如其分的定位后,任何关于教学模式存在价值的质疑、纷争就将尘埃落定,而我们也就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更具有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的问题上去。
2.教学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才能真正实现“连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服务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目标呢?这就涉及到了统一教学模式理念过程中最关键、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明确教学模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教学模式概念内涵的纷争,上文已述及,在此,根据教学模式的终极取向,对教学模式的内涵作如下归纳式的描述:其一,教学模式蕴含着特定的教学思想;其二,教学模式提供参考性的教学活动结构或教学程序;其三,特定的教学模式需要具有与其相匹配的基本教学策略或方法。
也许,这样一种界定看来有些眼熟,确实,在这里,我们无意去揭示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定义。因为以往我们所缺少的只是系统的、动态的眼光。当我们忽略“教学思想”的统帅作用时,教学模式就显得单薄、空洞,容易被机械模仿、照搬,最终在实践中窒息;当我们忽略教学模式对“教学结构”和“教学程序”的展示时,教学模式就缺少了简约性、可操作性;当我们忽视了特定教学模式对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的要求时,教学模式就难以化为师生的学习行动,难以从细微处渗透教学模式中所蕴含的教学思想。鉴于以往教学模式理解中的顾此失彼,我们在这里为教学模式作了一个归纳式定义。当然,这种归纳不是简单的粘贴,而是对教学模式不同层面上的关键因素的一个整合。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定义的合法性,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两个好处:其一,当我们着眼于教学模式三因素的整合性时,我们就能凭借由这三个因素组成的大筛子,有的放矢地勾勒教学模式的外延,将那些“残缺”的“教学模式”请回教学经验范畴中去;其二,当我们着眼于每一种因素的个性时,我们就能区分教学模式间的差异性和层次性,不同的教学思想区分出了一级教学模式,同一种教学思想下区分出不同的实施方式,即不同的教学结构、教学程序、教学策略,区分出了二级教学模式或者说是某一教学模式的变式,就目前许多学科教学模式而言,大都是这类二级教学模式。当一种教学模式界定能够利于勾勒教学模式的外延,区分教学模式的种类、层次,使教学模式群井然有序时,我们就能说教学模式理念统一工程已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
3.教学模式的实施取向
无论是从教学经验中提升、归纳而成,还是从教学理论演绎而成,教学模式一旦成型,就意味着它将开始另一段生命史,那就是到更为广阔的教学实践中去发挥作用并从中得到发展。但很多人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却走入了误区:一味地模仿教学模式的原型,或者,在无法探寻教学模式原型时就紧紧抓住模式所提供的教学程序、操作步骤不放。模仿教学模式原型容易被一些教学模式之外的东西牵着走:如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氛围等。但教学风格、教学氛围是内在生成的,它们难以模仿,当模仿失败时,人们就会片面地将责任归结为是教学模式的质量问题,质疑教学模式的存在价值。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一开始就是实施者本身的错,他们想的是实施教学模式,真正实施的却是教学模式之外的东西。紧扣教学模式的教学结构、教学程序,似乎要比模仿教学模式原型贴近主题些了,但问题仍然存在。因为特定的教学模式展示的教学程序、教学结构都是为了实现其教学思想服务的,都是特定教学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如果忽视教学模式蕴含的教学思想而只看到教学程序或教学结构,那么同样会使教学模式实施逐渐失去生命力。行文至此,教学模式合理的取向也就逐渐清晰起来:学习教学模式的核心思想,借鉴教学模式的教学结构、教学程序、教学策略,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中灵活地开展教学。
当人们对教学模式的价值和地位、内涵和外延以及实施取向的认识保持一致的时候,人们对教学模式所做的努力就会形成一股合力,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就能走出假性繁荣,走向真正的繁荣。教学模式也就真正能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间架起一座有益的桥梁。但就目前来看,我国教学模式理念尚较为混乱,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原本文所做的探讨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
标签:教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