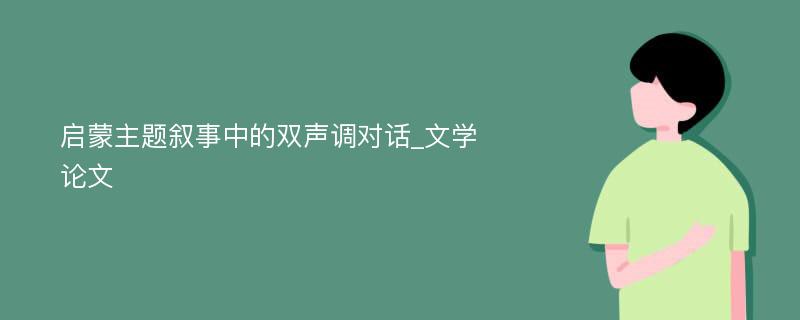
启蒙母题叙事的双声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3-0032-05
一 启蒙话语与马桥话语的碰撞
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条时隐时显、时起时伏的思想线索,这就是批判国民性,改造国民的灵魂,这一思想线索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文学母题。从世纪初年梁启超号召以新小说来新民新道德新风尚开始,直到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启蒙文学曾经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几度浮沉。李泽厚曾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一个当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命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把启蒙主题的几度浮沉的原因归之为20世纪民族救亡形势的挤压,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不过,我认为从形式上来看,启蒙乃是一种话语运动。启蒙者通过话语的力量向被启蒙者宣什么是理想的人生,你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合理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合理的制度。既然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话语的关系,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母题的浮沉更为深刻的原因就应该从启蒙话语自身的演变过程与具体情景中去分析。
中国20世纪的启蒙话语其演变过程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情景中呢?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将中国20世纪启蒙文学同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作过如下比较:第一,西方启蒙运动中张扬的理性是建立在几百年来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其启蒙所用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无不深深植根于科学的进步中,有的被科学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所论证,但中国自中世纪以来科技一直停滞不前,而封建理学道统却非常发达,理学不是理性,却披着理性的外衣成为封建礼教的宣道者。所以,20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不得不从西方寻找一种价值体系与理性话语来否定本土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理学话语。第二,西方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神学渊源,中国没有真正的本土宗教,中国的哲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同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国民虽然不愿意独立思考,却也具有一种不愿为某种信念哪怕是愚昧的信念而献身的世俗聪明。20世纪中国的启蒙者在攻击某种旧的观念时,所面对的往往是空虚的“无物之阵”。第三,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作为力量支柱,而中国的启蒙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启蒙者唯一可以自信的是自己掌握着先进的思想观念,因而也是掌握着话语的力量。[1]这些差异给中国20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不得不从西方寻找启蒙的话语方式与价值体系,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却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危险,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向国民宣传真理,而国民或者漠然无语,或者将启蒙者献出的鲜血去做人血馒头治痨病。这种理智与情感、愿望与效果、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悖违,使得中国20世纪启蒙文学的深度居然表现在建构启蒙与消解启蒙的双声对话中。(注:五四初期的“问题小说”之所以缺乏深度,就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双声对话的复义结构,只有启蒙的言说,没有对启蒙自身的拷问。)这种双声对话在鲁迅的小说中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意义张力,在现代启蒙主义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就为“狂”人设计了两种生命状态,狂态言说着启蒙话语,常态则意味着启蒙的失败。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的口对启蒙主义的许诺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而在《伤逝》中,子君这一启蒙主义的成果却像“铁屋子”里几个被叫醒的人那样,在意识到“就死的悲哀”中走向死亡。“一方面,鲁迅不断地拷问启蒙本身,对启蒙的意义、力量、结果与成效表示深深的怀疑,一方面,鲁迅又不断地表示自己这一代人应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他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长途跋涉的过客,始终聆听前面的神秘呼唤,即使前面是坟,也永不停顿。这正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对自我使命的深刻领悟。”[1]
《马桥词典》也具有这种双声对话的复义结构。很可惜的是,有些评论家见到的是它的启蒙性,有的评论家见到的是它对启蒙的消解性,那些固执于意识形态评论的批评者很难想象这二者居然会在一个作品中同时呈现。殊不知这正是20世纪那些有深度、有独立见解的启蒙主义文学家们无可回避的历史尴尬。在《马桥词典》中,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的继承是很明显的,这种启蒙传统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前面已经论及的对国民集体无意识的揭示与批判,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而且也表现在作者对下层民众生存苦难的关注。在“汉奸”一条中,作者用盐早一家的遭遇控诉了极左政治对基本人性的压抑与扼杀,在“小哥”一条中作者分析了马桥的女人无名化现象,显示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时尚的结合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剥夺,在“宝气”一条中,作者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欺软怕硬的德性,在“亏元”一条中,我们也看到了新时期农村中的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对穷人的欺压。诸如此类的词条都显示出作者对强势者的愤怒,对弱小者的同情,对人间苦难的一种悲悯。在《马桥词典》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启蒙作家经常使用的人道主义补偿模式。当年,郁达夫曾悲愤于一个人力车夫奋斗半生竟连买一辆车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让小说中的“我”在人力车夫的坟前烧上一辆纸车作为同情者的薄奠。《马桥词典》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兆青的多子与生计艰难,大概不亚于鲁迅笔下的闰土,他有一句名言,“我们这号人,赚不了别人的钱,自己的钱还是可以赚的。”为了节省,他在外面出工宁愿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其自苦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兆青不明不白死在一条小溪边,入殓时,“我抱了一床旧棉毯送到他家里,嘱他婆娘垫入兆青的棺木。他一生都习惯睡在扁担上,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睡一觉了。他一生忙忙碌碌,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懈一懈。”(“懈”)死者长已矣,而又有几个活着的人会为这样一个蝼蚁般微不足道的生命的凋谢长相欷嘘呢?作者虽然没有像郁达夫那样义愤填膺地去诅咒来来往往的富裕者,但他的同情是真挚的,感人肺腑的,显示着一个当代启蒙者同情弱小怜悯贫苦的最为可贵的情感倾向。
在解构启蒙话语方面,鲁迅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情节,这就是《祝福》中祥林嫂关于是否有地狱有灵魂的发问。我在《鲁迅小说启蒙主题新论》一文中对这一情节设计的深刻意义曾作过分析,我认为这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一场对话,‘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这正是启蒙者的典型特征:具有一种话语的力量。但是祥林嫂不问生只问死(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生的条件与兴趣),启蒙者所具有的话语力量立刻就显露出了尴尬与困窘。‘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启蒙者对自己掌握的话语力量的深刻反思。确实,如果自以为掌握了话语力量的启蒙主义连启蒙对象一个属于话语范畴的问题也回答不了,它又怎么能够担负起改变启蒙对象生存现实的重任呢?”[1]对启蒙话语力量的怀疑与困窘,在《马桥词典》中也是或明或隐地存在着。在《栀子花,茉莉花》词条中,作者用仲琪死后马桥人对他评价的模棱两可来揭示马桥语言的含糊其词:“仲琪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点,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但作者对他的分析无疑是明确的,而且带有一种深厚的同情:“其实,他一生中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在这里,马桥人的语言是非逻辑的,他们不习惯非此即彼的原则,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词就是他们的准确。而作者的语言显然是启蒙式的,他要用非此即彼的言说方式分辨出马仲琪死的意义所在。这两种语言发生碰撞以后,一种鲁迅式的尴尬与迷惑也同样出现在韩少功的启蒙言说中:“那么他该怎么办?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栀子花,茉莉花”,这是马桥的话语状态。上引的一段话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启蒙话语与马桥话语发生碰撞,启蒙话语无可奈何地露出它的尴尬与迷惑时,韩少功选择的应对策略是以认同马桥话语的方式来解构启蒙话语。小说中的我到马轿插队,经常要纠正马桥人的一些“不科学”的说法,比如说把所有的糖、饼干等都叫作“糖”,把广场叫做“晒坪”等等,但“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马桥的词语,如人死了,马桥人不叫死而叫“散发”。这个词虽然不“科学”,不规范,但它却有内蕴。作者对这个词的意蕴作了非常诗意化的解释:任何关于死的说法,“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浮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也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变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的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七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对于马桥语言的魔力也颇为信服,马桥人有“晕街”一词,这个词语竟造成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的远避。从这个词的功效中,韩少功深深感觉到“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马桥人还有一种“嘴煞”的说法,所谓“嘴煞”是指的语言上的忌讳,对此,韩少功也深有感慨地表示理解,他说:“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藉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指出和分析了科学主义的缺憾与力所难及之处,这一点我将在下一节中再详细讨论。
从《马桥词典》写作的基本观念来看,语言状态就是生存状态的一种标志,一种表象。对马桥言语状态的理解与认同,本身就意味着对马桥生存状态的理解与认同。所以,韩少功才会用充满善意的笔触写到本义对城市生活的拒绝,用满怀敬意的笔触去写复查在一句无意说出的嘴煞之后,陷入到沉重的罪恶感中终生未能解脱的事件。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启蒙主义小说中,启蒙对象的语言状态往往是被启蒙者所忽略的,因为启蒙对象的语言状态就是沉默,无边的沉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无物之阵,启蒙之声投入这一无物之阵中,就象雪花飘落在平静而渊深的海面上,立即消失于无形无影。鲁迅之所以解构启蒙,是因为激愤于启蒙对象的冷漠,激民于无物之阵的巨大的吞噬力,对鲁迅而言,启蒙乃是一种绝望的抗战,在绝望之中战斗不止,本身就是对绝望的反抗。因此,鲁迅不太关启蒙对象的话语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绝望的反抗方式。在这种意义上,《马桥词典》对启蒙对象的话语状态的关注与理解,显示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母题叙事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其促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主要的一种原因是两个时代启蒙者所具有的理论背景是大不一样的。在五四时代,启蒙作者信奉的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人们真诚地相信西方的价值观念是拯救中国的真理,而在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已经在中国的思想论界成了流行话语,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消解西方文化中心观念,主张文化模式的相对发展论,对西方文化以强势话语的形态压抑第三世界弱势话语,使第三世界文化沦入边缘状态这一世界性文化趋势保持强烈的警惕。所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本土文化多采取一种宽容、理解或认同的态度,承认每一种文化无论其相对与西方文化是多么落后,它都有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理由与权利。显然,《马桥词典》中启蒙主题的双声对话,一种声音来之于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另一种声音则是来之于90年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启示。
二 祛魅与含魅的叙事逆向
90年代的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现象,这就是小说叙事中的含魅性。这种含魅叙事在80年代后期的寻根文学中已初露端倪,90年代以来形成一种引人瞩目的叙事倾向。韩少功乃是这种叙事倾向的始作踊者,80年代问世的《归去来》、《爸爸爸》等作品已经开始超越现实主义的叙事规范,作品中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些唯物主义不能解释明白的信息,而《马桥词典》的出版,则说明韩少功对世界的含魅性已经形成了自觉的观念。宽泛地说来,含魅叙事在文学中的经常出现,可以算是巫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映。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巫与鬼总是相提并论的。不过,从巫风与文学的关系上来看,巫与鬼无疑是有所区别的。巫作为人与神沟通的桥梁,它的功能是直接指向神的,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说,楚人“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虽然后世巫也曾沦落为一种打鬼驱魅的低级术士,但巫的本意应该是神的使者。而鬼怪在原始思维中乃是比人更低一级的有灵物体,鬼是死去的人的精灵,怪是动植物的精灵,鬼与怪都是原始思维中万物有灵观念的虚幻构想。从原始人类直到宗教产生的文明社会,人与神的关系是倾听与被倾听,人为了提升自己的品质,愿意倾听神的声音。相反,人与鬼怪的关系是回避与禁忌的关系。如果说人与神的关系反映的是人对一种律令、法则与境界的崇拜与敬畏,那么人与鬼怪的关系则反映了人对一些自己不能具体把握、也无法用语言言说清楚的事物的畏惧与疑虑。这两种关系所滋生的感觉是有本质性差异的,它们给文学带来的是不同的意义深度。从《马桥词典》叙述的具体事件来看,作品表现出来的含魅性主要是后一种关系。
如果说含魅与祛魅这是几百年来以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从中世纪走出之后所面临的一个互存互动的悖反问题,那么,就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整个世纪的中心主题则是祛魅。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在20世纪所进行的中心工作乃是说明世界,揭示世界,在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人们建构起了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乌托邦,乐观地相信人的认知能力无所不及,无所不能。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科技文明来扫荡封建迷信,引进西方的人文思想来开启国人的意识蒙昧,引进西方文化的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来救治国家的空灵与玄虚,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界在认知世界方面的祛魅努力。韩少功作为70年代末通过高考第一批进入大学学习的作家,无疑是在其精神结构中深受启蒙理性浸润的。但是,到了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为什么韩少功的创作却会出现一种与20世纪中心主题反向运动的含魅趋势?我认为,其动因大致有二:一是湖南文学的巫诗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使湖南作家在个人气质上容易进入穿越时空、等齐生死、泯灭物我的思维状态,因而在题材的取舍、情节的构设等方面就不免对与这种思维状态很吻合的鬼怪精灵产生浓厚兴趣。二是时代精神的反拨所致,如前所言,时代的主流精神是祛魅,但是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祛魅精神是越来越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得世界祛魅的启蒙工作隐伏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在世界日益明晰化的同时,世界的丰富性也在被简约,世界日益被认知,但世界的意义维度却越来越狭窄。正是在这样一种悖论的启示下,如韩少功一类的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就容易对时代的祛魅主题产生怀疑,并且在对含魅事物的描写上由昔日严峻的启蒙话语走向宽容的多元话语。
在这种叙事转向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最为典型也最有深度的一例。从80年代初以《西望茅草地》、《风吹锁呐声》、《飞过蓝天》等作品蜚声文坛开始,韩少功以鲜明而强烈的理性批判的姿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早期作品侧重于政治层面上的拨乱反正,并对政治的罪恶进行人性深度的解剖,80年代中期《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揭起寻根的大旗后,韩少功个性气质上的“楚人血液”突然获得激活与复苏,楚巫文化的诗性思维方式有了突出的呈现。虽然这些作品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对国民劣根性的发掘与批判,显示着启蒙精神的绵延不绝,如丙崽的“爸爸爸”与“X妈妈”已经成为国人二极对立思维方式的一个经典的象征,幺姑的由人到物的退化也在给古老而僵化了的民族敲响着余音悠长的警钟。但是,丙崽的复活,幺姑的退化,显然已经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见到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些被虚空化了的形式,内容可以任读者去填充。读者的填充必定是歧义的,模糊的,这无疑与要求清晰明确地说明世界解答问题的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到《马桥词典》出版,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又一次实现了对自己的突破。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部奇特的小说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韩少功对意义深度的追求,但这部小说的意义深度是一个互相渗织的多重结构。最表层的意义维度上,是对文革时代的愚昧行为与文革话语的一般性批判,第二个层次是发现与挖掘马桥人愚昧行为与流行话语背后或深层结构中所显示出的国民无意识,第三个意义层次则进入到了对人之命运的不可知性与自然中神秘力量的敬畏与恐惧。总体看来,这三个意义层次联系着两个相互运动的基本意向:一是祛魅,用科学与理性揭示马桥人言语中的思维习惯与含蕴,揭示语言生存的黑暗与无明状态,二是含魅,在话语形式中对世界中那些不可知或不可言说的事物表示宽容、包含,或保持沉默。对韩少功而言,真正的自我突破无疑是后者,可以说,正是《马桥词典》含魅意向的存在,使得20世纪小说的启蒙主义话语真正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危机。
在《马桥词典》中,含魅意向的形成主要来之于两个方面,一是用语言将本来在科学中已有定义或定论的事物神秘化,《根》一词条中写到铁香最后抛弃当支部书记的本义跟“太不体面”的三耳朵私奔,这一故事当然可以运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来解释,铁香喜欢经常殴打她的三耳朵是一种女性受虐倾向的表现,但《马桥词典》用“根”一词将这一故事神秘化,铁香的父亲是个乞丐头子,有一个过路老人曾看过铁香的手心,说她的“门槛根”还没有断,铁香现在是书记的婆娘,日子过得正红火,她当然不会相信自己还会去讨饭。“她没有料到,自己多年后的结局,居然应验了过路老人的话:她跟随了三耳朵,一个穷得差不多只能挨门槛的男人,在遥远他乡流落终身。她像一棵树,拼命向上寻找阳光和雨水,寻找了三十多年,最终发现自己的枝叶无论如何病长,也没法离根而去,没法飞向高空”。铁香出人意料的行为最终是与那个神秘的无从解释的“劫数”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作为马桥中心的两棵枫树,关于它们有许多传说,如马鸣曾经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以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枫树最终被公社砍走打排椅,结果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搔痒症等等。这些传说似乎都可以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马鸣手痛也许是因为作画时间太长,过度疲劳所致,搔痒症也许是因为枫树的木脂中有一种让人皮肤过敏的物质,而枫树用作公社礼堂的排椅则完全有可能使这种皮肤过敏症流传开去。但是作者对这样一些传说的处理明显具有含魅的意味,所以作者说:“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经过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块石子,不会太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马桥词典》含魅意向形成的另一种来源是对日常生活中某些无从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做原生态式的叙述。这类事件的叙述在作品中是很多的,如《梦婆》词条写水水因儿子被炸死变成梦婆(精神病人)后,为人猜彩票中奖号码,几乎是屡试屡中,名噪方圆几百里。《晕街》词条写语言的魔力,当你用语言假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果然就会发生。《嘴煞》词条写复查因向罗伯借钱无着一时不忍骂了一句“翻脚板的”,第二天罗伯果然被疯狗咬死。《走鬼亲》是最典型的一个词条,它写铁香死后投胎转世为金福酒店的黑丹子,她居然认出了来到此地打工的儿子,此事流传开去后,几个干部押着她来到马桥检测她是否装神弄鬼,小说写道:“黑丹子一走进本义的家,就神了,不仅熟门熟路,晓得吊壶、尿桶、米柜各自的位置,而且一眼就认出了半躺在床上的老人就是本义。”更令人吃惊的是,她居然还叫出了一个连现在的马桥人都很陌生的人名字。上述一类事件在小说作品中出现也许是不足为奇的,小说作为虚构性创作它有权利表现鬼魅主题。我们在此最关注的是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视点与看法,从《马桥词典》的整体倾向来看,作者对这些词条的考稽,显然是对20世纪启蒙思想体系中的科学主义的置疑。在《嘴煞》词条中,韩少功对科学主义作了如下的描述:“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个常人了”,“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怪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在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之间,《马桥词典》没有也不愿做出明白的选择。作者在《肯》词条中剖析了自己在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之间的二难:“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与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与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无疑,正是这种两难使得《马桥词典》在启蒙话语与马桥话语的双声对话之外,形成了另一种双声对话的意义结构,一种是科学主义的祛魅意向,一种是信仰主义的含魅意向,而后者由于其标志着韩少功创作启蒙主义话语模式向多元的人文主义话语模式的转变,因而尤其引人瞩目。
1999年,我在一篇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神秘主义倾向发展问题的文章中曾作过如下的总结:“可以说,到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才真正具备了思潮的形态与能量,这不仅是因为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涉足的作家也越来越广泛,而且是因为90年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已经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念基础。这种世纪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对自然之力的敬畏。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它是人与大地之联系的重新修复。从文学的意义上看,它是对建立在传统认识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的超越,是对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传统历史构架的消解,也是文学自身摆脱浅薄与透明的人生乐观主义的一种努力。”[2]90年代小说的含魅叙事是中国文学的神秘主义形成思潮的主要力量,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无疑也应作如是观。但是,评论界对《马桥词典》中的含魅叙事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持一种批评态度。如邓晓芒说韩少功已经“浸透了道家精神”,虽然能够看出马桥文化的模糊、混沌、退缩与压抑生命的本质,却没有力量否定这个文化去创造新的语言。“只能以一种陈旧、古老、模糊不定、发育不良的语言冒充那使人的生存得以明确表达的自由语言,为‘言不言’、‘才说一物便不是’的马桥智慧编写一部落笔即已作废的《马桥词典》。”[3](P100)“使人的生存得以明确表达,”这是典型的启蒙主义要求,执著于启蒙主义的要求来看《马桥词典》的意义,这当然是评论家的权利,但这种阅读也势必缩减《马桥词典》所具有的丰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会遮蔽人们对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认识。这恰恰是我们在研究《马桥词典》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母题之间的联系时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收稿日期:2001-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