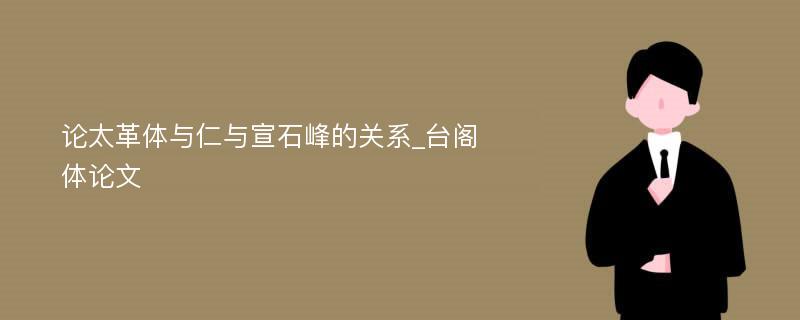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阁论文,风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2)02-089-05
在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批评史的研究中,只要论及明代,几乎没有人不提到“三杨”与“台阁体”的,但由于它作为官方文学的代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从而难以对其作出稍微深入一点的论述,往往用“歌功颂德,形式工稳”八个字将其一笔带过。但是,作为明代文学思想上重要一环的台阁体,在明代前期的几十年中曾牢牢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如果对它不作出具体深入的研究,则无论是对明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对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的认识,都将是极为不利的,因而本文便着重对台阁体诗文风格其与当时士风的关系作出具体的探讨,以期达到求真求实的研究目的。
就现存资料看,最早对台阁体作出概括的是宣德进士李贤,他在序杨溥文集时说:“观其所为文章,辞惟达意而不以富丽为工,意惟主理而不以新奇为尚,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赘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荒论,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严重老成之规模,真所谓台阁之气象也。”(注:《明名臣琬琰录后集》卷一。)从内容讲,为道与用;从风格讲,为温柔敦厚。应该说李贤的概括是颇为准确的,只是尚未与当时士风相联系。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为杨荣文集所作提要中则补充了李贤的不足,其曰:“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问,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别集类二三。)此处所言正是士人遭遇与其诗文体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讲也就是士人由其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性情心态如何造就了他们的文学风格的问题。应该说无论是李贤还是四库馆臣,他们对此一关系的感受都是既深刻又具体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士人心态的研究是至关紧要的,因为既然台阁体是当时士人“情动而辞发”的结果,那今天便可以通过“批文以入情”的手段,去探讨并描述出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来。
但是,在论述此一问题之前,还有一点尚须作出更具体的界定,即台阁体的流行时间问题。时下学者一般均笼统指称是明前期,但严格地讲它既不在洪武甚至亦不在永乐时期,而是在仁宗、宣宗及英宗前期的近二十年时间广为流行,高潮乃在宣宗一朝,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则是其余响。因为洪武时的高压政治只能令士人战战兢兢从而导致哀叹感伤的情调,永乐一朝虽可视为台阁体的发端期,却大多是半真半假的谀词。而在英宗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弱与朝政的混乱,就再也不可能具有台阁体那种雍容平和的气度了。台阁体的产生起码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时代环境,二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要达到亲融和谐的状态。而此二种条件惟有仁、宣时期方庶几近之。先看第一点。仁、宣时期可谓士人眼中的“盛世”。因为中国传统的盛世观念有其独特的内涵,它既不看重武力的强大,也不看重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更被视为舍本逐末的颓世衰风,圣人不是说过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注:《论语·季氏》。)所以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天下统一而百姓安乐,知礼不争而盗贼匿迹,即所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死于沟壑,其要旨则在于稳定和谐,这在《礼记·礼运》里讲的很清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注:《十三经注疏》卷二十一。)仁、宣士人感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似乎已接近此大同盛世,如杨士奇说:“今圣天子在位,诞敷恩德,以洽于万方。登贤拔材,咸列有位。贷逋赋,宥过眚,百政修举,乖歎和顺,万物条畅,岛夷洞獠,悉驯悉归。斯非所谓平庸之世者乎?故贵者遂乐于上,贱者遂乐于下。士农工商,无小大富贵,各以类而乐于其所。”(注:《东里续集》卷五《东山燕游诗序》。)窥诸历史现实,士奇的话并非毫无所据。明王朝至仁、宣时,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苦心经营,政治基本趋于稳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较之元末战乱时有较大恢复,各方矛盾亦暂趋缓和,整个王朝进入和谐有序状态,尤其是在宣宗时更为典型,史载:“当是史,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注:《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由是,士人们普遍地拥有了和乐的心态,杨荣有《行乐图自赞》曰:“澹然以居,恬然自适。当玉署之燕闲,正金銮之退直。光风霁月,慕前哲之襟怀;翠竹碧梧,仰昔是贤之标格。惟意态之雍荣,乃斯图之仿佛。至于策励驽钝勤劳夙夜,以感圣主之恩遇,乐盛世之治平者,抑岂丹青之所能窥测哉!”(注:《文敏集》卷十六。)此种“澹然”“恬然”的自适不是逃避社会而归依山林的隐士心态,而是志得意适的一种政治满足感。因为雍容典雅的诗风只能是关注社会的外向性心态的反映,而隐士的心态一般是封闭狭小的。
再看第二点。尽管士人的和乐心态与当时国家太平、政治清明的氛围有密切联系,但对此依然应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此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身居庙堂的台阁体作家对现实真实状况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在他们的诗文中,所表现的生活面相当狭窄,即使有几首写到农村场面的诗,如“桃蹊深浅红相间;麦垅高低绿渐肥。”(注:杨士奇《归至清河》,见《东里续集》卷五十九。)“茶输官课秋前足,稻种山田火后肥。”(注:杨溥《送归州太守复任》,见《明诗纪事》乙签卷四。)均为浮光掠影的远距离扫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以肯定,当时的大明帝国决不会和谐美妙到如台阁体作家所描写的那般地步,因而太平和乐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士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觉。此种感觉自然有其产生的基础,那就是士人在帝国中所处位置的变化,或者说是皇帝与文官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与洪武、永乐年间相比,在仁、宣二朝中士人与帝王间的亲和力大大加强,从而达到一种虽则短暂却颇为和谐融洽的程度,换言之即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达成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此种融洽平衡乃是由下述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一)从双方关系讲,他们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共同的情志兴趣,容易保持融洽和谐。仁宗与宣宗在潜邸时即长期受教于文官,从而结下较深的感情,一旦龙飞于天势必会尊重信任之,象三杨、金幼孜、蹇义、夏原吉诸人,在仁宗一系与高煦争夺皇位继承权中均曾出过大力,许多人还为此获罪于成祖而身陷囹圄,所以这群顾命大臣后来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新皇上的报答。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相处中他们形成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也为后来的君臣相处提供了有利的沟通条件。明末的钱谦益即充分注意到了此一点,他记仁宗曰:“仁宗在东宫久,圣学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乙夜繙阅,每至达旦。杨士奇,欧之乡人,熟于欧文,帝以此深契之。”(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上。)同时钱氏又记宣宗曰:“帝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篇短歌,援笔力就。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万机之瑕,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非但好文,而且在所好对象与传统继承上,均情投志合,由此也就明白了何以会形成台阁体文风的原因。而此种从政治利益到个人情趣的一致,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融洽。
(二)从帝王一方讲,亦须依靠并信任文官。因为仁宗、宣宗等守成之君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已不再具有祖宗开国的气度与才能,倘若失去文官的支持拥戴则将一筹莫展。三杨等人都曾是辅佐四朝的老臣,而且均多次提出过致仕的请求,朝廷的一再执意挽留固然说明了对他们的深厚情感,同时也显示出对他们的依赖之深。而要有效地依赖他们,就必须满足其各种人生的需求。这除了尽量提高其官位外,同时还使三杨等重臣身兼数职,目的显系令其支取更为丰厚的官禄。当然,日常的各种赏赐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有物质上的补偿意义,还显示了情感上的关怀。如正统四年杨士奇归乡省墓时,英宗特意“命兵部缘途给行廪,水路给驿船递运船,陆路给驿马运载车,从者皆给行粮脚力,往复并给。”(注:《东里续集》卷四十九,《南归纪行录》上。)杨士奇之所以将这些记录下来收进自己的文集中,显然是作为至高的荣耀并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的。不过对于这些儒臣来说,最为看重的还不是物欲的满足,而是对自己一腔忠诚的信任。皇上自然也能洞悉臣子们的衷曲,尽量予以满足。如仁宗登基伊始,便立即将夏原吉、吴中、杨勉、黄淮、杨溥、金幼孜等一帮被成祖下狱的文臣悉数官复原职。而且登基未及一月,便“赐赛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以便其直接对皇上密封言事。一枚图章虽小,却饱含了皇上的信任之意,而这在洪武永乐时则是不可想象的,难怪杨士奇特撰《赐银章记》文以致感激之意,其中曰:“既受赐,时皆以为千载之遭际,希阔之大恩也。”(注:《东里续集》卷五。)然而从历史上看,为臣子者直言敢谏尚不难做到,但做皇上者要容纳逆耳的忠言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打消臣子的顾虑,仁宗曾与杨士奇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上……谓杨士奇曰:‘朕尝处事有过,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惬朕意。’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惟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实有失,亦未尝不悔。’士奇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难于改。’”(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在此杨士奇虽是引用宋人富弼的话来提醒仁宗,不可以一己之喜怒来对待臣下的进言,但实际上是宛转地批评了太祖与成祖,因为早在解缙的奏章里,就已不客气地指出了“天下皆谓陛下(指朱元璋)任喜怒为生杀”(注:《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的事实。士奇的借古喻今可以视为是一种试探,当他得到皇上以道为取舍的承诺时,便立即称之为圣人之举,同时也体会到了皇上的真诚与信任。正是有了这种相互信任,二者的关系方能达到融洽的程度。据史载,宣宗曾“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皆报可。”(注:《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这种荐选官员的方式既充分体现了皇上对臣子的信任,更显示了君臣之间的和谐。
(三)从士人一方讲,则表现出忠于朝廷、勇于任事而又不流于放纵不羁的特性,这也保证了和谐融洽状态的存在。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士人的做人准则。既然皇上表现出对臣子足够的关怀与信任,那么作为臣子就没有理由不对朝廷忠心耿耿。客观地讲,士人们在经过从永乐到宣德的不同体验后,对三位皇上也产生了不同的情感深度,杨士奇如下的两首诗很好地凸显了此种差别:
谒长陵
忆昔六龙升御日,最先呈诏上銮坡。
论思虚薄年华远,霄汉飞腾宠命多。
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
文孙继统今明圣,供奉无能奈老何!
谒献陵
海宇洪熙戴至尊,愚臣殿陛最蒙恩。
常依黼扆承清问,每荷纶音奖直言。
万古兹山藏玉剑,九霄何路从金根。
余生莫罄涓埃报,血泪横膺不忍论。(注:见《东里诗集》卷二。)
面对长眠长陵中的成祖,士奇没有忘记最早被选入内阁的恩遇,故而不禁流下两行清泪。但是当他转而面对献陵中的仁宗时,回忆起他那种种“承清问”、“奖直言”的恩德,真恨不得跟了他去,于是禁不住“血泪横膺”。“清泪”与“血泪”虽仅一字之别,却明显令人感到情感分量的差别。相信具有此种差别的并非只士奇一人,比如他在为杨荣撰写墓志铭时,特意用下述方式开头:“正统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公奉敕归展先墓。既毕事,卜日启行,病作。众曰:‘曷俟少间?’公曰:‘君命不可稽也。’挟医以行。至临安武林驿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日也。”(注:《明名臣琬琰录后集》卷一。)这显然是为突出其忠诚无比的精神。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弋谦言事过激,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仁宗也颇厌烦,虽经杨士奇劝解,但皇上还是不高兴,因而只令其照旧供职,仍不准参加朝见。士奇又进言曰:“陛下有诏求言,今谦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为戒。且四方朝觐之臣咸在,岂能尽知谦过?若传于远人,将谓朝廷不能容直言。”仁宗表示愿意承认过错,并让士奇告谕群臣。不料士奇仍然不依不挠,非要让仁宗下玺书亲自引过认错。皇上最后无奈也只好照办。(注:王直《杨文贞公传》,见《献征录》卷十二。)这在太祖、成祖时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但仁、宣士人的勇于直谏又决不会流于放纵骄横,因为他们在成祖时所过的提心吊胆侍奉惟谨的日子,会长期萦绕在心头,时时提醒他们约束自己,即使遇到某些小的委屈烦恼也能隐忍自控。杨士奇在《题黄少保省愆集后》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此一特征:
读吾友少保公永乐中所作省愆诗集至于一再,盖几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于往事焉。……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礼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志夺嫡者,日夜窥伺间隙,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又结嬖近助于内。赖上圣明,终不为感。然为宫臣者,胥凛凛尯臲,数见颂系,虽四臣不免,或浃旬,或累月,唯淮一滞十年,盖邹孟氏所谓莫之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黄及士奇幸尚存,去险即夷,皆二圣之赐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身之诚,在吾徒不可一日忽也。故谨书于集后以归黄公,亦以自儆云耳。”(注:《东里文集》卷十。)此种去险即夷后的痛定思痛,使这些士人始终保持安不忘危的警觉状态,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比如杨溥的“为人谦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注:《杨公言行录》,见《明名臣琬琰集》卷一。)的性格,显然与其长期的牢狱生涯有直接的关系。从仁、宣士人主要成员的个人性情看,许多人本来并非系平和谦柔者,黄淮、杨荣、夏元吉等原都是刚直甚至狂傲的,可知他们后来的平和乃是长期修炼的结果。夏元吉在追述自己的性格形成时说:“吾幼时有犯未有不怒,始忍于形,中忍于心,久则无可忍矣。”(注:《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传》。)忍当然是对个性的扭曲,但时间久了也就视为当然甚至自然的了。此种多样性为统一性并全归之于平和谦柔,对一代士风来讲也许并不是好现象,但倘不如此,台阁体诗风乃至仁、宣之治也就无从说起了。
明白上述三方面原因之后,再回头来认识仁、宣士人心态,就简单容易多了。此处可以杨荣为例。他在永乐朝较其他文臣更得成祖的信任,而且“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注:《明史》卷一四八。)但正是他总结出上述所言的“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处世经验,故以其为例当更具代表性。他曾作有《七十自赞》曰:“荷先世积德之厚,叨列圣眷遇之隆。久侍禁近,冀效愚忠。当齿力之既衰,尚责任之愈崇。自愧乎进无所补,退不我从。徒存心之兢兢,而怀忧之忡忡。惟古人尧舜其君民者,素仰其高风。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于初衷者也。”(注:《文敏集》卷十六。)这七十岁的自赞,即可视为其晚年的心态,亦可算作其一生的总结。他虽身居高位,荣宠有加,却并未有任何的自傲自足,而是深感其责任的重大,以致使他整日抱着心之兢兢、忧之忡忡的心态。仔细体味此种心态,可以发现它是由清纯诚厚与谦恭畏慎二种要素构成的,简言之亦可称之为清与慎。其实杨荣本人便作过精练的概括与具体的说明,其《清慎堂箴》曰:“清如之何?清匪为人。以洁吾心,以持吾身;慎如之何?慎匪为彼。以审于几,以饬于己。心或不洁,私欲纷挈,正理日沦,惟利之趋。几或不审,终戾于善,火始一烬,燎原斯见。惟利是趋,悭人之归。善苟戾焉,害必随之。曰清曰慎,勿肆以污。日笃不忘,绰有馀裕。矧兹服政,以莅厥官。事上驭下,云为百端。清则无扰,慎则无过。匪清匪慎,云何其可?清或不慎,亦曰徒清。既清且慎,式安其荣。从事于斯,终必如始。益之以勤,斯为善矣。终始或间,弃于前功;一念以爽,斯玷厥躬。譬行百里,九十方半。惟能勉旃,金石斯贯。”(注:《文敏集》卷十六。)杨荣为人警敏,谋而能断,且性喜宾客,不拘小节,故死后被谥文敏,因而他决非迂腐刻板的陋儒。在这篇标准的修身养性理论箴文中,其中受有程朱等宋儒的影响不待言,但主要应视为其人生经验的结晶。全文始终围绕着自我应如何服政莅官、事上驭下而展开。在作者看来,清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从而保持应有的做人节操。清的对立面是“污”,污就是不洁,就是贪。贪了就会成为只知追逐私利的小人。此尚未脱宋儒心性修养的范畴。然而“慎”之一项便非心性修养所能涵盖,它除却有“饬于己”的自我整戒外,更重要的在于“审于几”。“几”有微、兆、危诸意,此外应按《易·系辞传下》“几者动之微”之意来理解,即世事变动运化之细微先兆。所谓“审于几”即善于发现事物之微妙征兆从而审时度势、把握胜机。慎的对立面是肆,“肆”即纵恣放任自我,若“肆”便会有“过”,便会与“善”乖违,那么“害必随之”。很显然杨荣的“审于几”之慎便包含着功利的成分,而且慎比清更为重要,“清或不慎,亦曰徒清。”倘若念头一差,自我便会受到玷污损害;只有“既清且慎”,方可永保自身的尊荣。这样的箴文只有经过宦海风涛者方可写出,这样的心态只有在多事的朝廷官场方能具备。这种心态当然既不同于洪武时的战战兢兢,也不同于永乐时的口甜心苦。它是自觉的自我检饬,并有积极的用世之心与周旋官场的自信,只是在其心理底层依稀可见功利的算计与不易觉察的淡淡隐忧。这也是台阁体诗文缺乏深厚底气的真正原因。
谷应泰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如果将谷氏的话视为是对历史事实的判断,那显然带有很大的想象夸张成分,因而我们宁可相信他的话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仁、宣之于明代犹如成、康之于周代、文、景之于汉代,是该王朝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就象宣德四年宣宗本人所言:“朝廷治化重文教,旦墓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饫夔龙俱,庶几致、治希唐虞。”(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尽管在宣宗左右环绕着德比仲舒、文过相如的群儒,其阁中充满了各种图书,君臣讲论,共重文教,但却依然是“希唐虞”的美好理想而已,并未已真达唐虞之盛世。而且即使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抱着清慎心态的士人也不可能人人皆与皇上亲密无间,而勿宁说大多数人都难以达到完美的和谐融洽境地,如洪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歌颂国家太平,仁宗拿给众大臣看,几乎所有人都出言奉承,说什么“陛下即位所行皆行政,百姓无科敛徭役,可谓治世矣。”只有杨士奇肯讲实情,告知皇上:“流徙尚有未归,疮痍尚有未复,远近犹有艰食之人。”弄得仁宗颇为尴尬,不得已只好半解嘲半讥讽地笑着说:“朕与卿辈相与出自诚心,去年各与绳愆叫谬图书,切望匡辅。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从所言。卿三人(指蹇义、夏元吉、杨荣)未有一言,岂朝政果无阕,生民果皆安乎?”(注:王直《少师杨公大传》,《明名琬琰录后集》卷一。)《明史·杨士奇传》还特意补了四字:“诸臣惭谢。”后来的史学家固然都对士奇的忠心直言给予了特别的表彰,不也同时说明了众人与此种境界尚有一定距离吗?于是谷应泰也不得不承认:“然而三杨作相,夏、蹇同朝。所称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进封五疏,屡有献替耳。其它则都俞之风,过于吁咈;将顺之美,逾于匡救矣。”(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
士人之所以始终抱有清慎的心态,君臣间之所以难达完美和谐者境地,谷应泰认为是由于帝王“让善即喜,翘君即怒”(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的人性缺陷,自然有其一定道理。但其更深一层的根源则是道与势矛盾的难以协调,士人若欲完全依道行事必然与帝王之势发生抵触,欲完全顺从帝王之势则必然违背道之原则,结果是依违于道与势之间而左右摇摆,起码在形式上保持了君臣间的相安无事与朝政的和谐有序。这从宣宗废皇后胡氏的事件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此事发生于宣德三年,正是仁、宣之治的高峰时期。事情的起因是胡皇后未能及时生育子嗣而贵妃孙氏却得了贵子,宣宗认为应该“母从子贵”而立孙氏为后,于是便召集众辅臣商议如何处置胡氏。宣宗的易后行为是否与他和孙氏间的私人感情有关今日已无法知晓,但易后肯定不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要牵涉到宫廷政治的大事,比如后来的万历皇帝曾经为了他心爱的郑贵妃而推迟立东宫太子,为了维护所谓的正义与国家利益,文官集团对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争,并最终迫使皇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仁、宣士人在面对同类事件时却表现各异。杨荣表示积极支持,蹇义为皇上寻到了宋仁宗降郭后为仙妃的先例,这显然是从了帝王之势。杨士奇则要守道循礼,始而说:“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今中宫母也,群臣子也,子岂当议废母!”继则曰:“宋仁宗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率台谏数十人入谏被黜,至今史册为贬,何谓无议?”即易后必将招致后世非议,其态度可谓鲜明。张辅、夏元吉二人依回其间说:“此大事,容臣详议以闻。”然而当他们得知“上有志久矣”并看到“上不怿”时,就只能替皇上谋虚胡皇后让位的方式问题了。杨荣的做法显系过分,他竟然编织出“诬诋”中宫的二十件过失之事,连宣宗都感到编的太离谱而生气地说:“彼何曷有此,宫庙无神灵乎?”(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还是杨士奇稳重周全,最后终于以胡氏有病身体欠佳的理由,令其自辞皇后之位。事情总算有了个体面的结局。至于胡氏交出皇后之位是否情愿其实已不重要,因为凭三杨诸人文过相如的才能,撰写出一篇堂而煌之的诏敕来,肯定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明通鉴》的作者夏燮要比谷应泰敏锐而简明,他没有《明史纪事本末》的曲折繁饰,而是直笔书曰:“上独召士奇至武英殿,屏左右,问处置中宫事。对曰:‘皇后今有疾,因其有疾而导之辞让,则进退以礼。’上俞之,乃令后上表辞位,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贵妃遂得立。”(注:《明通鉴》卷二十,宣德三年三月。)事情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得力于双方的相互让步,皇上只是引而不发地使用了皇权而没有一意孤行,听取士奇的主张而保全了皇后的面子;文官一方则亦没有固执己见,迁就了皇上的意愿而维持形式上的礼节,从而最终没有酿成君臣之间的对抗。
但是如此的局面显然并非完全建立在共同守道的基础上,而是君臣之间长期形成的相互理解的人事因素与建立在政治利害关系上的相互克制作为维系条件,因此它也就是非常脆弱的,其中环境与人事上的任何改变均可使之分裂离析。这就是仁、宣之治何以会如此短暂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台阁体诗文缺乏真正的情感深度与深刻蕴含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所拥有的只是温和与温柔,缺乏的却是生气与力度。如果说政治上的温和尚算不得重大过失的话,则文学上的缺乏生气与力度,就肯定是最大的缺陷。
标签:台阁体论文; 杨士奇论文; 明史纪事本末论文; 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明史论文; 杨荣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