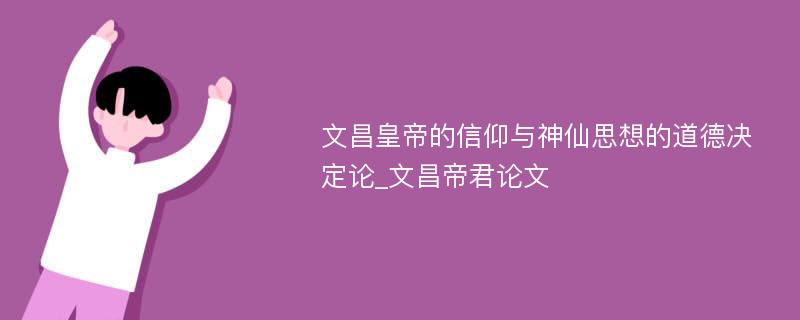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昌论文,决定论论文,帝君论文,神仙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文昌信仰向世人所提供的,不是传统的道教炼养术,而是阐扬老子“重积德”的思想,宣扬通过以“善”为价值导向的内在行为控制,可以达到人间理想或成仙不死。文昌信仰的社会操作性淹没了它的神学操作性,正因如此,它在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一、文昌神的起源及其与梓潼崇拜的整合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昌”本为星宫名称,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史记·天宫书》记载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古人为此六星所命之名,本身就具有十分耐人寻味的内在思想蕴义。因为,六星之名称,犹如人间的将相公卿,似乎是它们各自职辖的一种标示。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核心的神话传说。如屈原《楚辞·远游》:……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路曼曼其修远兮,徐珥节而高厉;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而为卫。”这表明,至迟在屈原的时代,作为天上星宿的文昌已被援入古代神话系统,演绎成为天上具有相当权力的神,称为文曲星、文星,主宰着人间的功名和禄位。《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昌,仓颉效象洛龟,曜书丹青,垂萌画字。”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仓颉视龟而从画,则河洛之应,与人意所惟通矣。”〔1〕古人认为,“奎主文章, 仓颉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天上众星象所成之文,即古来所谓“天文”。“得之自然,备其文理,象形之属,则谓之文。”〔2 〕《孝经援神契》解“文昌宫”之文化蕴义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宫’。”〔3 〕《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二:“文者理也,如木之有文,其象交错,古者仓颉制字,依类象形;昌者盛也,大也,言天地之文理盛大也。”〔4 〕或许这就是古人相信“文昌”主宰人间知识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功名、利禄,进而对其虔敬和膜拜的原因所在。
随着历史的推进,天上的星宿不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人间事务密切相关的神性,而且逐渐同被神化了的世间人物相参同附会,于是,人间至贤的精神被映射到天上,成为天上的神灵。经过这样的转化和重铸,文昌成为一个伦理符号。文化形态的这种演变,不仅有一个漫长的整合过程,而且人间的价值和审美逐渐成了它的核心要素。
关于梓潼文昌帝君的身世和姓名等,有多种说法。据《清河内传》载元渝州刺史的赵延之所撰《行祠记》说:“帝君储精列宿,降自有周,姓张讳仲,字孝友。辅宣王中兴,没为神明,累朝咸有大功,尤孜孜以忠君孝亲,扶植斯文,化淑民心为任。”〔5 〕《梓潼帝君化书》亦以帝君自言称其“自周历晋”〔6〕多次出没世间,教化救世。
《文昌帝君本传》称:“文昌帝君,姓张,讳善勋,周初吴会间人也”,其始祖是黄帝之子,因其“始造弦张弓,世掌其职,子孙因以为氏”,因而成为吴之显姓。文昌帝君乃是至孝之子。道经说:“张母少勤苦,六旬而疽发背,医觋罔效。帝君计穷,既为吮咀,乃病久食少。复成赢瘵。医曰:‘此痼疾,以人补人,庶可平复。’帝君剔股供之。空中语曰:‘上帝以汝纯孝,延汝母寿二纪。’翼早,勿药果瘳。”后来父母因疫毒流行,同日而逝,“帝君亲持畚锸营葬,庐墓三年,有二白雉栖树,祭则飞鸣而下,终制不见。葬五年,墓西水暴发,欲改卜,无及,乃斋戒守坟,日夜诵《大洞经》,并取向所奉金像,严事之墓前,溪谷变成坚角,皆孝感之所致也。”道经说,文昌帝君“其在晋武帝时为张亚,时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生于两越之间”。并称周以后,文昌帝君历七十三化。”晋朝“元帝(即司马睿,317—322年在位——引者)南渡,绥抚江左,帝君作儒士,称谢艾,跨白驴往河西应孝廉”,仁于东晋,曾以三万步骑大败敌寇,后战死;“士民于阆中梓潼县立庙祭祀,称‘梓潼君’,庙在九曲之北,有降笔亭,……其降笔多劝人以忠孝,有《阴骘文》及训语甚多。”〔7〕
据《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应验经》,元始天尊谓梓潼帝君曰:“汝居西蜀之中凤凰山上,显灵凡土,俱有象成,察九十四化之行,藏显亿千万劫之变化,掌救苦之一职,司祸福于四方。聆吾片辞,以裨寸善;尚加谨畏,以答慈悲。”其颂曰:“桂禄籍汝司,文章为汝全。若要登仁径,赖汝为衡权。”〔8 〕反映了文昌帝君在道教神学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当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川路经七曲山时,感张亚子之英烈精神而隆崇之;并有传说言玄宗曾得张亚子托梦显灵,故而对其甚为崇敬。唐僖宗则亲祀梓潼神,并奉之为济顺王。此后梓潼神益受士众崇信,成为天下共祀的大神。唐宋时期以科举取士,人们对文昌的信仰和崇拜亦甚盛,文昌神屡次受封。
事实上,文昌信仰在道教中早已出现。 北魏寇谦之所撰《老君音诵戒经》尝言:“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后于中方有。当简择种民,录名文昌宫中。”〔9〕但文昌信仰与樟潼崇拜的整合, 则是后来的事。
梓潼神和文昌神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东晋宁康二年(孝武帝年号,374年),蜀人张育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 曾大败敌寇,后来战死,蜀人怀念他,在梓潼县七曲山(四川梓潼县北),为其建张育祠,并尊奉他为雷泽龙神,当时七曲山另有梓潼神亚子祠,因两祠相邻,后人遂将两祠神名合称张亚子,并称张亚子仕晋战死。究其实,乃《晋书》所载张育之事迹。梓潼神张亚子又称张垩子或张恶子,据《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名恶子。”有关梓潼神张恶之显灵之传说甚多。如《太平寰宇记》卷84剑州梓潼县条引《郡国志》:“恶子昔至长安见姚苌,谓曰:‘劫后九年,君当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当见寻’。”〔10〕另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前秦建元十二年,姚苌到梓潼七曲山,见一神人对他说:“君早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姚苌问其姓名,神答曰“张恶子也”,言毕不见。及至姚苌“据秦称帝(即指姚苌建立后秦一事——引者),即其地立张相公庙祀之”〔11〕。
随着历史的发展,梓潼神逐渐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大神,并被假以扶鸾降笔,称其显灵之时“笔端无一事之不言,分身无一民之不救。九十五化之昭乎日月,亿千万劫之拯乎黎民。全忠孝之大伦,示臣子之彝式。”〔12〕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将梓潼神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二所载“元制诰”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维明有礼乐,维幽有鬼神。妙、显、微之一贯,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形功用于两间,矧能阻骘于大猷,必有对扬于懋典。蜀七曲山文昌宫樟潼帝君光分张宿友泳周诗相予泰运,则以忠孝而左右斯民;炳我坤文,则以科名而选造多士。每遇救于灾患,彰感应于劝惩。贡举之令再颁,考察之籍先定。贲饰虽加于涣汗,微称未究于朕心,於戏!予欲文才辈出,尔丕炳江汉之灵;予欲文治宣昭,尔浚发奎璧之府。庶臻嘉号,以答宠光。可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主者施行。”〔13〕从此神话中天上的“文曲星”与“梓潼神”合而为一。及至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清朝亦每年于农历二月三日派官员前往祭祀文昌神。
封建时代,文昌帝君作为学士科举诸等人士的保护神,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封建社会,倍受人们的虔敬和膜拜。人们梦想获得文昌神的佑助,通过科举获得商品次第,从而摆脱沉重的封建奴役。因此,在那些实行科举制度的朝代,文昌帝君受到非常隆厚的崇拜,寄托着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之中众多人士的梦想。祖籍四川仁寿的元代学者虞集(1272—1348)所著《道园学古录》卷四六《四川顺庆中路蓬州相如县人文昌万寿宫记》记述宋元之际文昌崇拜的大致情形,其文曰:“文昌宫者,蜀梓潼县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时,俗尚祷祠,鬼神之宫相望,然多民间商贾、里巷男女师巫所共尊信而已。独所谓七曲神君者,学士大夫乃祠之以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残,民无孑遗,鬼神之祠消歇。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灵异亦寂然者余四十年。延祐(元仁宗年号,公元1314—1321年间——引者)初元,天子特出睿断,明诏天下以科举取士,而蜀人稍复治文昌之祠焉。”虞集的这个宫记表明,不仅当时士众的文昌信仰十分隆盛,而且统治者对社会中的文昌崇拜也甚为支持。后人对文昌帝君的神性和神力的描述很多,并赋予文昌帝君以崇高的地位。《历代神仙通鉴》言文昌帝君乃“上主三十二仙籍,中主人间寿夭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足见文昌帝君神位之崇高。
二、文昌信仰与后期道教神仙观念中的道德决定论
(一)道教发生期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危机与前期道教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倾向。
纵观中国伦理发展历史,先秦伦理具有明显的主体自主性特性,这与百家争鸣、各执一端、“道德不一”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相关。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走向一致,尤其是汉代以后,纲常伦理成为统治者法定的伦理准则,儒家伦理观念在社会思想中第一次占据了“独尊”地位,其发展方向就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东汉后期到南北朝,中国社会又一次出现动荡不安的痛苦局面,进而社会政治分裂,汉代以来的纲常道德价值受到怀疑和践踏,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受到相对削弱。于是道教应世而生并以其宗教形式推行社会教化,把受到怀疑的纲常伦理加以改造,弥补其中某些不合自然、有伤人性、矫枉过正的缺陷,而以宗教神学为其强大的思想载体,神化封建伦理秩序,促进社会思想的秩序化和集权化,此后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时期中国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以道教为代表的宗教及其伦理和思想文化,却以潜伏的形式维护着中国社会的内在统一。这一点非常重要。其至隋唐时间,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及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道教及其伦理的社会控制功能再次得到加强,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经过唐以后再次出现的国家分裂混乱,社会道德又一次出现危机局面,使道教伦理功能的发展受到社会危机现实的强烈刺激;并且,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隋唐的鼎盛之后,表现出对社会控制的更深刻的需要。以“兴至道可以救之”为己任的前期道教神仙思想体素,就明显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这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思想,另一方面也是道教发生期中国社会的信仰一伦理危机使然。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乃是密不可分的。
(二)隋唐以后文昌信仰的兴盛和道教神仙思想中道德决定论的上升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经典时代,此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遗留问题,被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步所超越。在文昌帝君信仰研究中,科举制度对其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及其取士标准,不仅推动了通过个人努力以谋求社会地位上升这种观念的成熟,而且成为推动唐代及其以后中国社会文昌信仰盛行的内在动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其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汉代。汉文帝时,为了鉴明政治得失,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隋以后,实行分科取士,科举制度逐渐成熟。隋文帝废除为世族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立“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其至唐代,科举的科数、种类、等次都有诸多增制,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科举在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1、刺激了文昌帝君信仰传播和发展。因为文昌神的职能, 就是主宰人间功名禄籍。于是文昌帝君的重要性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而得到重视,备受尊崇。这是科举制度对道教神系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而科举制度中众多学子的屡试不中,造就了更为庞大的文昌帝君信仰群体,刺激了文昌帝君信仰的广泛流行。
2、按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科举取士的主要依据当是个人之德行和才能(尽管执行过程中或有舞弊现象),而不是出身门第,这就刺激了人们通过自我道德修养与能力提高来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这种观念反映在道教神仙思想中,就是传统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上升及其影响在实质上的社会化。
据《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说,“玉帝论定劫运更变,世人虽可悲痛,亦其自职尔时慈济真人暨诸圣各各稽首而白天尊,言臣等即是思,惟心大不忍,戚首蹙頞,力不能救。惟愿天恩,发慈悲心,开方便路,垂一金臂,援其焚溺,庶使人道不至类绝。臣等敢冒死谨言于是。”于是,“天尊抚几高抗,澄神默坐良久,答曰:迩者,蜀有大神,号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齐太乙之尊,位高南极,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轮回,司仕流之桂禄,考六籍事,收五岳形,历亿千万劫,现九十余化,念念生民,极用其情。是以玉帝授之如意,委行飞鸾,开化人间,显迹天下。盖此末劫实款可除;若欲消之,此神其可。武当为汝召之,俾救度末世,勿使类绝。”梓潼帝君对天尊说,要消除此劫,“先正人心;为人子者,训之使孝,为人臣者,训之使忠;训兄弟以友恭;训夫妇以和顺;训居上者使待下以情;训治事者使处心以公。率而行之,或者可以少弥。”元始天尊则称叹于梓潼神之救世曰:“奇哉帝子!悯念众生,说是因缘,心得开悟。若诸世人推行不已,则可消除劫难,兴国太平,人享高寿,物遂本性,五谷丰熟,歌谣满路;一或反之,则兵戈疫疠频仍相藉,横尸遍野,枯骨成山,而人类绝矣。”〔14〕此中不仅表明了梓潼神的开化救世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伦理道德的重大社会功能。
宋代以后,中国伦理发展史上伦理审美氛围的“逐渐收紧现象”逐渐形成。理学的出现和兴盛,即一力证。表现在道教伦理中,即在思想和行为观念上强化了它的约束力,使宗教的社会控制力增强,这同理学的形成和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了道教伦理的成分,对纲常伦理进行弥补、改造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收紧了道德约束之索,要求人们于心性意念、视听言动、时时处处严格约束自己、对照检查自己,“存天理,灭人欲”。但理学的一个先天弱点,同所有其他世俗社会社会伦理学说一样,就是缺乏功能强大的信仰载体。这对道教伦理的发展却是有利的。因为一方面理学为道教伦理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另一方面理学缺乏神学载体这一先天缺陷,则以时代对神学的需要成为促动道教伦理发展的历史杠杆。
(三)文昌信仰所反映道教神仙观念的主体化
在早期道教的修仙前提中,报孝父母乃是修仙者走向仙途的第一步:“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先当“仁爱慈孝,恭奉尊长,敬承二亲。”〔15〕这就是道教调和仙道理想与人道伦理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随着历史的推进,道教这种调和态度,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事实表明,道教成仙思想中道德决定特点,使道教修行学说的发展,在形态上越来越走向内在化。从早期道教浓厚的外丹信仰,发展到后来日益浓厚的内丹信仰,就充分说明了一点。内丹神学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它的道德前提论。至于日益民间化的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之类道书在内的道教劝善书系统,则更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后期道教向精神领域转移的大趋势。
随着历史的发展,道教以宗教神学的形式推崇和强化纲常伦理的力度得到强化。宋元以后,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并且在这种强化过程中,纲常伦理所具有的某些超乎人性的道德要求,又有所抬头。如元代净明忠孝道重要人物刘玉对教义的阐释,清楚地反映了道教内部思想观念的伦理至上特征。《玉真先生语录》记载:“或问:古今之法门多矣,何以此教独名净明忠孝?先生曰:别无他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16〕可谓一语破的。事实上,这也正符合历史上中国社会和伦理发展的特征。文昌信仰中这种道德决定论的特征不仅十分显著,可以看作是道教伦理的道德决定论的典型形态,而且,它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控制力度十分强大。
于是,“孝”的功能,由过去的仙阶第一步,上升为得道成仙的一种途径。托名文昌帝君《文帝教经》、《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经,对此都有详尽阐述。如《文帝孝经·孝感章第六》:“帝曰:吾证道果,奉吾二亲,升不骄境,天上聚首,室家承顺,玉真庆宫,逍遥自在。吾今行化,阐告大众;不孝之子,百行莫赎;至孝之家,万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殛,魔煞祸侵;孝子之门,鬼神护之,福禄畀之。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才化成,惟神敬孝,惟天爱孝,惟地成孝。水难出之,火难出之,刀之所至,地狱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亲,皆得解脱。四生六道,饿鬼穷魂,皆得超生。父母沉疴,即时痊愈……”若“人果孝亲,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列仙班。万事如意,子孙荣昌。世系绵延,锡自斗王。”〔17〕孝可得道,升为仙官。至孝可以消除万劫之灾,可以得到鬼神的佑护,上可解脱祖辈,治愈父母宿疾沉疴,中可自身得仙,下可佑庇后世,可见孝之为道,功德大矣。此亦可谓道教对《孝经援神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18〕思想的神学化演绎和发展。
“积德”就是积仙,积善足,则可成神仙。《文昌帝君阴骘文》即很好地体现了后期道教这种纯粹道德决定论的神仙思想:文昌帝君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史信友。……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19〕文昌帝君所要向人们证明的是,虽曾十七世为士大夫之身,但一直爱护吏民、救急周难、怜孤恤寡、积善不已,因此得天赐福,终成神仙。
这些经典所体现后期道教神仙思想体系的道德决定论特征十分明显。在思想实质上,这些经典并没有比《道德经》所提出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思想走得更远,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演绎而已。通过形式上的发展,积德成仙的道德决定论得到了强化,伦理道德逐渐取代了刀圭仙药,成为一个人可否升仙的制约因素。
道德的主体是人;道德决定的实质,就是人的主体性。道德神仙观念向道德决定论的演变。正符合一切宗教的发展必然逐渐走向人本休化和世俗化的规律。道德决定论所体现的后期道教发展的伦理化和世俗化趋势,一方面标志着道教的发展在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伦理化的道教正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地走向民间,走向广大的中国社会,从而发挥超乎道教伦理自身影响力的社会控制功能。这表明,一个大的民族宗教的衰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当一个宗教的社会功能在其总体发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成为它的主要功能,那么,它的衰落,将意味着它所孕育的社会控制功能的成熟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重要影响。文昌帝君崇拜在道德信仰体系中的酝酿成熟及其社会化、世俗化,乃至向民俗的转化,乃是后期道教发展的伦理化、民间化的一个重视表现。
注释:
〔1〕〔2〕〔3〕〔18〕见《孝经纬》第13、14、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4〕〔12〕〔13〕《道藏》第2册,第606、612、612页。
〔5〕〔6〕《道藏》第3册,第289、293页。
〔7〕〔17〕以上见《藏外道书》第4册第296—298、306页。
〔8〕〔14〕以上见《道藏》第1册,第815、816—817页。
〔9〕《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第3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太平寰宇记》第1册,第64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
〔11〕参见《新校本晋书并附编六种》第6册,第379页, 台北鼎文书局,1983年。
〔15〕《无上秘要》卷十五“众圣本亦品”。
〔16〕《正统道藏》本《净明忠孝全书》卷三《玉真先生语录内集》。
〔19〕《藏外道书》第十二册,第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