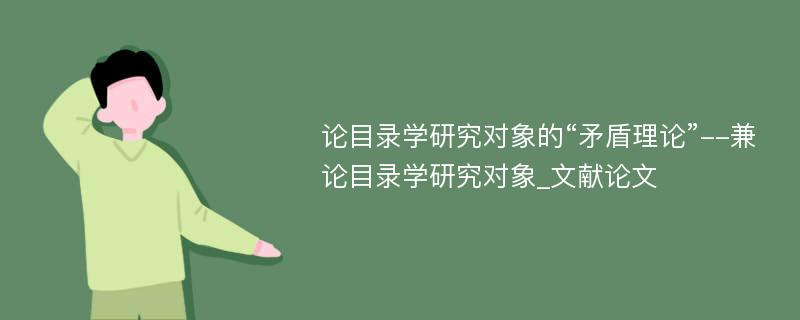
评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兼论目录学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的历史沿革
1959年,武汉大学陈光祚发表了《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他试图将马列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一门科学的对象”[1]的论断引入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提出了目录学正是由于人类巨大的图书财富和读者对图书的一定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2]。 此即为我国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的真正源头。陈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引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方法和在这一研究中引入了读者用户需求这个过去被忽视的重要方面[3], 并指出“图书财富”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这一贡献为后来“矛盾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但当时陈先生在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方法于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后,最终却没有将目录学研究对象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矛盾,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用书目索引的方式通报图书和宣传图书的规律”的认识,并被他人归结为“规律说”[4]。
1980年,彭斐章、谢灼华两先生共同提出了“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5] 的看法。一般认为,此即为“矛盾说”的正式出台,这一说法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①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一种社会或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抽象的矛盾。②用一种复合句式的句型表达这一说法。这两个基本的特征为后来多种不同版本的“矛盾说”所沿袭、继承。可称之为“矛盾说一”。
1982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第一次将“矛盾说”写进了高等学校目录学教科书,并将“矛盾说一”修正为“揭示与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6],可称之为“矛盾说二”。 在这次定义中,将“矛盾说一”中的“图书资料”改换成“文献”,将“报道”改为“报导”,在句末省略“文献”二字并代之以“它”,以示精炼。
1986年12月出版的《目录学》(中央电大)则进一步将其修正为“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7], 即将末句中的“它的”改换为“文献”,以示强调。该书紧接着又补充了一个说法,即“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即在上句的“文献”一词后增加了“的信息”三字,并将连接“揭示”、“报导”两词的系词由“和”改为“与”。可称之为“矛盾说三”与“矛盾说四”。
1991年,倪晓健主编的《书目工作概论》出版,该书重复了“矛盾说四”。
1991年,武汉大学曾令霞依据“矛盾说”的固有程式,将“矛盾说四”进一步匡正为“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求的矛盾”[8],即不仅增加了两个定语限定词, 改“需要”为“需求”,而且还将“文献的信息”改为“文献信息”,可称之为“矛盾说五”。
1996年12月出版的《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 对上述5种不同说法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正,提出了“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这一版本吸收了“矛盾说”以往各种版本的特点,是为“矛盾说”的最新版本,可称之为“矛盾说六”。
以上即为我国目录学研究对象讨论中,部分人所执“矛盾说”的历史沿革。
此外,尚需指出,在上述传统的“矛盾说”较为流行、走红的时候,有人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矛盾说”,即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日益增长着的庞大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9]。对此,可称之为“新矛盾说”。
2“矛盾说”有无科学依据?
2.1 从对立统一规律看“矛盾说” 既然坚持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抽象的矛盾——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就必须严格依据哲学的有关原理来进行考察与鉴别。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矛盾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即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其中同一性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二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贯通(如自然界中的正电和负电、生和死;社会中的对抗和缓和、战争与和平等)。而斗争性则是指矛盾双方相互离异、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性质和趋势。上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都不能单独存在并构成矛盾,只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结才能构成矛盾。
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从字面上看,“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不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也不存在相互离异、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性质和趋势。“矛盾说”对此也从未进行过必要的论证,因此,不能认为是辩证法范畴或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也就不能说是目录学领域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2.2 从概念表达(词语本身)看“矛盾说” 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在概念表达上,一般都是两个反义词、词组的组合,而不是两个长句型的组合。如战争与和平、阳与阴、天与地、男与女、雷与电、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倒退、先进与落后等等。但“矛盾说”在语义表达上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以简洁语词表达的概念。在概念表达上也不是严格的一字对一字,而是以一种句型表达。这一罕见的句型,其语法结构本身就不完整、明确。如上句是一个省略了主语的句子——即没有回答是谁在“揭示与报导文献”,当然,也没有回答只有什么东西才可用来“揭示与报导文献”。依据“矛盾说”中“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要求目录工作者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之句来看:①被省略的主语应为“目录工作者”。②“目录工作者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即为目录工作者科学有效地编制各种类型的目录。这样,还原被省略的主语后的“矛盾说”即应为:“目录工作者”、“揭示与报道文献”(即编制各类型的目录)与人们对它(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样,“目录工作者”与“人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矛盾,“揭示与报导文献”(即编制的各种类型的目录)与“特定需求之间”也可能有一定的矛盾”,但从目前“矛盾说”的固有句型来看,“揭示与报导”、“文献”、“人们”、“特定需要”等概念均无一一对应的概念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不能构成哲学意义上的矛盾。这并不是对“矛盾说”的苛求,而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概念表达方面的基本要求。
从“矛盾说”这一句型所包括的涵义来看,上句“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即表示人们对无序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加工,形成了有序的各种形式的书目,并已投入了“报导”、使用过程,文献处于有序状态,可概括出“有序”的概念;下句“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则包含着对文献有序化的需求,也可从中概括出“有序”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矛盾说”这一复合句式基本上是由两句正面的句式所组成,即上下两句之语义都表示肯定,而且,其字句或词组间毫无一一对应的可能,也就不能反映其概念间的同一、斗争性质和趋势。这样,怎能构成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又怎能成为目录学领域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呢?
“矛盾说”的上述错误,在于观察问题时,仅仅看到问题的表面,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并不善于从中予以概括与总结。如有人要说,带领和指挥部队向敌人阵地前进与手持武器坚守阵地不许敌人进犯的矛盾的话,我们则应简略地概括表述为进攻与防守的矛盾或攻与守的矛盾。因此,从本质上看,“揭示与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句式的本质就是有序与有序之间的矛盾,而有序与有序之间不可能是对立统一的,也是不能相互转化的。
2.3 什么是“矛盾两极”及“中介”
在“矛盾说”盛行十多年后,有人从理论上——从哲学意义上对“矛盾说”进行了局部的补充、完善,并认为矛盾说“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使研究者在注意书目文献中介地位的同时,把研究者的眼光引向矛盾两极的研究”。“书目文献作为连接矛盾两极的桥梁和解决矛盾的手段,不是在于书目文献本身,而是依靠其蕴含的书目情报”,“文献信息的揭示和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接受总是通过书目文献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在此,我们讨论一下比较新颖的“矛盾两极”及“书目文献”究竟是谁的“中介”——“矛盾说”的贡献何在?
苏联目录学家科尔舒洛夫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书目是图书与读者之间的媒介”[10]。陈光祚先生则认为“图书财富”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矛盾”。郑建明也曾说:“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以解决巨大的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并探讨其规律”[11]。对此,我们不提出异议。运用“矛盾说”有关术语对科氏等人的上述言论可以解释为:“书目文献”及其所“蕴含的书目情报”是“图书资料”(文献信息、文献的信息)、“文献”、“它”与“人们”这“两极”之间的“中介”,简言之,“文献”与“人们”之间的中介是“书目”。但“矛盾说”的“贡献”最终却将“两极”中的一极——“图书资料”、“文献”、“它”改换为“揭示与报导文献”、“文献信息的揭示”,即又新生出一极,这是否是“矛盾说”的一种“贡献”呢?诚然,科氏与陈氏的理论不是不可以突破,但我们不知道“矛盾两极”之一的“揭示与报导文献”、“文献信息的揭示”在此究竟表示着什么——是表示具体目录工作?还是“书目文献”、“书目情报”?如果是,则有可能“中介”与其中的一极相等同,“矛盾说”无存在的可能;如不是,则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抽象”东西呢?“矛盾两极”,能否存在呢?事实是:①“人们”通过“中介”(即媒介)——“桥梁”——“书目文献”所要了解、得到的主要是自己“特定需要”的文献本身,而不是需要了解、得到“目录工作者”及如何“揭示与报导文献”。②只有“目录工作者”才对“文献信息”进行揭示,并通过“书目文献”这一“中介”、“桥梁”将文献介绍给“人们”,而不是将自己及自己“揭示与报导文献”这一劳动介绍给“人们”。③“揭示与报导文献”这一句式语义不清,本身不应成为一极。这是因为,我国国家标准对书目的定义中写有:书目是“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即书目或书目文献这一概念——“中介”中包含有“揭示与报道文献”这一内涵——“矛盾两极”中之一极,两者应同为中介。此外,据孙二虎解释,“揭示与报道文献”即“目录工作”。而“目录工作”这一概念就包含有“目录工作者”、“目录”、“书目文献”等内涵。这样,“揭示与报道文献”与“书目文献”两者间便是因果关系,两者应同为中介——中介劳动与中介产品。类似这种中介即中介的命题是令人颇感奇怪的。④“矛盾说”句型中本身就包含有“矛盾两极”及“中介”这三个方面,如“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一句中,“人们”的“特定需要”与“图书资料(文献信息)”之间本身就是两极,而不是一极——一个“对”字已将两极清楚地勾划出来,但“矛盾说”至今未看到最为重要的“图书资料”(文献信息)这一极,未“把研究者的眼光引向”这一重要的一极,使人感到遗憾。此外,“揭示与报导文献”——即目录工作者的劳动及成果——中介劳动及中介产品——目录,应同为中介。
由此可见,持“矛盾说”者在对辩证法、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和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尚未真正了解时,便将两个非矛盾的概念当作矛盾或主要矛盾关系的概念并列。
2.4 从理论依据上看“矛盾说”
现有“矛盾说”的主要理论,主要是由《目录学概论》奠定并由《目录学》(中央电大)等著作所沿用、修改的下面一段人们熟悉的句式所组成,是为“矛盾说”的主要理论依据。为叙述方便,我们称其为“四段式”理论,现分段抄录(仅加上我们的字母分段号)如下:
A:“一方面文献的数量激增,类型也逐渐复杂, 采用书写印刷文献语文的品种越来越多,文献的新陈代谢也比较频繁”。
B:“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对于文献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提出对文献的需求。与此同时,读者对文献的需要往往是针对性特别强,时间非常紧迫”。
C:“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要求目录工作者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以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满足读者对文献的特定需要”。
D:“因此, 我们认为揭示与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目录学》(中央电大)里重复了以上的意见,仅将“目录工作者”改为(“上升”[12]为)“书目情报工作者”,此外,在文字上作了局部的变动。
以上摘出的四段式理论告诉我们:①A与B分别为矛盾的双方——“矛盾的两极”,即A+B等于C——“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该句式对这一矛盾作了较详尽的描述,理由较充分。②A与B“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前提条件,实际上支配、规定了C ——“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即只有A+B才能决定支配C的存在。 ③“揭示和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不能支配、规定其它矛盾——C不能支配、 规定A+B或其它。④D句——“因此,我们认为……”的结论, 即“矛盾说”的提出没有可靠的、起码的科学依据、理由。从逻辑学观点来分析上述现象,即为“矛盾说”的论证、论据不足,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具体来说,其理由虽然真实,但它与推断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在此,我们依据逻辑学的有关原理,对“矛盾说”的C、D两句暂作如下的局部修改。C:“这两者的矛盾”,作为前提和条件, 具有主要矛盾的某些特征,“揭示与报导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等其它各种矛盾,都是服从于这一主要矛盾的。因此,遵守逻辑规律不但是人们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也是进行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确定目录学领域主要矛盾时所必要的条件。
事实是,同“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的,起码还应有查寻与检索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查寻与检索比一般的需要——现实需要、潜在需要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可惜“矛盾说”的认识水平多年来仅仅停留在“需要”这一基础上,还未提高到查寻与检索这一步。试问,这一矛盾又应为什么矛盾呢?能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呢?由此看来,“矛盾说”并没有真正找到目录学领域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3 “矛盾说”地位、作用质疑
虽然“矛盾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说法,但其倡导者最近却主动地提出了“矛盾说”的“地位”、作用问题,如1996年彭斐章先生说:(陈光祚先生的)“文献流说的出台,是作者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再认识,并未动摇矛盾说作为研究基点的地位”,“我们近20年来所从事的探讨都是以矛盾说为基点的”。“矛盾说提出以后影响了老中青三代人”,“以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
“矛盾说”倡导者们的上述认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与“书目情报”概念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并可分别称之为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基点”、“学科基点”。其中,矛盾说又为“基点”之“基点”——“书目情报”这一基点即是在“矛盾说”这一基点上“升华”出来的,换句话说,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抽象的矛盾,在这一抽象的矛盾——“基点”上又“升华”出“书目情报”,这一再次抽象的“抽象概念”和“基点”或“学科基点”——当代目录学有两个“基点”。在此,我们对这一“升华”理论作如下初步质疑。
3.1
“矛盾说”与书目情报能否并列作为目录学的“基点”
“书目情报”是一个专门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与情报学关系密切的概念,“矛盾说”则是一种理论或说法——是由若干概念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矛盾说作为研究基点的地位”一句亦应加上定语——目录学,即成为“矛盾说”作为目录学“研究基点的地位”。那么,一门学科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目录学“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起点”究竟应表述为一个专门概念,还是应表述为一种理论和说法呢?将一个专门概念和一种理论或说法并列为一门学科的“出发点和起点”?
3.2 “矛盾说”能“升华”出“书目情报”吗
“矛盾说”的倡导者认为:“以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这是对“矛盾说”价值、作用的一种最新评价。
事实是,不论在中国或外国,在若干个世纪以前,自目录学称之为“学”的那一天起,在根本就没有“矛盾说”的情况下,书目这一概念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只是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传统的书目这一基点上,在“新时代条件下”,才逐步“升华”出“书目文献”、“书目信息”、“书目文献信息”、“书目情报”、“书目资讯”等概念,且书目信息、
书目情报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仅是同一个概念——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反过来说,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或“基点”离开了书目、书目文献这两个概念或基点,将无法“升华”出来。 在国外,
在根本就没有“矛盾说”及其影响的条件下,
在bibliography 这一基点上,
也能“升华”出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这一概念;在我国,同样在没有“矛盾说”的1959年,“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在传统的书目基础上,加上当时流行的“情报”概念,早已“升华”、“创造”出“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或“基点”。
3.3 “矛盾说”的“地位”受到“动摇”没有
“矛盾说”的倡导者说,“文献流说的出台……并未动摇矛盾说作为研究基点的地位”。“矛盾说”的倡导者近年追求“书目情报理论”在当代目录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自然也应是追求与关心“书目情报”这一“基点”赖以“升华”、“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基点”——“矛盾说”在当代目录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否受到“动摇”?在此,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矛盾说”在我国当代目录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当代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究竟是否受到动摇?
早在1981年,孙二虎就批评了“矛盾说”,并认为“严格地说,‘揭示与报导图书’或者说‘目录工作’是不会和人们对图书的‘特定需要’之间发生矛盾的”,进而认为“矛盾说”将其归结为“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并指出“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即“目录工作”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是“不会发生矛盾”的,即使有,也并不是“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13]。孙先生的文章公正、平和,不带任何偏见,早已从根本上——从理论上“动摇”了“矛盾说”的合理性,然而,“矛盾说”的提出者对孙先生言之有理的批评不屑一顾,既不作答,也不作较大的修改,我行我素地将“矛盾说”写进了大学目录学教科书——至此,“矛盾说”便有了一定的“地位”。
1989~1990年,杨沛超、纪晓萍、张治江等人先后对有了一定的“地位”的“矛盾说”提出了较系统、合理的批评,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体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不是什么抽象概念,目录学亦应如此”[14]。张治江则进一步指出:“研究规律是科学的本质,研究不同事物的规律形成具有不同特性的科学。……如果我们不从一个具体的客观事物入手,就无从探索什么关系和规律,从本质到本质,从规律到规律,不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本质关系和运动规律决不能超越具体事物去发现和掌握。因此,我们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具体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不是什么抽象概念,目录学亦应如此”[15]。
1993年,石宝军又针对“矛盾说”的流行及危害,号召人们跳出这一“囹囫”[16]。
所谓的“矛盾说”理论,在《目录学概念》中仅有570个字, 且有不少疏漏,孙二虎、张治江等人的文章,不但在文字数量上超过了“矛盾说”,在学术水平也超过了“矛盾说”,即从理论上彻底动摇了“矛盾说”的“地位”,奇怪的是,近20年来,“矛盾说”的支持者们对孙、张等人的合理批评意见从未作出过任何较系统、认真的回答、辩护,表现出一种有“地位”者的派头,且自我评价越来越高。事实上,“矛盾说”仅在由“集体研究力量”主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央电大《目录学》、《管理》以及倪晓健主编的《书目工作概论》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学教科书、著作中有一定的“地位”,而在近年出版的其它一些目录学著作中,并没有什么地位,也谈不上“影响老中青三代人”。最有说服力的是,1990年初,陈光祚先生在对“目录学研究对象再认识”时,不仅“动摇”、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认识,而且,其文章的影响也足以“动摇”矛盾说的“地位”。我个人认为:至少在陈先生这一代人的心目中,“近20年来”从来就没有“矛盾说”的什么“地位”——“矛盾说”没有影响陈先生,反而是陈先生的研究影响了“矛盾说”——导致了“矛盾说”的产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
4 目录学领域里“最基本、 最主要的矛盾”和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4.1 目录学领域里“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什么是目录学领域里“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呢?我们只能严格依据辩证法的方法去概括、判断,并用简略的语词表达,而不能仅凭一知半解、依靠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想像。
从文献目录的产生、发展来看,人类对文字记录有系统的收藏管理活动导致了目录的矛盾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大量繁杂无序的文献与人们对文献利用时的有序要求,则是这一过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范畴,其它各种矛盾,如“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查寻与检索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人们对书目情报的需要与书目情报能力之间的矛盾”,“书目的供与求之间的关系”——“矛盾关系”,“书目情报服务质量好坏的矛盾、宏观书目控制水平高与低的矛盾、手检与机检的矛盾、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的矛盾”等等,无不服从于这一“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的运动与发展。这样,经过对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矛盾体系的全面的观察、分析,并运用辩证法的方法进行概括,对目录学领域里“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可表述为:文献的无序(混沌)与有序之间的矛盾。
4.2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确定
4.2.1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 目录学领域里“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的确定,并不意味着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因为一门学科领域内的主要矛盾与研究对象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目录学——严格地说,包括所有的学科在内,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考虑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科学地确定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二是审慎处理学科研究对象与学科名称、学科核心概念体系[17]、学科基本理论体系等一系列关系。
如前所述,杨沛超、纪晓萍、张治江等人早就指出:“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体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不是什么抽象概念,目录学亦应如此”。因此,我国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只有在毅然选定了某种社会现象以后——即在消除、克服那种以某种抽象的矛盾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矛盾说”的消极影响之后,在抛弃了形式主义的学风之后,才能回到辩证法的正确认识轨道上来,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4.2.2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目录。 在以上探讨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本文先后排除了“矛盾说”、“规律说”,同时还排除了以“矛盾说”为代表的长句型表达对象说——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表述亟须用简洁的语词表达。那么,近年流行的“目录说”、“目录工作说”、“目录活动说”、“目录事业说”等说法实际上都是以一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看法,看法较为接近,且语言表达较精练,可纳入我们选择的范围。
我认为,在进行最后的选择时,应考虑到以下几种因素:学科研究对象即学科的逻辑起点、基点、最元初概念,几者应是一个概念,而不应是两个概念或两个基点;学科研究对象与学科核心概念体系、学科名称等应保持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致中途发生歧义;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之间亦有较严密的逻辑联系,并以此同其它学科相区别;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的方法与其它学科相一致,不搞无科学依据的标新立异。根据以上要求,简言之,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目录,目录学即是关于目录的学问,而不是关于某种矛盾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