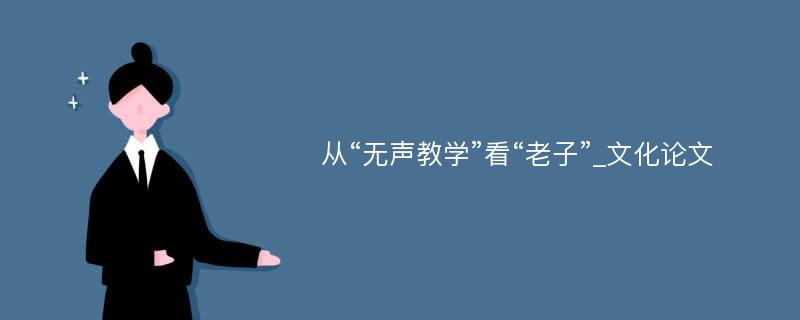
从“不言之教”解读《老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之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2)01-0048-04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如何表达思维及语言能否全面准确地表达思维,从上古到现今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老子》是先秦时期“周守藏室之史”[1](《老庄申韩列传》)老聃的一部著作,他用五千言诗一般的文字,记录了其独具特色的思想。千百年来,《老子》一直吸引着人们去揣摩、去思索。既然表达思维离不开语言,老子自己也是借助语言文字将思想的火花流传下来,却又为何他在书中一再主张“不言”、“贵言”,屡次提出“不言之教”呢?这唯有通过老子自己的言说去追寻答案了。
一、从“不言之教”看《老子》的否定性思维
在《老子》81章中,有18章提到“言”,有10章提到另一个与“言”关系密切的词——“名”。略举数例: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2](第14章)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2](第34章)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2](第47章)
善言无瑕谪。[2](第27章)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2](第31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第56章)
这些引文中的“名”可解作“命名为”,而“言”可解作“叫做”、“说”,意为对概念进行界定或者讲话。然而,书中还有一些“名”与“言”,其内涵就值得推敲了。如《老子》第1章就提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里把“名”和书中至高无上的概念“道”相提并论。胡曲园在《论老“道”》中阐释说:“老子在全书开章第一段里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名与实的问题。”[3](P163)可见老子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微妙玄通的“道”要靠“名”来阐述,要通过语言和概念来把握,然而一旦通过言说把思维呈现出来时,又不是恒常的“道”、恒常的“名”了。所以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2](第1章注)可见,从《老子》开篇伊始,思维与言说之间就似乎出现了悖离。老子心中或许有一个明白而又深奥的“道”存在着,可一旦通过语言进行释放时,又无法准确地加以表述。所以通观《老子》全书,它往往不是在阐述“道是什么”,而是在告诉人们“道不是什么”。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第14章)
“道”是如此神奇,它不皦不昧,无状无物,无前无后……老子用一系列否定式的判断来描绘“道”,仅仅说明了“道不是什么”。为何他不能用一个实实在在的肯定判断告诉人们“道”是什么呢?这就与他面对言说时所感到的困惑有关了。也许任何一个对“道”的定义式的肯定性陈述,都无法准确表达出他心中玄妙的“道”。因此,他只能采取一种极为特别的言说方式,即否定式言说。
常见的思维方式是从正面思考,从正面提出论点,然后再加以论证。与老子同处春秋时期的墨子还提出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4](《非命上》)的论证“三表”原则,以肯定自己的论点。唯独老子提出“正言若反”[2](第78章),常常用否定性言词来表达观点,他的书中充满了“无为”、“不争”、“无知无欲”、“不恃”、“不有”、“弗居”、“不仁”、“不盈”、“不自生”、“无身”等大量否定词语。据笔者粗略统计,《老子》五千言中共用“不”235个,“无”99个,81章中仅有一章没有使用“不”或“无”,若再加上其它如“勿”、“弗”、“未”、“莫”、“非”等有否定含义的词语,则全书充斥着否定句式。
使用否定词语和否定句式的频率之高,表明老子用的不是最常见的肯定式思维,而是通过否定来树立自己的观点。在当时大众意识中都以“强大”、“进取”、“智慧”等行为作为人的正面特征加以肯定和宣扬时,老子运用逆向思维,看到了“柔弱”、“谦下”、“退让”等貌似消极的行为之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把它们揭示出来,并以他独特的否定式言说一以贯之,自成体系。这是他了不起的成就,不仅与春秋战国时的其他诸子显著不同,就是在中华文化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也绝无仅有。
为了阐明深不可识的“道”,老子感到了言说的困惑,常常感叹:“道常无名”[2](第32章)、“道隐无名”[2](第41章)、“绳绳兮不可名”[2](第14章)、“吾不知其名”[2](第25章)……而不得不舍弃对“道”的命名,也即是取消对“道”的肯定式、确定式言说。
这种取消阻断了人们通过追问“是什么”而踏进知识理性的殿堂,但同时又为人们洞开了思维的另一扇大门——直觉体悟之门。老子能从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体验中,直觉出许多社会人生的道理:看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2](第23章),他悟出暴力不能长久;看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第5章),他悟出无为;看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2](第8章),他悟出包容……这种思维方式与通过严密论证后得出结论的逻辑思维不同,它是一种超验的直觉把握。“悟”的过程往往不是一个使用语言将思维逐步明朗化进而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在思维的混沌状态下,在语言的模糊状态中,突现智慧的灵光而得到超验认识。在这里,语言丧失了对思维的逻辑梳理作用,似乎变得无足重轻了。正因为老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才试图淡化“言”对“思”的作用,而一再说“希言自然”[2](第23章)、“悠兮其贵言”[2](第17章)。他是怕常规的语言所造成的思维定式,遮蔽他用直觉领悟的方式所敞开的另一片思的天空吗?此时再来看老子所发出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2](第43章)的感叹,不正说明了他运用的是人们很少运用的非常规的超验的直觉思维,而这种思维并不依赖甚至排斥清晰的逻辑话语吗?“不言之教”以淡化语言的逻辑性的方式,使思维退出了经验世界而有了形而上的可能,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5](《天下》)的无言世界中,洞察到人与世界的另一些色相,另一些意义。
老子独特的否定性思维模式,不仅使《老子》一书充满了思想魅力,而且开启了思维的直觉领悟之门,深深影响了中国人重直觉轻逻辑的思维特色的形成。
二、从“不言之教”看《老子》的政治理想
仅从语言哲学层面论述“不言之教”中包含的语言和思维的深刻变革似乎是不够的。因为“不言之教”的“教”字意为“教化”、“政教”,具有鲜明的政治学意义。
虽然以老子为始祖的道家学派,在后世被视为不问世事、隐迹山林的学派,但《老子》并非与政治绝缘。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日衰,西周有序的统治逐步涣散,而各诸侯国为揽权夺地,开始了持久、激烈而复杂的争斗。当时的知识分子——先秦诸子们,就如何重整被破坏了的统治秩序或建立新的合理的统治秩序纷纷发表见解,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儒家重礼,墨家尚贤,法家重刑……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实用性。而老子也明确地提出了“无为而治”:
为无为,则无不治。[2](第3章)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2](第47章)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2](第48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第57章)
这些言论,都是劝诫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减少人为的措施,让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生活。这一主张正是针对当时统治者为权势为私欲不断地侵民扰民而提出来的,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所不同的是,孔子、墨子、韩非子等人都主张“有为而治”,老子却主张“无为而治”。
为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老子提出了许多措施,如“谦下不争”、“冲虚不盈”、“见素抱朴”、“守静归根”等等,“不言之教”亦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老子说: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2](第43章)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2](第2章)
陈鼓应先生将此中的“言”字解释为“政教号令”[6](P68),毫无疑义是把它当作政治学的内容。所以老子说“不言之教”,并非不要政府,不要教化,而是反对苛烦的政策条款,主张统治者不要发号施令干扰人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前文说过,老子运用的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以此反观人们日常持之不疑的许多肯定性判断,独具只眼地揭示出貌似合理之下隐藏的不合理,貌似公平之下包含的不公平。例如他指出: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2](第18章)
当一般人都把“仁义”、“慧智”、“孝慈”等品质作为人的正面性格加以肯定,甚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对它们大加宣扬时,老子却发现这些品质恰恰是社会混乱、人性丑陋所引出的不良后果。这种发现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惊!
既然老子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看到了“仁、义、孝、慈”等行为无助于“治”而提倡“不言之教”,那么,“不言”在政治领域又意味着什么呢?不妨先来看看与老子同处春秋时代的孔子、墨子如何看待政治中的“名”、“言”吧。
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统治秩序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颜渊第十二》)的“正名”[7](《子路第十三》)主张,即依礼来确定名分,用“名”来规范“实”,使统治者通过确立政治上的绝对发言权而取得政治特权,以解决当时统治者的权力名存实亡或名不符实的问题。然而,是否用语言规范了“君、臣、父、子”这些名词的内涵及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儒家所倡导的统治秩序就一定会实现呢?非也。因为“正名”之后,如果没有一个执行环节,“实”仍会不符于“名”。而墨子恰恰看到了“行”的重要性: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4](《公孟》)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4](《兼爱下》)
墨子认为如果要名符其实,必须在言说和行动之间确立“言行一致”原则,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信”。在孔子那里,“信”虽然也极倡导,但终究要让位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7](《子路第十三》)的伦理关系,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也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7](《子路第十三》)。
在提倡言与行应具有一致性、确定性即“信”的原则上,老子与墨子倒相当接近:
居善也,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2](第8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2](第81章)
他们都认为“信”是维持良好统治秩序的保证。“信不足焉,有不信焉”[2](第17章),百姓对政府丧失了信任,也就意味着统治出现危机。与墨子不同的是,老子并不认为“言善信”是一剂救世良方,相反,他认为统治者到了要用“言”(即政治话语)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地步,已是不合于“道”了。故老子心中理想的政治,是按照“道”的规律运作的政治。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2](第73章)
天地从来不发号施令,但“万物并作”[2](第16章),都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整个自然界依旧和谐宁静而生机蓬勃。“人道”亦如“天道”,没有统治者政教号令的干预,人民才会自然自足地生活,社会才会如自然界一样和平安宁。故此老子提出“不言之教”,在他的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取消了“言”的存在,也就是取消了统治者发号施令的政治特权,以给个体的生存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
老子认为,统治者的有为而治,不断地发号施令、横征暴敛,是对“道”的背离与破坏,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多言数穷”[2](第5章),即是说烦苛的政令,会导致统治败亡。因此,老子主张统治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第64章),使人类社会如自然一样自在自为地发展。老子强调”不言之教”,即是反对统治者运用政治号令左右社会生活,亦即反对统治者动用任何政治特权干预社会按自身规律运作。老子对生命和社会的自然状态的充分肯定,为后世追求个体意识觉醒、寻找理想社会生活的人们开辟了一片可供栖息的精神家园。
与孔子主张通过“正名”确立政治权力和墨子主张通过“言必信”确立良好的统治秩序相比,老子主张通过“不言”来消解统治者的政治话语权力,也就意味着要取消与之相应的政治特权。其愿望虽然美好,却令统治者难以接受,“无为而治”也就终究是一种政治理想。但老子批判政洽的勇气和否定政治特权的主张自有其积极意义,对中国历史也产生过积极影响,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老子“不言之教”的成功运用。
三、从“不言之教”看《老子》的文艺思想
老子的“不言之教”不仅在哲学和政治上有着独特意义,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极为重大。
前文说过,老子在言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感到了语言表达思维的困境,似乎任何“名”“言”都不能充分表达“道”的意义,所以他只能一再称说“道”的“无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第25章)
这种语言对于思维的力不从心,可说是“言不尽意”论的萌芽。
的确,语言不可能把事物的方方面面毫无遗漏地呈现出来,它在表达思维和情感时总存在局限。言不能尽意,在表达上就总会有空缺或不明,于是老子就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2](第14章)。在文学创作中,这些空缺和不明,恰恰给作品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韵。正如老子所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2](第21章)。空缺和不明并不意味着空白和一无所有,而是有“物”有”象”存在着。由于这些物象是不确定的、恍惚的,需要读者自己发挥艺术想像去领悟,因此它们也是多姿多彩的,“一千个读者就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提倡“不言之教”,便是肯定了语言的空白能给人以丰富的艺术想像和审美体验,所以他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第41章)。
在《庄子》一书里,“言不尽意”的观点得到进一步明确的阐发: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说,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5](《秋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以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5](《天道》)
庄子认为意不可言传,魏晋时期的何宴、王弼等人也主张“言不尽意”论,认为“圣人体无,无不可以训”[8](《文学》),所以才有了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的诗篇和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吟咏。作家们自觉地将“言不尽意”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使作品具有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而往往造成作品重意境而轻论证的特点。这对于要求有严密逻辑的论说文来说,也许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对充满诗意的抒情文字而言,“言不尽意”反而能给作品以多重的丰富的意义,语言的空白反而更能调动读者内心的审美体验,且使作品更为含蓄蕴藉,真正达到一种简洁而丰富,意象有限而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唐代司空图所提出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9](《含蓄》)的审美旨趣可以说是对“不言之教”的最佳诠释了,也可以说是古人在体悟了言意之间的悖离后,再次找到了言意之间新的契合点——“不言”,并由此开创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文艺学。
此外,老子“不言之教”的否定性思维,其特色是阻断了正常的逻辑思维而开启了直觉领悟之思。直觉思维对条理清晰的理性语言的疏离,淡化了语言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导致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用模糊语言,使得读者可以做出亦此亦彼的解读,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发挥和取舍,从而进一步丰富作品的意义。从后世所说的“诗无达诂”中,就可见老子这种否定性思维方式及其使用的模糊语言的特色,对丰富文学意蕴、丰富文学解读的深远而长久的影响。而且,《老子》本身就不乏模糊概念和模糊语言,这种模糊性使《老子》全书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去研读。反过来,这种丰富的解读,又充实了老学,这恐怕也是老子独特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成果吧。
老子以“不言之教”展现了其独特的否定性思维方式,给人们开启了崭新的思考领域,对中国古典哲学、政治学、文艺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一书的许多论断或许会使学者们进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但此书独特的视角却能给一代又一代人以智慧的启迪。
收稿日期:2001-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