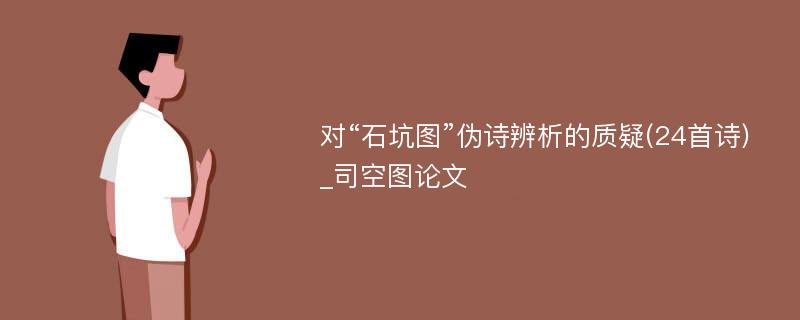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四论文,司空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考定《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诗家一指》所收明初人怀悦《二十四品》伪造,并托名司空图。由于《二十四诗品》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拥有一批声誉卓著的研究者,因而《辨伪》一出,如石破天惊,引起学术界强烈震撼。
《辨伪》检索了大量古代典籍,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使学术界不得不认真思考《二十四诗品》真伪的问题,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加入了思考的行列。也许是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本文对《辨伪》的某些论述尚存疑问,现试分论如下。
一、关于“二十四韵”
《辨伪》说:“我们对于《二十四诗品》的怀疑,最初即从‘二十四韵’一语引起”;“如果苏轼这段话确是就《二十四诗品》而言,因其时距唐尚近,此书也就确无可疑了”;“‘二十四韵’的实际所指揭开后,作伪的真相也就大白于世了。”《辨伪》选择“二十四韵”为突破口,自信抓住并成功地解决了关键问题。
为便于讨论,谨再录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有关“二十四韵”的一段话: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前人认为,“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辨伪》则否定之,其理由为“‘韵’字在唐宋人诗(当为“诗题”——笔者)中极多见,一般均指近体诗之一联”,“而谓一篇为一韵,则鲜有此例。”称一联为一韵,确实常见,而且不局限于近体诗,《辨伪》所言不误;但谓鲜有以韵指篇之例,则不实。《辨伪》第三节开头所引郑鄤《题诗品》“此二十四韵”即以韵指篇之例:而且陆机《文赋》“或托言于短韵”,李善注云,“短韵,小文也。”以韵指篇之意甚明,可见这一用法并非鲜见。至于毛晋以“二十四则”称“二十四韵”,不过是同义词转换而已,未必虑及以韵指篇的不妥。再则,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文赋》“短韵“之注亦采用李善说,以韵指篇当已成为现代人可以接受的常识。倒是以韵指诗之一联,通常则限于一篇之内的计数,而鲜有以之统计不同诗作中诗联之例,也许正因为如此,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七百八)在统计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引诗句数目时,用的量词是“联”而不是“韵”。
《辨伪》为彻底否定“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诗品》,进而论证“二十四韵”另有所指: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引自己诗作中的二十四联。作者取《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该文,将所引诗联逐一以阿拉伯数字编序,恰得24目,于是便引出“除了四处作者(指司空图——笔者)自注引上句以便对方理解诗意外,此书自举己作恰为二十四联,也即苏轼所云之‘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的结论。为了论证的严密,《辨伪》附带说明了两点:一,上引抄本由原抄者以北宋本校过;二,此本以外,尚存《与李生论诗书》引诗为二十三联、二十五联、二十六联的版本,并说这种差别“不影响前文的推断”。
如上述,要确指“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必须有苏轼所见的《与李生论诗书》中引诗数目恰为二十四联为先决条件。而《辨伪》则说:“苏轼虽未说所见为何本,但如为集本或《唐文粹》,恰为二十四韵。如所见为《英华》,则仅为二十三韵,惟北宋时《英华》秘在内府,外间不易得见。”以如此游移的日气推测,自然得不出苏轼所见恰为引诗二十四联版本的结论,又如何能确指“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
问题还远不止此。除《辨伪》所及引诗数目的差异外,尚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引诗统计的二十二联之数(见卷七百八)。而且,引诗中四处司空图自注引上句(共四联),《辨伪》说是“以便对方理解诗意”,苏轼是否也这样认为?试看: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晴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书司空图诗》)
其中“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即出于第16联“远陂春早渗,犹有水禽飞”下的注文,苏轼偏偏称“此句最善”,可见苏轼所论包括注文中的诗句,并未如《辨伪》所说可以在计数时“除了”的。那末,加上注文中的四联,就更难恰合二十四联之数了。苏轼称道的另一处“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倒是正文中的第12联,不过,《辨伪》所引“静”作“闭”,“坛高”作“幢幽”,与称轼所引显然不是同一版本,二十四联之数仍无法确定。
《辨伪》还引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中有关“二十四韵”的一段文字,说洪氏看法“与本文以上的考证,若合符契”。惜其引用不全,为便于全面理解,谨照录全文如下: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褂,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鵰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迥孤忱,犹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司空表圣诗》)
洪氏此文可分两部分,前者为引述苏轼语,“予读表圣《一鸣集》”后为自己对东坡论述的补充。引述部分包括《书黄子思诗集后》与《书司空图诗》两文,以“又云”示分界。这一分界,不应忽视,因为苏轼两处议论虽同由《与李生论诗书》而发,却分别有所侧重:一是说“其论诗”,即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一是说司空图“自论其诗”。《书司空图诗》专评司空图诗,故以其所定论诗标准“得味于味外”衡量,摘其佳句而称“善”、“工”,又以杜甫诗对照,指出其诗远未达“才力富健”;《书黄子思诗集后》则着重介绍司空图诗论,以其为评论黄子思诗作的标准。作如是观,则无论洪迈如何理解,苏轼笔下的,二十四韵”是否可能是司空图诗歌理论著作的代称(或筒称),而非指其具体的诗句(联)?如将苏轼转引的“得味于味外”的文字与司空图原文加以对照,怀疑就更难以避免了:
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苏轼引文)
若醛,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司空图原文)
二者差异十分明显。古人作文,凡遇引述,大率依赖平时诵读记忆,而非手持原文逐字抄录,苏轼写《书黄子思诗集后》当亦是如此。他转引上段只凭记忆径以己意写出,而对司空图诗句却对照原文逐一点数而录,恐东坡居士无复东坡居士矣。至此则知,《辨伪》作者就“二十四韵”所作的认真计数实无必要,本文之所以沿其开辟的弯路行进一过,并不惜辞费时加评点,是为让读者随山观景,加深感受,也能作出“不必要”的明确判断。
洪迈指出苏轼二文由《与李生论诗书》而发,从这点上说,确实“若合符契”,虽然洪氏转录之中也有少量的漏增和异文,却无伤大雅;而对于《辨伪》“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之说的确立,是无可相助的,更休说“若合符契”了。
二、关于怀悦是《二十四品》的作者
找到收录《二十四品》(全文与《二十四诗品》基本相同)的《诗家一指》,确实是《辨伪》“重要的发现”,这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中富了《二十四诗品》流传的版本(不是一个,而是一系);二、进一步证明《二十四诗品》在诗歌理论领域的巨大影响(《诗家一指》对其他论诗著作只是摘录,惟有对《二十四诗品》照录全文)。不过,看来《辨伪》对于找到《诗家一指》所表现的惊喜,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而是认准其中的《二十四品》足以成为定《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的确凿证据。为使《二十四品》成为这样的证据,必须证明其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晚于司空图的另一位。《辨伪》正是这样做的。它以大量篇幅从多方面论证《二十四品》的作者即是《诗家一指》的作者(应为“编集者”——笔者)——明代人怀悦。
鉴于《诗家一指》的性质,它不可能全部是出自编集者笔下的文字。《辨伪》亦深明此理,将其分为作者(即编集者)自撰和摘录他人论诗法之精要议论两部分,《二十四品》自然必须归于自撰之列。不过,也许是《辨伪》的百密一疏,致使产生论述细节上的自相矛盾,令人对怀悦的《二十四品》作者身份产生怀疑。
《辨伪》在第五部分中,引述有关《二十四品》的三条注文,即表现了显然自相矛盾的态度:
二为《二十四品》下之原注,称此部分为“动荡性情“的“发思篇”可知各品非仅关乎风格,且欲感发情思,启迪作者。今人研究《二十四诗品》,多指出其非仅言诗歌风格,且有关于创作者之修养、主体与自然的关系等论述,于此自注可得证明。
这条不仅指明“自注”,且作了阐发。
另注中“中篇秘本”何所指,也有待研究。这条与上条同属题注中文字,自然也是“自注”却“有待研究”了。
颇疑各品名下之原注,为刊书者补入,未必为怀悦所注。
这条虽也是谈《二十四品》的注,只是与上两条地位不同,不在题目下而在品名下,《辨伪》已有意将其从自撰部分剔除。
从这三条引述,可以看出《辨伪》力图行文严密。试看:
“动荡性情”、“发思篇”一条,于证怀悦撰《二十四品》无碍而有益,故指明“自注”而阐发之。
“中篇秘本”一条,于怀悦撰《二十四品》之论证有所不利,故不提“自注(《辨伪》明知是自注)”,取委蛇而“待研究”之。
“颇疑”一条,被剔除出自撰部分之外,《辨伪》述其原因为:“颇无伦序,又与原注(指题下注:其实品名下注亦是“原注”——笔者)所云不合,且《一指》惟言诗法,不涉具体作者、作品之批评。”其实问题并不在此,且看《辨伪》多次引用过的许学夷《诗源辨体》的一段文字:
《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炼、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
这里的的“卑浅”当不会指《二十四品》本身,因为正如《辨伪》所指出的,《二十四品》是《诗家一指》中”最具艺术见解的”部分。许氏“以典雅归揭曼硕”云云,是说把某品归在某作家名下。显然是针对写出作家之名的注文而发,其”卑浅”之评是针对注文的。许氏指出有关注文的失当到了“卑浅”的程度,根据的是什么标准?且看下表
未评"卑浅" 评为"卑浅"
《选》诗 孟浩然 杜少陵 孟郊 赵松雪 (赵虞) 范德机 揭曼硕
1 2 4 1 1
1 2 1
表中将注中所及作家、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赵虞”为赵孟钴(号松雪)、虞集的合称,故归于“赵松雪”旁,加括号以示特例(若“赵虞”分开,“虞”当排在“揭曼硕”后);阿拉伯数字对应注文涉及的品数。许氏的“卑浅”只加于“赵松雪”以下诸人,而绝不涉及“孟郊”以上作品、作家,表明其评论是根据某一时间标准而发。即:《二十四品》只能对出现于基一时间之前的作品、作家进行评论,而绝无对出现于某一时间之后的作家进行评论的可能。“卑浅”之评正是对注文所犯类似关公战秦琼的低级错误的鄙视与嘲讽;而“不足言”三字,是否表明不仅许氏而且当时的一般读者都清楚,《二十四品》产生于孟郊之后、赵孟钴之前这一时间段呢?写出那样被许学夷无情嘲弄且又令《辨伪》为难的蹩脚注文的怀悦,同时又写出“最具艺术见解的”《二十四品》以供自我糟蹋,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如果《二十四品》确为怀悦所创作,那末,它应是源,而不是流。然而从《辨伪》所作《历代诗话》本与《诗家一指》本的对校中,却发现了如下的异文:
《缜密》“水流花开”,《诗家一指》作“水流花门”。
虽属形近而误,然不辞之甚:
《旷达》“日往烟萝”,《诗家一指》作“日住烟梦”。
不仅形近而误,而且失韵。
创作原本不可能出现以上的失误,因此《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不会是源,而只是流,并且是较源头产生了讹变的拙劣的流。《历代诗话》中的《二十四诗品》是比它更晚出现的流,却显而易见地较接近于原本。
三、关于胡震亨未知有《二十四诗品》
《辨伪》认为:“万历前此书尚未传世,或此前尚无人知司空图撰有此书。”它列举了明代一批饱学之士为证据,其中包括明末学者胡震亨。《辨伪》分别在第二、第六节中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后作出论析:
胡氏罄毕生精力,搜罗唐诗及有关资料,故其所见唐人诗格一类著作,远富于稍前之胡应麟。对一些仅见书目和史传之书名,尚搜罗无遗,而后人推崇备至的《二十四诗品》却绝不叙及,实在于情理上说不过去。
可知胡氏曾通检《一指》全书,包括《二十四品》。但胡氏《唐音癸签》中多次引及司空图论诗语,又曾备载唐人诗学著作之总目,但均不云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之著,其所辑《唐音癸(当为“统”——笔者)签》中的司空图诗集也不收《二十四诗品》,是胡氏不以为《一指·二十四品》为图撰。
两处论析后邢加了胡氏生前《二十四诗品》虽已出世,可能因流布未广而未得见的说明。
胡氏真的未见《二十四诗品》吗?恐怕未必。我们至少可以举出胡氏可能知其问世并得睹该书的两处书证,都与汲古阁主人毛晋相关。
一是《津逮秘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二”《津逮秘书》提要云:
卷首有胡震亨序。震享初刻所藏古笈为《秘册汇函》,未成而毁于火,因以残版归晋,晋增为此编。凡版心书名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亨之旧;书名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者,皆晋所增也。
证之以毛晋祟祯庚午(三年,1630)七夕后一日《津逮秘书序》,可知提要所言不虚:
迩盐官胡孝辕氏复以秘册二十余函相属,惜半烬于玉林辛酉之火,予为之补亡,并合予旧刻,不啻百有余种,皆玉珧紫教,非寻常菽粟也。
而检崇祯本《津逮秘书》,版式亦如提要所言,胡藏毛刻区别分明。如八集中《诗品二十四则》为毛刻,书名即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同集中宋祁《益部方物略记》一卷,书名在鱼尾下,卷首有“明胡震亨毛晋同订”字双行,卷末有胡震亨题识。由此可知,《津逮秘书》乃毛晋与胡震亨合作出版的丛书,排除胡氏见及收入其中的《诗品二十四则》(尤其是同集中收有胡氏藏版的品种)的可能性,恐怕情理上说不过去。惟提要中所言“卷首有胡震亨序”,崇祯本题为“小引”。
二是《隐湖题跋》。卷首有胡震亨《毛子晋诸刻题跋引》,照录如下:
子晋既刻其所藏书若干种,各为之题辞行世矣。友人爱其书,尤爱其题辞,劝子晋盍单行之,于是又有题辞之刻。书之有题辞也,(feng)刘向较上叙录,以数言言作者著书大意,惟筒质精确为得体。后世若晁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稍近之;若曾子固诸书录,汪洋辨博如序论然,既失之;其他苏、黄书传跋,寥寥韵致,言取自适,未必尽中于其书,尤去叙录远矣。今子晋语虽多隽,不为苏、黄之佻;辨虽多详,不为曾氏之冗。大抵原本晁、陈两家,以持论为主,而微傅之沮绩,以合于都水氏序录之遗,则信之传者,宜同调之多爱也。世人嗜高文大篇,往往不如其嗜短行小藻,击节吟咀不能已,虽俗好之偏有然,乃吾谓子晋自雅足当之。友弟海盐胡震亨识。(《虞山丛刻》)
《隐湖题跋》二卷一百五十二篇,为毛晋自利,《表圣诗品》即列其中,胡震亨作引当能见之。
据上引二书有关资料,胡震亨在世时应已知《二十四诗品》其书,并曾得睹;而《隐湖题跋》卷首尚有陈继儒、李毅、孙房、王象晋、摩诃衍人正止、夏树芳等人六篇叙、引、题词,则当时知其书者已有包括释徒在内的相当范围,而此范围内的人物在当时的学术界亦具相当的影响。
四、关于《四库全书》本《二十四诗品》
在《辨伪》列举的《二十四诗品》版本中(当包括抄本——笔者)有“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本)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一”于“本事诗一卷”、“六一诗话一卷”之间有“诗品一卷《内府藏本》”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曾引录其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新一版)在“诗品一卷”条下亦有“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的著录。
但是,在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后发现,集部诗文评类中《本事诗》与《六一诗话》直接相连,其间并无《诗品》一卷。现存《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溯阁本诗文评类中亦不见《诗品》一卷,惟文澜阁本诗文评类有丁氏兄弟补抄本《诗品》一卷,然并非原帙。
这一意外情节,笔者已另撰《司空图诗品在四库全书中的失收与重复》试加论述,此处不赘。
五、关于《艺圃搜奇》本《二十四诗品》
《辨伪》以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刊行于崇祯年间)为《二十四诗品》现存最早之收录。陈先行《〈说郛 〉再考证》〔2〕指出,明末盛行以剜板重印手法辑丛书之风,所举丛书品种即包括《续百川学海》,而其中所收《二十四诗品》首题“唐司空图撰,汪嘉嗣阅”,正说明是利用前人刊行过的旧版印制而成,则《二十四诗品》刻版时间当早于《续百川学海》的刊行,只是一时尚无法确指其刊用的版源,只能留待日后进一步查考。
还有一部收录《二十四诗品》的丛书,《辨伪》未予列举,即:《艺圃搜奇》。
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嗵亭知见传本书目》,在“诗品一卷”(即《二十四诗品》)条下分别作如下著录:
津逮秘书本 龙威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 续百用学海水 夷门广牍本 艺圃搜奇本历代诗话本(《标注》) 续百川本 艺圃本 夷门本 历代诗话本 津逮本 学津本 (《书目》)
二者均著录了《夷门广牍》本和《艺圃搜奇》本。其中周履靖《夷门广牍》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荆山书林所刊,明显早于《续百川学海》,但目前所存之本,未见收有《二十四诗晶》。按其“艺苑”一门,收有钟嵘《诗品》,继则《文录》(题宋唐庚撰),其间未见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艺圃搜奇》情况则颇为特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一一”云
旧本题徐一夔撰,……是书前有至正戊申自序,称:“钱塘陈子彦高避兵携李,惠子之五车,茂先之三十乘,携以俱来。适余亦栖止是邦,尝得借观,兹编皆古今名人杂著之小者,从无刊版。彦高检有副本,悉以赠余。装成若干册,名之曰《艺圃搜奇》。”云云。彦高,陈世隆字也、故是书或亦题世隆所编,凡一百三种。其中舛谬颠倒,不可缕举,其最甚者,如:褚少孙补《史记》,自前代即附刊《文记》 中,并非秘笈,而取为压卷,名曰《史记外编》,又佚其《平津侯列传》、《建元以来侯年表》二篇:挚虞《文章流别论》乃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文,犹有所本也;至《谷神子》即《博异记》,《醴泉笔录》即江休复《嘉钓杂志》,苏轼《格物粗谈》即伪本《物类相感志》,俞琬《月下偶谈》即《席上腐谈),杨万里《诚斋挥麈录》即王明清《挥麈录》,晁说之《墨经》即晁子一《墨经》,大抵改易书名人名以售其欺:至镏绩虽元明间人。而《霏雪录》成于洪武中,此编既辑于至正戊申,犹顺帝之末年,何以预载其书?且所录《灌畦暇语》,与李东阳重编残阙之本一字不易,岂元人所及见邪?其为近时所赝托,不同可知矣。原本有录无书者凡十三种。国朝曹寅为补录之,厘为二卷,盖寅亦为奸黠书贺所给也。
不仅指其“舛谬颠倒”,且斥其为“赝托”。钱大昕《艺圃搜奇跋》则云:
右《艺圃搜奇》二十册。元末钱墉陈世隆彦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槁李,相善。彦高箧中携秘书数十种,检有副本,悉以赠大章,大章汇而编之。此书世无刊本,黄虞稷《志》、《明史·艺文》亦未著录,故知之者鲜。曹子清巡盐扬州时尝抄以进御,好事者始得购其副录之。岁己丑,予如京师,道出吴门,从朱文游假得,舟中无事,取读之。其中如《文昌杂录》、《韵语阳秋》、《默记),皆非足本;《谈薮》所纪多宋南渡事,而误以为庞元英著。元英撰《文昌杂录》,见《宋史·志》,而此编转阙其名、皆不免千虑之失。书成于至正末,而所收镏绩《霏雪录》。多言洪武间事,盖大章仕明之后别有增人矣。(《潜研堂文集》卷三十)
也批评《艺圃搜奇》取材编纂的失当,程度却较提要大为减轻,只说“不免千虑之失”;同样指出所收镏绩《霏雪录》已入洪武年间,却并不就此指斥其伪、而采取“盖大章仕明之后别有增入”的宽容态度。跋中提及的朱文游,即著名藏书家朱奂,顾广圻《题清河书画舫后》云:
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极盛,至席玉照(名栳)而殿,一时嗜手抄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书散出,予见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书贾钱听默,皆甚重常熟派,能视装订签题根脚上字,便晓是某家某人之物矣。(《思适斋集》卷十五)
潘祖荫《稽瑞楼书目序》亦云:
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玉照殿之;一专收精抄,亦始于毛氏、钱氏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乾嘉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白堤书贾钱听默,能视装潢线订,即知某氏藏本。
可朱免具有很强的鉴别版本能力,他借给钱大听《艺圃搜奇》时,当未言其伪,否则钱氏不会不加引述。钱氏观书于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较《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为早,然提要易见而钱跋流传不及其广,故一般受提要指伪的影响,将《艺圃搜奇》成书时间定得很晚,不仅在明末的《津逮秘书》、《续百川学海》、《说郛》一百二十卷本之后,甚至清初编成的《学海类编》亦列于其前。这一成书时间的推断是否合乎实情,请看以下《艺圃搜奇》流传的逆向探寻。
曹寅是拥有《艺圃搜奇》的,除了前引记载之外,尚有其所编刊《栋亭藏书十二种》(康熙四十五年扬州诗局刻本)收有《艺圃搜奇》本《墨经》一证,该书题下署“宋晁说之以道著”,与提要所载正同。曹寅曾以朱彝尊处钞有大量古书,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
栋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坨 ,曝书亭之书。栋亭皆抄有副本。
而朱彝尊又从曾获得曹溶大量藏书,何琪《法书考跋)云:先生(指曹溶——笔者)殁后,将旧抄宋元版书五百册质于高江村,竹槂先生倍其质而有之。
是朱氏不惜重金在竞争中战胜高士奇而购得曹溶的藏书。曹溶为浙江秀水人,称“欎李曹氏”,与徐一夔至正戊申序文“避兵檇李”语中地望正合(朱彝尊亦秀水人),有可能获得成于其地的《艺圃搜奇》。这一推测尚有如下的证据。《学海类编》是曹溶编辑(门人陶越增订)的丛书,其中收有提要所载《艺圃搜奇》改易书名人名的品种:
醴泉笔录(余集四)
苏轼格物粗谈(余集四)
俞琬月下偶谈(余集五)
杨万里诚斋挥鏖录(余集五)
至此,可知(艺圃搜奇)成书当早于《学海类编》。而从曹溶利用《艺圃搜奇》中的若干品种作《学海类编》部分底本,可知《艺圃搜奇》自成书至曹溶时一直在欎李流传。如果同意前引钱大昕跋文对《艺圃搜奇》收入至正戊申后著作的宽容态度,即认为《霏雪录》为徐一夔仕明后补入,则其成书可提前至明初,那末,同是秀水人的怀悦从中取《二
十四诗品》编入《诗家一指》,并非没有可能。至于李东阳辑录本《灌畦暇语》的收入,进而宽容,可认为是后人补抄增入(或调换原来更残阙之本):不宽容,则认为《艺圃搜奇》至少是李东阳之后的“赝托”,与怀悦无涉了。
《艺圃搜奇》后来流传到与钱大听(1728—1804)同时的朱奂手中,又为更晚的邵懿辰(1810—1861)、莫友芝(1811—1871)所及见,至傅增湘(1872—1950)时则恐已不见其书(《藏园群书经眼录》未见著录)。有清一代,宫廷所及不止一部,至少有过曹寅进献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汪如藻家藏本;私家有曹溶《学海类编》依据本,朱奂藏本,邵懿辰、莫友芝所见本:公私均有见藏,南北均有流传,可知抄本有一定数量。但目前已罕有提及此书者。进一步考明《艺圃搜奇》的成书与流传,最好是发现其尚存的传本,对于讨论《二十四诗品》的真伪,当不失为一条有益的线索。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辨伪》确有多处可圈可点,但仍存在论据欠确凿、论证欠严密之处,有些甚至存在于它自己所选定的关键部位。在失去了“二十四韵”即《与李生论诗书)所引二十四(?)联、怀悦即《二十四品》的作者这两个根据之后,《辨伪》所作《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伪造的结论一时恐还难以确立。
既然还未能作出最终结论,因而一切从事《二十四诗品》研究(把它看做司空图之作而研究)的学者,似乎大可不必因《辨伪》出现即改弦更辙,尽可继续进行研究,不受影响:自然也不妨从《辨伪)的启示中引入新的活力。这也是本文的真诚愿望。
注释:
〔1〕《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以下简称《辨伪》。
〔2〕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辨伪》论《说郛》—百二十卷 本时曾引及。
标签:司空图论文; 二十四诗品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书黄子思诗集后论文; 文化论文; 津逮秘书论文; 霏雪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