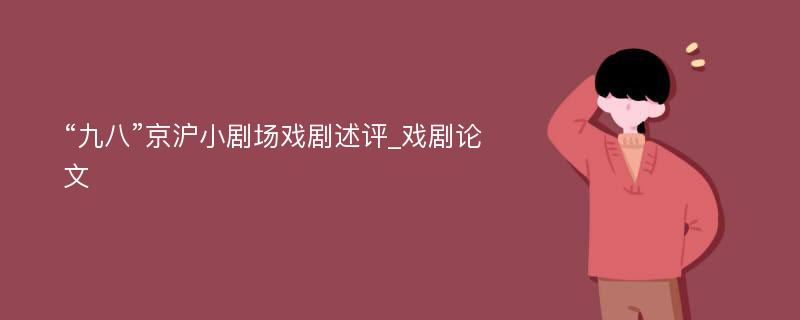
’98北京上海小剧场戏剧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上海论文,北京论文,戏剧论文,小剧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的盛夏金秋,京沪两地戏剧界有四次小剧场演出盛会: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94编导班于六月举办的《在回归线上——戏剧与梦想1998》小剧场话剧规模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八月至十月举办的《’98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小剧场剧目展演》;中央戏剧学院于十月举办的《’98国际戏剧邀请展》;上海戏剧学院于十月举办的《’98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暨学术讨论会》(以下简称’98“四展”),共演出了28台戏(其中有两台是重复的)。我有幸观看到了全部演出,并参加了部分座谈,对我的戏剧观念、艺术视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和扩展,有顿悟、有思索、有困惑。对这些戏的评价、喜厌和围绕这些演出的思考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述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这四次盛会,其目的大致相同,都是为了促进戏剧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细致方面仍有差异: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院长在邀请展开幕式上致词说:“多年来……迫切希望有机会能与东、西方艺术家交流切磋,互通信息。……举行一次小型的纯为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的活动。”上海戏剧学院荣广润院长作为组委会中方主席提出“共创戏剧文化新局面”,写道:“此届国际小剧场戏剧节,其主旨在于从戏剧艺术这个层面为上海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小剧场戏剧也是结合教学的品种之一和促进教学的组成部分。”而中戏编导班的莘莘学子们则为剧场观众的大量流失堪为担忧,毕业生们不禁困惑:那曾经令我们魂牵梦绕的‘戏剧’究竟怎么了?它到底是什么?……他们怀着激情与梦想,用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共同体验一次对戏剧本质的回归历程”,他们希冀着“这种回归也许正意味着对戏剧本质的创造与发展”。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林克欢院长如是说,“世界在变,人也在变,戏剧焉能不变。问题是如何变,往什么方向变。……舞台无限深广。它能容纳下整个已知的世界与未知的世界,表现人的一切方面。狭窄的是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情感。”因此青艺组织了这次展演,“目的在于向广大观众、也向戏剧工作者介绍另一种思路、另一种语汇、另一种呈现……”。
正因为目的之间的细微差别,四家单位组织、邀请的剧目亦不相同。
中戏94编导班在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毕业作业中精选细排,推出四台戏:《为了狗和爱情》、《血色玄黄》、《昔日重现》、《八世夫妻》。年轻人对身边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更为敏锐、关注,他们对文艺应反映生活、干预生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易热血沸腾,充满“激情与梦想”。因此,四台戏里有三出是现实题材剧,它们确实不是他们所困惑和弃绝的那种“晦涩或是直白的教条”,也不是“那些炫耀得让人看不懂的形式”。94班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这次演出是他们面向社会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所以四出戏同是“对戏剧本质的回归”,却尝试了丰富的不同的体裁:现代悲喜剧、现代生活剧、荒诞轻喜剧和历史传奇剧。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除了剧院自己的《绿房子》、《花房姑娘》和北京彼岸工作室的《窒息》外,还邀请了香港疯祭舞台的《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创世纪》、台北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的《2000》、东京榴华殿的《FALSE(虚假)》, 这四台演出确实是对我们原有观念的一次令人瞠目的挑战:这是话剧吗?《元州街~》、《2000》、《FALSE》三台戏,整个演出一句台词都没有! 这是戏剧吗?《创世纪》不明明是一场现代舞蹈吗?《2000》通场都是迟滞的舞蹈动作和形体造型。林院长说:“作为不同时代的人类自我诘问的戏剧,永远是一种立一言破一言、立一义破一义、不断自我摧毁的艺术。它的永恒魅力,它活生生的生命,正寓于不断建构、不断解构、没有终止的过程之中。”世界戏剧处于这个“没有终止的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呢?中国戏剧呢?
中央戏剧学院的邀请展共有八项活动,其中有五台演出:日本新宿梁山泊剧团的《人鱼传说》、英国基尔德霍尔音乐戏剧学院和温布尔顿设计学院的《第十二夜》、英国大卫·格拉斯剧团的《失去的孩子》三部曲第一部《汉森和格瑞泰机器》及学院研究所的《在路上》、表演系的《仲夏夜之梦》。除了《在路上》属小剧场,其他都是大剧场演出,不过“中戏”本来就没说是小剧场展演。只是《第十二夜》的演出形式明显地属小剧场,但也搬进了大剧场,舞台上除了演员外,还安排了二十几个观众,这很象是在大剧场里套了个小剧场演出。我揣测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英国的学院今天是怎样诠释和演出莎士比亚的,利于更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人鱼传说》扩展了舞台的物理空间,《在路上》运用了新的舞台光、影技术,《仲夏夜之梦》探索了对经典作品的当代化演出。《汉森~》竟然能展现婴儿在母体宫腔内的蠕动!……这些都是“纯为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主旨的极好议题。
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节阵容最庞大:新加坡“破难舰队”的《欲望天使》、加拿大卡泊·提姆剧团和德国切米尼兹剧院的《崩溃》、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当鲨鱼咬人时》、挪威巴克·特鲁本剧团的《真棒》和《Superper》、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办公室秘闻》和《拥挤/母语》、深圳大学艺术学院的《故事新编铸剑篇》、上海沪剧院的《影子》、“上戏”的《谁杀了国王》、还有(与北京相重的)日本的《FALER (虚假)》及北京的《在路上,佛主保佑我》。有七国参加,国内又有三城市参与,共十二台戏,各具特色、各显风姿。上海是遐迩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对外来的、新鲜的最敏感,接受起来也最迅捷,“上戏”的戏剧节体现了这个城市的效率性和包容性,应和了荣广润院长的“共创戏剧文化新局面”,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十二台戏虽千姿百态,但绝对是清一色的小剧场戏剧,诚如荣院长所说“小剧场戏剧,除了实验性,还以规模小、成本低为特征。”他还特别指出:“‘小’,并不意味艺术水准低下,它的实验性既在于艺术价值上的探索,又在于市场生存方式的实践。”不论这十二台戏的“探索”和“实践”成功与否或成功的程度有多少,它都让我们饱受眼福,深得其益。
综合算来,’98夏秋在京沪两地舞台上共有八个国家十三个城市二十一个剧团演出了自己的作品,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讲什么叫戏剧,辞海里、课堂上,都这样回答: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就叫戏剧。为此,我们就要讲戏剧性,讲戏剧的动作、冲突、规定情境、人物,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在编剧结构上,流行了几百年的李渔的“立主脑、脱窠臼、密针钱、减头绪”,一人一事、因果相连、顺自然时序联贯发展的叙事方式,人们已经觉得它陈旧了。而线性的中心叙事形式正盛行在我国剧坛上,不论有几条情节线、不论时序如何颠倒,都得围绕着一个中心;几条情节线不论怎么交叉、不论怎么铺叙,顺叙、倒叙、插叙,都是单一视点。
今番却不同了。’98夏秋京沪两地四次戏剧展演(下简称“’98四展”)的剧目在文学结构上、舞台表现形态上,可以说是五光十色、千姿百态。
关于叙事结构,我大致归纳一下,主要的有如下几类:
*有情节、有人物、有人物关系、有冲突,叙事方法上比较传统。这类剧目的代表作品有上海的沪剧《影子》。其它也大致相似的有北京的《花房姑娘》、日本的《人鱼传说》、 美国的《当鲨鱼咬人时》; 94编导班的四出戏亦属此类;两出莎士比亚的戏《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在演出形式上有可喜的探索,在叙事结构上则未做变动,当然也属这类。
*有情节、有人物,但在情节中穿插了非情节、带有隐喻的段子,并且反复出现。这样,情节就不那么连贯了;穿插于情节和段子的人物便不那么清晰分明了,变得似是而非了;观众在理解时就可能会有多重感受、多重释义,这类的演出作品是“青艺”的《绿房子》。
*没有一个整一的故事,也没有连贯完整的情节,由几个平行发展的层面组合而成,没有我们惯用意义上的要说明一个什么主题思想,而是想表现一个理念。属这类的有上海戏剧学院的《谁杀了国王》。十六世纪莎士比亚是明确指向克劳狄斯杀了国王。而今《谁~》剧作者曹路生说,是的,有可能克劳狄斯杀了国王,也有可能是王后杀了国王、哈姆雷特杀了国王,还可能是国王自杀,演出便平行展现了五个既相关又独立的片断。它不是侦破推理剧,也不是悬念剧,而是在说明每个人都会面临“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忍受还是抗争;死后是依然存在还是不复存在……译意有多种)的两难处境。另外有香港当代舞蹈团的《创世纪》,它把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和印地安的古老传说中的关于创世纪的故事平行地表现出来。
*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打破了中心叙事形式,由一些零碎的片段拼贴组合起来;虽有人物,但人物的面貌不甚清晰,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模糊的,甚至是未知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松散、薄弱的;人物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只是似是亦非的差异;这类戏展现的是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理心态;它并不想明确地阐释些什么,而是想用自己的感受来引起观者的沉思。北京“中戏”的《在路上》描述了出租汽车司机的一种生存状态——不知驶向何方、无目的地忙碌、对人生无意义的消耗,不安定感、不确定感。加拿大卡泊剧团英语版本的、德国切米尼兹剧团德语版本的《崩溃》描述了人类的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心理状态——病态的人在周遭的嘲讽和愚钝中,处于边缘的尴尬境地,难以与周边交流,受着痛苦的煎熬。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谁不曾有过病态呢?谁不曾没有不安全感?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语言,没有冲突、没有事件,当然也没有人物关系,甚至取消了角色的性别差别,只传达了一种情绪、一种氛围、一种可以见仁见智的意念。这类戏最突出的例子是香港的《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和台北的《2000》(下面专述)。
*完全游戏型的,演员在台上非常自由,音乐、舞蹈、自由的形体律动、戏耍、朗诵、歌唱,大家同时表演,观众可以自由选择观赏视点。挪威演出的《真棒》和《Super-per》就是这种。 《真棒》告诉了我们在挪威的某个村镇,那里居民的祖辈来自中国,他们世世代代怎样在那里生活、繁衍、发展,那里的人们和这里的人们共享着一个太阳。非常热情、强烈地表达了挪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第二个戏也配有翻译解说,但是音乐、戏耍的声音太大,什么也听不到,也就只能看演员们在台上怎么高兴了。
*以往的剧本都是单一视点,从一双眼睛去看生活。《崩溃》却不是了,它的节目单上这样写:“剧中的特色是对于同一剧情截然不同的映射,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前半部是通过女人的眼睛,后半部是通过护士的眼睛。”对同一件事、同一种遭遇,不同的眼睛去看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结论。这种非单一视点的剧作结构,是真正摒弃了戏剧的耳提面命,犹如我们生活中常说的:你换个角度去看看、去想想呢!
说到’98四展上的舞台表现形态,我有一种“万紫千红,无边光景”的感受。
首先,它彻底打碎了话剧的“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卷首“戏剧”中,开章明义“‘戏剧’一词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英文为“drama”,中国又称之为‘话剧’。”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都是从历史上就只搞话剧的。搞戏曲、搞舞蹈、搞歌唱,那有戏曲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戏曲剧团、歌舞剧院。然而,今天多种艺术元素综合到话剧中来了,它不再仅仅靠“话”单翼飞翔了;舞、歌、高科技的投影、摄像、现代美术都成了托起话剧可以任意翱翔的丰羽巨翼。
在文学结构比较传统的剧目中,几乎每一出都加进歌舞因素,加强了形体语汇。《八世夫妻》里用踢踏舞步和手指的弹颤表现一对年轻夫妻在愉快地打电脑,你说它是情节,是;你也可以说,它是舞蹈;观众的快感不仅来自于情节,那手足的律动和踢踏舞的节奏使观众的欢愉从心底里流淌出来。《仲夏夜之梦》表现两个青年男女一个求、一个拒,一个缠、一个推,用了一连串简练、干脆、高难的形体动作,形成一个个连续不断的优雅、典丽的造型,似舞蹈又非舞蹈,它的这种边缘性更增添了它的魅力,真是美不胜收。
日本新宿梁山泊剧团演出的《人鱼传说》更是全剧都载歌载舞,它的最主要的特色还不在此,而是对演出空间的拓展。《人鱼传说》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操场上夜色中帐篷里演出的,剧中,演到“遥远的海那边,漂来载着一家老小的帆船”,天幕突然打开,在沉沉夜色中,一艘木船(高大的车台)从天边(操场的那一端)缓缓驶(推)来,船上的人群呈金字塔造型,他们举着熊熊燃烧着的火把,欢喜若狂地呐喊着。这一处理把现实存在的空间借用到假定性的戏剧空间里来了,它出现的意外、距离的趋近、呐喊声的狂热、火光的闪耀,都给观众的视听感官和观赏心理以极强烈的刺激和兴奋。剧终时,台板突然从中线处翻开,从台板的下面喷射出无数高大、强力的水柱,它把全剧推向了高潮,观众整个沸腾起来了。这是日本新宿梁山泊剧团的创举,是它独有的特点,他们自己命名为帐篷戏剧,剧团团长金守珍说:“帐篷剧有把外面世界拿到剧场里面的力量。”
当然,话剧综合了歌舞成份并不等于纯“话”的话剧就失去魅力,更毋庸说就不能存在。纯“话”的话剧是戏剧——话剧多种存在形态的一种。’98四展中,新加坡演出的《欲望天使》就是两个异族大学生坐在舞台两侧的桌后,滔滔不绝地交谈,从考试谈到忧虑谈到未来谈到家庭谈到母亲,戏一直进行到将近五分之四时,两个人才开始有心理的交锋和形体的交手。中途确有观众退席,但我环视四周,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观众安静地全神贯注地看到剧终。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掌握语言是人们用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和影响他人的工具和活动;语言是有语调的,说得好就会有旋律、有节奏,十分悦耳,听者是种享受。《地质师》就毫无歌舞成份,是个纯“话”剧的极好个例。
日本榴华殿剧团的说明书上有如下字句:“这个戏的台本既没有台词,也没有任何舞台指示。”“如果是一种要让观众所看的单单用语言并不能充分表达清楚的戏剧的话,那么借助台词和舞台指示以外的手段,而构成的台本,应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段话已经说明他们的演出是没有台词的,但演出中形体动作非常多、非常强烈、非常快速,有些是有明确的示意性的:一个女孩吊在空中,她的下方坐着一位妇女,妇女痛苦地呻吟着、扭动着,女孩也蠕动着,最后妇女一个激烈动作,在喊叫声中女孩落地了。它表现女孩出生了。婴儿在宫腔里蠕动也是用强烈的形体动作表现的。剧团自称是“以传统的杂耍场为表演形式”,把这样的戏称作“无言实验剧”。可能因为类似于杂耍,场子要求大,所以舞台美术非常简单。
相比之下,台北《2000》的舞台显得非常豪华又非常简练:舞台的后半部铺满一张硕大的雪白的人造毛长长的地毯,舞台的前半部撒满了闪闪烁烁的白色的珍珠,台上只有三把折叠椅,椅子的骨架是不锈钢的,椅背椅面是用透明的有机玻璃做的,一个淡蓝、一个浅绿、一个鹅黄,显得那么剔透、高雅。香港《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在16米深、16米宽的舞台上演出,却只用了2.5米见方的区域,把它围起来, 灌进了水,四个演员就在这里面演。美国的《当鲨鱼咬人时》的舞台就显得比较拥挤,大道具较大较多,这也是因为这个戏有三个时空:布莱希特睡着了的现实时空、他梦境里的舞台——他的众多作品的片段都要在这里演出、他梦境里思辨的地方。 《人鱼传说》的布景就更复杂了。 ’98四展在舞台美术方面有简有繁、有精致有朴陋,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貌”。
’98四展出现了舞台演出中舞台上多焦点、即无焦点的剧目,香港《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就是四个演员同在演,没有了舞台中心,似乎是多焦点,观众不知道应该先看谁、后看谁,实际上成了无焦点。以往的演出要求是,在舞台上每一个瞬间只能有一个焦点,引导观众去依次注视舞台上所表现的内容。’98四展里的绝大多数都还是一个焦点。
’98四展中最令我困惑的,或者说我最陌生的、最打开我眼界的是香港的《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和台北的《2000》。
《元州街~》共四个角色:满身裹着白绷带的男子、女扮男装的男性军官、穿一身黑西服的男子、年轻的平民女子。在不到3 米的方框里,裹着白绷带的男子居中,始终未挪动位置,他在坚持着什么、抵御着什么。军官在施着淫威,胁迫着黑西服男子什么。着黑西服的男子先是弓着腰,把一张张的纸放在裹着白绷带的男子四周,后来他脱去了衣服,渐渐挺起身来。年轻的女子翻看着一个箱子,从箱内拿出一叠纸来,她诧异、惊鄂、愤怒,把手中的纸抛向空中。戏进行到快近剧终时,观众才发现那个不到3米的方柜丙已经灌满了水。 四个人一直闭口不言(没有台词),并同时表演。整个表演过程有跌宕起伏、鲜明的节奏变化。在方框的两侧有两个高台,一边是一个演奏民族乐器的,另一边是一个擂鼓的。
它在说什么?我拼命地使劲地去想、去理解,起先我想它大概是讲中国的历史:中间那个男子是中国的象征,军官代表一切侵略者,黑西服是软弱者的象征,而那女子是淳朴的中国人民。后来我觉得这样理解是否太图解了,我又理解是示意人的生存状态;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带着创伤(裹着白绷带),每个人都会遭遇到险恶和外部压力(军官),每个人都会有内在的软弱性(着黑西服的男子),每个人又都会有正义性、反抗性(年轻女子)。在座谈会上还有人理解成一个类似电影《红色恋人》的故事。
《2000》共三个演员,他们都紧紧地带着白帽,不露出头发,三人都身穿裙子,着黑袜。观众一直在猜,他们都是女的吗?谁是女的?谁是男的?编导有意取消了他们的性别差异。他们的形体动作缓慢、造型典雅,时而又表演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动作。它在说什么?我不再使劲想了,我把它当作一首无标题交响乐,我去感受它。这样观赏它的时候觉得很轻松、很优美。
《2000》编导魏瑛娟女士介绍自己在美国学习的戏剧发展三阶段:文本→剧场艺术→表演艺术。她的意思是说,戏要按文本排练的事已经过时了;取消文本,不论采用什么方式,要引发演员的感受,激发演员做出各样动作,编导按照自己的理念再加以取舍、梳理,形成演出;在剧场里演出,就是剧场艺术;而今天已经不拘囿于剧场了,公园、广场、地铁通道……都可以演出,因此,现在的戏剧就是表演艺术。魏女士有感于人们对2000年的期盼,大家都在议论2000年来临的时候会怎样、怎样,她说:其实从1999年12月31日到2000年1月1日,和平时任何一天到第二天有什么不同?时间就是这样平平常常、日复一日地过去的。她采用描写春、夏、秋、冬的几段音乐启发演员,编导、组织出这台演出,没有文本。剧终前,她指导演员都把头扬起,望着天,静默良久。有的观众认为这最后的场面是表示怀着无限的希望。而实际上,魏女士的想法大相径庭。她是用此传达一种淡然、无奈,在新世纪来临时,不要无谓地许诺,不要豪言壮语。
《元州街~》的编导何应丰先生是有厚厚一本文本的。据剧组介绍,排练时他就读,演员就感受,做动作,最后的演出和他读的本子已经完全不同的。何应丰先生说:“每个演员都是诚实地呈现生命。编导没有权利要求观众这么看或那么看,只要求观众分享”。不看什么?分享什么?我理解是不要求看主题,看立意,看教诲;而从肢体语言的符号中去分享生命的跃动、生命的节奏、分享情感情绪的振动;从这种分享中每个观赏者按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内涵。
说实话,看这样的戏实在太累了,不断地猜、不断地想、不断地悟。简直是一场大脑马拉松。
以往组织这样国际性的戏剧展演,都必须由政府部门出面,或者由行业总会牵头,譬如剧协。’98四展都是由一个具体单位自行组织的。甚至一个学院里的一个系里的一个班,由自己当独立制作人,自行组织了连续一个月的四台戏的演出,虽然94编导班并没有挂上国际性的,但这次这样集团型的演出,在戏剧学院也是破天荒的。
这标示着我们的市场意识在加强,大一统的观念在打破,紧紧依靠国家的体制在动摇。
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一出戏演完,必须开一个座谈会。这本是好事,大家互相谈谈,交流、沟通,有助于戏的进一步提高,也有益于与会者从中都学到些什么。久而久之,座谈会成了“审判会”,戏的主创人员是来接受“审判”的,主创人员即使没听懂或没听清别人说什么,也不宜发问,一说话就好象你不虚心听取意见。近二、三年来,这种座谈会又成了赞扬会,只听得一片剧本好、导演好、舞美好、演员好。私下里说:现在搞一个戏多不易啊,再批评多不忍心呀!因此,座谈会丢失了真正的交流、真正的沟通,失去了真诚和真实。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剧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便都会有适应自己特殊情况的戏剧探索。正如上海沪剧院在节目单上写的:“小剧场艺术在话剧领域里并不少见,然而出现在戏曲舞台上却是一件新鲜事儿。”因此,上海沪剧院能推出《影子》就是在探索的路上跨出了新的步子。同样,新加坡的“破难舰队”旨在寻求发展新加坡自己的戏剧、艺术和文化,所以两个年轻演员表演的自如、自然、轻松和最后节奏的变化是值得赞赏的。
也正因为要有适应自己特殊情况的戏剧探索,那么我们该建设什么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呢?该建设什么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剧场戏剧呢?’98四展不可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确实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在此,我想借用林克欢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98四展“提供个例,而不是提供样板突破疆界,而不圈定领地;寻求对话、寻求自由的艺术实践……在众语喧嚣中,为戏剧发展保留无限的可能性。”
标签:戏剧论文; 话剧论文; 北京演出论文; 艺术论文; 仲夏夜之梦论文; 人鱼传说论文; 在路上论文; 创世纪论文; 崩溃论文; 编导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