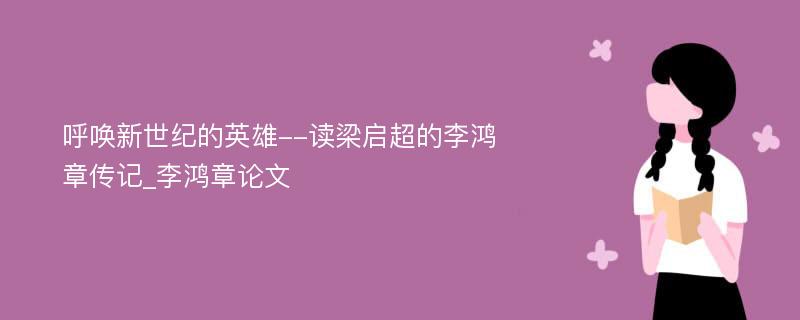
呼唤新世纪的英雄——读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英雄论文,李鸿章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1年10月7日,李鸿章死了。不过50天, 梁启超就拿出一本《李鸿章传》来。他不止写了李鸿章,而且写了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因此又名《中国四十年大事记》。90年后再来看这本书,有好些地方似乎说的是新近的事。
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他左右中国政局近4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事。他举办的洋务,如海军、招商局、电报局、金矿铁矿、广方言馆(外语学校)等等,今天看来自难免简陋之感,当时却都是中国的新鲜事,都曾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可是甲午一战,中国竟败给原来比中国还落后的日本,而且败得那么惨,海军简直全军覆没,二十多条军舰都成了日本的战利品。原来他所谓洋务,不过如他自己所说,“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其实是经不起风雨的。于是李鸿章也由誉满天下变为谤满天下,许多人甚至骂他为卖国贼。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深信自己的“以夷制夷”的方略有效,还应邀去欧洲各国走了一趟,并与帝俄签订了密约。但结果是引狼入室,招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幸而慈禧把他派到广东去当总督,因此没有卷入义和团那场风波,到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还是由他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头子出面为慈禧打圆场。屈辱的《辛丑条约》签订了,他也累得呕血而死了,赢得皇室对他的崇高评价——“文忠”两字的谥号,入祀贤良祠。这又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该怎么评价呢?就梁启超来说,当年他同老师康有为一道发动“公车上书”,主张变法,不正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吗?李鸿章只知道学西方的皮毛,对中国这间破屋东补西贴;而康梁则主张学西方的根本,对中国这间破屋重加改造,不正是从李鸿章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吗?可是,梁启超写此书时,并不急于批判李鸿章,倒是先承认李鸿章是个非常人,在中国也可谓之英雄;而且,“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凡是李的长处,他都肯定了;凡是李的委曲,他都代为表达了,然后再指出李鸿章失败的症结。那就无论是谁,都不好辩驳了。例如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起先曾反对中俄密约后来又替李鸿章辩护的, 就承认梁对于李鸿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洞若观火”。李鸿章如果地下有灵,也会心悦诚服吧。梁启超真不愧大手笔。
梁启超是怎样肯定李鸿章的长处呢?先就李的才识来说,平定捻军是个最好的证例。捻军是北方农民造反的部队,但首领却多是土豪或大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组织,飘忽不定,勇悍异常,造反18年,纵横上10省,许多王公大臣将军都败在他们手下,莫可奈何。李鸿章却看准了捻军的弱点,一年即予平定。梁启超是反对武力镇压人民的,认为平捻只是“自残同种以保一姓”,算不得什么“功”。但他对李的“谋定后动,料敌如神”,仍赞叹不置。
李鸿章的见识又如何呢?显然也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当时有许多大臣和言官,或主张停造轮船,或主张召回留学生,李鸿章都坚决顶住。他一再上书,说明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要图生存,只有“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日,非惟可忧,抑且可耻!”这话说得多么中肯,又多么沉痛啊!
再说李鸿章的遭遇。以官职论,不能再大了;以任职的时间论,难得更久了。他有什么可悲的?所以当时的论者动不动就说李是“权臣”。梁启超不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他指出:李鸿章是生在数千年君主专制的中国,又生在中国专制政体极度完备的时代,加上满清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对汉族大臣格外疑忌,所以李不可能成为权臣。他名义上是“大学士”且破例居于首席,可说是首相了吧,然而正如《清史稿》所说,“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宫,非真相。”其实,即使真的入阁办事,也不是真正的宰相,因为实权操在最接近皇帝的军机处,而军机大臣中,自同治初年到光绪末年,都没有李鸿章的份。李又兼管外交,许多重大事件都由他交涉,许多重要条约都由他签订,他算不算个外交大臣呢?不。清廷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才设外务部,这以前只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设大臣数人,往往以王公为首席,这中间又没有李鸿章,李往往受制于总署那班人。李还兼管海军、淮军、商务、交通、学校等等,但又都是加派的兼差,其本职仍只是直隶总督,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已。在总督衙门中,除了总督本人和卫队的几名军官以外,其他都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只是总督聘用的幕僚以及地位低贱的“书吏”。以这种扭曲的官制而兼办那么多中国从未有过的新事业,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李的才干;另方面也就难以照顾周全,迟早会捅出大漏子。何况满朝文武多是保守派,常常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横加梗阻,正如李鸿章所说,“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严复挽李鸿章,上联说:“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而这正是梁启超所以“悲其遇”的缘故。
那么,李鸿章的过错究竟何在?梁启超只举出四字:不学无术!这又是出人意外而又深入事理的。李鸿章可议之处甚多,并非这四个字所能概括,但那些只是枝节。例如李鸿章之豪富是有名的,梁只在书末轻轻附带一笔:“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就一个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还是看他学识何如。常人不学无术,只不过庸庸碌碌而已;政治家不学无术,就有把国家引入歧途的危险。其为害之大,又岂是用金钱所能估算的?
梁启超不是“惜”李鸿章之识吗?何以又说他不学无术呢?李鸿章力主学西方,比保守派确是高过一筹;但他对西方仅有表面的而无实质的了解,因此他的“洋务”也就只限于船坚炮利而不知学习西方的根本。梁启超批评他“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当时谈洋务者,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水平。北洋舰队的规模并不弱于日本,为什么日本胜而中国败?就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变,人的思想作风未变,所以同样的船坚炮利,却未能充分发挥效用,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
改变体制、培养人才,本不是一蹴可至的,梁启超对李并未苛责;他对洋务着重批评的只是两点,一是范围太狭,仅限于军事和商务,而不知学习西方的政治和学术;一是方法错误,不肯放手让民间去办,而要官办或“官督商办”。梁启超说:“中国人最长于商,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但一加上“官督”二字,那就“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李鸿章这种做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或者说是以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来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外交方面,由于不学无术,李鸿章更是着着皆错。仅就甲午战争而论,梁启超就指出他的12处失着。例如,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李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就承认:“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通知。”朝鲜从明代起就曾受日本侵略之苦,中国怎么无缘无故就承认日本有权出兵朝鲜?真是荒唐之至。而这一失着就种下了甲午战争的祸根。又如,李派往朝鲜的陆军前后竟有6支, 各部的将帅旗鼓相当,都由李一人遥控,岂不是犯了兵家大忌?海军提督丁日昌一再请战,李都不允,以至坐失战机,束手待毙,断送了整个北洋舰队。更令人愤恨的是李既无力自强,便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外国,企图“以夷制夷”,殊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若今日之中国,而妄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之联俄,正是如此,其结果是俄索旅大,法索广州湾,德索胶州湾,一时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主要是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他虽经常指责别人“昧于大局”,而他自己“于大局先自不明”;他经常责备别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他自己就“故习难除”。他的不学无术,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产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的危机。至于继李鸿章之后如袁世凯之流,那就连“不学无术”四个字都谈不上了。
梁启超在最后一章中,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16个人物相比较,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比。一是与日本的伊藤博文比,关于前者,梁说:“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堕其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关于后者,梁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他的结论是:“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写到这里,梁启超“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于是引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一诗作结。原来他之所以评论李鸿章,是为二十世纪之中国呼唤英雄!90年后重读此传,更不禁要为中国呼唤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批风貌全新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