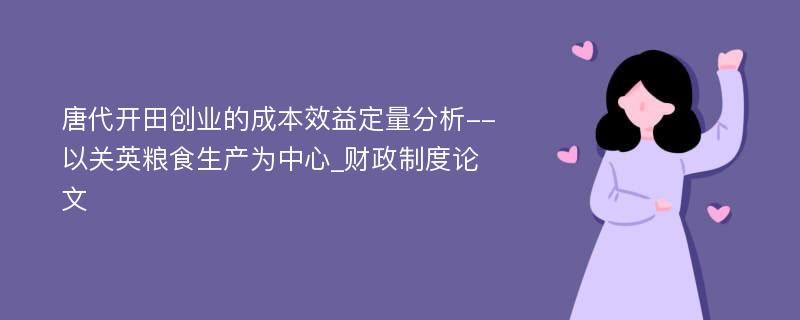
唐代屯田、营田费用与效益的量化分析——以官营粮食生产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营论文,唐代论文,粮食生产论文,效益论文,费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3-0042-07
关于唐代“屯田”、“营田”问题,无论是从土地制度,还是从财政及社会经济等角度,研究者对诸如二者在概念上的区别、屯田营田的分布、组织管理、规模、劳动者的身份变化及屯田营田的军事作用等关注较多,研究成果甚丰;(注:参见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58页。)而对屯田营田的财政、经济效益问题的探讨则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屯田营田的费用与效益的量化问题更是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暂时搁置有关“屯田”与“营田”区分的争论,只从供应政府粮食需求的角度,把它们都作为官营粮食生产组织一起论述;通过对唐代屯田营田的费用效益进行可能的计量分析,联系它们可能节省的转运费用及和籴费用,说明唐代屯田营田对政府财政及社会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册府元龟·屯田》引“宋白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屯田之利,由是兴矣。”(注:《册府元龟》卷五0三,《邦计部·屯田》。)指的是屯田具有节省长途转运费用、就近及时解决军粮需求的优点。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效果,史籍有不同记载。《旧唐书·娄师德传》记武则天下诏慰劳娄师德的屯田功绩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注:《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则言:“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说的是从边境地区军粮供需的全局来看,边境营田收获有限,尚需和籴军粮以满足需求。建中前,“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注:《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毕諴传》载,大中年间毕諴任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使,“时戍兵常苦调馕乏,諴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以省度支经费”。这些又是关于唐后期屯田、营田的效益胜于度支漕运与和籴的史实。可见,就军粮供给而言,屯田与转运、和籴三者比较,其效益孰优孰劣,不宜一概而论,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费用效益分析。
一、有关数据的说明
屯田营田的总费用包括粮食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本文主要估算屯田营田的生产成本,即由政府提供的耕牛、农具和种子等直接材料费用,直接雇工费用及以直接组织管理生产人员的雇工费用等三项。至于屯田营田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期间费用及兴修水利的费用,由于史料所限,难以估算,暂不计入。若是军屯,军士所需口粮因已计入度支的供军之费,故屯田成本中无需再计。若是募人屯田营田,政府尚需支付招募人丁的工价。
首先,关于耕牛的费用。《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厩库》“官私畜毁食官私物”条疏议曰:“假有一牛,直上绢五匹”。《册府元龟》卷五0三《邦计部·屯田》也记载:文宗太和中,殷侑为沧、齐、德等州观察使,为管内河北两州百姓“每户请牛一具,支绢绫五匹”。可证《唐律疏议》所规定的耕牛价格在唐后期还有现实意义。
当然,牛价会有地区差别。如《大谷文书》(注:本文所引《大古文书》材料均转引自王仲荦遗著《金泥玉屑丛考》卷六《唐西陲物价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201、204、205、207页。)3451号云:[细犍牛]一头,上直钱四千二百文,次四千文;次犍牛一头,上直钱三千二百文。同书3786号《唐开元年代西州用练买牛簿》又记:一头乌伯犍八岁用练九匹,一头灰犍六岁[练]七匹。
《大谷文书》3097号记:大练一匹,上直钱四百七十文,次四百六十文;生绢一匹,上直钱四百七十文,次四百六十文。伯希和敦煌文书第3348号背《唐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载:大生绢匹估四百六十五文,大练匹估四百六十文。
价值3200文的一头次犍牛可折价值460文的大练7匹;价值4200文的细犍牛与9匹价值460文的大练等值。可见敦煌吐鲁番的牛价是以质量中等、价值460文的大练为计价标准的,价格通常在大练7匹到9匹之间。
在与游牧民族邻界的边疆地区,牛价较低,每头不过三匹。《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载,贞元三年李泌对复府兵之策云:“今吐蕃久居原、会之地,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条。)本文暂取中等牛价5-7匹绢练为参数。又,牛的服役期约12年,(注:参见农业部编《农业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则每头牛年值约17-23尺绢练、合钱192-267文。
《通典》卷二《食货二·屯田》载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云:“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即每屯需牛33-42头,最多至63头。本文通取每屯50顷、150亩配牛1头为参数。
其次,关于农具价格。《宋会要辑稿·食货三·营田》记南宋乾道五年(1169),政府在楚州宝应、山阳等县安置“归正人”时所给农具包括: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耙各一副,锄、锹、镢、镰刀各一件。每牛三头用开荒錾刀一副。每一甲(五家)用踏水车一部、石辘轴二条;木勒泽一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十七,“营田”条。)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暂取其中的犁、锄、镰等部分农具作参数。关于唐代犁耙的价格,史无确载,现以《浦泖农咨》所云犁价1000文代替。
《大谷文书》3082号记:锄一孔,上直钱五十五文,次五十文,下四十五文。《大谷文书》3100号载:斧一孔重三斤,上直钱一百一十文,次一百文,下九十文。钢镰一张,上直钱五十五文,次五十文,下四十五文。本文通取中等价为参数。
农具的使用期限,据近代调查,犁约20年,锄约13年,镰约6年。(注:参见潘鸿声《解放前长江黄河两流域十二省区使用的农具》,《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假定斧的使用期也为6年,则一具耕犁的年价值约50文,锄斧镰的年价值共约29文。
再次,屯田营田的粮种费用。《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载北魏时黄河流域种谷(粟)“良地一亩用子五升”;同书卷二《大小麦第十》云:种瞿麦法以伏为时,“良地一亩用子五升”。
《册府元龟》卷五0三《邦计部·屯田》记载:
(文宗太和)七年(833)四月,以宣武军先置营田别加田卒,至是敕罢其卒,计所停粮五万七千余斛。节度使杨元卿奏请于营田顷亩之内,加税小麦三万九千余斛以代给其粮,而留其卒。诏许之。
据此,若按每人每年食米7.2斛计算,(注: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军资篇》载:“军士一年一人支绢布十二匹”;《人粮马粮篇》云:“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若支粟,“一月一石”。)39000余斛小麦可供5417人一年食用。则敕罢的宣武军田卒总数可能约是5417余人。已知,度支停给宣武军粮食57000余斛,其中39000余斛为口粮。剩余的18000余斛度支如何支配?一般情况下,政府提供军镇屯田营田者的口粮及耒耜、耕牛、种子等。本文推测,这18000余斛粮食可能是政府下拨的营田粮种,每亩约5升。按《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所记,元和中韩重华奏请“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知屯田营田者一般是人耕70余亩,而5417人共可耕田约379190亩,则18000余斛粮食正可为这379190亩土地提供每亩约5升的种子。其实情如何,由于史料所限,无法确知。本文暂取每亩5升粮种作参数。
二、量化研究例证
根据上述参数,现分别将唐代部分地区、特定时期的屯田营田的生产费用及当地军粮的转输费用、和籴费用试算如下。
例证一:武则天时期甘州屯田的生产费用与和籴费用估算。
大足元年(701),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其时“凉州粟麦斛至数千”(注:《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假定凉州所属的河西节度管兵为天宝时期的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以每人年食粮7.2石、马每匹年食粟27石计,(注:《大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尚乘奉御执掌条“春冬日给稿一围,粟一斗,盐二合。秋夏日给青刍一围,粟减半。”)则河西兵马年需粮料共约105万石。以每石数千,假定为4贯计,若军粮全部靠籴买,则需支出和籴费420万缗;若籴买一半,尚需210万缗;若籴买四分之一(26.25万石),也要费钱105万缗。由于政府所拨军费有限,只靠高价籴买实难满足军需。因此,郭元振遂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那么,第一年屯田的生产费用是多少?
《新唐书》卷一百七《陈子昂传》记垂拱二年(686)甘州四十余屯,“岁取二十万斛”,平均亩产一石。《新唐书》卷一百一十《黑齿常之传》载,高宗调露年间(679-680)于河源“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平均亩产二石。假定李汉通所开屯田全部为军屯,其总数仍为垂拱年间的40屯200000亩,以150亩配牛1头为准,共需牛1333头,每牛一头配耕犁一具。假定每头牛年值267文,耕犁年值50文,牛犁1333头具的年度总费用约为422561文。
人耕70亩,200000亩需军士约2857名;每人各配锄、斧、钢镰一把,共2857套;锄、斧、钢镰各一把的年费共约29文,则农具的年度总费用约为82853文。
种子:以每亩5升计,40屯耕地需粮种1万石。若每石4贯,共值4万贯。
上述三项费用共计约40505414文。屯田的生产成本只占和籴费105万缗的3.8%。假定丰年亩产1.5石,40屯可收粮食30万石。平均每石粮食的生产成本约135文。若亩产2石,40屯可收粮食40万石。平均每石粮食的生产成本约101文。均大大低于和籴军粮之费(数千文/石)。
《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又载:“及(李)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注:《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由于生产发展了,粮食供求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当地粮价大幅度下降,军粮的和籴价由之前的每斛数千降至数十文。(注:《册府元龟》卷五0三《邦计部·屯田》。)若以开元十六年(728)最贵处绢每匹七百文计,(注:《唐会要》卷四十,《定估赃》。)一匹绢籴数十斛意味着一、二十文钱即可籴粟麦一石。在这种价格水平下,若一年所需军粮全部和籴,只需费钱2.1万缗。若一年所需军粮全部通过屯田供给,其总费用是多少?
假定河西军年需粮食仍为105万石,若亩产量仍为2石,则需耕地525000亩,耕牛3500头,耕犁3500具。仍假定每头牛与耕犁的年价值为267+50=317文,则牛犁3500头具的年均费用约为1109500文。
仍假定人耕70亩,525000亩耕地需屯兵7500员,每人配锄、斧、钢镰各一张,年价值共29文;则7500套农具的年度总费用约217500文。
种子:以每亩5升计,525000亩耕地需粮种2.6万石;若每石20文,总费用为520缗。
以上三项总计1847缗。而和籴费用却须2.1万缗。可见,在每石20文的粮价水平下获取等量军粮,屯田因种粮价格大幅度下降,其费用仍然大大低于和籴费用。换言之,当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即使军粮的和籴价已大幅度降低,军士屯田的生产费用亦可能比同等条件下的和籴费用低廉。
例证二:天宝时期,粮食的时价与和籴价相差5文时,河西地区屯田的生产成本与和籴费用估算。
天宝八载(749),河西屯田收入二十六万八十八石。(注:《通典》卷二《食货二·屯田》记:“天宝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后上元中,于楚州古谢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若以《大唐六典》所载开天时期的河西屯田总数154屯(注:《大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云:“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安西二十屯,踈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77万亩为准,平均亩产仅约3.4斗。150亩地配牛1头,则77万亩耕地需牛5133头;若以这一时期的敦煌牛价每头3200文、年价值267文计;加上每牛一头配耕犁一具,其年价值仍为50文,则5133头牛、犁的年度总费用约为1627161文。
仍假定人耕70亩,77万亩耕地需屯兵11000员,每人配锄、斧、钢镰各一张,年值共29文;则11000套农具的年度总费用约为319000文。
假定每亩需粮种5升,77万亩地共需粮种3.9万石;以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三四八号背面《唐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记载沙州天宝三载冬交籴粟斗估廿七文、天宝四载(745)春和籴粟斗估三十二文(注:参见杨际平《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计算,每石粟的时价约是270文;则3.9万石粮种通计为粟,约值1053万文。
以上三项开支总计约1.248万贯。屯田所获的26.0088万石粮食的平均生产成本约为每石48文。而当时当地的军粮和籴价是每石320文。屯田的单位生产费用低于和籴费用272文,占和籴费的15%。
可见,天宝时期,在农业比较发达的河西地区,屯田的生产成本明显低于和籴等量军粮的费用,经济、财政效益明显超过和籴。
例证三:元和时期,韩重华在振武云州等地屯田的生产成本与军粮转运费用估算。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云: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引者按:每亩产粮5.3斗),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引者按:人耕70余亩),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
史文明载,开屯田是为了节省度支的转运费用及杜绝和籴的积弊,提高政府财政开支的效益。招募百姓屯田3800余顷的财政效益也很显著。“岁收粟20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这段史文的可信度如何?二十万石粮食的生产费用是多少?若全部转运,其费用又是多少?
假定耕牛一头值绢5匹(每匹虚估1250文,时估800文(注:《全唐文》卷六三四,李翱:《疏改税法》。)),虚估价值6250文(时估4000文);每头牛年值为虚估521文(时估333文);耕犁一具年值50文,虚估78文;3800余顷耕地需牛犁约2533头具,年度费用约1517缗(时估970缗)。
假定锄、斧、钢镰的年价值仍为29文,依元和时绢的虚时估比例作价,其虚估价约为45文;人耕70亩,3800余顷耕地约需劳动力5429个,年度农具总费用虚估约244缗。
每亩粮种5升,3800余顷耕地需粮种1.9万石;按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所言元和十五年的虚实估绢粟价格“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注:《全唐文》卷六三四,李翱:《疏改税法》。),即米价虚估约为每石781文计,则1.9万石种子的费用约为1.4839万贯。
以上三项合计约1.66万贯。
募工价:《唐会要》卷八十九《疏凿利人》记载,建中元年京兆尹严郢上奏云:内园植稻,召募京兆人营田,“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丰州开渠,“每岁人须给钱六百三十(《册府元龟》卷五0三《屯田》作“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
我们知道,建中初物价水平极高,那么,当时的实际雇价水平如何?按建中元年绢每匹4000文、米每石2000文(注:《全唐文》卷六三四,李翱:《疏改税法》。)计算,一丁岁给钱96贯、米7.2斛,共可折绢27.6匹。高出每年27匹(日绢三尺)的法定雇价0.6匹。水稻种植的劳动强度较大,(注:《大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条云:“凡营稻一顷,将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但是官方所给工值却仅比一般雇工价高出0.6匹绢,可知这种雇价水平偏低。而从关辅募人到丰州屯田,政府所给工价是每人每年63贯、米7.2斛,折绢19.35匹,低于法定雇价。因北方屯田多以种粟为主,故暂取雇工价19.35匹绢为参数。
则5429人的一年口粮39089石、工值104508匹绢,共可折虚估钱约16万贯。
即:屯田所得20万石粮食,折虚估钱约16万贯,其生产费用约需17.66万缗(每石约883文)。尽管募人屯田费用很高,有些得不偿失,但与所省度支长途馈粮费2000万缗相比,募人屯田供军的财政效益极佳。
对唐后期的军粮转运费用,贞元八年陆贽上疏云:“千里馈粮,涉履艰险,运米一斛达于边军,远或费钱五六千,近者犹过其半。”(注:《陆宣公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其后,元稹在《为河南百姓诉车状》中言道:
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等车。准敕粮料使牒共雇四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钱三十五文。约计从东都至行营所八百余里,钱二千八文(应为二十八千),共给盐利虚估匹段。绢一匹,约估四千已上,时估七百文。绸一匹,约估五千,时估八百文。约计二十八千,得绸、绢共六匹,折当实钱四千五百已来。
五百乘准敕供怀州已来载草。
右件草,准元敕令于河次收贮,待河开般运,送至行营。续准度支奏,令差河南、郑滑、河阳等道车,共一千乘般载。今据每车强弱相兼,用牛四头,每头日食草各三束,计一十二束。从武德界至行营约六百里,车行一十二日程,往来二十四日,并停住约三十余日。计每车须食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粮在外。若自赍持,每车更须四乘车别载沿路粮草。(注:《元稹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
可知车脚价为每车每里虚估钱35文,折实钱5.625文。但并未言明每辆车的载重量。那么一辆车的载重量多大?《通典》卷十《食货十·漕运》云:
开元初,……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天宝七年,运二百五十万石。每递用车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毕。
由八百辆车两个月内运粮80万石、100万石,平均每车每日需运粮约17石、21石;1800辆车三个月内运粮250万石,平均每车每日需运粮约15石;若按行二日休一日计算,运送80万石、100万石、250万石粮食,平均每车每个工作日需运粮约25石、31石、23石;可知,运粮车的装载量一般在20石之内,最多30余石。本文取每车载粮20石为参数。则元稹所云车脚价的标准是1250斤每里虚估35文,时估5.625文。低于《大唐六典》规定的标准(1000斤100里900文)。故下文计算把往返途中所消耗的人夫食粮及牛的草料也计入政府支付的费用内。
按元稹所记脚价标准,假定运粮车的装载量为每车20石,从京师运送20万石粮食至2710里外的云州,(注:《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云中郡·云州》。)需车1万辆及为运粮车牛、人夫别载沿路粮草的车18万辆,(注:已知,“约六百里,……计每车须食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粮在外。若自赍持,每车更须四乘车别载沿路粮草。”则2700余里每车需2700/600*4=18辆车别载沿路粮草。)共19万辆;行程按重车每日50里、轻车每日70里,且行2日、停住1日计,往返约需140日。(注:2700/50=54天(行路)加上27天停住,共需81天;回程:2700/70≈39加上19日停住,共需58天;往返合计139。为计算方便,取140天为参数。)则19万辆运粮车的单程脚价虚估共1795.5万贯。
以每车4牛1人,人日食2升、牛一头年食粟4.5石计,车牛人夫140天共需粮食:
(0.02×140×190000)+(4.5÷365×140×4×190000)≈1840000石;
以元和时期米价虚估每石781文计,184万石粮食可折钱144万贯。
仅19万辆运粮车脚价与车牛人夫往返所需粮食的费用之和就已达1939.5万贯。若再计入车牛所耗食草,其运费总额应超过虚估钱2000万缗。由此可知,韩重华在振武、云州等地进行屯田,节省的可能是度支的虚估转运费用。
又《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记大中末,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諴“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这段史料是否可信?若依上例估算的从西京至云州2700余里的运费2000万缗粗略估计,从西京至450里外的宁州,运费约为333万缗。可证史料所记不误,但也是虚估。若按元稹所记的运费标准细算,则此段史料所记省费之数可能被夸大了:
已知邠州“去西京二百八十里”,宁州“去西京四百五十里”。(注:《通典》卷一百七十三,《州郡三》。)假定运粮车的装载量为20石,从京师运送30万石粮食至280、450里外的州、宁州,分别需运输车1.5万辆及为运粮车牛人夫别载沿路粮草的车2.8、4.5万辆,(注:已知,“约六百里,……计每车须食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粮在外。若自赍持,每车更须四乘车别载沿路粮草。”则280、450余里每车需280/600*4=1.87,450/600*4=3辆车别载沿路粮草。),共4.3、6万辆;按重车每日50里、轻车每日70里,且行2日、停住1日的行程标准,往返分别约需15、22日。(注:280/50≈6天(行路)加上3天停住,共需9天;回程:280/70=4加上2日停住,共需6天;往返合计15。450/50=9天(行路)加上4天停住,共需13天;回程:450/70≈6加上3日停住共需9天;往返合计22。)4.3、6万辆运粮车的单程脚价分别是42.14、94.5万贯。
车牛人夫15、22天共需粮食4.5、9.15万石;(注:(0.02×15×4.3万)+(4.5÷365×15×4×4.3万)≈4.5万石,(0.02×22×6万)+(4.5÷365×22×4×6万)≈9.15万石。)若以元和时期米价虚估每石781文计,则4.5、9.15万石粮食可折钱3.5145、7.15万贯。
仅4.3、6万辆运粮车脚价与车牛人夫往返所需粮食价值两项之和就分别已达46、102万贯。若再计入车牛所耗的食草,其运输费用总额虚估应不超过200万缗。无论史载毕諴所开营田省费之数是否准确,可以确定的是,就地屯田因其生产成本明显低于转运费用,其财政效益比较显著,应无误。
三、小结
综上所述,可得初步结论如下:边地军镇的军士屯田,由于政府毋需在衣食之外再支付任何劳务费用,因此,只要屯田营田的收成估计平均亩产量若达5斗以上,其生产成本一般会低于同等条件下的和籴费用。若与千里转运之费相比,更是节省良多。在这种情况下,军士屯田无论是财政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特别显著。若是募民屯田,政府在提供耒耜、耕牛、种子之外,还须支付屯民的工钱,在亩产量不过6斗的情况下,这种屯田入不偿费。同样,军士屯田在亩产量不高时,也是入不敷出。换言之,这类屯田营田就其本身的投入产出而言,经济效益并不突出。但是,若把屯田营田的成本效益与长途馈粮或高价和籴的费用三者进行综合比较,即可发现,屯田营田的财政效益相当显著。如相对于“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沂河舟溺甚众”,(注:《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或者“逐年旋支钱收籴,悉无贮积”(注:《册府元龟》卷五0三《屯田》,文宗太和六年条。)的和籴,乃至巨额转输之费(如20万石粮食运至云州一带需支付虚估2000余万缗的运费),募人营田既能使“军中足食”,其成本费用支出的财政效益无疑应兼倍而计,更不待说对于当地农业开发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当是唐朝有时在经济成本核算有所亏损的情况下依然采取就地屯田营田以供军粮的原因。此外,卓有成效的屯田营田不仅可增加军镇收入,对改善军镇的财政状况十分有利,如大中年间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有耕市之利”(“营田之利”和“互市之利”);(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一年十月条胡注。)而且由于唐后期有些营田军镇会主动地将自己掌握的营田收获纳入中央财政支出计划,屯田营田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如宝历元年(825)冬,沧景节度使杨元卿上言请求将营田收获的廪粟二十万斛付度支充军粮;河阳节度使崔弘礼上言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石,从宝历二年减去度支所给数(注:《册府元龟》卷五百三,《邦计部·屯田》。)等等。其财政效益比较显著。
而且,唐代屯田营田一般多是在农业水平较低、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地区进行,它又是重新配置人力与土地资源,发展当地农业生产,解决政府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如,开元七年(719)姜师度任同州刺史,“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注:《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良吏下·姜师度传》。)开元八年受到玄宗褒奖,云:“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繇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畲之润。”(注:《册府元龟》卷四九七,玄宗皇帝《褒姜师度诏》。)可见由于兴修水利、开置屯田,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经济水平。同时,玄宗下诏:“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来召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工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注:《册府元龟》卷四九七,玄宗皇帝《褒姜师度诏》。)姜师度修复通灵陂以及利用该项水利兴置屯田,并把垦熟的官田授予无地贫户的作法,“不但大大增加了唐朝京城的仓储,而且对维护已遭严重破坏的均田制有所裨益,直接造福于当时当地的农民”。(注:参见陈明光《唐人姜师度水利业绩述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再如唐后期如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注:《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李承传》。)以及元和十五年的李听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时,“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李)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注:《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李晟附子听传》。)等,无疑都说明屯田确实会推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发展。
必须指出,屯田营田作为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带有较强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功利性,所以它对当地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一定的地区性与时效性。例如,军政部门撤罢屯田营田人夫,尤其是调离边疆的守军,而当地又缺乏劳动力时,屯田营田所带动的农业进展就很难保持。天宝前朔方五城的大规模屯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可见,由于战争影响、边军撤离,到建中时期已经大部荒废,成为其数至广的“旧屯”。(注: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建中元年二月条严郢奏疏。)但这并不能否定唐代屯田营田确曾取得的成效。
